2从GATT到W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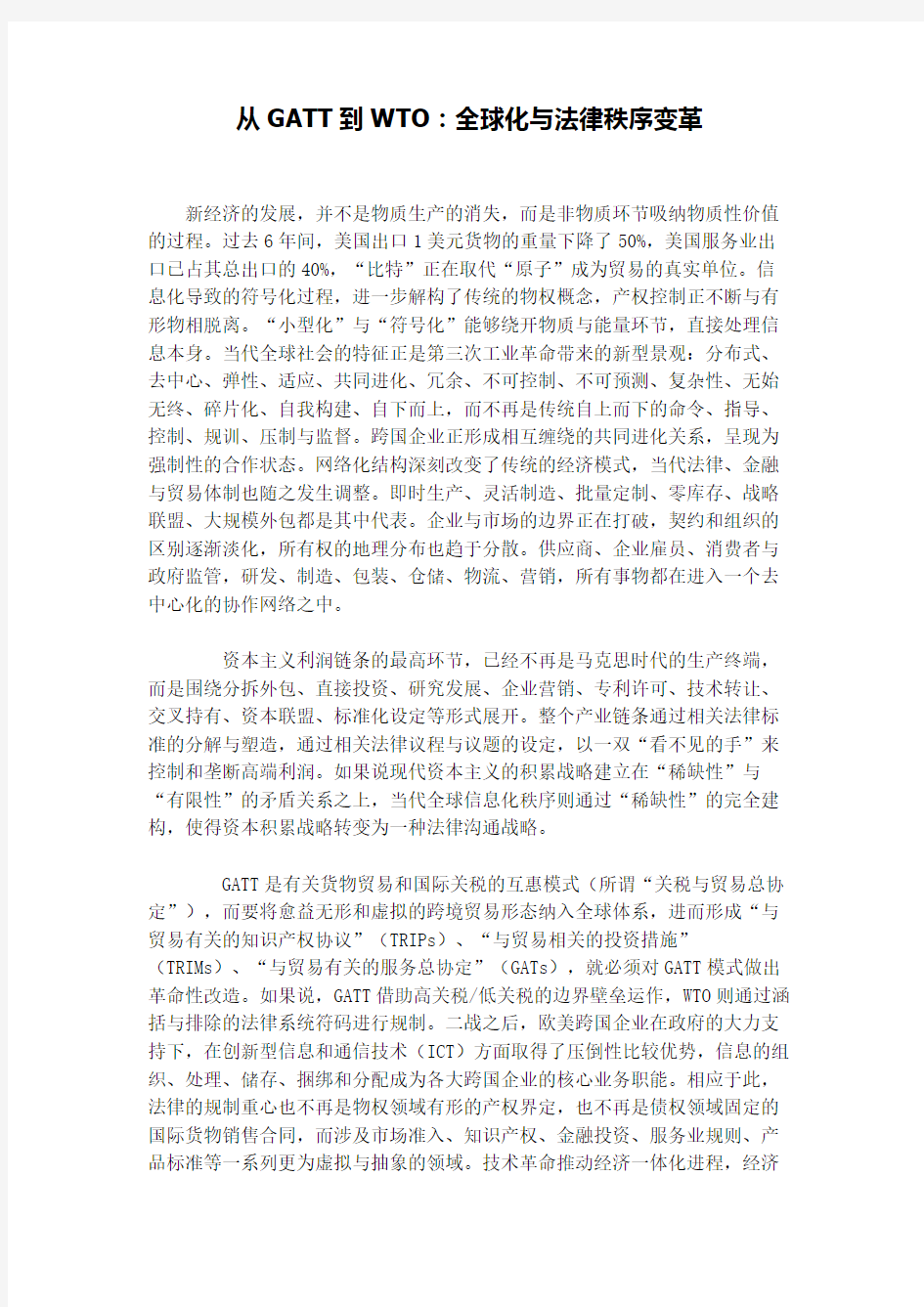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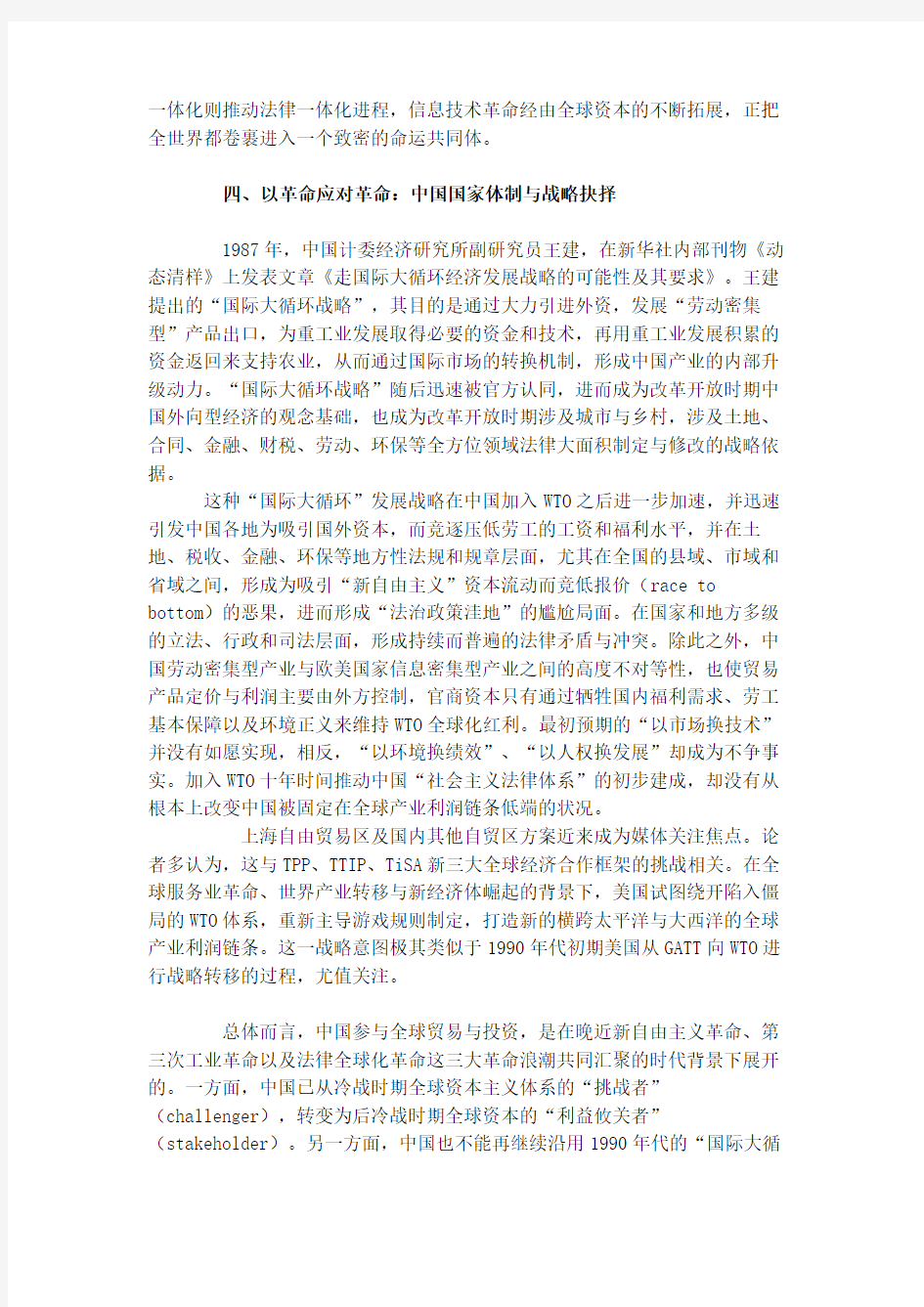
从GATT到WTO:全球化与法律秩序变革
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物质生产的消失,而是非物质环节吸纳物质性价值的过程。过去6年间,美国出口1美元货物的重量下降了50%,美国服务业出口已占其总出口的40%,“比特”正在取代“原子”成为贸易的真实单位。信息化导致的符号化过程,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的物权概念,产权控制正不断与有形物相脱离。“小型化”与“符号化”能够绕开物质与能量环节,直接处理信息本身。当代全球社会的特征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型景观:分布式、去中心、弹性、适应、共同进化、冗余、不可控制、不可预测、复杂性、无始无终、碎片化、自我构建、自下而上,而不再是传统自上而下的命令、指导、控制、规训、压制与监督。跨国企业正形成相互缠绕的共同进化关系,呈现为强制性的合作状态。网络化结构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当代法律、金融与贸易体制也随之发生调整。即时生产、灵活制造、批量定制、零库存、战略联盟、大规模外包都是其中代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打破,契约和组织的区别逐渐淡化,所有权的地理分布也趋于分散。供应商、企业雇员、消费者与政府监管,研发、制造、包装、仓储、物流、营销,所有事物都在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
资本主义利润链条的最高环节,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终端,而是围绕分拆外包、直接投资、研究发展、企业营销、专利许可、技术转让、交叉持有、资本联盟、标准化设定等形式展开。整个产业链条通过相关法律标准的分解与塑造,通过相关法律议程与议题的设定,以一双“看不见的手”来控制和垄断高端利润。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战略建立在“稀缺性”与“有限性”的矛盾关系之上,当代全球信息化秩序则通过“稀缺性”的完全建构,使得资本积累战略转变为一种法律沟通战略。
GATT是有关货物贸易和国际关税的互惠模式(所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要将愈益无形和虚拟的跨境贸易形态纳入全球体系,进而形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TRIMs)、“与贸易有关的服务总协定”(GATs),就必须对GATT模式做出革命性改造。如果说,GATT借助高关税/低关税的边界壁垒运作,WTO则通过涵括与排除的法律系统符码进行规制。二战之后,欧美跨国企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创新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方面取得了压倒性比较优势,信息的组织、处理、储存、捆绑和分配成为各大跨国企业的核心业务职能。相应于此,法律的规制重心也不再是物权领域有形的产权界定,也不再是债权领域固定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而涉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服务业规则、产品标准等一系列更为虚拟与抽象的领域。技术革命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经济
一体化则推动法律一体化进程,信息技术革命经由全球资本的不断拓展,正把全世界都卷裹进入一个致密的命运共同体。
四、以革命应对革命:中国国家体制与战略抉择
1987年,中国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重工业发展取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持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形成中国产业的内部升级动力。“国际大循环战略”随后迅速被官方认同,进而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观念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涉及城市与乡村,涉及土地、合同、金融、财税、劳动、环保等全方位领域法律大面积制定与修改的战略依据。
这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进一步加速,并迅速引发中国各地为吸引国外资本,而竞逐压低劳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并在土地、税收、金融、环保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层面,尤其在全国的县域、市域和省域之间,形成为吸引“新自由主义”资本流动而竞低报价(race to bottom)的恶果,进而形成“法治政策洼地”的尴尬局面。在国家和地方多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层面,形成持续而普遍的法律矛盾与冲突。除此之外,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欧美国家信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高度不对等性,也使贸易产品定价与利润主要由外方控制,官商资本只有通过牺牲国内福利需求、劳工基本保障以及环境正义来维持WTO全球化红利。最初预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如愿实现,相反,“以环境换绩效”、“以人权换发展”却成为不争事实。加入WTO十年时间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成,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利润链条低端的状况。
上海自由贸易区及国内其他自贸区方案近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论者多认为,这与TPP、TTIP、TiSA新三大全球经济合作框架的挑战相关。在全球服务业革命、世界产业转移与新经济体崛起的背景下,美国试图绕开陷入僵局的WTO体系,重新主导游戏规则制定,打造新的横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全球产业利润链条。这一战略意图极其类似于1990年代初期美国从GATT向WTO进行战略转移的过程,尤值关注。
总体而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是在晚近新自由主义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法律全球化革命这三大革命浪潮共同汇聚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中国已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者”(challenger),转变为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再继续沿用1990年代的“国际大循
环”战略,也难以继续“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战略。必须看到,古典放任自由的国际贸易正被追求规则与监管一致化对接的全球贸易取代。贸易议题正被层出不穷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这些“人权”标准所包围,在投资、金融、政府采购、标准与认证、竞争政策、物联网、互联网等领域,中国正真正进入所谓的“改革深水区”。这其实也是从“自由主义贸易”到“自由主义体制”的“华盛顿共识”升级版的召唤。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初期曾经希望通过“国际大循环”战略“以市场换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决策层将持续面临“以自由体制换市场空间”的艰难战略抉择。
贸易体制改革的法律政策效果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WTO进程未必会使所有人获益,在零和博弈的情形下,中下阶层往往成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上海自贸区未来所形成的政策套利空间,也有可能成为谙熟新自由主义修辞的“达沃斯人”(Davos man)的逐利工具。“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政治构想,其意图是通过某种“双赢”许诺来说服既得利益群体支持变革,而一旦“利益均沾”被证明不现实,则最终取决政治领导层能否打破僵化利益同盟的决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失败经历,更多不是人才、智力和知识储备的不足,而来自具有“双刃剑”效应的“特殊体制”。
为应对三波全球化革命浪潮的汇聚冲击,中国“特殊体制”必须做出自我革命的应对。面对新自由主义革命,中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权机制发展,平衡官商资本的一枝独大,防止精英寡头独占全球化红利而将改革成本转嫁于弱势群体,在资本自由扩张与国民福利增进、在全球化精英与底层平民之间保持平衡,通过民主监督机制抵御权贵资本的阴暗面,杜绝跨国资本与垄断资本的“逆向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需要转变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型经济发展,在全球产业转移中抓住机遇期逐渐占领高端领域,尽早实现信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的产业转向。面对法律全球化革命,中国则需全方位的法律理论创新与战略政策调整,全球竞争的核心不再是军事弹压与武力恫吓,不能再简单依靠技术化的法律移植与垄断化的立法创制,而亟需在外交议题设置和法律规则主导权层面提升“软实力”,以积极应对“全球治理”的法律挑战。
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革新,最终取决于内政体制的自我革命。美国霸权的持久活力,得益于其民主框架对精英与民众利益的吸纳和平衡,得益于其宪法革命对不同群体权利要求的阶段性实现,从而使其能够充分动员国内阶层一致对外参与世界竞争并捍卫本国利益。国际经贸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全球化加速已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在残酷却没有硝烟的全球竞争中,国家体制的力量将愈益凸显。这一切都最终取决于中国体制自我革命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