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 扫灰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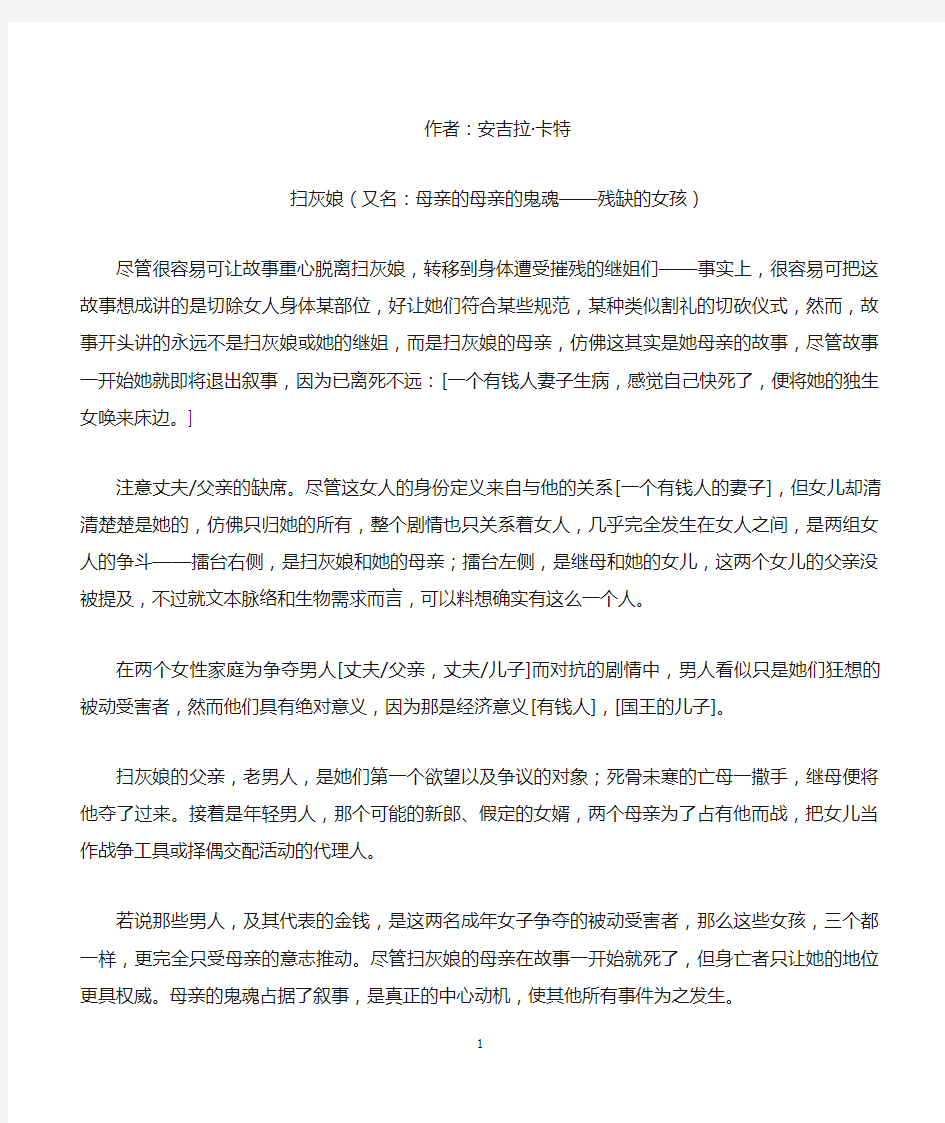

作者:安吉拉·卡特
扫灰娘(又名:母亲的母亲的鬼魂——残缺的女孩)
尽管很容易可让故事重心脱离扫灰娘,转移到身体遭受摧残的继姐们——事实上,很容易可把这故事想成讲的是切除女人身体某部位,好让她们符合某些规范,某种类似割礼的切砍仪式,然而,故事开头讲的永远不是扫灰娘或她的继姐,而是扫灰娘的母亲,仿佛这其实是她母亲的故事,尽管故事一开始她就即将退出叙事,因为已离死不远:[一个有钱人妻子生病,感觉自己快死了,便将她的独生女唤来床边。]
注意丈夫/父亲的缺席。尽管这女人的身份定义来自与他的关系[一个有钱人的妻子],但女儿却清清楚楚是她的,仿佛只归她的所有,整个剧情也只关系着女人,几乎完全发生在女人之间,是两组女人的争斗——擂台右侧,是扫灰娘和她的母亲;擂台左侧,是继母和她的女儿,这两个女儿的父亲没被提及,不过就文本脉络和生物需求而言,可以料想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在两个女性家庭为争夺男人[丈夫/父亲,丈夫/儿子]而对抗的剧情中,男人看似只是她们狂想的被动受害者,然而他们具有绝对意义,因为那是经济意义[有钱人],[国王的儿子]。
扫灰娘的父亲,老男人,是她们第一个欲望以及争议的对象;死骨未寒的亡母一撒手,继母便将他夺了过来。接着是年轻男人,那个可能的新郎、假定的女婿,两个母亲为了占有他而战,把女儿当作战争工具或择偶交配活动的代理人。
若说那些男人,及其代表的金钱,是这两名成年女子争夺的被动受害者,那么这些女孩,三个都一样,更完全只受母亲的意志推动。尽管扫灰娘的母亲在故事一开始就死了,但身亡者只让她的地位更具权威。母亲的鬼魂占据了叙事,是真正的中心动机,使其他所有事件为之发生。
临终前,母亲向女儿保证:[我永远都会照顾你,陪伴你身边。]故事将告诉你她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母亲作出承诺的此刻,扫灰娘还没有名字,只是她母亲的女儿,我们只知道这样。是继母取笑地叫她扫灰娘,抹消了她原有的名字[不管那名字是什么],将她逐出家庭,赶离众人分享的餐桌,孤独一人与炉台灰烬为伴,除去她偶然得之的高尚女儿地位,代之以偶然失之的低下仆人地位。
母亲说会永远照顾扫灰娘,但她死了,父亲再娶,给了扫灰娘一个仿母,这母亲自己有女儿,爱她们激烈一如亡母生前——且我们将看到死后亦然——爱扫灰娘那样。
第二桩婚姻带来恼人的问题:谁才是这个家的女儿?我的!继母宣布,把新命名为扫灰娘的非女儿赶去扫地、刷洗、睡炉台,她自己的女儿则在铺著干净床单的扫灰娘床上。扫灰娘不再被称为她母亲的女儿,也不是她父亲的,只剩下一个干枯、肮脏、余烬焦炭的外号,因为一切都已化为尘埃灰烬。
此时假母亲睡在真母亲死去的床上,并且,据推想,在那张床上与丈夫/父亲交欢,除非这档事她并不喜欢。故事没有告诉我们这丈夫/父亲在家庭或婚姻中发挥什么功能,但我们大可推测他跟继母同睡一张床,因为已婚夫妇都是这样。
对此,真的母亲/妻子又能奈何?就算熊熊燃烧著爱、愤怒与嫉妒,她终归已经死了埋了。
这故事的父亲在我看来是个迷。他是否太迷恋新妻子,以致于看不见自己的女儿满身厨房污垢,睡炉台睡得灰头土脸,而且整天操劳干活?就算感觉个中有隐情,他也乐于把整出戏全都交给女人去导去演,因为,尽管他总是缺席,别忘记了扫灰娘睡的灰烬可是在他的房子里,他是看不见的环节,将两组母女连结成一道激烈冲突的算式。他是不移动者,是不为人见的组织原则,就像上帝;也像上帝一样,某种黄道吉日突然冒出来,引进带动情节的最重要工具。
此外,若没有这缺席的父亲,就不会有这个故事,因为如此一来便没有冲突。
若她们能暂时抛开己见,友爱地讨论一切,一定会联合起来驱逐父亲,然后所有女人都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若她们决定留下父亲,可以叫他负责做家事。
父亲引进带动情节的重要工具是,他说:[我即将出门出差,我的三个女儿想要什么礼物?]
注意:他的三个女儿,
我想到,继母的女儿可能根本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就像扫灰娘也是他的亲生女儿,她们都是他的——所谓的——(自然)女儿,仿佛合法性本身便不太自然。这样一来,故事里的个股势力可就重新排列组合。若是如此,他默许另两个女儿占上风就比较说得通了,仓促的再婚和继母的敌意也更有理由。
但如此也会使故事变成另外的模样,因为提供了动机等等。这表示我得给这些人全提供一个过去,得让他们成为各有好恶与回忆的立体人物,还得想出他们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如此将使<扫灰娘>改头换面,把童话故事所需的
最简单线条及典型联系公式:[然后……]变成资产阶级写实主义的复杂技巧。他们得学会思考。一切都改变。
我还是固守原来知道的好。
他的三个女儿想要什么礼物?
[我要一件真丝洋装。]大女儿说。[我要一条珍珠项链。]二女儿说。遭遗忘的三女儿要什么呢,被一时善心叫出来的她,在围裙上擦干因家务操劳磨破皮的双手,带来一身旧火烬余气味?
[我要你回家路上第一根碰着你帽子的树枝。]扫灰娘说。
她为什么要这样东西?她是否其来有自地猜着自己在他眼中多没价值?或者是否梦境要她使用这道未获承认欲望的随机公式,让盲目几率为她挑选礼物?除非是她母亲的鬼魂,难以瞑目,不停寻找回家的方式,藉女孩之口代她说出要求。
他带回一根榛树枝,她将树枝种在母亲坟上,以泪水浇灌。树枝长成榛树。当扫灰娘前来母亲坟上哭泣,斑鸠呢喃:[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会永远保护你。]
于是扫灰娘知道那斑鸠是母亲的鬼魂,知道自己仍是母亲的女儿,而尽管先前她哭泣悲号、渴望母亲,但现在她的心稍稍一沉,因为发现母亲虽死犹存,此后听命于母亲了。
时候到来了,该国又要依例举办特殊舞会,国内所有处女都前来,在国王儿子面前跳舞,让他挑选想娶的对象。
斑鸠为此激动欲狂,一心要把女儿嫁给王子。你或许以为她自己的婚姻经验会教她心存警惕,但没有,该做的就是得做,一个女孩除了嫁人还能怎么办?激动欲狂的斑鸠一心要女儿嫁人,于是飞进屋里,叼起那件真丝新洋装,拉出窗外,丢给扫灰娘。接着是珍珠项链。扫灰娘用院子里的帮浦打水好好洗个澡,穿上偷来的新衣首饰,悄悄溜出后门,前往舞会场地,但继姐待在家里生闷气,因为他们没东西可穿。
斑鸠紧跟着扫灰娘,啄她的耳朵要她舞得更活跃,好让王子看见她,爱上她,跟在她身后,发现那只掉落鞋作为线索,因为,若没有仪式性地羞辱另一个女人并摧残她两个女儿的身体,这故事就不算完整。
寻找穿得下这只鞋的脚,对于施行此一羞辱仪式是不可或缺的举动。
另一个女人不顾一切想得到这年轻男人,为了抓住他可以不择手段。不是少一个女儿,而是多一个儿子:她如此渴望儿子,让女儿跛脚也在所不惜。她拿起切肉刀,砍下大女儿的大脚趾,好让她的脚能穿进那只鞋。
女人挥舞切肉刀逼近自己的孩子,孩子张皇失措只恨自己不是男儿身,而老女人想要的是比脚趾更重要的身体部位。[不要!]她大叫。[母亲!不要!不要动刀!不要!]但刀还是砍了下来,她把脚趾丢进火堆灰烬,之后扫灰娘发现了,为之惊奇,对母亲这种现象感到既敬畏又恐惧。
母亲像尸布围裹住这些女孩。
王子觉得这哭泣的年轻女子毫无面熟,她一脚穿鞋一脚没穿,被母亲胜利地展示在他的面前,但他说:[我答应过要娶任何能穿下这只鞋的人,所以我会娶你。]于是他们双双骑马离去。
斑鸠飞来绕着这对新人转,没有呢喃或低鸣,而是唱着可怕的歌:[看!看!鞋里有血!]
王子立刻把冒牌前任未婚妻送回家,对这伎俩感到生气,但继母匆匆砍掉另外一个女儿分脚跟,立刻把这只脚塞进空出来的染血鞋,就这样,信守承诺的王子扶新的女孩上马,再度离去。
斑鸠又回来唠叨了:[看!]当然,鞋里再次满是鲜血。
[让扫灰娘试试。]急切的斑鸠说。
于是现在扫灰娘得把脚放进这惨不忍睹的容器,这绽开的伤口。仍然粘稠温热,因为这故事的许许多多文本从没提过王子在几次试穿之间洗过鞋。赤脚穿上血淋淋的鞋是件苦事,但她母亲,那斑鸠,以轻柔呢喃的低鸣催促她,无法违背。
如果不能毫无反感地投入这绽开的伤口,她便嫁不了人。斑鸠就是这么唱的,而另外一个欲狂的母亲只能无力站在一旁。
扫灰娘的脚小如中国女子的缠足金莲,就像一截残株。几乎已形同截肢的她,将小脚穿进鞋里。
[看!看!]斑鸠胜利叫道,尽管在扫灰娘穿鞋站起、开始走动的同时,牠暴露出自己的鬼魂身份,变得愈来愈虚幻不实。叽吱,残株般的脚在血淋淋鞋里踩出声音。叽吱。[看!]斑鸠唱到。[她的脚正合这只鞋,就像尸体正合棺材!看我把你照顾得多好,亲爱的!]
豆瓣读书评分9分以上榜单
豆瓣读书评分9分以上榜单 1、詹姆斯.M.凯恩《邮差总按两遍铃》詹姆斯.M.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以及《双重赔偿》都是经典的黑色小说,而前者更加出色,可以算是最具文学性的类型小说之一,同时极具宗教感,饱含怜悯。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情侣,几乎带着一种天真,笨拙的杀了人。而当人犯下罪行之后,上帝便远离了他们,爱与信任皆被摧毁。结局让人难过:爱是如此无力,脆弱的人通不过考验。 2、约翰.勒卡雷《柏林谍影》约翰.勒卡雷的小说《锅匠、裁缝、士兵和间谍》以超级豪华阵容拍成电影之后,再次唤起了读者对他的阅读热情。在《柏林谍影》中,著名的史迈利还只是一个幕后人物,主角仅仅是个无名小卒,一个落魄的间谍,他所献身的东西那么虚无和不可靠,而意料之外的爱情也成了陪葬品。冷酷,无情,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柔。 3、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安吉拉.卡特是文字上的“朋克女巫”,语言和情节皆很奇诡,汪洋肆意。这本书算是最成熟最好读的安吉拉.卡特作品了,疯狂而快乐的两姐妹的家族史,开头就很棒:“大家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朵拉.欠思。欢迎来到错误的这一边。”错误,毫不在意的各种错误,疯狂又快乐。顺带提一下:这本书经常被称作女性版的《百年孤独》。 4、保罗.奥斯特《隐者》还是应该读一读保罗.奥斯特的,他就跟村上春树一样,让你知道所谓“讲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比“写作能力”更需要天赋。他写得不是那么经典文学,但他大部分的书都非常好看。有些破绽,当然,但还是很好看。这本《隐者》算是写得相当成熟的一本了。
5、劳伦斯.布洛克《八百万种死法》不能不提劳伦斯.布洛克,他塑造的酒鬼侦探马修的形象,简直像是行走在黑色纽约的一个潦倒诗人,又带着轻微的血腥气。《八百万种死法》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也最好看。同时,这也是写给纽约的别致情书。 6、杜鲁门.卡波特《冷血》杜鲁门.卡波特在《冷血》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毅力,以对细节和情绪无可指摘的斤斤计较,写出了这本恰似虚构小说的“非虚构作品”。他对凶手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入,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凶手形象,也成为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推荐一读再读。 7、丹尼斯.约翰逊《耶稣之子》《耶稣之子》里面的主角无一不是瘾君子、底层人士、罪犯……那么绝望但却毫无自怜,极其冷静。这本薄薄的小书让威廉.巴勒斯的《瘾君子》显得不够洗练不够浓缩不够带劲。 8、荒木经惟:《东京日和》奇怪的是,著名的摄影师们往往写东西也不错。森山大道、荒木经惟以及杉本博司都出过随笔集,大概文字和图像这两种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一致的部分。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东京日和》,还曾经被拍成过电影,弥漫着感伤。他写道:“妻走后,我只拍天空。” 9、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村上春树是超一流的游记作者,很少有人能把游记写得如此私人又如此有趣、娓娓道来,栩栩如生,而且还很励志。这本《远方的鼓声》我出门总会带着,随手都可以拿起来读,读了无数遍也不厌倦。
评安吉拉卡特的《与狼为伴》的女权意识
评安吉拉卡特的《与狼为伴》的女权意识 [摘要] 本文通过解读安吉拉·卡特改写的童话故事《小红帽》,从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述了作品中的女性文学的现代意义及其魅力。作者通过对传统童话的颠覆,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式,从故事的道德主题和具体细节重新展现了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形象与地位的认识,探索了最终男女平权的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塑造了现代女性的新形象。 [关键词] 安吉拉·卡特女性文学批评童话颠覆 安吉拉·卡特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她的作品文体繁杂,题材多样,她是20世纪文坛上值得研究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当代英国文坛典型突出的女权主义作家之一。她擅长把哥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童话故事、女权主义观点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把经典的故事进行颠覆和改写,达到传统形式和现代意识的完美结合。她尤其喜欢对经典的童话进行改写,正如“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童话故事所发现的是适应男性统治的社会道德观,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男性价值观的烙印。”童话中的女人总是扭曲的,被动的等待男子的拯救,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只是隶属于男子的客体。经典的童话中男女形象的刻画固定的模式表现为“男子优越,女子卑劣;男人主动,女人被动;男人咄咄逼人,女人温顺;男人是虐待狂,女人是受虐狂。”为了消解和颠覆这一格局,揭露童话的伪善性,卡特改编童话故事的内容贯穿女权主义思想,同时注入浓烈的哥特式小说的恐怖对经典童话进行改写。 卡特在改写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三个原则:修正现有权利倾向,让边缘任务中心化;否定原作中对某一个人物的传统定义而赋予人物以新的形象;强调女性的主观能动性。童话把男权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植根于女人的头脑,从而达到规范女人的行为目的。卡特反对大男子主义,男权思想,对女性问题尤为关注。《与狼为伴》中尤其突出其女性主义特色,女性主义即指针对女性自始以来的不平等地位和两性伦理问题所发起的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的萌芽,最早出现在贵族社会与中古女修道士的作品中,她们企图借由女性和圣母所象征的慈悲和爱欲精神,来强调女性也有其精神层面,而不是男性欲求下的客体。 一、《与狼为伴》的情节、主题与传统童话的颠覆 狼外婆的原型开始于何时何地,又如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版本我们不得而知。在1977年,安杰拉卡特根据夏尔佩罗的《小红斗篷》改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与狼为伴》,文体、风格迥异。佩罗的《小红斗篷》是这样写的:小红斗篷拉开没栓,进了门。随后发现姥姥在床上很古怪,她对姥姥说:“姥姥,您的手臂好大!”姥姥说:“手臂大,好抱你,亲爱的。” “姥姥你的牙好大!” “牙大好吃你!”话音刚落,那只邪恶的狼就像小红斗篷扑过去,几口就把她吃掉了。所以,佩罗在正文后的“教训”中告诫“小孩子,尤其是长得漂亮、教养也好的女士,千万别去同陌生人搭讪。”而卡特的《与狼为伴》中的小姑娘自作主张去看外婆,虽然小姑娘天真无邪,但并不像佩罗笔下的《小红斗篷》那样无知,她知道狼为何物,并且用匕首武装了自己,
安吉拉卡特 扫灰娘
作者:安吉拉·卡特 扫灰娘(又名:母亲的母亲的鬼魂——残缺的女孩) 尽管很容易可让故事重心脱离扫灰娘,转移到身体遭受摧残的继姐们——事实上,很容易可把这故事想成讲的是切除女人身体某部位,好让她们符合某些规范,某种类似割礼的切砍仪式,然而,故事开头讲的永远不是扫灰娘或她的继姐,而是扫灰娘的母亲,仿佛这其实是她母亲的故事,尽管故事一开始她就即将退出叙事,因为已离死不远:[一个有钱人妻子生病,感觉自己快死了,便将她的独生女唤来床边。] 注意丈夫/父亲的缺席。尽管这女人的身份定义来自与他的关系[一个有钱人的妻子],但女儿却清清楚楚是她的,仿佛只归她的所有,整个剧情也只关系着女人,几乎完全发生在女人之间,是两组女人的争斗——擂台右侧,是扫灰娘和她的母亲;擂台左侧,是继母和她的女儿,这两个女儿的父亲没被提及,不过就文本脉络和生物需求而言,可以料想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在两个女性家庭为争夺男人[丈夫/父亲,丈夫/儿子]而对抗的剧情中,男人看似只是她们狂想的被动受害者,然而他们具有绝对意义,因为那是经济意义[有钱人],[国王的儿子]。 扫灰娘的父亲,老男人,是她们第一个欲望以及争议的对象;死骨未寒的亡母一撒手,继母便将他夺了过来。接着是年轻男人,那个可能的新郎、假定的女婿,两个母亲为了占有他而战,把女儿当作战争工具或择偶交配活动的代理人。 若说那些男人,及其代表的金钱,是这两名成年女子争夺的被动受害者,那么这些女孩,三个都一样,更完全只受母亲的意志推动。尽管扫灰娘的母亲在故事一开始就死了,但身亡者只让她的地位更具权威。母亲的鬼魂占据了叙事,是真正的中心动机,使其他所有事件为之发生。 临终前,母亲向女儿保证:[我永远都会照顾你,陪伴你身边。]故事将告诉你她如何做到这一点。 在母亲作出承诺的此刻,扫灰娘还没有名字,只是她母亲的女儿,我们只知道这样。是继母取笑地叫她扫灰娘,抹消了她原有的名字[不管那名字是什么],将她逐出家庭,赶离众人分享的餐桌,孤独一人与炉台灰烬为伴,除去她偶然得之的高尚女儿地位,代之以偶然失之的低下仆人地位。 母亲说会永远照顾扫灰娘,但她死了,父亲再娶,给了扫灰娘一个仿母,这母亲自己有女儿,爱她们激烈一如亡母生前——且我们将看到死后亦然——爱扫灰娘那样。
原版格林童话三篇精选(最新)
话是为满足孩子对世界的美好想象而设计出来的脱离实际的故事。在常见的童话故事《格林童话》中,王子和公主令人艳羡的爱情故事是贯穿整本书的主线,善恶有报也是每个故事最后的结局。 美好的结局看似都是童话的最终归宿,但真正的故事却并非如此。 在《格林童话》中,由于王子给予的真爱,白雪公主咳出了毒苹果醒来;因为猎人的帮助,小红帽救出了外婆。但在最初完稿的《格林童话》中,皇后嫉妒白雪公主是因为其与亲生父亲的禁忌爱情,而小红帽因为大灰狼文质彬彬的样子被骗,最终成为了盘中餐。 《格林童话》从定稿至今共删改了45年,之所以被修改如此长的时间,原因与其故事本身的主题思想是分不开的。这本书里的故事皆来自于民间收集,原版书籍写作时正处于欧洲风气极差的时间内,人们对于社会的暗讽只能从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吐诉。 原版故事中,灰姑娘的继母教唆女儿通过自残穿上玻璃鞋以获得荣华富贵,而灰姑娘为了发泄怨恨让小鸟啄瞎了姐姐的眼睛,唤醒睡美人的也不是王子的吻,而是不知名的国王留给她的孩子,莴苣姑娘并没有与国王过上幸福的日子,而是在王后的嫉妒下被点燃长发烧死。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原版《格林童话》之所以被定义为黑暗童话,并非是因为其本身的思想有问题,而是在被贴上“儿童读物”的标签后,《格林童话》才被归类为不利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存在而被冠上“黑暗”二字。 《格林童话》改版的最终意义是传输最正统健康的思想,而不是让孩子小小年纪就沉浸于社会的现实中,而且相对于那时欧洲的黑暗社会来说,一本讽刺现实的书籍在和平年代的最大作用是鉴戒和参考,因此总的来说,《格林童话》的改版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现象,但原版的保留亦是不可忘却的历史沉淀。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过一个传闻: 现在的《格林童话》不是原版!原版黑暗、血腥、暴力……不是给孩子看的! 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原版”的确有着许多少儿不宜的内容,但这个“原版”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原版”。 童话?不,是精怪故事 出自格林兄弟之手“原版”的《格林童话》除了一些翻译上的用词、语法以外,基本与市面上流传的版本差不太多。
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thejamestaitblackmemorialprize)
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thejamestaitblackmemorialprize) 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是英国最古老的文学奖。 此奖项创办于1919年,每年评奖一次,是布莱克夫人(Mrs Janet Coutts Black)为了纪念她的最后一任丈夫而设立的;她向苏格兰艺术协会(Scottish Arts Council)进行了捐助。奖项的获得者是由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系的教授们从前一年在英国出版的英语作品中选出的。获奖者不分国籍。 布莱克奖包括小说奖和传记奖,各项奖金一直为3000英镑,2005年时奖金提高为各项一万英镑。布莱克纪念奖的获奖者大部分都是知名的作家人士,前任的获奖者中包括了著名的D.H.劳伦斯、E.M.福斯特、罗伯特·格雷夫斯、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萨尔曼·拉什迪等。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像威廉·戈尔丁、南丁·戈迪默、J.M. 库切、多丽丝·莱辛,190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也凭借自己的回忆录获得1923年的传记奖,还有获得过布克奖、柑橘奖、都柏林奖等众多英语文学奖的作家也获此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的1943年小说奖获奖者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获奖作品是英译本的《西游记》 小说类历年获奖者名单: 1919 Hugh Walpole,《The Secret City》休·沃波尔 1920 D. H. Lawrence,《The Lost Girl》大卫·赫伯特·劳伦斯 1921 Walter de la Mare,《Memoirs of a Midget》沃尔特·德·拉马雷 1922 David Garnett,《Lady into Fox》大卫·加内特 1923 Arnold Bennett,《Riceyman Steps 》阿诺德·本涅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