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抽动症患者预计超百万他们不想被注视但渴望被关注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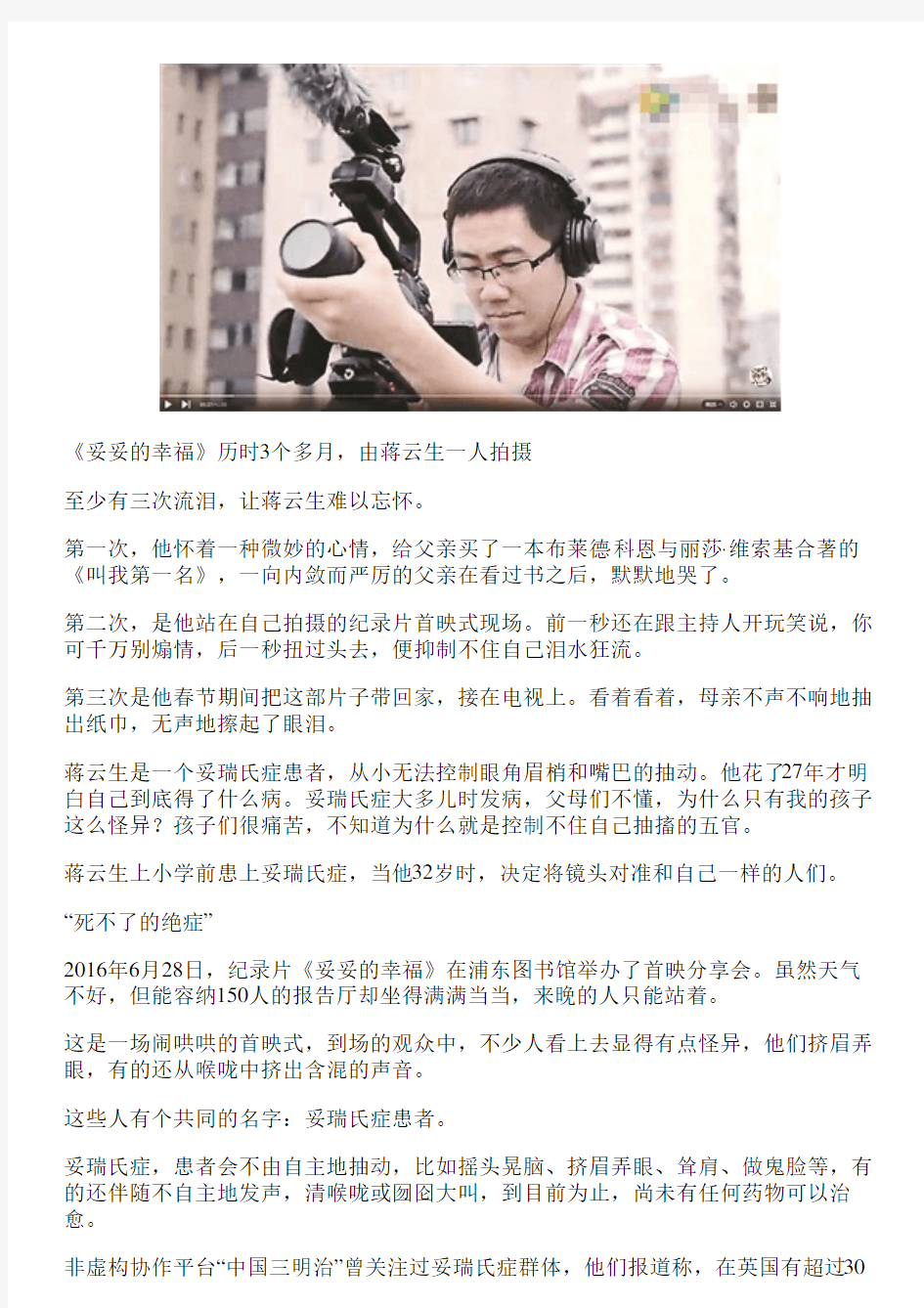
中国抽动症患者预计超百万他们不想被注视但渴望被关注
第一集《我就是我》的主人公尚洋是一名花艺师,他也是整部片中妥瑞氏症状况最严重的一个人
第二集女主人公果果与妈妈相处的方式就是吵架
《妥妥的幸福》历时3个多月,由蒋云生一人拍摄
至少有三次流泪,让蒋云生难以忘怀。
第一次,他怀着一种微妙的心情,给父亲买了一本布莱德·科恩与丽莎·维索基合著的《叫我第一名》,一向内敛而严厉的父亲在看过书之后,默默地哭了。
第二次,是他站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首映式现场。前一秒还在跟主持人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煽情,后一秒扭过头去,便抑制不住自己泪水狂流。
第三次是他春节期间把这部片子带回家,接在电视上。看着看着,母亲不声不响地抽出纸巾,无声地擦起了眼泪。
蒋云生是一个妥瑞氏症患者,从小无法控制眼角眉梢和嘴巴的抽动。他花了27年才明白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妥瑞氏症大多儿时发病,父母们不懂,为什么只有我的孩子这么怪异?孩子们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抽搐的五官。
蒋云生上小学前患上妥瑞氏症,当他32岁时,决定将镜头对准和自己一样的人们。“死不了的绝症”
2016年6月28日,纪录片《妥妥的幸福》在浦东图书馆举办了首映分享会。虽然天气不好,但能容纳150人的报告厅却坐得满满当当,来晚的人只能站着。
这是一场闹哄哄的首映式,到场的观众中,不少人看上去显得有点怪异,他们挤眉弄眼,有的还从喉咙中挤出含混的声音。
这些人有个共同的名字:妥瑞氏症患者。
妥瑞氏症,患者会不由自主地抽动,比如摇头晃脑、挤眉弄眼、耸肩、做鬼脸等,有的还伴随不自主地发声,清喉咙或囫囵大叫,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
非虚构协作平台“中国三明治”曾关注过妥瑞氏症群体,他们报道称,在英国有超过30
万的成年人和儿童患有妥瑞氏症;在台湾几乎每200人中,就有一人患妥瑞氏症;然而在内地,因为没有妥瑞氏症协会,所以没有一个官方的准确数字,若根据台湾和英国的比例,中国内地的患者人数大概超过百万。
蒋云生不幸是其中之一,如若不仔细看,他就是人海里极为普通的年轻人。然而仔细看他时你会发现,他的眉梢眼角和嘴巴会不由自主地抽搐,有时看上去像是在做一个嘲弄或者揶揄的鬼脸。
蒋云生花了27年才弄明白,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这就是一种死不了的绝症,要伴随我终生。”
“怎么知道生下你来会这样”
因为抽搐,蒋云生从小没少遭罪。抽搐症状在他学龄前便出现了,不由自主地挤眉弄眼,抽搐、装鬼脸、耸肩膀。一开始,父母强令他改正,察觉出不对劲后,还带他看眼科,兜兜转转才来到了精神科。
最后,沈阳医科大学将其确诊为多动症。但无论中医与西医,总也治不好。这烦人的症状让蒋云生的整个青少年阶段都过得不愉快。有时候父亲心情不好,看他在旁边一个劲儿抽来抽去做鬼脸,总会骂上几句,甚至一巴掌打过去。
为了寻找纪录片的主人公,蒋云生他以自己为主角,拍了一个简短的广告片,寻找愿意像他一样曝光自己故事的病友。少女果果看到广告之后,主动找到他想要参加拍摄。
果果是这个纪录片的主角之一,她父母离异,母亲甚至认为,果果的病症爆发跟父母关系紧张有关。
“你为什么要来拍这个片子?”蒋云生问果果。
果果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忍回去一些情绪,“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病。”
异样的目光不仅仅来自于路人——尽管坐地铁的时候,总会有人疑惑地看着这个漂亮的少女不停抽搐。但更多时候,不解来自于身边。老家的人曾以为她是被蛇精和蛤蟆精吓到了,还有同学嘲笑她,问她是不是吃了摇头丸,一度,果果甚至不敢走出家门,也没有朋友,唯一陪伴她的就是不受控制的身体。
母亲将她的病痛归因于自己的基因不好,甚至是缺钙,“反正在我心里她就是个病人。我怎么知道生下来你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相爱相杀,是果果与母亲的日常生活,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吵。每次吵架,果果的抽搐就会加重,身体抑制不住地抖动,并且伴随着剧烈的怪异声音。
“但我很怕跟我妈不吵架。”果果向蒋云生解释,母亲从不鼓励她,这让她觉得痛苦,但她还是会认真地跟母亲较真、吵架,她惧怕冷战。
在果果面前,蒋云生是1983年的“大叔”,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95后交流。直到他发现果果是个文艺少女,喜欢上豆瓣,听民谣,还是歌手阿肆的“迷妹”,而阿肆正好是
蒋云生的朋友,他让阿肆给果果寄了一张唱片,一下子就“收买”了小姑娘的心。
焦虑的爱
没有人能够给出妥瑞氏症的具体成因,在医学研究中,有假设说是因为多巴胺的分泌,也有说可能是链球菌的感染,但均未有定论。这对于习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普通人来说,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失控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
海夫人,因自己孩子患病,而致力于普及妥瑞氏症知识的公益人士,8年来每天都在面对焦虑而失措的父母。
她有11个群,一万多名家长和患者,在用尽了各种靠谱不靠谱的治疗方式之后,将她当作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海夫人告诉记者,曾经有个孩子因抽动而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家长咬着牙将孩子送进了精神病院,“9岁住到16岁,最后真得精神分裂了。”
不少抽动症的患者都在吃氟哌啶醇等精神类药物,这些药物多是用于治疗躁狂、帕金森或癫痫,对抑制抽动是有一定的作用,但往往一开始是半颗一颗地吃,后来就变成了一把一把地吃。
曾有个有钱的家长,为了患抽动症的孩子,跑遍全国顶级的神经内科,几百块一个专家号从北京挂到上海,西药中药轮流吃,一开始有效,随着用药量越来越大,孩子开始出现思维含混不清的状态。
急病乱投医让这个家长转向了莆田系医院,对方跟他说,孩子是颈椎的问题,于是住院按摩了两个月。结果出院不到一个月,孩子又开始发作且更加厉害,再去找这家医院,医院说只能开颅了。
这个家长在给海夫人的电话里哭得一塌糊涂。“他知道找莆田系医生不靠谱,但他什么药都吃了,什么方法都试了,但给孩子开颅他不敢。”
对比这些案例,蒋云生感激自己的父母,他没有被逼着吃药。在1990年代的东北,这种病让医生和蒋云生一家都束手无策。最后母亲放弃了让他变得“正常”起来。
放弃“完美的孩子”
蒋云生说:“这个病要学会跟它共处,你要接受它。”然而对于每一个患妥瑞氏症孩子的父母来说,接受这件事不容易。
“妥友”们都会反复提起一部电影《叫我第一名》,影片主人公Cohen就是一个有抽动症的男孩。从上小学起,小Cohen常常要拼命咬住铅笔,以免自己不受控制地发出怪声,父亲不理解儿子的病症,他常常命令儿子不要发出怪声,但这并不能由Cohen做主。
这戳动了无数妥瑞氏症患者的心。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与家人相处,是妥瑞氏患
者,以及他们家长们的一门必修课。
很多父母信奉残酷的生存逻辑:逼孩子优秀,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实际上,家长对孩子的方式不对,但家长本人却不知道。”海夫人说。尽管没有具体病因,但医学上普遍认为,某些精神刺激会诱发儿童抽动,例如家长对孩子苛责过多,家庭不和或者环境气氛紧张,
“很多家长想不通,隔壁邻居他们天天打孩子,孩子也没得抽动症啊。”海夫人说,“患妥瑞氏症的孩子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们很敏感,家长错误的教育方式很容易伤害敏感的孩子。”
来自杭州的董妈妈是蒋云生纪录片的另一个主人公,她是一名备受煎熬的母亲,两个孩子先后暴发了妥瑞氏症。
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大的还没好,小的也开始抽,她甚至一度想要通过考雅思出国,逃避现实。
慢慢地,董妈妈开始反思,是否对待儿子的方式太过严厉——刚生小儿子的时候,大儿子也只是个小男孩,但是她却要求他早早地自己睡觉,不管他怎么哭闹,怎么央求,坚决不同意儿子跟她一起睡。
“其实当时我就是自私。孩子有了弟弟,其实他觉得妈妈被夺走了。”董妈妈很自责,她自己从小是好学生,所以对儿子的成绩要求特别高。
意识到这些后,她不再对儿子的成绩提那么高要求了。她开始鼓励孩子做完作业就去做运动,而不是加课外习题。慢慢地,孩子不那么紧张了,抽动的症状竟减轻了,以至于消失。
董妈妈感慨,“养孩子,其实是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事情。儿子只是成绩不好而已,但却是个好孩子啊。”
然而像董妈妈一样想得开的父母是少数,更多的父母,面对妥瑞氏症时却在“怎么治不好”的焦虑中打转。
“有很多家长是非常功利的,我跟他说,你对孩子宽容一点,但是他宽容了,孩子没有好转,他就会急躁。就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是好不了。”董妈妈说。
父亲的道歉
蒋云生与自己的和解从2010年开始。一次派对中,有个外国人拍他肩膀,问他是不是有妥瑞氏症,这是蒋云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上网一查,症状全符合。活到27岁,他终于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他专门买了那本小Cohen的故事《叫我第一名》给父亲,看完书之后,父亲哭了。父亲给他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说:对不起。
在蒋云生辞职拍公益纪录片时,父亲虽然不赞成,但没有说话,父子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默契。
但首映这一天,蒋云生的父母却没有来。
“我预感自己会哭,不想让父母看到,所以没有让他们来。”他解释。开场前,他还跟女主持人开玩笑,让她千万别把自己给煽情哭了。但一开场,他自己就先流了泪。
2016年8月,片子的另一位主人公吴尚洋来到了沈阳,蒋云生的父母执意要去沈阳请他吃饭。吴尚洋是整个片中妥瑞氏症状况最严重的一个人,动作幅度最大,反应最激烈,时不时还会发出怪声。见到了他,让蒋云生的父母既佩服又感慨,他们想起了儿子。“吴尚洋都这么严重了,依旧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花艺师。”
蒋云生的父亲跟北青报记者说:“他(蒋云生)做公益以后,我害怕他耽误太久的时间。但现在看来,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无论他将来做什么,我们永远支持他。”这些话他从未与儿子说过,蒋云生也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杨宝璐
本文作者:环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