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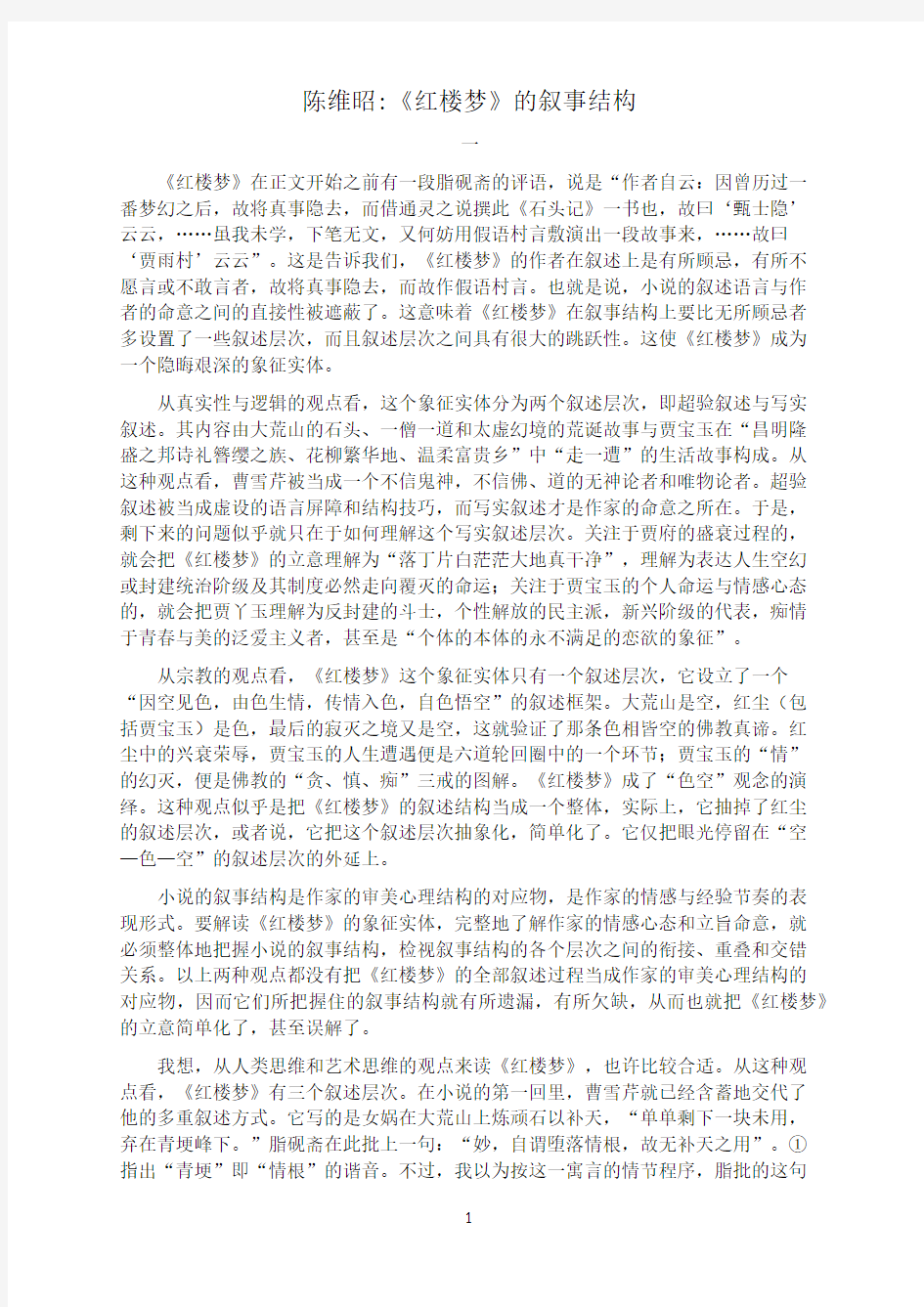

陈维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
一
《红楼梦》在正文开始之前有一段脂砚斋的评语,说是“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
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
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故曰
‘贾雨村’云云”。这是告诉我们,《红楼梦》的作者在叙述上是有所顾忌,有所不
愿言或不敢言者,故将真事隐去,而故作假语村言。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语言与作
者的命意之间的直接性被遮蔽了。这意味着《红楼梦》在叙事结构上要比无所顾忌者
多设置了一些叙述层次,而且叙述层次之间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这使《红楼梦》成为
一个隐晦艰深的象征实体。
从真实性与逻辑的观点看,这个象征实体分为两个叙述层次,即超验叙述与写实
叙述。其内容由大荒山的石头、一僧一道和太虚幻境的荒诞故事与贾宝玉在“昌明隆
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走一遭”的生活故事构成。从
这种观点看,曹雪芹被当成一个不信鬼神,不信佛、道的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超验
叙述被当成虚设的语言屏障和结构技巧,而写实叙述才是作家的命意之所在。于是,
剩下来的问题似乎就只在于如何理解这个写实叙述层次。关注于贾府的盛衰过程的,
就会把《红楼梦》的立意理解为“落丁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理解为表达人生空幻
或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制度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关注于贾宝玉的个人命运与情感心态的,就会把贾丫玉理解为反封建的斗士,个性解放的民主派,新兴阶级的代表,痴情
于青春与美的泛爱主义者,甚至是“个体的本体的永不满足的恋欲的象征”。
从宗教的观点看,《红楼梦》这个象征实体只有一个叙述层次,它设立了一个
“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叙述框架。大荒山是空,红尘(包
括贾宝玉)是色,最后的寂灭之境又是空,这就验证了那条色相皆空的佛教真谛。红
尘中的兴衰荣辱,贾宝玉的人生遭遇便是六道轮回圈中的一个环节;贾宝玉的“情”
的幻灭,便是佛教的“贪、慎、痴”三戒的图解。《红楼梦》成了“色空”观念的演绎。这种观点似乎是把《红楼梦》的叙述结构当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它抽掉了红尘
的叙述层次,或者说,它把这个叙述层次抽象化,简单化了。它仅把眼光停留在“空—色—空”的叙述层次的外延上。
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物,是作家的情感与经验节奏的表
现形式。要解读《红楼梦》的象征实体,完整地了解作家的情感心态和立旨命意,就
必须整体地把握小说的叙事结构,检视叙事结构的各个层次之间的衔接、重叠和交错
关系。以上两种观点都没有把《红楼梦》的全部叙述过程当成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的
对应物,因而它们所把握住的叙事结构就有所遗漏,有所欠缺,从而也就把《红楼梦》的立意简单化了,甚至误解了。
我想,从人类思维和艺术思维的观点来读《红楼梦》,也许比较合适。从这种观
点看,《红楼梦》有三个叙述层次。在小说的第一回里,曹雪芹就已经含蓄地交代了
他的多重叙述方式。它写的是女娲在大荒山上炼顽石以补天,“单单剩下一块未用,
弃在青埂峰下。”脂砚斋在此批上一句:“妙,自谓堕落情根,故无补天之用”。①
指出“青埂”即“情根”的谐音。不过,我以为按这一寓言的情节程序,脂批的这句
话应该倒过来表述为:因无材补天,故堕落情根。所谓“补天”,就是“补天济世”。
②这段寓言无非是表达这样的意思:不能为朝廷出力,不能为天子分忧,不能“治国
平天下”,只好把心灵归宿寄托在女子身上。石头不得补天,便来至太虚幻境,于西
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见到一裸绛珠仙草,遂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感其灌溉之恩,发
誓以眼泪为报,这就是“木石前盟”。后来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在石头上镌上字,把它
携带到红尘的富贵(荣国府)风流(大观园)地去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至此,
我们可以梳理出《红楼梦》的三个叙述层次:一是石头无材补天,便幻形入世,堕落
情根,投胎于贾府中,怡情于大观园里;二是“太虚幻境—大观园”的叙述层次,它
是“薄命司”的象征,是石头堕落之处,宝玉痴情之所;三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空—色—空”的叙述层次。这三个叙述层次是相交、相涵、互切、互补的,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织成了《红楼梦》的象征实体。曹雪芹以多重叙
述建构起《红楼梦》隐晦艰深的象征实体,我们若以还原的方法,对其象征实体进行
解构,那时,将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曹雪芹。
二
脂砚斋曾在小说正文“无材补天,幻形入世”之下日“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
③曹雪芹的一生惭恨便是不能“补天”。我想,“补天”就是补封建主义的天,这已
经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也是早已被否定的“陈腐”之论。被否定的理由是,它无法解
释曹雪芹为什么那样无情地展现封建社会的末世穷途。我以为这种否定是由于误解了
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而造成的。尽管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是面对人生的,但每一个
民族的文化对于人有不同的规定,因而每一个民族对于人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认
识和表达方式。人生问题在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中将被归纳为不同
的文化命题。整个民族,包括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都是面对其文化命题去
展开思维的,也就是说,文化命题成为思维和想象的起点,④一种不与社会合作而执
着于自己的信仰与追求的心理倾向,可以是对于不同的文化命题的反应。它可以是反
社会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也可以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主义”,还可以是反对社会的腐化之风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理性的卫道者。显然,忽略文化命题而只专注于小说的心理倾向,那么,对于小说的命意,就会“因读者的
眼光而有种种”。所以,扣住文化命题便是阐释文学创作题旨的起点与关键。
要了解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就必须知道他为什么不得补天,不得补天之后
为什么便堕落于情根,痴情于女人;而不象脂批所说的“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
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有此一部鬼话”。⑤在“无材补天”与“堕落情根”之间,有作家的一番隐哀,他的“一把辛酸泪”,他的“惭恨”、“悲怨”,都蕴含在
这两者之间的过渡上。然而,在叙述上,作家恰恰省略了这一过渡,而把笔墨集中倾
注在情根上,这使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模糊起来,使《红楼梦》的主题几乎成为
千古之谜。当然,“真事”仅仅是“隐去”,而不是销声匿迹。依据贾宝玉在红尘中
的痴狂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暗渡之陈仓,从而找到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
且搁下石头不得补天而堕落情根的原委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贾宝玉这个情种的痴狂状
态吧。《红楼梦》第五回的“红楼梦”曲的引子劈空便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无疑,在警幻仙姑看来,贾宝玉就是开辟鸿蒙以来的头号情种。这个“情”字并非指
爱情或情欲,它与肉体之欲无关,也与终身归属之爱无涉,所以这种情痴情种不是淫
魔色鬼,不是皮肤滥淫之蠢物。诚然,贾宝玉于抓周之时即对脂粉钗环爱不释手;他
也曾说过一番关于“男子”“女儿”的著名的奇谈怪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
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⑥仅此而言,恐怕不
止政老爷要目之为酒色之徒。然而,只要我们想起贾宝玉对待薛宝钗、史湘云的态度,我们就会象贾雨村那样罕然厉色地责怪政老前辈错看了宝玉。宝钗、湘云无疑是宝玉
倾心向往的闺阁中之皎皎者,就连其雪白浑圆的胳膊和天然展露的睡态也曾令宝玉神
昏目眩。可就因宝钗、湘云劝他一句“仕途经济”的话,劝他读书应试、官场应酬、
做宫济世,他便大觉逆耳,马上翻脸,“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
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须眉蚀物。
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⑦在那
样的时候,再不见他的淫魔色欲,再不见他那种只知有人不知有己的对于女儿的体贴
温存;在那样的时候,他再也不觉得女儿的清爽。看来,贾宝玉并非凡是女人就爱,
凡是青春美貌才华出众者就爱,就觉得清爽。事实上,凡是关心闺阁外面的官场世道
的女人,凡是热心于男人的事业的女人,凡是利欲薰心的女人(贾宝玉认为凡是嫁了
男人的女人都是利欲薰心的),贾宝玉统统都不爱。他曾说,女孩儿未出嫁时,是一
颗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这时虽还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
宝色,是颗死珠,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⑨为什么女人一嫁了男
人都变成了死珠、鱼眼睛了呢?丫环春燕算是真正听懂了宝玉的胡话。她说宝玉的话“虽是混话,倒也有些不差。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姊妹两个,如今越
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⑨是否“把钱看得真了”,是否利欲薰心,这才是宝玉判
断女人的真正的价值标准。显然,《红楼梦》里的所谓“女儿”、“男子”、“情”、“淫”等都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作家赋予它们以象征意义。所以,“女儿”,或者说妇女问题,并不是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
还在贾宝玉年纪尚幼,不知情欲为何物的时候,警幻仙姑便推之为“天下古今第
一淫人”。⑩这“淫”不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皮肤滥淫,
也不是恋爱、婚姻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意淫”,是“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它使
贾宝玉可以与闺阁中的女子成为“良友”,但于世道中却未免迁阔怪诡,将招来“百
口嘲谤,万目睚眦”。如果尚嫌警幻仙姑的表述过于玄虚模糊,那么,请看看脂批的
揭示:“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日‘意淫’。”[10]所谓“情种”,所谓“意淫”,便是指对女子的体贴、关怀,是一种精神上的博大无私的爱。
当我们留心于小说所例举的范畴,我们就能明白,石头为什么堕落情根,贾宝玉为什
么把“意淫”给予“闺阁”。女儿与男子,闺阁与世道,意淫情痴与仕途经济,清爽
与浊臭,这几对范畴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同一主旋律的不同变奏。这个主旋律就
是纯洁与污浊。这才是贾宝玉的所爱所恨,这才是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在封建
时代,世道自然是男人的世道,仕途经济自然是属于男人的事业。这样,“男子”便
是官场、世道、“仕途经济”的象征。而这些事业和人生价值取向却跟女人无关。因此,当贾宝玉嗅出官场、世道和“仕途经济”的浊臭气味的时候,当他把这种感觉表
述为“男子是浊臭的”的时候,他就自然会把“女儿”当作其对立范畴而赋予“纯洁”的象征意义。
三
可是,官场与世道的腐臭凤气的对立范畴为什么是“纯洁”、“清爽”,而不是“反封建”、“反礼教”或“个性解放”、“个体自由”?这就涉及到中国哲学、中
国思想对其文化命题的界定与表述。“人欲”与“天理”的关系,人的生命需求与社
会的价值取向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所面对的真正的文化课题。自从孔子
的儒家思想产生以来,中国文化主流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去建立大一统的专制等级制度。这种制度要成为可能、要获得强化,就必须以放弃或压抑个人私欲为前提。为此,它
必须建立一种社会本位的意识形态。孔子的仁、礼思想,尤其是孟子的义利之辨和舍
生取义思想,正是表明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它以价值的形式去抑制个体的生命需求,以使对专制等级制度的绝对性的确认成为个体的自觉。程朱理学把这种价值取向推向
极端,表述为“存天理,灭人欲”。儒家传统思想把对于专制等级制度及其价值体系
的绝对理性的顺从规定为“善”的人性,然后要求个体放弃生命的感性需求,把“从善”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这必然蕴含着本体论与认识论、先验假定与道德实践的深
刻矛盾。一方面,社会绝对理性要求个体泯灭自我本位意识,体认善,体认外在理性
的绝对性;但另一方面,对绝对理性的“自觉”体认必须由每一个个体去完成,作为
生命体,个体的全部需求将与道德实践过程相始终,而且,与生命藉求密切相关的某
些心理素质如意志、情感、知性,将成为道德实践的必不可少的动力。那么,对以抑
制个体生命需求为前提的社会绝对理性的确认怎样才能达到个体的自觉?唯一的途径
只有一条,就是不给个体以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的权利,通过政治暴力强制个体去
盲从。然而,在理论上否定人欲的存在价值,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使人欲销声匿迹。
生命毕竟是活生生的,如果通过政治暴力把“天理”规定为社会的绝对价值,那么,
任何动机都将打着“天理”的旗号出现,人欲也只好改头换面,画上“天理”的脸谱,在堂而皇之的“天理”幌子蔽护下,人欲获得了安全感和可能性。从人欲的角度看,
这种改头换面是“人欲”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途径,但是,从“天理”的角度看,这
种改头换面就是人格上的虚伪矫饰。于、是,“人欲与天理”的文化课题就转化成被
表述为虚伪矫饰的道德问题。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只要它把否定人欲的合理性
的道德思想作为社会唯一的绝对的价值标堆,那么,虚伪矫饰必然会成为一个严重而
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虚伪矫饰的程度正与其否定人欲的程度成正比。明清两朝把程朱
理学规定为国教,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在它的重压下,人欲畸形地成长为虚
伪矫饰。正因为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否定程度之空前,因而明代社会的虚伪矫饰道德的
严重程度也同样是空前的。王阳明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伪饰道德:“外假仁义之名,而
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
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凌相戕,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
体以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12]李贽也曾无情撕去理学
家耿定向的假道学面孔:“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13]虚伪矫饰,这就是明代中叶以来以李蛰为代表的个体觉醒思潮
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是曹雪芹所面对的文化命题。曹雪芹的全部艺术想象就是以这
一文化命题作为起点的。
在《红楼梦》的第四回里,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是如何描绘官场世道的。贾雨村
赖贾、王两大家族之力,补升应天府知府。一到任,他便面临一大考验:本地四大家
族之一的薛家之公子薛蟠因与乡宦之子冯渊争一女子而把冯渊打死。贾雨村本来不谙
官场门道,想秉公执法,建树一点政绩,便下令执拿薛蟠归案。幸亏经葫芦僧点破劝导,才知道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且得罪四大家族,不仅官爵,恐怕连性命
也难保。但他还要装模作样,说“况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弹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是我实不能忍为者。”对于贾雨村的这番造作,脂砚斋一再斥为“假极”、“全是假态”、“奸雄”、“奸雄欺人”。[14]贾雨村并非天生奸雄,只是“良明不昧势难当”。[15]执拿薛蟠,则必以前途性命为代价,这代价是贾雨村付不起的。当他听说薛蟠所抢之女子正是他的恩人甄士隐的女儿时,也只好说:“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身家性命为重,他无暇去顾及什么报恩护法,他终于徇情枉法,胡乱了结此案,让杀人凶手薛蟠逍遥法外,顺应了那个浊臭的世道。而且,怕葫芦僧以后揭穿他的伪饰面孔,便找了他一个不是,把他远远地充发了。经过这番磨炼,贾雨村“世事洞明”了,“人情练达”了,然而同时,他也就加入了那个浊臭世道里的臭虫的行列。曹雪芹正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16]贾雨村便是浊臭官场、世道的象征。
有了对官场世道的这番叙述之后,作家的不得补夭之惭恨、他的“情痴”便获得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参照。这样,大荒山的神话叙述与红尘中的写实叙述就在我们眼前串成了一个整体,大荒山下的石头遭遇与红尘中的贾宝玉的人生历程便联成一个完整的叙述层次。我们由此而知道,曹雪芹抱不得补天之惭恨“泪尽而逝”,这不是他不向往天宇,而是天空(官场)中有阴霾杂布,这阴霾亵渎了他的道德人格信念。我们也由此而知道,贾宝玉“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17]是因为读书是为了应试,应试是为了做官,要做官就必须精通庶务。“读文章”与“通庶务”,便是把人引导向官场的浊臭之域。曹雪芹相信,人性是纯洁自然的,因而他不可能在浊臭的官场里去实现“补天”的人生理想。他由官场的浊臭而否定官场,进而否定任何通向这浊臭之域的道路:读书、应试、应酬、庶务,最后连做宫、应试、应酬的主体—男人也给否定掉了,用贾宝玉的话来说,就是“须眉浊物”。
对于官场的浊臭之风,李贽斥之为伪饰,而提出“童心”作为对立范畴,曹雪芹则嗤之为“浊臭”,而提出“女儿”作为对立范畴。并非从人类学或生理学上研究儿童心理或妇女心理,而是把“童心”,“女儿”作为伪饰道德的对立面,作为人的纯洁自然天性的象征以表达自己的道德人格信念。所谓无材补天,便堕落情根,所谓梦游于太虚境、沉迷于大观园,无非表达这样的心理厉程:本想挤身官场,以“治国平天下”,但官场的浊臭之风与他对于纯洁自然天性的信仰相悖,他拒绝了官场,而官场也抛弃了他,使他不得补天。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变信仰,他把对纯洁自然天性的向往转化为对于少女的体贴与爱。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红楼梦》的另一个叙述层次“太虚幻境—大观园”的真正命意了。
四
人们都说,大观园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太虚幻境是大观园的神话象征和神秘暗示。不错。大荒山为真,红尘为假,小说为枉入红尘的石头取名贾(假)宝玉。石头适心于太虚幻境,贾宝玉则怡情于大观园。他被写成一个天生的情痴情种,他一厢情愿地把少女当成纯洁自然天性的象征而予以深深的眷恋和怜惜。这种“一厢情愿”表明,贾宝玉的“情痴”,与其说是体贴、怜惜少女,不如说是自恋,是真诚地执着于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常常处于失望的痛苦中。事实上,大观园里只有一个女子配得上他的“意淫”,这便是林黛玉,这便是石头在三生石畔精心浇灌、无限怜惜的那棵
绛珠仙草。因为“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话,所以深敬黛玉”。[18]
他把休黛玉视为唯一知己,与她建立起刻骨铭心、生死不渝的爱。
如果大观园这个女儿国是一个永恒的乐园,那么,贾宝玉就可以永远高枕无忧地
安睡在大观园里,石头的不得补天之惭恨就可以在女人的胸怀中得以稀释、融化,就
如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家之后,还可以一头扎进大自然的怀抱。然而残
酷的是,曹雪芹清醒地知道,大观园并不永恒!它的女儿们在太虚幻境里属于“薄命司”。警幻仙姑引领贾宝玉梦游太虚境,就是要向他暗示女儿国的幻灭,暗示女儿们
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命运。从“太虚幻境—大观园”
的叙述层次与“石头—贾宝玉”的叙述层次的关系来看,与其说,“薄命司”暗示着
金陵众钗的毁灭,不如说,它宣告了贾宝玉的“立足境”的破灭,宜告了曹雪芹的心
灵依托之虚幻。
你叫曹雪芹怎能不对“红颜薄命”、对“美韶华去之何迅”发出如此撕心裂肺的
悲恸与浩叹!本来,贾宝玉因执着于纯洁自然天性而不得补天,故转而痴情于女儿国。然而,既然他欣赏的是少女的纯洁与超功利,那么,出嫁的女人(已受过男人的站污,、青春已逝的女人,就再也不纯洁、不清澈了,因而再也不能作为纯洁自然天性
的象征了。而“太虚幻境—大观园”所无情地展现给他的却是“红颜薄命”与“美韶
华去之何迅”,是女儿必要出嫁、必要变老、必要被男人站污与毁灭,这叫他如何不
发出绝望的拗哭。当贾宝玉对着一株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杏树时,他想起了邢岫烟将要
出嫁一事。他想,岫烟出嫁不出两年,也会象眼前这株杏树一样绿叶成荫子满枝;再
过儿天,这杏树子落枝空,而岫烟再过几年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邢岫烟这一去,大观园“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19]少了一个好女儿,意味着贾宝玉又少了
一份心灵依托。而“太虚幻境—大观园”正在向宝玉展示,“好女儿”将一个个地消失,直至香消玉殒,群芳尽碎。这样,贾宝玉(也是曹雪芹)的心灵将永远处于无家
可归的流浪之中。
人不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生是淡乎寡味的一潭死水。然而有了信仰之后,
信仰却无所依归、无所寄托,这才是悲痛中的大悲痛。
五
难道就这样让心灵永远处于无家可归的流浪中吗?不,曹雪芹要找到灵魂的家园。那么,何处才是灵魂的家园?何处才是“立足境”?曹雪芹说:出家。于是他为小说
设置了“空—色—空”的神话叙述层次。不要以为曹雪芹在宣扬佛教思想,不要把
《红楼梦》当成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在释遨牟尼尊前的一次忏悔。曹雪芹对佛教的本
体信仰没有什么兴趣。在印度佛教思想中,“色空”观只是它的人生观、世界观,佛
教藉此引申出它的本体信仰:涅槃、寂灭。但是,在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无君无父”的本体信仰与中华民族的祖宗崇拜倾向相悖而被拒绝在中国文化的大门
之外,被接受的印度佛教思想主要是“色空”、“轮回报应”、“十二因缘”等观念
以及“禅定”的方法论。抽掉了彼岸世界,剩下来的这些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功能就
不是引向出世间,而是被用来解释人生苦难,以使受难者更宁静地生活于人世间。要
把这样的一些观念叫做佛教思想,实在勉强得很。《红楼梦》的“色空”观同样不是
佛教意义上的。小说中,空空道人读了石头上所镌之字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
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于是改名“情僧”。这是由道士变为和尚。可见,曹雪芹是
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佛、道概念的,只要他对于宇宙、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失落感得
以表达就行。曹雪芹的“空”的感受是由“一僧一道”(即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一起
去完成的,尽管小说的非写实的叙述层次是借着这一僧一道去建构,但小说表现出来
的思想、心态却非僧非道。所以,与其说“空—色—空”的叙述层次表达了曹劣芹的
佛教现念,毋宁说,它是一种神话叙述。
所谓的“色空”观念已经融化在中国民族的心理结构中。林黛玉可以说:“无立
足境,方是干净。”[20]但贾宝玉不能。尽管贾宝玉一直有出家的念头,但他也一直
肩负着沉重的生活眷恋和家族恩德。这两方面的重负使他不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方面,虽然他感受到作为心灵依托的女儿国终将毁灭,他仍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它
的向往与眷恋,曹雪芹的道德人格信仰始终没有因此而崩溃。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因为聚时欢喜,散时则冷清、伤感,所以不如不聚的好。林黛玉也许可以成佛。贾宝
玉却只愿人常聚、花长开,到了筵散花谢时,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所以
贾宝玉断然成不了佛。他对生活实在有着太多的眷恋了,虽然最后出家去了,但他
“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21]另一方面,他要“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22]然而,慈悲给予他的恩德,他却无法偿还,无法报答。尽管贾政经常严颜厉色吃喝他,甚至对他大加答挞,贾宝玉却从来不曾恨过贾政。他可以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但他一
直依赖着天恩祖德,过着锦衣纵袴、饫甘餍肥的生活,蒙受父兄师友的教育规劝。不
读书做官,他就报答不了天恩祖德。这样,家族对于贾宝玉来说就有着双重意义:它
既满足了贾宝玉的生存和享乐需要,为他提供贵族生活环境(因而他不象李贽那样对
私欲有着特殊的敏感,所以他的出家比起李贽来更是拖泥带水)。但同时,它又以封
建正统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去教育规劝他,为他规定了生活方式和读书做官的人生
道路。这双重意义对于那些“国贼禄鬼”来说,并不矛盾,而是“好风凭借力,送我
上青云”。但是,对于贾宝玉来说却是无法统一的,不能并存的。他既然执着于纯洁
自然天性,那么,官场以及通向官场的道路都只能引起他的反感、唾弃。这样,贾宝
玉对于家族便具有双重意向:既感恩戴德,又嫌恶唾弃;既留恋家族为他提供的生活
环境,又必须摆脱家族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和行为规范。他以为先‘谢慈悲”,然后“剃度在莲台下”,便能够找到立足境。这在他跟家族的关系上,似乎可以调和家族
对他的双重意义之间的矛盾。但在心灵深处.他知道,不去做官,不挽回家族颓败的命运,他就报答不了家族,报答不了天恩祖德,从而也就不能解开潜意识中那个祖宗崇
拜情结。于是,一种沉重的负债感将伴随着贾宝玉出家的每一步。
总之,贾宝玉是肩负着生活眷恋与家族恩德的重压而走向那个寂灭之境的。同李
赞一样,同古代所有反叛程朱理学的人一样,贾宝玉不可能是一位个人主义者。甚至,他身上的个体化倾向并不强烈,他的天性的最大特点便是“意淫”,便是对少女的忘
情的体贴,对纯洁自然天性的广博无私的爱。小说最终走向“色空”,不是忏悔,不
是寂灭,而是对这种爱的脆弱性的无可奈何的心理平衡,是女儿国幻灭之后,作家为
其纯洁自然天性的信仰找到的一个新的心灵依托之所。它不是对于感性世界的否定,
而是对于家族对他的双重意义的折衷。他的出家没有宗教上的宁静,却有诗人式的不
能自拔的痛苦。这痛苦不是所谓“感情与理智相冲突”的痛苦,而是他的人格本身的
内在分裂的痛苦。他行动上遁人空门,但心理上却是“云空未必空”。他的人格分裂
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坡中。我说曹雪芹不是佛教或道教信徒,这并不意味着他是
无神论者或可知沦者。人的认识能力相对于客体来说,永远是有局限的,然而人又具
有超越其认识闭限的意向,因而必然借助于神话感知和神话思维方式。[23]把曹雪片
当成无神论者或可知论者就会把《红楼梦》里关于“茫茫”、“渺渺”、虚虚、幻幻的叙述当成浪漫主义者的“审美静观”。康德指出,审美静观“对于它的对象之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是全然不关心的”,[24]恩斯特·卡西尔指出“这样一种不关心,恰恰是迥然不同于神话想象的。在神话想象中,总是暗含有一种相信的活动”。[25]不难证明,中国古代作家对于天命、因果、色空、灵异的态度绝对不是漠不关心的,在他们对这个超验之域的观照、制作、改造的过程中,都暗含着一种相信的潜质。然而,所有这些超验之域已经为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所同化,而充实为一个更具弹性的综合型文化实体,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性质而成为中国文化实体的一个质素,从而共同构造着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塑造着中国民族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从人类思维的特点看,这就是神话感知和神话思维方式。曹雪芹之运用神话叙述不是因为他信佛信道,但他相信冥冥之中有超越于人类的能力并主宰着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它也许叫“宿命”,也许叫“定数”,也许叫别的什么名堂,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超越人的认识闹限的外在理性。曹雪芹借着神话叙述表达了他对宇宙、对人类的感受。《红楼梦》的神话叙述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主要的,它是曹雪芹的神话感知和神话想象方式的对应物。
通过对《红楼梦》的象征实体作这样一番解析,把《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分解为三大叙述层次,并阐释叙述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重新建构起‘红楼梦’的情感流程。这样,我们的理解也许可以比较贴近曹雪芹的情感心态以及他在《红楼梦》里的立旨命意。
——————————————————
〔注释〕
①、②、③、⑤《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夹批。
④、[23]由于篇幅的关系,关于中国民族、中国文学的文化命题,关于中国文学的神话叙述问题等,都不可能充分展开,本人将另文专述。
⑥、⑦、⑧、⑨、⑩、17、18、29、20、21、22分别引自《红楼梦,第2、36、59、
59、5、3、36、
58、22、5、22回。本文引文主要以“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依据,兼参照《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11、14分别为甲戌本第五、第四回夹批。
12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聂文蔚》。
13李赞《焚书》卷一。
15王府本夹批。
16鲁迅评‘金瓶梅》语。
24、2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中《神话与宗教》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