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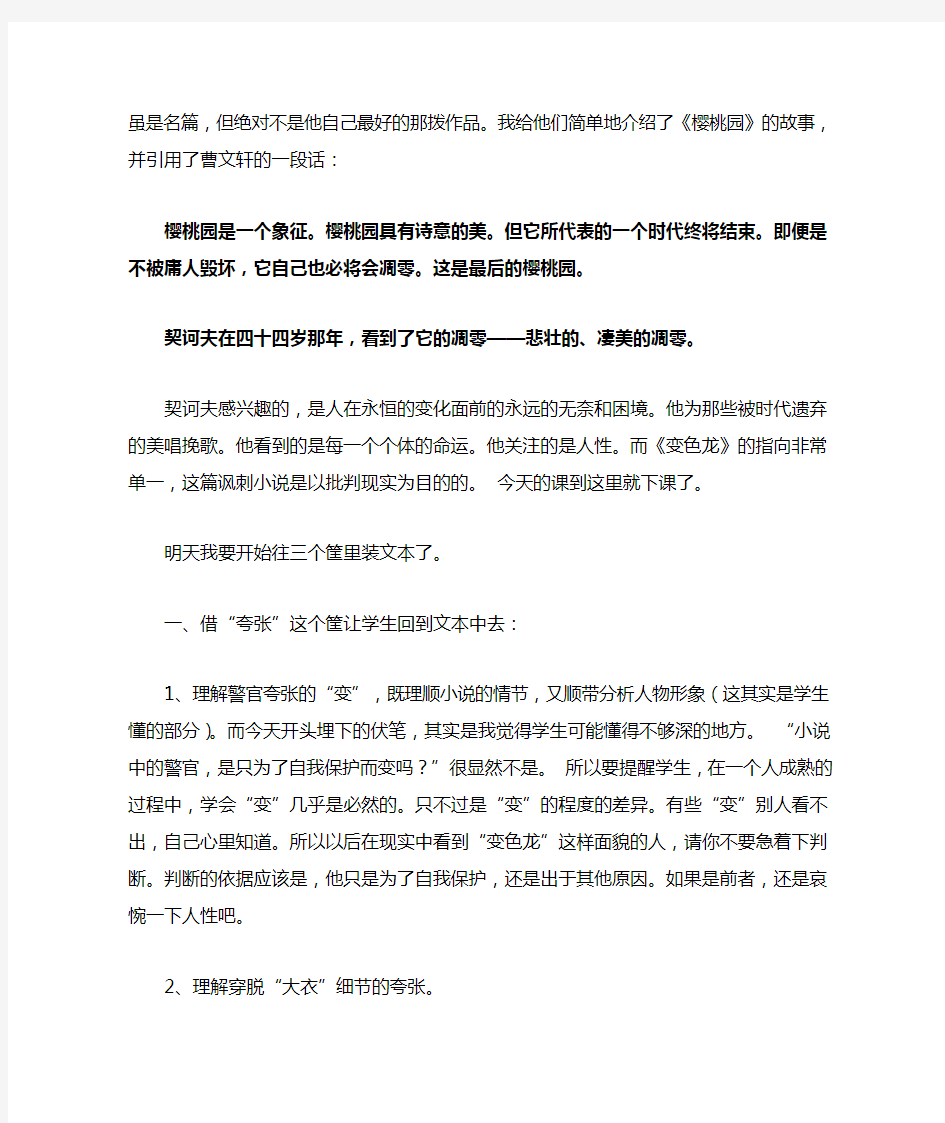
把《变色龙》上出花样来
又到三年一次上《变色龙》的时候了。上过四轮,也没上出什么新意来。上这样的课属于浅文怎么处理的问题。好像没有多少我可以发挥的地方。我现在的教学理念是,学生不懂的地方才是我要用力的地方。这篇小说学生还真没有什么看不懂的。黑白分明,直奔主题。课前为了测试学生是否读懂,我问了以下问题:“你们觉得现实生活中有变色龙吗?” “当然有啊!” “它是怎么变的呢?” “墙头草,两边倒。” “这吹的是什么风呢?” “功名利禄。” 然后我就猛夸学生。“这篇小说你们自己都读懂了,好像用不着我再上了。” 话是这么说,课还是要上的。哪些地方学生并没有真懂,哪些地方懂得不够深入,是我备课要突破的地方。
今天上课是这样开始的:“自然界的变色龙有哪些?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自我保护。” “对,自然界的变色龙碰到天敌时,‘变’是为了自我保护。” 我把这个部分做了板书强调。这是我对小说解读的伏笔。
听完录音以后,我说,“我这次读《变色龙》感觉它越来越不像小说,而像另一种我们熟悉的舞台形式——小品。说到小品,你们会联想到谁?” “赵本山。” “赵本山最被人熟悉的还是他的春晚小品。联系你们看过的他的小品,你们觉得小品有什么特征?” 七嘴八舌之后,达成下面三条共识:夸张、喜剧、讽刺。“下面我们将通过文本来验证,我的直觉对不对。” 这就是我这一次教学《变色龙》找的三个筐。要把浅显、熟悉的文本,往三个筐里装。
装之前,我还是把契诃夫的另一个身份——剧作家先做了介绍。从2004年纪念契诃夫去世一百周年说起。当时的《读书》曾经专版介绍了林兆民重排《樱桃园》的过程,包括对契诃夫文学成就的评价。我记忆很深。我说,《变色龙》只是戏剧大师的一个小品。虽是名篇,但绝对不是他自己最好的那拨作品。我给他们简单地介绍了《樱桃园》的故事,并引用了曹文轩的一段话:
樱桃园是一个象征。樱桃园具有诗意的美。但它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终将结束。即便是不被庸人毁坏,它自己也必将会凋零。这是最后的樱桃园。
契诃夫在四十四岁那年,看到了它的凋零——悲壮的、凄美的凋零。
契诃夫感兴趣的,是人在永恒的变化面前的永远的无奈和困境。他为那些被时代遗弃的美唱挽歌。他看到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他关注的是人性。而《变色龙》的指向非常单一,这篇讽刺小说是以批判现实为目的的。今天的课到这里就下课了。
明天我要开始往三个筐里装文本了。
一、借“夸张”这个筐让学生回到文本中去:
1、理解警官夸张的“变”,既理顺小说的情节,又顺带分析人物形象(这其实是学生懂的部分)。而今天开头埋下的伏笔,其实是我觉得学生可能懂得不够深的地
方。“小说中的警官,是只为了自我保护而变吗?”很显然不是。所以要提醒学生,在一个人成熟的过程中,学会“变”几乎是必然的。只不过是“变”的程度的差异。有些“变”别人看不出,自己心里知道。所以以后在现实中看到“变色龙”这样面貌的人,请你不要急着下判断。判断的依据应该是,他只是为了自我保护,还是出于其他原因。如果是前者,还是哀惋一下人性吧。
2、理解穿脱“大衣”细节的夸张。
进去是为了出来,出来时要理解,如此之夸张,只是为了让情节更富戏剧性。按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传统小说的分析,小说的情节应该有内在的逻辑性,而此文情节的推动很显然依靠的是偶然性。这不符合一般小说的规律。更像是一出小品。
二、借“喜剧”这个筐要完成以下任务:
我会问,看着这出闹剧,谁在笑?为什么笑?
这个问题是要把小说中的“群众”拉出来,整个情节的推动,警官的每一次“变”,都离不开那些群众的推波助澜。契诃夫对群众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会顺带比较一下《孔乙己》里那些酒客。群众在中外这两位大师的笔下,面目是一致的。大师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这里还是想启蒙一把,我还想问学生,如果你身处在这出闹剧中,你会是什么表现?
三、借“讽刺”这个筐达成对小说主题的理解:
讽刺警官,讽刺群众,讽刺当时的整个社会。如果有时间,顺带一下对社会环境描写的理解。
课堂小结:课始说过,《变色龙》不是契诃夫最好的作品,但是没有《变色龙》这样的激愤之作,契诃夫就不够圆满。他是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
如果有时间,我想给学生再读一篇能够代表契诃夫短篇风格的小说。预想的课先说到这,看看明天课堂上还会生成哪些东西。
这篇小说我采用的还是文本细读的方法。在其中一个班的教学中,采取的是读一段讲一段的方式。课前设计找了三个筐,夸张、喜剧、讽刺来装文本。完全靠的是直觉。关于喜剧的内涵,在别的论坛已经被人掐过了,此处就不再检讨。我在用喜剧这个筐时,实际上只是用了“笑”这个点。我问学生,除了你们在阅读小说时会笑以外,小说里还有谁在笑。他们为什么可以笑。小说里在笑的只有群众,警官自始至终处于紧张之中。群众为什么可以笑,因为此事不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可以安心地看戏。群众对情节的推波助澜作用,对警官的“变”起的作用,在细读中,学生感受得非常清楚。群众中除了一个“独眼龙”算是有名字的,其他的都是“人群中有人说”。
“这条狗象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官长。……”
当叶尔德林犹犹豫豫地说出下列的话时:“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人群中有人却下了斩钉截铁的判断:“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在读到上面几段时,很明显,叶尔德林一直在“深思”。“深思”了半天之后,又把前面的判断推翻了。不过用的词是“不过也可能”。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证据不充分。而人群中“有人”却那么确定,用的是“没错”加感叹号。
我提醒学生去比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
比较的结果是,因为警察要对这个判断负责任,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而插嘴的人不需要负责任,他可以张口就来。
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拿群众的“张口就来”作为批判对象的。还比较了《孔乙己》一文里的酒客。
今天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会再去思考群众的张口就来的含义。我想,根据文本,我可以理解成起哄,也可能确实是知情人(但是我在文本中还没有找到证据)。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倾向于是起哄。因为此人无名无姓。前面插嘴的群众,后来契诃夫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让“独眼龙”这个人亮相了。而此处契诃夫很显然没想让这个插嘴的人亮相。
目前我的看法是,契诃夫在写作时那么明确地给警官冠以“变色龙”的称呼,他讽刺的对象很显然主要是奥楚美洛夫,而不是群众。在这么单一的场景中,推动情节的波折靠的也只能是群众。
至于刘俐俐用罗兰巴特关于叙事作品的“核心功能”和“催化功能”对《变色龙》的解读,因为没看到原书,不知道她具体的分析。所以现在还不敢下判断。
即使这个解读我看完之后能够接受,但怎么落实到课堂上,让初三的学生接受,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想请问您有没有用这种解读教过《变色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