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民间叙事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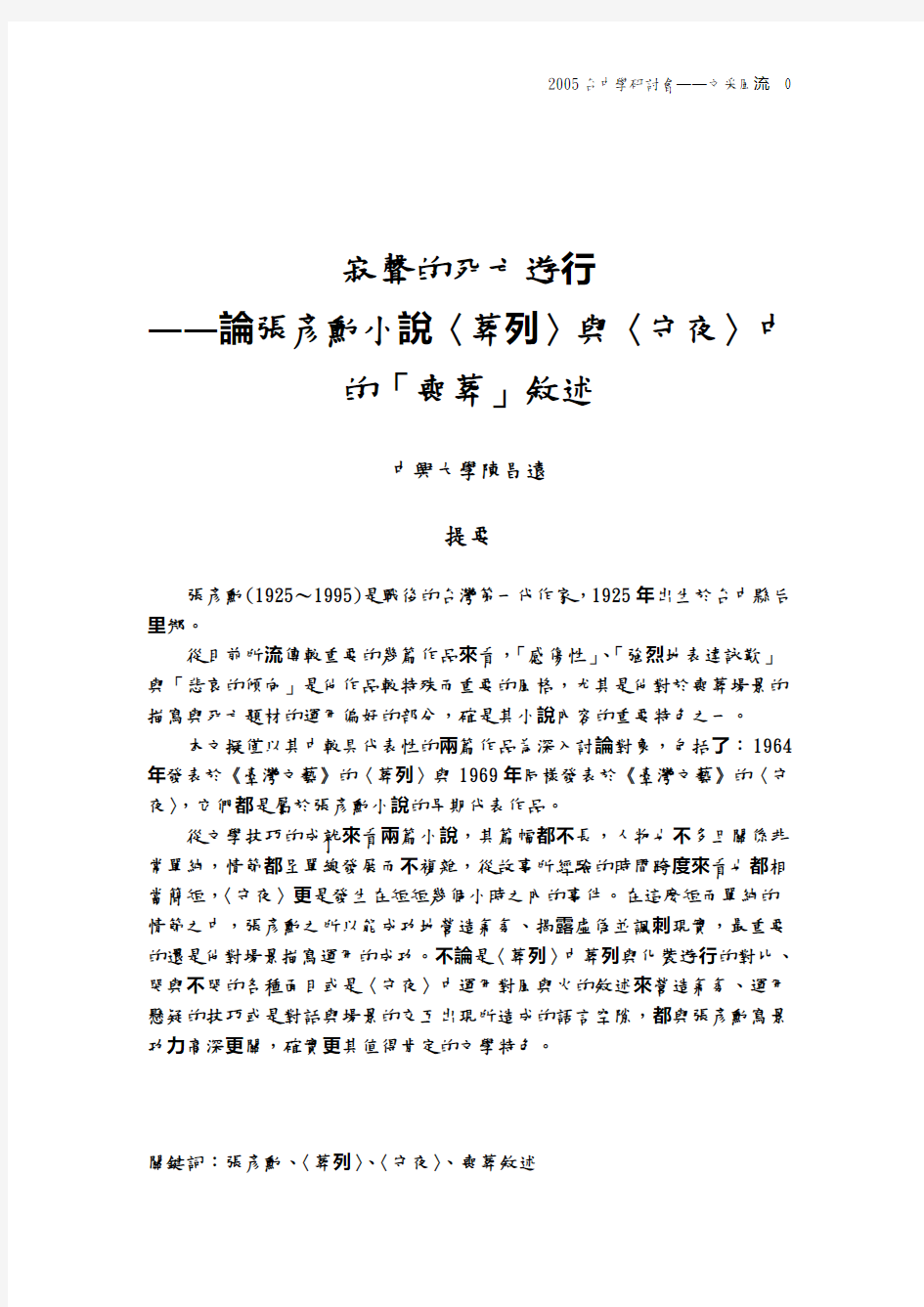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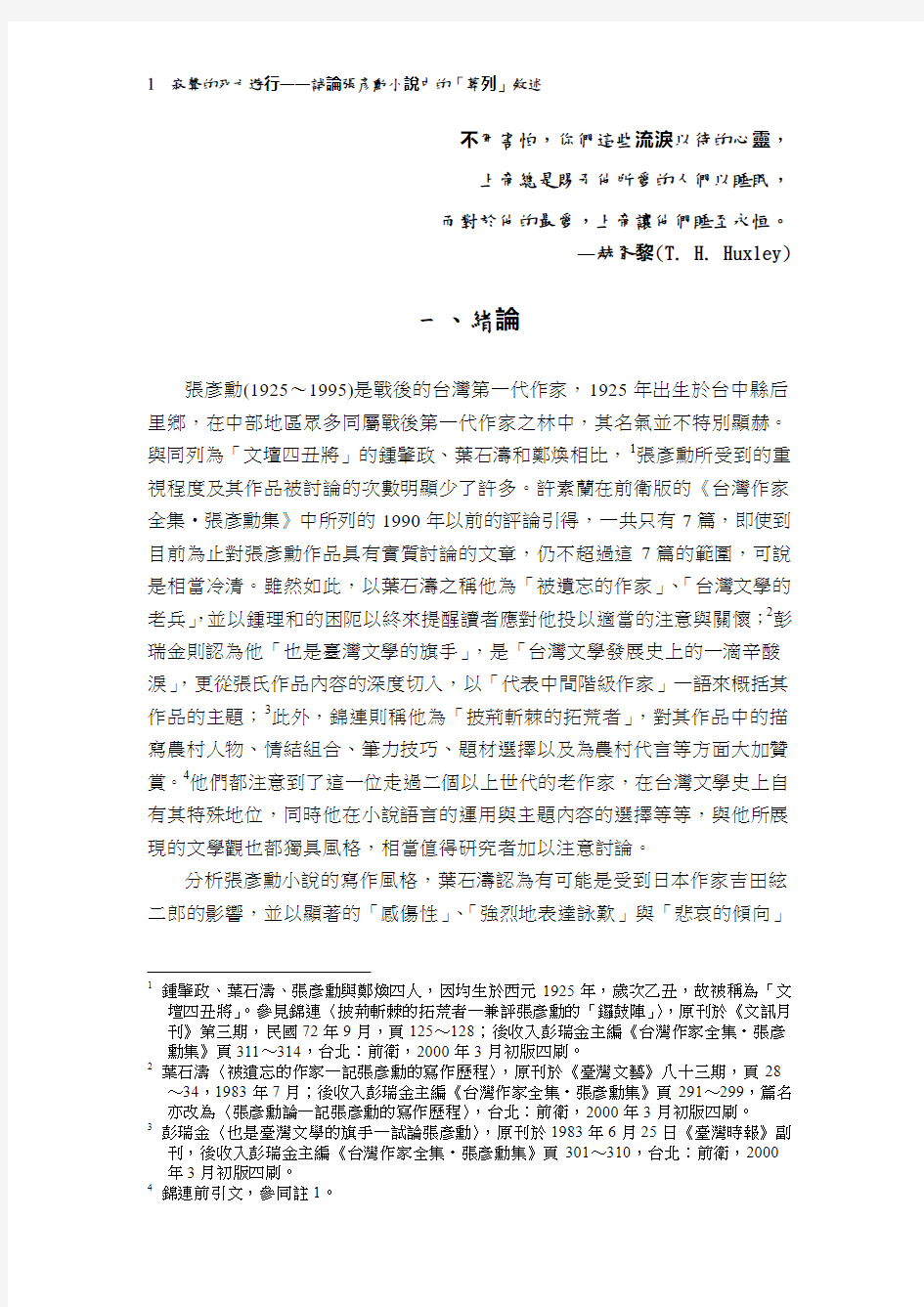
寂聲的死亡遊行
――論張彥勳小說〈葬列〉與〈守夜〉中
的「喪葬」敘述
中興大學陳昌遠
提要
張彥勳(1925~1995)是戰後的台灣第一代作家,1925年出生於台中縣后里鄉。
從目前所流傳較重要的幾篇作品來看,「感傷性」、「強烈地表達詠歎」與「悲哀的傾向」是他作品較特殊而重要的風格,尤其是他對於喪葬場景的描寫與死亡題材的運用偏好的部分,確是其小說內容的重要特色之一。
本文擬僅以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兩篇作品為深入討論對象,包括了:1964年發表於《臺灣文藝》的〈葬列〉與1969年同樣發表於《臺灣文藝》的〈守夜〉,它們都是屬於張彥勳小說的早期代表作品。
從文學技巧的成就來看兩篇小說,其篇幅都不長,人物也不多且關係非常單純,情節都呈單線發展而不複雜,從故事所經驗的時間跨度來看也都相當簡短,〈守夜〉更是發生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的事件。在這麼短而單純的情節之中,張彥勳之所以能成功地營造氣氛、揭露虛偽並諷刺現實,最重要的還是他對場景描寫運用的成功。不論是〈葬列〉中葬列與化裝遊行的對比、哭與不哭的各種面目或是〈守夜〉中運用對風與火的敘述來營造氣氛、運用懸疑的技巧或是對話與場景的交互出現所造成的語言空隙,都與張彥勳寫景功力高深更關,確實更其值得肯定的文學特色。
關鍵詞:張彥勳、〈葬列〉、〈守夜〉、喪葬敘述
不用害怕,你們這些流淚以待的心靈,
上帝總是賜予他所愛的人們以睡眠,
而對於他的最愛,上帝讓他們睡至永恒。
―赫胥黎(T. H. Huxley)
一、緒論
張彥勳(1925~1995)是戰後的台灣第一代作家,1925年出生於台中縣后里鄉,在中部地區眾多同屬戰後第一代作家之林中,其名氣並不特別顯赫。與同列為「文壇四丑將」的鍾肇政、葉石濤和鄭煥相比,1張彥勳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及其作品被討論的次數明顯少了許多。許素蘭在前衛版的《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中所列的1990年以前的評論引得,一共只有7篇,即使到目前為止對張彥勳作品具有實質討論的文章,仍不超過這7篇的範圍,可說是相當冷清。雖然如此,以葉石濤之稱他為「被遺忘的作家」、「台灣文學的老兵」,並以鍾理和的困阨以終來提醒讀者應對他投以適當的注意與關懷;2彭瑞金則認為他「也是臺灣文學的旗手」,是「台灣文學發展史上的一滴辛酸淚」,更從張氏作品內容的深度切入,以「代表中間階級作家」一語來概括其作品的主題;3此外,錦連則稱他為「披荊斬棘的拓荒者」,對其作品中的描寫農村人物、情結組合、筆力技巧、題材選擇以及為農村代言等方面大加贊賞。4他們都注意到了這一位走過二個以上世代的老作家,在台灣文學史上自有其特殊地位,同時他在小說語言的運用與主題內容的選擇等等,與他所展現的文學觀也都獨具風格,相當值得研究者加以注意討論。
分析張彥勳小說的寫作風格,葉石濤認為有可能是受到日本作家吉田絃二郎的影響,並以顯著的「感傷性」、「強烈地表達詠歎」與「悲哀的傾向」
1鍾肇政、葉石濤、張彥勳與鄭煥四人,因均生於西元1925年,歲次乙丑,故被稱為「文壇四丑將」。參見錦連〈披荊斬棘的拓荒者─兼評張彥勳的「鑼鼓陣」〉,原刊於《文訊月刊》第三期,民國72年9月,頁125~128;後收入彭瑞金主編《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頁311~314,台北:前衛,2000年3月初版四刷。
2葉石濤〈被遺忘的作家─記張彥勳的寫作歷程〉,原刊於《臺灣文藝》八十三期,頁28~34,1983年7月;後收入彭瑞金主編《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頁291~299,篇名亦改為〈張彥勳論─記張彥勳的寫作歷程〉,台北:前衛,2000年3月初版四刷。
3彭瑞金〈也是臺灣文學的旗手─試論張彥勳〉,原刊於1983年6月25日《臺灣時報》副刊,後收入彭瑞金主編《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頁301~310,台北:前衛,2000年3月初版四刷。
4錦連前引文,參同註1。
作為其重要的風格表現。5從目前張彥勳所流傳較重要的幾篇作品來看,直接而明顯地表現出這樣風格題材的,無疑是他對於喪葬場景的描寫與死亡題材的運用偏好的部分,而這也確是其小說內容的重要特色之一。雖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這一類主題內容的篇章並不在少數,但本文擬僅以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兩篇作品為深入討論對象,包括了:1964年發表於《臺灣文藝》的〈葬列〉與1969年同樣發表於《臺灣文藝》的〈守夜〉,它們都是屬於張彥勳小說的早期代表作品。6
在這些對喪葬死亡的場景敘述中,作者不但透過場景的佈置來達到氣氛拱托與營造的效果,進而形成情節上的轉折或衝突,增加小說故事的可看性與思考內容的深度。更重要的是,從作者對這一類敘述題材的偏好運用與成功描寫的這個事實來看,其背後應有其更為實際的因素存在,這即是作者的個人經歷與人格特質在作品敘述中既隱又顯地呈現。
本文的即試圖對這些涉及到喪葬與死亡題材的幾篇作品進行分析討論,一方面經由文本的深入閱讀,掌握其表面的文字脈絡與內涵,從敘事分析的角度對這些作品的文學意涵作重新的評價;另一方面則配合作者生平與時代背景因素,對這些作品特殊風格的形成原因進行解讀,以期增進對這樣一位「忠實走一生」的文學老兵的認識,並還給他應有的榮耀。
二、〈葬列〉中對傳統喪葬場景的描寫――人間風景素描
家
葉石濤認為張彥勳小說的優點在於「風景的描寫」,彭瑞金也認為他「始終像個賣力、耐心的人間風景素描家」,由此可以皆了解到對客觀場景的描寫敘述,並進而運用這些場景來營造氣氛或與小說人物心理過程相呼應,被認為是張彥勳小說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成功之處。從小說中對喪葬場景的描寫來看,張彥勳確實無愧於這些稱譽。
這種經由人物視角的轉移,使小說中人物的心理過程與景物描寫產生相5葉石濤前引文,參同註2。
6以上各篇作品的發表年代與刊物,係根據張彥勳自己所編訂的寫作年表,見彭瑞金主編《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頁317~325,台北:前衛,2000年3月初版四刷。另外,除了以上所列兩篇小說,自1982年到1984年陸續發表於《文學界》的「鑼鼓陣三部曲」─〈鑼鼓陣〉、〈阿順仔從陰間回來〉、以及〈一個死〉,亦涉及死亡喪葬題材的運用,但此時期張彥勳作品的關懷角度已不同於前期,對喪葬事件的描寫亦非故事中佔重要敘述地位的部分,故本文暫不擬予列入討論範圍。
互呼應的效果,並造成獨特風格的例子,最明顯的作品就是小說〈葬列〉。這篇小說所敘述的,就正是一個完整的台灣傳統社會處理喪葬的事件簿,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從一個少年孩童的角度來述說一個從生到死的殯葬事件過程。
為什麼張彥勳要挑選這樣一個,在家族中無足輕重、在年齡上如此年幼的小孩來作為整篇小說的敘述者呢?從小說語言的角度來觀察這篇作品時,可以發現其生澀而不甚自然的敘述話語,這或許可以被視為是小說寫作中失敗的部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當身為敘述者的主人公是一個未成年的孩童時,於是他表現出來的語言生澀本來也就自然而然、應該是如此的了。同時,更由於小孩子不同於大人的觀察力,使得敘述者更得以展現其特別、好奇、細膩與單純的一面。以這樣的理由來思考,作者之所以選擇家族中不起眼的孩童來作為故事的敘述者,正是一個在敘述策略得以造成「陌生化」效果的選擇。7這種「陌生化」的效果則造成了這篇作品在敘述視角上,有時似乎是有點兒前後矛盾的地方;在語言上,也略顯生硬,但卻更能產生吸引讀者好奇心與閱讀的樂趣。
就情節而言,雖然整篇小說被分成四個段落來敘述,其實從故事內容來看,主要可以分成二個敘述情節的主軸:一部分是對傳統喪葬禮俗的描寫,包括了彌留時的處理、喪禮的過程到出殯時葬列的場面,這一部分是以場景的描寫為內容;另一個部分則是對家族成員之間為爭產而造成的諸多磨擦的敘述,諸如:父叔之間的打鬥、婦女之間的對立等等。而在這兩條主線的背後所隱涵的,則是作者藉由小說主人公所發出的,對於人性冷暖、情感真假之間的傷感、懷疑與嘲諷。
小說共分為四個段落。故事剛開始是主人公探視其生病即將死亡的祖父,並由此進行聯想與回憶的敘述,內容主要是對故事背景─家族成員為爭產而失和─作交待。在面對即將來到的親人死亡,主人公的心理反應是典型而直接的:
7俄國形式主義者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остpанениe或譯為「反常化」)的說法,認為:「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對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頭更成其為石頭。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視象那樣,而不是如同你所認知的那樣;」而要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方法則是「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復雜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他並以列夫?托爾斯泰運用反常化的例子作說明,「……反常化手法在於,他不用事物的名稱來指稱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樣去加以描述,就像是初次發生的事情,同時,他在描述事物時所使用的名稱,不是該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的名稱,而是像稱呼其它事物中相應部分那樣來稱呼。」見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手法的藝術〉,收入方珊等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頁1~10,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6月。
帶著悲戚,我踱出病房,心中沮喪得異常難過。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懼感好似浪潮,打自胸口湧上,卜卜跳盪的心臟,連呼吸也感到急促。
(頁25)8
這段敘述的主人公的身份是年幼的孩童,相較於故事中其他的成年人物,主人公大概是未曾經歷過處理喪葬的類似經驗,因此,他由此所產生的反應也就比故事中所有其他的人物都來得更顯自然、深刻而且發自內心。而這樣悲戚、恐懼的心情,放在故事一開始的地方,正是作為後文中敘述到其他成年人在面對整個喪葬時所表現出來的冷漠、虛偽與制式反應的強烈對比,是整個葬列觀察實驗中的一組「對照組」。
當一般人在面對死亡時,通常會有兩種自然的態度,「一種是把死亡當做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另一種則是把死亡當做自個兒會解決的事。」9但不論是那一種態度,不論是發生在自己或是親近的親人身上,死亡都是人們所恐懼、逃避、不願提起的對象。於是主人公開始回憶有關於他祖父與家人有關的事蹟,從敘述者的心理來說,這些回憶是重溫舊夢式的自我心理治療過程,更是一種心理上的逃避過程,因為主人公認為:
我簡直不能置信祖父可會如此的脆命,……(頁25)
「子福」是更了,祖父卻一輩子沒能好好兒享過福氣;為了這個家,他確確實實吃盡了苦頭。……在我家祖父是個磐石般的存在。是的,祖父是個磐石般的存在,這個極其複雜的大家庭,就是全賴他一個人支持了的;要是失去了他,就是等於沒更支柱的房子,早該給坍塌。
(頁26)
用巨石原型意象─磐石來表達對家族長的地位,這個磐石即是一個巨大的父親崇拜形象,也是「地父」原型意象的一種現代表述,10是主人公心理上的
8本文所引用張彥勳作品,皆引自彭瑞金主編《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台北:前衛,2000年3月初版四刷,不另註出處,僅標明頁碼。
9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頁21,台北:張老師文化,1997年4月。
10在許多神話中,雙親意象的角色分配往往是以天父地母的結合形式出現,即母親通常是地親,父親通常是天親,但事實上「至少在理論上,二者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實現一項或者甚至兩項功能。」如:古埃及人的神話傳說中,「就有一對名叫努特和蓋布的神,努特是女的,代表天;而蓋布是男的,代表地。在創造世界之前,努特與蓋布結合,但這就激怒了太陽神拉,於是太陽神拉就命令空氣神舒插入他們之間,將他們隔開,於是努特(女)就變成了弓形的天,而蓋布(男)就變成了平臥的肥沃的大地。」參見[美]阿瑟?科爾曼(Arthur Colman)、莉比?科爾曼(Libby Colman)著,劉文成、王軍譯《父親:神話與角色的變換》(The Father─Mythology and Changing Roles),頁3~5,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依賴,更是其心中世界安定的表徵,失去了這個表徵就相當於整個世界的不安、混亂與崩潰,因此主人公需要對即將失去了他生命中的磐石進行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治療與補救。
另一方面,通過「支柱」與「房子」的比喻,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正是具體而形象地說明了,對於原本幼小且未經接觸過死亡經驗的孩童心靈來說,這樣一位重要心理支柱的死亡消失,就像房子失去了支柱而倒塌,舊的房子將因此而被毀滅,在心理重建的過程中,經歷過一次這樣與死亡如此接近的喪葬事件之後,或許也可以被視為是他從原來的舊世界、舊階段到另一個新世界、新境界的「生命禮儀」儀式之一。11因此,相對照於主人公在故事一開始的難過、恐懼,到了故事的末尾,主人公已經能夠將這些經驗當作過去的事實加以接受:
我不曉得她們是真哭還是假哭?是真是假,我不用去質疑,反正我已不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我不會相信一向把祖父不放在眼中的她們倆,真會一下子變得如此傷心。(頁39)
小街,完全給抛在後頭了,而葬列依然緩緩地開走著。鑼鼓聲已停息,再也沒更人哭泣。我們默然地走著,踏著碎石,走在那條滿是飛塵的小路上,默默地……再也沒更人哭泣……。(頁40)
年少生澀的過去被「抛」在後頭,因為主人公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但相對的,原本被敏銳地感受到的各種聲音這時已「停息」,哭泣也沒有了。因為聲音的停息與哭泣的停止事實上都暗示著主人公感受力的退化,而感受力的退化正是主人公社會化、公式化與物化的象徵,也就是原本敏銳的心靈與感情漸漸走向麻木與慣習,而這也是人類成長的代價與通過人生歷練的成果。
在這一段主人公的回憶的內容中,透過家族成員間為爭產而引起的糾葛與紛擾,一方面顯示出主人公對祖父心理上依賴的表面現實原因─他是父叔之間爭執的唯一有力的仲裁者;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大人們為了爭產所不惜顯露出來醜惡的嘴臉。於是,父叔為了爭取更多的財產,險些鬧出人命,母親與嬸母之間也發生了嚴重的對立。面對這些生命的無常與人世的現實黑暗,
年9月一版一刷。
11關於各種「生命禮儀」,尤其是其中有關「過渡儀式」的部分,可參見[美]巴巴拉?梅厄霍夫(Barbara Myerhoff)〈過渡儀式:過程與矛盾〉,收入方永德等譯﹝美﹞Victor Turner 編《慶典》頁138~174,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及﹝美﹞Victor Turner 〈模棱兩可:過關禮儀的閾限時期〉,收入史宗主編,金澤、宋立道、徐大建等譯《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頁512~530,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4月。
主人公既感慨又無奈,但年幼的他面對這些無能為力的敏感卻只能對著門外的自然景觀徒自悲涼:
踱出門樓,我走到了果子園,心中的傷感倍加深沉。蔚藍的天空,白雲縹渺;五月的太陽把荔枝的果子照得爍爍發亮。
祖父一生刻苦自勵,憑著那雙厚大的胳臂立家置產,把一個衰落頹廢的家,整頓得井井更條。這一片果子園自然是他血汗的結晶;然而他可能再也無法看管它了呀,即使祖父果真他界而去,這片園地,豈不是也成了他們所爭執的對象嗎?(頁29)
睹物思人,面對美麗大好的果園與晴朗光明的景色,主人公的心情卻是黑黯而傷感的,這一切都源自於他對祖父即將死亡這件事的恐懼與擔憂。
到了第二段,敘述祖父自病危到剛死亡這一段時間內,整個家裡的處理場景與家人的反應情況,實際的殯葬處理過程從此時開始啟動。從祖父昏迷病危開始,原本散居各地的家人開始陸陸續續地回到家中,這原本應是令人感到憂心難過的現象─因為這表示了祖父情況的危急,在主人公的敘述中,卻反而將其與「大年夜的團聚」來相類比:
屋子裏嘈雜異常,比除夕夜的團圓可要熱鬧。我真懷疑到底大家是不是真為祖父的病危而歸來?或只為湊湊熱鬧?(頁30)
用節慶的歡樂氣氛與喪葬的死亡氣味相對比,一方面在嘈雜的環境之中顯露出對眾人對待死亡的不夠莊重與嚴肅的不滿與諷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早先爭產的陰影下,家人之間原就不和穆,除夕夜本來就很有可能是不熱鬧的,在這裡提到這一點只是再次從側面點出了家人不和的事實。像這樣用熱鬧來對比稱呼喪禮的例子,在故事的後段還一再地出現,更一步步地加重了對這整件喪葬禮儀中的不合人性、虛假性所進行的諷刺。當第三段中寫到夜間所進行的喪儀時,不但將喪儀的鑼鼓聲與嗩吶聲比成「交響曲」,更說道:
……成天哄哄鬧鬧,簡直像在做著莊脚戲(鄉下戲)。傍晚,太陽剛下過山,庭院裏便擠滿了看熱鬧的莊稼男女;許多婦女為了一睹為快,顧不得涮碗筷和洗手脚,穿過田畦小路紛紛趕來參觀。(頁35)
以看戲的態度來看待原本嚴肅的死亡喪葬儀式,這簡直成了嘉年華式的迎神賽會場合了,這樣的態度對死者該是多麼的不恭敬,對於死亡又是多麼的不
尊重,但這一切竟都被視為習以為常。而在這場觀眾盛多的表演會中,各種戲碼在道士的引導下慢慢地進行著,演員們則各盡其責地試圖打動場外評審觀眾的心,以邀得美譽,對虛名的渴慕遠遠超過了對親人的思念與不捨的情感。於是除了情感深刻的四叔之外,原本對祖父毫無情感的二嬸母與三嬸母竟然也:
出乎眾人意料的,便是二嬸母了;在「孝女」行列中,以她的號啕為最兇。可是三嬸母好勝的脾氣,那會叫她認輸?哭一回停一回,簡直的跟二嬸母作著一場哭鬧比賽。(頁37)
感情原只有真假,現在竟然被拿來作為比賽的項目,這樣以作戲與看戲的心情來描述喪儀,到了故事最後的出殯行列時,真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高潮。當葬列的隊伍開始進行時,主人公聽著鑼鼓聲響起,看著街樓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頭,心裏所想的竟然是,這個樣子「簡直的像在觀覽化裝遊行。」:
事實上,這與化裝遊行更什麼兩樣?
將最嚴肅的生命禮儀與滑稽的化裝遊行相類比,其所產生的落差與震憾效果,確已頗近於「狂歡節」儀式中的「上下對話」的語言效果。12
然而諷刺的是,就在就在這一段敘述之前,當道士在夜深人靜、觀眾散去之後做法事時,失去了觀眾的舞台上,真的有心留下來陪伴守靈的人卻僅有兩個:
倦怠的經文和著鬆弛的木魚聲,幽微地響在靜寂的夜空中,越加顯出晚春夜的蕭條。三叔流黏涎子在打盹兒;幾幾乎所更的家人,都打著呼魯睡著了。守在稻草上,我和四叔就是隨著道士做完法事,僅更的兩個人。(頁37)
寂靜的空間中,沒有了看表演的群眾,虛偽的面具也就不用再戴著了,於是兩相對照之下,原來部分的人都只是這場戲中臨時的一角,性情的真假原不在觀眾面前哭泣聲音的大小,盡管四叔的哭與主人公的不哭,但他們都是真性情的表現,也可能才是茫茫春夜裏真正心懷祖父的傷心人。
面對這些虛偽的表演,於是主人公開始對家人的感情之真假產生懷疑,但對於一個年幼的孩童來說,要如何才能找到判斷感情真假的標準呢?主人
12關於巴赫金的狂歡節理論,參見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頁189~223,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初版一刷。
公的方法是觀察他哭得傷心與否來與自己的平日印象相印證。於是,對各個家人在各種情況下的各種哭泣的描寫,就成了小說中敘述者重要的觀察與描述的對象。
在台灣的傳統喪葬禮俗中,「哭」原本即是整個喪葬儀式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這一方面是家人表達生離死別哀痛的實際情感所需;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是牽涉到喪葬禮儀中會影響到在世親人的平安與吉利的儀式,所以「哭」的時間、地點與方式都是倍受關注的。13於是當大姑媽一進門口便放聲大哭時,雖然主人公心中不忍,「鼻腔也酸溜溜的。」但事實上,這時祖父雖然昏迷但還未真的去逝,依照習俗是不宜在病人前哭泣的,14所以二叔才會挺身而出,勸她不要哭鬧。但是這樣的考量是基於禮俗,卻不見得能合於個人的情感,於是大姑媽怒斥:
嗬!我不能哭?我不能叫?阿爹才是你們的?哼!你們這般孝子,竟
然把阿爹逼成這個樣子!(頁30)
禮俗原是基於人情而設,但在某些時間、場合又反而因其僵化與制式而阻礙了人情的發展,究竟兩者之間熟輕熟重確實難有定論。對於一個天真年幼的孩童而言,雖然主觀上可能認為性情之真是比較重要的,但其個人的信心畢竟顯得不足,因為相對於大姑媽的哀號,主人公對於自己的不哭則感到相當不安:
不知為什麼,凝望著他那副慈祥而輕閉著雙眼的面龐,我流不出眼
淚:也許祖父死得太突然,或許死得太帄靜的緣故,使得我這曾經是
他最疼過的大孫子,卻沒能為他的死即刻上前去慟哭。他的死帶給我
以茫然、空虛和恐懼!啊,難道我是個不孝的孫子嗎?我是頂愛祖父
的呀!為什麼我偏偏擠不出淚來?我是很悲傷的呀!(頁31~32)
哭泣與悲傷之間,其實並不能完全畫上等號,但是在一般人的眼中,既無法真正得知別人的內心情感世界,就只能藉由外在的表情表現來作為判斷的依據了,因此主人公雖然明知自己對祖父的感情,但還是害怕自己的不哭泣讓別人視他為不孝,因為他正是這樣來看待其他親人的哭泣表現的:
13關於喪家大小在死者斷氣之後,何時才能慟哭的禮俗,可參見黃文博《台灣人的生死學》頁16~25,台北:常民文化,2000年8月初版一刷。
14洪進鋒《台灣民俗之旅》頁377,「哭路頭」條:「家中有人去逝,要召集家族在死者身邊大聲慟哭,但在還沒死去前,無論如何,都不能在病人前哭泣,以免意外刺激。」台北:武陵,1998年10月初版二刷。
三叔沒更哭,臉上也尋不出悲哀的表情。……難道他真的沒更一份兒
感情?(頁32~33)
至於二叔和三叔,還用我說嗎?他們壓根兒就不落淚,在他們臉上,
幾幾乎尋不出一絲兒的憂色,只盲目地履行著他們的職分,跟著大家
作著無謂的應付而已。(頁36~37)
相對於此,主人公為了與二叔、三叔的表現作對比,二次特別地強調了四叔感情的深刻與脆弱:
同樣是男人,四叔可就不同;祖父臨終時,他是唯一掉淚的男性,這
倒使我大大地感到意外。……他的悲歎比任何人都深刻,而最感人肺
腑。(頁33)
「孝男」,大家公認的,當然首推四叔了。我說「當然」,由於他是
唯獨掉淚嚎啕的男人。確乎,比起任何人,四叔的悲歎最為深刻;打
自回來,不知淌下多少眼淚。他的感情似乎特別脆弱,永遠掉不盡淚
兒似地。(頁36)
雖然有哭沒哭,原是個人情緒的表現方式不同,但卻被用來斷定一個人的孝親與否,這大概正是主人公與世俗人間同樣無法免除的「形式主義」之一吧!
故事的最後是出殯的葬列場景。相對於前面描寫喪葬儀式的陰黯氣氛,出殯的整個場景不但是「沒有風而異常憂悶的大熱天」,而且太陽像火球般地烘烤著大地,烈日使肌肉「好似騰沸的開水冒上熱氣兒」,真正是一個既熱且鬧的時空環境。在這個嘈雜又熱鬧的環境之中,人們不由自主地扮演著他們各自的角色,而隨著長長葬列的展開,人群雖然開始左右搖晃起來,隊伍向前開拔,但實際上葬列中的人們「閉上眼睛,暈暈糊糊地走著,蠻沒勁兒的。」就像葬儀中的魁儡一樣,被動地被驅趕於葬列的隊伍中,一切的行禮如儀,都只是「昨天,一位親戚的老翁,事先這樣子指點了我們的。」
然而在這被沉悶的空氣所瀰漫的整個葬列進行式中,在這嘈雜的、既熱又鬧的一刻,主人公卻突然發現,原來這一切原來與化裝遊行沒什麼兩樣,因為不論是父叔或是姑媽的打扮都是非常的怪異:
父叔們麻草履,頭頂纏了一捆草繩圈兒。女的是同樣的打扮,不過頭
上戴著的是角尖的三角白布,再加上姑媽手上的紅色燈籠―那不怪異
才怪呢?(頁39)
喪葬的服飾原是以非平常的服裝為區別,這是從文化心理的角度對喪服的了解與認知。但主人公的敘述就正是以不同於學者或閱聽人的角度,而是從孩童的角度來觀看,因此不但將這樣的服裝與銀幕中的日本武士古里古怪的裝束相類比,更將參與葬列的眾人都比作了臨時演員與小丑。一方面是從新視角觀察舊事物所帶來的新觀點,使讀者對喪服的意義重新加以體會與認識;另一方面也是藉由將化裝遊行與葬列隊伍的相對比敘述,對葬儀中眾人的虛偽面目進行反諷式的嘲弄。那些自以為能夠騙得了觀眾的「孝男」、「孝女」們,實際上都只是像童話故事中,被純真孩童戳破沒穿衣服真相的國王一樣:自以為聰明其實是為了愛面子、好虛名而自欺欺人,反而連孩童都比不上。
在這齣名為「葬列」戲的最後高潮一幕,是夾雜在化裝遊行隊伍裡的二嬸母和三嬸母的狂叫:
突然飄來一陣刺耳的狂叫,一緩一急的打自我背後發出。……搖撼著身子,她們倆哭得聲淚俱下,儼如蜂擁而來的兩股潮流,陣陣發響。
(頁39)
既是恐怖的幽靈,又是跳梁的小丑,兩者的結合則是人世間現實的醜惡面貌。在原本應是悶熱的烈日下,使人感到一陣對人性的寒意;在光明的太陽底下,展現出更為陰暗的角落;在喧鬧嘈雜的高潮聲中,讓人頓時失去了整個葬列隊伍的聲音,而只剩下二位嬸母瘋狂的舞步與搖撼的身子,故事的畫面瞬間凍結。然而面對這虛假而瘋狂的一切,主人公則表現出其經過一場生命儀式洗禮之後的靜觀態度,而只是將這一切視為是一場夢,一場「無從解釋的白晝夢。」因為他知道,不久,將「默默地……再也沒有人哭泣……。」也再也沒有人會去回想他所關心的祖父的一切,就如同葬列一樣,隨即消逝在街端。
三、〈守夜〉中慘白而無奈的嘲諷――家族爭產的真實醜
惡面貌
雖然同樣屬於張彥勳早期的作品,但相對於在〈葬列〉中面對死亡時的嚴肅、灰黯與些許的諷刺筆法,發表於1969年的〈守夜〉則是以另外一種近於反諷或嘲弄的手法來運用死亡這個事件,在小說中從頭到尾所漸漸地營造出恐怖懸疑的效果,使得故事的結尾帶有相當諧謔的黑色喜劇效果,是早期台灣文學中較少見的處理死亡題材的角度。
〈守夜〉敘述的是農民戴老頭兒為了揭穿他的兒子阿火與媳婦罔市試圖謀財害命的計謀,在鄰長羅大明的幫助之下,運用假死、裝鬼與錄音等方式,讓阿火與罔市的毒計無所遁形地被揭露出來。彭瑞金認為這篇小說寫的是「有田產的農民」的故事,而其主題則是在揭露「人性的貪婪」,15若與前段所討論的〈葬列〉一篇合而視之,更可以看出其對傳統家族中,成員間為爭產而不擇手段的真實醜惡、貪婪面貌的慘白而無奈的嘲諷。
觀察這篇小說中運用場景描寫來達到營造故事氣氛的效果,其中對於風與火的描述是很有特色而值得切入關注的重要焦點。在故事的一開始,冷風與孤燈的結合就開始塑造守夜靈堂的陰森感覺:
一陣冷風刮進來,戴老頭兒脚底旁的一盞燈火猛地擺盪,和著一堆燒紙錢的火焰,晃晃搖搖,盪得牆上的影子也跟著搖曳了;左左右右,曲曲彎彎的真像一群幽靈在陰府跳扭扭舞。
風中殘燭的景象映照在蒼白的牆上,幽靈的跳舞將場景帶到恐怖的死亡陰府中,強調的是陰森、肅殺的氣氛與冷凜的溫度。在原本即令人不寒而慄的靈堂中,再加上冷風的助威,更使故事在一開始即充滿詭譎的氣氛。
風與火的陰森作用在這一段的最後部分又起了一次效果,那是在女兒阿蘭與阿火夫婦對話之後。風不但大而且陰涼,再加上雨的濕潤,氣溫愈顯下降:
阿火起身踱去窗口邊,往窗外瞧去,只見風越刮越大,循著屋脊掠下,擊得玻璃乒乒乓乓作響。屋外是一片闇夜,月娘和星星早已躲起來了,遠處的林木和房子在風裏舞動著,像怪物。(頁76)
有風有雨再加上闇夜的響聲,這是屋外的恐怖效果,相對於屋外的怪物,在屋內則有死亡的陰影,雖然安靜,但這樣的安靜比屋外的聲音更令人害怕,尤其是對阿火夫婦來說,屋內所要面對的是被他們所謀害的對象,與這個無言的被害者獨處,無論如何心理上都很難平靜以對的。於是在狂風暴起的時候,剩罔市一個人在靈堂時,她看到了令她感到最害怕的一幕:
突然,一聲尖銳的喊叫起自她口中,阿火的老婆,她四肢朝天,整個人兒栽倒在地板上拼命掙扎。……阿爸的脚,好,好像在動。
15彭瑞金〈也是臺灣文學的旗手─試論張彥勳〉,原刊於1983年6月25日《臺灣時報》副刊,後收入彭瑞金主編《台灣作家全集?張彥勳集》頁301~310,台北:前衛,2000年3月初版四刷。
這時候並不是風雨最強的時候,但風雨的節奏似乎配合著故事情節的漸進,毛毛雨開始下降,罔市在恐懼的氣氛中第一次認為自己看到了死屍的移動,使整個場景頓時掀起一陣緊張,雖然理性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但對於作賊心虛的阿火夫婦而言,這卻是心理上不可承受之重。
從故事一開始,戴老頭兒就已經是客廳裡的一具死屍了,表面上他的死可以說是相當突然、來不及作任何的喪葬準備,以至於「連遠行黃泉的一套壽衣也來不及趕上穿。」這樣的敘述一方面強調戴老頭兒死得突然,另一方面卻也顯露出這一起葬禮其實存在著不合禮、不合理的地方,這正是作為後來故事發展的重要訊息與伏筆所在。
在台灣一般民間傳統的喪葬習俗中,一般壽終正寢者的壽衣是以「五套」為主,即便非壽終正寢如戴老頭兒被認為是喝毒藥的死於非命者,理論上至少也還要有三套壽衣才像樣子,16似戴老頭兒這樣的有錢人家竟然會一套都來不及穿,除了真的非常突然不得已的情況外,也暗示著處理喪葬事宜的家人的不用心,或者另一種可能是─從後文得知─這一切也是戴老頭兒的設計與安排,當他他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靈堂中時,實際上對靈堂中發生的一切嘹若指掌,甚至透過羅鄰長作了某種程度的操控。
在戴老頭兒的靈堂上,女兒阿蘭身穿孝服,蹲在戴老頭兒脚旁邊號泣邊燒紙錢,從民俗來看,這件事本來應該是由媳婦罔市來從事才對,交由女兒來做當然也不是不可以,但對照著罔市在旁邊說著風涼話,更加深了讀者對這一家人之間情感的好奇心,面對親人的離奇死亡,身為長子與長媳的阿火夫婦竟然能如此平靜地說出:
也許阿爸的歲壽該終,要不然那會死得這麼突然呢?……是啊,妳阿
兄講得對,一切都是命運,怨歎無用啦。
在親人被認定死亡之後,面對永別的事實,有感情的親人總是難以承認,也不願意去相信,最傷心最悲痛的莫過於此時,但身為親生獨子的阿火竟然表現得如此平淡,就像是早已有所心理準備一般,確實惹人疑竇。
於是作者藉著阿蘭之口,對戴老頭兒的死提出質疑:
阿火悵然地:「他竟把殺鼠藥當作胃散吃了。」「阿兄,你也更責任,怎麼不把它好好收起來呢?」(頁75)
面對這樣直接的質疑,阿火無言以對,反而是罔市搶著回答:
16黃文博《台灣人的生死學》頁18,台北:常民文化,2000年8月初版一刷。
是我收起來的,放在最高層的擱板上,誰知,阿爸卻把它拿來吃了。
(頁75)
這種說詞無疑在事情發生之前即預先準完成,質疑被表面上合理的說詞暫時掩蓋。但這樣掩蓋的說法,在阿火夫婦二人不斷的被心理上的恐怖氣氛影響之下,故事隨著阿火的睡著,罔市第二次被自己心裏的鬼形驚嚇:
抽個冷子,又是一聲尖叫,……罔市緊緊摟住阿火,心驚肉跳的喊。
阿火被鬧得也發抖了,渾身酸軟無力,幾乎站不穩。
結果發現原來只是羅鄰長的來到,一切都是自己嚇自己,「白天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在羅鄰長離去之後,場景再度陷入先前的死寂,但屋外的風聲依舊刮刮作響。在錚錚雨聲中,暴風雨來臨,那代表最後一線光明的戴老頭兒脚底下的油燈也被風吹熄了,整個靈堂成為真正的黑暗所在,在這黑暗與死亡最接近的地方,阿火夫婦看到了戴老頭兒屍身再次的移動,在不知不覺間親口說出了自己謀財弑親的秘密:
「不用看,阿爸喝醉酒吃錯了藥,全村誰不知道?」「可是,阿火,你別忘了那是我們的安排,我要你把阿爸的胃散偷偷換過來……」
原來這個原本以為是意外的事故,竟然是一件為產弑親的天倫悲劇。當謎底揭曉之後,故事迅速進展,阿蘭也聽到了阿火夫婦的對話而出面興師問罪,卻反被阿火夫婦施以暴力,而就在雙方打得你死我活之際,阿火的夢魘真的出現了,戴老頭兒在「嘻嘻嘻嘻─」的笑聲中還魂了。這真是全篇情節的最高潮。當戴老頭兒第一次以鬼的姿態出現時,很容易就使阿火夫婦的心防完全潰堤,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當戴老頭兒表明自己沒死時,阿火夫婦又試圖否認一切的犯行。於是戴老頭兒正式攤牌,拿出最有力的證據:
羅大明應聲走去靈桌前,拉開抽屜,取出一件東西―是一架錄音機。
「放出來聽聽看!」戴老頭兒嚴肅地命令著說。羅大明熟練地操作了一下,錄音機裏跑出來一段對話―(頁90)
這正是阿火夫婦犯行的自白,再也沒有狡辯的餘地了。故事至此,留下垂頭喪氣的阿火,與計畫得售但心機同樣可怕的戴老頭兒等人。
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一方面交互運用喪葬場景描寫與人物的對話,使簡單的情節在詳細的場景敘述中得到舖展,人物雖然不多,關係也很單純,但放在生動的景物描寫之中,經由簡短的對話緩緩推進情節的發展,在漸進式
的風雨聲中,成功地一步步營造出靈堂中守夜的死亡恐怖效果另一方面,作者運用懸疑的技巧,由於作者有意識地限制了敘述者的視角,讓讀者自始至終都只能隨著被限制的視角移動,由於這樣的限制造成了讀者好奇心的一步步加強。雖然一開始也是隨著敘述者的角度來觀察,認為戴老頭確實是死了,因此對於靈堂中所發生的風吹草動,亦會同樣感到恐懼與不解。但隨著故事的進展,讀者終能在故事的敘述縫隙中遇到某些現象,一方面雖有疑點卻受限於敘述者的敘述,始終只能與阿火夫婦一同守夜歷險,另一方面則在真相大白之後,更能得到疑惑頓解的快感。這正是作者運用高明的敘述技巧所達成的文學效果。
四、結論――無言的結局
從人生的歷程來看,死亡既是人人所不能免,卻又是眾人所共諱,對於死亡的恐懼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之一,然則如何去面對它、看待它終是人生中重要的一環。在〈葬列〉中,張彥勳透過一個小孩子的眼睛,不但紀錄了一個客觀的殯葬處理過程、一個主觀的心靈成長歷程,更讓讀者藉由一幕幕的戲劇畫面看到一齣真實的人性諷刺劇,對於人世界現實的真/假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與體悟。而在〈守夜〉裏,經由一個表裏不一─表面為自然死亡,實則為謀殺或反設計─的死亡事件,更使我們凜於即使親如父子,為了現實的利益仍有可能發生如此可怕的猜疑與恐怖的謀殺。類似這些作者之運用死亡題材來進行他對於人性不信任之控訴,其客觀場景描述之真實感不但令人不忍逼視,再加上故事中的事件都鎖定在家產與利益的爭執上,更令人相信張彥勳對於這樣的應是有其相當深的感觸與實際的傷痕體驗,才能如此成功地達到撼動人心的效果。
從文學技巧的成就來看兩篇小說,其篇幅都不長,人物也不多且關係非常單純,情節都呈單線發展而不複雜,從故事所經驗的時間跨度來看也都相當簡短,〈守夜〉更是發生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的事件。在這麼短而單純的情節之中,張彥勳之所以能成功地營造氣氛、揭露虛偽並諷刺現實,最重要的還是他對場景描寫運用的成功。不論是〈葬列〉中葬列與化裝遊行的對比、哭與不哭的各種面目或是〈守夜〉中運用對風與火的敘述來營造氣氛、運用懸疑的技巧或是對話與場景的交互出現所造成的語言空隙,都與張彥勳寫景功力高深有關,確實有其值得肯定的文學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