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者》中费里斯的逃离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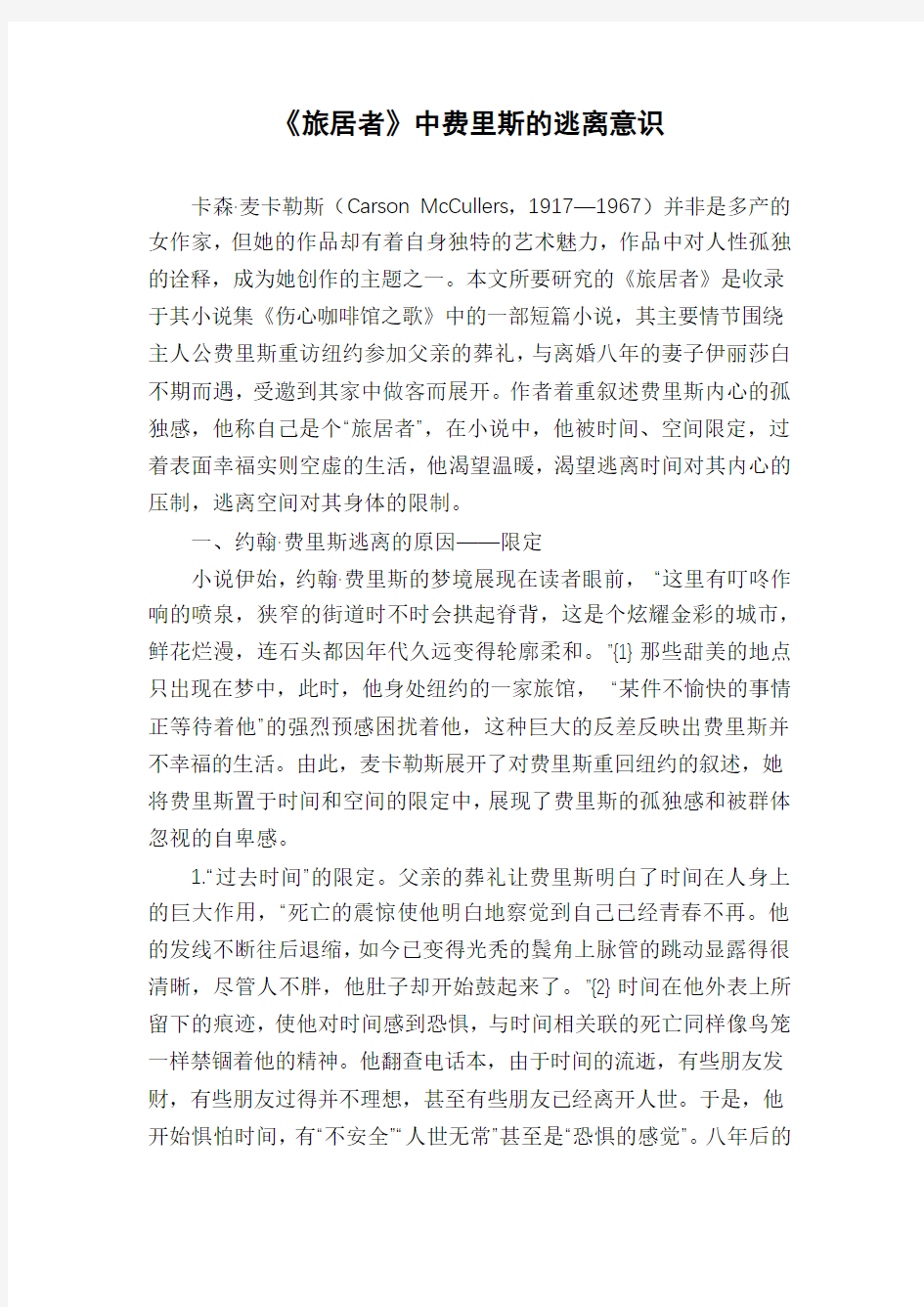

《旅居者》中费里斯的逃离意识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并非是多产的女作家,但她的作品却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中对人性孤独的诠释,成为她创作的主题之一。本文所要研究的《旅居者》是收录于其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其主要情节围绕主人公费里斯重访纽约参加父亲的葬礼,与离婚八年的妻子伊丽莎白不期而遇,受邀到其家中做客而展开。作者着重叙述费里斯内心的孤独感,他称自己是个“旅居者”,在小说中,他被时间、空间限定,过着表面幸福实则空虚的生活,他渴望温暖,渴望逃离时间对其内心的压制,逃离空间对其身体的限制。
一、约翰·费里斯逃离的原因——限定
小说伊始,约翰·费里斯的梦境展现在读者眼前,“这里有叮咚作响的喷泉,狭窄的街道时不时会拱起脊背,这是个炫耀金彩的城市,鲜花烂漫,连石头都因年代久远变得轮廓柔和。”{1}那些甜美的地点只出现在梦中,此时,他身处纽约的一家旅馆,“某件不愉快的事情正等待着他”的强烈预感困扰着他,这种巨大的反差反映出费里斯并不幸福的生活。由此,麦卡勒斯展开了对费里斯重回纽约的叙述,她将费里斯置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中,展现了费里斯的孤独感和被群体忽视的自卑感。
1.“过去时间”的限定。父亲的葬礼让费里斯明白了时间在人身上的巨大作用,“死亡的震惊使他明白地察觉到自己已经青春不再。他的发线不断往后退缩,如今已变得光秃的鬓角上脉管的跳动显露得很清晰,尽管人不胖,他肚子却开始鼓起来了。”{2}时间在他外表上所留下的痕迹,使他对时间感到恐惧,与时间相关联的死亡同样像鸟笼一样禁锢着他的精神。他翻查电话本,由于时间的流逝,有些朋友发财,有些朋友过得并不理想,甚至有些朋友已经离开人世。于是,他开始惧怕时间,有“不安全”“人世无常”甚至是“恐惧的感觉”。八年后的
此时,与前妻伊丽莎白的偶遇了加深了时间对费里斯的限定,以至于在小说大部分的时间中,费里斯都活在“过去的世界”,八年后的费里斯对前妻伊丽莎白仍旧有感觉,“心会起了一阵强烈的颤动”,接着“又会有那样一种轻率与优雅的感情”。接下来,费里斯拼命追赶伊丽莎白,此时,伊丽莎白成为费里斯对过去时间追逐的对象,伊丽莎白正是费里斯过去时间的代表,费里斯放不下过去,无法接受时间对其自身的改变,对伊丽莎白的不断追寻正是对过去时间的追寻。
从小说开始到对伊丽莎白钢琴曲的叙述,费里斯由毫无察觉地被过去时间限定达到了彻底被过去时间限定,他的情绪也由开始仅有的一丝预感“不愉快的事情”发展到陷入深深的孤独、痛苦中。伊丽莎白的出现,成为他对过去时间追逐的主要目标,从追寻伊丽莎白的影子到见到伊丽莎白本人,费里斯内心的孤独感、失落感越发强烈。由此,当费里斯看到伊丽莎白一家和睦的生活,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嫉妒,这样的心理具体体现在他对伊丽莎白一家人的谎言中。叙述者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客观直白地指出了费里斯在撒谎,这无疑告诉我们过去时间对费里斯的限定使他的生活非常不愉快。小说尾声,费里斯仍未摆脱过去时间的限定。
2.家庭物理空间的限定。家庭成员的活动涉及到的与情感互动相关的各种实在物构成的地理场域以及想象空间,包括家庭物理空间、家庭心理空间、家庭行动空间等。{3}《旅居者》叙述的人物主要活动场所即伊丽莎白的家。小说的主题,表达的基本思想,主要是通过伊丽莎白的家来体现的。旅居者费里斯行为地点的转移,在纽约生活的叙述,主要场所仍旧是在伊丽莎白的家。因此,小说的主要活动地点是伊丽莎白的家,即上文所讲的家庭物理空间。正如小说中费里斯自己所言,应该称他为“旅居者”而不是“移民”,他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生活漂泊不定,而在不定的生活中,他时刻受到空间的限定,费里斯受伊丽莎白的邀请来对方家里做客,在此叙述过程中,伊丽莎白的家成为限定费里斯的具体空间对象。哈贝马斯认为,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
所以,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地皮的有限性,现代家庭的物理生活空间比旧时呈现出更加封闭的状态。不论家庭物理空间的形式怎样变化,其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性质没有改变。家庭物理空间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可以说这是公共空间的特殊部分。{4}伊丽莎白的家正是由伊丽莎白、丈夫巴莱、两个孩子构成的公共空间。“一幢楼前有雨棚和看门人的住宅,她的那套公寓是在七层。”“雨棚”“看门人的住宅”将公寓围住,对外部的一切产生排斥感。费里斯初到伊丽莎白家的时候,一切都感到不自在,孩子不在时他找不到话说,最后在酒的帮助下才勉强可以找到话题聊。同时,内部的家族成员在限定空间内不容易看到外面的世界,伊丽莎白的儿子比利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长大,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不再做家中的孩子。家庭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具有内部开放性,仅对家庭所构成的人员开放,因此,伊丽莎白一家并不会感到不自在,而费里斯在他们眼中是陌生人,公共空间并不为他开放,相对于费里斯来说家庭公共空间是私人空间。当伊丽莎白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谈话时,“费里斯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旁观者——巴莱一家人中的一个闯入者。他为什么要来呢?他在受苦。他自己的生活似乎过得如此孤单,活像一根脆弱的支柱,几乎没能撑起岁月的残骸中的任何东西。他觉得在这家人的房间里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5}。伊丽莎白一家的家庭公共领域将费里斯限定,这个封闭的空间使他产生封闭感、陌生感,将其内心的孤独重新唤起并加深。此后,费里斯将自己定义为“旅居者”,与前妻见面后,看到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完美和谐,不禁又使他想到自身漂泊的孤独感,父亲的离开,让他看到时间对人的摧毁。在整个受邀过程中,他始终处在内心孤独的煎熬中,他既不能进入伊丽莎白一家设定的家庭公共领域,更不能闯入家庭成员的私人领域。他被称为“闯入者”限定在别人的家庭空间内。这次的孤独造访,消解了费里斯的心,他明白自己需要一个稳定的家,一种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离开伊丽莎白一家的家庭公共领域后,费里斯回到巴黎,仍旧处
于家庭公共空间的限定中,无序又混乱。与此同时,时间永远都在控制着他,城市的更迭使他成为“旅居者”,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下,他生活在孤独和悲伤中,这样的生存状态一直延续。
二、约翰·费里斯对限定的逃离
上文中分析出费里斯在小说中受到两种因素,即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活在过去”的内心使费里斯一直受到过去时间的限定,从而感受到现在生活的漂泊与痛苦;特定空间对他的限制使得他对自身的孤单生活更加绝望。然而,他并非甘于忍受双重因素的限定,小说中也表现出他对以上两种因素的反抗与逃离。
费里斯所转移的空间地理位置:佐治亚州——纽约——巴黎,正是他逃离的三个阶段,正如小说的名字“旅居者”,对空间环境的不断转换正是费里斯逃离方式的一种。从巴黎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他开始寻找过去的朋友,企图逃离目前的时间限定;在纽约,前妻伊丽莎白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令他产生了嫉妒之心,空间的限定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不愿再做一个“闯入者”,而是渴望安稳的生活,因此他又从这个限定空间中逃离,想追寻新的生活;最后到达巴黎后,他企图通过自己的真心得到与燕妮安稳的生活,可是他的内心仍旧陷入绝望与痛苦中。小说中费里斯对空间的逃离主要集中在前妻伊丽莎白的公寓中,对费里斯这个“闯入者”而言,公寓意味着对人的禁锢、束缚,这与他的“旅居者”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当他看到伊丽莎白生活美满的时候,瞬间感觉自己成为了局外人,想要逃离。通过费里斯的视角,麦卡勒斯将空间的限定与费里斯的逃离意识呈现出来,展现了空间对人性自由造成的局限。
费里斯逃离的另一种方式是精神脱离身体而趋向自由。小说以费里斯的梦境为开篇,建构了一个自由、独立的世界,“这是个炫耀金彩的城市,鲜花烂漫”,值得注意的是,他醒来后的世界并非如梦中的世界,梦中对自由的建构正是费里斯精神逃离的表现。之后费里斯被家庭空间限定的同时,精神的逃离时刻出现在他脑海中,与伊丽莎白再相见,伊丽莎白已经再嫁,并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这与费里斯内心的
孤寂形成了强烈反差。此时,他的精神逃离了此刻的孤寂,“忆起那些年月里的事”,“预先未曾料到的回忆使费里斯一下子回不过神来”,精神逃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费里斯的限定,精神的游离使得费里斯暂时摆脱了孤独和痛苦。
麦卡勒斯的《旅居者》充分体现了空间和时间对人的限定,同时也体现了人对限定的反抗与逃离。特定的家庭空间的外表下掩盖着的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对外界突然闯入的排斥,同时也表明麦卡勒斯对时间的质疑。■
■
{1}{2}{5} [美]卡森·麦卡勒斯著,李文俊译:《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11页,第112页,第117页。
{3}{4} 戴烽:《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青海社会科学》2021年11月第6期,第32页,第3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