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小说的叙事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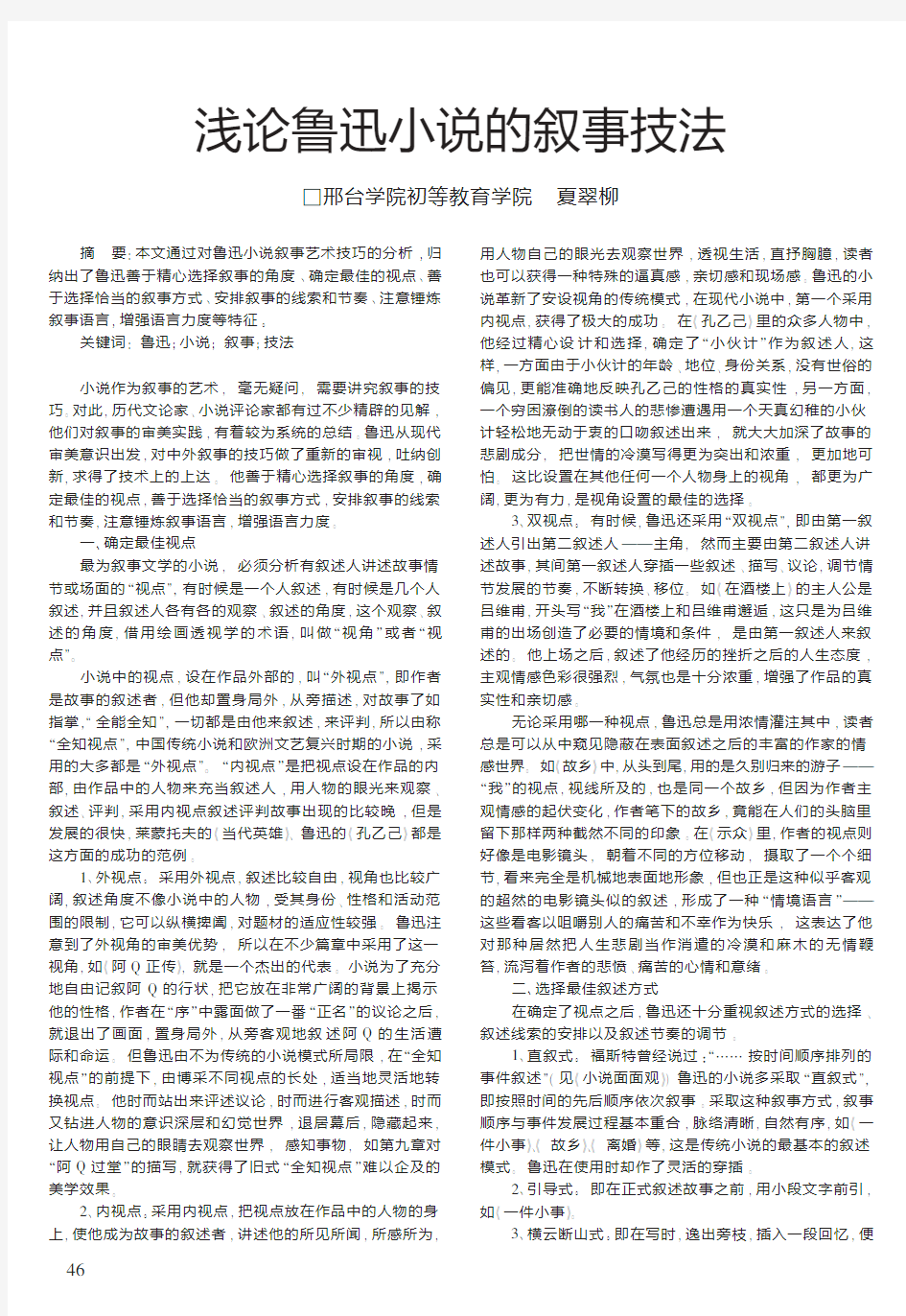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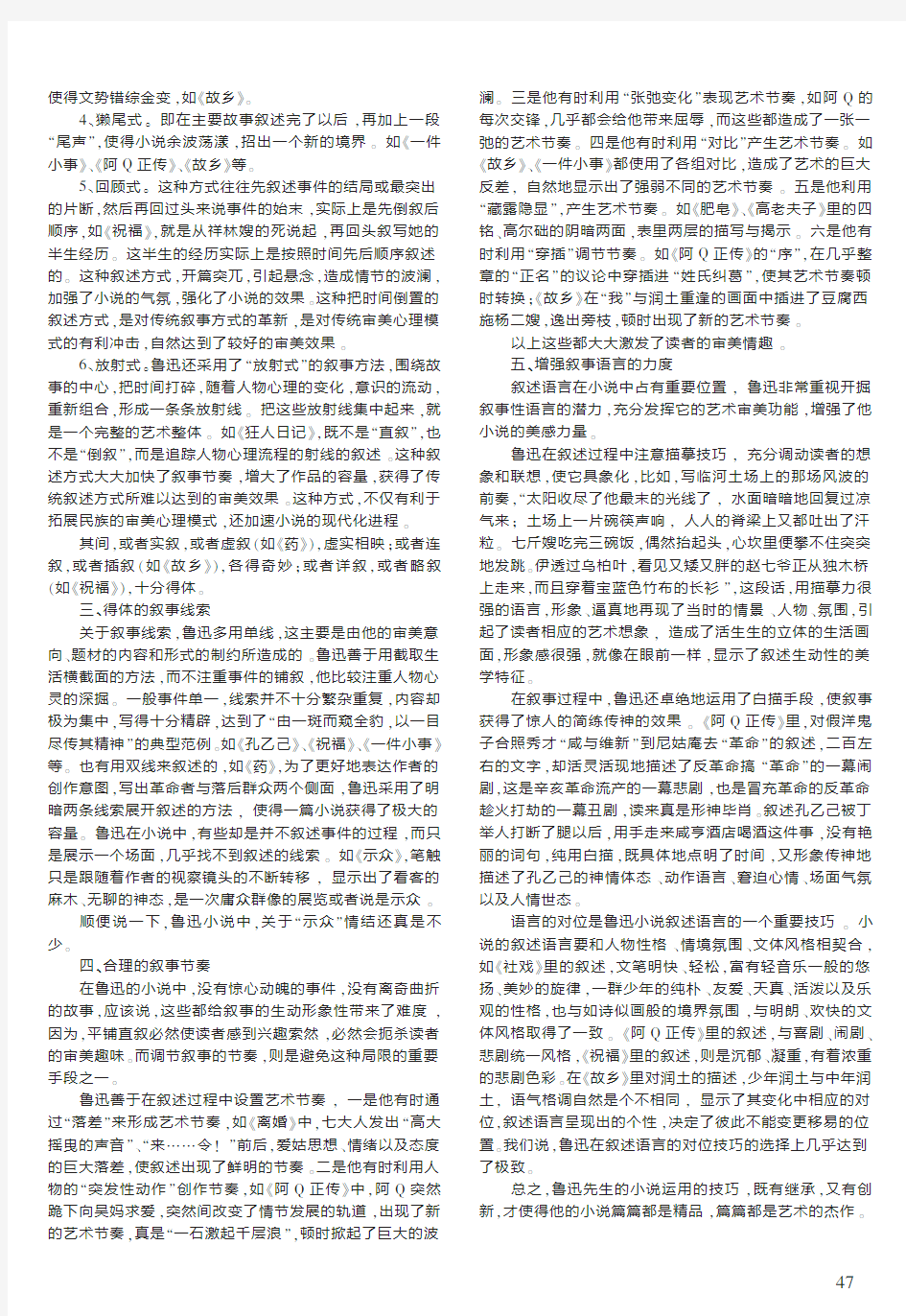
摘要: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叙事艺术技巧的分析,归纳出了鲁迅善于精心选择叙事的角度、确定最佳的视点、善于选择恰当的叙事方式、安排叙事的线索和节奏、注意锤炼叙事语言,增强语言力度等特征。
关键词:鲁迅;小说;叙事;技法
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毫无疑问,需要讲究叙事的技巧。对此,历代文论家、小说评论家都有过不少精辟的见解,他们对叙事的审美实践,有着较为系统的总结。鲁迅从现代审美意识出发,对中外叙事的技巧做了重新的审视,吐纳创新,求得了技术上的上达。他善于精心选择叙事的角度,确定最佳的视点,善于选择恰当的叙事方式,安排叙事的线索和节奏,注意锤炼叙事语言,增强语言力度。
一、确定最佳视点
最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必须分析有叙述人讲述故事情节或场面的“视点”,有时候是一个人叙述,有时候是几个人叙述,并且叙述人各有各的观察、叙述的角度,这个观察、叙述的角度,借用绘画透视学的术语,叫做“视角”或者“视点”。
小说中的视点,设在作品外部的,叫“外视点”,即作者是故事的叙述者,但他却置身局外,从旁描述,对故事了如指掌,“全能全知”,一切都是由他来叙述,来评判,所以由称“全知视点”,中国传统小说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采用的大多都是“外视点”。“内视点”是把视点设在作品的内部,由作品中的人物来充当叙述人,用人物的眼光来观察、叙述、评判,采用内视点叙述评判故事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发展的很快,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鲁迅的《孔乙己》都是这方面的成功的范例。
1、外视点。采用外视点,叙述比较自由,视角也比较广阔,叙述角度不像小说中的人物,受其身份、性格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它可以纵横捭阖,对题材的适应性较强。鲁迅注意到了外视角的审美优势,所以在不少篇章中采用了这一视角,如《阿Q正传》,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小说为了充分地自由记叙阿Q的行状,把它放在非常广阔的背景上揭示他的性格,作者在“序”中露面做了一番“正名”的议论之后,就退出了画面,置身局外,从旁客观地叙述阿Q的生活遭际和命运。但鲁迅由不为传统的小说模式所局限,在“全知视点”的前提下,由博采不同视点的长处,适当地灵活地转换视点。他时而站出来评述议论,时而进行客观描述,时而又钻进人物的意识深层和幻觉世界,退居幕后,隐藏起来,让人物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感知事物,如第九章对“阿Q过堂”的描写,就获得了旧式“全知视点”难以企及的美学效果。
2、内视点。采用内视点,把视点放在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上,使他成为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为,用人物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世界,透视生活,直抒胸臆,读者也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逼真感,亲切感和现场感。鲁迅的小说革新了安设视角的传统模式,在现代小说中,第一个采用内视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孔乙己》里的众多人物中,他经过精心设计和选择,确定了“小伙计”作为叙述人,这样,一方面由于小伙计的年龄、地位、身份关系,没有世俗的偏见,更能准确地反映孔乙己的性格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一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的悲惨遭遇用一个天真幻稚的小伙计轻松地无动于衷的口吻叙述出来,就大大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成分,把世情的冷漠写得更为突出和浓重,更加地可怕。这比设置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视角,都更为广阔,更为有力,是视角设置的最佳的选择。
3、双视点。有时候,鲁迅还采用“双视点”,即由第一叙述人引出第二叙述人——
—主角,然而主要由第二叙述人讲述故事,其间第一叙述人穿插一些叙述、描写、议论,调节情节发展的节奏,不断转换、移位。如《在酒楼上》的主人公是吕维甫,开头写“我”在酒楼上和吕维甫邂逅,这只是为吕维甫的出场创造了必要的情境和条件,是由第一叙述人来叙述的。他上场之后,叙述了他经历的挫折之后的人生态度,主观情感色彩很强烈,气氛也是十分浓重,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亲切感。
无论采用哪一种视点,鲁迅总是用浓情灌注其中,读者总是可以从中窥见隐蔽在表面叙述之后的丰富的作家的情感世界。如《故乡》中,从头到尾,用的是久别归来的游子——
—“我”的视点,视线所及的,也是同一个故乡,但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起伏变化,作者笔下的故乡,竟能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那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在《示众》里,作者的视点则好像是电影镜头,朝着不同的方位移动,摄取了一个个细节,看来完全是机械地表面地形象,但也正是这种似乎客观的超然的电影镜头似的叙述,形成了一种“情境语言”——
—这些看客以咀嚼别人的痛苦和不幸作为快乐,这表达了他对那种居然把人生悲剧当作消遣的冷漠和麻木的无情鞭笞,流泻着作者的悲愤、痛苦的心情和意绪。
二、选择最佳叙述方式
在确定了视点之后,鲁迅还十分重视叙述方式的选择、叙述线索的安排以及叙述节奏的调节。
1、直叙式。福斯特曾经说过:“……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叙述”(见《小说面面观》)鲁迅的小说多采取“直叙式”,即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叙事。采取这种叙事方式,叙事顺序与事件发展过程基本重合,脉络清晰,自然有序,如《一件小事》、《故乡》、《离婚》等,这是传统小说的最基本的叙述模式。鲁迅在使用时却作了灵活的穿插。
2、引导式。即在正式叙述故事之前,用小段文字前引,如《一件小事》。
3、横云断山式。即在写时,逸出旁枝,插入一段回忆,便
浅论鲁迅小说的叙事技法
□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夏翠柳
46
使得文势错综金变,如《故乡》。
4、獭尾式。即在主要故事叙述完了以后,再加上一段“尾声”,使得小说余波荡漾,招出一个新的境界。如《一件小事》、《阿Q正传》、《故乡》等。
5、回顾式。这种方式往往先叙述事件的结局或最突出的片断,然后再回过头来说事件的始末,实际上是先倒叙后顺序,如《祝福》,就是从祥林嫂的死说起,再回头叙写她的半生经历。这半生的经历实际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的。这种叙述方式,开篇突兀,引起悬念,造成情节的波澜,加强了小说的气氛,强化了小说的效果。这种把时间倒置的叙述方式,是对传统叙事方式的革新,是对传统审美心理模式的有利冲击,自然达到了较好的审美效果。
6、放射式。鲁迅还采用了“放射式”的叙事方法,围绕故事的中心,把时间打碎,随着人物心理的变化,意识的流动,重新组合,形成一条条放射线。把这些放射线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如《狂人日记》,既不是“直叙”,也不是“倒叙”,而是追踪人物心理流程的射线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大大加快了叙事节奏,增大了作品的容量,获得了传统叙述方式所难以达到的审美效果。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拓展民族的审美心理模式,还加速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其间,或者实叙,或者虚叙(如《药》),虚实相映;或者连叙,或者插叙(如《故乡》),各得奇妙;或者详叙,或者略叙(如《祝福》),十分得体。
三、得体的叙事线索
关于叙事线索,鲁迅多用单线,这主要是由他的审美意向、题材的内容和形式的制约所造成的。鲁迅善于用截取生活横截面的方法,而不注重事件的铺叙,他比较注重人物心灵的深掘。一般事件单一,线索并不十分繁杂重复,内容却极为集中,写得十分精辟,达到了“由一斑而窥全豹,以一目尽传其精神”的典型范例。如《孔乙己》、《祝福》、《一件小事》等。也有用双线来叙述的,如《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写出革命者与落后群众两个侧面,鲁迅采用了明暗两条线索展开叙述的方法,使得一篇小说获得了极大的容量。鲁迅在小说中,有些却是并不叙述事件的过程,而只是展示一个场面,几乎找不到叙述的线索。如《示众》,笔触只是跟随着作者的视察镜头的不断转移,显示出了看客的麻木、无聊的神态,是一次庸众群像的展览或者说是示众。
顺便说一下,鲁迅小说中,关于“示众”情结还真是不少。
四、合理的叙事节奏
在鲁迅的小说中,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应该说,这些都给叙事的生动形象性带来了难度,因为,平铺直叙必然使读者感到兴趣索然,必然会扼杀读者的审美趣味。而调节叙事的节奏,则是避免这种局限的重要手段之一。
鲁迅善于在叙述过程中设置艺术节奏,一是他有时通过“落差”来形成艺术节奏,如《离婚》中,七大人发出“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令!”前后,爱姑思想、情绪以及态度的巨大落差,使叙述出现了鲜明的节奏。二是他有时利用人物的“突发性动作”创作节奏,如《阿Q正传》中,阿Q突然跪下向吴妈求爱,突然间改变了情节发展的轨道,出现了新的艺术节奏,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三是他有时利用“张弛变化”表现艺术节奏,如阿Q的每次交锋,几乎都会给他带来屈辱,而这些都造成了一张一弛的艺术节奏。四是他有时利用“对比”产生艺术节奏。如《故乡》、《一件小事》都使用了各组对比,造成了艺术的巨大反差,自然地显示出了强弱不同的艺术节奏。五是他利用“藏露隐显”,产生艺术节奏。如《肥皂》、《高老夫子》里的四铭、高尔础的阴暗两面,表里两层的描写与揭示。六是他有时利用“穿插”调节节奏。如《阿Q正传》的“序”,在几乎整章的“正名”的议论中穿插进“姓氏纠葛”,使其艺术节奏顿时转换;《故乡》在“我”与润土重逢的画面中插进了豆腐西施杨二嫂,逸出旁枝,顿时出现了新的艺术节奏。
以上这些都大大激发了读者的审美情趣。
五、增强叙事语言的力度
叙述语言在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鲁迅非常重视开掘叙事性语言的潜力,充分发挥它的艺术审美功能,增强了他小说的美感力量。
鲁迅在叙述过程中注意描摹技巧,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使它具象化,比如,写临河土场上的那场风波的前奏,“太阳收尽了他最末的光线了,水面暗暗地回复过凉气来;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了汗粒。七斤嫂吃完三碗饭,偶然抬起头,心坎里便攀不住突突地发跳。伊透过乌柏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这段话,用描摹力很强的语言,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人物、氛围,引起了读者相应的艺术想象,造成了活生生的立体的生活画面,形象感很强,就像在眼前一样,显示了叙述生动性的美学特征。
在叙事过程中,鲁迅还卓绝地运用了白描手段,使叙事获得了惊人的简练传神的效果。《阿Q正传》里,对假洋鬼子合照秀才“咸与维新”到尼姑庵去“革命”的叙述,二百左右的文字,却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反革命搞“革命”的一幕闹剧,这是辛亥革命流产的一幕悲剧,也是冒充革命的反革命趁火打劫的一幕丑剧,读来真是形神毕肖。叙述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以后,用手走来咸亨酒店喝酒这件事,没有艳丽的词句,纯用白描,既具体地点明了时间,又形象传神地描述了孔乙己的神情体态、动作语言、窘迫心情、场面气氛以及人情世态。
语言的对位是鲁迅小说叙述语言的一个重要技巧。小说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性格、情境氛围、文体风格相契合,如《社戏》里的叙述,文笔明快、轻松,富有轻音乐一般的悠扬、美妙的旋律,一群少年的纯朴、友爱、天真、活泼以及乐观的性格,也与如诗似画般的境界氛围,与明朗、欢快的文体风格取得了一致。《阿Q正传》里的叙述,与喜剧、闹剧、悲剧统一风格,《祝福》里的叙述,则是沉郁、凝重,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在《故乡》里对润土的描述,少年润土与中年润土,语气格调自然是个不相同,显示了其变化中相应的对位,叙述语言呈现出的个性,决定了彼此不能变更移易的位置。我们说,鲁迅在叙述语言的对位技巧的选择上几乎达到了极致。
总之,鲁迅先生的小说运用的技巧,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才使得他的小说篇篇都是精品,篇篇都是艺术的杰作。
47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毕业论文 题目: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姓名:刘玲 学号:200630214042 系别:汉语言文学 年级:2006级 指导老师:何兵 完成时间:2009年3月28 浅析梁晓声小说《人间烟火》的叙事艺术 [摘要]:梁晓声在叙事技巧的使用上是极为娴熟的,我们可以通过对他的代表作《人间烟火》为例进行分析从而获得证明。在《人间烟火》中作者就成功地运用了倒叙,张弛有度等叙事手法。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
艺术效果,其作品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给读者韵味无穷的美感享受。读者还可以用这种手法去阅读更多的作品和创作。 [关键词]:梁晓声;倒叙;张弛有度;娴熟 正文:梁晓声1940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山东荣城。现为中国语言大学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自今作品逾千万字。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很高,同时他还是中国当代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其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1)《人间烟火》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作品写于八十年代初期,其作品带有了那个时代的新鲜气息,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身心变化和城市风貌。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尤其是倒叙和张弛有度等叙事技巧的运用上的应用极为娴熟。下面将作详细地分析,以求对作者类似的作品在叙事艺术的把握上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 一、倒叙的运用上 那什么是倒叙呢?倒叙是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重要、最突出的片段提到文章的前边,然后再从事
件的开头按事情原来的发展顺序进行叙述的方法(2)。从这个定义看,文中有两个地方很明显的运用了倒叙。 文章的开篇就写到主人公之一葛全德,他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光华街上走着,作为一个建筑工人的他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眼前的一切,心情极其的复杂。可看到这里读者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心情如此郁闷,以至于会引发联想,主人公怎么会一个人就这样沿着一条街漫无目的的游荡呢,天色已晚,可是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 一直到了作品第六页,才开始讲他如此这般游荡的原因,也进入了事件的原由,他同情施工队这些普通家庭出身,本人却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小伙子们,他不忍看见他们受这样的欺负所以就因工资问题和同事(西血鬼)们打架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到作品第一部分结束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开始葛全德的所作所为是为什么,心中的一个个迷团才得以一一解开。那作者这样叙述的目的是什么呢?采用倒叙的方法的作用是,增强文章的生动性,使文章产生悬念,更能引人入胜,同时也可以避免叙述的呆板和结构的单调(1)。 作品将葛全德在光华街上的行为放到文章的开端是很少见的,首先,人们会想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冷清的街上瞎逛,却连一点回家的意思都没有,从而使文章产生了悬念。其次、把打架后的反思和状况放在前面,使读者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内心略见一斑,一个活生生的葛全德仿佛就站在我们
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每个作家者有独特的关键词,鲁迅也例外。鲁迅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有暗藏在他的两篇重要的序言之中:《<呐喊>自序》(1922)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阅读两篇序言,我们发现由这些关键词:寂寞、忘却、死、沉默、隔膜、无聊、麻木等组成了一个意义错综的网络。在其中,死是一个中心纽结。可以说,“死”之于鲁迅,犹如“审判”之于卡夫卡,“瘫痪”之于乔伊斯,是关键词关键词。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个词被溶解和浓缩,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这些词围绕着它进行向心——离心的旋转或扩延。 一、反讽是解读鲁迅关键词的一个最佳出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序言本身就是两个反讽式的陈述。词语互相说明着有不断破坏着彼此的词典意义,以至于它们超越了序言的散文性的实用意图而具有诗的价值。鲁迅曾说自己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我们不妨把他的话转化一下:他不肯相信某个辞的字面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好名称的词的字面意义。如果说,反讽带有“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性质的话,那么,鲁迅本人的怀疑气质和反讽的性质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换言之,他的气质构成了他的文体的始基,造就了反讽式的叙述策略。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反讽的杰出运用。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认为,反语(即反讽)是鲁迅小说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在这个大的语境之内,鲁迅的词语必然“充满意义”或同时并蓄数种意义。反讽离字面意义最远的距离最偏的角度突破常用语言
的规约,赋予词一种敏感和适应能力,授予词性的奇异和含混。 借助反讽,鲁迅成功地抵抗的伪抒情主义。伪抒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病态发展。五四时期流行的抒情小说,有很多大用大量空洞华丽的同义词镀饰出来的“半成品”。在这样的作品里,词语只能承担扁平的意义,而在鲁迅这里,词语经过反讽的“淬火”工序之后,经的起“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的考验”。 二、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死 死亡。 鲁迅一直被死亡意念所缠绕。他一生都在感受触摸和思考死亡——它的恐怖、它的寒冷和它的无所不在。他在死亡的阴影下成长——祖父因为科考贿赂而被判了“死缓”,父亲忧愤成病,久医不愈。于是,同死亡争夺亲人就成了周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鲁迅早最深刻的记忆。 他在死亡谣言的追击下求学南京——“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便以为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在这里,“走投无路”意味着绝境,而“灵卖给鬼子”意味着与“鬼”为伍。所以,在鲁迅的亲人看来。他的“走异路,逃异地”就等同走不归的死路。实际上,逃出家乡之后,鲁迅再也不能“回家”了。隐喻层面上来讲,他的确把灵魂卖给了“鬼”—摩罗。摩罗是“挣天抗俗”魔鬼,是“国民的公敌”,是令一切正统意识和识时之彦畏惧的化身。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摩罗却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鲁迅看来,摩罗是“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也即中国历史惰性的解毒剂。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论毕飞宇小说的叙事策略 摘要:毕飞宇小说通过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以及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和“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毕飞宇对叙事方式的多方位尝试并没有导向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本质。 关键词:毕飞宇;叙事方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 毕飞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从1991年发表中篇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频频获奖的《玉米》,再到2005年的长篇新作《平原》,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走过了十多个年头。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极为灵动的曼妙气质。无论是对叙事内蕴的巧妙处理,还是对潜在人性的冷静揭示;无论是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控制,还是对叙事细节的精致化临摹,都体现出一种轻盈而又舒缓、丰沛而又沉郁的审美内涵,呈现出卡尔维诺所推崇备至的那种“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体现了毕飞字作为一个南方作家特有的艺术特性。 一、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方式 毕飞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高度自觉的灵性意识。他不像一般的作家那样常常被某些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深邃的理性思考所遮蔽,使叙事陷入某种正面强攻式的紧张状态。而是相当轻松地摆脱“意义”对叙事的过度缠绕,通过一些轻缓曼丽的智性话语,在“以轻击重”的逻辑思维中,迅速传达作品内在的审美意旨。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娴熟。 在《孤岛》、《楚水》、《叙事》等早期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毕飞宇对“意义”还充满了信心,甚至会不时地出现“意义”在叙事中裸奔的情形。但是,随着《哺乳期的女人》、《马家父子》等作品的问世,他开始自觉地致力于某种不露痕迹的精雕细刻,执迷于举重若轻的审美境界。他带着南方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机敏,以一种优雅从容的叙事方式,将很多凝重而尖锐的人性主题伪装起来,用一种轻逸的文本拥裹着深远的思索,使话语形式与审美内蕴之间保持着强劲的内在张力。例如,《怀念妹妹小青》看似在着力于叙述妹妹小青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是主人公那充满悲剧性的几个重大人生转折,却明确地凸现出历史深处的残酷、悲壮和劫难。而这种历史的不幸正是毕飞宇的审美目的,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少女妹妹只不过是作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一个生命符号。《哺乳期的女人》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这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是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一位大家。在鲁迅小说中有大量的“我”,如《一件小事》中有“我”,《社戏》中有“我”,《孔乙已》中有“我”,《祝福》中有“我”……这些“我”是不是就指作家自己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鲁迅作品中的“我”并不就是鲁迅本人。那么,既然不是鲁迅先生本人,是不是就是鲁迅先生编造的人物形象呢?鲁迅先生为什么在小说中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 笔者认为,鲁迅在小说中大量塑造“我”的形象,不但是叙述方式的需要,更是内容表达的需要。 在小说创作时,作家必须考虑一定的叙述视角,也就是说作家表现生活时,要考虑到叙述的角度,考虑到表达的方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在怎样的视力范围内来反映生活。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观点是传统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作家虽然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但却是一个“知情的旁观者”,处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地位。一切事件、各种人物都可以被作家收摄、检视,它好比是作家的一个踞高临下的广视角镜头,可以任意地扫描一切,观察一切,突现一切。这种具有广视功能的叙述观点,对作家表现生活来说无疑是十分方便的,因为它便于冷静而客观地刻划人物,观照人生,尤其适合于中长篇小说组织规模宏大的社会内容。我国作品大多采用了这种全知全能的第
三人称叙述方式。 但如果仅仅使用这一种方式,尤其是短篇小说,形式就会单一和板滞;由于缺乏视角的变化,容易流于平铺直叙;如果把握不好,还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感。这就要求有时也需变换叙述的视角。 用第一人称叙述观点的主要优点在于缩短了叙述人、作品人物及读者之间的感情距离,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把叙述人“我”直接摆进作品的环境,有时甚至介入事件的矛盾冲突之中,能便于作家选择和调整最佳视角,便于渗透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为深入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方便。这样作家可以淡化作品里需要淡化的某些成分,强化某些需要强化的成分,增强作品的主体思辨色彩和抒情氛围。 鲁迅先生就较好地通过突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小说模式,变换叙述观点,运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较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孔乙已》中的那个“我”——二十二岁的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和没有学会弄虚作假的那套市侩的生意经,不但遭到了掌柜的苛责,而且也受到了主顾们的歧视,因而,只好专管温酒这一单调而无聊的职务。小说正是以“我”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写了孔乙已的穷困、痛苦及死亡;又以“我”的生活的刻板及在“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情况,进一步显示了孔乙已沦落为“使人快活”供人奚落的材料的可悲。“我”虽然不象咸享酒店的一帮人那样把孔乙已当作嘲弄的对象,但在大家嘲弄孔乙已的时候,“我”也“可以附和着笑”,也只有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从《呐喊》《彷徨》论鲁迅小说的叙述模式.
从《呐喊》《彷徨》论鲁迅小说的叙述模式 摘要: 鲁迅,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是文学界无法跨越的高山。他的眼光独到又深邃,他的思想先进,他的语言尖锐又发人深省。追寻鲁迅的脚步,学习鲁迅的精神,使我们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又更加广阔,更加深远的认识。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探寻鲁迅小说的写作模式,诸如看客模式,吃人模式,还乡模式,从叙述模式,观鲁迅笔下国民的思想,以观20世纪初期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呐喊》;《彷徨》;看客模式;吃人模式;还乡模式 i
On the Narration Style in Luxun's Novel of Nahan and Panghuang Abstract: Luxun,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literati in the 20th. Nobody can reach the same height in literature but him, just because he has special and deep feeling, developed mind and his sharp words. By following his steps and learning his spirit, we can get a wider and further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20th. By exploring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his novels in Panghuang and Nahan, such as the style of lookers, eating people and returning to hometown, from those all styles we can see people’s mind in the literature, so we can see the whole Chinese’s appearance in the 20 centry. Key words: Nahan;Panghuang;mode of tourist;mode of killing and being killed;mode of returning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1)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鲁迅女性形象封建悲剧反抗 Abstract: Mr. Lu Xun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writer in modern China. The female image in his novels have different types and feature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spontaneous women against women, the old and the new cracks in three type. In this paper, from his works capture the fourth Shan's wife, Xianglin's wife, love regardless, Zijun this several with strong tragic color female one analysis. Lu Xun under the several major female tragedy, its inherent personality, author both sorrow for their unfortunate, nuqibuzheng, but mining works resulting in the root of their tragedy is oppressed, toxic to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udal ideology. Key words: Lu Xun female image against feudal tragedy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TYY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TYYUA16H-TYY-TYYYUA8Q8-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论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论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及美国现当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之一。作为一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在他去世后十年引起批评界广泛的关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批评家们主要关注的都是他作品中人性的主题,生动的情节,频繁的巧合,出人意料的结尾以及幽默的语言等方面。 对于欧?亨利独特的叙事策略,至今没有得到批评界应有的关注。鉴于此种现状,本文试图运用相关的现代叙事学理论来分析欧?亨利的数篇经典短篇小说,目的在于发现其精妙的叙事技巧,展现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欧?亨利的作品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开篇先简要介绍欧?亨利的生平,文学成就及其研究现状。然后,通过运用相关的现代叙事学理论,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分析欧?亨利的数篇小说:多变的叙事角度(聚焦模式及相应的话语形式;游动的叙事空间和协调一致的叙事时间。 通过对欧?亨利的三篇短篇小说的分析,笔者发现对于不同的作品,欧?亨利采取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及相应的话语形式,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他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画面。并且,每种叙事视角在揭示小说主题及塑造人物性格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欧?亨利主要把纽约、西部的得克萨斯和拉丁美洲的洪都拉斯作为其作品的三大叙事空间。这里的叙事空间所指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为一体的文化空间。对不同叙事空间的人物他倾注了不同的情感:对纽约寄予的是同情;对西部展示的是欣赏;对拉丁美洲表现的则是谅解。 在叙事时间方面,本文研读了欧?亨利的三个典型的短篇—《带家具的出租屋》1906、《麦琪的礼物》(1906和《爱的牺牲》(1906。通过使物理时间服务于心理时间以及撷取生活片段,欧?亨利使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得到有机统一,道出生活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doc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内容摘要:鲁迅先生的小说真实的描述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善良纯朴的本性,更让我们深知了他们的软弱性,是旧中国社会制度对他们进行残害和蹂躏的。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软弱性 封建礼教病态社会 严家炎先生曾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书中这样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走向成熟。”可见,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之巨大,也足见鲁迅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和典范作用。 鲁迅小说能受到如此高度的评价,是与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和悲剧性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先觉悟的,他们和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思想意识上的弱点,也与时代浪潮的起伏分不开,他们坎坷的生活历程可以反映出中国革命的艰难和曲折。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重视,说明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从狂人、孔已己、陈士成到子君、涓生、四铭等,鲁迅描写了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使之构成为一个可以烛照历史进程的系列,既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生活中所肩负的重任,也表现了他们的软弱或妥协,多方面揭示了他们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精神危机,为他们的新的出路进行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自然,鲁迅本人也是知识分子,在这些题材的作品中,也有着鲁迅本人心灵经历的痕迹和思想的投影。鲁迅不是孤立的描写知识
穿长衫的人。这个有着“乱蓬蓬的花白胡子”,青色脸色,皱纹间又时常夹杂些伤痕的老人,虽然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长衫,却显然不是“长衫主顾”的一类,而是属于“短衣帮”那一伙的。在咸亨酒店里,他又是怎样一个“穿长衫的”可笑人物啊!他是那样贫穷而又颓唐,衰老而又迂腐,“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令人发笑。据说他原来也读过书,可是他既无财产,又无靠山的家世,注定了他的终于没有进学的命运,而封建教育又把他变成一无所能,不爱劳动,好吃懒做的废料。于是,愈过愈穷,一直弄到给人抄书,将要讨饭,以至偷窃……除了供人愚弄和嘲笑,别无生活价值。可是,孔乙己潦倒穷困到这种程度,却还是舍不得脱掉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以显示自己读书人身份。当人们故意问他:“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还要“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而当人们问他“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却使孔乙已“显出颓唐不安模样的脸上笼上一层灰色”…… ( 注:呐喊/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5页 )说明孔乙已的生活虽然已经濒临绝望的境地,却还迂执的沉溺在腐儒的自尊自大的幻梦里,死守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律条,而冷酷的现实又极端残忍的嘲弄了他这种轻视劳动的腐朽观念,无情的把他逐出长衫的行列扔向短衣帮。这里,鲁迅借助孔乙己的形象,深刻的揭露了科举制度怎样摧残和毒害一个善良贫穷的读书人,并愤怒谴责了封建豪绅阶级和那黑暗残酷的环境怎样给予了这个小人物以严重的侮辱和损害。 总之,孔乙已是—个不幸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冷酷的社会环境之中。短衣帮也处在社会最底层,然而他们对豪强者充满敬畏,对不幸者又肆意嘲弄。他们以看见孔乙己“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的样子为乐事。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教学内容
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
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杨文军 (仰恩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 362014 摘要 :《那儿》所采用的双线结构和间离策略使工人阶级英雄“小舅”的崇高形象获得了说服力;在话语设置上, 《那儿》存在一个由众声喧哗到工人阶级英雄话语独白的过程,这是服从于作者的叙事立场的; 《那儿》所运用的反讽和隐喻提升了该小说的艺术层次,对当下的底层叙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那儿》 ;双线结构;间离;复调;反讽;隐喻 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在《当代》 2004年第 5期刊出之后,引发了热烈而持续的大讨论。一个中篇能获得如此反响,这种热度在当下文坛实属罕见。到 2006年初为止, 共有七次较为集中的关于《那儿》的讨论,另有许多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那儿》。 [1]可是纵观这些讨论和文章,发现其焦点并不是作为文学文本的《那儿》本身,而是《那儿》所切中的“国企改革”这根敏感的社会神经,仿佛《那儿》之所以具有(讨论上的价值, 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何过人之处 (很多论者认为《那儿》“ 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 [2] ,而是因为它“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了一场“悲壮与凄凉交织的、失败了的国有资源保卫战” , “ 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郎(咸平教授用经济学和数字化方式所揭示的严峻现实。” [3]当然, 《那儿》所涉及的题材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者曹征路的创作初衷也非常明确,就是质疑“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 [4]。但是一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故事,在曹征路看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除了“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一点点率真” , 还要有一种“审美展开的耐心” [5]。文学的叙事艺术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脱离艺术性而谈论内容和题材,不仅不会廓清、反而往往会遮蔽内容和题材的意义。对于《那儿》艺术性的简单质疑, 曹征路表示不满:“就我自己的追求而言,我在这篇小说的双线结构、叙述张力、跨文体的交叉并用、象征隐喻的多处设置,语言的粗砺性追求,以及意境的营造等方面
论鲁迅小说的语言特色
论鲁迅的小说语言特色 关键词:鲁迅小说语言特色性格形象 一、善于通过“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 鲁迅最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白描”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中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要求作家用最精炼、最节省的文字,不加渲染、烘托,刻画出鲜明生动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在鲁迅的笔下,常常准确地把握人物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不加渲染、不铺陈,用传神之笔加以点化,有如芙蓉出水,朴实自然。 例如在《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反用寥寥几笔,便使人物神情华肖,栩栩如生: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它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是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寥寥几字,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然而却抓住了孔乙己与别人不同的特点,把孔乙己的思想、性格、经济及社会地位揭示了出来。“站着喝酒”说明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属于“短衣帮”的;“穿长衫”则表明它是读书人,与“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的“长衫”客有某些共同之处,“唯一的”说明在酒店里只有他一个是这样的身份特殊的另类。他喝酒的方式与衣着的不相称,反映出它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的矛盾:从经济上说,他的地位很低,是属于“短衣帮”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他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仍然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的“读书人”。接下来描写他“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从脸色上看,说明他生活很艰难。从“伤痕”上看,暗示他常遭凌辱,从“乱蓬蓬”的胡子上看,表明他生活落魄潦倒。而他那件“又脏又破,似乎是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则说明他又穷又懒,而对这件“又脏又破”长衫,为了显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他一直没有脱下,揭示了他自命清高的性格特征。“满口之乎者也”则表明他卖弄“学问”。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鲁迅反用粗线条的勾勒,就活灵活现地把一个迂腐落后、贫困潦倒的深受封建教育迫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善于通过个性化语言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语言是刻画性格的重要手段之一,作家在创作中,必须要根据不同人物阶级、职业、经历、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选择富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去表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才能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来。鲁迅也是极善于通过人物个性语言塑造典型形象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语言都是极富个性化的。例如在《孔乙己》一文中,主人公孔乙己所说的话并不多,然而几乎句句都是个性化、性格化的语言。例如:“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
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6710105588.html, 浅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 作者:马维维 来源:《科技资讯》2019年第31期 摘 ;要:在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阅读风气逐步在社会上流行,其中不缺乏各种小说,但是较受欢迎的乃是先锋派的小说,主要是此种小说派系的创写风格不会拘泥于传统的小说写作形式,并给社会大众呈现了新颖的故事情节和小说风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余华。余华是一个把传统小说写作风格转变较为彻底的作者,其小说不仅仅是在内容上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其叙事的风格和手段也空前绝后。所以该文简要地从余华小说的叙事内容、时间、距离等方面积极探索了余华小说的叙事艺术,从而给社会大众一个真实有效的阅读指引。 关键词:余华小说 ;叙事艺术 ;碳素 ;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42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9)11(a)-0219-02 在我国各类小说的学派中先锋小说占重要的地位,对比传统的小说派系来说,先锋小说派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和艺术性,而且其最大化的创写风格就在于叙事过程中使用的虚实结合方式,把小说的故事情节虚拟化,而且带有一些创新性的实验精神,让社会大众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继续探索下去的欲望,感染着一代代的群众。并且余华小说不光是在小说内容方面有创新,还在叙事技巧方面发生了变革和加强,趣味性较为明显,在我国乃至世界小说界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1 ;重复的叙事模式 叙事的重复来自于对每一件小事的语言重复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其中不乏多种修辞手法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方式,从小说的整体上看,叙事重复是整个场景被无限地复制,或者是人物之间的相似之处,而后顺着余华一部小说的主线能够从其他的小说中找到有关的线索,这就表明余华小说的叙事重复体现在其各个小说之间的关联性之中,每个情节中语言的重复、情感的重复以及主题的重复,都在余华小说内部得以实现。其中语言方面的重复是把一样的话语多次使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借用不一样的场景角度和人物突显话语在不同场景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体现出余华创作的思想感情。 就以《许三观卖血记》这一小说为例,其中不乏语言方面的重复使用,而且伴随着小说主题的重复以及故事情节叙述的重复,比方说在写到一乐不是许三观的亲生孩子时就采用了语言的重复,而且一个字也没有变化,这样的言语重复更能加强流言蜚语在故事中的作用,也能够给读者巨大的冲击。而且在小说的第十八章,在许三观和其妻子的互动中,也使用了语言重复,从而组建了一个新的小说篇章。另外,在小说故事中的“精神会餐”情境中,许三观用言语
论鲁迅小说的语言特色.
论鲁迅小说的语言特色 摘要:翻开近百年来的历史,我们看到,在文化战线上继往开来成为一代风范的,首推鲁迅。毕其一生,他以其非凡的贡献参与了一代历史的创造,成为一个时代特定的人格代表。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创出的作品,在海内外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在新的时代仍不断展现着它们难以磨灭的现实意义。而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创作出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些形象,堪称现代的语文作品中的典范,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走进这些人物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正是刻画人物形象,展示其性格的重要手段。本文试从这一角度,谈一谈鲁迅小说中的语言特色。 一、善于通过“白描”和“画眼睛”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是鲁迅作品语言的一大显著特色。 鲁迅最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白描”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中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它要求作家用最精炼、最节省的文字,不加渲染、烘托,刻画出鲜明生动的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在鲁迅的笔下,常常准确地把握人物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不加渲染、不铺陈,用传神之笔加以点化,有如芙蓉出水,朴实自然。 例如在《孔乙己》中,对孔乙己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反用寥寥几笔,便使人物神情华肖,栩栩如生: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它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是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寥寥几字,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然而却抓住了孔乙己与别人不同的特点,把孔乙己的思想、性格、经济及社会地位揭示了出来。“站着喝酒”说明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属于“短衣帮”的;“穿长衫”则表明它是读书人,与“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的“长衫”客有某些共同之处,“唯一的”说明在酒店里只有他一个是这样的身份特殊的另类。他喝酒的方式与衣着的不相称,反映出它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的矛盾:从经济上说,他的地位很低,是属于“短衣帮”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他不愿与“短衣帮”为伍,仍然把自己
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分析
“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分析 唐欣 近年来,“主旋律”小说在大众层面成为关注的热点,不仅带动了新一轮图书销售的热潮,而且与小说同步或稍晚出现的相关影视剧也在各大媒体热播,一些小说作品还频频在政府设立的各种奖项中夺冠。然而,此类小说创作在学术界却遭到了冷遇,鲜见对其进行深层剖析的评论文章。“热”与“冷”之间,颇为令人深思。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伦理诉求有很大关联。这种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在小说为老百姓代言的表层话语下,其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并进而转换为一种“人民伦理”[1],从而潜在的为中心意识形态予以合法性论证,并达到与其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共契。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执行了一种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功能,而削弱了其作为小说所应有的审美品格与人性深度。 一、人民话语的意义共契 “主旋律”小说作家们的写作旨归往往直接诉诸普通“老百姓”,例如《抉择》的作者张平曾宣称:“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2]作家陆天明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写作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认可、喜欢,就是要参与当下时代的变迁。”[3]何申、谈歌等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并在其笔下主人公的信念中进一步彰显。因此,我们首先需对“老百姓”一词进行必要的话语指认。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说,“老百姓”即区别于军人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般居民。正因“老百姓”一词颇具中性色彩,并且语义指涉面极广,例如还有许多与之相近的家族概念:“人民”、“大众”、“群众”、“平民”等等,因此,它在“主旋律”小说作家的笔下便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并进而成为其写作的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性表现在:一方面,“老百姓”可以在褒义层面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在主流话语中,作为人类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人民”是一个超级能指,它赋予其声称者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与历史的神圣性,从而也就成为“主旋律”小说作者的一种策略性借势;而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可以与“大众”话语相联,进一步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接轨,此种大众策略使小说也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这种意义的多歧性使得“主旋律”小说中的“百姓话语”具有了极大的弹性,从而不仅在主流话语层面稳固地获得了其叙事的“合法性”,还在市场层面持续畅销。 在人们所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对于社会正义与公正的侵蚀下,“主旋律”小说中以“老百姓”为话语旨归的叙事策略,正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面临合法化危机的中心价值体系的修葺愿望,而对于这种愿望的最直接表达策略莫过于基于“人民”的话语诉求,一些小说正是以巧妙运用“老百姓”的话语方式与主流话语达成意义共契。例如在《抉择》中,李高成曾义正辞严地对腐败分子郭中姚说道:“共产党要是能让金钱买垮的话,那还轮得上你们这些东西!你居然还会以为只要有严阵这样的人做了你的靠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连工人也不放在眼里,连共产党也不放在眼里!你怎么会把这一切看得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凭我现在的身分,我只须一个电话,半个小时以内,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冲到你这儿来,半分钟内就会把你撕得粉碎!……你竟还以为要是共产党不存在了,你还可以稳稳当当地当你的资本家?你记着,若真要是有了那一天,工人们头一个要惩罚的就是你,老百姓会把你这一身的肥肉沤成了一堆粪!”这里,主人公的此番表白因代表着广大老百姓而获得了其身份伦理及道义的优先性,并因这种正义感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人物的对白,毋宁说象一份政党反腐败的宣言书,因为它在小说的审美表意实践中仍然延用的是“政党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和修辞表达”[4]方式,而“百姓”话语则更化为了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它为受到侵蚀的主流话语提供了拯救其合法性的正当性资源。而小说结尾处也颇意味深长,李高成与东欧某国原劳动部长就东欧剧变进行了探讨,最后他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让人民期待太久”! 在此,百姓话语的小说叙事已暗中置换为迎合主流话语宣扬的“人民伦理”之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因此,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