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题目及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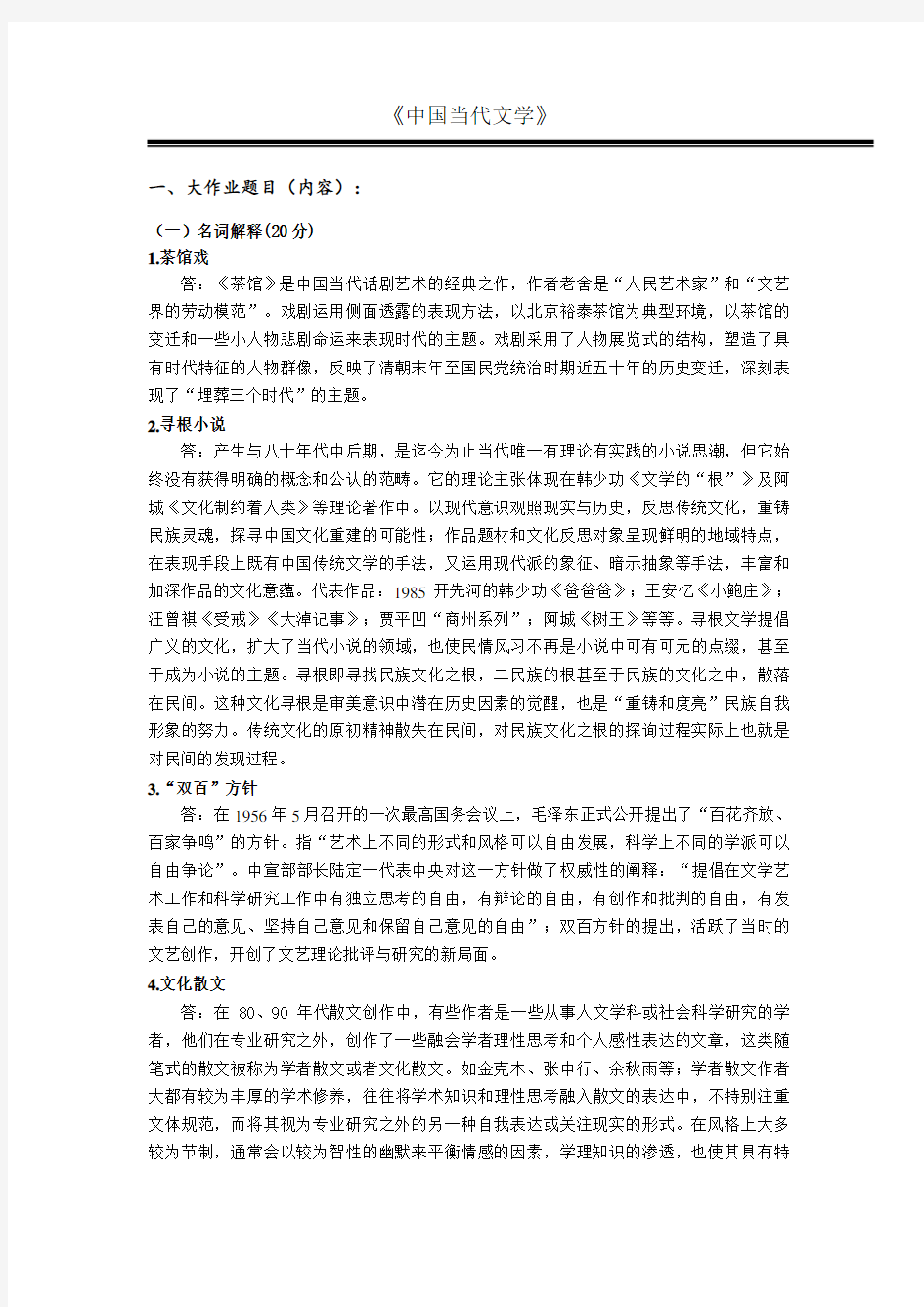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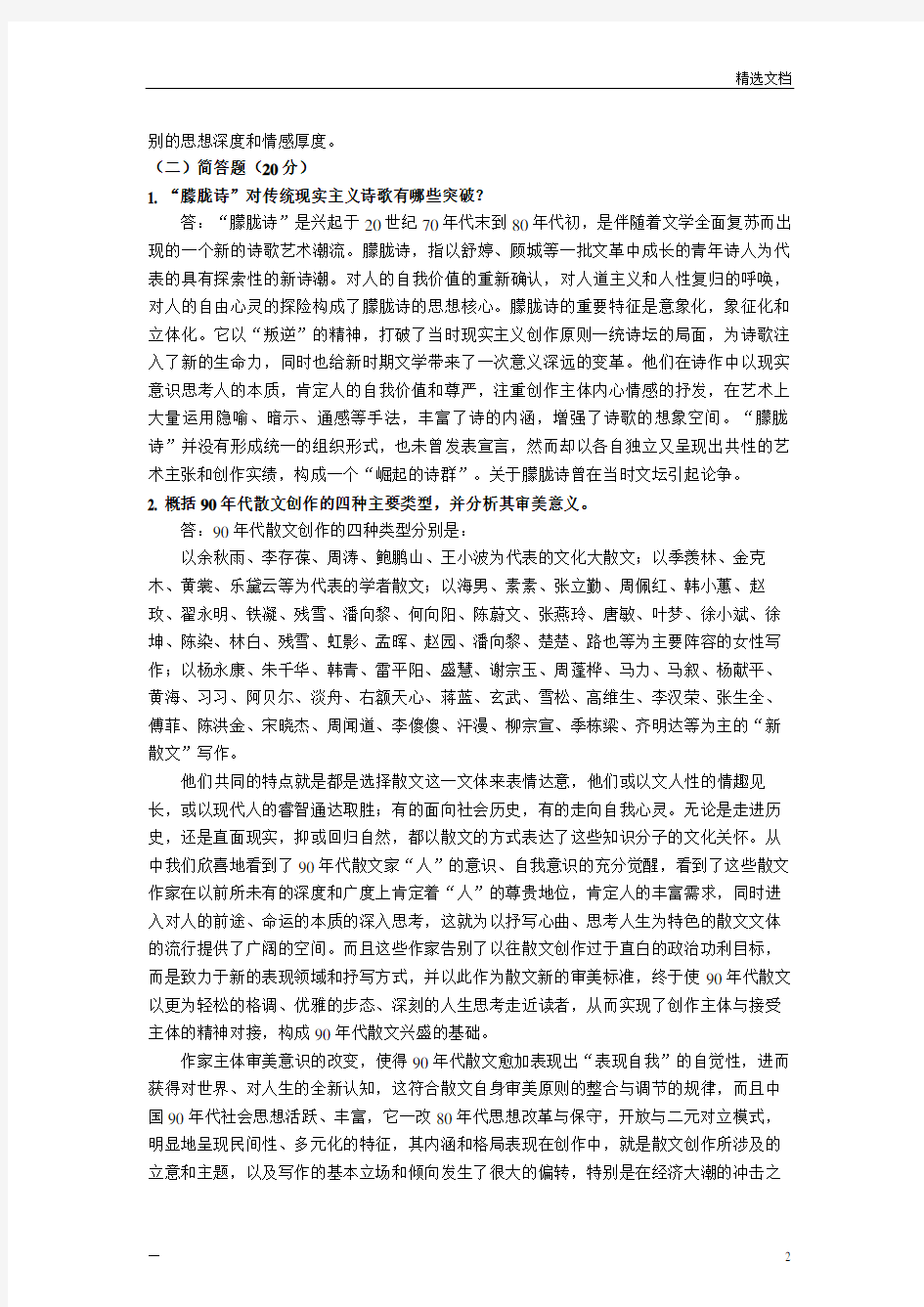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一、大作业题目(内容):
(一)名词解释(20分)
1.茶馆戏
答:《茶馆》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作者老舍是“人民艺术家”和“文艺界的劳动模范”。戏剧运用侧面透露的表现方法,以北京裕泰茶馆为典型环境,以茶馆的变迁和一些小人物悲剧命运来表现时代的主题。戏剧采用了人物展览式的结构,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群像,反映了清朝末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深刻表现了“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
2.寻根小说
答: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3.“双百”方针
答: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4.文化散文
答: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
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二)简答题(20分)
1. “朦胧诗”对传统现实主义诗歌有哪些突破?
答:“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朦胧诗,指以舒婷、顾城等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为代表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朦胧诗的重要特征是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
2. 概括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分析其审美意义。
答:90年代散文创作的四种类型分别是:
以余秋雨、李存葆、周涛、鲍鹏山、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黄裳、乐黛云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海男、素素、张立勤、周佩红、韩小蕙、赵玫、翟永明、铁凝、残雪、潘向黎、何向阳、陈蔚文、张燕玲、唐敏、叶梦、徐小斌、徐坤、陈染、林白、残雪、虹影、孟晖、赵园、潘向黎、楚楚、路也等为主要阵容的女性写作;以杨永康、朱千华、韩青、雷平阳、盛慧、谢宗玉、周蓬桦、马力、马叙、杨献平、黄海、习习、阿贝尔、淡舟、右额天心、蒋蓝、玄武、雪松、高维生、李汉荣、张生全、傅菲、陈洪金、宋晓杰、周闻道、李傻傻、汗漫、柳宗宣、季栋梁、齐明达等为主的“新散文”写作。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选择散文这一文体来表情达意,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从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90年代散文家“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看到了这些散文作家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同时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这些作家告别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而是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和抒写方式,并以此作为散文新的审美标准,终于使90年代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雅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90年代散文兴盛的基础。
作家主体审美意识的改变,使得90年代散文愈加表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进而获得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知,这符合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的规律,而且中国90年代社会思想活跃、丰富,它一改80年代思想改革与保守,开放与二元对立模式,明显地呈现民间性、多元化的特征,其内涵和格局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散文创作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偏转,特别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
下,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个人化的趋势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当然“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社会因素对于作家的影响,使90年代的散文创作必然出现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个时期的创作,或者富有哲理和人道精神,或者婉转抒情、或者倾向于个体内心的倾诉,或注重文体的创造与革新,甚至是一些大众消费的散文也应运而生。因此散文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其中,老一代的博大、中年一代的厚重、年轻一代的锐利,使当下散文创作呈现着三代同堂的繁荣局面。他们为我们散文的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给我们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有意的启示。
(三)论述题(60分)
结合建国30年与80、90年代的小说作品的比较,论述新时期以来小说在题材、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出现了怎样的演化趋势?并请说说你对这种演化趋势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有理有据。)
答:首先,在题材方面,“文革”题材小说研究的兴起。对于“文革”题材小说,学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明确定义,很多研究者几乎都不对“文革”题材小说进行界定,“文革”题材小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文革”题材小说大体上等同于许子东所说的“文革小说”。新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出现伊始,可以说关于它的研究就应运而生了。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发表,全国读者来信不断,围绕《班主任》的座谈纪要和评论也随之而来。卢新华的《伤痕》一发表,大有全国读者泪流成河之势,《〈伤痕及其他〉———短篇小说和评论选》也随之出现。古华的《芙蓉镇》和莫应丰的《将军吟》刚一出版,《〈芙蓉镇〉评论选集》和《〈将军吟〉评论选集》就紧跟而来。戴厚英的《人啊!人》一问世,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便蜂拥而起。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关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评论意味着新时期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已经发生。1983年开展的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蓬勃发展。由于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有不少以书写“文革”中的人和事为主,所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又活跃起来。从“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兴衰与当时文艺政策的或松或紧呈正比关系,与之相随的“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大致上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叶永烈、胡月伟、师东兵、林青山等人的“文革”传记、“文革”纪实和“文革”秘闻也在那个时候同步出现。这些“文革”题材作品(小说)在反思“文革”的同时也不乏消费娱乐的倾向,它们同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叙事的四重向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题材小说(作品)大量涌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兴起的“文革”研究密切相关。1986年“文革”发动20周年之时,知识界对“文革”的言说持续升温,邵燕祥倡议建立“‘文革学”,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人们牢记文革”,以防“文革”再来,针对巴金的提议,附议者不少,但也不乏“怀疑”者。总的来说,那时人们呼唤“研究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到来。今天看来,一批早期的“文革”研究著作、“文革”口述著作就产生于那个时比如金春明、王年一、周明、冯骥才等人的书籍。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呼吁进行“‘文革’文学”研究。1988年11月10日,《文学自由
谈》《开拓文学》编辑部主持召开了“文学与‘文革’”座谈会。《钟山》1989年2期刊登了潘凯雄、贺绍俊《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一文。随着全国经济政治形势的紧张,1989年夏季前后至邓小平“南方讲话”(1992年1月1日到2月21日),“文革”研究受到限制,“文革”文学研究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也走向低潮。其实,早在1988年12月10日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这种趋势似乎就已经注定。可以说,从1989年夏季前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段时间,既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蛰伏期,又是“文革”题材小说创作及研究的突围期。从中也可以看出,“文革”文学研究和“文革”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伴随着文革研究”的兴衰而呈现出上下起伏的状态,这与政治经济形势和文艺政策的变化遥相呼应。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这种局面得到改观。
其次,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人物形象仍缺乏丰富性和立体感、缺乏历史意味和独特的审美个性。如果观察新时期之初的主要小说思潮,如伤痕小说及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的部分作品,就可以发现大部分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还较多地拘囿于类型化、扁平人物的窠臼,还未塑造出有独特审美价值、充分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新时期小说的真正起步肇始于刘心武的《班主任》,但以《班主任》和《伤痕》为先声的伤痕文学思潮就精神实质而言,与其说是次文学思潮,还不如说是一次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它是经历了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和生活的大灾难之后,思想解放与灵魂觉醒浪潮的第一次涌动,是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文学的面目所进行的一次非文学的抗议活动。像很多人概括的那样,文学成了时代情绪的突破口。作家则成了时代情绪的代言人。在这样一场带有很强的政治批判色彩和情绪宣泄色彩的文学浪潮中,作家不是冷静的,也不可能以超脱事外的所谓静观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创作,所以作家在选择叙述切入点时,就采取了一个迅捷而简便的方式:讲故事。要印证这一点,只要看看《伤痕》、《在小河那边》、《我应该怎么办》、《枫》、《杨花似雪》、《重逢》等一大批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占据了审美重心的显然是故事,是这些故事展开的具体形式情节。当然其中也有人物,但人物往往是展示故事情节的工具,是故事的载体。小说让读者回味的是那些感伤、凄绝的故事,而不是性格化的人物,人物性格的光辉显然被情节的曲折、离奇,故事的沉重以及隐附于故事中的感伤情绪遮掩了。甚至在当时被称作典型的一些人物形象,在今天看来也缺少典型所具有的性格的丰富性和立体感,缺乏真正的典型所具有的丰厚的历史意味和独特的审美个性。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以后,人们谈论最多、评价最高的是谢惠敏这一人物形象,认为她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不可否认,这一形象有其独特性和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但是作为艺术典型的性格构成来说,她的性格是单一的,除以扭曲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积极和红以外,她的性格缺乏更加丰满的特征和丰富的色彩。她的独特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及意义也在于这一性格强烈的针对性,她触到了一个社会普遍关心的政治热点,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形成这种反思的社会气氛的逐渐单薄,这一形象的批判针对性散失以后,她的性格的单薄和单一与一个真正典型所具有的强大的历史凝聚力和丰厚的审美意蕴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明显了。
我对于对于上述演化趋势的看法如下:
第一,向人的文化存在的扩展。传统的典型观建立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哲学社
会学基础上,而对其所作的解释则是共时性和政治化的。社会关系基本上等同于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就是专政和斗争关系,因此人的真实性存在被简化和政治化了。新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中国作家从思想解放、文化热、拉美爆炸文学等政治、文化、文学思潮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新思路:人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人既是共时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历时的文化传统的积淀物,人是政治动物又是文化动物。这种看似简单的命题,却是历经几十年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才获取的新知。当然,创作中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并不始自理论上的自觉并酿成文化思潮的寻根小说。事实上,在这之前,反思小说中一些成功的作品已经触到了这样的文化岩层。比如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陈奂生,作者对这一形象文化心理的出色描绘,使他成为在现实与历史间闪回,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叉点上站立的出色的农民典型。
第二,具有向人性。具体地说是向人的个体性生存空间的拓展,更有效地消解政治化典型的性格模式。人不仅是体现横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动物,也不仅是体现纵向文化积淀的文化动物,而且他还是肉身并被赋予灵魂的个体存在物,他自己就是一口深井,心灵本身就是一只神秘的黑箱。横向的社会关系纵向的文化关系与垂直、立体的心灵层次,构成了人的三维存在,作为人学的文学就应该是这一三维空间的全景扫瞄。新时期小说在典型观念上的突破,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为人性和非理性正名,把它看作人的课题中应有之义,看作文学描写名正言顺的聚焦点。事实上,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对大写的人的呼唤和塑造,已明显地表明了典型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旗帜鲜明地转轨,这可以在两种典型特征的比较中得到充分说明。与革命现实主义所倡言并努力塑造的英雄和新人形象不同,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更多更明显地受到了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小人物、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是这些小说所钟情的人物形象。李顺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王老大《笨人王老大》、张铁匠《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农民形象,许灵均《灵均肉》、钟亦诚《布礼》、罗群、冯晴风《天云山传奇》、陆文婷《人到中年》等知识分子形象,在精神气质与审美特征上同江姐、杨子荣、乔光朴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具体回答他是谁,即围绕他们展开的生活层面上看,道德伦理关系、人性内容、个性心理成为构成性格的主导因素,这同在阶级之间展开的政治大搏斗中,在激烈而尖锐的思想观念冲突中所成就的英雄与新人相比,其生活形态和审美形态显然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要突破典型观念政治化的旧有窠臼,需要来自美学方面强有力的补充和支持,而美学方面的突破恰恰来自于对人理解的丰富,来自于对人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与描写。如果重温一下代表新时期人物形象塑造最高成就的众多形象,如田玉堂《内奸》、陈奂生、张种田《西望茅草地》、魏天贵《河的子孙》、田家祥《拂晓前的葬礼》、金斗《桑树坪纪事》、陆文婷《人到中年》、朱自冶《美食家》、徐秋斋《黄河东流去》、倪吾诚《活动变人形》、王一生《棋王》、四爷爷《古船》、白嘉轩《白鹿原》等就会发现,他们无一不是建立在丰富的人性基础上,具有多重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并且在某些形象身上,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鄙等对比强烈的性格特征错综复杂地纠合在一起,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魏天贵作为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热心为群众办好事,敢做敢为,自有质朴、真诚的一面,但有时又愚昧且狡猾;他的行为动机既有崇高的一面,但有时又私欲膨胀,甚至牺牲他人满足自己的私欲。由英雄到末路的田家祥,集伟人与小人、领袖与最狭
隘的农民、天使与野兽等多种人格因素于一身,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中一个少有的复杂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文婷这一形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形象标志着典型观念上的一次崭新的突破。具体地说,在典型化的观念上,陆文婷形象的塑造将分轨而制、分道而行的两极文化特质和审美特质进行了奇妙的综合。一方面,她具有英雄与新人的特质心灵纯净美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恪尽职守、舍己为人以及超人的意志与耐力等,具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优良素质,表现出一种肯定性和建设性的文化向度。她身上没有一点像乔像乔光朴那样的英雄形象所表现出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盛气与霸气。另一方面,她又奇妙地表现出平凡人、小人物的异常质朴、亲切的一面。同英雄形象对世俗性生活的拒绝相反,她在爱情、婚姻、家庭等日常性的生活中表现出一个普通女性正常的需求与合理的愿望。陆文婷等形象的成功塑造,标志着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的塑造终于走出了神的阴影,走出了高大全的窠臼,使英雄获得了普通人的面目、普通人的心理,获得了现实中人的生活形态。这样一个英雄世俗俗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感性化、审美化的过程,是人性的丰满带来了典型内涵的丰富和典型化的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