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宗师李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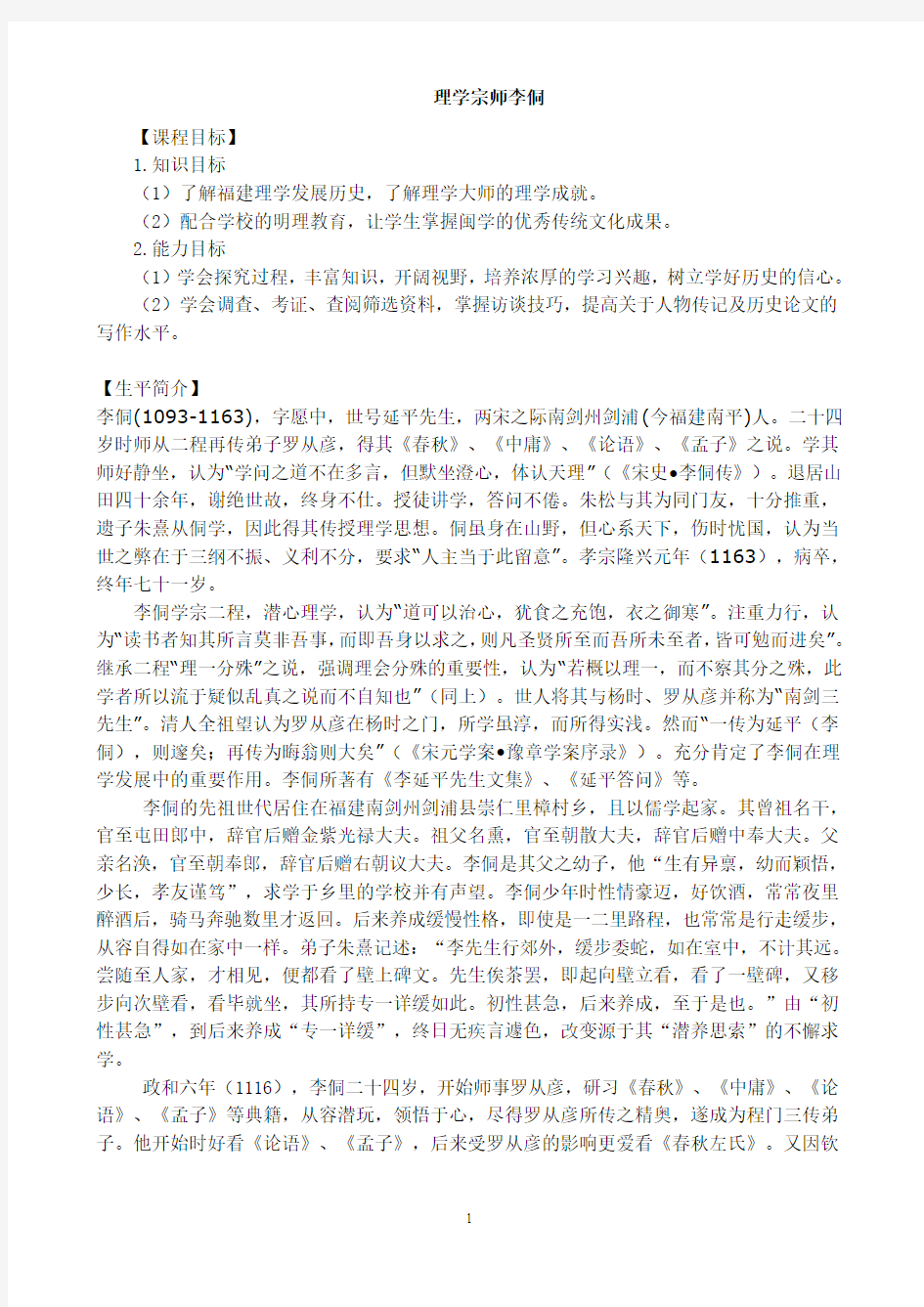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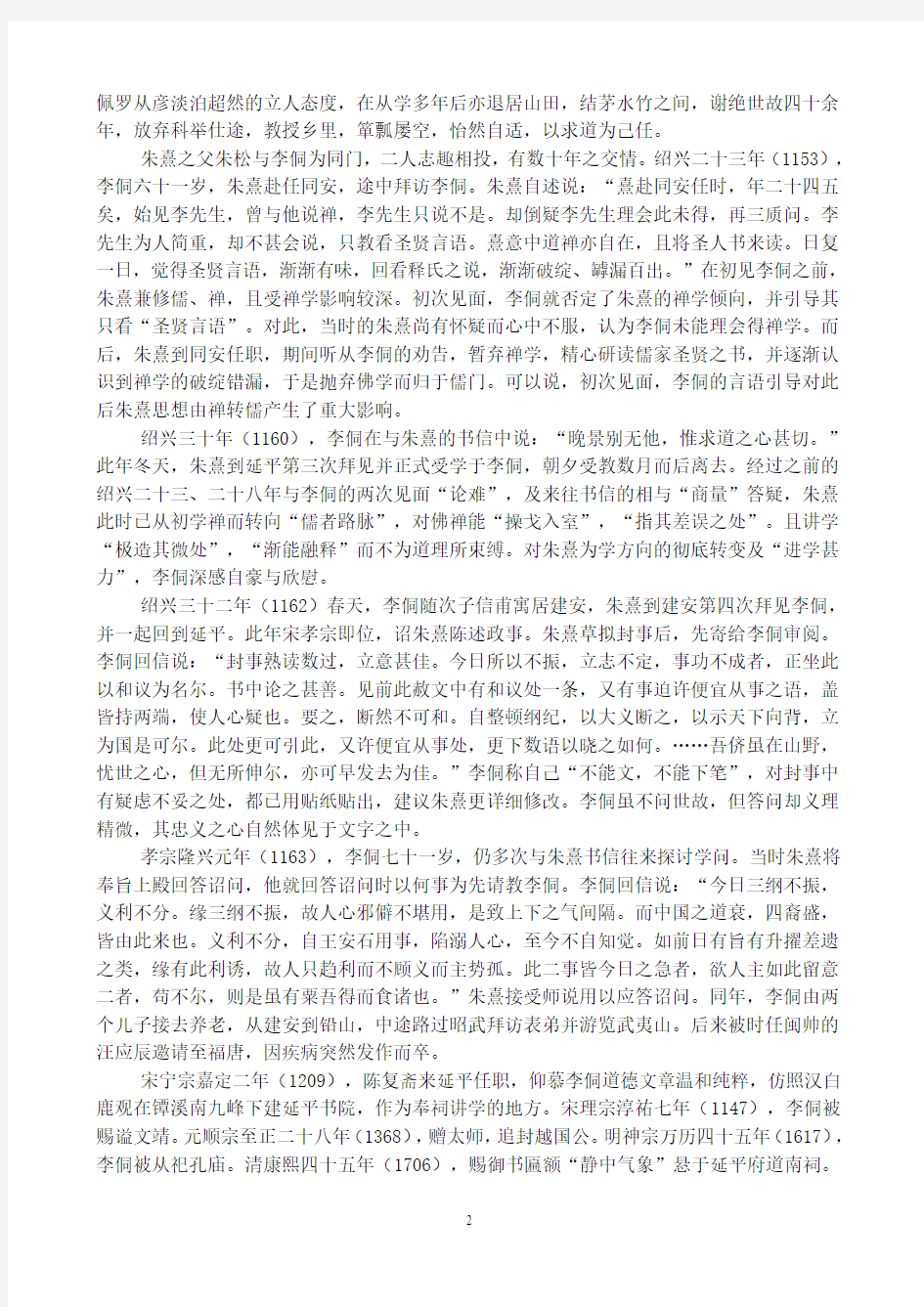
理学宗师李侗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福建理学发展历史,了解理学大师的理学成就。
(2)配合学校的明理教育,让学生掌握闽学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
2.能力目标
(1)学会探究过程,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树立学好历史的信心。
(2)学会调查、考证、查阅筛选资料,掌握访谈技巧,提高关于人物传记及历史论文的写作水平。
【生平简介】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号延平先生,两宋之际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二十四岁时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学其师好静坐,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史?李侗传》)。退居山田四十余年,谢绝世故,终身不仕。授徒讲学,答问不倦。朱松与其为同门友,十分推重,遗子朱熹从侗学,因此得其传授理学思想。侗虽身在山野,但心系天下,伤时忧国,认为当世之弊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要求“人主当于此留意”。孝宗隆兴元年(1163),病卒,终年七十一岁。
李侗学宗二程,潜心理学,认为“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注重力行,认为“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继承二程“理一分殊”之说,强调理会分殊的重要性,认为“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同上)。世人将其与杨时、罗从彦并称为“南剑三先生”。清人全祖望认为罗从彦在杨时之门,所学虽淳,而所得实浅。然而“一传为延平(李侗),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序录》)。充分肯定了李侗在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侗所著有《李延平先生文集》、《延平答问》等。
李侗的先祖世代居住在福建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村乡,且以儒学起家。其曾祖名干,官至屯田郎中,辞官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父名熏,官至朝散大夫,辞官后赠中奉大夫。父亲名涣,官至朝奉郎,辞官后赠右朝议大夫。李侗是其父之幼子,他“生有异禀,幼而颖悟,少长,孝友谨笃”,求学于乡里的学校并有声望。李侗少年时性情豪迈,好饮酒,常常夜里醉酒后,骑马奔驰数里才返回。后来养成缓慢性格,即使是一二里路程,也常常是行走缓步,从容自得如在家中一样。弟子朱熹记述:“李先生行郊外,缓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计其远。尝随至人家,才相见,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罢,即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毕就坐,其所持专一详缓如此。初性甚急,后来养成,至于是也。”由“初性甚急”,到后来养成“专一详缓”,终日无疾言遽色,改变源于其“潜养思索”的不懈求学。
政和六年(1116),李侗二十四岁,开始师事罗从彦,研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典籍,从容潜玩,领悟于心,尽得罗从彦所传之精奥,遂成为程门三传弟子。他开始时好看《论语》、《孟子》,后来受罗从彦的影响更爱看《春秋左氏》。又因钦
佩罗从彦淡泊超然的立人态度,在从学多年后亦退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放弃科举仕途,教授乡里,箪瓢屡空,怡然自适,以求道为己任。
朱熹之父朱松与李侗为同门,二人志趣相投,有数十年之交情。绍兴二十三年(1153),李侗六十一岁,朱熹赴任同安,途中拜访李侗。朱熹自述说:“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回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在初见李侗之前,朱熹兼修儒、禅,且受禅学影响较深。初次见面,李侗就否定了朱熹的禅学倾向,并引导其只看“圣贤言语”。对此,当时的朱熹尚有怀疑而心中不服,认为李侗未能理会得禅学。而后,朱熹到同安任职,期间听从李侗的劝告,暂弃禅学,精心研读儒家圣贤之书,并逐渐认识到禅学的破绽错漏,于是抛弃佛学而归于儒门。可以说,初次见面,李侗的言语引导对此后朱熹思想由禅转儒产生了重大影响。
绍兴三十年(1160),李侗在与朱熹的书信中说:“晚景别无他,惟求道之心甚切。”此年冬天,朱熹到延平第三次拜见并正式受学于李侗,朝夕受教数月而后离去。经过之前的绍兴二十三、二十八年与李侗的两次见面“论难”,及来往书信的相与“商量”答疑,朱熹此时已从初学禅而转向“儒者路脉”,对佛禅能“操戈入室”,“指其差误之处”。且讲学“极造其微处”,“渐能融释”而不为道理所束缚。对朱熹为学方向的彻底转变及“进学甚力”,李侗深感自豪与欣慰。
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天,李侗随次子信甫寓居建安,朱熹到建安第四次拜见李侗,并一起回到延平。此年宋孝宗即位,诏朱熹陈述政事。朱熹草拟封事后,先寄给李侗审阅。李侗回信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亦可早发去为佳。”李侗称自己“不能文,不能下笔”,对封事中有疑虑不妥之处,都已用贴纸贴出,建议朱熹更详细修改。李侗虽不问世故,但答问却义理精微,其忠义之心自然体见于文字之中。
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侗七十一岁,仍多次与朱熹书信往来探讨学问。当时朱熹将奉旨上殿回答诏问,他就回答诏问时以何事为先请教李侗。李侗回信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来也。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遗之类,缘有此利诱,故人只趋利而不顾义而主势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朱熹接受师说用以应答诏问。同年,李侗由两个儿子接去养老,从建安到铅山,中途路过昭武拜访表弟并游览武夷山。后来被时任闽帅的汪应辰邀请至福唐,因疾病突然发作而卒。
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陈复斋来延平任职,仰慕李侗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照汉白鹿观在镡溪南九峰下建延平书院,作为奉祠讲学的地方。宋理宗淳祐七年(1147),李侗被赐谥文靖。元顺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赠太师,追封越国公。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李侗被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赐御书匾额“静中气象”悬于延平府道南祠。
李侗一生不著书,不作文,乡居“颓然如一田夫野老”。后来朱熹将与其往来问答的书信编成《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简称《延平答问》。此书不仅是记载李侗言行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成为李、朱二人传授心法和“朱子授受衣钵”。清人张伯行说:“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彻始彻终。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认为李侗虽不留意著书作文却能答问教人,正是其答问使朱熹之学渊源有自,上承洛学,充分肯定了李侗在道南一脉中的地位。
李侗师从罗从彦,上承龟山、伊洛之脉,立志于接续儒家道统,探求圣学之传。其学说虽师出有门却不泥守。朱熹称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朱熹弟子赵致道说:“李先生之学,不但得于所授,其心造之妙,实有先儒之所未言者。”李侗还以所学接引后学,答问不倦。虽其本人性格如朱熹所说,“为人简重,不甚会说”,李侗也称自己“素来拙讷,发脱道理,不甚明亮”,“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答问内容多让朱熹“意会消详之”。但在师徒的叩问与激发中,朱熹却受益良多,说:“其后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盖其上达不已日新如此。”每一见师学问即有进益的朱熹在《李先生行状》中多论其师“开端示人”之处,概括而言,有“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洒然融释”等几个方面。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
李侗以理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上承二程、杨时以太极论理。李侗指出其理会有错误,认为太极为至理之源,在天地为理,在二气交感化生的万物包括人中亦存在。“人与天理一也”,理贯穿万物之始终,因此不能将天地之理与人之理隔截为二。李侗不仅以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本源,还论阴阳二气及其交感化生万物,朱熹以仁为心之正理,将人与禽兽相区别。李侗认为朱熹所说有所窒碍,仁是天地之理,万物的生成都有理有气,万物从本源上都是理,理贯万物之始终且“无顷刻停息间断”,但在气化过程中万物又因各自禀受的气有“秀”、“偏”之分而产生差异。其中人得五常中和之气最灵秀,其他物只是得气之偏。因此理非“惟人独得之”。此处,李侗虽没有直接将万物生成概括为“理一而分殊”,但其所说的“本源则一”即是“理一”,也即仁,万物由于禀气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即“分殊”。李侗以理本气化不仅说明万物之化生来源,而且也从本体的角度论证了“理一”与“分殊”的客观存在。
在解说张载的《西铭》时,程颐、杨时以仁义论说“理一而分殊”,李侗继承二人之说,亦以“仁只是理”关注“理一”与“分殊”的伦理内涵,强调知仁。李侗继承发挥杨时之说,注重从“知”字上下工夫理会“仁”。他认为本源是“体用兼举”的,只有从知觉的角度下工夫理会,才会“透彻”、“了了”本源之分殊,才能达到体用兼举的学术宗旨。对此,朱熹理解说:“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对朱熹的理解,李侗加以肯定,称其“概得之”。虽然李侗为学宗旨是注重体用贯通,“理一”与“分殊”兼举,但为与“异端”之学相区别又重视对“分殊”的论说。
朱熹在问学李侗之初留意禅学,为李侗所不许。李侗用“理一分殊”之说引导朱熹辨别儒与异端。李侗认为儒学和异端之学的区别,主要是对“理一分殊”之旨、特别是“分殊”的认识与掌握不同,主张对“理一”,即“一视同仁气象”的理解并不难,对“理一”的把握也并不能将儒与异端真正辨别开,重要的、难得的是对“分殊”的把握,只有在“理一”的基础上认真仔细地理会人伦日用等分殊才是儒者气象,也才能真正划清“吾儒”与“异端”的界限。诚然,朱熹在李侗的引导下又超出李侗之思想范围而转向重视“分殊”之穷理,但李侗强调“分殊”主要是为了将儒学与“疑似乱真”的异端之学区别开来,而其“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的重“分殊”思想也是对杨时注重“分殊”的继承与发挥。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李侗上承师门,为学注重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发之中即是性。李侗认为性不可见,只能“自性而观”,即反身内求。
李侗从学罗从彦,罗从彦好静坐,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李侗继承师说也静坐体验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即是静坐体认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体验未发时气象。道南学派自杨时即注重对未发之中的静中体验,李侗注重静中体验未发直接源于罗从彦,并上溯于杨时,朱熹说:“盖李先生为默坐澄心之学,持守得固。龟山之学,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之学,出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李侗以所学又传之朱熹,“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李侗高扬这一道南指诀,对其作了进上步的发挥。
罗从彦提出静坐的修养方法,但没有具体诠释,这一点为李侗所发展。李侗所说的静坐就是打叠、猛醒提掇、收摄心使之不放逸,保持虚明专一。同时静坐也并非心中虚无一物,因为“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而是要“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是时时处处主于天理、存养天理。李侗的静坐理论后来为朱熹所批判继承。朱熹不主张专一静坐,认为李侗为学“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而是继承程颐注重敬,但他对“敬”内涵的阐释却吸取了李侗学说中静坐的理论,如“敬”有随事检点、常惺惺、收敛等义。
李侗主张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及“静坐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并非空头泛泛的涵养,而是含有实际的工夫在里面。《中庸》中有“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之说,朱熹认为此语即是未发气象。李侗认为直言此未发气象而没有体认工夫就“无甚气味”,即缺少体认工夫之意趣,《中庸》中所语乃是体认而存养之气象。可见,李侗的“静坐中之超越体证即涵一超越之察识(识生理仁体、天命流行之体,乃至中体大本)”。而体验未发的工夫还体现为养气,养气是使心与气合,李侗强调心与气合一需“集义”,也即有道德内容,而集义之气即是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篇中有:“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李侗认为养“浩然之气”应以“知言”作为下工夫处,“知言”是善于辨别言辞义理,也即于日用处下工夫。通过“知言”养浩然之气就形成未发时之“塞乎天地气象”、“不倚不偏气象”。
可见,李侗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作为向内的直觉体验工夫,是对大本道体的体认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的体验,是超越之体证与超越之察识的合一,知言与养气的会通。
洒落融释说
李侗强调学问应是为己之学,为学需反身而诚,重在自得,在李侗看来,读书不应拘泥文字而求其词义,应是“即吾身以求之”,“此并非不读书,要在能就其所指点而消化之于自己生命中而体现之以成为吾人之德行,此即其所言莫非己事也。此并非是依照它所说者去做,乃是它所说者即是吾之生命中本有之事,故由其指点而豁醒,即一一皆为己事也”。李侗强调“即吾身以求之”,是因为大本道体在于己,因此通过反求诸心,可达至学问“惬适”自得之处,即是“清通和乐之象”。
李侗论学者之弊病,说:“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洒然冰解冻释”也即“洒落融释”。明人周木称李侗之学“虽出于罗、杨,而自得之妙则又青于蓝而寒于水”,“其学也妙体用而为一,合显微而无二。实斯文之正脉,吾道之的传,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无异趣者。”清人季芷将李侗比为颜渊,说:“先生其似颜子乎!颜子终日不违如愚,先生教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颜子箪瓢屡空不改其乐,先生历四十余寒暑啜菽饮水亦自有余;颜子于圣人根本有默契处,孔子谓非助我。先生谨守龟山之学数年后,心广体胖,非文字言语所及。先生云‘赖天之灵尝在目前,如此安得不进?’几于喟然一叹,又何其言之似颜子乎!”清人毛念恃称李侗犹如孟子,说:“延平之有李先生,亦犹邹鲁之有孟夫子也。东鲁之道立极于吾夫子,而孟子为之大声疾呼,乃辟百家而一归我夫子之圣。闽南之道倡始于杨龟山,而李先生为之阐微继渺,乃衍伊洛而大传于紫阳之贤。”李侗在道学传承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弟子朱熹的影响。朱熹早年出入于释老十余年,“初师屏山、籍溪,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自受学于李侗,渐知释学之非而归儒。朱熹自己也说:“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钱穆认为:“盖朱子之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议。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可以说,李侗对朱熹学术方向及学术脉络的形成都产生了很重要影响,而朱熹在承接的同时又有所转向。如李侗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本为纠正朱熹之笼统于禅,或只涵养不体认之说,但亦开朱熹对分殊之重视及爬梳;日用处融释本是将杨时以来静中体验未发的直觉内向体认理论向体用一贯的完善,但亦开朱熹重日用而向外格物穷理之理路等。朱熹的这些转向也说明,李侗建构的体用混圆之学中,已蕴涵有可消解其静中体验未发的内向直觉体验之成分。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他的理学思想,对朱熹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李侗的“太极”思想对朱熹的影响。“太极”这个词语最早见于《易·系辭上》,而宋代理学家提到太极的则是周敦颐。周敦颐认为“无极”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而“太极”则是阴阳混沌未分之气。张载是以气为本,用“太极”来说明气。邵雍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将“太极”作为他的象数哲学的最高范畴。二程则是以理为本,“太极”
未被提到基本范畴的位置。杨时则把“理”称为“太极”,并且是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这样,朱熹的“太极”思想就为封建道德在宇宙的存在和自然规律中制造了根据。
第二,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对朱熹的影响。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直至李侗,都衷心信服《中庸》里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求中未发”之思想。他们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要求体验未发之“中”,强调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龟山集》卷4)罗从彦认为人性未发之中即体现了天理,祇要人们能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处事就会自然合理、中节;因此,他更主张心性修养要从喜怒哀乐未发、思虑未萌的本然状态开始下功夫,并提倡运用“观心”的方法,静中体认天理。“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罗豫章先生》)
第三,李侗的“理一分殊”说对朱熹的影响。首先,是李侗将“理一分殊”和体用相联系的思想,被朱熹接受;朱熹并在此基础上用体用范畴对“理一分殊”作了更为广泛、更为精致的阐发。其次,朱熹即接受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同时,也吸收李侗的“太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太极即是一理又是众理的综合,太极包含万物整体而万物又各具一太极。这就使李侗的“太极”说和“理一分殊”说到朱熹时得到了新的发展。再次,朱熹深受李侗重“分殊”思想的影响,在强调“理”为万物之本的基础上,全力以求“理之用”。朱熹在《挽延平李先生三首》诗中就表达了对老师李侗教诲的思念,“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有疑无与折,浑泪首频搔。”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朱熹自24岁初见李侗,31岁正式受学,其间曾四次见李侗。朱熹之学有来自李侗的影响,也有直承程颐,但就程氏学脈而言,杨时一传而为罗从彦,罗从彦再传而为李侗,则朱子为杨时之三传。罗从彦、李侗亦因朱熹而知名。
【思考题】:
李侗的理学思想在哪些方面对朱熹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