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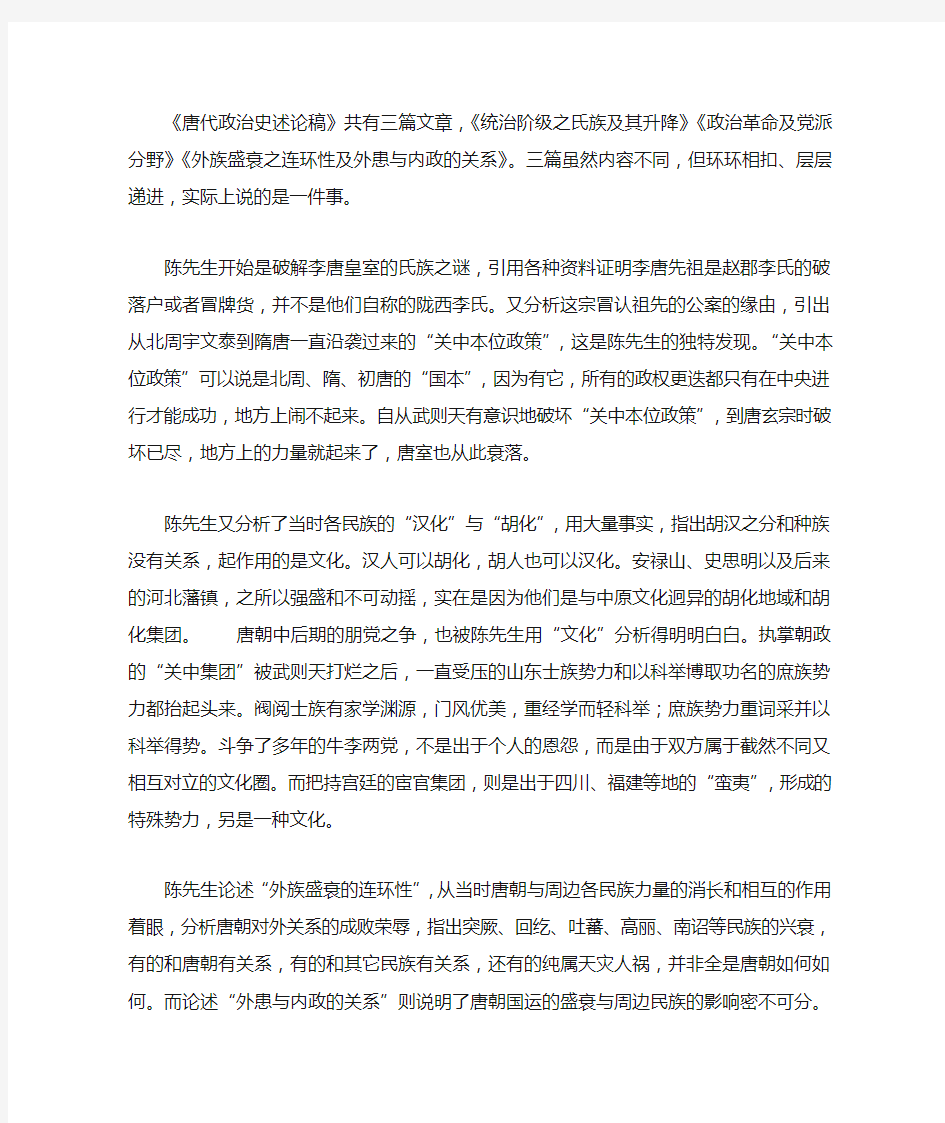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共有三篇文章,《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三篇虽然内容不同,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
陈先生开始是破解李唐皇室的氏族之谜,引用各种资料证明李唐先祖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或者冒牌货,并不是他们自称的陇西李氏。又分析这宗冒认祖先的公案的缘由,引出从北周宇文泰到隋唐一直沿袭过来的“关中本位政策”,这是陈先生的独特发现。“关中本位政策”可以说是北周、隋、初唐的“国本”,因为有它,所有的政权更迭都只有在中央进行才能成功,地方上闹不起来。自从武则天有意识地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到唐玄宗时破坏已尽,地方上的力量就起来了,唐室也从此衰落。
陈先生又分析了当时各民族的“汉化”与“胡化”,用大量事实,指出胡汉之分和种族没有关系,起作用的是文化。汉人可以胡化,胡人也可以汉化。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后来的河北藩镇,之所以强盛和不可动摇,实在是因为他们是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唐朝中后期的朋党之争,也被陈先生用“文化”分析得明明白白。执掌朝政的“关中集团”被武则天打烂之后,一直受压的山东士族势力和以科举博取功名的庶族势力都抬起头来。阀阅士族有家学渊源,门风优美,重经学而轻科举;庶族势力重词采并以科举得势。斗争了多年的牛李两党,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由于双方属于截然不同又相互对立的文化圈。而把持宫廷的宦官集团,则是出于四川、福建等地的“蛮夷”,形成的特殊势力,另是一种文化。
陈先生论述“外族盛衰的连环性”,从当时唐朝与周边各民族力量的消长和相互的作用着眼,分析唐朝对外关系的成败荣辱,指出突厥、回纥、吐蕃、高丽、南诏等民族的兴衰,有的和唐朝有关系,有的和其它民族有关系,还有的纯属天灾人祸,并非全是唐朝如何如何。而论述“外患与内政的关系”则说明了唐朝国运的盛衰与周边民族的影响密不可分。唐朝的灭亡,一方面固然是黄巢起义摧毁了唐朝的经济命脉--江南地区,另一方面也和西南方向南诏民族的搔扰牵制大有关系。
以上的论点,多是前人不曾发现,而属陈先生首创。以我的感受,陈先生治学,不独重视史料考据和辨证分析,也另有深意存焉。他祖父陈宝琛是维新变法的志士,因变法失败而丢官;父亲陈三立是著名的晚清四公子之一和大诗人,因痛于日寇侵华绝食而亡;他自己曾中过晚清的探花,又出国留过学,一生经历,正是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中国那个时代,不仅面临着异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本民族在各方面水深火热,而且其固有的文化也面临着异化、堕落和销亡。他曾说王国维是被“文化所化”之人,他自己何尝不是!王国维以身殉了即将销亡的文化,陈寅恪为其作了墓碑,自己却为了这文化而活着。著书立说,也无不是发扬中华文化之优秀成份,立弘愿将其传承下去,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现让他伤心的“胡化”。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文化精神,在有关方面让他出任“中古所”的所长时,晚年的他“极其狂傲”地提出“不学马列”,并要国家领导人出具书面的保证。其实他何曾拒绝做为学术思想的“马列”,只是不想把“马列”奉为不与其它学术平等的神圣而已。
抛开这些不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及其观点,用于研究现当代的许多问题,我觉得也颇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书笔记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890—1969)的传世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是我们研究中国隋唐史的必读之书。前者从礼仪开始,备述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各项制度的渊源流变,追溯隋唐制度之三个来源:一为北魏、北齐;二是南朝梁、齐;三是西魏、北周,从而纠正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隋承周禅,而隋享国日短,唐继隋祚,隋唐制度都来源于西魏、北周的错误认识。但“至于唐代政治史事,以限于体例,未能涉及”(P1),遂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问世,该书对有唐一代的政治史作了精辟
的论述,上溯两晋、南北朝与隋,下启唐以后的变化,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动态中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方法的经典之作,为后世学者研究唐史作出了示范。本文就学习中的一些认识和体会,作一小小的总结,以巩固学习效果。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成于1941年,是陈先生研究隋唐史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分为三部分论述唐代的政治史: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作者从民族升降、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外患与内政关系三处落笔,深入地剖析了一代政治。上篇共四十八页,作者开宗明义的指出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问题在于种族与文化,这也是本篇重点论述的问题。实际上此观点也是陈寅恪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一个重要的角度。随后从现有的史料出发,考证了李唐氏族的世系,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P11),其血统原是华夏族,后与胡夷混杂,宇文泰入关之后,曾令相从之汉人改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即在此时,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并进一步指出,有唐一代的官书所记载的李唐皇室渊源的史料,大部分是被后人讳饰夸诞过的,我们对此不可全信。这里作者为我们鉴别史料真伪做出了榜样。但李唐果真出于赵郡,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也提出有疑问:“李唐岂真出于赵郡李氏耶?若果为赵郡李氏,是亦华夏家也,又何必自称出于陇西耶?”李渊距宇文泰入关不到一百年,果真在这时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唐室君臣不会一点不知,史书中应该会留有痕迹。更何况唐太宗一贯是打击、敌视山东望族,而重用关中军事权贵,他提拔的宰相,山东11人中,也大多为庶族,他对山东士族的政策与他的赵郡郡望是矛盾的,此处姑且存疑。
之后作者提出胡化和汉化的问题(P17),指出北朝时文化重于血统,汉人与胡人的分别,不论血统,只视其所受的教化为汉或为胡而确定,诚所谓“有教无类”。此点有中国人传统上重文化、轻血统的观念有不谋而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对边区的少数民族的蛮夷戎狄之称,大体上就不是按血缘来划分,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与中原姬姓、姜姓诸族互相通婚,如晋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而他们区分蛮夷更是以一种文化,以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如不像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非城市国家的地区,则称为蛮夷地区。唐时的胡汉只分别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唐时河朔地区已成胡化地区,与尊孔教、重礼教及以科举仕进为安身立命的中原地区其文化上有着极大的差别,并由此举出四个例子证明二者文化之区别:例证之一,秀才卢霈年二十不知周公、孔子,只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例证之二,其地暴刑暴赋,唯恤军戎,对衣冠士人遇如奴隶;例证之三,从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得知长安文化区不容这样有野心之人,惟有北走河朔;例证之四,李益虽登进士而不得意,北走范阳。进而根据《旧唐书·藩镇传》,并取其它有关史料中有关诸传活动范围在河朔地区及以外地区的人相参考,发现有两种人,一是其族本为胡人,二是其族原为汉人,但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无异。前者为种族,后者为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为胡风,中原也把此类人看作胡人,因此可见此时区别胡化与汉化之标准亦更终于文化。作者认为善骑射者,胡人之风也。安史之徒之所以善战,作战力强,主要原因在于民风善胡。其后以大量的史料考证安禄山之为九姓胡(《旧唐书》称为杂种胡人),史思民为突厥杂种胡人,及善战事。更以大量的篇幅叙述同时并后来河朔及其藩镇胡化之事迹,并得出结论:玄宗之时,河朔地区的胡化就已经开始了。指出其地区胡化的三个原因:远因为隋季之丧乱;中因东突厥之败亡;近因动突厥之复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种族与文化的问题不仅是我们研究隋唐史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历史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二
中篇的标题是“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在本篇中作者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掌握玄武门与否,是中央政治革命的关键所在,即北门禁军之向背与革命成败的关系问题。书中祥述了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其成败都与玄武门的得
失,是否掌握北门禁军有密切的关系;二是皇位的继承问题;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间的关系问题;四是牛李党争问题;五是唐代的科举;六是永贞内禅与宦官专权问题;七是内廷与外廷之联合与斗争及其在文宗时期在政治上的盛衰分合。
这里仅就第三个问题(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间的关系(P69-78))谈谈自己的认识。作者在上篇论述了关中本位政策之由来,并形成了以李唐皇室为首的关陇军事集团。但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上崇尚门阀之风,山东士族形成极高的门第,如崔、卢、李、郑四大姓,李唐虽贵为天子,但其社会名望不及山东诸姓,甚至到了文宗的时候,还感叹说:“吾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为改变这种情况,关陇集团凭借手中的政权对山东士族进行打击,唐太宗时修《姓氏录》则是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进行斗争的表现。这一斗争还反映到唐初的统治政权中,以唐太宗朝为例,太宗提拔的宰相二十八人,其中山东人士十一人,大多是山东寒族,如张亮,本是一个农夫,魏征、戴胄、马周、张行成的家门都甚为微寒。这是何故呢?究其原因,太宗不提拔当时名望极高的山东士族,为的是避免其势力过于强大,从而平衡山东士族与士族之间的势力,最终达到使关陇集团的势力与山东士族相平衡,甚至超过山东的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李唐从建国始,两集团间就一直处于打击与反打击的关系中。
三
下篇论述的是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虽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但在本篇中他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用唯物主义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我们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不应用孤立的眼光去分析,去观察,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并且是变化发展的。作者认为所谓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意指“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外族发生关系,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唐室中国也必然受到他的影响,或利用其机缘,或坐受其弊。”(P125)所以作者告诉我们研究唐代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应仅仅看到某一个少数民族,而应通晓诸外族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正确的分析唐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利弊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P125)。之后作者从史料出发举突厥覆灭为例,认为它的灭亡“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P128)又如回纥从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钜”,而到了文宗的时候“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P129)这又是外族盛衰连环性之的一个很好例证。文中还分析了吐蕃、高丽、南召等少数民族的盛衰,及其少数民族之间或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观全局,论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特别是对吐蕃、高丽与唐朝的关系时说:“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是这一连环性最明显表现。
其次,作者论述了外患与内政的关系,指出“中国无论何代,即当闭关锁国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与其他民族相接触”。(P148)而这种接触在李唐时期尤为频繁,而这种频繁的冲突对内政也产生影响,当外族向中原发难时,外患的变化必然引起内政的动荡。书中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外患对唐内政引起的影响:一,吐蕃的强大,致使唐屡次对其用兵,导致另外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的废除;二,回纥与中原的绢马贸易,影响了中原的财政经济;三,南召的侵边是导致唐朝灭亡的一重要原因,认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到这里作者在读者面前勾画出唐政治史的大致轮廓,他概要的总结了唐代政治史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是我们研究隋唐史的入门之书,必备之书,它不仅给我们指出唐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之所在,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开拓了我们研究历史的思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书札记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书札记-
今据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下简称《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一书检索所得其引用书籍总计64种之多,所引书目虽均为研究政治史所用,略加分析即可视为唐史研究之门径。
全书所引“正史”共计《旧唐书》、《新唐书》、《北史》、《南史》、《晋书》、《宋书》、《魏书》、《梁书》、《周书》、《隋书》、《北齐书》11部,基本涵括从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历史。《旧唐书》、《新唐书》、《隋书》作为隋唐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是治隋唐史者的共识,何以先生要将此段历史的研究放在从两晋开始直到唐末长达700余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加以考察?先生有一段话可以做出解释:“总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P332,三联2000年6月版。)南北朝实为我国历史一极为特殊重要的时期,其影响要到隋唐两朝才会有较为清楚的脉络,先生在论述中国中古学术时说:“盖自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虽西晋混一区宇,洛阳太学稍复旧观,然为时未久,影响不深。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保持不坠者,固有地方大族势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崔浩与寇谦之》,同前书,P147-148)这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变化,然而论及唐初政治变化时,学术的下移实为关键。试举先生论述隋唐制度渊源时认为:“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叙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P2,中华书局1963年5月新1版。)而隋唐制度渊源有一支正是继承北魏的文化。可见研究隋唐史不可不明晓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以明历史发展的轨迹,才是治史的真境界。陈先生极力推崇治史者的“通识”,观先生所著之书,“通识”之学是先生期许为治史者所应有的标准,并以个人实践身体力行,斯为后世学子之垂范。
通观全书,陈先生在所引用的史料中,绝大多数是《旧唐书》、《新唐书》,这正是证明了他所一贯所推崇的从平淡出探赜发微的治史精神。先生论及隋唐制度时曾言:“独其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出遗文,足资补正,然其关系,重要者亦至少”。(同上书,P1)有唐一代之史料,传世者最重要的是后晋刘煦所编修的200卷的《旧唐书》和北宋欧阳修、宋祁所修的225卷的《新唐书》,两书各胜专场,都有传世的价值。《旧唐书》多采用唐代历朝《实录》入书,史料价值很高,可惜失之熔裁,显得芜杂枝蔓;而《新唐书》先有宋祁编撰,然后欧阳修再主持编撰,文笔优美是其一长,但过分讲究文笔,删去了大量的史实,却又是其短。两书并行于世自有其道理,旧书虽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新书也增加了相当多的史料,尤其是新书增加了旧书所没有的“表”,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书的编修者所处在宋代最繁荣的宋仁宗时期,大量的公私著作的出现,客观上为新书的编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和人文环境,而且新书的编撰者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才识俱佳,这一切都保证了新书的质量。但是,体例结构的完善掩饰不了新书在史料方面的困窘,稍晚的吴缜就写了《新唐书纠缪》,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于唐代史实多取材于《旧唐书》。今天我们研究唐史时,两书都不应该偏废,应该怎样来研究他们呢?后世学子当以先生《述论稿》一书为老师,从先生的亲身实践中学习,以一窥唐史研究的门径,今略举数例以明先生之卓识也。
如该书第70页,论述山东世族时便以旧书为主,取《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传上袁朗》:“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
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但新书也有增添新史料处,该书第29页到30页论安禄山时,取《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同时又取《新唐书》卷225卷《逆臣传安禄山传》:“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少孤,随母嫁虏将安延偃。……乃冒姓安,……通六蕃语,为互市郎。”这是新书胜旧书的例证。)
总之,两书各胜专场,对此陈先生有一段话作了最好的说明:“《旧唐书》多保存原始材料,不多改易词句。……然则唐史新旧两书,一则保存当时名称,一则补充其它解释。各有所长,未可偏废。”(《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金明馆丛稿二编》,P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1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陈先生在该书中引用了《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玉海》三部类书,《太平广记》为唐以前古小说的渊薮,《玉海》为宋人王应麟著作的汇编,《册府元龟》则为宋真宗时编撰的一部类书,北宋以前的史书大多整段辑入,完整保存了北宋以前的史实,《旧唐书》在后晋编成,在传刻的过程中有许多讹误,《册府元龟》则保存史料较为完整。于此,可见陈先生对史料的审慎态度。
二.注解的史料价值
古人著书因为时代相隔,前时代之书,后人难以理解,于是为书作注解就成为必做的工作。注解的价值不仅为读书者指点迷津,同时注书者在注解的过程中一般会引用大量的书籍,而且注书者在注解的过程中多有个人的见解,这些都是历史研究的珍贵材料。
( T陈先生是较早重视注解的史家,遍检《述论稿》一书,《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三书中,陈先生尤重的是它们的注解。以《资治通鉴》为例,《述论稿》中引用最多的是胡注。这是因为胡三省以毕生之力研究《通鉴》,实为王应麟以后最有成就者,他对史实的认识多有卓见,可以发前人之微言大义。此外,后人对唐史的认识也可作为史料入书,如《述论稿》开篇就举朱熹的话来说明本书的本意。对于史论的价值,陈先生早有论定:“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意于即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同上书,P248。)- `/ y' F: n+ Y) K T8 |, R
三.诗文证史
后人论及先生史学,总以“诗文证史”为先生治史的最大特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同上书,P236)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敦煌学,但是用来说明诗文集中史料的应用还是十分恰当的。在先生笔下,唐史研究之所以开一时代之风气,并发扬光大,傲然独立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之林,新材料的应用斯为关键。在《述论稿》一书中论及唐代中叶统治阶级之升降,就大量采用《元氏长庆集》、《全唐诗》、《樊川集》、《昌黎集》等书的记载,并与正史相参证。这一点先生早有论述:“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撰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史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与灌输与私书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同上书,P74。)
四.小说杂记
遍览《述论稿》所引书目,有大量小说杂记之类的著作,如《大唐创业起居注》分类虽有歧异,(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于《史部编年类》,P420,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书目答问补正》则列于《别史类》,P80,中华书局1963年2月第1版。)但此类书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在纪录唐初起的史实是最具权威的。这样的例子在《述论稿》中还有许多,如该书在第74、78、83、114、118页五处引用《唐语林》,可见其价值。但正如陈先生所说:“大抵私家撰述易流于诬妄”(同上)这一点是私家撰述的通病,无论其
体裁如何,这是在历史研究需要加以注意的。(如《贞观政要》属于史部,而《玉泉子》、《大唐新语》、《幽间鼓吹》、《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等书则列入《子部小说类》)
五.今人著作
张尔田先生的《玉溪先生年谱会笺》于李商隐史实考订精详,为治唐史者所必备,陈先生采其说入书,暗喻后世学子所遵循着两事:“关注别人的研究成果,引用时不加隐没。”六.读书重版本
}先生取《贞观政要》时特加注明为“戈本”,这是由“戈本”的价值决定的:“书中之注,为元至顺四年临川戈直所作。又采唐刘芳晋刘煦……二十二家之说附之,名曰集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杂史类》,P463,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这是“戈本”价值所在。至于其他书籍虽未列出版本,从此例可以推想。
七.考古材料的应用
' 《述论稿》第54页采用《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来证明“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即先生所谓:“此亦新史料之发现,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同书同页)对于考古材料的应用,先生在论述王国维先生学术成就时曾言:“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王观堂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P219)近代学术的发展是因为地下资料的发现,有尤以殷墟、汉简和敦煌文献的发掘为最。但是,先生于此考古之材料的作用不无保留:“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至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同上书,P219)看来多数之文字记载还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唐史研究当以文献为主,考古及其他物质遗存当与文献相参证。(先生以甲骨文为“地下实物”)
八.余论
敏自入学以来,抱定史学研究之信念,欲承前哲众贤之遗业,并发扬光大,以见我中华复兴之盛业。忆及七年前初听先生之名,景山仰止之心难以自已,及读先生之书,方初步明了先生之学术浩浩乎无涯际,先生曾谓王国维先生“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王观堂先生遗书序》,同上书,P219)这何尝不是先生自况也。环顾神州,倡言先生学术者不知凡几,但得先生之神韵者仅数人而已,斯为本国学术之悲也。敏自幼“先天不足”,资质驽钝,欲强以承先生之遗业并发扬光大为念,非一时狂妄浅薄之言。今日之情势大异先生之时,前哲筚路蓝缕之功与技术之进步真为吾辈学子之臂助,适逢中华复兴之时,吾国学术必能承前哲遗业而放异彩,以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此为吾辈学子所共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