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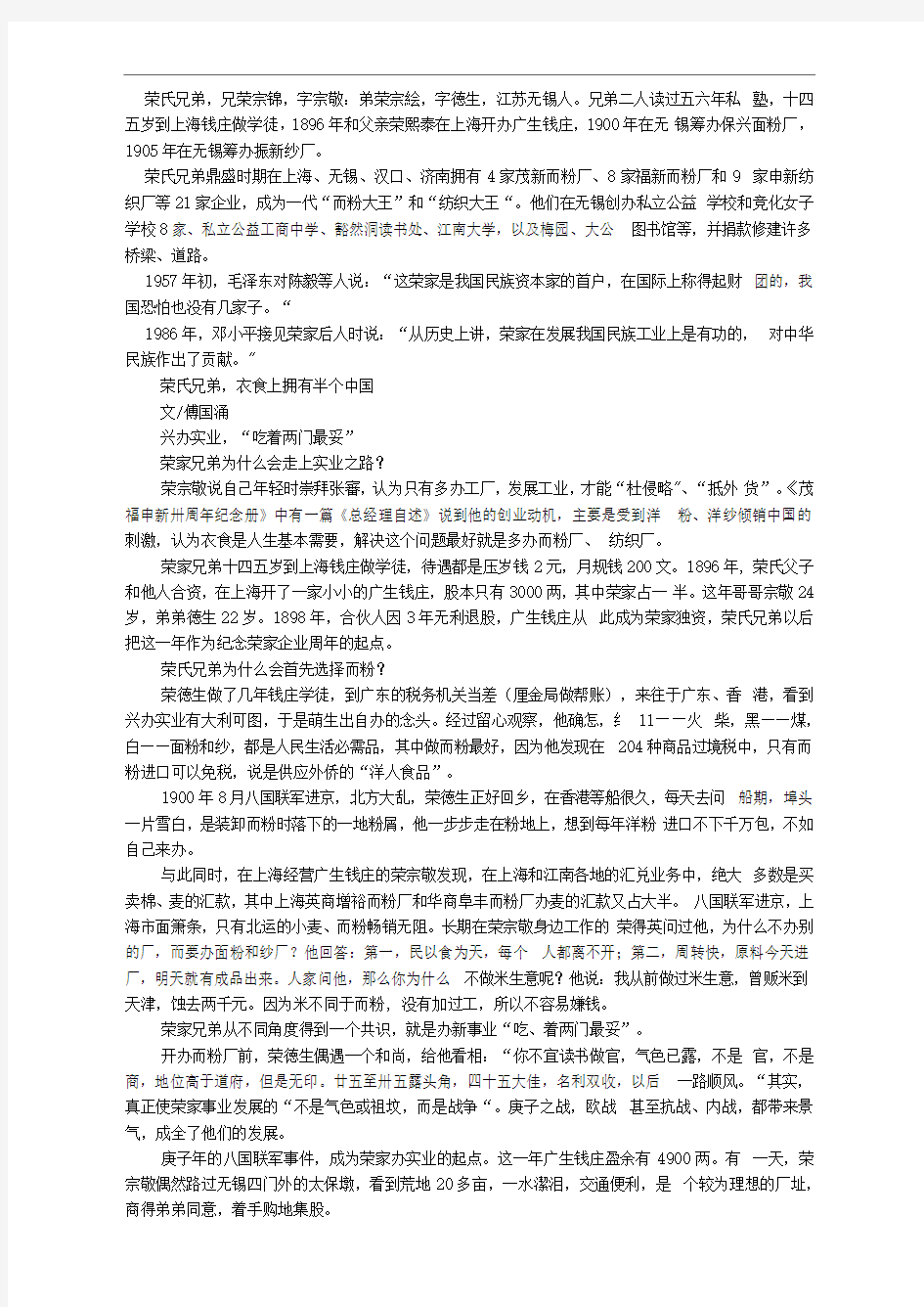

荣氏兄弟,兄荣宗锦,字宗敬:弟荣宗絵,字徳生,江苏无锡人。兄弟二人读过五六年私塾,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1896年和父亲荣熙泰在上海开办广生钱庄,1900年在无锡筹办保兴面粉厂,1905年在无锡筹办振新纱厂。
荣氏兄弟鼎盛时期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拥有4家茂新而粉厂、8家福新而粉厂和9 家申新纺织厂等21家企业,成为一代“而粉大王”和“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创办私立公益学校和竞化女子学校8家、私立公益工商中学、豁然洞读书处、江南大学,以及梅园、大公图书馆等,并捐款修建许多桥梁、道路。
1957年初,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这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
1986年,邓小平接见荣家后人时说:“从历史上讲,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
荣氏兄弟,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文/傅国涌
兴办实业,“吃着两门最妥”
荣家兄弟为什么会走上实业之路?
荣宗敬说自己年轻时崇拜张審,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中有一篇《总经理自述》说到他的创业动机,主要是受到洋粉、洋纱倾销中国的刺激,认为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就是多办而粉厂、纺织厂。
荣家兄弟十四五岁到上海钱庄做学徒,待遇都是压岁钱2元,月规钱200文。1896年, 荣氏父子和他人合资,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股本只有3000两,其中荣家占一半。这年哥哥宗敬24岁,弟弟徳生22岁。1898年,合伙人因3年无利退股,广生钱庄从此成为荣家独资,荣氏兄弟以后把这一年作为纪念荣家企业周年的起点。
荣氏兄弟为什么会首先选择而粉?
荣徳生做了几年钱庄学徒,到广东的税务机关当差(厘金局做帮账),来往于广东、香港,看到兴办实业有大利可图,于是萌生出自办的念头。经过留心观察,他确怎,纟11——火柴,黑——煤,白——面粉和纱,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做而粉最好,因为他发现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而粉进口可以免税,说是供应外侨的“洋人食品”。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京,北方大乱,荣徳生正好回乡,在香港等船很久,每天去问船期,埠头一片雪白,是装卸而粉时落下的一地粉屑,他一步步走在粉地上,想到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
与此同时,在上海经营广生钱庄的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其中上海英商增裕而粉厂和华商阜丰而粉厂办麦的汇款又占大半。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面箫条,只有北运的小麦、而粉畅销无阻。长期在荣宗敬身边工作的荣得英问过他,为什么不办别的厂,而要办面粉和纱厂?他回答:第一,民以食为天,每个人都离不开;第二,周转快,原料今天进厂,明天就有成品出来。人家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做米生意呢?他说:我从前做过米生意,曾贩米到天津,蚀去两千元。因为米不同于而粉, 没有加过工,所以不容易嫌钱。
荣家兄弟从不同角度得到一个共识,就是办新事业“吃、着两门最妥”。
开办而粉厂前,荣徳生偶遇一个和尚,给他看相:“你不宜读书做官,气色已露,不是官,不是商,地位高于道府,但是无印。廿五至卅五露头角,四十五大佳,名利双收,以后一路顺风。“其实,真正使荣家事业发展的“不是气色或祖坟,而是战争“。庚子之战,欧战甚至抗战、内战,都带来景气,成全了他们的发展。
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事件,成为荣家办实业的起点。这一年广生钱庄盈余有4900两。有一天,荣宗敬偶然路过无锡四门外的太保墩,看到荒地20多亩,一水潔泪,交通便利,是个较为理想的厂址,商得弟弟同意,着手购地集股。
荣家世交朱仲甫与兄弟二人商左集股3万,各认一半。以3000两为一股,兄弟各以3000 两入股,另外再集9000两。实际招到了13股,取厂名为保兴而粉厂。当时全国而粉厂只有区区四五家,他们去参观取经,连主要的轧粉车间都不让进。到1902年保兴正式投产时,全国开工的面粉厂也只有12家,苴中民族资本的8家,保兴是规模比较小的一家,只有4 部石磨、3道麦筛、2逍粉筛,但是以法国石磨配英国机器,价格比较便宜,可以互补不足,而且有60匹马力的引擎在当时也是较为先进的。
1921-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称荣氏是中国而粉工业的创始人。
吴椎晖有个说法,无锡人富于“两发主义”,第一是“发痴”,第二是“发财“。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没有发痴的坚决毅力,必致中途失败:任何事业不抱有“发财”希望,即无百折不回的意志,也难以为继。这就不难理解,南通只有一个張密,而无锡不止荣氏一家,至少还有杨家、唐家、薛家、周家等企业家族,无锡因此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赢得了“小上海”的称誉。
但是当荣家兄弟在1900年创业时,无锡风气未开,先是地方士绅告他们擅自将公田、民地圈入,官府査对并无此事。这些人又告保兴而粉厂的烟囱妨碍文风,还有谣言说烟囱要用童男童女祭灶,才竖得起。官司从无锡打到常州,又从常州一路打到南京,靠了合伙人朱仲甫的官场人脉,最后两江总督批示:“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平,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风有碍?"保兴而粉厂还在当地获得10年专利,听说无锡知县为此被摘了顶戴。
1902年2月保兴面粉厂正式生产,一个日夜可出而粉300包。当时无锡上粉行很多,本地而粉需求只有一二百包,但浙江、上海一带酱园业需要的面粉都到无锡装船,外销而粉量很大。因为市井传言机器粉颜色白,里而掺和有毒的洋药,所以,他们还要加上土粉才能销出去。1903年,而粉厂没有大的起色,合伙人朱氏见无利可图,提岀退股。荣家兄弟表示荣姓股份决不出让,反而增股到2.4万两,占了近半数,成为最大的股东。此时股本扩大到了5万,又添了新机,改爼为茂新而粉厂。到1905年,而粉厂每天有500两盈余。弟为经理,在无锡管厂;兄为批发经理,常驻上海,主要管广生钱庄。荣徳生每天只睡6个小时,早起晚归,心情却很愉快。
“兵船“渡过危机,驶向世界
1908年,荣家而临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方面国内麦收不佳,美国而粉倾销,麦贵粉贱, 茂新连续3年巨额亏损;另一方而荣宗敬因卷入投机风潮,亏本5万两,牵动钱庄资本,广生摇摇欲坠。
摆在荣氏兄弟而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求助朋友,苦度难关,但这条路很难,债主纷至沓来,往来行庄都不信任他们,荣徳生自称这是入市以来最困难棘手的一次;二是将钱庄歇业,集中力疑办工厂,兄弟俩商左:保茂新、振新(1907年他们与别人合伙在无锡开办的纱厂), 放弃广生。他们从此发愤用力,专心办厂。弃车保帅的选择对于荣氏兄弟来说是痛苦的,广生钱庄毕竟由父亲一手创办,是他们创业的起点。
1910年,茂新因为机器新,而粉品质好,营业出现转机,开始使用绿“兵船"商标。同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兵船"得了三等奖牌,荣氏兄弟深感欣慰。
1912年,茂新再次因资金周转困难,原料跟不上,而陷入困境。荣徳生自述这是创业以来的第二次风险。正在危急之时,听说无锡到了大批川麦,各厂因市而不好,不敢放手进货,货主急于回川,愿意赊欠,等而粉卖出再付款。靠这批麦子,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一年,而粉业兴旺,茂新扩大生产,又添新机,又建厂房。“兵船"牌开始龙俏,成为面粉市场的爼牌,价格超过阜丰岀产的名牌“老车“。一年下来,茂新大大盈利,还淸历年所有欠债,还盈余数万两,荣氏在而粉业的蹿升由此开始。茂新面粉在开机生产10年后异军突起, 从此信用大著,销路大增。
1913年荣氏兄弟再接再厉在上海开办了“福新”面粉厂,品牌借用“兵船”,牌子硬,货没出来,就已被订购出去,货款预付,周转金不用愁。办麦也和茂新搭在一起,信用、关系一切现成,购进麦子,付的是上海7天期的商业汇票,小麦当天装船运到上海厂里只要一个晚上,再有一天就变成了面粉,此时批发部已收到预付的货款,兑现汇票在时间上还绰绰有余。所以,福新一开厂就很顺利,几个月嫌了4万多。福新系统在上海滩迅速扩张,福新二厂、三厂、四厂接连出现,1916年开始筹办福新五厂,伸展至汉口,在上海则一直开到八厂为止。
源出太湖,穿越整个上海市区的苏州河沿岸,荣家企业的烟囱一支又一支冒烟。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一起,荣徳生在1916年就认定可以放手做纱、粉。
原因很简单,都是必需品。也正是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提供了出口机会,外国向茂新订购“兵船“,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走向英、法、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因为供不应求,价格大大上涨。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就规定以“兵船“为中国出口的标准粉。
荣氏兄弟遇上了一个天赐良机,1915年一1921年的7年间,国内一下子出现了81家面粉厂。中国从一个而粉输入国变成了输岀国。直至1919年,在无锡的5家而粉厂中,荣氏拥有4家,占资本额的80%.到1921年,茂新、福新12个面粉厂,从最早的4部粉磨增加到301部,每日夜可出面粉76000多袋,占全国而粉产量的23.4%、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的31.4%,生产能力扩大了250多倍,发展速度之快,在整个中国企业史都是空前的。(到1936 年,茂新、福新12个厂每日夜可出而粉96500袋,占全国“关内“的32.7%。)
至此,荣氏兄弟“面粉大王”(“麦粉王”)的名声不胫而走。
荣家兄弟的事业从4部石磨开始,等到石磨改成钢磨,大如圆桌的石磨才宣告退休,4 部石磨,一共8月,设在豁然洞旁的小广场,正好是8张茶桌。2007年2月初,我在梅园“乐农别墅“(荣徳生晚年住所)前看到的3张石桌,就是保存下来的碎片按原样用铁箍箍成的3貝石磨。它们不仅是荣家事业的见证,也成了中国企业史上的重要文物。
茂新最早的厂房已被日军炸毁,现存建筑是1946年重建的,包括麦仓、制粉车间、粉库和灰色的三层办公楼。车间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台圆筒状的扬麦机“除尘器”,一个随意放着的大石磨,以及两条依墙而立、高达9米的螺旋形转梯,这是当年从英国进口的原装设备,面粉打包后就是通过转梯从5楼滑到一楼,然后用小推车推泄。厂区紧挨码头,遥想当年,闻名遐迩的绿“兵船"而粉就在这里装船,运往世界各地。
创办“申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荣家兄弟在而粉业大展身手的同时,在纺织业也得到起飞的机会。早在1905年,他们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07年2月开车,所产“球鹤“纱曾经风行无锡、常州等地,可以与日纱名牌“蓝鱼牌”相匹敌。荣徳生担任振新经理,有意扩大振新,甚至想办4个纱厂,从无锡发展到上海、南京、郑州,将3万纱锭扩大到30万。振新董事会听到荣徳生的构想很是惊慌,说照这样嫌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荣徳生说:“要拿大钱,所以要生产,照3万锭能赚几何?“当时的纱厂还没有一家超过3万锭的,此事被称为企业史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故事。就在此时,大股东荣瑞馨指控荣徳生账目不淸,甚至打起了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合作很难继续下去,荣家兄弟选择退岀振新。
申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全称是“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资本以他们兄弟为主,共投资30万元。1915年,他们买下苏州河边周家桥24亩地,一个废油厂的旧址,四周一片荒地,没有街市,连马路也没有。等到申新出现,附近陆续有了店铺,上路也变成了柏油路, 周边的繁华从老照片上可以感觉到,厂门前两旁的行道树虽然新种,店而楼房却很气派。
1916年,申新开车时只有12960枚纱锭,规模不如振新,但是,正如申新大门口的“业精于勤"横匾所说,荣家兄弟有信心。他们采取无限公司形式,就是吸收振新的教训,痛感有限公司的股东束缚太大,一旦意见分歧,没办法发展。无限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会没有大权,总经理掌握全权,也就是集中于荣宗敬一个人。无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只能转让给内部的股东,章程规左“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于其他人°"而且企业可以随便改组,有利于他们兼并苴他股东,特別是小股东,运作完全以荣家为中心。
申新开办,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贏利。
1917年,荣氏兄弟买下日商“恒昌源”,改为申新二厂,这是中国棉纺工业史上华商纱厂购并日商纱厂的唯一一例。1919年,他们集资150万在老家无锡筹办3万锭的申新三厂, 因为荣瑞馨不希望
振新纱厂的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从中作梗,费了一番周折,靠了张春的帮助,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照无锡当地县长,好不容易才办成。却又因为世界大战,他们订购的机器姗姗迟来,到1922年1月31日才正式开车出纱。申新三厂横跨无锡的梁淸溪河两岸, 东岸是纱、布厂,西岸是公事房、职员宿舍、发电、轧花、修机等部,有桥相通,南通太湖, 北邻运河,离铁路线很近,位垃很好,设备精良,鼎盛时工人6000、职员120多人,许多管理制度的创新、劳工自治区等都由此试验。
有人说,而粉和棉纺对于荣家,如同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21 年,荣家的纺织厂从1个发展到了4个,有10850员工,19万枚纱锭,日出纱500件,布6000匹。与1918年相比,1922年全国棉纺业的纱锭数增加了1.1倍,申新是9.4倍,全国布机台数增加了1倍,申新是1.7倍,荣家占有全国民族资本纱锭的20%,布机的28%,成为中国纺织业当之无愧的首席代表。
1919年,荣宗敬在上海江西路58号买下二宙八分地,1921年造起一座英国城堡式的办公大楼,称为“三新大厦“。《茂福申新卅周年纪念册》说,总公司的地位如同人体的头脑,各厂是五官百骸,总公司对各厂一视同仁,希望它们平均发达,他们的关系比唇齿还要密切。总公司下而主要有两个账房,一个外账房,办理进货、岀货的手续单据,并向各厂汇报:一个银账房,专管银钱出纳和资金周转。茂、福、申新各厂分别经营,会计独立,各有股本, 照股分红,厂长总揽厂务,分别负责,但各厂的采购和销售成品,都要通过总公司,总公司简直就是申新的棉纱布市场和福新的麦粉市场。
每天中午,上海的各厂长一泄都要到总公司向总经理请示,总公司说到底就是荣宗敬个人集权的体现和他威望的化身。国内舆论界把荣家兄弟誉为实业界的“骑士”,日本的小学课本中有专文介绍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48岁的荣宗敬第一次在可容纳上百人的会议厅开会,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他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一贯低调谦虚的弟弟也不无骄傲地说:“事业几满半天下“。
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
开工力求貝足,扩展力求其多
主持汉口申新四厂的荣家女婿李国伟回忆,荣宗敬常对他们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苴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 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
荣宗敬的一个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出别人的弱点,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市而银根紧时, 他大量抛棉花,月底交割时逼对方收现货。如果手中没有现货,他便调大疑车辆到申新各厂的仓库运存棉来交付。上海市场棉价一跌,全国行情跟着下滑。这时,他命令各地分庄大量收棉。上海抛岀一万担,各地收进几万乃至十万担。
荣宗敬本人虽不懂新设备、新技术,但他相信外国机器,早年他曾为振新纱厂买了先进的发电机,装的马达在当时内地工厂中是第一家,安装后效能非常好,追随他多年的荣鄂生说:“宗先生脑筋新,真是了不起。"在荣家兄弟心目中,原料好,机器新,就能赚钱。
荣徳生说哥哥“添机成癖”,其实两人在这一点上想法一致,他也喜欢新机器,他们都觉得与其留着现钱,不如多添机器。他女儿荣漱仁回忆:
我父亲和伯父都具有兴办工业的信心和决心,所办各厂大多由小而大,从租地、租屋、欠机、添机入手。平日财无私蓄,一切资金除拨出一部分作为地方公益和建设之用外,全部放在企业的营运上而,一有盈余就力图扩大再生产,从没有其他程产、谋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并无雄厚的大资本做后盾,而是靠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靠他们在金融界的信用。1914年荣宗敬42岁生日时,弟弟到上海祝贺。他说办厂就和滚雪球一样,只能往前滚,不能停,这样,别人还在犹豫,自己已发展壮大。他的愿望是自己50 岁时拥有50万纱锭,60岁60万锭,70岁70万锭,80岁80万锭。弟弟也认为“要拿大钱, 所以要大量生产。“
办钱庄岀身的荣宗敬,不断向银行、钱庄借款来扩大企业。他曾对金融界的人说:“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他至少以个人鋼义在7个钱庄、2个银行、1 家保险公司有投资,以公司划义在3家银行有投资,多的几千股,少则几十股,包括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他
在上海储蓄银行开始投资20万,后来增加到45万,成为大股东。他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对他喜欢在银行、钱庄搭一点股份,他弟弟和其他人都不大理解。他对身边的人说:“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一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十万、二十万的资金。“
荣宗敬解决资金的一个秘诀,就是“肉烂在锅里“。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人家关厂,而你却一月幷多起来?他回答:“我是有钱就要开厂,人则有钱就分掉。”这英中道出了荣家企业发展的奥秘之一。申新总公司会计部的荣得英证实,申新除了股息,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余不断滚下去,用来扩大再生产;就像烧肉,老汁水永远不倒岀来。别的厂就不同,红利都分掉。所以积累不起来。
1921年后,棉纺业的黄金时代迅速消逝,棉贵纱贱,许多企业包括穆藕初的徳大、张密的大生等纷纷衰落,被银团接管甚至倒闭、拍卖。从这一年到1931年的10年间,华商纱厂改组、出租、停工、出售、归债权人接管的共有52家。此时荣家却反其道行之,不断收购或添资扩厂,从1925年到1931年的4年里,申新从4个厂扩展为9个厂,这是中国企业史上独具魅力的“荣宗敬速度“。申新9厂纱锭达到521500枚,布机5000多台,雄居全国纱业首席。这一年荣宗敬59岁,离他60岁60万锭的宏愿已不远。几十年后,黄裳到无锡采访荣徳生,还在访问记里感叹:“申新已经有了九厂,振新却还是振新,寂寞地留在了无锡市面不好,为什么他还要买别人办不下去的厂?不少人想不明白,荣宗敬却自有想法:
一、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二、对申新来说,添了一家厂,总公司只要添一本账即可,人手也不用添,工程师、职员都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反而可以减轻(买下老厂,旧职员归原主资遣),小职员提升几个,薪水又不必马上提髙:三、对总公司来说,只要添一本账簿,也不要另设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四、减少一家纱厂也可减少竞争对手,申新并进一家厂,力量更大,竞争更有利。因为产额越多,进料、销货越便易,管理、营业的费用也越节省。
荣宗敬常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虽然没有钱,人家肯欠,我就要借。”“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早就成了他的一句名言。许多人不理解荣家兄弟拼命扩厂,他们的解释冠冕堂皇: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况吾国人口众多,而工业生产落后,产品不敷供应,仰求外洋。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未曾被人点破,申新规模越大,银钱业就越不得不给它放款。有人说,对于银行、钱庄,申新“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申新厂多人多,一旦倒下,那么多工人失业,不是荣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会牵动整个上海。
但是拼命扩厂,负债经营,有利也有弊。申新到1931年负债已达4000多万。短短十几年从1个厂扩大到9个厂,不是有充足的资本,而是靠借贷,一旦金融不再输血就会出现重大风险。这是造成申新1934年搁浅的根本原因之一。
申新搁浅,纺织大王
“弄勿落了“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徳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20多年后,他仍淸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他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此时已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9个纺织厂织岀来的布有1.0236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55圈。
申新并不是1934年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4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而不好,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20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21&33元,市场价却只有204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14.33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
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 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另一原因是赋税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到1500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此外,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1200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岀就在500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
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岀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但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了,赶紧提取存款。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16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汁达6375.9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6898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500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1200多万元,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押款。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总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二点。15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一天凌晨4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而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6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李不仅是棉纺专家,还是申新债主之一荣丰钱庄老板的儿子)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8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
创业易,守业难,
申新侥幸逃过政府吞没
当时,荣家还有无锡的茂新而粉厂有点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徳生求援,但徳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28日,荣徳生长子荣伟仁
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而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徳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于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3 次遇险,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泄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 年荣伟仁早逝,荣徳生痛苦地回忆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荣徳生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11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4点的火车去上海, 到上海只有7点多。9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500万元。
16家往来钱庄的老司务或学生,一夜没有离开上海江西路申新总公司大门口,知道荣家有了办法,才各自散去。人们当时普遍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太多,无力消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过去举债扩厂,全力发展,靠的是信用,信用一失,一切都完了。荣徳生魄力虽不及乃兄,但脚踏实地,说话可以算数。
从1934年6月以来,荣宗敬不断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求助,给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会等部门都写过信。荣徳生到南京当面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岀希望能发行公司债来渡过难关,汪的答复是交给实业部办,实业部则说派人到上海调査再说。
当年7月,实业部提出《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由李升伯执笔的报告书对荣家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报告书认泄申新已资不抵债,还严厉批评申新无组织、无管理,经营亳无系统,结论是:“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而甚多。长此以往,为害更烈。“
报告书提出两条应对方针,一、由政府责成该公司速行淸理,以6个月为限;如果淸理不成,由政府派员淸理。二、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各厂,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据公司法成立新公司,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政府应借给申新300 万元作为营运资本。
实际上是实业部长陈公博想乘人之危,盘算由财政部拨款300万元接管申新,变成国营企业。
荣宗敬对实业部不说“救济”而说“整理“大为不满,得知这一消息,更是气愤难忍,“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他给孔祥熙、蒋介石写信,发出“民商何罪,申新何辜“的呼号,在写给蒋的信中还有一句硬话:“在民商毕生致力于此,为不忍坐视事业之朋溃,鞠躬尽瘁,又何敢辞?”
8月6日荣宗敬给汪精卫的信中说:
平心论之,组织不健全,管理不妥善,无可讳言:岂有无组织、无管理,而可创办二十一厂,奋斗三四十年者?
同一天,他给薛明剑(时任工商部丝绸研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府调查实业专员)写信说:创业易,守业难,三十余年如何过去,不可专家一评而全功尽弃。我做事专家尚未入学, 可笑,可笑。
要强的荣宗敬而临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存亡危急关头,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同情他的实业部商业司司长张翼后说:“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此时,无锡籍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再次拔刀相助,亲自给汪精卫、陈公博、孔祥熙等人写信,而且直接写信给蒋介石。7月18 0,正在牯岭避暑的蒋复电,对于维持荣氏兄弟实业事,已告知孔部长,孔祥熙已回复:“荣宗敬事极表同情,自当设法维持"。财政部确实派人到上海调査,并且与实业部意见不同。7月27日,他给汪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弟以成败论英雄,觉营业之开展有如荣宗敬、陈嘉庚诸君,英才必非寻常,维持英业,并当维持英人。棉业而有荣先生,为值得维持之一人。“对于实业部想借“整理“之名将申新收归国有,无锡纺织厂联合会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表示反对,对实业部的估价也表示异议,认为低估了申新资产。无锡申新三厂、天津市纱厂业同业公会、河北省各纱厂都公开表示,人民毕生惨淡经营的实业,如果政府乘人之危收归国有,于法于理都令人心寒,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