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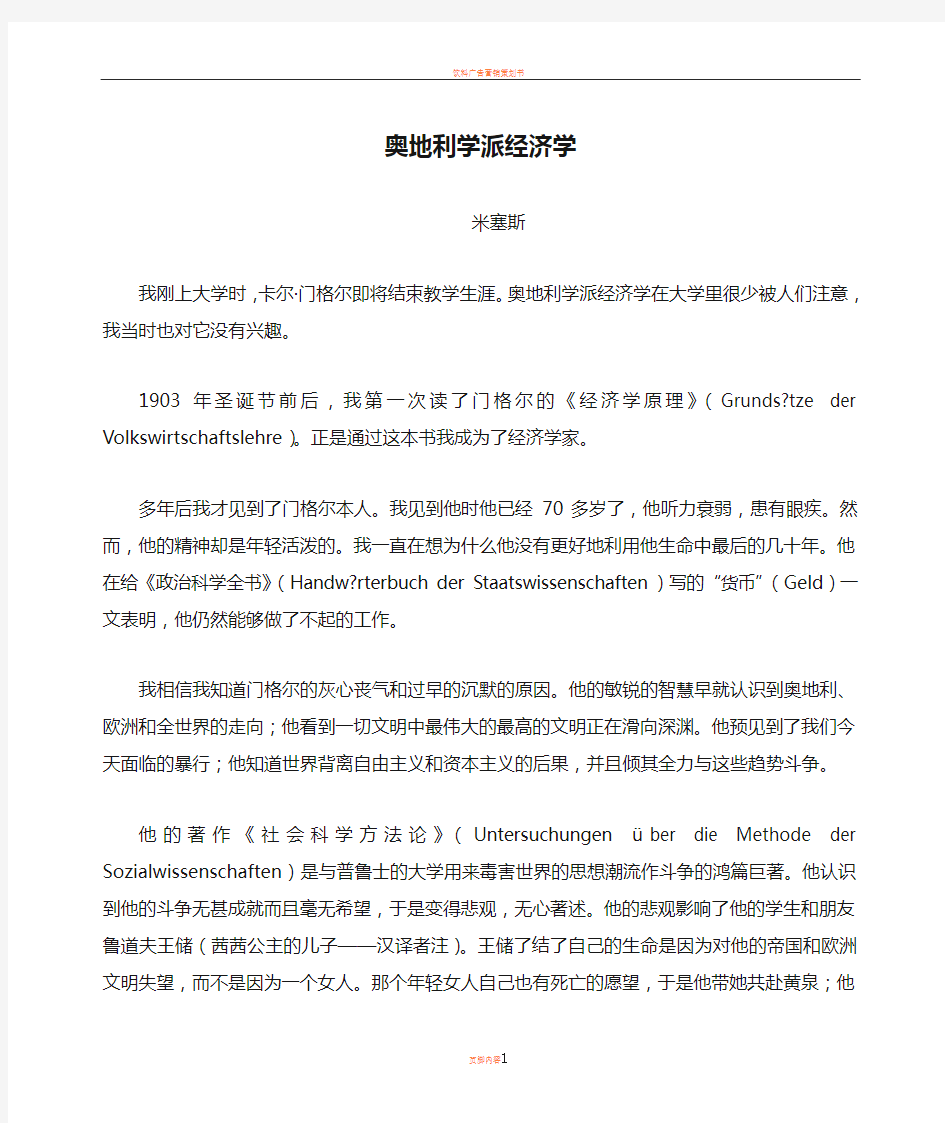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米塞斯
我刚上大学时,卡尔·门格尔即将结束教学生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大学里很少被人们注意,我当时也对它没有兴趣。
1903年圣诞节前后,我第一次读了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Grunds?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正是通过这本书我成为了经济学家。
多年后我才见到了门格尔本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70多岁了,他听力衰弱,患有眼疾。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年轻活泼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没有更好地利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十年。他在给《政治科学全书》(Handw?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写的“货币”(Geld)一文表明,他仍然能够做了不起的工作。
我相信我知道门格尔的灰心丧气和过早的沉默的原因。他的敏锐的智慧早就认识到奥地利、欧洲和全世界的走向;他看到一切文明中最伟大的最高的文明正在滑向深渊。他预见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暴行;他知道世界背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果,并且倾其全力与这些趋势斗争。
他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是与普鲁士的大学用来毒害世界的思想潮流作斗争的鸿篇巨著。他认识到他的斗争无甚成就而且毫无希望,于是变得悲观,无心著述。他的悲观影响了他的学生和朋友鲁道夫王储(茜茜公主的儿子——汉译者注)。王储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对他的帝国和欧洲文明失望,而不是因为一个女人。那个年轻女人自己也有死亡的愿望,于是他带她共赴黄泉;他自杀不是为了那女人。
我的祖父有个兄弟,在我出生前许多年就逝世了。他是兰道(Joachim
Landau)博士,奥地利议会自由党成员,也是党内同僚麦克斯·门格尔(Max Menger)——卡尔·门格尔的兄弟——的好友。有一次他告诉我祖父他与卡尔·门格尔的一次谈话。
据我祖父在1910年前后对我的转述,卡尔·门格尔说过这样的话:
欧洲列强的政策会导致一场可怕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将是恐怖的革命、欧洲文化的毁灭和所有国家人民的贫困。预见到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后,能够提出的唯一的建议是投资于黄金和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证券。
事实上,门格尔本人的储蓄投资于瑞典证券。
一个人在40岁之前就如此清晰地预见到灾难和所有他所看重的事物将遭遇毁灭,他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失望。古代诗人仔细考虑过,普利亚木(Priam)王要是在20岁的时候就预见到特洛伊的沦陷,他该会过怎样的生活!卡尔·门格尔认识到他本人的特洛伊的不可避免的灭亡时还没有走过人生旅程的一半。
同样的悲观侵蚀了所有敏锐的奥地利人。奥地利人的一个可悲的过人之处是能够认识命运。格里尔帕泽(Grillparzer)的忧郁和烦躁出自同一根源。在迫近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使最纯粹、最能干的爱国者菲绍夫(Adolf Fischof)陷入孤独。
人们不难理解,我经常与门格尔讨论纳普的《货币的国家理论》(Staatliche Theorie des Geldes)。(纳普宣称,货币在起源和本质上都纯粹是国家的产物——英译者注。)
门格尔说:“这是普鲁士警察科学的逻辑发展。人们应当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呢?它的精英分子在经济学出现200年后依然崇尚这样的胡言乱语并将其奉为圭臬,而这些胡言乱语甚至并不是新东西。这样的人民会做
出什么事情呢?”
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继承者是维塞尔。维塞尔是诚实的学者,具备高度的修养和出众的智慧。他幸运地比别人更早地了解门格尔的著作并且敏锐地认识到其意义。他在某些方面为这门学科添加了一些内容,但是他不是原创型的思想家,而且可能总体上说为害超过了贡献。他从未真正掌握主观论的精髓,这一局限使他犯下了许多不幸的错误。他的配分(imputation)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的关于价值计算的观点表明,他不能被称为奥地利学派成员。他更多地属于洛桑(Lausanne)学派,该学派在奥地利有两位接触的代表人物:奥斯匹茨(Rudolph Auspitz)和李本(Richard Lieben)。
奥地利学派特有的使之获得永恒的声誉的是它的与经济均衡或者无为相对的经济行动的学说。奥地利学派采用了静止和均衡的观念,没有这些观念经济学思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它始终明白这些观念的纯粹工具的性质。奥地利学派致力于考察市场上实际支付的价格,而不仅仅是在某些从来不可实现的条件下支付的价格。它拒斥事数学方法,不是出于无知或者对数学的精确性的反对,而是因为它并不看重对假设的静态的均衡条件的详尽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未屈从于价值能够被测度的致命错误,并且从未误解这一点:统计数据与经济学理论无关,而仅仅属于经济史。
由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关注人类行动的学说,甚至熊彼得也不能算该学派成员。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熊彼得声称自己赞同维塞尔和瓦尔拉,但并不赞同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在他看来,经济学是“经济量”的学说而不是人类行动的学说。他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是典型的均衡论产物。
有必要纠正“奥地利学派”这个表述可能引起的误解。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都没有想创建一个学术圈里惯常使用的意义上的学派。他们从未试图把年轻学生转变为信徒,他们也没有向这些学生提供教职。他们知道,通过著述和教学能够促进人们掌握一种适用于论述经济学问题的方法,并因此对社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培养经济学家。作为先驱者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认识到人们无法规划科学进步,也无法根据计划培育创新。他们从未试图宣传他们的理论。只要人们具备了接受真理的条件,真理就会靠自己传播。如果人们缺乏掌握其实质和意义的能力,用粗鲁的方式使人们口头信服一个学说是没有用的。
门格尔从未讨好能够给推荐他担任教职的同事。作为部长和前任财政部长,庞巴维克本可运用它的影响;但他从来鄙视这样的行径。门格尔的确偶尔试图阻止(比方说)茨威德内克(Zweideneck)晋升教授,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进展一无所知,但并不成功。庞巴维克从不这么做。事实上,他促使而不是阻碍戈特尔(Gottl)和施潘(Spann)教授在布鲁纳技术大学(Brünner Technische Hochschule)的晋升。
哈耶克在审阅门格尔的科学论文时发现的一份文件最好地阐明了门格尔在这样的问题上的立场。它是这样说的:“在科学中,只有一个方法能够确保观念的最终胜利:人们应当允许任何反对意见充分表达。”施莫勒(Schmoller)、布赫(Bücher)和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则不同。他们拒绝在德国的大学里教授那些不盲从他们的人。
于是,奥地利的大学里的教职落入德国历史学派信徒的手中。韦伯(Alfred Weber)和施比托福(Spiethoff)则在布拉格大学得到了教席。某位君特(Günther)教授成为英斯布鲁克的经济学教授。我提到这一切只
是为了纠正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的边际效用学派垄断了经济学教育的说法。熊彼得多年来是波恩(Bonn)的全职教授。这是德国的大学惟一一次任命一位现代经济学领域的教师。在1870年到1934年间在德国的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或者现代英国学派的著作。无薪讲师(Privatdozent,德国大学里晋升教授前先要做不领薪水的讲师——汉译者注)只要被怀疑属于上述学派就不会晋升为教授。奈斯(Knies)和狄策尔(Dietzel)是德国的大学里的最后两位经济学家。在德意志帝国,他们不教授经济学而是教授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沙皇俄国也是一样,人们教授“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经济史而不是经济学。奥地利的教授和讲师能够教授经济学这一事实与德国“经济政治科学”(economic state sciences)的极权主义主张不相容。
奥地利学派发端于奥地利文化,这个文化在德国必然会遭到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镇压。在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学派是奥地利的。在这块土壤上,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哲学能够生根。在这块土壤上,波尔扎诺(Bolzano)的认识论、马赫(Mach)的经验主义、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以及布劳厄(Breuer)和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成长壮大。奥地利的氛围中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幽灵。在奥地利,人们并不认为“克服”西欧的观念是他对国家的义务。在奥地利,人生享乐说(eudaemonism)、犬儒主义(hedonism)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没有被禁止而是得到了研究。
认为奥地利政府支持所有这些伟大的学说是不对的。相反,它撤消了波尔扎诺和布伦塔诺的教职;它孤立了马赫,没有骚扰胡塞尔、布劳厄和弗洛伊德。它把庞巴维克视为能干的官员而不是经济学家。
庞巴维克是英斯布鲁克(Innsbruck)的教授。他逐渐对这个职位感到厌倦;他无法忍受这个大学、城市和梯罗尔(Tirol)省思想的贫瘠。他更愿意去维也纳的财政部工作。他最后从政府部门退休时本来能够享受丰厚的退休金,但他拒绝了,而是去维也纳大学当了教授。
庞巴维克的讨论班的开学是维也纳大学历史上以及经济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庞巴维克以价值理论的基础作为第一学期的主题;鲍尔(Otto Bauer)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消除价值理论中的主观论。整个冬季讨论班上全是鲍尔和庞巴维克的的讨论,其它人插不上话。鲍尔的出众才华显而易见;他表明自己是值得这位大师认真对待的对手——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是致命的一击。我相信,最后就连鲍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他放弃了写书回应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的想法。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系列著作的第一卷引起了希尔福丁(Hilferding)情绪激烈的反对。鲍尔公开对我承认说希尔福丁没有理解问题之所在。
我在1913年晋升教授前定期参加庞巴维克的讨论班。在我参加的最后两期冬季讨论班上,大家讨论的是我的货币和信贷理论:第一期讨论我对货币的购买力的说明;第二期讨论我的工商业循环理论。庞巴维克和我关于这些观点的分歧后面再讲。
庞巴维克是杰出的讨论班领袖。他把自己更多地视为讨论班主席而不是教师,并且偶尔参加辩论。不幸的是,饶舌者有时候滥用参加者享有的自由。纽拉特(Otto Neurath)狂热地说出的胡言乱语特别扰人心烦。主席的严厉制止经常是有益的,但是庞巴维克不愿意这么做。他赞同门格尔的想法,相信在科学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庞巴维克的毕生的工作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他对旧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以及他本人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然而,人们仍然可以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庞巴维克能够做出更多贡献。他在讨论班上和个人谈话中表达的思想远远超出他的著述。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承担新的艰巨任务。他的神经不再适合于艰苦的工作。甚至2小时的讨论班都会让他难以成眠。只是通过最严格的入场作息制度,他才获得了科学研究所需的精力。他的全部身心都属于经济学,只有在交响乐会上才有放松和娱乐。
对奥地利的未来及其文化的担忧让庞巴维克的晚年蒙上了阴影。战争爆发后几个星期,他的心脏病发作。我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在特兰博尔(Trampol)以东的前线。9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巡逻回来后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讣告。(文/米塞斯译/彭定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