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悖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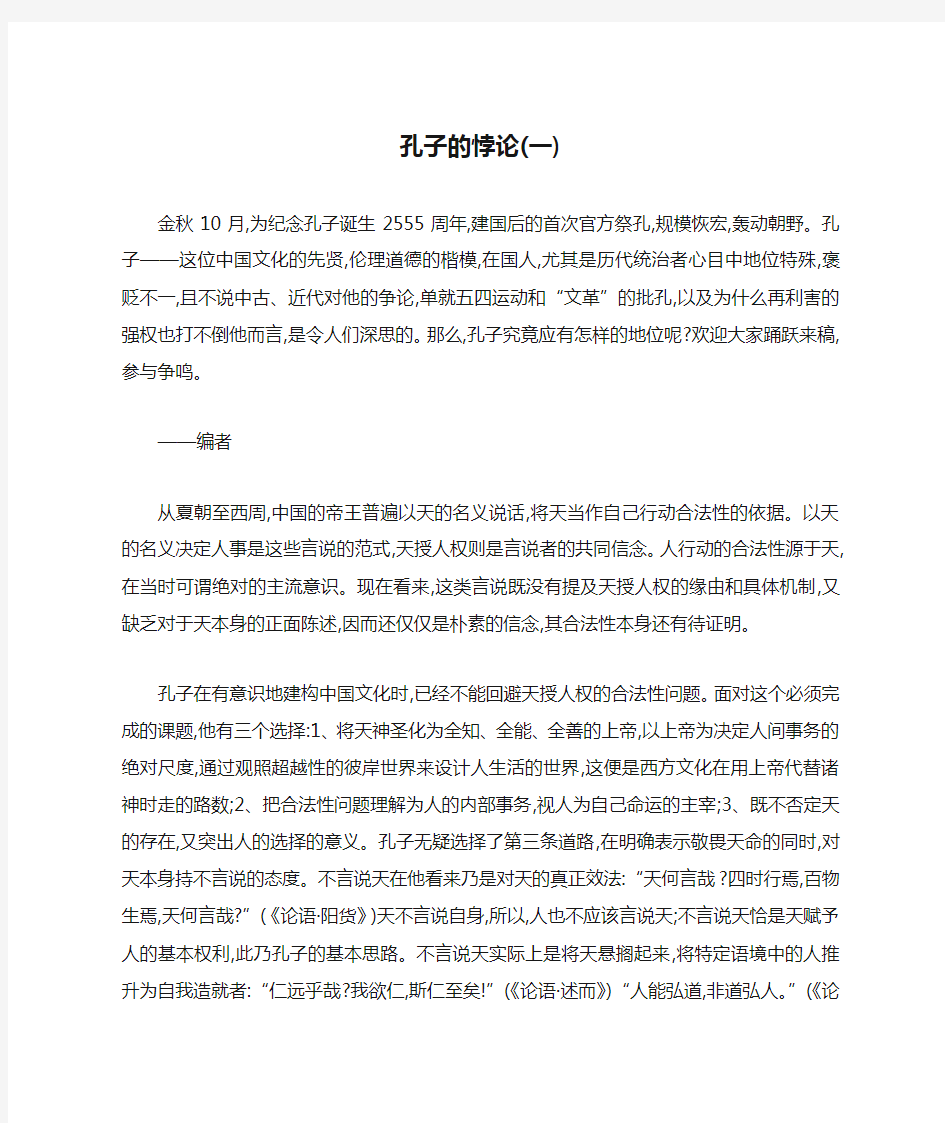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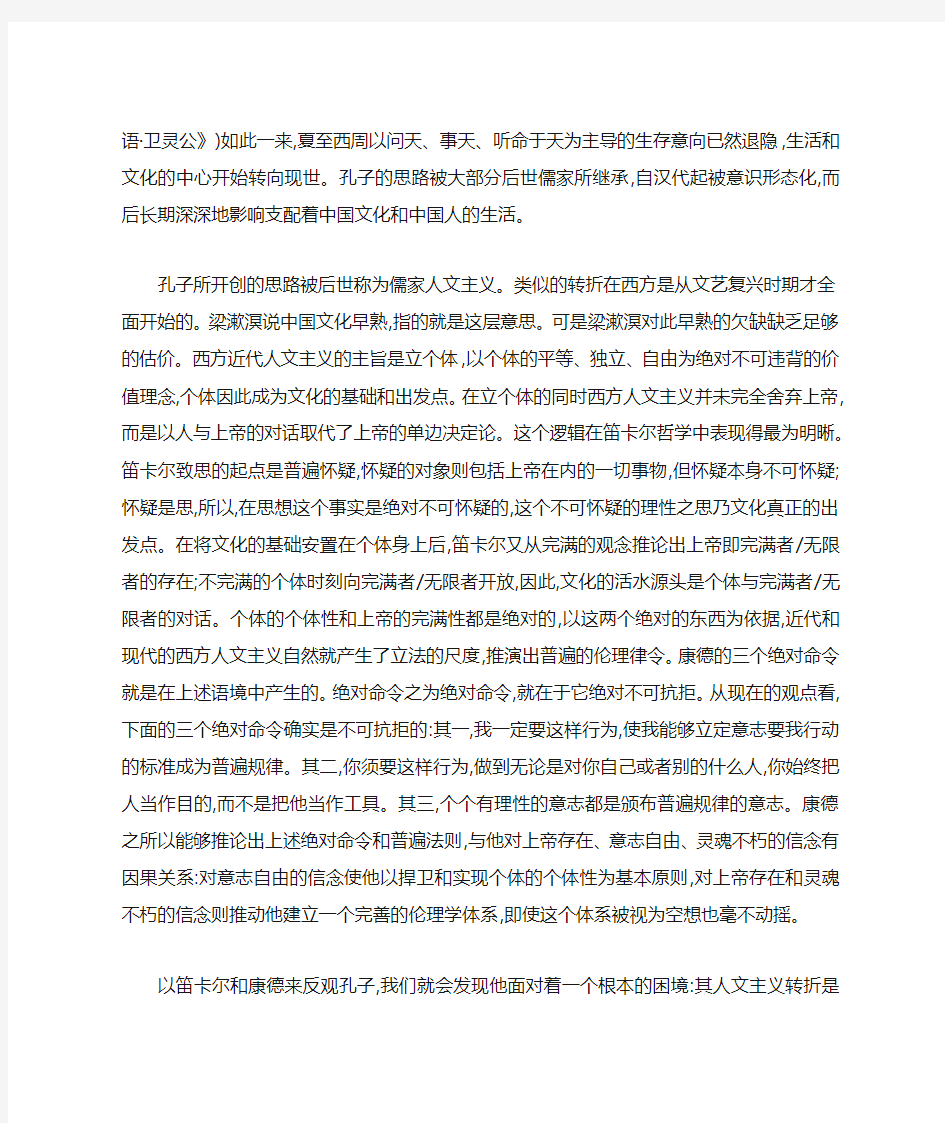
孔子的悖论(一)
金秋10月,为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建国后的首次官方祭孔,规模恢宏,轰动朝野。孔子——这位中国文化的先贤,伦理道德的楷模,在国人,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心目中地位特殊,褒贬不一,且不说中古、近代对他的争论,单就五四运动和“文革”的批孔,以及为什么再利害的强权也打不倒他而言,是令人们深思的。那么,孔子究竟应有怎样的地位呢?欢迎大家踊跃来稿,参与争鸣。
——编者
从夏朝至西周,中国的帝王普遍以天的名义说话,将天当作自己行动合法性的依据。以天的名义决定人事是这些言说的范式,天授人权则是言说者的共同信念。人行动的合法性源于天,在当时可谓绝对的主流意识。现在看来,这类言说既没有提及天授人权的缘由和具体机制,又缺乏对于天本身的正面陈述,因而还仅仅是朴素的信念,其合法性本身还有待证明。
孔子在有意识地建构中国文化时,已经不能回避天授人权的合法性问题。面对这个必须完成的课题,他有三个选择:1、将天神圣化为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以上帝为决定人间事务的绝对尺度,通过观照超越性的彼岸世界来设计人生活的世界,这便是西方文化在用上帝代替诸神时走的路数;2、把合法性问题理解为人的内部事务,视人为自己命运的主宰;3、既不否定天的存在,又突出人的选择的意义。孔子无疑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在明确表示敬畏天命的同时,对天本身持不言说的态度。不言说天在
他看来乃是对天的真正效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言说自身,所以,人也不应该言说天;不言说天恰是天赋予人的基本权利,此乃孔子的基本思路。不言说天实际上是将天悬搁起来,将特定语境中的人推升为自我造就者:“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如此一来,夏至西周以问天、事天、听命于天为主导的生存意向已然退隐,生活和文化的中心开始转向现世。孔子的思路被大部分后世儒家所继承,自汉代起被意识形态化,而后长期深深地影响支配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
孔子所开创的思路被后世称为儒家人文主义。类似的转折在西方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才全面开始的。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早熟,指的就是这层意思。可是梁漱溟对此早熟的欠缺缺乏足够的估价。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主旨是立个体,以个体的平等、独立、自由为绝对不可违背的价值理念,个体因此成为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在立个体的同时西方人文主义并未完全舍弃上帝,而是以人与上帝的对话取代了上帝的单边决定论。这个逻辑在笛卡尔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晰。笛卡尔致思的起点是普遍怀疑,怀疑的对象则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事物,但怀疑本身不可怀疑;怀疑是思,所以,在思想这个事实是绝对不可怀疑的,这个不可怀疑的理性之思乃文化真正的出发点。在将文化的基础安置在个体身上后,笛卡尔又从完满的观念推论出上帝即完满者/无限者的存在;不完满的个体时刻向完满者/无限者开放,因此,文化的活水源头是个体与完满者/无限者
的对话。个体的个体性和上帝的完满性都是绝对的,以这两个绝对的东西为依据,近代和现代的西方人文主义自然就产生了立法的尺度,推演出普遍的伦理律令。康德的三个绝对命令就是在上述语境中产生的。绝对命令之为绝对命令,就在于它绝对不可抗拒。从现在的观点看,下面的三个绝对命令确实是不可抗拒的:其一,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我能够立定意志要我行动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其二,你须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把他当作工具。其三,个个有理性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康德之所以能够推论出上述绝对命令和普遍法则,与他对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朽的信念有因果关系:对意志自由的信念使他以捍卫和实现个体的个体性为基本原则,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信念则推动他建立一个完善的伦理学体系,即使这个体系被视为空想也毫不动摇。
以笛卡尔和康德来反观孔子,我们就会发现他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困境:其人文主义转折是在个体未立而天又被悬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他在建立自己的伦理体系和社会法则时既缺乏现世维度的绝对依据,又没有超越性的真实指引。这个困境可以归结为:绝对尺度的缺席。由于缺乏一种绝对的存在作为立法的尺度,《论语》难以建立起普遍的道德律令和社会规则,使得那些具有普遍意味的道德律令和社会规则往往处于自我消解的状态。在《论语》中唯一绝对不可怀疑的是君—臣和父—子的等级秩序和宗亲结构,而君—臣和父—子是相对的人间关系,以君—臣和父—子为绝对,更说明绝对者在《论语》中的实际退隐。以相对为绝
对只能消解普遍的伦理律令和社会准则,最终使普遍的伦理律令和社会规则无法建立。
在《论语》中具有普遍意味的伦理律令和社会规则是仁。《中庸》如是转述孔子对仁的解释:“仁者,人也。”朱熹在为《论语》做注时更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述而》)不管上述解释是否完全切合孔子的愿意,但后世儒家将仁当作普遍的道德律令和内心品质则是无疑的。仁是《论语》中的核心范畴,由仁又衍生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个道德律令。如果说仁的核心是爱的话,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爱人的具体方式。孔子在言说爱时没有限定对象,因此,仁和相应的基本道德律令在充分实现自身时应该具有普适性/绝对性。普适性的爱是博爱,绝对的道德律令则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孔子对于君—臣和父—子关系的尊崇却意味着这种普适性/绝对性无法实现。要使“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并进而使爱成为博爱,就不能设定不能遵守道德律令的例外者,然而君—臣和父—子关系恰恰以设定例外者为前提,所以,孔子的上述言说必然具有悖论式的结构:1、君立自己为君,但却不允许别人动此念头,君想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就必然消除那些同样具有这个欲望的人,正如他不想被别人统治却要统治别人一样。既然君时刻违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那么,他与仁就实际上处于对立状态,视君—臣关系为绝对等于否定仁的原则本身。2、对于父权的无限制服从甚
至使得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以父子相隐为正义不但意味着信的原则难以实现,而且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律令无法贯彻到底:我在未能遵守信的原则时是希望他人对我诚实的,否则,我就无法判断他人对我的真实态度,所以在“为亲者讳时”我实际上没有服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令;换句话说,那个被“其父攘羊”的人肯定是不希望窃者之家“子为父隐”的,而当他的父亲也犯类似错误时他却要尽“子为父隐”的家庭义务。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道德律令与父—子关系本位是冲突乃至正相对立的。君和父都有对于道德律令的豁免权,道德律令的绝对性自然无从谈起。既然道德律令本身都要服从君—臣和父—子的等级秩序和宗亲关系,那么,所谓的博爱更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