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理精华》是一部重要的印度梵文医典 陈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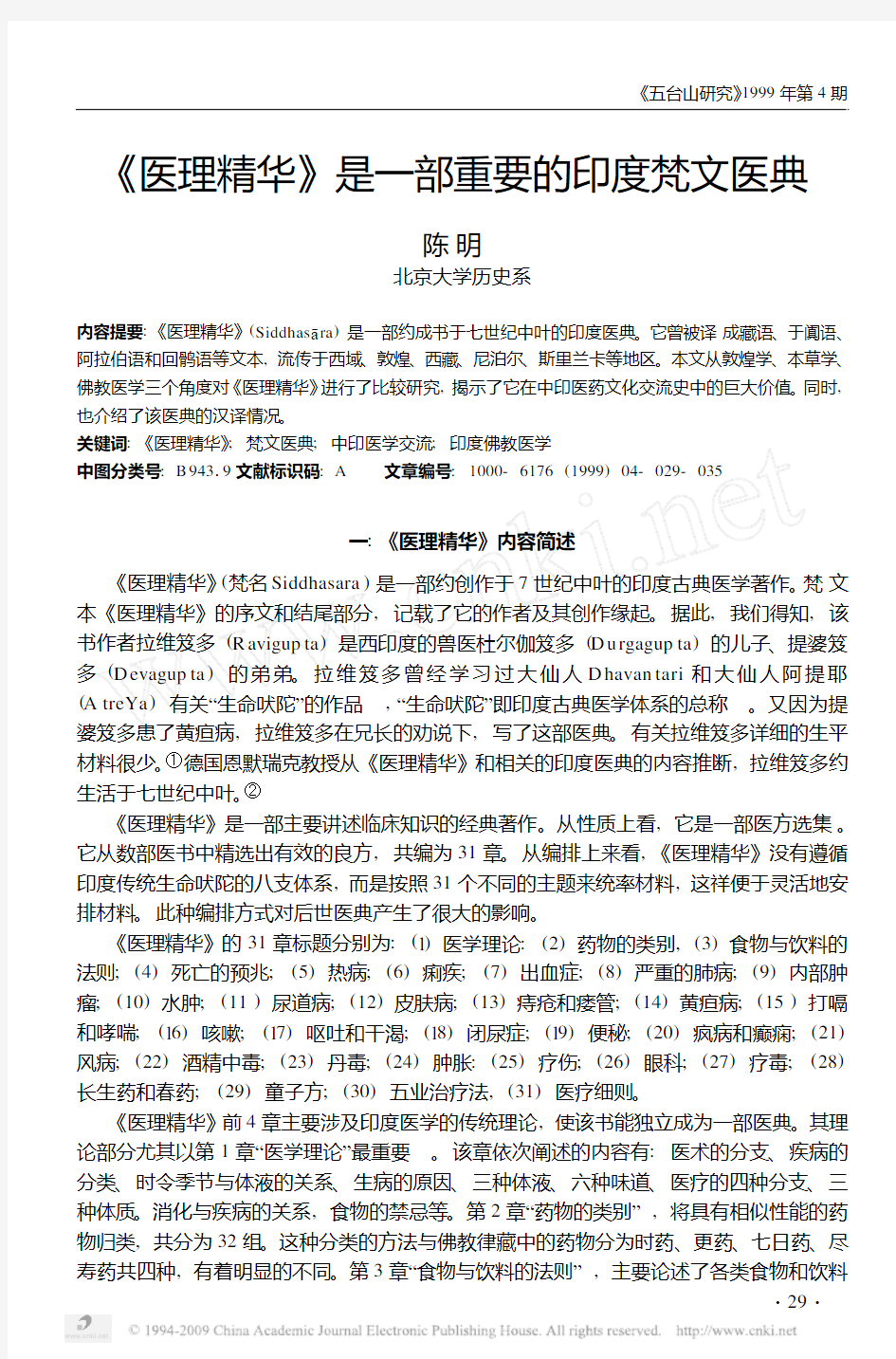

《医理精华》是一部重要的印度梵文医典
陈 明
北京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医理精华》(Siddhasāra)是一部约成书于七世纪中叶的印度医典。它曾被译成藏语、于阗语、阿拉伯语和回鹘语等文本,流传于西域、敦煌、西藏、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区。本文从敦煌学、本草学、佛教医学三个角度对《医理精华》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它在中印医药文化交流史中的巨大价值。同时,也介绍了该医典的汉译情况。
关键词:《医理精华》;梵文医典;中印医学交流;印度佛教医学
中图分类号:B943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1999)04-029-035
一:《医理精华》内容简述
《医理精华》(梵名Siddhasara)是一部约创作于7世纪中叶的印度古典医学著作。梵文本《医理精华》的序文和结尾部分,记载了它的作者及其创作缘起。据此,我们得知,该书作者拉维笈多(R avigup ta)是西印度的兽医杜尔伽笈多(D u rgagup ta)的儿子、提婆笈多(D evagup ta)的弟弟。拉维笈多曾经学习过大仙人D havan tari和大仙人阿提耶(A treYa)有关“生命吠陀”的作品,“生命吠陀”即印度古典医学体系的总称。又因为提婆笈多患了黄疸病,拉维笈多在兄长的劝说下,写了这部医典。有关拉维笈多详细的生平材料很少。①德国恩默瑞克教授从《医理精华》和相关的印度医典的内容推断,拉维笈多约生活于七世纪中叶。②
《医理精华》是一部主要讲述临床知识的经典著作。从性质上看,它是一部医方选集。它从数部医书中精选出有效的良方,共编为31章。从编排上来看,《医理精华》没有遵循印度传统生命吠陀的八支体系,而是按照31个不同的主题来统率材料,这祥便于灵活地安排材料。此种编排方式对后世医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医理精华》的31章标题分别为:(l)医学理论:(2)药物的类别,(3)食物与饮料的法则;(4)死亡的预兆;(5)热病;(6)痢疾;(7)出血症;(8)严重的肺病;(9)内部肿瘤;(10)水肿;(11)尿道病;(12)皮肤病;(13)痔疮和瘘管;(14)黄疸病;(15)打嗝和哮喘;(l6)咳嗽;(l7)呕吐和干渴;(l8)闭尿症;(l9)便秘;(20)疯病和癫痫;(21)风病;(22)酒精中毒;(23)丹毒;(24)肿胀:(25)疗伤;(26)眼科;(27)疗毒;(28)长生药和春药;(29)童子方;(30)五业治疗法,(31)医疗细则。
《医理精华》前4章主要涉及印度医学的传统理论,使该书能独立成为一部医典。其理论部分尤其以第1章“医学理论”最重要。该章依次阐述的内容有:医术的分支、疾病的分类、时令季节与体液的关系、生病的原因、三种体液、六种味道、医疗的四种分支、三种体质。消化与疾病的关系,食物的禁忌等。第2章“药物的类别”,将具有相似性能的药物归类,共分为32组。这种分类的方法与佛教律藏中的药物分为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寿药共四种,有着明显的不同。第3章“食物与饮料的法则”,主要论述了各类食物和饮料
的性能,主治的病症以及饮料的注意事项。其食物和饮料包括米类、豆类、肉类、蔬菜类、水果类、盐类、水类、奶类、油类、糖类、汤类、饼类等。第2、3章列举药物的性能,这两章与传统中医的本草学著作性质有某些神似之处。第4章“死亡的预兆”,讨论了垂死病人的临床表现、种种预兆,以及垂死病人所作梦境的凶兆与吉兆,医生与信使所见情形的征兆。
《医理精华》第5至30章,以不同的病症为单位,论述该病的病因、分类,更主要的是条列治病的药方。每章各讨论一种疾病,开列出许多药方,其中属于理论部分的是该病的成因、所分的小类、该病的临床表现等。第31章是对全书医疗方法的补充说明。整部医典涉及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眼科等多方面的疾病治疗,由于《医理精华》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医方,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曾有人将拉维笈多与罗迦(《 罗迦本集》的作者)、妙闻(《妙闻本集》的作者)合称为印度古代三大医学家。
二:《医理精华》的写本及其意义
《医理精华》在七世纪中期撰成之后,不仅经常被后世的印度医学家所引用,而且成了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医典。它以印度为核心,向东、北流传到尼泊尔、西藏、于阗、敦煌,向南传播到斯里兰卡,向西传入了阿拉伯世界。因此,从医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医理精华》的意义更加重大。《医理精华》有以下几个语种的文本。现存世的这些语种的本子,有的完整,有的只是些残片。具体说明如下:
(1)《医理精华》的梵文本
《医理精华》原本是用梵文撰写的。现今存世的梵文抄本不下10个,而且是用天城体、婆罗谜体、N aw ari、M alayalam、T elugu、Sinhala等多种字母抄写的。1980年,恩默瑞克教授利用其中的六个贝叶写本(即写本A CD E M和B),出版了《医理精华》的梵文精校本。③他在该书的“前言”部分详细介绍了校注情况。
从时间上来看,现存最早的为写本C,卷尾有非常清楚的题记,注明写于“1114年9月9日(星期三)”。写本A可能写于1347年。写本B可能写于1443年。它直接抄自写本C。二者均写于尼泊尔中部城市帕坦(patan)的M an tga1王宫中。写本D与写本E抄写日期不明。写本E保存于南印度,日期较晚。
此外,还有一个保存在京都的《医理精华》尼泊尔抄本。
巴黎还有一个《医理精华》抄本,标题为“Siddhasara-sam h ita”。它由K.Sam path Kum arachak ravarth i于l901年ll月15日至1902年7月10日,抄于印度马德拉斯市(M r2 dras)的G.O.M.S.S图书馆,原卷编号为:M S M adras R.N o.799。
恩默瑞克的粗校本出版之后,J inadasa L iyanatan te又在斯里兰卡发现好几个《医理精华》的梵文抄本。④
(2):《医理精华》的藏文本
《医理精华》的藏文译本非常完整。它的藏译名为“s m an-dp yad gces-p a Grub-pa zes bya-ba”(大意为《医书:最佳的选择》)。它保存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T an ju r〕中,共有三个版本,分别为:①德格版,D l9la-286b,N o.4434,②那塘版,N138a-236b,“Tom e do1321”;③北京版,P142a一248b,N o.5877。
《医理精华》藏文本的译者共有三人:胜友(J inam itra)、A dityavar m an和Candra。藏
译本最后有题记,大意为“印度学者胜友和A dityavar m an、以及翻译家Candra尊者,翻译和编排了它(《医理精华》)”。胜友是一位有名的翻译家,他在九世纪初期就参加了编纂《翻译名义大集》(M ahavyu tpatti)。在《拉达克王统记》中提到过胜友,他是作为吐蕃王赤祖德赞的译者而入藏的。胜友是赤祖德赞时代的梵学权威,这一点也被《彰所知论》所证实。⑤可见,《医理精华》译成藏文的时间就在九世纪初期,不过它传入西藏的具体途径和缘由,目前还不清楚。
总体看来,《医理精华》藏文本既完整,意思又清晰明了。它非常接近于梵文原本,绝大部分是准确的散文翻译,在有些地方还加入了译者们的评论性的补注。它不仅比现存标明日期的最早梵文抄本的时间上还要早,而且要多出不少的句子,它跟于阗文本的关系更接近。1982年,恩默瑞克教授将其藏文本,译成了英文本。⑥
(3):《医理精华》的于阗文本
《医理精华》于阗文本有两件。第一件是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盗”走的,入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原编号为Ch.ii002。该文书是现存最长的敦煌于阗文写卷。根据该文书的《序言》,它是从藏文本转译而来的。据敦煌的相关文书推测,它的转译时间大约在十世纪。从该文书的词汇上来判断,恩默瑞克教授认为其于阗文本虽以藏文本为底本,但同时也参考了梵文原本。
Ch.ii002号文书是个残本,它的第一页(fo li o)正面有一个标题,“54pattra sedasarā”,意为“54叶Siddhasāra”,但实际上现存64纸。不过其中的fo li o100,与《医理精华》无关,属于另一种医书。第156叶背,有用粟特文写的“张金山”(Cw kym s’n)姓名。张金山是入仕于阗的汉族人,于阗王尉迟达磨中兴五年(982)七月,张金山(Cā-k i mā-sana)等一行三百人出使沙州。《医理精华》是张金山之物,被他带到沙州的。⑦据此推算,《医理精华该写本的年代大约在982年张金山出使沙州前后。
《医理精华》于阗文本的第二件即P.2892,它也是个残本,对应于Ch.ii002中的fo li o5 -14,但抄写年代不详。
(4):《医理精华》的阿拉伯文本
《医理精华》的部分内容还传入了阿拉伯,时间大约在九世纪未或十世纪初。其阿拉伯译名为Sndh s’r。而R hazes(A bu B ak rM uhamm adibn zakariya ar-razi)经常摘录Sndh s’r 中的内容。1981年,恩默瑞克教授发表《拉维笈多的〈医理精华〉在阿拉》一文,⑦⑧将R hazes 所摘录的三段内容与《医理精华》原文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极为相似。
(5)《医理精华》的回鹘文本
《医理精华》是13世纪前译成回鹘文的。现存的加鹘文本共有11个残片,由G.R. R achm ati所转写并刊布。⑨其中的1、5、6三个残片,被贝利教授识别出来。βκ残片第1-7号已在《医理精华》中找到了相应的位置,而第8-11号残片还没有对勘出来。据说近年来D r.D ieter M aue在研究用婆罗迷字体所写的回鹘文和梵文《医理精华》的双语残片。回鹘文本与梵文各抄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行深入研究。
三:《医理精华》的汉译及其研究
早在1948年,季羡林先生在《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βλ一文中,就谈到了所谓的“国医”—中医学内,实际上有许多印度医学的成份。象印度文化的其他因子影
响中国一样,印医对中医的影响亦是极其深远的。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看法。能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成份,乃是一个民族得以强盛的优秀品质之一。在提倡以更开放性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拿来主义”的作风也不是说不可,而是要研究吸收,为己所用。而回顾历史上魏晋风度、隋唐气象的形成,莫不得益于对东西文化精华的吸收和同化,因此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那些活生生的例子,对当今的现实仍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故单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也有必要研究一番印度医学。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指出,“仔细地比较中国的和印度的传统药典,来探究药物学中互相借鉴的地方,是极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βμ《医理精华》本身保留了大量的临床良方,在医学交流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完全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可惜一般的中医研究者,由于对“胡语”没有掌握,对印度医典了解不多,故难以开展这一研究工作。国内的印度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也没有对此热心关注,以至于印度医典的汉译成了一块荒芜的处女地。笔者有志于在这方面做些抛砖引玉的工作,为中医学者提供一部印度医典的汉译本,使中印古代医学文化交流与比较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笔者求学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期间,在王邦维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并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全文约为24万字。
《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下篇为翻译。研究篇共含两章八节,第一章即“《医理精华》与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第二章为“《医理精华》与印度佛教医药”。
笔者以恩默瑞克教授的《医理精华》梵文精校本为底本,以他的藏文英译本为参考,将《医理精华》的梵文本全部翻译成汉语。《医理精华》本身所附的《医理精华词汇》(Siddhasara -n ighan tu),也一并翻译了出来。在力求翻译的准确、科学等基础上,对部分比较重要的名词术语,作了较详的注释。并且以《医理精华》第二章“药物的类别”中的词汇为中心,整理了一个简要的词汇表。如果该学位论文能够正式出版的话,那么将附录《医理精华》的全部梵汉词汇表。
基于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的出发点,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医理精华》。
(l):从敦煌学的角度来考察。
其一,研究《医理精华》和《鲍威尔写本》βν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于阗文本出土于敦煌藏经洞,后者出土于新疆库车地区,二者同属于丝绸之路上的文物。《鲍威尔写本》中的前三个部分都是医学资料,大约抄写于四世纪中期,远早于《医理精华》的成书年代。通过比较二者的医学理论、疾病数目、五业治疗法,特别是“大苦药”、“大苦酥药”与“大苦药粉”,治咳嗽方、治小儿方等一些药方,我们找出了其中相同的部分,并分析了其异同的原因。我们初步认为,作为在西域地区流传的、主要由“胡人”(印度人和中亚某些民族)使用的这两部医典,完全属于印度传统医学理论“生命吠陀体系”的范畴,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医理精华》是否受到了《鲍威尔写本》的直接影响,但从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少相同或相近的药方来看,可以说《医理精华》要么与《鲍威尔写本》有着共同的来源,要么受到《鲍威尔写本》的间接影响。此外,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鲍威尔写本》有明显的佛教色彩,而《医理精华》中没有任何佛教的痕迹。这两部医典中相同或相近的成分在说明印度医学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和交流史上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至于将它们与中医进行比较,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其二,可以从敦煌出土的汉文医药文书来看《医理精华》,找出相同的药物用法,以判断二者相互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关系。在敦煌藏经洞的遗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医学文献,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上还有弥足珍贵的“形象医学”材料。虽然敦煌医学文献的全体是中医药文献,但是在藏医类、医方类、佛医类、医事杂论类等医学文书中,仍然可以找到与中印医学交流的有关材料。另外,在吐鲁番、黑城子、楼兰、吐峪沟、麻扎塔格、和田等地出土的医学资料,内容不如敦煌资料那么丰富,但是在中外医学交流史上的价值却不可低估。通过对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书和《医理精华》中的荜菝(长胡椒)等10多种重要药物的比较,我们发现其中没有完全相同的药方,这说明《医理精华》没有直接影响到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中医,但是其药方的用法却有不少一致的地方。外来的药物传入之后,中医与藏医不仅能吸取印医的理论和常用方法,而且对药物的使用有所发明和改进,这就是中印医学交流的具体成果。此外,在中印医学交流的过程中,佛教起到了巨大的中介作用。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由于中印医学是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医在接受外来医学文化的时候,不可能采取照单全收的态度,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其精华部分,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身,对中医的发展也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
其三,可以研究见于《医理精华》中的几个胡语药方,考察在西域地区不同的胡语文化圈中的医学交流的史实。《医理精华》既有与新疆库车出土的《鲍威尔写本》中相同的药方;也有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典《耆婆书》(J tvaka-pu staka,音译《时缚迦书》)中相同的药方;还有与吐鲁番本回鹘文《杂病医疗百方》、西藏传世的《四部医典》中相同的用药方法。利用《医理精华》、《耆婆书》等医书中的材料,笔者推断出一则
卢文文书,乃是残存的“达子香叶散”方。βο此项发现对揭示《医理精华》在西域地区不同的文化圈中的传播与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2):从本草学的角度来考察。在唐宋时期存在着一种好用“胡药”的社会风习。唐末时期中医本草著作中记载了《医理精华》所用的一些印度药物,可以考察中医和印医对它们的性能认识上的异同,并且初步理清这些药物传入汉地的轨迹。通过简要比较《证类本草》所见的《医理精华》所用的“仙茅”等16种药物,我们可以初步看出中印医学使用药物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药物的性能分析是综合性的,药物多用于复方之中,所治的疾病也是多种多样的。双方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中医本草学对每一种药物的有无毒性是非常关注的,而《医理精华》中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一方面。第二,对药物的性能分析所依赖的体系不同。中医强调药物的味、性、毒等方面,印医则主要强调药物与风、痰和胆汁的关系。因为在它们背后整个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背景是不一样的。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印度、波斯等“舶来的”药物,对唐宋时期道家求仙风气的盛行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是外来的物质文化对本土精神生活影响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3):从印度佛教医学的角度来考察。《医理精华》本质上是一部完全客观的、科学性强的世俗医典,就连其中的比喻也很少与宗教有关,它与佛教可以说毫不相干。不过,《医理精华》与印度古代“生命吠陀”体系一脉相承,而印度佛教医学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上都继承了“生命吠陀”体系的成分。可以说,印度佛教医学是在医方明的基础上,接受佛教义理所发展起来的,也是印度古代医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将《医理精华》与印度佛教医学进行比较,既可以深刻揭示前者的特点,也有助于对后者深入的探讨,能明
后者中哪些是传统的“生命吠陀”的成分,哪些是佛教的创造成分。因此,将《医理精华》与佛教医学从医学理论、药物的分类与相关疾病的疗法等多方面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世俗医学与宗教医学各自的特征。此外,利用汉译佛经中的梵文医药术语(包括药物、疾病等的名称)与《医理精华》词汇来准确地比定,能为佛教医学研究者扫清些许障碍。
印度佛教医学与《医理精华》相比,一方面在理论上增加了许多佛教的义理,试图去解释人类疾病的原因,并指出宗教意义上的灭除病苦的途径与方法;另一方面在临床实践上大大地强化了咒语的治疗作用。可以说,咒语的至高地位已成了佛教医学在临床治疗方面的显著特色。在大乘佛典特别是在金刚乘佛典中,有许多魔术般效力的曼陀罗(m an tra)和陀罗尼(dharan i)咒语。这些咒语除了治疗佛教所说的魔病、业病和鬼病之外,还可以与药物合用治疗人体的日常病症。极端的是,《佛说咒小儿经》、《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疗痔病经》等类佛经中,没有提到任何一类药物,纯粹是靠着咒术不可思议的神奇威力来治病的。佛典医学也有不用咒语、只用药物的医案,但它们大多记载在律藏之中,而且数量远远少于咒语疗法。律藏中的医药事(梵bhaisajya-vastu,巴bhesajja-kkandhak)是律藏文献最古老的部分之-,因此它们代表了最早的佛教医学的形式。βπ从单纯的药物治疗到越来越多地使用咒语,这正是佛教医学发展的轨迹。而《医理精华》中的咒语方寥寥无几,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用来驱除少儿身上所附的邪魔的医方,即si.29.56—29.58,它列出了一段曼陀罗咒语。
佛教医学疗法除了最重要的咒语疗法(有时是药咒合用)之外,还有食疗法、沐浴法、香药法。食疗法有两种,即饮食法、断食法。饮食法指用各类食物来治病,比如食药粥法;而断食法是指在一天或数天内绝食,以清除由消化不良等所带来的种种弊病。沐浴法又叫澡浴法,这是由于印度炎热的天气所要求的。香药法是指主要用香药来祛病、提神、健身的方法。香药法往往不是独立使用的,常用于沐浴或者咒术之中。
佛教医学的医方有两种类型:单方与复方。单方主要体现在纯粹的药物治疗中,如律藏中的大部分医案。复方主要用于密教类经典中,数种药物与咒语共同使用。佛教医学的医方也有两个特色:其一,单方多,复方少;其二,很少有列明了每味药物的剂量而又与咒语无关的医药方。因此,尽管佛教医学看似洋洋洒洒,而实际管用的大型验方却并不多见。
与佛教医学不同的是,《医理精华》中的医方则单方少,而复方多。其疗法也多种多样,催吐法、催泄法、灌鼻法、缓下法、灌肠法等五业治疗法均有,而且也提倡食疗、断食、沐浴、香药等常见的方法。《医理精华》中的药方是传统型的,有药物的剂量。具体的使用过程。其中绝大多数是验方,客观性与科学性较强,几乎没有佛教医学的宗教色彩,当然其中用到(或者不用)某些药时也可能涉及到印度人的哲学观念和生活习俗。
总的看来,《医理精华》汉译本将为中印古代医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份基础性的文本资料。在《医理精华》的文献和理论方面,固然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利用汉文材料,以便充分发挥我们更大的研究优势。此外,在当今开发东方传统医学资源的国际性浪潮面前,如何对《医理精华》的药方进行临床研究,加以开发与利用,为人类的健康造福,这无疑是一个更有潜力、也更实用的课题。
注释:
1:法国学者J.N audou曾发现有三个同名的拉维笈多,他们的作品都被译成藏文并收入了《大藏经》。至于《医理精华》的作者是其中的哪-位,尚无确切的证据。
2:Emm erick R.E,1977.“R avigup ta’s p lace in Indian M edical traditi on”,Indo logic T aurinensia,III -I V,1975-76.To rino1o,pp.209-221
3:Emm erick R.E.,1980Siddhasara O f R avigup ta,vo l.l:T he sansk rit text(=V erzeichnis der o rien2 talischen H andsch riften in D eutsch land,ed.W.V o igt,Supp lem entband23.1)”,F.Steiner V erlag, W iesbaden.
4:J inadasa L iyanaratne,1989.“T he literary heritage of SriL anka”,St II,15,pp.119-127.J inadasa L iyanaratne,1990.“R avigup ta’s Siddhasara:N ew L igh t from the Sinhala V ersi on”,JEA S,1,pp.69-84.
5:张广达,1993年,《九世纪吐番的〈敕颁翻译名义集三种〉》,载于《周-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46-163。
6:Emm erick R.E,1982.Siddhasara of R avigup ta,vo l.2:T he T ibeten versi on w ith facing English translati on(=V erzeichnis der o rientalischen H andsch ri ften in D eutsch land.ed W.V o igt,supp lem entband 23.2),F.Steiner V erlag,w iesbaden.
7:张金山出使沙州之事,见于《于阗使臣张金山燃灯发愿文》(Ch.ii.0021a,a)。张广达、荣新江, 1993年,《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26页。
8:Emm erick R.E,1981.“R avigup ta’s Siddhasara in A rabic”,Studien zur Gesch ich te und Kultur des vo rderen O rients,Festsch rift fur Berto ld Spule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ed.H.R.Roem er and A. N o th,L eiden,pp.28-3l.
9:R achm ati G.R.,ed.1932.“Zur H eilkunde der U iguren”,II,(Sitzungsberch te der p reu-B ischen A kadem ie der w issenschaften,ph il.-H ist.K lasse,1932,X X II),pp.21-418—430
10:H.W.Baily,1953,“M edicinal p lant nam es in U igur T urk ish”,in:M elanges Fuadk-op rulu ,Istanbul,pp.51-56.
11:该文后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6-7页
12:参见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221页。
13:A.F.R udo lf Hoernle,T he Bow er M anuscri p t,rep rinted,N ew D elh i,1987。
14:陈明,《一个新发现的 卢文药方的考释》,《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99年2期,65-73页。
15.Zysk,1998,A sceticis m and H ealing in A ncient India:M edicine in the Buddh istM onastery,D elh i. p.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