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以后_以后_亚历山大_索库洛夫的方舟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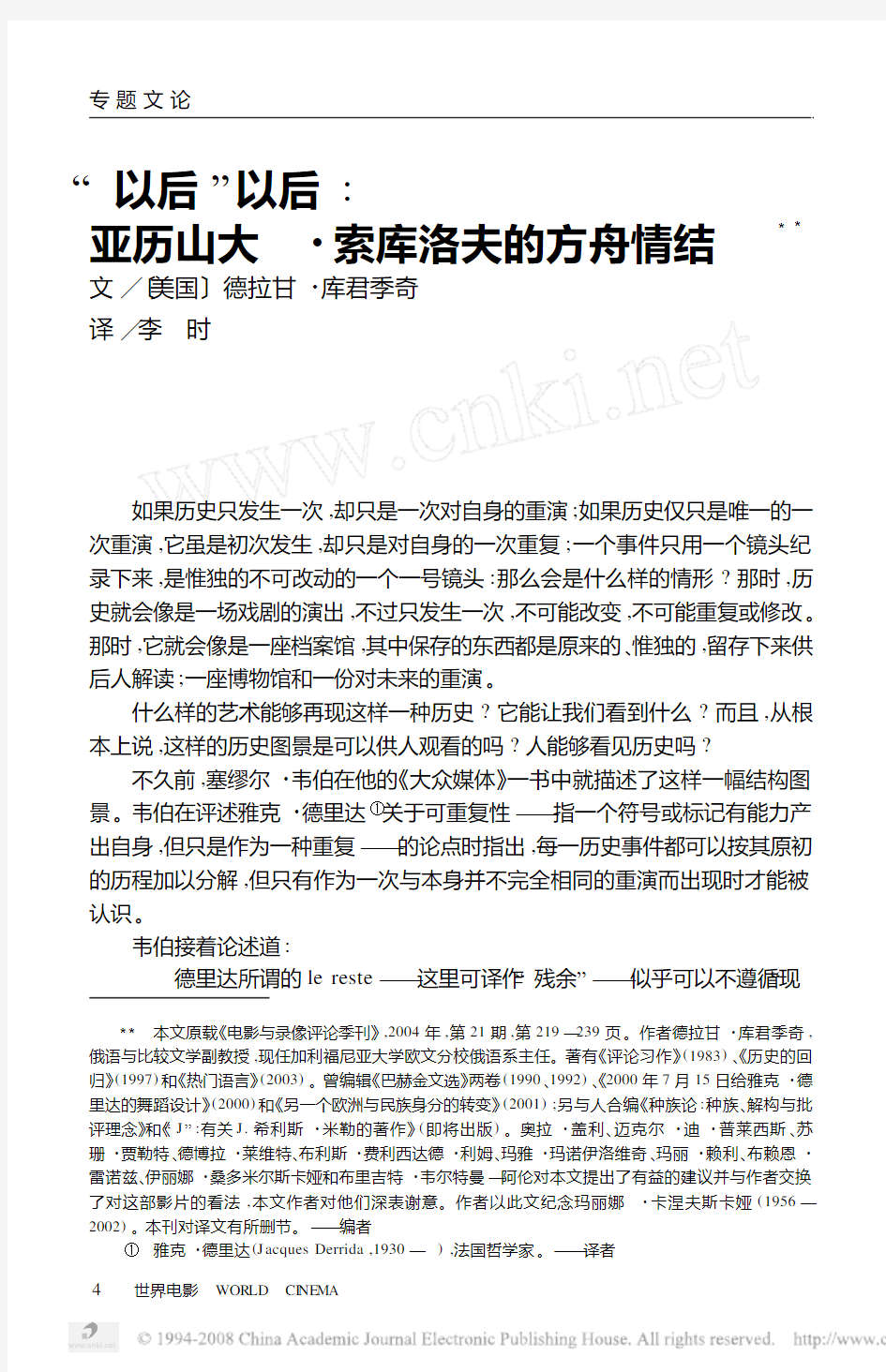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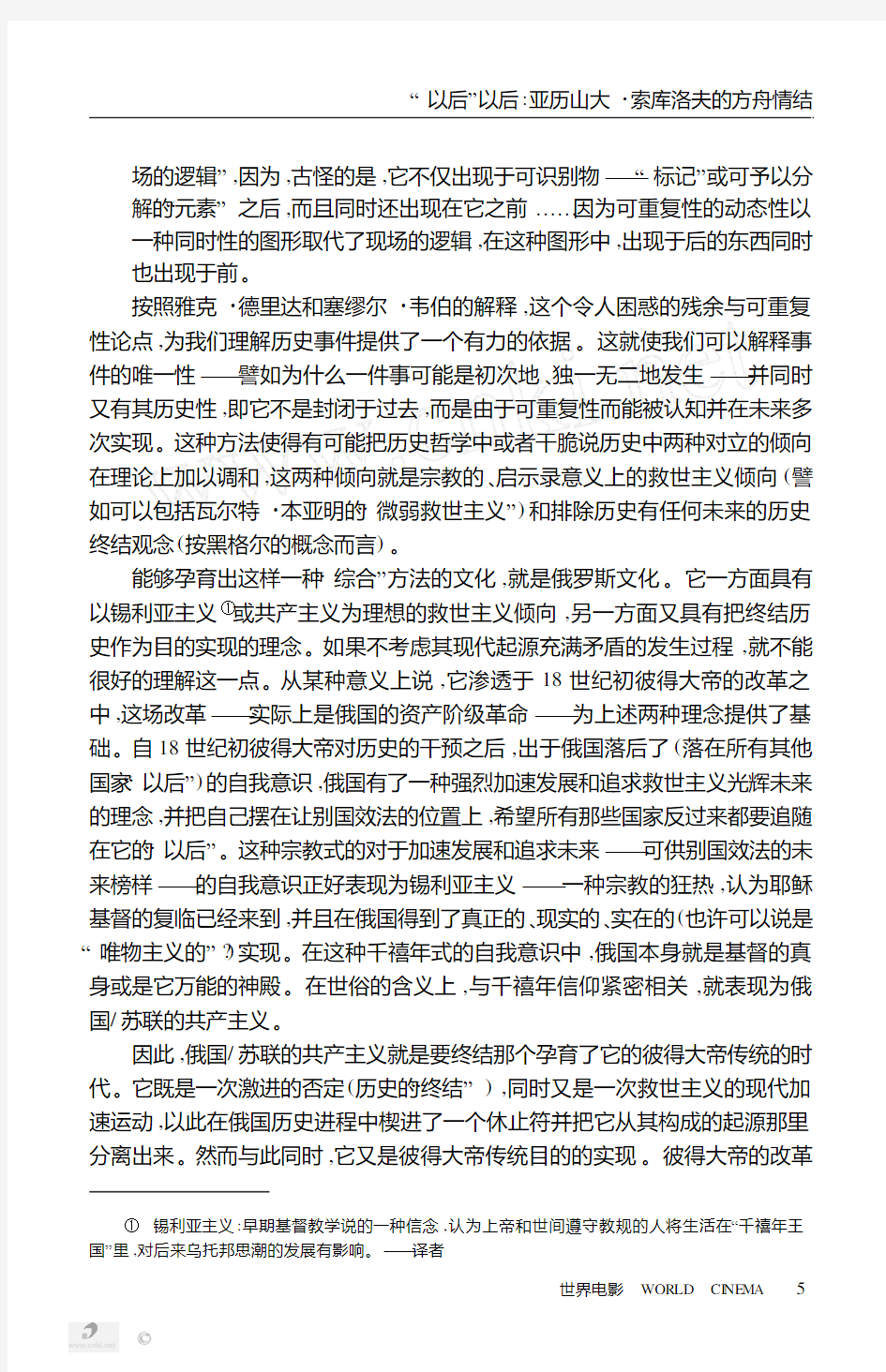
“以后”以后:亚历山大?
索库洛夫的方舟情结33
文 〔美国〕德拉甘?库君季奇
译 李 时 如果历史只发生一次,却只是一次对自身的重演;如果历史仅只是唯一的一次重演,它虽是初次发生,却只是对自身的一次重复;一个事件只用一个镜头纪录下来,是惟独的不可改动的一个一号镜头:那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时,历史就会像是一场戏剧的演出,不过只发生一次,不可能改变,不可能重复或修改。那时,它就会像是一座档案馆,其中保存的东西都是原来的、惟独的,留存下来供后人解读;一座博物馆和一份对未来的重演。
什么样的艺术能够再现这样一种历史?它能让我们看到什么?而且,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历史图景是可以供人观看的吗?人能够看见历史吗?
不久前,塞缪尔?韦伯在他的《大众媒体》一书中就描述了这样一幅结构图景。韦伯在评述雅克?德里达①关于可重复性———指一个符号或标记有能力产出自身,但只是作为一种重复———的论点时指出,每一历史事件都可以按其原初的历程加以分解,但只有作为一次与本身并不完全相同的重演而出现时才能被认识。
韦伯接着论述道:
德里达所谓的le reste ———这里可译作“残余”———似乎可以不遵循“现3①3 本文原载《电影与录像评论季刊》,2004年,第21期,第219—239页。作者德拉甘?库君季奇,
俄语与比较文学副教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俄语系主任。著有《评论习作》(1983)、《历史的回
归》(1997)和《热门语言》(2003)。曾编辑《巴赫金文选》两卷(1990、1992)、《2000年7月15日给雅克?德
里达的舞蹈设计》(2000)和《另一个欧洲与民族身分的转变》(2001);另与人合编《种族论:种族、解构与批
评理念》和《“J ”:有关J.希利斯?米勒的著作》(即将出版)。奥拉?盖利、迈克尔?迪?普莱西斯、苏
珊?贾勒特、德博拉?莱维特、布利斯?费利西达德?利姆、玛雅?玛诺伊洛维奇、玛丽?赖利、布赖恩?雷诺兹、伊丽娜?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布里吉特?韦尔特曼—阿伦对本文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并与作者交换了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本文作者对他们深表谢意。作者以此文纪念玛丽娜?卡涅夫斯卡娅(1956—2002)。本刊对译文有所删节。———编者
雅克?德里达(J acques Derrida ,1930— ),法国哲学家。———译者
场的逻辑”,因为,古怪的是,它不仅出现于可识别物———“标记”或可予以分解的“元素”之后,而且同时还出现在它之前……因为可重复性的动态性以一种同时性的图形取代了现场的逻辑,在这种图形中,出现于后的东西同时也出现于前。
按照雅克?德里达和塞缪尔?韦伯的解释,这个令人困惑的残余与可重复性论点,为我们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这就使我们可以解释事件的唯一性———譬如为什么一件事可能是初次地、独一无二地发生———并同时又有其历史性,即它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由于可重复性而能被认知并在未来多次实现。这种方法使得有可能把历史哲学中或者干脆说历史中两种对立的倾向在理论上加以调和,这两种倾向就是宗教的、启示录意义上的救世主义倾向(譬如可以包括瓦尔特?本亚明的“微弱救世主义”)和排除历史有任何未来的历史终结观念(按黑格尔的概念而言)。
能够孕育出这样一种“综合”方法的文化,就是俄罗斯文化。它一方面具有以锡利亚主义①或共产主义为理想的救世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具有把终结历史作为目的实现的理念。如果不考虑其现代起源充满矛盾的发生过程,就不能很好的理解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渗透于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之中,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上述两种理念提供了基础。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对历史的干预之后,出于俄国落后了(落在所有其他国家“以后”)的自我意识,俄国有了一种强烈加速发展和追求救世主义光辉未来的理念,并把自己摆在让别国效法的位置上,希望所有那些国家反过来都要追随在它的“以后”。这种宗教式的对于加速发展和追求未来———可供别国效法的未来榜样———的自我意识正好表现为锡利亚主义———一种宗教的狂热,认为耶稣基督的复临已经来到,并且在俄国得到了真正的、现实的、实在的(也许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实现。在这种千禧年式的自我意识中,俄国本身就是基督的真身或是它万能的神殿。在世俗的含义上,与千禧年信仰紧密相关,就表现为俄国/苏联的共产主义。
因此,俄国/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要终结那个孕育了它的彼得大帝传统的时代。它既是一次激进的否定(历史的“终结”),同时又是一次救世主义的现代加速运动,以此在俄国历史进程中楔进了一个休止符并把它从其构成的起源那里分离出来。然而与此同时,它又是彼得大帝传统目的的实现。彼得大帝的改革
①锡利亚主义:早期基督教学说的一种信念,认为上帝和世间遵守教规的人将生活在“千禧年王国”里,对后来乌托邦思潮的发展有影响。———译者
由于激进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模式,既加强了俄罗斯的国力,同时也导致其民族个性的消解。苏维埃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种模式的一次公开的、平民主义式的毁弃,但所用的手段却依然是他们原本要竭力消除的现代技术幻想。苏维埃革命以一种自我免疫(通过这种自我免疫,保存的机制毁掉它所要保存的机体)的方式试图保护其自身由原先促使其形成的机体中解脱,解脱彼得时代的以及它自身的革命理想。苏维埃革命之后,对俄国历史的认知充满了困惑,因为革命前的历史变得既不能承续、复归,也不能为之惋惜。彼得大帝时代变成了一个令人忧伤困惑的东西:既不能“理直气壮地”追念它,又不能干脆把它忘却。它成了一个忧伤理想的时代,还要在俄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或艺术中加以“消化”。因此,它便成了俄国的未经追思的未来。
我曾经提出,就其结构的许多方面而言,俄国是一个追随历史“以后”而来的国度。一部艺术作品需要怎样才能不仅成为那一历史情境的表征,而且是它自我反映的形态?亚历山大?索库洛夫的《俄罗斯方舟》就是这样一部独特的影片,它的立意就是要做一次“追随”历史的搜寻。它把历史再现为一次独有的事件,一宗档案,它既像是一次对历史的“现场”跟踪,又像是一次标本的复制,对历史的“已死的”、自成一体的、鬼魂出场的搬演。或者更确切些说,这是一部地地道道模拟历史的影片。同时也是这样一部电影,它标志着人们开始把彼得大帝时代的传统当作对俄罗斯曾有的理想精神的怀旧对象。
这部影片里“发生”了什么呢?镜头从一片黑暗中逐渐变亮,“注视”着一群
年轻军官和美丽女人走进一座宫殿。这座宫殿就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这在片头字幕里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作为本片制片方将这座博物馆的名字标示得同片名一样显著(这就设定了一种很强烈的自我反映的角度,或者说,从一开始就表明这是一部由该博物馆制作的有关该博物馆的影片)。旁白告诉我们,那应该是19世纪初,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视觉景象的回忆,因为伴随摄影机、代表镜头视线的旁白叙述者说自己是个失明的盲人。影片从开头直至结尾,将不会有任何切换,或者说中断,就是说,这部影片是由一个单独的长镜头(一个用斯泰迪康摄像机拍摄的一贯到底、不加剪辑的单独镜头)构成的。镜头跟随这一群人穿越俄国历史的许多阶段和“场面”,从彼得大帝时代直到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也就是1917年革命前夕,由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主持的盛大舞会为止,这时以群像为最终结束(在终场的舞会上,由玛林斯基剧院乐团演奏格林卡为献给沙皇而谱写的音乐)。
镜头这时跟随这群人走出舞会大厅,走向冬宫外雾气迷漫的涅瓦河,面对暗蓝色的水面。因此,叙事时间跨越了整个彼得大帝改革的时代,从18世纪初至1913年这一时代的结束。在整个影片中镜头还紧紧跟随着另一个人物,他被说成是著名游记《俄国通信:1839年的俄罗斯》的作者居斯蒂纳侯爵,①这位侯爵同代表镜头视线的俄国叙述者展开了一场对话。对话用俄语进行,居斯蒂纳———大约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居然也说着流利的俄语。因此正是这个居斯蒂纳引导着镜头的运动和视线,并使得动作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展开(这场运动不太具有线性和连续性,而是常常进入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时空境界)。
在影片末尾镜头和叙述者离开舞会大厅的那个场面里(移摄镜头跟拍一组已经是由不同时代人物组成的人群———可以看见普希金,与一些身穿彼得帝国不同时期制服的军官一起,走下由拉斯特雷利建造、在毁于大火后又由斯塔索夫重修的著名的约旦阶梯),居斯蒂纳没有跟随镜头继续行进,而是留在了彼得大帝传统的历史时代环境中。在时间的含义上,他没有跨越按年代纪事的叙事时态界限(即1913年,也就是大战和革命前夕),而叙述者和镜头的视线,看得出来是不受这种约束的。因此,他们是属于“现在”时态的,他们知道后来的历史(以及已经隐约可见的灾变)。
《俄罗斯方舟》展示了俄国历史中的一些场景,让它们在我们眼前“展开”,而
①居斯蒂纳(Astolph de Custine,1790—1857),法国文学家,保皇党人,曾应沙皇尼古拉一世邀请访问俄国,他的游记对俄国专制制度作了否定的评价。———译者
这一切全都以这座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能代表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荣耀的宫殿为背景,这座爱尔米塔什宫,又称冬宫,是伊丽莎白女皇和后来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位时期委托彼得大帝时代最杰出的建筑师巴托洛缪?老拉斯特雷利之子小拉斯特雷利建造的。这座冬宫从一开始就同时被视为一座博物馆,因为从叶卡捷琳娜女皇时起就委托画家作画以在宫中陈列。可以认为,影片《俄罗斯方舟》就是介乎保存历史“现场”事件的“方舟”,和用电影再现这一历史的“档案”之间的一种东西。
影片的另一方面也与对历史的理解有关,即把历史理解为历史以后的或者灾变以后的发展,这便是片名所暗示的背景。《俄罗斯方舟》是这样一部影片,它发生在一场历史的灾变、一场启示录式的大洪水之后,而在这之后或预计它来临之前把一些特殊的文化瑰宝和政治遗产保存下来留给未来。这场灾变没有在影片中出现,而是以代表镜头视线的叙述者的失明而表达出来,它就是苏维埃革命。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早于这场革命,但又是革命后、灾变后的一次对俄国历史巨变的再现。这部展示爱尔米塔什宫的影片同时也展示了圣彼得堡市本身经历了那段历史之后的环境,它的时间和这座城市一样,是在“一场现代乌托邦之后和一场激进的现代灾变之后”。
影片在涉及身分定位问题(例如确定俄罗斯民族归属)方面的戏剧性在于,回忆的范围也包括那些与俄罗斯毫无关系的艺术品,即纯属来自西方的、因而在结构上处于“记忆范围”之外的东西。因此它在结构上是被德里达称为“归档热”
(Archive fever)的一种体现:“因为所谓归档(怀旧),如果这个词或这个概念能
够稳定代表某种含义,那么它绝非如自发的、现场的和内心体验那样一种记忆或回忆。恰恰相反,归档(怀旧)只能产生在上述记忆始发和解体的那个地方”。所以,《俄罗斯方舟》也是这样一部影片,它表现自己的后历史性、归档(怀旧)情结、方舟情结,但恰恰是在它的历史解体的那个地方。
影片中的所有场景都以爱尔米塔什或者说冬宫为背景,所有事件都既像历史的陈列,又像“现场”展开和搬演。我们跟随镜头穿过各式各样的房间,从地窖到舞会大厅,从彼得大帝在场的场面到最后一次沙皇主持的舞会。影片创造了一份逼真可信的俄国历史“名人录”,它的意图部分地应该是要观众,当然是俄国观众,认出熟悉的俄国历史人物,同时也试图让人们认出和确认片中出现的如今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陈列着的若干名画:埃尔?格列柯的《彼得和保罗》、凡?戴克的《圣母和沙鸡》,或者伦勃朗的《献祭以撒》。所以影片不可避免地分解为对历史的呈示和对历史的“现场”搬演。但是,借助于熟悉的人物形象实现历史复归的地点并不完全与身分定位吻合。在这部影片中,历史“复归”到其自身不断异化的那个地点。
这部影片的惟独的“事件性”不仅因为所记录事件本身而显得突出,还由于纪录或者说收录它们的方式而得到强调。整部影片是用高清晰度摄像机一次拍成的一个镜头,从而成为有电影史以来最长的长镜头。就这一点而言,这部影片是一次令人惊奇的成功,它成功地实现了一种巨大的“杂耍蒙太奇”和复杂的场面编排。影片的动作要求整个场面调度必须反复排练至娴熟,以便用一个镜头一次拍摄下来。开头有两次出错,第三次一气呵成。俄国历史上被称为彼得大帝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就这样用一种独一无二的视线连眨眼都没有眨一下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那些似乎是属于历史的、属于博物馆的东西,全部被摄像机的一个“现场”镜头记录下来,复活起来。
影片从失明的黑暗开始,这就提示我们,这是历史,或者毋宁说,是已经成为陈列品的历史,因而也就是“故事”。也许可以说,影片并没有展开或开始,而只是开始了对历史的模拟,按历史装扮起来,像是历史的一次重演和复现。同时又是历史的独一的、惟一一次的、不可仿造的纪录、记忆和存档。所以,《俄罗斯方舟》是一部关于俄罗斯人的“方舟”①情结的影片。
叙事者的旁白从一开头就是从失去记忆开始的:“我睁开眼睛,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一点也不记得我发生了什么事。”可见这部关于档案的影片是从虚无或
①这里是作者的一个文字游戏,“方舟”Ark加上形容词词尾造成一个新词arkive,发音和“档案”archive完全相同。———译者
失忆或者说丧失回忆能力(“一点也不记得”)开始的,是从本身记忆的和视觉的空白中展开的。影片告诉我们,这是19世纪的某个时候,地点是在圣彼得堡。叙述者以及观众隐身在影片的事件中,因为叙述者说:“他们看不见我。”被称作“隐身效果”的鬼魂出场般的效果使得我们可以观察一切却不被别人看到,使得叙述者像鬼魂般出没,整个叙述从一开始起就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鬼魂般的时空之中。而同时这种时间又是处于一种不可坚持的、不可延续的悬置状态之中。所以,这部影片就随着那种视线不停地漂移。
这种盯视着变幻无常事态和历史灾变的视线,只能是历史之神安吉卢斯?诺伏斯(Angelus Novus)的视线,如瓦尔特?本亚明所描述的那样:“他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转过去……注视着一次独一无二的灾变……”历史之神凝视的眼睛在这部影片里被再现为一个极长的长镜头的独眼视线,把历史按原始状态纪录下来,也就是说,把历史在其发生和成为记忆的地方,在其存在和毁灭的地方纪录下来。可以说,索库洛夫这部影片的守护神既是警醒的又是盲目的,它既能看见历史,同时又看不见历史。这就是为什么片中有多处提及失明。譬如影片一开始就是叙述者的旁白:“我睁开眼睛,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一个前来参观的女人是个盲人,她用手触摸那个安琪儿模样的雕像(彼埃特罗?泰内拉尼的《昏厥的普绪刻》),而她本人也被当作天使,从而体现了对历史之神安吉卢斯?诺伏斯的比附;当叶卡捷琳娜女皇第二次在片中出现时,我们看到她正同一些小孩表演一个盲人的滑稽戏;而且,这一切的发生地点即这座博物馆本身的收藏品中就包含了许多以盲人为题材的名画,如:路加斯?范?莱登①的《杰里科盲人的复明》、多米尼科?费蒂②的《多比的复明》和贝尔纳多?斯特罗西③的《多比的复明》(爱尔米塔什馆藏精品之一),克尔斯泰因?德?奎宁克的《有多比雅和天使的风景》、让?比勒维尔特④(即乔瓦尼?比利维尔蒂)的《离多比雅而去的天使》以及亚伯拉罕?布鲁马特⑤的《有多比雅和天使的风景》。
据《旧约?次经》,多比是一以色列盲人。天使拉斐耳在多比的儿子多比雅做了许多好事后让他抓住一条鱼,用鱼胆治好了多比的眼睛(关于视力与忧郁症[melainchole———黑色胆汁]的关系下文中再谈)。
①
②③④⑤路加斯?范?莱登(Lueas van Leyden,1489或1494—1533),北欧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
家。———译者
多米尼科?费蒂(Domenico Fetti,1588或1589—1623),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画家。———译者贝尔纳多?斯特罗西(Bernardo Strozzi,1581—1644),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画家。———译者
乔瓦尼?比利维尔蒂(G iovanni Biliverti,1576—1644),意大利画家。———译者
亚伯拉罕?布鲁马特(Abraham Bloemaert,1564—1651),荷兰画家。———译者
如此极力强调与失明有关的东西,是要告诉我们,任何博物馆本身都可被“看”作一个这样的空间,在这里视线的明视能力既能显示出来,也可变得模糊,而被转为画幅中再现的和记忆中的视觉。正如雅克?德里达在他为另一座革命博物馆———卢浮宫———所写的《盲人回忆录》中指出的,《圣经》中多比雅的故事告诉我们,“多比最终看到的……不是这件或那件东西、这个或那个人,而是他的视觉本身”。这就是为什么索库洛夫的历史守护神的过分警觉也可能是盲目的,而影片本身则可被视为介乎于高度明察的视力和极端无情的黑暗之间的东西。
我们听到有人说,我们“来得太迟了”,到达博物馆的时候已经是历史的结束。在冬宫的地下室我们见到彼得大帝,从那里我们沿螺旋式楼梯走上来,听到有人说起“彼得大帝最初的要求”。原来,叙述者还有一个同伴,一个“欧洲人”,“俄国的”叙述者跟随这个“欧洲人”一起贯穿整部影片。这个“俄国”叙述者常常重复那个“欧洲人”的最后一句话或整段谈话,同时跟随他一起走过博物馆的各个房间。通过居斯蒂纳与“俄国”叙述者的对话所表达出来的俄国与欧洲的对峙,是一次调侃式的重复,它模糊了视觉表现的确切性和叙事的真实性。它还使整个叙事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模棱两可,从而排除了任何确定的解释或者哪怕是稍微含糊些的时空定位的可能性。所有的东西都是模棱两可和飘忽不定的,是一件真实的独一无二的事件,又是对它的一次调侃和重演。
整个叙述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种反时态的、时间错乱的模式中开始的,影片的开头就被分解给两个叙述者,表现为游走的电影场景的分裂状态。迟到的主题(舞会参加者匆匆奔跑着,他们已经来迟了,而且在巨大的宫殿中一再迷路),必定同这种故意的反时态的叙事相关,而且只能从这种角度来解读:在这里,一个或另一个叙述者或一些事件总是与时间不符。叙述本身的交替并不表明场景和地点的不同,一方面是那个总是落在时间之后、落在历史之后的博物馆里的空间,另一方面,那个俄国叙述者则讲述着历史的知识、历史的事件,乃至它“未来的”结局。
反时态的模式和视线的一分为二(而且也是从一开头就如此)是俄国导演索库洛夫和德国摄影师蒂尔曼?毕特纳得以拍出这部开创电影史新篇章的影片的补充因素。它既是属于电影史的,严格说来又不是属于电影史的,因为用来叙述和纪录事件的手段是摄像机而不是胶片。没有一种胶片可以用来拍摄对俄国历史的如此长时间的注视,而且眼睛一眨也不眨。如果说电影摄影机可以一眨也不眨地———与人眼相对而言———进行拍摄,而摄像机则是用扫描的方式纪录视觉信息,连电影摄影机中每秒24次的遮蔽都没有。在这里,镜头的眼睛不但一
刻也不被打断,而且其纪录方式就是摄像机式的不眨眼地、一刻也不间断地纪录现实的方式。与场面编排的打断、杂耍的组接和使用胶片的方式相对应,这里是不间断的数字化与电子化的视线流。
而且,在主题上也用一种历史流来对应记忆的和陈列的间断方式,所以这部影片(我们仍然这样叫它,既是为了方便,也是因为事实上它仍然保持着电影的某些痕迹:必须转成胶片以便发行放映,而且仍须在电影院上映等等)介乎于一种对身历其境的历史的叙述和博物馆展示或陈列所构成的干预,一种对本身叙事的自我反映式的介入之间。
影片制作中这种两方面分离的现象,由于在参加一次电影节竞赛放映之后不久发生的丑闻而更加显得突出(电影节向来是以炒作丑闻为能事的。不过这次涉及《俄罗斯方舟》的丑闻的性质却是和它在影片中表现的势力有关:俄国改革中把文化与传统分割开来的科技模式的松紧交替)。影片获欧洲电影学院“技术指导奖”提名,这无疑意味着完全归功于蒂尔曼?毕特纳用斯泰迪康摄像机一个镜头一贯到底的拍摄(毕特纳在拍摄中运用了他在拍摄汤姆?蒂克韦尔的《罗拉,快跑》时的成功经验)。
这项提名遭到亚历山大?索库洛夫的强烈抗议,他强烈反对把他所认为的属于艺术成就的作品整体影片因这一提名而被割裂,因为它只承认技术表现的成功,而在他看来那只是审美整体的组成因素之一。“显然,德国专家在这一作品中的作用被人为夸大了,这是一部具有鲜明民族性的俄国作品,它只可能在俄国实现,在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俄国文化部的参与下实现。在俄国制片乃至欧洲制片都感到极大困难的年月里,没有俄国政府给予的支持,《俄罗斯方舟》的设想和拍摄是根本不可能的……影片导演:亚?索库洛夫,制片人:亚?捷里亚宾,俄国圣彼得堡,2002年11月29日”。
贯穿整部《俄罗斯方舟》表现出一种焦虑,即由居斯蒂纳所代表的那种目光在叙述者心中引起的某种焦虑,叙述者在这里仿佛以较缓和的语调重复着居斯蒂纳的某些最为激烈的评语,同时他在爱尔米塔什即冬宫内走动时始终有一个在演员表里被称为“间谍”的人伴随。由独一无二的镜头所体现的整体上的警觉氛围(由居斯蒂纳引入,再经叙述者、间谍等不同角度的重复强化)可以借用恰达耶夫在《狂人的辩解》(写于1836年)中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即俄罗斯为这种警觉殚精竭虑,无法把目光从西方移开。西方给俄罗斯品格带来的这种分裂堪称构成了《俄罗斯方舟》的表达空间。就这种意义而言,索库洛夫影片的文本精确地表达了对俄罗斯所以形成其品格的那一深刻冲突的探究。毫无疑问,这一精彩表达被绝口否认,并且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由影片作者加以复原,然而且只
能称作是为了保持“艺术上的完整性”,然而这一艺术创造当然又是“俄罗斯的”。情况仿佛是为了保持民族属性的纯洁性,导演不得不从影片的成功中抽去技术成就的异国性质。在影片里强有力地表达出的并成为这部影片的创作动力的那种焦虑感,可以说在这里形成一个盲点,使人看不到反对这部影片的民族归属本身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暗示。索库洛夫看起来就像是他那个欧洲伙伴的一个强烈维护自己权利的孪生兄弟。
由彼得大帝发动的俄国的现代化在俄国第一座博物馆———珍品陈列馆中得到了体现。彼得大帝在这里陈列了一大批动物标本、岩石和矿石标本,而且还有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体器官和胚胎。所以,俄国的现代化和最早的革命就是把俄罗斯做成博物馆的陈列品。启蒙思想的引进表现在博物馆的空间,在这里,动物、矿物、怪胎和人体器官全都是标志着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开创,或者可以说是大洪水后、大灾变后对俄罗斯进入历史的一个纪念(当然,诺亚方舟可以看作是最早对动物进行分类保护的一次尝试,一座“自然”精华的博物馆。在我们试图理解博物馆在索库洛夫的《俄罗斯方舟》中的作用时,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因此,珍品陈列馆的作用并不是俄国保存对于自己过去的记忆或其民族品格光辉的地点,而是以革命的精神期盼帝国的扩张和荣耀的所在。这不是一个纪念的遗址,恰恰相反,正如有人就一般博物馆已经指出过的,这是“博物馆的革命性的产物,除了引起人们寻根的激情、归属感和认同感之外,还呼唤人们对文化进行反思”。马略夫尔对博物馆的精彩概括也完全适用于珍品陈列馆:“作为一座博物馆,它告诉我们,没有除旧更新,没有遗忘,就没有文化的发展,所以,按照尼采哲学的精神,文化始终是艺术性的一种培植”。
珍品陈列馆的这种革命性质是我们应该铭记的,因为正是彼得大帝第一个在俄国创建博物馆,并最早推动了对文化珍品的收藏,这些珍品也就奠定了灿烂辉煌的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方舟》的主角———的基础。珍品陈列馆的这一层含义也给现今这个收藏场所留下了一份历史存在的痕迹,即保持和遵守那位开明君主法律的原始训谕,从而保持了对珍品陈列馆的政治影响力的铭记:正是它既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也是记述这座博物馆的这部影片的基础和原型。《俄罗斯方舟》中的另一个主角,欧洲人居斯蒂纳侯爵,具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他始终嗅到一种气味,那就是福尔马林。充斥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福尔马林气味实际上属于另一个博物馆,即珍品陈列馆,因此可以看作是俄国第一个收藏场所的痕迹。
居斯蒂纳嗅到的、充溢于爱尔米塔什的福尔马林也许还提示着来自索库洛夫的某种自我反映的介入,提示着用一个单独镜头完整保存“生活”———如他在
影片中所作的———与用福尔马林保存藏品标本———保持有机物的原来形态而似乎并不需要任何展示的屏蔽———两者之间的吻合。拍摄影片与制作标本之间的联想决不是一种牵强附会。正如制作标本时把皮肉保存在福尔马林中,从而使皮肉中的生命保持它永远不朽的、幽灵般的形态一样,电影胶片“这小小的皮”,这片薄膜,也因在洗印过程中完成化学分解而被固定下来。两者都把皮肉展示给我们,如里欧塔德在《无电影》一文中说的,“像是[透明的]肉体在展示自身”。
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可以说是珍品陈列馆的一个复制,片中是这样表现这一点的,即在影片一开头,在冬宫即爱尔米塔什的最深处,在它的地下室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位皇室人物就是彼得大帝。就是说,奠定博物馆基础的第一文献,如索库洛夫所表现的,就是出自这个俄罗斯第一位改革家的。而且,也正是彼得大帝首先开始了艺术品的收藏,他的藏品成了建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基础。所以爱尔米塔什在这部影片里,以及在历史上,既是一个陈列的场所,一个纪念过去的场所,又是一个发生政治动乱、革命和历史断裂的场所。影片和博物馆两者都摇摆于两种不同的呈现体系之间。
影片在呈现方式上的摇摆不定更因下述情况而变得突出,即影片主人公有时又进入彼得大帝时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在影片中,彼得大帝时代在叙事时间上被限定为上起彼得大帝,下讫1913年最后一次革命前的舞会)。片中有三处把
叙事直接延伸到革命后时代的场景,对于本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一个场景
里,居斯蒂纳走进了一个列宁格勒围城①时期的房间,当时博物馆藏品几乎全部被转移到西伯利亚,这里只剩下一堆空画框。一个木匠正在给自己打制棺材,因为他与围城期间成千上万的居民一样已经快要饿死了。这个场景中的空画框可以说正是对整个博物馆的一个转喻,正如影片中所展示的:影片对博物馆在审美的或政治的含义上的表现可以说就是俄国历史形成过程的一种陈述。“这样一座”博物馆,以及这样一部影片本身,的确可以被视为俄国历史的一副空框架,或者说是俄国历史形成机制的一种陈述。
在另一个场景中,居斯蒂纳走进今日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意大利天光小厅,并同两位圣彼得堡退休人员就丁托列托的《施洗约翰的降生》展开了一番议论。这场邂逅突出了场景在时间上的错位:居斯蒂纳根本无法理解现今圣彼得堡的风情,只有对当今服饰的简陋格调大感诧异。
第三个直接侵入今日现实的地方则是把博物馆历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物拉在了一起。在博物馆的某一大厅里,我们看到1934至1951年任馆长的约瑟夫?奥尔别利、1964至1990年任馆长的鲍利斯?皮奥特罗夫斯基,还有他的儿子现任馆长(自1992年起)米哈伊尔?鲍利索维奇?皮奥特罗夫斯基。前两位均已过世,所以自然是由演员扮演的,而米哈伊尔?皮奥特罗夫斯基则是本人出场。这三位正在讨论如何修复一件遭到虫蛀的皇冠(一个不太含蓄的对革命的暗示)以及宫殿的墙内是否仍遍布着苏联时期克格勃安装的窃听器,这些东西都隐藏在无数的挂毯背后,根本无法检查出来(据米哈伊尔?皮奥特罗夫斯基对撰写爱尔米塔什历史的杰拉尔丁?诺曼所说,这些窃听器仍旧存在但已不使用了)。这时有一个人进来请现任馆长出去一下,谈话于是中断。这个场景可以说代表了整部影片贯彻始终的表达模式,即把这座博物馆的空间当作反复书写的古老书卷,上面留下了各个不同时代幽灵般的痕迹,它们同时存在并互相印证。
这种以时间错位方式表现现代情景的段落仿佛是影片中的一些休止和中断,突出了观众与爱尔米塔什所经历事件之间的距离感。时间上的中断表明了属于彼得大帝时代的和属于当今时代的事件之间的距离。苏联时期所造成的中断借助于把宫殿表现为博物馆并模糊其政治含义而被“填补”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转入现代的段落似乎要“修补”爱尔米塔什的政治内容(克格勃、战争),而第三次则是居斯蒂纳颇为倨傲地拒绝把博物馆看作一个绘画陈列馆。与此同时,历史上的恐怖———这是表明冬宫深深卷入历史进程的重要标志(除了以攻打
①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从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872天,史称“围城900日”。———译者
冬宫开始的革命时期的恐怖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博物馆的人员在斯大林时期的清洗中被判刑和处决),在影片中却明显缺失。这是不能展示的负面历史,是真正的停顿、时间的中断,是在影片时间结构和俄国历史中插入的灾变时段,它是不能呈现于视觉影像的。
拒绝或者委婉地抵制把爱尔米塔什看作博物馆,这一点可能是表明索库洛夫不愿意把这座博物馆看作仅仅是过去某段历史的存档。整个影片可以看作是小心地抹去了整个苏联时期,对于这一时期,除了它的缺失实际上未作任何表现。此外,这部影片显然也抹去了占主导地位的电影传统———谢尔盖?爱森斯坦所首创的杂耍蒙太奇和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所倡导的拍摄生活原貌并予以大量剪辑的做法。
这样的时间布局构成一个比喻,暗示它既不能接受当代历史的含义,也不能抹去过去历史的顽强存在———它透过叙事的时间框架而呈现出来。同时,这个比喻式的结构在下述场景中被强调表现出来:居斯蒂纳先是面对伦勃朗的《献祭以撒》,后来又在《浪子回头》面前陷入沉思(这两幅画是爱尔米塔什藏品中最著名的作品)。在这沉思中我们听到飞机声,这表示列宁格勒正处于围困中。这一场景过后,叙述者告诉居斯蒂纳,围城期间死了一百万人,接着两人讨论起为这一历史献祭所付出的代价(“代价太大了,”居斯蒂纳说,但接着又说,“不过,也许并不算大”)。
所以,影片表现的这个中断并不是因剪辑而造成的切换,而是由于这个比喻性献祭的插入。影片一方面毫不间断地拍摄着“现实的”事件和历史,同时又不时被比喻性场景打断,使人不能直接感知时态。反过来说,本来是回顾和思考场所的博物馆,却一再被历史和政治的赤裸裸的现实突然插入。事实上《俄罗斯方舟》所表现的只不过是“现实的历史”和它变成博物馆藏品的归档之间的不断交叉。
摄像镜头不间断的警觉目光在这部影片中形成了对参照系无数次的重复和分割。呈现模式既是历史的重演,又是历史的一次展现;既出于导演索库洛夫的场景编排,又出于摄影师毕特纳的技巧处理;且往返回响于叙述者和“欧洲人”居斯蒂纳两个角色的调侃式对话之间。影片中所表现的居斯蒂纳保留着《1839:俄国通信》作者“原型”的某些痕迹。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和保皇党人,“去到俄国本是为了寻求反对代议制政府的论据,从俄国归来时却成了一个宪政鼓吹者”,他所写下的这部游记大概是任何游历过俄国的人所写下的最具批判性的文献之一(堪与瓦尔特?本亚明的《莫斯科日记》媲美)。这本书里含有若干对俄罗斯特点及其未来历史的惊人的真知灼见和准确预言。比如,试看居斯蒂纳对圣彼得
堡空旷的空间是怎样思考的:“在圣彼得堡将会第一次出现巨大的人群,城市将被冲垮。在一个如此组成的社会里,人群就意味着革命。”
索库洛夫的居斯蒂纳没有保留如此强烈的批判力度。不过,他是牢骚满腹的,既是批判又是痛心地哀叹俄国“重复着西方的错误”。在《俄罗斯方舟》中,居斯蒂纳有时像是一个懂得鉴赏艺术的审美家(在一个地方,他热烈赞叹着:“妈呀,妈呀,卡诺瓦的《三美图》”),有时像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对这些事件他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理解)。他认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是西方的一个翻版,他的这些深刻见解又被画外的叙述者加以翻版,加以重复,分别以调侃或无奈的语气重复着。例如,叙述者告诫居斯蒂纳不要进入那个呈现列宁格勒被围城景象的房间,或者谴责他对俄罗斯的评价太过粗暴(“我读过你们大诗人普希金的诗,法文译本,没什么了不起”)。
居斯蒂纳被表现为既是“现实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一件博物馆的古董或者说艺术品。在一个场景里,他向试图粗暴地把他逐出某个房间的职员吹胡子瞪眼。在同一时间里,这个场景既把居斯蒂纳表现为叙事时间里的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把他变成一个艺术品的代表或者说比喻(这也有力地突出了影片表现方式的力度变化)。鼓起两腮吹气或喷水的形象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装点在圣彼得堡各处水景以及布置在彼得戈夫(卡尔洛?巴托洛缪?拉斯特雷利仿照凡尔赛宫的马尔里流瀑建造的景观)的那些海怪、美杜莎、仄费洛斯、埃俄罗斯、波塞冬和特里同①等等的雕像。
这一场景突出显示了影片叙事的比喻式结构,叙事的展开在这里把各个事件呈现为不同形象的反复,这些形象不仅代表孤立的含义,而是随着一系列地点的转换,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把叙事不断向前推进。这个场景标志着一种叙事方式,即场景的含义要通过一系列地点的变化才能把握,每一地点决不能理解为某种单独孤立的含义。叙述者尽管熟知历史事件,却也表现得对这一场景的比喻含义不甚理解,因而责备居斯蒂纳说:“我不大喜欢您,先生。”
《俄罗斯方舟》略去了居斯蒂纳本人的著作中某些极富预见性的见解,因而局限了他对今日俄罗斯的理解(他那广泛涉猎的能力完全可以对俄罗斯现状作
①美杜萨(Medusa),又译墨杜莎,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原为一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无数毒蛇,面目奇丑无比。仄费洛斯(Zephyrus),希腊神话中的西风神。埃俄罗斯(Aeolus),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他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分别代表十二种风。波塞冬(Poseidon),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能呼风唤雨,引发地震。特里同(Triton),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之子,他吹响海螺时可以兴风作浪,也可以使风浪平息。
出解释),但同时又表现了他充分理解俄罗斯在1913年冬所面临的灾变深渊。在叙述者与居斯蒂纳的最后一段对话中,居斯蒂纳拒绝前进,停留在彼得大帝传统的时代范围之内,不愿跟随叙述者一起“进一步”走入历史,达到今天的视角并获得充分的历史理解。然而与此同时,当叙述者失去了居斯蒂纳时,他便体验到一种迷失或失去历史的感觉,所以最后一个场景的结束是叙述者的一段独白,哀叹他无力完全理解俄国历史。由于这两个叙事角色的相互匹配,对俄国历史的“完全”理解便产生于欧洲和俄国之间相互倾慕与鄙弃、盲目与洞察的辩证关系中。
长镜头使得一个事件或一段情景的时间自动呈现出来:“长镜头的时间就是事件的时间。”专门研究长镜头问题的乔恩?比斯利-默里在分析塔尔科夫斯基的《牺牲》时说:“长镜头纪录的‘真实性’是以段落本身的不可重复性为证的。”索库洛夫的《俄罗斯方舟》可以说是证明这一理论观点的范例,但与此同时,由于它在技术记忆上的极端做法———把事件的时间压缩在一部影片里,《俄罗斯方舟》又对技术视觉论的电影理论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难题。
如果说,在偶尔使用长镜头的常规影片中,是整体影片时间包含或框定这些长镜头,那么,在《俄罗斯方舟》中,整体事件就是影片本身。这一独特影片本身就是由拍成它的一个凝视的目光所框定的,也就成为录像本身中的一段。所以,这部影片是一个镜头中的镜头,它既是对事件展开的极度明察,又是对影片观察能力本身的显示。影片紧紧跟踪着目光,它既是这种目光的警觉的代理,又是这一目光的盲点。这就再次可以说明,为什么影片开头是由叙述者的失明状态逐渐转入影像的。而这部影片的制作(按字面含义而言,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确就是这部影片的制作方)就是由影片所要“看见”和拍摄的博物馆本身承担的。所以,这部影片既是它产生的历史的视觉痕迹,同时也是产生它的历史的创造者。就像一条麦比乌斯带①,《俄罗斯方舟》成为它的电影框架与它的参照系之间的无限分割。
影片最初具有的极度明察的视觉至少在一处地方被强调表现出来,即当我们看到叶卡捷琳娜女皇在爱尔米塔什宫里演出一场戏剧的时候(叶卡捷琳娜女皇还是一位作家,并亲自导演了几出她所创作的巴洛克风格戏剧,例如《奥尔嘉》)。所以,视觉的产生和历史的产生就同时呈现在影片本身中。这种深邃的、极度明察的视觉则由保存视觉记忆和文化的场所本身———博物馆———进一步强
①麦比乌斯带是将一长方形纸条的一端先扭转180°再和另一端黏合起来所得到的单侧曲面。———译者
调出来。居斯蒂纳在博物馆里一路走一路赞叹着那些绘画的精美,而镜头的运动则紧紧追随着他的目光。
不过,这种对于历史及其视觉存档的明察却是建筑在完全的失明,建筑在摒除或删节之上的。一些事件发生于后彼得时代,但是没有一件哪怕隐约地提及如下这一惊人的巧合,即爱尔米塔什不仅是俄罗斯帝国权力和权威的源头,而且这座冬宫即爱尔米塔什宫也是苏维埃革命的标志性地点。苏维埃夺取政权和发动革命正是以攻打冬宫为标志的。
把这一历史从视野中抹去并不意味着降临在爱尔米塔什以及那个体制和时代上的灾变在影片中就感觉不到和不存在(在叙述者对居斯蒂纳说的一句话里提到了这一点:“我们也有过将近80年的一个体制,那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也许正是这一时期的缺失,才使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恐怖(任何一次历史灾变最深远的影响只有在该事件变成档案后的点滴遗迹中才能让人感受到,这恰恰是历史灾变的特点)。贯穿整部影片可以听到刺耳的尖厉杂音和嘎嘎的低沉轰鸣,中间偶尔穿插着格林卡或柴可夫斯基极富抒情性的钢琴曲片段。这些声音回应着灾变的不协和音。最后的结尾也暗示着恐怖:居斯蒂纳拒绝跟随叙述者跨过时间的门槛,他含泪的目光和失落而忧郁的表情突出表达了事件的断裂。同样,在影片开头,事件的突现也是借叙述者从灾变造成的失明中醒来而表现出来的。他只能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灾变,但一点也不记得了(“发生了大灾难,我一点也不记得我怎么了”)。
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方舟》中的一个缺失环节,它对这座宫殿的灾难性影响构成了拍摄这部影片的隐含的渊源。正由于它是一件后历史的、后灾变的事情,这部影片救世的明示题旨才可能是有意义的。爱尔米塔什就是苏维埃历史洪水之后的俄罗斯方舟。
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电影传统恰恰是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冬宫形成的,那么这种隐含的渊源感觉就更加突出了。几部最闻名的影片,如普多夫金的《圣彼得堡的末日》,尤其是爱森斯坦的《十月》都曾把冬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如果没有爱森斯坦的《十月》和在《十月》中的“吊桥”一场所使用的蒙太奇技巧(其重要性和知名度仅次于《战舰波将金号》的“敖德萨阶梯”),电影史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但影片《十月》恰恰表现为冬宫的毁灭,冬宫作为历史遗址和展示场所在影片中被表现为可憎恨的所在。影片的主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贬斥这座宫殿的富丽堂皇。影片拍摄工作本身就是对这座博物馆景观的贬损。在《十月》里,爱森斯坦以巴洛克风格的雕像作为腐朽的制度的象征,把冬宫作为一个展示场所。
在攻打冬宫的一个极短的场景里,布尔什维克战士通过地下室进入宫中,这时摄影机镜头凝视了一下存放在地下室的物件,显示这是一些馆藏物品,上面挂着写有“埃及”和“叙利亚”字样的标签。这个场面可以说就是把冬宫表现为博物馆的储藏室。维克多?史克洛夫斯基在他1939年的《日记》里回忆起:“冬宫的工作人员们说,第一次攻打冬宫造成的损害远没有第二次(即拍摄电影时)严重。因为布尔什维克们要打倒的是临时政府,而不是宫中的陈设。”在史克洛夫斯基的反思中,苏维埃革命时期,冬宫一方面在政治上趋于中性化,另一方面在文化和艺术上则是被抹杀。《俄罗斯方舟》正是从这种灾难性的盲目状态中发掘出了它的视觉资源。
影片使用极长的长镜头的另一隐含的潜在背景,是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利用剪辑作为影片创作手段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带电影摄影机的人》不仅包含极短的镜头,组成异常急速的段落,打断历史时间的“正常”流逝,抹去过去的历史(被毁掉的剧院),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潜在的、不可见的镜头,即短到不足24格,低于视阈,因而不能被感知,而只是影片的视觉潜意识。《俄罗斯方舟》可以作为表明吉尔?德洛兹所谓的二战前现代主义电影的运动形象与其后的时间形象之间的差异的最令人信服的例证。
影片所展示的正是用摄像机“临场的”目光保存传统的那一个瞬间。临场的目光看到了一个整个被抹杀、被毁掉的时代。正是这种极限的视觉与展示的毁灭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俄罗斯方舟》最引人注目的效果。它并不想要“重建”帝国的过去,而只是证明着历史的破坏力量和过去的不可逆转,影片所“重建”的这个
时代和世界遭受着多重的政治历史的和审美的抹杀。这个长镜头所能展示的(“事件的时间”)实际上是摄像机与它所表现的“对象”之间的一个不可见的休止和中断。这个不间断的、从理论上说是无限的、至少是没有任何切换的、一直不眨眼的目光,所看到的是对可见的、所展示的东西的无情地损毁和毁灭。这就造成《俄罗斯方舟》在结构上那种取向不定,并把这艘方舟推向一些出人意料的、毫无预期的地点(与创作者索库洛夫公开声称的意识形态———或视觉形态?———目标形成对比和恰恰相反)。
可见事物的毁灭一度是索库洛夫创作上最专注的主题。他的一些影片不仅突出地表现死亡和毁灭,而且还直接展示死亡的时刻,使死亡尽可能成为可见的过程。这在他后来的两部影片《第二圈》和《母与子》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两部影片的主题都是关于父母的死亡。前一部是儿子回到家时发现父亲已死。整部影片讲述的就是送葬的准备和葬礼的过程。索库洛夫影片中“处理”死亡的特点就在于,他不是用影片来否定或拔高死亡的主题,使观众得到一种不朽的印象。正如米哈伊尔?扬波尔斯基在他对索库洛夫作品一系列出色的分析中指出的,《第二圈》的导演“不是给我们呈示一个虚构的战胜死亡的过程,而是让我们面对死亡本身”。这种处理方法的结果是:在索库洛夫的影片中,可见世界的轮廓趋于消失,无论镜头聚焦保持清晰还是事物界线变得模糊(例如在《母与子》中和《俄罗斯方舟》的结尾部分)。世界的轮廓变得模糊是因为他把活的躯体同“死的”物件以一种不明确的形状并列在一起。在这方面,《第二圈》就是模糊了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可见世界存在的坐标,从而使影片中有了一些“盲区”。
索库洛夫创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极度偏爱忧郁的感情。恰恰是忧郁,而不是悲伤(可以回忆一下弗洛伊德那个有名的界定,悲伤时对痛失的对象可以借悲悼礼仪或以艺术或电影之类进行替补而得到补偿和外化)。忧郁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挚爱而痛失的对象仍然完整地深埋在一个人的心底,不能借悲伤而驱除,同时以一种失落的空虚感充满他的心理。在忧郁中,“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失落。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可以说,索库洛夫的影片就是用空虚填满他所表现的世界,并以痴迷式的归档保藏使这种空虚内化。因而影片不是用电影去补偿失落,而是变成一种积淀,一种档案———或者博物馆———把不能或不肯消失的失落保存下来。影片的时间就是以痛失对象的空虚来充填画框的那个时间;而进入镜头的可见物越多,影片给人造成的失落感却会越重。索库洛夫的影片在这点上追求做到极致,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采取用长镜头拍摄(或如《俄罗斯方舟》那样只用一个长镜头拍摄)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方式了。
此后,他的影片《母与子》(1997)也是以同样富于激情的表现方式为基础的。
影片第一个镜头大约就有8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垂死的母亲和她的儿子没有动作,只是儿子走出画框8分钟然后又回到垂死的母亲的床前。全片只有很少的镜头,而这些镜头又都是透过污浊不清的透镜或加了变形纱罩拍摄的。目光本身变得游移不定,仿佛是表示眼中含满泪水。扬波尔斯基在他关于《母与子》的文章中指出,索库洛夫的影像“是从废墟中,从死亡的一团混乱状态中呈现出来,仿佛是把生命翻转过去,而不是把它展示出来。在索库洛夫的创作中,可以找到某种类似的东西,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影像(表现)活生生地呈现,然而却是从废墟亦即死亡中呈现出来的”。索库洛夫拍摄影片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并非———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生存走向死亡的感觉,而是某种生存于死亡之中,处于垂死的艰难境地的感觉,或许可以说是生存伴随着别人死亡的感觉。在《母与子》中,死亡的对应时态与因别人死亡而死亡的感觉通过一段对话表达出来———母亲临死时对儿子说:“我为你心疼,并不是因为你要孤独地留在世上,而是你不得不承受我现在的状态,承受我的死亡。”这样就把影片的时态在形象的运动中分解开来,抓住了生命中的和把生命在死亡中分解的差别。不过这里的死亡并不是被体验为自我的隔绝,而是别人在我心中死去,我在别人心中死去。
确切地说,生命的毁灭,生命参与和承担死亡,正是索库洛夫影片创作激情的基础。正因如此,毁灭的废墟才会在索库洛夫的影片中起着那么重要的标志性的作用,像在《母与子》中那样(影片中他们的家被展示为已被风雨摧毁;同样,《第二圈》中父亲死后的房子也是漏雨的)。在他1996年拍摄的短片《罗贝尔:幸运的生活》中,则把废墟作为主题做了最充分的发挥。选定罗贝尔①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这位画家毕生都在描绘废墟,而他的作品———我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俄罗斯方舟》———在爱尔米塔什藏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确实,在爱尔米塔什藏品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恰恰是于贝尔?罗贝尔,他的绘画数量和在藏品中的位置堪与伦勃朗媲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收藏的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描绘废墟的:《公共浴室遗迹》、
《废墟风景》、
《园中露台废墟》,以及凑巧与在爱尔米塔什拍摄的本片非常有关的《隐士的居所》②。正如迪迪埃?马略夫尔指出的,在罗贝尔的绘画中,视线的毁坏、景物的瓦解本身造就了一个空间,使艺术“在巨大灾变之后,在历史和艺术终结之后”得以存在。所以,也正是于贝尔?罗贝尔使
①②于贝尔?罗贝尔(Hubert Robert,1733—1808),法国风景画家,有时被称为“废墟罗贝尔”。———
译者
爱尔米塔什一词原意即为隐居处或隐修院。———译者
我认清了索库洛夫所要表现的爱尔米塔什的内涵。
罗贝尔在他的《想像中的卢浮宫游廊废墟景象》中把卢浮宫博物馆画成历史浩劫之后留下的残迹。但裂迹只能是残留物的废墟,而当这些残留物被展示在博物馆里时,就会使我们想到,各种博物馆的确是一些档案和方舟(或约柜),艺术品在这里分类陈列造成了一个废墟的空间,或者说它是灾难所造成的结果。“归根结底,《想像中的卢浮宫游廊废墟景象》中的废墟就是这幅绘画本身;历史异化的震撼体验就是艺术的审美表现”。那不仅仅是罗贝尔在描绘废墟,那是艺术本身在变成废墟,它出现在历史中并被罗贝尔的绘画赋予了可见形态。
与《母与子》和《罗贝尔:幸运的生活》一样,《俄罗斯方舟》使得此类的景象可以拿出来展示。这个博物馆中的长镜头拍下了文化化为废墟的过程。俄罗斯的全部文化档案都呈现在这里,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说它是第一次是因为,它的全部“现实”被摄像机的“临场”目光在它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次捕捉下来。摄像机镜头把文化的现实、把一个完整的时代,在其历史和政治表现的源头和起点捕捉下来。而同时,《俄罗斯方舟》又纪录下了那个历史的毁灭、毁灭的历史以及那个失落了的世界的宝贵档案。
影片中“故事的发生”同时既是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它既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不可模拟的事件,一次没有样本、没有先例、没有重复的事件,同时又是一座纪念碑,是过去和未来之间一个时段的历史和纪录,是一段历史的轨迹,是一次重演、一个反复记号、一份档案、一艘方舟和一个符号。因此,索库洛夫的每一个镜头都总是一个回马枪。《俄罗斯方舟》表现的既是苏维埃历史发生之前的,也是这段历史结束而留下一片废墟之后的事情。它既是在历史发生之前,也是历史发生之后。《俄罗斯方舟》是这样一部影片,它要展示给人看的可以归纳为历史的机制本身:它独一无二地初次发生,又作为第一次的复制而发生。它告诉我们,全部历史的发生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重复,一次反复,但是只发生一次。
《俄罗斯方舟》也可以说展示了、利用了并抹去了一个本身令人忧伤哀悼的时代。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副本、成为废墟后的潜台词,即苏维埃俄罗斯,像是在影片中游荡的幽灵,隐现于影片的字里行间。这部影片仿佛是以极大的努力去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抹去那个抹掉片中所展示的传统的整个历史时期。苏维埃艺术一再重复援引爱森斯坦、马列维奇或维尔托夫的模式。普多夫金的《圣彼得堡的末日》(1927)和爱森斯坦的《十月》(1927)的结尾都结束在同一个地点,即冬宫中的约旦阶梯。两部现代电影经典作品的两个结尾被援引而作为《俄罗斯方舟》的结尾,但在语义上和意识形态上却被翻转了。而把生活当作死亡加以收藏和陈列的整个做法不能不使人回想起维尔托夫在《关于列宁的三支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