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树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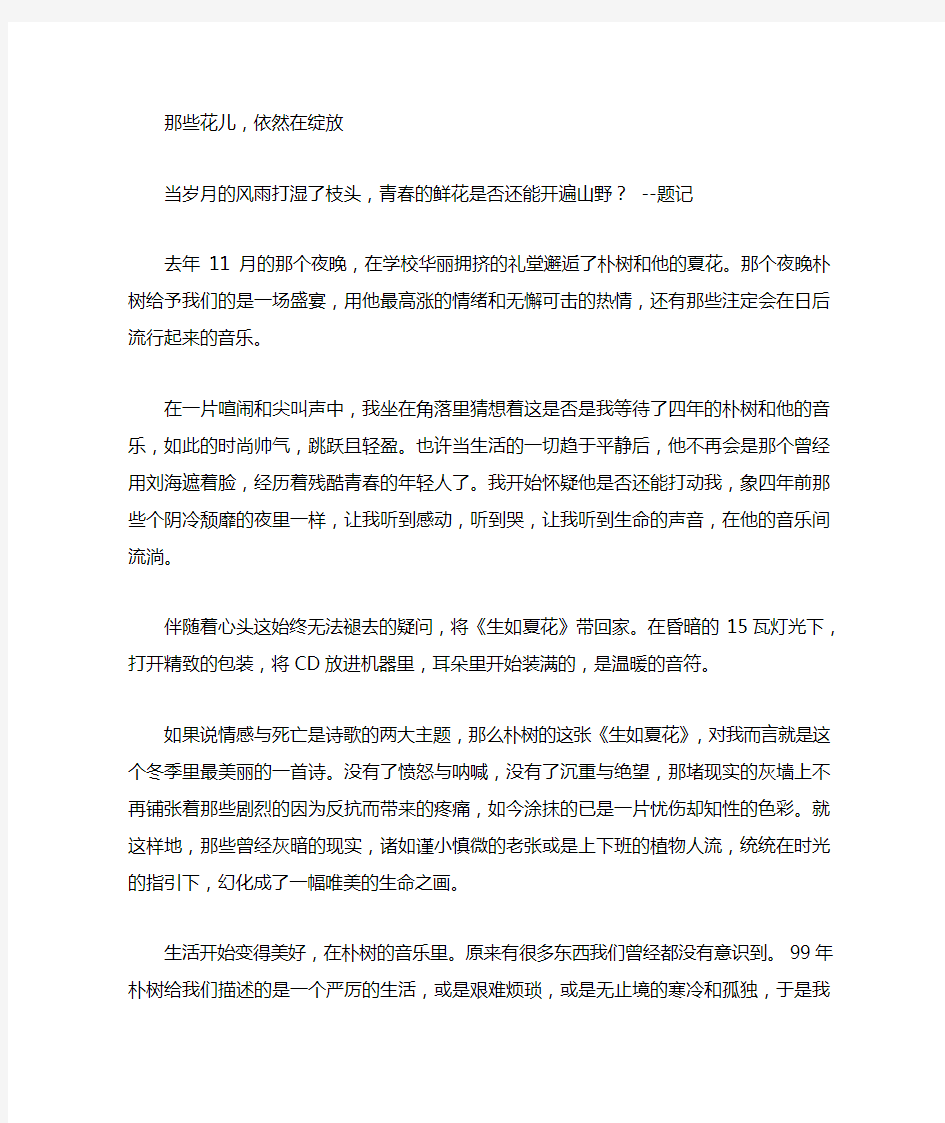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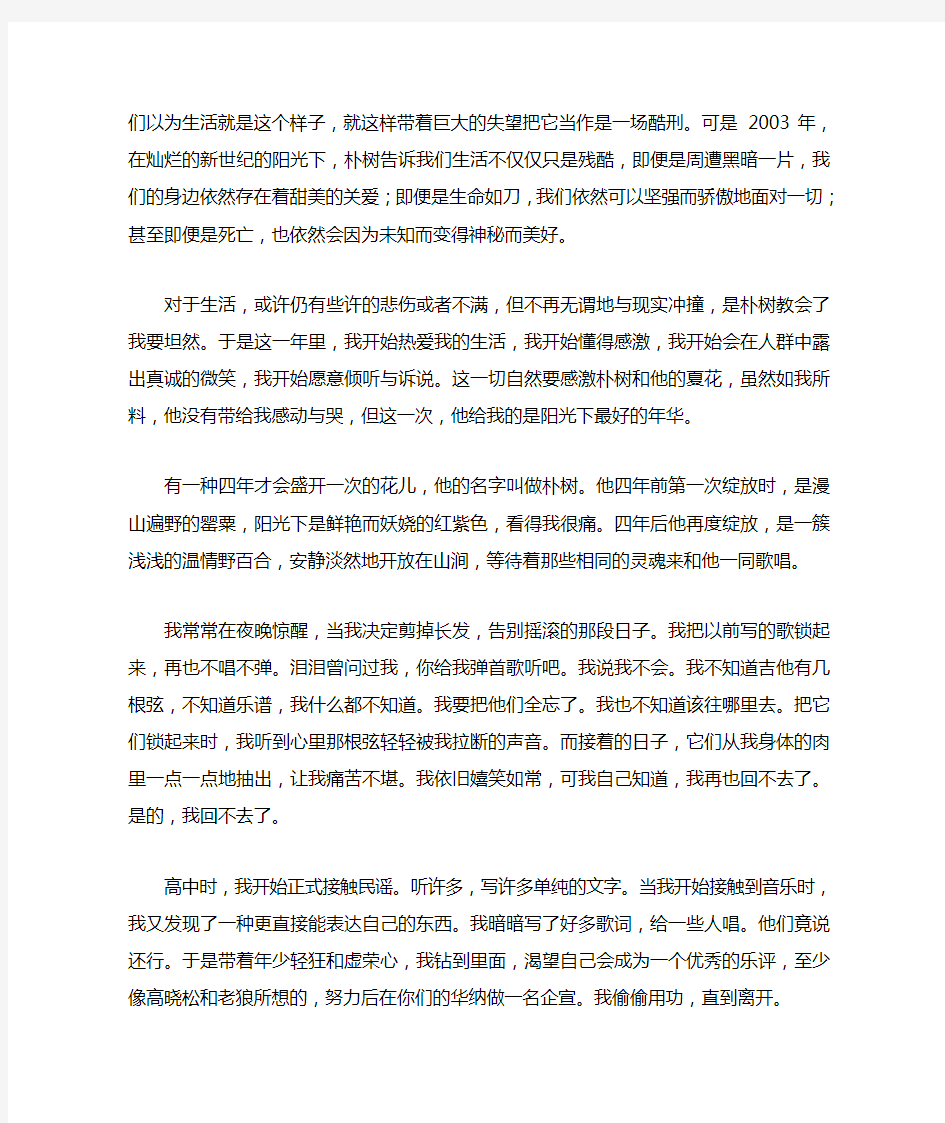
那些花儿,依然在绽放
当岁月的风雨打湿了枝头,青春的鲜花是否还能开遍山野?--题记
去年11月的那个夜晚,在学校华丽拥挤的礼堂邂逅了朴树和他的夏花。那个夜晚朴树给予我们的是一场盛宴,用他最高涨的情绪和无懈可击的热情,还有那些注定会在日后流行起来的音乐。
在一片喧闹和尖叫声中,我坐在角落里猜想着这是否是我等待了四年的朴树和他的音乐,如此的时尚帅气,跳跃且轻盈。也许当生活的一切趋于平静后,他不再会是那个曾经用刘海遮着脸,经历着残酷青春的年轻人了。我开始怀疑他是否还能打动我,象四年前那些个阴冷颓靡的夜里一样,让我听到感动,听到哭,让我听到生命的声音,在他的音乐间流淌。
伴随着心头这始终无法褪去的疑问,将《生如夏花》带回家。在昏暗的15瓦灯光下,打开精致的包装,将CD放进机器里,耳朵里开始装满的,是温暖的音符。如果说情感与死亡是诗歌的两大主题,那么朴树的这张《生如夏花》,对我而言就是这个冬季里最美丽的一首诗。没有了愤怒与呐喊,没有了沉重与绝望,那堵现实的灰墙上不再铺张着那些剧烈的因为反抗而带来的疼痛,如今涂抹的已是一片忧伤却知性的色彩。就这样地,那些曾经灰暗的现实,诸如谨小慎微的老张或是上下班的植物人流,统统在时光的指引下,幻化成了一幅唯美的生命之画。生活开始变得美好,在朴树的音乐里。原来有很多东西我们曾经都没有意识到。99年朴树给我们描述的是一个严厉的生活,或是艰难烦琐,或是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于是我们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带着巨大的失望把它当作是一场酷刑。可是2003年,在灿烂的新世纪的阳光下,朴树告诉我们生活不仅仅只是残酷,即便是周遭黑暗一片,我们的身边依然存在着甜美的关爱;即便是生命如刀,我们依然可以坚强而骄傲地面对一切;甚至即便是死亡,也依然会因为未知而变得神秘而美好。
对于生活,或许仍有些许的悲伤或者不满,但不再无谓地与现实冲撞,是朴树教会了我要坦然。于是这一年里,我开始热爱我的生活,我开始懂得感激,我开始会在人群中露出真诚的微笑,我开始愿意倾听与诉说。这一切自然要感激朴树和他的夏花,虽然如我所料,他没有带给我感动与哭,但这一次,他给我的是阳光下最好的年华。
有一种四年才会盛开一次的花儿,他的名字叫做朴树。他四年前第一次绽放时,是漫山遍野的罂粟,阳光下是鲜艳而妖娆的红紫色,看得我很痛。四年后他再度绽放,是一簇浅浅的温情野百合,安静淡然地开放在山涧,等待着那些相同的灵魂来和他一同歌唱。
我常常在夜晚惊醒,当我决定剪掉长发,告别摇滚的那段日子。我把以前写的歌锁起来,再也不唱不弹。泪泪曾问过我,你给我弹首歌听吧。我说我不会。我不知道吉他有几根弦,不知道乐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把他们全忘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把它们锁起来时,我听到心里那根弦轻轻被我拉断的声音。而接着的日子,它们从我身体的肉里一点一点地抽出,让我痛苦不堪。我依旧嬉笑如常,可我自己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是的,我回不去了。
高中时,我开始正式接触民谣。听许多,写许多单纯的文字。当我开始接触到音乐时,我又发现了一种更直接能表达自己的东西。我暗暗写了好多歌词,给一些人唱。他们竟说还行。于是带着年少轻狂和虚荣心,我钻到里面,渴望自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乐评,至少像高晓松和老狼所想的,努力后在你们的华纳做一名企宣。我偷偷用功,直到离开。
爸爸最后一次大病时,我还在复读。从医院回来,我常常打完饭后,坐在一片空地上。我看着西南的天际,看着飘过的白云和蔚蓝的天空,想,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我感谢爸爸赐给我的生命,我要好好的过。要是我能用自己的二十年换取延长爸爸生命的五年,我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所以爸爸去世后,我不能再玩了。真的不能玩了。它召唤我回去,虽然这让我痛不欲生。
所有的白云苍狗桑田沧海云淡风轻都再与我无关,唯一让我存在的理由仅仅只是一个——活着。动物凶猛的那个年代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只能在午夜枕边回味那个愤怒的年代。每天晚上,对着镜子里的那个面容憔悴胡子唏嘘眼神浑浊的影子,我再不敢正视自己内心那些曾有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想起以前有段时间,我们要排《旅途》,我天天带个耳机,准备把它扒下来。三月末的一天我到校报去送我们校区的新闻稿,坐上了19路车。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坐在左边第三个靠窗的位子,听着听着,泪流了满脸。我要告别它们了,尽管我十分不愿,可我必须这么做。
稿子我没送就回去了。那一夜,围着云龙湖走了两圈,三个空酒瓶被我依次扔进湖里,烟也抽完了,鞋里的水到天明也没干。爬回学校,爬到2#楼顶,姑娘们睡沉好久了。望着头顶上晴朗的天空,注视着那一颗颗神秘莫测的星星。星星多得无法计数,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直到我眩晕。眨一下眼,它们立刻都消失了。是的,你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星星,我知道,我看到的都是几百万光年前的幻影,至于它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说不上来。以前,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包括那些曾经的我们、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是一些怀着梦想,扇动着破烂的翅膀妄想飞到云端的**,是一些特别的人。今夜,我不这样想了,我们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几个,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决定按班步就落入俗套。继续做回我的恶俗小人。
所幸,我们的朴树还在为一些理想歌唱。我谢谢他。
稿子是我在办报纸时写的,我曾把它刊登上去,后来转载在校报上,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朴树,希望在能坚持的时候坚持住自己的一些理想,哪怕是愤怒青春时的尾巴。
走在都市丛林中的行吟歌手
两千年央视春节联欢会上,一个长发的大男孩在台上忧郁地唱着:“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要相爱用尽这一生------”俄罗斯式的小民谣里,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让人们记
住了歌手的名字——朴树。
其实,加入麦田的朴树早与1997年底便开始录制首张个人专辑,但在98年底,他决定废弃已制作完毕的作品,彻底否定以往的音乐与编配。在重新的编配与制作过程中,仆树的格外兢业也使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喜欢的表达方式,并如自己所愿做成了不沾任何潮流产物的纯洁的声音。首张专辑《我去两千年》推出后,被称为“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人们一直期待的城市感与时尚感终于有了一个样板的专辑”。
朴树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用歌声方式表达出年轻一代告别昨日的心情乃对新时代的憧憬。他所创造出来的美好,只有在音乐和歌词里才能体会。在这张风格并不完全同意的专辑中,既有代表朴树民谣根底与新音色向往的《召唤》和《旅途》,又有硬式摇滚的电子化身的《妈妈我……》和《活着》;既有《白桦林》那样抒情的俄罗斯情歌,也有《NEW BOY》这样的新浪潮作品……但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那首用轻快的电子琴舞曲包装着的《NEW BOY》挥洒的只是青春和欢乐的话,那么就错了,揭开这首歌的阳光外衣,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真正的朴树:真挚率直、朴素自然、才气四溢,内心深处的迷惘、无法回避的枯涩以及带有一些对悲愤的、现实的嘲讽。我们还能在《别,千万别》、《活着》这几首歌里读出朴树的尴尬与无奈,在现实都市的精神困境中的挣扎,在沉湎与过去时的“艰难而感动,幸福并且疼痛”。还有多少在城市中感慨徘回不知未来的大学生在《那些花儿》雨尘无邪的笑生和朴树忧伤的嗓音中追忆一幕幕已去的年少,不眠的夜晚,挥霍的张扬和曾经的爱恋。在这首朴树情感流畅最彻底的作品里,他几乎用无歌词的哼唱替代了多年积压在心底的种种忧伤,让我们读出朴树和自己敏感的内心以及那些苍白的感伤……
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跟朴树的经历和性格有关。朴树自小便在北大静静长大,少年时开始接触吉它。当他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便固执地认为唯有音乐可以让他自由表达。为此,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书的他退了学,而且他还认真地认为爱是一件需要负责的事,自己却没有心理准备去为一个人承担责任让她辛福,最终朴树和女友分了手。从此,他开始远离人群默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音乐的感知的世界里,感觉、思考,并沉淀,如土钢筋水泥的都市森林里一棵守望着青春的清新的树。
朴树身上交汇着对往昔的怀恋,对显示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的抗拒。他认为无奈的现实会渐渐磨去自己对理想的执着,可是为了坚持理想又不得不努力地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朴树难得的可爱和真诚就在与:在他忧郁的牢狱中,羁押着的一众囚人总会适时暴动,砸毁心窗,开怀蹦跳。
自然,作为新生代的歌手,朴树的不足也显而易见:歌词的不整齐和字句间的韵律还值得仔细推敲,而且由于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学习,在录音棚里的一些换气在卡带里也可以轻易捕捉到。所幸朴树的作曲风格实在异于常人,这稍微弥补了一些缺憾。但从词中某些段落少了的厚重和踏实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出朴树掩饰不住的慌张,对现实、未来的慌张。或许是简单的经历让朴树更多地停留在幻想与憧憬之中。
还好,我们的朴树还在成长,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天才原创音乐人,只要他对音乐心灵至一,感情至上,只要他敏锐地整顿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对于朴树和他四月的新专辑,我们的等待只揭示一个事实:美好而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