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集解序翻译培训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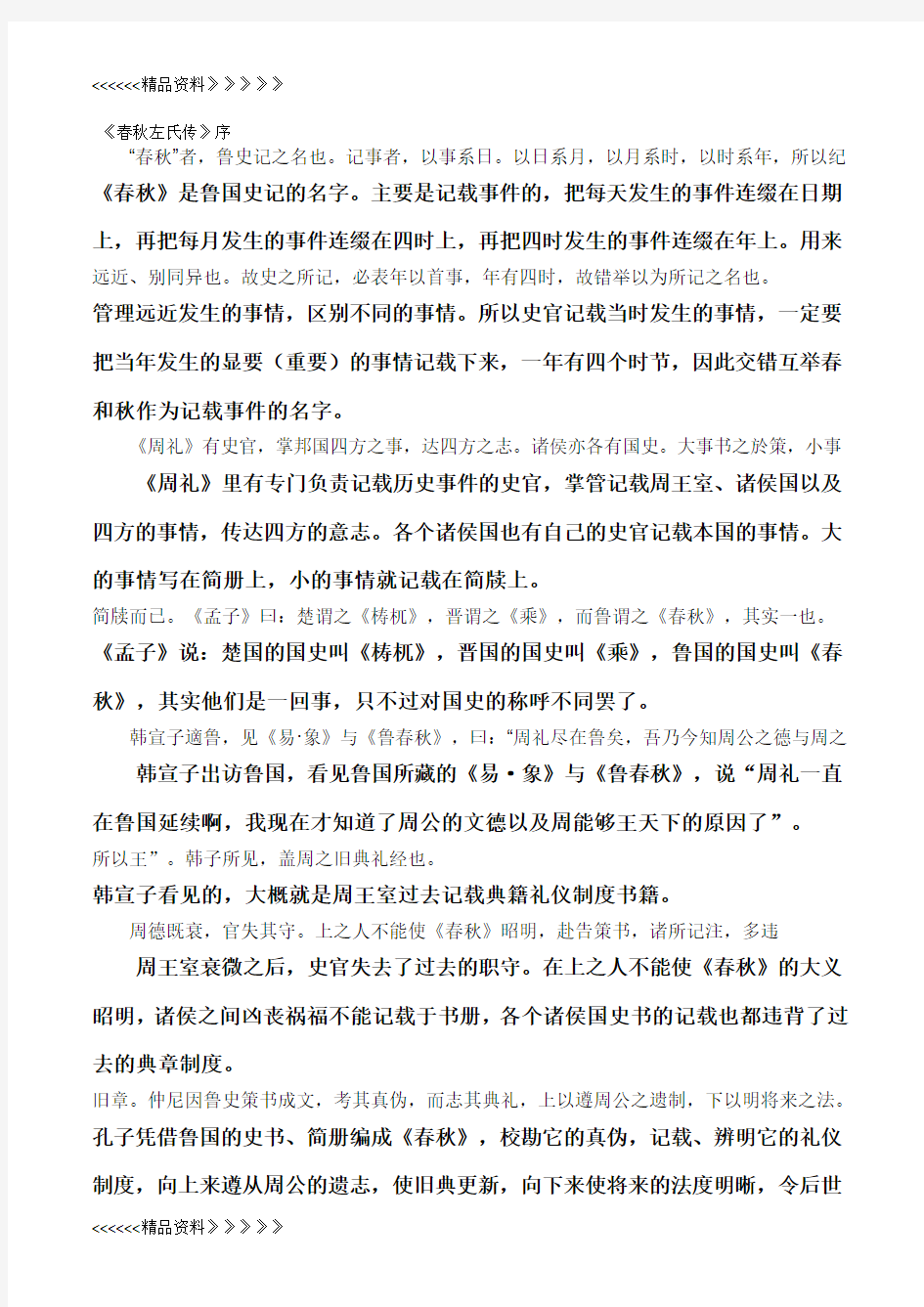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字。主要是记载事件的,把每天发生的事件连缀在日期上,再把每月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四时上,再把四时发生的事件连缀在年上。用来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管理远近发生的事情,区别不同的事情。所以史官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一定要把当年发生的显要(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一年有四个时节,因此交错互举春和秋作为记载事件的名字。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於策,小事《周礼》里有专门负责记载历史事件的史官,掌管记载周王室、诸侯国以及四方的事情,传达四方的意志。各个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记载本国的事情。大的事情写在简册上,小的事情就记载在简牍上。
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说:楚国的国史叫《梼杌》,晋国的国史叫《乘》,鲁国的国史叫《春秋》,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只不过对国史的称呼不同罢了。
韩宣子適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韩宣子出访鲁国,看见鲁国所藏的《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一直在鲁国延续啊,我现在才知道了周公的文德以及周能够王天下的原因了”。
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韩宣子看见的,大概就是周王室过去记载典籍礼仪制度书籍。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
周王室衰微之后,史官失去了过去的职守。在上之人不能使《春秋》的大义昭明,诸侯之间凶丧祸福不能记载于书册,各个诸侯国史书的记载也都违背了过去的典章制度。
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孔子凭借鲁国的史书、简册编成《春秋》,校勘它的真伪,记载、辨明它的礼仪制度,向上来遵从周公的遗志,使旧典更新,向下来使将来的法度明晰,令后世
有规范的行为准则。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
他施行教化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字的更改来达到褒贬劝诫的目的。其他地方就沿用原来的旧史,旧史文章有的富有文采有的质朴,言辞也有详有略,
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所以不必改动。所以《左传》说:“他的志向是善良的。”又说:“不是圣人谁又能修订《春秋》呢?”大概周公的志向,孔子不过是遵从然后使他昌明罢了。
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
左丘明学习的《春秋》是孔子传下来的,他认为经书是不能更改的文字,所以他写作《左传》或者是在经文的开始之前就叙述事件,或者是在经文后面再叙述事件来结束经文的大义,或者是依托经书来辨别道理,
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
或者是采取和经文不同的叙述来表达相同或相异的道理,随着经文的大义而书写传文。他重视体例,之前的典籍旧史,没有全数列举,这是因为这些史事并非圣人修订经书所看重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了记载的典籍,一定广泛的记载详细的言说。他的文章迂缓,他的意旨深远,想要让学者探求事物发展的起源和结果,寻求历史事件的细微末节,探究尽事件的结果。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传文文义宽松,使读者自己去探求他的深意;文义饱满,让读者自己去探寻满意的答案。就像江海雨泽浸润大地,冰雪自然溶解流散一样自然,这样之后才会有然后为得也。
自己的心得体会。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
《春秋》的要旨或体例都是国史修订的常制,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史书旧日
就有的章法。孔子遵从并且修订了它,使它成为《春秋》通行的体例。
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
左丘明通过左传传文来显露阐述经文中那些幽微的事情,表达他的大义之类都是依据已有的先例来阐发大义,指出这些人行事的正确与否。那些称为“书”、“不书”
“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文章,都是用来启发新旧文章,来表达大义的,这些叫做“变例”。然而也有史书不写,
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
但符合孔子大义的,孔子就据此阐发自己的大义,这些大概就是《春秋》新的大义,因此传文不称这些为“凡例”,就是要委婉的通达经文的大义。还有一些经文传没有阐述相关的大义,只是通过事情来叙述
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那么传文也直接叙述它,这些不是春秋通行的法则。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
传文的体例有三种,为经文作传的情况有五种。第一种情况是“辞微而义显”,文字在这里显现,但是大义却在那里。像“称族,尊君命”;
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
“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这类的就是。第二种情况是“用精微的语言来记录史事”,用简约的语言来说明制度,推及到其他方面来知道叙述的体例。“参”就是这种情况。
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
第三种情况是“言辞委婉,写成文章”,用委婉的言辞来表达大义,来使文意通顺。各类避讳,郑国用玉璧交换许田就是这类情况。第四种情况是“直言而不委婉”
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直接书写史事,全部显现文章的意思。楹联用朱漆染红,宫庙上的装饰桷进行了雕刻,周天子向诸侯要车,齐侯来报告对戎人的大捷,就是这类情况。第五种情况是“惩治恶行勉励善行”,求名而死,
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欲盖弥彰。把齐豹称为“盗”,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名叛贼就是这类情况。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推究这五种体例,来探寻经传的大义,就可以依据一类事物的知识或规律,而增长同类事物知识或规律。将这些大义附于春秋二百四十年的事情之上,王道的正法,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有人说:《春秋》通过不同的文字来表达大义。如果如你所说,那么经文当有事情相同文字不同大义也就不存在的情况。然而先儒所传,都不是这样。
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答曰:《春秋》虽然通过一个字来寄寓作者的褒贬态度,然而也需要通过几句话来成文,不同八卦的爻辞,可以交错综合成六十四卦,
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本来就需要通过传文来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多了,现在可以看见的遗留下的文字就有十几家。大体上都是效法遵循前人的学说,
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进不能成为结合经传之文来穷尽它的变化,退不能固守左丘明的传文。对于左丘明的传文,有不能解释通的地方就隐藏不说,甚至还有肤浅的引述
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公羊》、《谷梁》,正好混乱自己。杜预现在所以和那些通过《公羊》《谷梁》来解释《春秋》的人不同的原因,就是要专门修治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体系,一定来自于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