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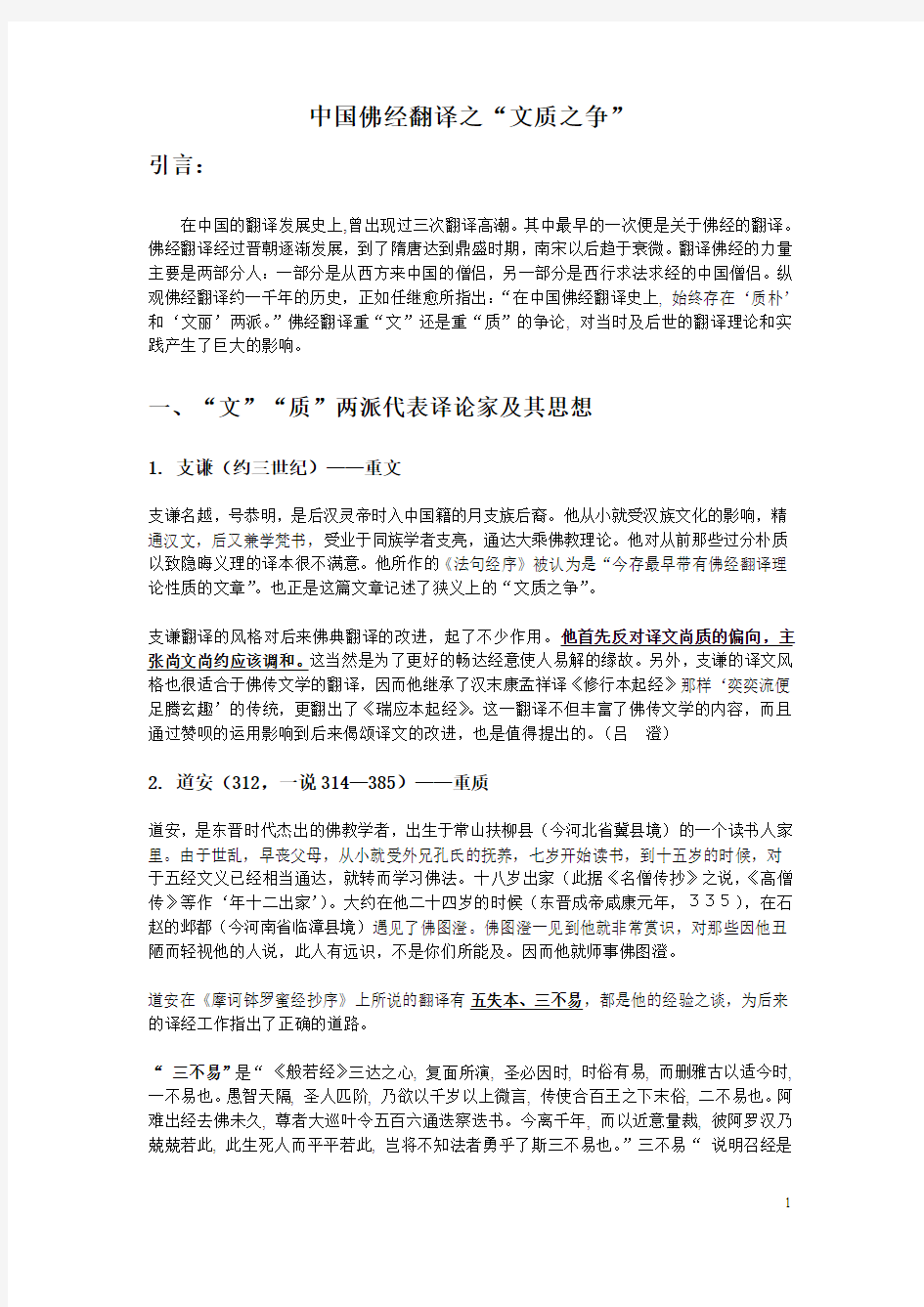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
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三不易”是“《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说明召经是
佛因时而说的, 古今时俗不同, 要使古俗适应今时, 不易做到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 更不易做到, 佛经法集时, 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相互审查校写, 如今去古久远, 无从征询,又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更是极难的事,故译人应该注意译经经文艰辛, 尽可能忠于译事。同时, 译经既有此诸多不易, 故在“案本而传”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适当变通。其变通规则即为“五失本”、“一者胡语尽例, 而使从秦, 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 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己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己乃后说, 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五失本”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是语法上的问题。梵语名词、代词、形容词等有三性, 三教, 八格的分别。动词有六时辞法、语气的分别, 语尾的变化也很繁杂。在句法上每一个词的位置也与汉文不同, 如果按梵本对翻、硬译, 而不回辍文字, 则读起来不但不顺, 不象汉语, 甚至也读不懂, 故知此“本”不失, 便不成翻译。第二是文与质的问题,虽然道安力主直译, 忠实审慎。但梵语的习质毕竟不同于汉文, 倘完全直译, 不加文饰, 就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故道安还是相当注重文饰, 不过是直译基础上的文饰。于是, 在五失本中定下了一条作为当时译经的通行规则。而且从当时译《婆须蜜经办赵正担任润文开始, 译场就聘有润文的专家。可见, 当时直译派也不是完全排斥修辞的。第三是译文的削繁删冗, 求简明易了, 包括“五失本”的最后三条。第三失本是指梵本的褐颂有许多重复的句子, 在印度人读来, 反复咏叹, 更能增加其韵文的华美和意味的深长, 但是译为汉文, 不仅失去了原来的音节之美, 而且显得语意重复, 不合中国人的口味。因此需要削除。第四失本是指梵本时常有解释的词句夹杂在正文里, 与正文内容相混淆, 使读音难以分辨, 因此也需要删去。第五失本是指梵本在叙述一事完了将过渡到别一事时往往将这事再重复一遍。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完全不必要的, 因此便允许译者把它省略。总之, 翻译时遇到这五种情况, 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情况的存在, 实际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道安的“三不易”, “五失本”理论精当中肯, 对当时以及后世的译经事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钱钟书曾称其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之篇。
道安不仅提出了翻译史上“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学说,而且较之支谦更多更系统地引用文质概念论述佛经翻译问题。道安主张质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佛经翻译初期,语言上的障碍大,道安本人不懂梵文,对佛教教义不甚了了。出于对教义的虔诚,不敢轻易,所以难免拘泥于原文。(2)初期参加译经的僧人本身文学造诣不太高,主要靠佛性的理解进行翻译,语言上不甚讲究,况且佛经流传范围主要限于僧人,只求通晓大意。(3)不懂得华文和梵文各有其文与质,较多地强调梵文的质朴和华文的文饰,故而形成质派的基本主张。
3. 慧远(334—416)——文质并重(厥中论)
慧远,本姓贾氏,晋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崞县东部)人。他从小好学,十三岁(346)就随从他的舅父游学洛阳,习儒家典籍,及老、庄之学。慧远继承其师道安的遗志,热忱弘法。他初事道安,即以建立教法宏纲为己任,以后他更推广此意,欲根据教法移风易俗。(游侠)
从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在翻译文体的问题上,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即由直译趋向于意译。道安主张直译,鸠摩罗什倾向意译,慧远融合了这两家的主张,提出“厥中”论。他的佛经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明的邻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编辑]绪论 佛经翻译事业始于东汉,至前秦苻坚始有组织的翻译佛经,由道安组织翻译事业,唐朝时,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誉为「四大译师」。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1],另有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贵霜佛教僧人支谦,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间将36部佛经翻译成中文。道安译经时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学者,则不从事译书。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如罗什之于《般若》、《三论》,真谛之于《唯识》,玄奘之于性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 佛经的翻译可分为三个时期: [编辑]东汉至西晋 东汉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西汉的哀帝时期伊存至中国口传佛经。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 [编辑]东晋至南北朝 此一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主。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经典的贡献巨大。罗什于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凡384卷,有《坐禅三昧经》3巻、《阿弥陀经》1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4巻、《法华经》7巻、《维摩经》3巻、《大智度论》100巻、《中论》4巻等。去看看佛经网站,https://www.360docs.net/doc/e96465052.html,上面什么都有 [编辑]隋至唐中叶 此一时期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在长安设立了国立翻译院,参与的学生与人员来自亚洲东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时间在今西安北部约150公里的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1330卷经文译成汉语。其后则有义净、不空等。 宋元以降再无大规模佛经翻译事业,虽偶有译者,不过补苴而已。
中国翻译史1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Plan Teaching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2.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ountri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istory 中国翻译史的大致分期 1.由汉代到唐宋的上千年的佛经翻译【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谢灵运、真谛、彦琮、慧远、玄奘、不空】 2.明清交替之际的科技翻译【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熊三拔、李之藻等】 3.清末民初的文学和科技翻译【李善兰、华蘅芳、傅兰雅、林纾、严复、梁启超等】 4. 民国时期的翻译【赵元任、朱生豪、林语堂】 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傅雷、钱钟书、杨绛】 Lecture 1 佛经翻译 I.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 《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翻译的不同称呼:“象寄”、“象胥”、“鞮译”“舌人” 寄send; entrust; rely on 象be like; resemble; image 译translate; interpret 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 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人歌》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秦汉时期对“翻译官”的种种称谓: “行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典乐”、“译官令”、“译官丞”等。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II.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公元前六至五世纪 创立地点:古印度 佛教流传:公元65年之前传入中国 我国的佛经翻译
【曾素英】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第20卷 第4期 2007年8月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Vol.20 No.4August 2007 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曾素英 (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收稿日期:2007205210 作者简介:曾素英(1979-),女,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要: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关键词:佛经翻译;倾向;直译;意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4-0556-03 佛经翻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佛经翻译是由梵语译入汉语,译作种类繁多,其间翻译大师辈出,如汉桓帝时的安世高、三国时的支谦、晋代 的道安、符秦时代的鸠摩罗什、隋朝的彦琮和唐朝 的玄奘等。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质”与“文”作为 衡量译文的标准。“文”与“辞采”,即修饰译文,使 之通达;“质”指“朴质”,即紧扣原文,不增不减。“文”与“质”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译”与 “直译”[1]。自东汉至唐宋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史 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下面将从什么是直译和 意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起,进而阐述两种译 法在几大译师译文中的应用与体现。 一、“直译”与“意译”的含义与关系何谓“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在我国古代,论述译经之道的人并没有提出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因此,在我国佛经翻译中存在的这两种倾向,将之称为直译和意译,还不如遵从当时的习惯说法,称之为强调“质直”和强调“文饰”的两种倾向更合适一些。把翻译中这两种方法称之为直译和意译大概始于清末明初。茅盾1934年在《直译、顺译、歪译》一文中曾经说:“直译这个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1980年茅盾在《〈矛盾译文选集〉序》中又一次谈到这件事:“‘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用白话文翻译……‘直译’这名词,就是在那时兴起的。” [2] 茅盾在《直译与死译》一文中说:“直译的意义 若就浅处说,只是‘不改变原文的字句’;就深处 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和风格’。”[2] 他又说:“我以为所谓直译也者,倒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 ”[2]而朱光潜的观点却有很大不同,有点像“逐字翻译”:“所谓直译是指依原文的字面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更动。”[2] 关于意译,朱先生如是说:“所谓意译是指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完全依原文的字面和次 第。”[2] 也许到目前为止,对直译和意译的最佳界定莫过于许渊冲先生,他说:“直译是把忠于原文 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 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 是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 文形式的翻译方法。”[3]61不难看出,两者只是大 同小异,都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是忠于原文的形式还是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译和意译的关系是什么?首先,直译和意译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种翻译方法。在一切翻译活动中,直译和意译尽管方法不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和所要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其二,直译和意译是在传译活动中兼用的两种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方法的出现和相互关系
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_吕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5年7月Jul. 2005 第16卷第3期VOL.16 NO.3 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呼声也与日俱增。实际上我们有两个理论资源:一方面是大量国外翻译理论的引入,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另一方面则是对我国古典翻译理论尤其是佛经译论的重新研究,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做到卓有成效,翻译学科才能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就指出:“我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已有相当精辟的见解,倘能用现代学理,发掘出新,当能发幽显微,推陈出新[1]。”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要回到中国传统译论的源头,进行佛经翻译理论的探源和清理工作。佛经翻译理论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和基础,其中的文质之争,一方面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另一方 论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与质 吕 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内容提要:文质之论起源于中国古典的人论、文论,作为翻译理论贯穿于整个佛经翻译过程。就本质而言,文与质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了后来经过翻译移入中国的直译与意译概念。文质之论不但与翻译方法有关,而且关系到翻译所涉语言、文本风格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论,使其区别于今天的直译意译之争,对于澄清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与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对于加深翻译的本质认识,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之论;传统译论;直译意译;现代译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05)03-0023-04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W en (literary) and Zhi (qualitative) were derived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heories in Humanity and Writing. As a part of translation theory, Wen and Zhi, go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uddhist Sutra, are totally d ifferent from both literal and liberal western translation terms. T hey are concerned with transl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aspects such as language and writing style.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ove that Wen and Z hi are typical C hinese concepts, which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from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I t tries to clarify some basic concep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 heory, which has both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 concepts of Wen and Zhi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literal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 :2005-03-28 作者简介:吕洁,女 (197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英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文 化与交际。 面也涉及古典人论、文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在翻译领域内有一种倾向,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概念上经常把文质问题混同于直译和意译问题。本文认为,为了恢复中国传统译论的原貌,从而准确而有效地加以继承,必须首先正本清源,进行必要的理论清理,然后再使文质与直译意译问题互相阐发,才会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准备条件。 一、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概念的理论基础 和最初表述形态 佛经翻译既是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广义的文学翻译。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来源是文艺学和美学。例如,王克非先生认为:“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2]。”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e96465052.html,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作者:桑吉扎西 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1期 摘要: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被人誉为“千年译经”,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经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以及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及其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进行了以下简要分析,旨在增加人们对于佛经翻译与译经的了解程度,以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古代;佛经翻译;佛经译经;翻译理论;影响 前言: 佛经翻译是以佛经本为载体,通过对佛经本中的经文内容翻译,以达到传播佛经理念,福音惠及更多群众,以争取更多信仰佛经之人皈依佛门。佛经译经的方式无意识中促进了中国古代翻译学的兴起。中国历史上最早流传的翻译作品为战国时期的《越女求爱歌》,指最早被记载在册的翻译作品,但是,真正见过的人甚少,因此,《越女求爱歌》仅流于传说之中。 1佛经翻译 相关学者将中国翻译史总结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两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属于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展开了对佛经翻译的热潮;其二,为明末清初,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外国很多作品开始流入中国古代,并且当时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开始了对《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几何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类书籍,自此开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书籍的翻译,并且掀起了影响不小的翻译热潮;“五四运动”前后属于中国翻译的 第三次高潮,翻译的主要内容为文史哲理等方面,涉及到的范围更加广泛。而第四次高潮,而是近现代的翻译高潮被学者归纳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以及多元文化的流入,为佛经翻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可谓是如火如荼,不仅是名著文学著作的翻译,还有相关资源内容的翻译,不仅为中国翻譯理论的完善起到了推进作用,更加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往来以及文化互通。无论从哪个时代开始划分,将翻译分为几个不同的高潮发展时期,佛经翻译就是三千年以来中国翻译历史的起源,起到引导与基石的重要作用,对于我国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翻译技巧的发展史是螺旋状向前渐进的,每一次的新策略新方法都是在前面翻译实践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中国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格义”“合本子注”再到“五失本三 不易”和“五不翻”对不可译死角的探索与对策,引导了后来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 出。中国翻译理论与技巧的探索呈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形上升趋势,在发展中逐渐成熟起来。王克非说中国佛经翻译经历“由幼稚的直译而至幼稚的意译,又由成熟的直译而至较成熟的意译,终至二者兼得的发展模式”。任东升认为早期的佛经翻译阶段演进情况是沿着“逐字式直译———追求文雅———信达并举三段式”。目前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译者、译著、译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
中国翻译史笔记
中国翻译史 袁素平 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 中国文化的特色:从未中断过。 巴比伦灭了 印度,埃及曾经沦为殖民地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季羡林:“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永保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 中华文化的源头: 易经the art of changes Confucius 孔子 Mencius 孟子 Confucianism 儒家文化 太极生两仪include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西方之水: 第一次高峰:从明朝末年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最终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潮。清朝末年其实是引起了中华文化的后退。 梁启超: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掀开了翻译政治小说之幕,林纾翻译文艺小说。 第二次高峰:以1919年为界,掀起第二次高峰 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其一半的活动是和翻译相关的。 第三次高峰: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近现代出不了大家。 中西文化之别: 中国重智即动头脑的能力 外国重用即动手实践能力 因此要:手脑联盟
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2.明末清初,欧洲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3,4之间是断档的历史)4.改革开放至今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1.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 而不野”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2.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促使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3.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踏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体裁,以及用音 译取代前期的音译。(复译,重译等) 4.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由此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北魏孝文帝:促进中华文化的融合 千古一后:冯太后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 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三不易”是“《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说明召经是佛因时而说的, 古今时俗不同, 要使古俗适应今时, 不易做到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 更不易做到, 佛经法集时, 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相互审查校写, 如今去古久远, 无从征询,又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更是极难的事,故译人应该注意译经经文艰辛, 尽可能忠于译事。同时, 译经既有此诸多不易, 故在“案本而传”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适当变通。其变通规则即为“五失本”、“一者胡语尽例, 而使从秦, 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 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己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己乃后说, 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五失本”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
佛经翻译中的_文质之争_
第10卷第4期2010年4月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Vol .10,№4Ap ril,2010 收稿日期:2010-01-28 作者简介:刘笑千(1984-),女,河南郑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刘笑千 (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郑州450002) 摘要:“文质之争”是沿着一条“由质到文”的道路发展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研究其历史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翻译与世界接轨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佛经翻译;文;质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0)04-0101-02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 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1〕18-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文质之争(一)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这场争论,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224年”〔2〕175 。后来,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这 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3〕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最先出现的是“质”派,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 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4〕283 。梁皎慧《高僧传》评 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145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复、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 意义不够清楚”〔4〕283 。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公元189年),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 存文饰”〔1〕23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约230~308年),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事 事周密耳”,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31 。 释道安(314~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 “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6〕9 。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 自来矣。为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6〕12 。 继“质”派之后,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其代表人物有支谦、鸠摩罗什。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生于中国。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 质的文章”〔6〕6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于是,任继愈说:“这场争论,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实际的 结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2〕175 。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词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 (一 )时间范围 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 (约 230~308年 )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译经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广。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悉则悉矣 ,而辞质胜文也” ,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耳” ,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释道安 (314~385年 )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 ,多嫌胡言方质 ,而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也。何者 ? 传胡为秦 ,以不闲方言 ,求识辞趣耳 ,何嫌文质 ? 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为传事不尽 ,乃译人之咎耳”。 继“质”派之后 ,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 ,其代表人物有支谦、
古代佛经翻译看译者的主体间性
摘要:人们一直认为我国传统翻译中过多地强调了“意译”,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采用“归化”而非“异化”的方法并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翻译活动中建立起来包括原作者、译者、读者、监督者以及出版者等在内的主体间性关系。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更多地关注到这样的主体间性,翻译的质量和效果就会更好。 关键词:佛经;翻译;主体间性;归化;异化 一、引言 不论是在哲学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关于主体性的讨论早已成为过时的话题。但这一概念在翻译研究中仍然会引起诸多的争论。特别是近几年来,学者们对翻译中主体性的讨论更是热烈。通过讨论和争鸣,有学者认为“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1],有学者认为翻译的主体应包括作家、翻译家和读者[2],还有学者认为,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等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3]。然而,不论争论的分歧多大,对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作用似乎都给予了充分的认同,同时对传统译论中过分渲染的“意译”、“归化”都给予了一致的批评。本文拟从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史实,探讨佛经翻译中对翻译主体作用的认识,进而说明译者的主体地位以及与其他主体间性的关系在我国古代译经活动中就已经确立,并成为衡量译经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概述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主要是指东汉恒帝时期(公元148年)至宋朝初期(公元988年)的佛经翻译活动。由兴起到鼎盛再到衰退历时800多年。一般认为,公元2世纪来到中国的伊朗僧人安世高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其一生译经34部,40余卷。此后,从事佛经翻译的有名大师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等。这五位译师中有四位是外籍僧人,只有玄奘是汉人。鸠摩罗什(公元343年)祖籍印度,东晋时来到中国,在甘肃居住17年,后在58岁时到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一生译经35部,300多卷,“他首次将印度佛学经典按照原本直接介绍进中土,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复兴和隋唐时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16。印度僧人真谛于公元546年应邀来中国弘扬佛法,在中国一呆就是23年,译经共38部,118卷。唐代名僧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亲去印度取经,历经17年回到长安,随后献身译经事业近20年,共译经75部,1335卷。不空大师生在印度(公元705年),幼年随舅父来到中国,一生译经110部,共143卷。中国佛学翻译史研究中,都选择这五位大师作为代表人物,这不仅因为是他们的译经水平高,更因为他们的译经分别代表了几个主要的佛学宗派。 从佛经翻译的影响程度看,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经活动被公认为影响最大,不仅是他们各自的译经数量在当时居领先地位,而且他们的译经质量也都堪称一流。这里说的质量标准莫过于“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或“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批玩”或“善批文意,妙显经心”(唐·释道宣《续高僧传》)。 从翻译方法看,五位大师采用的翻译方法各有不同。安世高和鸠摩罗什均是来中国后学习汉语的,并很快通晓汉语。但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安世高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力求保存经典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则采用了达意的译法(即意译法),对佛旨经义进行弘扬和阐发,“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又不失“天然西域之语趣”。真谛是应邀来华传经,起初不识汉语,译经时要配有专门的“传语”,然后再由“笔受”记录整理成文。60岁以后,真谛才“渐善解华言,不须传译”了。因此,他的译经多采用直译的方式,文字难免有“艰涩”的地方,但他主要是以讲解经义为主要目的,因而译文多少带了些他自己的见解。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译经又带着意译的烙印。唐代名僧玄奘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29岁赴印度学习梵文经典,46岁取经回国。他不仅通晓梵文,更深得佛学经义的要旨,可谓是“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因此,在翻译佛典时能“出语成章”、“览文如己,转备犹响”(唐·释道宣《续高僧传》)。不空大师虽为印度人,但他幼年时就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精通梵汉语文,译文通俗易懂,“所翻经论,皆洞精微”。比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在真谛大师手上被译为《仁王般若经》,不空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