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散文中的“文化抗战”思想探析
浅谈张承志前期小说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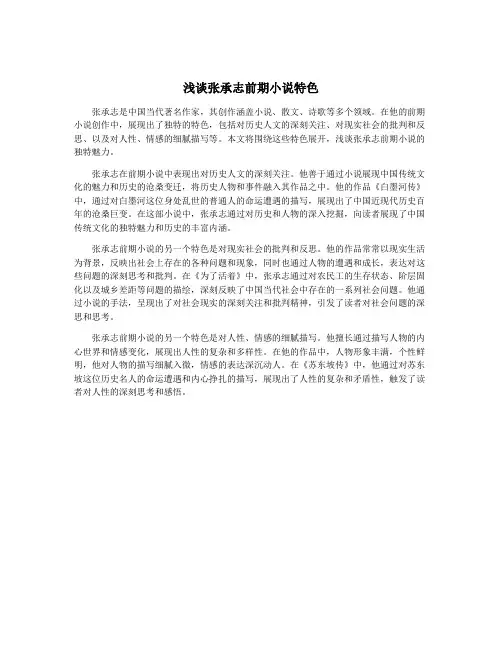
浅谈张承志前期小说特色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其创作涵盖小说、散文、诗歌等多个领域。
在他的前期小说创作中,展现出了独特的特色,包括对历史人文的深刻关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对人性、情感的细腻描写等。
本文将围绕这些特色展开,浅谈张承志前期小说的独特魅力。
张承志在前期小说中表现出对历史人文的深刻关注。
他善于通过小说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历史的沧桑变迁,将历史人物和事件融入其作品之中。
他的作品《白墨河传》中,通过对白墨河这位身处乱世的普通人的命运遭遇的描写,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百年的沧桑巨变。
在这部小说中,张承志通过对历史和人物的深入挖掘,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历史的丰富内涵。
张承志前期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思。
他的作品常常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反映出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同时也通过人物的遭遇和成长,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批判。
在《为了活着》中,张承志通过对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阶层固化以及城乡差距等问题的描绘,深刻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他通过小说的手法,呈现出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和批判精神,引发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深思和思考。
张承志前期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对人性、情感的细腻描写。
他擅长通过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他对人物的描写细腻入微,情感的表达深沉动人。
在《苏东坡传》中,他通过对苏东坡这位历史名人的命运遭遇和内心挣扎的描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性,触发了读者对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张承志论文:论张承志作品中的苦难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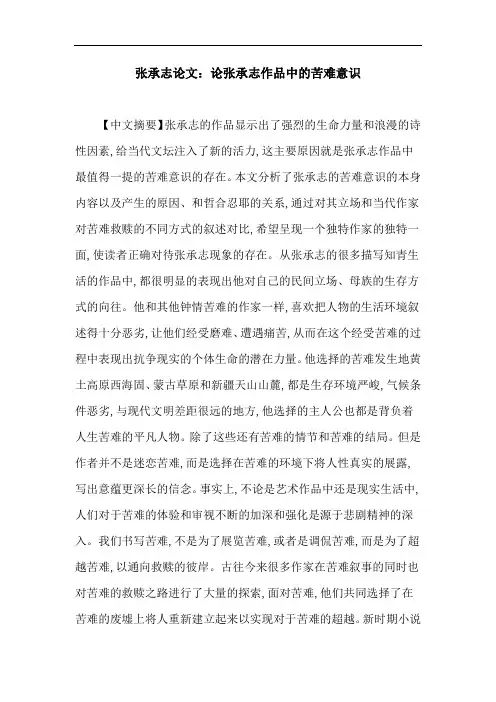
张承志论文:论张承志作品中的苦难意识【中文摘要】张承志的作品显示出了强烈的生命力量和浪漫的诗性因素,给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主要原因就是张承志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苦难意识的存在。
本文分析了张承志的苦难意识的本身内容以及产生的原因、和哲合忍耶的关系,通过对其立场和当代作家对苦难救赎的不同方式的叙述对比,希望呈现一个独特作家的独特一面,使读者正确对待张承志现象的存在。
从张承志的很多描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中,都很明显的表现出他对自己的民间立场、母族的生存方式的向往。
他和其他钟情苦难的作家一样,喜欢把人物的生活环境叙述得十分恶劣,让他们经受磨难、遭遇痛苦,从而在这个经受苦难的过程中表现出抗争现实的个体生命的潜在力量。
他选择的苦难发生地黄土高原西海固、蒙古草原和新疆天山山麓,都是生存环境严峻,气候条件恶劣,与现代文明差距很远的地方,他选择的主人公也都是背负着人生苦难的平凡人物。
除了这些还有苦难的情节和苦难的结局。
但是作者并不是迷恋苦难,而是选择在苦难的环境下将人性真实的展露,写出意蕴更深长的信念。
事实上,不论是艺术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苦难的体验和审视不断的加深和强化是源于悲剧精神的深入。
我们书写苦难,不是为了展览苦难,或者是调侃苦难,而是为了超越苦难,以通向救赎的彼岸。
古往今来很多作家在苦难叙事的同时也对苦难的救赎之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面对苦难,他们共同选择了在苦难的废墟上将人重新建立起来以实现对于苦难的超越。
新时期小说对于“苦难”的叙述大概分为三种救赎路径:一种是忍耐苦难的态度,还有悲剧英雄人物的反抗,也有张承志这种为代表的在宗教中寻找解脱的方式。
希望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接受张承志的警醒,将苦难意识牢记,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不平坦,寻找更高的价值追求,建筑人类真正的精神家园,这就是张承志作品中苦难意识寻在的现实意义所在,我们不必追究他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是否有合理性,当我们接受他特殊的存在时,就会看到一个自由境界的领域又高扬了一面灿烂的旗帜。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判之五十二:张承志的孤傲与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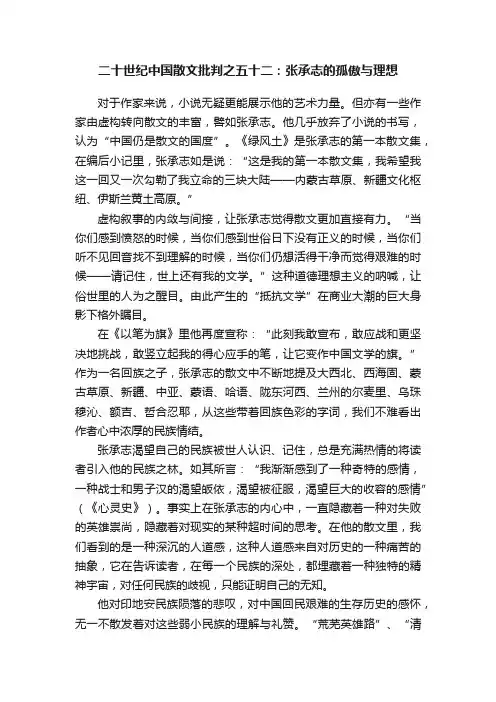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判之五十二:张承志的孤傲与理想对于作家来说,小说无疑更能展示他的艺术力量。
但亦有一些作家由虚构转向散文的丰富,譬如张承志。
他几乎放弃了小说的书写,认为“中国仍是散文的国度”。
《绿风土》是张承志的第一本散文集,在编后小记里,张承志如是说:“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我希望我这一回又一次勾勒了我立命的三块大陆——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
”虚构叙事的内敛与间接,让张承志觉得散文更加直接有力。
“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
”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呐喊,让俗世里的人为之醒目。
由此产生的“抵抗文学”在商业大潮的巨大身影下格外瞩目。
在《以笔为旗》里他再度宣称:“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
”作为一名回族之子,张承志的散文中不断地提及大西北、西海固、蒙古草原、新疆、中亚、蒙语、哈语、陇东河西、兰州的尔麦里、乌珠穆沁、额吉、哲合忍耶,从这些带着回族色彩的字词,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心中浓厚的民族情结。
张承志渴望自己的民族被世人认识、记住,总是充满热情的将读者引入他的民族之林。
如其所言:“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和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心灵史》)。
事实上在张承志的内心中,一直隐藏着一种对失败的英雄祟尚,隐藏着对现实的某种超时间的思考。
在他的散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沉的人道感,这种人道感来自对历史的一种痛苦的抽象,它在告诉读者,在每一个民族的深处,都埋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宇宙,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
他对印地安民族陨落的悲叹,对中国回民艰难的生存历史的感怀,无一不散发着对这些弱小民族的理解与礼赞。
“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鲜花的废墟”、“匈奴的谶歌”,字里行间透散出作者孤绝的行走。
论张承志小说中的民族文化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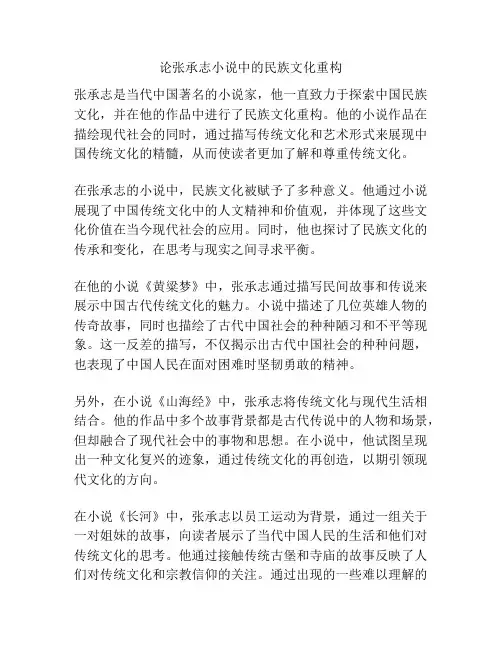
论张承志小说中的民族文化重构张承志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小说家,他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民族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进行了民族文化重构。
他的小说作品在描绘现代社会的同时,通过描写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使读者更加了解和尊重传统文化。
在张承志的小说中,民族文化被赋予了多种意义。
他通过小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并体现了这些文化价值在当今现代社会的应用。
同时,他也探讨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变化,在思考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在他的小说《黄粱梦》中,张承志通过描写民间故事和传说来展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魅力。
小说中描述了几位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同时也描绘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陋习和不平等现象。
这一反差的描写,不仅揭示出古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坚韧勇敢的精神。
另外,在小说《山海经》中,张承志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他的作品中多个故事背景都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和场景,但却融合了现代社会中的事物和思想。
在小说中,他试图呈现出一种文化复兴的迹象,通过传统文化的再创造,以期引领现代文化的方向。
在小说《长河》中,张承志以员工运动为背景,通过一组关于一对姐妹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他通过接触传统古堡和寺庙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关注。
通过出现的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来展示传统中的神秘与精神,传达了“天意”和“力量”的思想。
总之,张承志的小说在民族文化重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用小说讲述了中国人民经历的传统文化的无尽魅力,揭示现代社会中与传统文化的转型,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到现代文化中,成为了当今中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张承志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尝试通过小说来进行民族文化的重构,以期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同时也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生活中,为现代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首先,张承志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反思传统文化的态度。
论张承志的小说

论张承志的小说张承志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新时期的鲁迅”。
他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研究。
本文将围绕张承志的小说展开论述,探讨其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思想和成就。
一、张承志的小说创作特点1.反映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动景象张承志的小说关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如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分化、道德沦丧等,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景象。
例如《大明宫》就描绘了一个历史名胜古迹大明宫被摧毁的惨状,反映了现代社会建设中的历史遗忘和文化破坏。
2.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命运张承志的小说中有很多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命运,比如流浪儿童、贫民窟居民等。
他们通常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面临重重的困难。
例如《像少年花粉般飞扬》就以流浪儿童为题材,展现了这些孩子艰苦的生活和心灵世界。
3.注重深入人物心理描写张承志的小说注重深入描写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探索人性的复杂性。
通过细腻的叙述手法和真实的情感刻画,使人物形象更具有鲜明性格和感染力。
例如《冬天里的一只鹿》中的男主角阿信就是一个富有思想深度和内心挣扎的典型形象。
二、张承志小说的主要思想1.批判社会现实张承志通过小说批判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揭示出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
其作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人群的命运。
通过生动的叙述方式,直接、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的特征。
2.倡导人性反思张承志小说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倡导人性反思。
他的小说展现了许多内心挣扎、思想的深度和矛盾,表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通过人士形象塑造和情节表现,探索人性的真谛,呼吁人类关注自身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
三、张承志小说的文学成就张承志小说的创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他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在艺术上也有着不俗的成就。
例如,张承志曾获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当代优秀青年作家奖等多项荣誉,他的作品也多次被翻译成其他语言面世,受到了国际上读者的欢迎。
对话还是对抗:比较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张承志的“抗战文学”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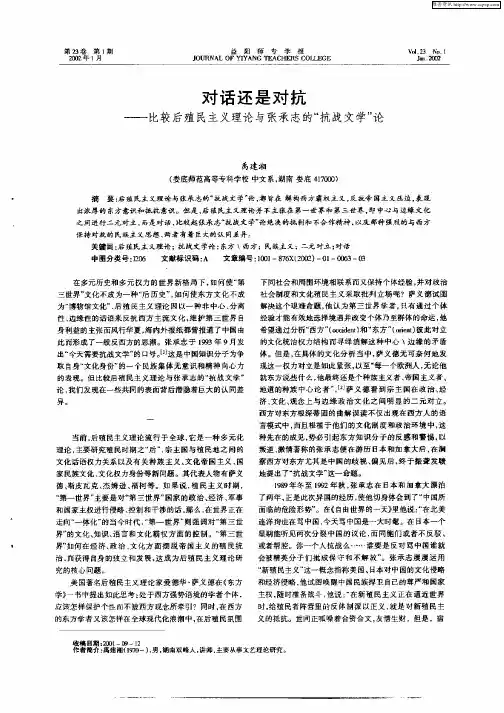
论, 我们 发现在一些 共同的表面背后潜 隐着 巨大的认 同差
异。
地道 的种族 中心 论者 L 萨义 德 看到 宗主 国在 政治 、 , 2 经 济、 文化 、 观念上 与边 缘 政 治文 化之 间明显 的二 元对 立。 西方对东方根深蒂 固的 曲解误 读不仅 出现在 西方人 的语 言模式中 , 而且 根植 于他们 的文化制 度 和政治 环境 中, 这
中国分类 号 : 0 I6 2 文 献标识 码 : A 文章编号 :01 yx(o2 一 l 03— 3 10 一s6 2o ) O 一06 0 下同社会 和周 围环境相 联系而又保 持个体经验 , 并对 政治 社会制 度和文 化殖 民主义 采取批 判立场 呢?萨义 德试 图
在多元历史和 多元权力 的世 界新格 局下 , 如何使 “ 第 三世界” 化不成为一种 “ 历史 ” 如何使 东方 文 化不成 文 后 ,
出浓厚的 东方意识和抵抗 意识 。但是 , 后殖民主义理论 并不主 张在 第一世界 和第三 世界 , 中心与边缘 文化 即
之间进行二元对立 , 而是 对话 , 比较起 张承志“ 战文学” 抗 论绝决的抵制和不旮作精神 , 以厦那种强烈的与西方
保 持对抗 的民族主义思想 , 两者有着 巨大的认 同差异: 关键词 : 后殖 民主 义理论 ;抗 战文学论 ; 东方 \西方 ;民族主义 ; 二元对 立 ; 对话
维普资讯
第 2卷 3
第 1 期
删 R N札 。
20 D 2年 1 月
孟 。肛 u
J0. . O1 a 舱 2 n 3№
对 话 还 是 对 抗
比较后殖 民主义理论 与张承志 的“ 战文 学” 抗 论
浅谈张承志文学创作思想的多元构成
他 的诗歌意境 高远 、犀利透彻 ,然而,张承 志真 正为人所称道 的,是他熔铸在作品中的独有的强 大 的思想魅力——一个具有英雄气质的先行 者对 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从 2 O世纪 7 0年代末 登上
文坛,张承志就 以强 烈的理想主义精神鲜明地区 别于当时的 “ 伤痕文学 潮流 ,理想主义贯穿了
浅谈张承 志文学创作 思想 的多元构成
于凤 芹
( 长春职业技术 学院,吉林 长春 1 3 0 0 3 3 )
摘要:张承志是学者型的少数民族作 家, 是 中国当代文学中一面独立 的旗 帜. 张承志 阅历丰富,学 识渊博 ,经历独 特。个性不羁,他的创作 思想复杂多元,主要 由热烈浪漫的理 想主 义,富于
生存压力 。……我 的微渺文学 ,不 过是三片大陆
的一杯沙土石砾 。我用一生 的履历 ,否定了寄生 强权和屈从金钱的方式。 多年来 , 他远行跋涉 , 从 内蒙古、黄土高原、新疆腹地 ,到 日本 、中亚 、 地中海 以及拉丁美洲 ,涉猎建筑学 、植物学 、蒙
伊斯 兰黄土高原是张承志整个生命 的理想依 托, 他对 。 三 大陆 的 山川、 民族充满着宗教般 的眷 恋,称颂她符合人道 的生存准则 ,仰慕 其原始强
人物 ,无论男女老幼 、善恶美丑,都透露 出平静
的作 家” 和 当代文坛少有 的学者 型作家 ” ,旷
新年更是认 为 “ 张承志是 中国文学 中一面独立的
旗 帜, 他 以一个人的存在平衡了中国文坛 。 ” 张承 志具有 独立 不羁 ,冷峻热烈的审美 品格,他 以独 自的方 式表达着他的精神哲学 ,以熔铸诗歌、音
力和 基于生存 意识的人性悲壮 ,崇 尚它 的道 德操 守和理想人格, 因此张承 志作 品中的男主人公主 要为 “ 三 大陆 ”的少数 民族人物 ,他们 在作家笔 下都具有开天辟地 的男子汉 血性和 悲壮雄浑的等众多领
从“效果历史”看张承志的历史陈述——读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
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已经是久负盛名的作家了。
他的小说《黑骏马》《心灵史》《北方的河》等,在新时期文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到了80年代末,张承志的创作由小说方向转向了散文方向,并出版了相关的散文集,如《荒芜英雄路》《一册山河》《以笔为旗》等。
然而,在近年出版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张承志以学术和散文相糅的手笔,将日本的部分人文历史画面细腻地呈现出来。
据相关文献记载,张承志从1983年5月去日本进修,于1984年6月回国。
他第二次去日本任教的时间是1990年11月,直到1993年4月重回中国。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自1983年以来,张承志曾多次赴日本求学或任教。
在2006年,张承志背起行囊又去日本,在那居留两个月,并对日本相关的历史文化作了系统的考察。
张承志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去思考日本文化,可以说,他关于日本文化的相关创作是离不开他自己的切身体验。
他对日本的那种独特的情怀,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的。
纵观张承志散文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对张承志散文的研究评论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有目光犀利,成之有理之作,但是笔者认为,张承志的散文呈现出了一种效果历史的迹象。
如1988年《午夜的鞍子》,2002年《公社的青史》,写于1993年、审定于2005年的《夏台之恋》,以及2008年写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等作品,从中都可以看到张承志对历史的陈述。
然笔者认为,张承志散文《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这部作品中对历史的陈述呈现出了一种效果历史。
因此,笔者从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来看张承志散文对历史的陈述这一层面来谈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效果历史”“效果历史”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从“效果历史”看张承志的历史陈述——读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佘丽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摘 要:在张承志看来,历史需寻求真实,历史应是心史。
从他的创作文本来看,只能说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历史。
浅谈张承志前期小说特色
浅谈张承志前期小说特色
张承志是中国当代一位著名的作家,其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戏剧等多个领域,但在其前期小说作品中,有着一些鲜明的特色。
张承志的前期小说作品中常常融入了浓厚的乡村情怀。
他对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人文风貌等有着深刻的思考和描绘,通过对农民生活的细致观察,他将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安放在一个真实的乡村背景中,使得作品更加贴近自然和乡村生活的真实性。
张承志前期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满。
他对人物形象塑造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通过对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等方面的描绘,使得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物的性格特点。
这些人物常常是纯朴善良的农民,或是坚韧勇敢的农村妇女,他们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承志的前期小说作品中,往往带有浓厚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味。
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剖析,批判了一些社会现象和不公平的现象。
他通过小说,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的冷酷和不公,唤醒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张承志前期小说的风格也非常独特。
他在小说中注重细腻的描写和节奏的掌握,使得作品拥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他的文字平实、朴实,常带有一些幽默和讽刺的成分,给人以轻松愉快的阅读感受。
张承志的前期小说作品具有浓厚的乡村情怀、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社会关怀和批判力度,同时还具备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些特色使得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颗新星。
试论张承志《北方的河》
试论张承志《北方的河》张承志是新时期涌现出的一位创作风格比较独特的小说家。
他的小说常富于粗犷强悍的气势、绚丽浓重的色彩和丰富沉实的底蕴。
他的作品反映的也不是一己的苦闷、追求,更多的是反映一代人共有的理想、追求、欢乐和苦恼,尤其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角。
被人们称为“大地和青春的礼赞”、“青年奋击者的壮美诗篇”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更以广阔的艺术视野、深沉的历史感、雄浑的气势、强烈的时代精神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一、崇高的风貌《北方的河》中描述的是自然领域中的崇高在艺术领域里再现出的雄浑粗狂强悍的力的崇高。
深不可测的无定河谷,河谷两侧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使人仿佛置身于沟壑梁鍪的波峰浪谷里;陕北高原边的道道沟壑,笔直地跌向迷朦的巨大峡谷,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从天尽头蜿蜒而来,迷朦辽阔,威风凛凛,这就是北方的第一大河——黄河。
小说描写了雄越激昂的自然风貌,在这苍劲雄伟的大自然中,作者着力描写了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义无反顾地选择更艰苦、更富有牺牲精神的专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他就像那些北方大河一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坚定地朝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
小说的主人公毅然改变专业,报考更对他口味的、注定要经历艰苦跋涉的人文地理专业研究生。
他不惜自费考察河流,奔走于无定河、黄河、湿水之间,他要用实地考察得来的知识信心十足地“轰炸”那张考卷。
就连徐华北都能从那张《河的儿子》的照片上看到他与黄河血脉相通的东西:“这是——他。
”“他就是这样,干什么都不顾一切,瞧,他又朝着他的目标冲上去了。
”他艰苦奋斗、脚踏实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斗争精神正是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对祖国江河大地的向往、对“河的精灵”的探索、对民族精神的追求、对祖国美好未来的追求。
他没有一味地沉浸在额尔齐斯河的流连、永定河的烦恼、湿水的沉思中,没有让女友的离异、朋友的隔膜、事业的曲折打掉他前进奋斗的勇气,而是“让黄河托浮着”,被黑龙江送向那辽阔的人生入海口。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张承志散文中的“文化抗战”思想探析张承志的文化抵抗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
本文立足于对张承志散文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新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抵抗思想的内在动因及其限度。
标签:张承志;文化抵抗;文化侵略张承志在散文《无援的思想》中提出“今天需要抗战文学”的创作需求。
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以笔为旗》、《谁是胜者》等散文集,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抗战文学”主张。
在《错开的花》自序中,他提出了他的“抗战宣言”:“严峻的时代临近了,列强们又一次在谋算。
我们无力,我们只有背后的黄土高原,以及手中的一支笔。
那么,至少应当有文化的抵抗。
”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文化领域里,“冲突”一般被称为“文化阻抗”(Cultural Resistance)。
两种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本身就隐含着文化摩擦力的存在。
在双向互动过程中,一种民族文化总会要对另一种民族文化采取抵制的态度。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甚至认为:“文明间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边界,成为危机和流血的冲突地点。
”[1]此后一段时间乃至目前,“文化冲突”或者说“文明冲突”乃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当下现实话题。
尽管亨廷顿的分析有“危言”之嫌,但作为一家之说也并非故弄玄虚。
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抚育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
我们所说的民族个性,实则文化个性,是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及行为方式。
它一方面与邻近民族的文化发生竞争,另一方面,当邻近民族文化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则由竞争发展为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
作为一个刚从海外归来,有着深厚的民族情结的作家,张承志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甚至于可以说,恰恰是这种“冲突理论”,才真正契合了作家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思考和期待。
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指的是“对旧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影响作批判性的反思”。
[2]从其出现的历史语境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
从批判精神和策略着眼,我们发现,张承志是深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尤其是赛义德的“东方学”。
张承志在《投石的诉说》一文中曾提到过艾德华·赛义德:“第三世界的理论名著《东方主义》的作者艾德华·赛义德曾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弯下病弱的身体,拾起一块石头,朝以色列的方向投了出去。
他用这石头,表达了对这象征语言的理解。
他表示自己也要加入被侵占與被侮辱一方的行列,也要使用这种语言。
”[3]对张承志来说,受到和他有着同样族源的赛义德的影响,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何况还有更多重要的理由是赛义德的批判思想和张承志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赛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的产物。
欧洲文化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
东方在“东方学”中“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谎言。
”依赛义德的理解,欧洲中心文化的核心是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欧洲的东方观念也是这种文化霸权的产物,这种“东方学”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
所以赛义德说,“东方学的现实是反人性的”。
[4]赛义德的这些批判思想和精神,亦以同样的方式彰显于张承志的文本之中。
除此之外,杰姆逊、艾勒志·博埃默分别主张第三世界文学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时代环境中,应以一种异质文化的身份进入全球的文化对话之中,进而真正消除第一世界文学文本的中心性。
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于一个有着中华民族认同,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有着深厚北方民族史知识涵养的青年学者型作家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思想,经由现实环境的激发,直接构成了张承志“抗战文学”的由来,并对其“文化抗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张承志曾说:“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
[5]这里的“新体制”,指新世界体制,即由列强操纵并主宰的全球格局。
它之所以“新”,是因为和“旧体制”相比,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列强的核心有所转移,由新盎格鲁·萨克逊人(美国人)替代了旧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人);二是主宰世界格局的方式有所改变。
由过去的军事征服为主改变为“文化征服,经济侵略”,必要时才辅之以军事打击。
因此,抗击“文化侵略”,打破现存格局,解构西方强权话语就成了张承志“抗战文学”的主要内容。
张承志有一段陈述:“新的时代将是大多数穷国与西方对立的时代,将是艰难求生的古老文明与贪婪的殖民主义对立的时代。
”[6]在这个时代,全球化的进程将会使古老文明受到冲击,并可能进而消解现代民族国家乃至民族差异性。
对于一个生长于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具有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人,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还不止于此,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有向强势民族国家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趋同的倾向之时,有着浓厚民族情结的张承志便会义无返顾地站出来,“哪怕只是为了自我,我也决心向这个世界开枪。
”[7]试看一段话:“自诩是保卫祖国的人也在加油地在长城上给日本人跑腿,活像是新潮派的皇协军。
然而日本人的长城观是欧文·拉铁摩尔的长城观——拉铁摩尔认为:中国这个存在,其合理的边界是长城。
时间到了1992年,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学已经变成了流行整个西方七国的分裂中国的舆论。
”作家说:“长城几经修复但确实残破不堪。
黄河已经沉重得快要完全滞涩。
长江被人口和暴雨改造着,……但这一切并不说明中国应该由西方列强来统治。
”[8]张承志所体认到的“文化侵略”,是针对西方列强,但主要是日本而言。
其原因恐怕与作家的日、加之旅以及日本对中国曾经的侵略历史有关。
他曾经不无忧患、满腔热忱地呼吁:“应该有很多人深入、生动地描写长城地带,描写黄河和南方的长江流域。
应该是一种新鲜的文章,不像贱卖民俗肤浅猎奇的电影,也不像搜集鳞爪故作大说的实录——它们应该生动地、缓缓地淌入人们的肺腑,用真实的描写给人们以认识和尊严。
”[9]在作家看来,有着“奸商立场的日本”,正在以其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念,妄图借助其强大的媒体篡改历史,颠倒历史真相。
“章回体地琢磨中国”,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肢解中国而制造舆论。
所以作家写道:“总要有人站出来向这世界开枪。
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
”我们看到,张承志以“黄河儿子”这种身份自觉地去抵抗新体制,实即显明了中华民族——中国这一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与他所体认到的西方“文化霸权”主宰下的全球同质趋向的二元紧张。
同时,张承志还不止是“黄河儿子”,而且还要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他站在世界古老文明的文化立场上,捍卫正义、捍卫“艰难求生存”的古老文明,主张第三世界自己的文明阐释权,对抗西方强权话语。
在《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这篇散文中,他写道:“美国国家地理播出了一个称为‘寻找阿富汗少女’的电视片。
”作家写道:“在对肖像的解释中,有两个因素尤其不能忽视。
一是权力和话语权力经常强化或干扰解释……其次,技术因素常常更是一个微妙的插入者……不消说他们会利用肖像艺术本身的暧昧和多解。
他们热衷的更是对肖像的添加解释。
”作家批评道:“美国《国家地理》对阿富汗封面少女的寻找活动和报道,既不是真实的艺术,也不是客观的报道,而是不义战争的宣传。
”[10]在《投石的诉说》中,张承志亦揭露了他所体认到的这种强权话语的不义性。
他说:“以一已之死诉说的人蒙受着诽谤。
他们动人的语言和难忘的形象,在火狱烈焰的映衬下,在巨大的话语压迫下,被描黑画丑,被下流歪曲。
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媒体,在卑鄙地诱导。
满足于自私的小康,人们习惯了白日的谎言。
确实炸弹造成了伤亡,但是,以死为语言的人所实践的同样不是战争行为,而是语言的传达。
他们企图用悲愤的一声轰响唤醒世界:我们只剩下了生命。
人们,你们听见了吗?”[3]在这样的“诉说”中,张承志进行着他对“新体制”的反抗,进行着他对“新体制”主宰下的强权话语的解构。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首先局限于话语层面。
话语层面的抵抗只能通过情绪化或概念化的表述,显明由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利益的损害,由此实现对全球化的抵抗。
他强调中文写作,强调写作的“母语性”。
按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倡导“母语性”正是捍卫本土文化独立性的一种方式。
张承志以中文写下的文本解构西方强权话语,从而揭露西方文化的本质,试图唤起国人乃至于第三世界文化圈对西方文化的反抗。
然而,如果这种话语层面的抵抗不落实到制度層面,则注定是无力的。
对制度层面的对抗,有赖于一个合法的制度来定义民族利益,继而拟定相应的行动准则。
而当今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迄今仍然没有一个完善的内部机制,这使得张承志的抵抗限于话语层面而空无所依。
除此之外,在张承志的“抗战”中,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一面,却忽视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的一面。
在为反叛者、弱小者张目的同时,也同样以漠视他人的生命价值为代价,尤其是在局部战争不断升级的今天。
的确,弱小者值得同情,反叛者也未必可耻,希腊人曾经在神话中把自己的典范赋予叛逆,他们塑造过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对旧有秩序和规范反叛的英雄。
但如果对秩序的反叛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进行时,这种反叛本身就吞噬了真诚、善良和美丽。
纽约世贸大厦中的无辜逝者、俄罗斯别斯兰学校里的枪下亡魂,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法国哲学家加缪告诉我们,反叛的思想必须警惕“由于厌倦和狂乱而沉醉于暴虐或奴役之中。
”参考文献:[1]张承志.岁末总结[J].中国作家,1994,(11).[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8):3.[3][11]张承志.投石的诉说,谁是胜者[M].现代出版社,2002:83.[4][美]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87-92.[5][6][7]张承志.无援的思想[J].花城,1994,(1).[8]张承志.失去公园的伊朗兄弟,张承志作品集:散文卷[M].海南出版社,1995.[9]张承志.以笔为旗,张承志作品集:散文卷[M].海南出版社,1995.[10]张承志.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谁是胜者[M].现代出版社,200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