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楼阁拜谒图》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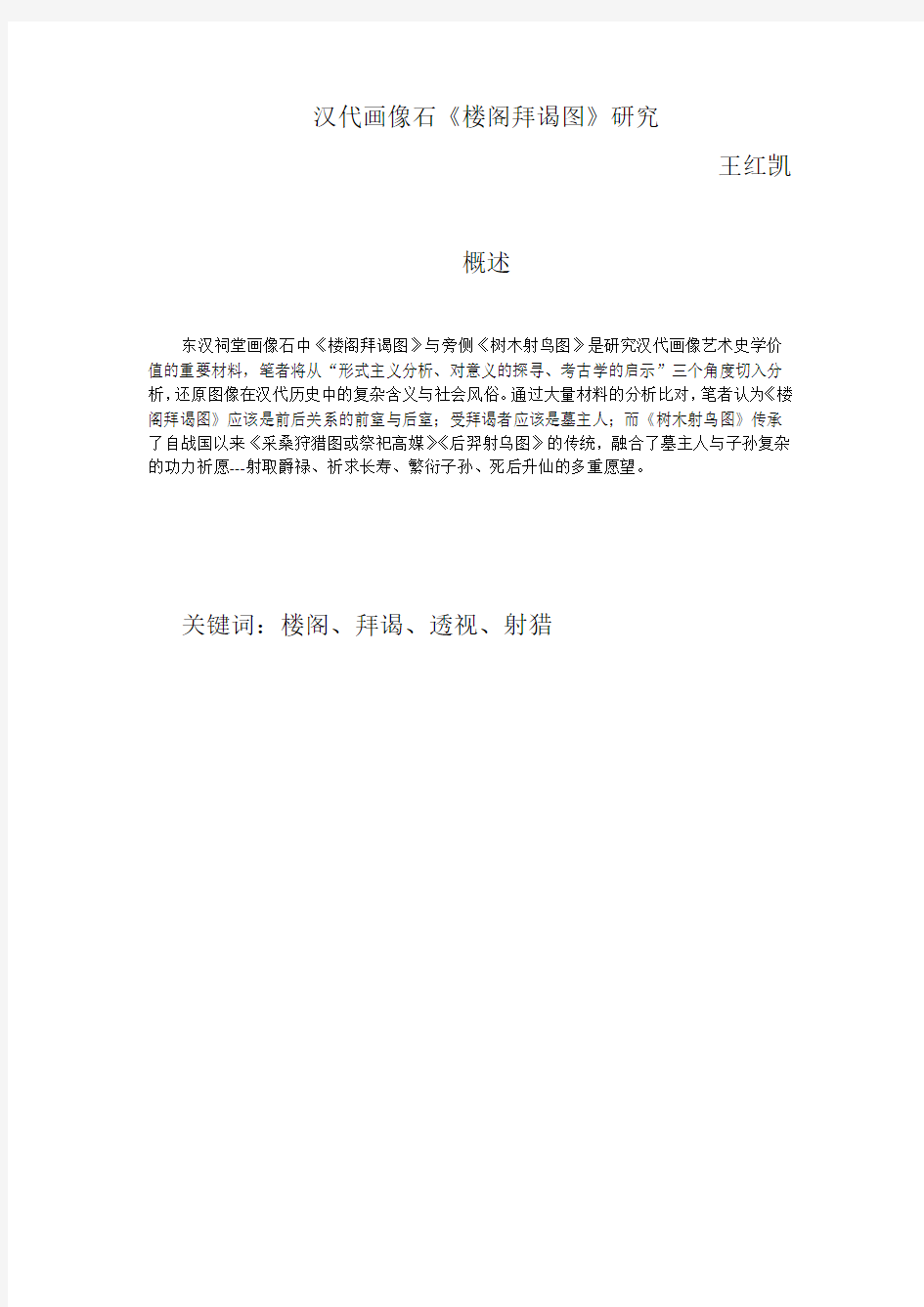

汉代画像石《楼阁拜谒图》研究
王红凯
概述
东汉祠堂画像石中《楼阁拜谒图》与旁侧《树木射鸟图》是研究汉代画像艺术史学价值的重要材料,笔者将从“形式主义分析、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三个角度切入分析,还原图像在汉代历史中的复杂含义与社会风俗。通过大量材料的分析比对,笔者认为《楼阁拜谒图》应该是前后关系的前室与后室;受拜谒者应该是墓主人;而《树木射鸟图》传承了自战国以来《采桑狩猎图或祭祀高媒》《后羿射乌图》的传统,融合了墓主人与子孙复杂的功力祈愿---射取爵禄、祈求长寿、繁衍子孙、死后升仙的多重愿望。
关键词:楼阁、拜谒、透视、射猎
腾固在1937年通过对汉代画像石与希腊石刻艺术的分析比较,精辟的指出:“浮雕亦有二种不同的体制,其一是拟雕刻的(高浮雕),希腊的浮雕即属于此类,在平面上浮起相当高的形象而令人感觉到有圆意;其二是拟绘画的(浅浮雕),埃及和古代亚细亚的遗品即属于此类,在平面上略作浮起,使人视之,但觉得描绘之物像携刻于其上。中国的石刻画像自然属于第二种,在佛教艺术以前,中国从未有过类似希腊的浮雕。但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有好几种,如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因为其底地磨平,阴刻的线条用得丰富而巧妙,所以尤近于绘画,像南阳石刻都是平浅浮雕而加粗率的线条阴勒,和绘画实在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对于中国汉代的石刻画像也想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此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属于这一类” [1]。
被腾固誉“拟绘画”的孝堂山和武梁祠的石刻不仅具有“生动之致,几于神化”的艺术与美学价值,而且也是众多美术史家研究汉代民俗、礼仪、制度、典章、服饰等等视觉艺术领域的重要材料。
从北宋伊始,金石学兴起,“以补正史、正诸儒之谬误”成为宋代史学界对于汉代时刻的基本理念。金石学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积累了大量金石铭刻拓片资料,著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十卷为跋尾,对藏品进行评论和考订,其中汉画像石拓片占了相当比重。书中首次著录了今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南宋洪适的《隶释》一书不仅收录了比《金石录》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对画像内容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和考证。在《隶续》中,收录摹写了包括武氏祠在内的山东、四川等地的大量汉代石祠堂、墓碑、墓阙上的画像,在汉画像石研究中首开摹录图象的先例。元明时期,学术废弛,金石学日衰,有关汉画像石的著作寥若晨星。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复兴,汉画像石也重新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
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将具有史学价值的武梁祠画像研究区分为三个部分“形式主义分析、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2]”。“对意义的探寻”一栏中巫鸿指出了一些石刻画像的重要图像的研究价值:诸如《楼阁拜谒图》、《桥头攻占图》、《泗水取鼎图》等。无论是图像尺寸还是图像位置,都表明对于它们的解读会是还原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史学价值的关键线索。
笔者就以武梁祠正壁中央下部的《楼阁拜谒图》来作为研究的重点,从“形式主义分析、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三方面来构筑起整个图像在东汉流行演变的轨迹。
《楼阁拜谒图》可以说具有严密的叙事性图像模型,整个图像在祠堂正壁画像区域核心位置,按历时性顺序分为《车马出行图》、《树木射鸟图》、《楼阁拜谒图》、《仙禽异兽图》。
图1、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龛室后壁
对此图像程序的阐释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楼阁拜谒图》,对于此类图像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黄明兰的“穆天子朝拜西王母”、土居淑子的“礼拜天帝使者”、长广敏雄的“礼
拜齐王”、巫鸿的“礼拜汉代君王”、信立祥的“祠主受祭图”。
贺西林认为:汉代墓葬艺术的构图模式按照墓室结构分为上,下两大部分,并且将原因归结于死后魂魄的分野。墓室顶部、祠堂尖顶、四壁上部一般表现天象与仙境;而墓室四壁下部主要表现现实场景。由于上部属于魂的归宿,下部属于魄,故而符合“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传统观念[3]。贺西林这一说法确实与汉唐之间墓室绘画顶部图像绘画情况相符合。
而大部分的《楼阁拜谒图》均位于祠堂正壁中央下部位置,明显属于人间叙事场景,与天帝和西王母等仙境主神无涉。
黄明兰和土居淑子的错误研究结论应该基于两个图形程序的误解。首先是楼阁的上层及中央的贵族女性。楼阁的高度与居于中央的女性,加之围绕在楼阁四周的仙禽异兽,自然会令学者产生西王母和天帝的研究结论。
《史记封禅书》记载:“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广诸宫室[4]”。
诚然“仙人好楼居”,但是《楼阁拜谒图》当中的两层楼阁真的就是上下高度上的两层吗?笔者难以信服。
Ludwig Bachhofer 、George Rowley、Martin Powers都认为武氏时刻属于汉代时期“空间意识还未完全发展的时期”,风格较为平面化、二维化,缺乏诸如山东金乡朱鮪祠堂画像的空间感、三维幻觉特征(如图2)。
图2、山东金乡朱鮪祠堂图像
Martin Powers研究认为不同风格的联系在东汉时期并行不悖,不同的社会阶层基于自身社会属性的考虑选择不同的刻画风格;而武氏祠堂是汉代典型的儒家阶层,儒家阶层选择较为古典的二维平面风格与其他阶层拉开距离,保持自身文化的觉醒。
宋代洪适《隶释》卷六《从事武梁碑》记载:“武椽,椽讳梁,字绥宗。椽体德忠孝,岐嶷有异。治韩诗经,阙帻传讲,兼通河洛、诸子传记。广学甄彻,穷综典囗,靡不囗览。州郡请召,辞疾不就。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诲人以道,临川不倦。耻世雷同,不闚权门。年逾从心,执节抱分。始终不贰,弥弥益固。大位不济,为众所伤[5]”。
巫鸿研究认为整个巫鸿祠堂画像的设计都是基于一个东汉儒家今文学派的自我设计。武梁本人“治韩诗经,阙帻传讲,兼通河洛、诸子传记”,他的个人文化倾向以及社会阶层属性决定了他对于画像石古典主义风格的选择。
比较武氏祠堂所有的图像,二平面性几乎具有普遍性,典型的《泗水捞鼎》与《七女为父报仇》都为塑造成了上下维结构的平面性图像。
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探讨武梁祠石刻画像《楼阁拜谒图》时,曾指出阙间的建筑并不是
楼阁,而是一前一后两个独立的建筑:
由于不懂得远近法与鸟瞰法,建筑前面(或门)与建筑内部被上下相叠地表现出来,如果第二层画像是后殿,第一层就是前殿;如果第二层是后室,那么第一层就是前室[6]。
笔者将从“阙与楼阁”的三种组合方式,探讨汉代石刻工匠刻画所谓的楼阁组合元素的随意性。第一类:双阙与单层建筑。图3~图5所示的东汉画像石的双阙与单层建筑组合中,人物活动位于单层建筑以下,尤其图3滕州画像石刻画中,工匠有意营造出近大远小的透视感,虽然这种努力没能取得成功,但是这种倾向表明了工匠意识到这种探求的重要性并付诸于实践,工匠是刻画表明了建筑前后关系的种种尝试。
图3、山东滕州画像石图4、江苏徐州画像石
图5、江苏徐州画像石图6、江苏徐州画像石
第二类组合方式--双阙与楼阁(如图8、9、10)所示,巫鸿与信立祥均认为汉代祠堂根源于西周宗庙。宗庙与墓葬基于死后魂魄的分野,分别对于魂与魄的祭祀,为吉礼与凶礼。《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
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二端即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以报气(魂)也”
[7]。
宗庙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基于对祖先魂的祭祀;而墓地位于郊外,对于魄的祭祀。赵翼认为“盖因上陵礼之制,士大夫皆仿之立祠堂于墓所”。战国至东汉的演化过程中,西周传统宗庙逐渐附属于个体性墓葬,魂与魄的祭祀逐渐合为一体,东汉乡他君祠堂题字“兄弟暴露在冢,不避晨夏,覆土成墓,列植松柏,起立石祠堂,骥二亲魂灵有所依止。”宗庙功能附属于墓葬,魂与魄融合为一体,东汉时期的祠堂亦称之为“祠庙”“斋祠”“食斋祠”。
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宗庙建筑形式:“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庙,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像生之具[8]”。
俞伟超研究认为宫殿“前朝后寝”与宗庙“前庙后寝”墓葬“前室后寝室”是相互联系的。
所以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高度上的上下楼阁其实并不“高”,上下结构的楼阁应该是前后关系的,它模仿了宗庙“前朝后寝”的结构形式。工匠在具体雕刻时受到二维平面风格的束缚,故而只有将宗庙的前后关系刻画成上下关系。
图7、孝堂山祠堂,武梁祠堂,前石室,左石室结构图
另外的证据来自前石室与左石室,两者结构样式与武梁祠略微不同,而在正壁中央开龛,即清代黄易记载的“架屋两间”(如图7),而楼阁拜谒图刚好位于龛室之中,故而将其解释为《拜谒祖先图》符合东汉祠堂祭祀礼仪,也与祠堂建筑结构相符合。
对于上层楼阁(即后寝)居中的女性形象如何解释也就顺理成章了,巫鸿与杨宽认为东汉时期的墓葬多为家族型,而夫妇合葬成为定制。对于子孙而言,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都是其祭拜的对象[9]。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武梁祠堂中存在大量的对母亲行孝的孝子图像,诸如:丁兰、闵子骞、曾子、老莱子等。前朝(下层楼阁)属于男性祖先所在居于;后寝(上层楼阁)属于墓主人妻妾即女性祖先所在地,子孙祭拜的对象应该是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的集合体。
图8、山东曲阜画像石
图9、山东嘉祥孝堂山祠画像石
图10、山东嘉祥孝堂山祠画像《楼阁拜谒图》展开示意图
第三类建筑为庭院回廊式建筑,在前凉台孙倧墓庭院图中,双阙、门、庭院、堂、后院等建筑构建起中轴线般前后格局。如下图所示,画匠侧面俯瞰式的构图,有效的回避了正面构图带来的技术上的局限性,从而很好的将建筑体系中前堂后室的关系视觉化。
图11、山东东汉前凉台孙倧墓线描图
山东嘉祥焦城村出土祠堂图像,受拜谒者后题刻“此斋主也”(非“此齐王也”)。信立祥认为斋即斋祠、祠堂;斋主即祠主、墓主人(如图12)。而山东嘉祥五老洼出图的画像石刻中,中心人物旁边榜题“故太守”。表明受拜谒者并非他人,而是墓主人[10]。
图12、山东嘉祥焦城画像石拜谒图
图13、山东嘉祥五老洼出图的画像石
南阳许阿瞿与“齐郡王汉特之男阿命”两位汉代画像石艺术中有名的儿童,父母在刻画他们的形象时也采用了楼阁拜谒图的基本样式,表明了这一图式在汉代的普及性。
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1973年出土于南阳市东郊的曹魏墓中,是三国人用汉代画像石重新筑造坟墓时被挪用作墓顶石的,该墓志画像石70厘米×112厘米,石面左方为志文,隶书,竖刻6行,满行23字,共136字,末行有16字漫漶,不能尽识,曾将拓片寄于郭沫若同志考订断句加标点,其文曰:“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逝),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壬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财连(联)篇(翩),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埽,以快往人。[11]”从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名叫许阿瞿,年仅五岁不幸于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三月十八日就夭折了,全家极为悲伤。此石的右边刻有画像分上下两格,上格左边一幼童跽坐于榻上,旁边有铭文“许阿瞿”三字。许阿瞿前有三幼童,或托木乌,或牵引木鸠车玩耍。下格为舞乐场面,或飞剑跳丸,或踏盘鼓甩袖而舞,或抚琴吹箫奏乐。
《孝经》提到五种孝行:“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居养病的孝行更多的是家庭内部的事,后两者孝行表现在丧葬与祭祀的共同场合中,成为孝子扬名立万的大众表演。汉代察举孝廉制度、孝子的伪善与表演推动了汉代丧葬艺术的蓬勃发展。桓宽《盐铁论》云:“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后。故黎民慕效,至于废室卖业。[12]”丧葬艺术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汉代石刻工匠、作坊、格套榜题、某种图式的社会化与普及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阿瞿与王阿命两位儿童画像(且父母不需要从孩子的丧葬中得到任何实质的利益,故而儿童的丧葬石刻画像来源于父母的真正的爱,而不是伪善)也采用了成人丧葬图像的模式。
另外需要阐述是就是围绕楼阁的仙禽异兽,难道它们是仙境的营造方式吗?笔者难以认同,首先仙禽异兽围绕着楼阁,而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故而对于它们的解释必须和楼阁联系起来,孤立的研究它们势必会出现图像解释上的误导。
笔者上面已经引用了贺西林的研究,仙禽异兽围绕着的楼阁位于建筑下端,故而与仙境、天象无关;从图像位置来看只能与楼阁拜谒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种汉代墓葬中的“镇墓辟邪”图像具有相关性。在西汉晚期洛阳烧沟61号墓门额描绘的著名的“羊头与虎吃旱魃”图像,《风俗通义》记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汉代铜镜也记载“左龙右虎辟不羊”。而对于旱魃,《诗·大雅·云汉》记载:“旱魃为虐,如惔如焚”。孔颖达疏:“《神异经》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
羊通“祥”,象征吉祥,整个图像可以解释为虎噬食旱魃之后,墓室出现祥宁瑞和的景象(如图14)。
图14、洛阳烧沟61号墓羊头与虎吃旱魃
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第二重漆棺,表现了墓主人在气的作用下,由保护者和祥瑞的陪伴下前往永生之地的景象。祥瑞包括:舞乐者、仙鹤、九尾狐、仙人骑鹿。祥瑞在这里主要扮演着保护墓主人并且赐予祥和宁静(如图15)。
图15、马王堆一号墓第二重漆棺保护者形象
所以,仙禽异兽围绕着拜谒图像的楼阁,寓意给墓主人带来永久的宁静与祥和的景象,墓主人得以安宁,得以永生。黄明兰、土居淑子和长广敏雄的研究的没有根据的。[13]对于《车马出行图》,巫鸿的解释是标榜核心人物的社会地位。笔者不赞同此说法,信立祥研究认为,车马出行图不能一概而论,应该与图形在建筑中的位置联系起来。车马出行图位于祠堂拜谒祖先图形下方,而且位置具有普遍性。“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象征墓葬,位于祠堂下方,如朱鮪墓葬结构图所示,祠堂在上,墓宅在下。所以,《车马出行图》表现的应该是承载墓主人灵魂到祠堂接受子孙的祭拜的过程。
图16、费伟梅描绘朱鮪祠堂结构图
《树木射鸟图》可以说也是解释《拜谒祖先图》的关键。信立祥研究的认为是祭祀祖先涉猎牺牲的解释也不予采纳。因为鸟雀并非汉代祭祀祖先的祭品。汉代普遍的祭祀牺牲有:牛、羊、猪、鸡、鱼、犬等。牛、羊、猪属于太牢、少牢;鸡、鱼、犬等属于平民的祭祀牺
牲,在武氏祠左石室的供案石中刻画了“鱼和鸡”能说明这一情况。所以《树木射鸟图》应该还要其他解释。
台湾学者邢义田的研究值得重视,邢义田搜集了大量的《树木射鸟图》,发现普遍化的《树木射鸟图》应该具有4个因素:树木、射弋者、雀鸟、猴子。所以《树木射鸟图》全称应该是《射猴射雀图》[14]。
邢义田研究认为《射猴射雀图》应该寓意《射爵射侯图》,象征射取爵位,立官置吏。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后室就出现了类似的图像(如图17、18),榜题为“立官桂树”。《史记龟测列传》:“立官置吏,劝以爵禄”,《乐府诗集·相逢行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15]”。
图17、和林格尔墓后室图像图18、选自邢义田《画为心声》页166图31.b 在汉代雀与爵通用,和林格尔墓前室顶部南侧题字“朱爵”,实应为“朱雀”。《陈留耆旧传》曰“圉人魏尚。高帝时为太史。有罪系诏狱。有万头雀。集狱棘树上。拊翼而鸣。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鸣即复也。我其复官也”。《礼记·射义》:“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16]”
故而雀与爵通用,猴与侯通用,爵与侯象征富贵;雀与猴就是“爵与侯”的图像形式。
那么《射爵射侯图》位于《楼阁拜谒祖先图》旁侧有何寓意呢?在汉代为何具体普遍性呢?南北朝时期,在保留了汉代几乎图像程序的西北地区此图像与孝子、列女、古圣先贤图像为何消失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
汉代的官员选拔是察举孝廉制度,州县内定期都会推举一定名额的闻名乡里的孝子上报中央,授予官职,和林格尔墓主人就曾经“举孝廉”,前室中央明确记载了他早年因“孝廉”而入仕的经历。
众多汉代祠堂都是子孙出资建筑的。巫鸿,邢义田都指出:祠堂的榜题与其说是发自对父母的孝心,不如说是对于自我孝行的宣扬。大量榜题都会出现“花钱数万”“请名匠高平**”的夸耀自身孝行的文字,乡他君祠堂刻铭“兄弟不避晨夏,列植松柏,起立石祠堂”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郑岩也指出,在汉代,祠堂更多的是社会性质的场所,夸耀孝行,赢得孝行的美誉,立官置吏正是汉代孝子孝行背后的真正社会隐因[17]。
另外一方面,“射爵射侯”可能只是代步了祖先殷切希望的某一方面,笔者认为《树木射鸟图》含义应该更加复杂,战国《采桑宴乐攻战狩猎纹壶》的狩猎图像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漆箱侧面的《神人射乌图》代表了这一图式的最早版本。
西汉时期《树木射鸟图》中树枝螺旋般缠绕,这种形象与西汉流行的某种神木相类似。《山海经·海内经》:“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
过,黄帝所为。”《吕氏春秋·有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墬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
东汉时期四川南溪3号石棺(如图19)当中具有一个严格的叙事结构:画面中央是半启的天门,右侧是刚刚乘坐仙鹿到达的持节方士,引申文献《典略》天师“持九节仗为符祝”,可知此人应该是巴蜀地区五斗米教的师,他正下跪礼拜端坐于老虎座上的西王母,一个仙女正在向她通报。右侧的螺旋般缠绕神树好像就是墓主人辞别家人前往西王母仙境的桥梁。类似的图像还出现在四川新津宝子山石棺顶部石刻图像中,巫鸿认为石棺的图像发布规律与位置有关系,而位于石棺顶部的都与天象、仙境有联系。图像中树木螺旋般缠绕也与四川地区流行的三段式神仙镜有关联[18]。
图19、东汉四川南溪出土3号石棺
图20、东汉四川新津宝子山石棺顶部石刻图像
图21、东汉四川地区三段式神仙镜
三段式神仙镜的中央为仙境的主宰西王母与东王公,四周环绕着羽人与仙禽异兽,底部为缠绕的神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这种具有神树某种属性的树木在汉代《树木射鸟图》中仍有残余,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工匠对于某一传统图像形式的传承与变革。
另外一方面《树木射鸟图》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祭祀高媒之神的仪式上。《礼记·月令》:
“孟春三月……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仲春之月,……玄鸟至。至元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在周代,高禖神仍辅佐木帝治理着阳春三月;周天子的迎春祭礼,紧紧地围绕着农业丰产祭祀进行;在祭礼中,嫔妃以弓箭插入弓套之中并授于高禖之前,这是一种具有浓烈的性巫术意味的祭式:炎黄时代的丰产祭仪“葛天氏之乐”的性狂欢,到周代帝王前已雅化为“授弓矢”,其目的同样在于祈求丰收与多子多福。如下图,“采桑”“弓矢”“男人媾和”都体现了祈求繁衍子孙、多子多福的愿望。
图2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采桑狩猎纹铜壶
对于《树木射鸟图》中猴的形象,应该也有祈求长寿的寓意。《抱朴子.对俗》记载“猕猴寿八百岁变为猿,猿寿五百岁变为玃。玃寿千岁”。对于生命的祈望、死亡的恐惧成为贵族阶层、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共同理想与祈望。《庄子·刻意》记载:“吹呼吸,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19]”。《左传.昭公二十年》“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春秋齐国青铜器的铭文时常刻画“勿死、难老”的字样,也同样表达了逃离死亡的终极人生目的。
故而,汉代《树木射鸟图》可以传承了自战国以来《采桑狩猎图或祭祀高媒》《后羿射乌图》的传统,融合了墓主人与子孙复杂的功力祈愿---射取爵禄、祈求长寿、繁衍子孙、死后升仙的多重愿望。
而对于汉代画像石刻的美学价值,邓以蛰先生在《画理探微》中言:“吾人观汉代动物,无分玉琢金铸,石雕土范,彩画金错,其生动之致几于神化,逸荡风流,后世永不能超过也。汉代艺术,其形其形之方式唯在生动耳。[20]”生动儿二字差可以概括汉代石刻艺术的精华。
参考文献
[1] 腾固《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
[2]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
[4]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68到1370页,中华书局出版社
[5]宋洪适,《隶释》卷六《从事武梁碑》,中华书局出版
[6]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7]《礼记.祭统》第1605页,载巫鸿《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第74页下注解
[8]东汉蔡邕《独断》,第20页,中华书局出版
[9]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11]郑岩,《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性质与其他》载《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第98页,北京大学出版
[12]恒宽《盐铁论》,中华书局出版
[13]巫鸿,施杰译《泉下的美术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载《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秦汉史论著系列》,中华书局出版
[15]《乐府诗集》第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6]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载《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秦汉史论著系列》,中华书局出版
[17]巫鸿《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中的纪念碑性》,郑岩,李清泉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8]巫鸿著,郑岩等编《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载《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王先谦《庄子集注》第96页,国学社整理《诸子集成》(第3册)
[20]邓以蛰,《画理探微》,载刘纲纪编《邓以蛰美术文集》,88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战国秦汉画像砖文献简目
战国秦汉画像砖文献简目 刘未辑 王仲殊《空心砖汉墓》《文物参考数据》1953,1期。 安金槐:《郑州二里岗空心砖墓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6期。 王寄生:《闻喜西官庄汉代空心砖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4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新繁清白乡东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6期。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四川德阳县收集的汉画像砖》,《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 重庆市博物馆编:《重庆市博物馆藏四川汉画像砖选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 赵世纲,《淅川县见到的几种汉代花纹砖》,《文物参考数据》1957,8期。 于豪亮:《几块画像砖的说明》,《考古通讯》,1957年4期。 赵世纲:《淅川县见到的几种汉代花纹砖》,《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8期。 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方继成:《汉砖花纹释例》,《人文杂志》,1958年1期。 游清汉:《河南舞阳冢张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9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南关159号汉墓的发掘》,《文物》,1960年8、9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汉代画像砖拓片》,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 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1961年11期。 居方:《汉代收获渔猎画像砖》,《历史教学》,1962年10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二队:《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汉画象空心砖墓》,《考古》,1963年11期。 王褒祥:《河南新野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考古》,1964年2期。 孔次青:《山东曲阜纪庄发现汉代空心砖》,《考古》,1964年9期。 居举郎澜、金仁:《贵州赫章县发现的汉砖》,《考古》,1964年8期。 吕品、周到:《河南新野新出土的汉代画象砖》,《考古》,1965年1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省收集的古代花纹小砖和文字砖〉,《文物》1965,5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年10期。 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说东汉市井画像砖》,《文物》,1973年3期。 张观教:《市井像砖市楼上应为鼓钲并悬》,《文物》,1974年1期。 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4期。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组等:《略论秦始皇时代的艺术成就》,《考古》,1975年6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1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期。茂陵文物保管所等:《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7期。
徐州汉画像石
引论 从内容上看,画像石所表现的几乎无所不包,它不但反映了一个汉代社会而且表现了一个想象奇异的神话世界,把汉朝人脑子里所想的,所需求的都揭示出来了。事隔两千年左右,社会的变化很大,当我们在欣赏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画面时,有的虽已不明其意,也有的并不陌生。譬如那些礼仪和宴会上的场面,庖厨和杂技,以及耕田者,纺织人和打铁的人。有些生活和生产的方式仍然继续。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脉络是难以割断的。它的变化正是说明文化的生命力,源远流长不等于一成不变,有变化才有活力,有活力才能发挥前进,所以说,事隔两千年左右,我们回头看那些画像石时,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现象。因此需要对画像石进行“解读”和“诠释”。 一、徐州汉画像石的历史和发掘 徐州是中国汉画像石的集中分布地之一。清同治《徐州府志》碑碣考中就有徐州沛县发现汉画像石的记载。民国年间,著名书法家、收藏家张伯英(徐州人)也收藏、保存了一些汉画像石,但这些都是未经科学发掘的零星发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铜山县的茅村、洪楼、苗山、白集、利国、柳新、汉王,睢宁县的张圩、邳州市的燕子埠、新沂市的瓦窑、沛县的栖山等乡镇,保护性发掘了一批汉画像石墓。目前,徐州地区保存的汉画像石共有1300多块,其中,大部分收藏在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内,现在实际对外展出的有600多块。 徐州地区的汉画像石,从雕刻技法、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看,不同于河南南阳、陕北、晋西、四川一带的汉画像石,而和山东南部一些地区的汉画像石极为相似,因为这两个地区在汉代同属徐州刺史部,经济、文化关系密切,互相影响,形成了同一风格。 汉代画像石艺术是在当时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和厚葬之风盛行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艺术渊源,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那精美的画面不仅反映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且使我们得以窥见汉代社会风貌。 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两汉时期一直为封建王朝所重视。西汉初期,刘邦封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地方广大,有薛郡、东海、彭城等共36个县,西到河南,东至大海,南达淮河,北到今山东的临沂和泰安的汶河一带,今天苏、鲁、豫、皖交界的广大地区皆以今徐州为中心,徐州无疑成为“五省通衢”的重要门户。两汉四百年间,这里共有楚王、彭城王十八代,至于其荫封的王子侯孙、豪族世家就更多了。豪强之家生时恣意享乐、极尽其欲,死后则崇仰厚葬,加之崇仰鬼神,迷信之风甚盛,多爱把自己所崇拜、爱慕的东西在墓中雕刻成画。豪族贵戚如此,一些中小地主也竞相效仿。同时,徐州地区盛产石灰岩、青石,为营造汉画像石墓提供了充足的石料来源。因此,众多的汉画像石墓便在徐州一带兴盛了起来。 二、汉画像石中的社会活动与现代生活的联系 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就会十分的困难。目前看来,对画像石的分类多根据直观的印象进行分类。主要的学术分类有:李发林将其分为4类:(1)表现祥瑞和神话故事的图像,(2)刻画自然风景的图像,(3)反应社会现实生活的图像,(4)描绘历史人物故事的图像。吴文祺和蒋英炬将其分为4类:(1)表现社会生活的内容,(2)描绘社会生产的内容,(3)表现神话传说及鬼神信仰的内容,(4)描写历史故事的内容圆。日本学者土居淑子将其分为7类:(1)具有故事情节的画像,(2)关于祭祀礼仪的画像,(3)有关天象和然现象的画像,
汉代画像砖制作工艺
汉代画像砖制作工艺 汉代画像砖同画像石一样,它们是古代劳动人民为我们留下的一种珍贵的艺术品。“一方面是墓室的建筑构件;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艺术装饰。”然而,两者在质料、制作工艺、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者较大区别。汉代画像砖的种类繁多,砖和画像的制作工艺复杂。现就汉代画像砖的制作工艺等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汉代画像砖的形制 古代的砖主要用于建筑,目前发现最早的砖是山西侯马春秋时期遗址中的少量遗存,但数量不多,有长方形与方形砖两种,素面;到了战国,除长方形砖、方形砖以外,还出现了凹槽砖、门字形砖和空心砖花纹;秦代因为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大型建筑工程的需要,作为建筑构件的砖,品种也有迅速增加,如出现了无棱砖、曲尺形砖、楔形砖及子母砖等。秦代的空心面仍多饰米字形,以及回纹、棱形纹、龙纹和凤纹等,主要用于宫殿大型建筑设置。 汉代砖的种类比战国和秦代大为增多,制作也非常精美,而且大量被用于墓葬之中。其中汉代画像砖(包括花纹砖、铭文砖等)可分为两大类:实心砖和空心砖。 (一)实心砖:主要有长方形、方形、梯形、楔形及长条形等各种形制。其中,长方形绳纹和方形花纹砖,这两类砖一般较规整,大小尺寸分别相同或相近;方形砖一般稍薄,它们主要用于墙体或铺地;长条形砖,这种画像砖形制一般狭长,具有随意性,因为它主要用于墓室之中,大小尺寸是由墓室结构决定的;小楔形砖,该砖主要为加固墓顶等用。梯形砖,一般两端为卯或榫结构,主要用于墓顶。另外,在以上各形制的画像砖中,均有一部分因建筑结构需要,带有子母榫。 (二)空心砖:多为大型中空长方形条状。最早发现的空心砖是战国的,砖的上下面及两侧面皆为平面,两端挖空成两个圆孔或长方形孔。当时空心砖主要用于建筑墓内的室。到了汉代空心砖又有很大发展。”汉代的空心砖都是用以构筑墓内椁室的,因为椁室形制的不同,和空心砖在椁室构筑中部位的差异,形制也不一样,大体上室有屋脊形与箱形两类,长方形空心砖多用于箱形室,只是砖的大小有些不同而已。至于屋脊形室所用空心砖,由于建筑结构较为复杂,作为这种椁室构件的空心砖其形制种类也相应的复杂多样,这些空心砖可以看作现代板式结构建筑和预制构件的先河。” 二、汉代画像砖的制作方法 画像砖的制作,一般来说实心砖制作较为简单,空心砖由于其形体较大,制作要求难度大,其制作工艺相对复杂。 (一)空心砖。空心砖的制作较为复杂,根据对南阳新野及周边地区出土的残断空心砖认真观察和分析,空心砖的制作至少有雕制模具、原料的筛选、加工制泥,拉坯成形、印制花纹、入窑烧制等工艺过程。 第一,雕制模具。它直接决定画像的内容和画像质量的好坏。一般先选料,制作画像砖的母模多为木质,部分小印模为陶质。这是因为木质易于雕刻,可以表现画面的细部。材料确定后,接下来画师们根据构思进行勾画,用笔将图像画在木料之上,最后才由雕刻工匠进行细致入微的雕刻。由于空心砖长短不一,形状各异,根据墓内结构的不同要求,雕制出各种各样的木模,然后再制成凹槽形状模具。
汉画像石的考古研究分析
汉画像石的考古研究分析 汉画像石的历史价值 在我国,汉画像石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大的区域:一是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地区;二是豫南、鄂北地区;三是陕北、晋西北地区;四是四川、重庆、滇北地区。全国范围内汉画像石的发现数量,大概在六千余石。现代研究汉画像石的学者,把这些汉画像石资料进行了科学的分类,主要有生产活动、社会生活、历史故事、远古神话、天文星象、祥瑞辟邪、图案装饰等,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画像石以不同的题材,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科技和法律,成为形象化的汉代史料、汉代百科全书。 1973年3月,河南省南阳市王寨汉画像石墓出土一块画像石,上刻一彗星图。此图刻绘在前室石梁下面,画像左边刻有背负日轮的一只阳乌,东边刻一满月,月中有蟾蜍。画像表现的是日落月升的傍晚,日月之间刻有六星连线组成的“∪”形,是省略化的天庙星。月亮右边又有六星也有线相连,是与天庙星相邻的东欧星。东欧星上下各刻一彗星,两彗星皆彗尾向东,彗头向西。依照古代星图,天庙、东欧为南宫朱雀十七度张宿统辖的二星。《后汉书?天文志》载:“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俱攻破南阳……光武兴于河北,复都洛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研究者魏仁华先生认为,此图所绘,即是新莽地皇三年出现于张宿的彗星,而且较《后汉书》的文字记载更为形象
生动。文图相映,为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解。在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画像石中,首次发现了一幅描绘汉代刑徒的画像。“画面周围有执笏而坐的官吏,中间在腰佩弓箭手执长刀的武士围绕中,有一群蓬头散发的人,其状悲惨,有的被一个或两个手执长刀或三角刀形器的武士揪住乱发,有的匐伏地上,有的没有头发,这些人就是汉代的刑徒。 古人不剃发须,剃掉发须是判罪的刑罚”,这幅画像就表现了对刑徒髡发的情景。汉代刑徒是官府手工业的重要劳动力,还从事国家的各种劳役,是和农民、手工业工人一起创造汉代物质文化的大军。研究者认为刑徒画像是研究汉代阶级关系、政治、法律等的珍贵形象资料。除此之外,全国各地出土的有纪年的汉画像石刻,则以直接的方式、可靠的形式把历史的瞬间清晰地刻录在了石头上。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全国有纪年文字的汉画像石刻有七十多处。南阳也有发现,如唐河郁平大尹墓主室中柱上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久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天凤五年即公元18年。纪年汉画像石刻准确地提供了墓主人的姓名、官职、下葬时间、地点等,对研究画像石墓的断代、汉代职官制度、民情风俗、书法艺术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汉画像石作为一种成熟的石刻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雕塑史上的地位也不可小觑。由于年代久远,汉画像石成为保存下来的研究汉代绘画的实物资料。由汉画像石可以看出汉代绘画的特色:题材多样,形式独特。石刻与绘画相结合,既表现了汉代美术的多样化,也表现出一种成熟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形式美和内在美,其吸引力和震撼力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画是在汉画石刻
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造型特征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5b11182751.html, 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造型特征研究 作者:张明月 来源:《艺术科技》2016年第11期 摘要: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艺术是中国造型艺术之大宗,其中人物造型高度概括简化, 充分表现出一种整体、深沉而雄大的恢宏气势,是艺术创作中形神兼备的高度体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夸张的艺术表现力,标志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成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画历来强调的以形写神、意韵生动的艺术理念在这里找到了最早的源头。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人物造型;概括;简化;整体 0 引言 在一次艺术考察中,我在洛阳艺术博物馆近距离观看真实的画像石拓片以及墓室中的画像石,接触到汉代画像石,被其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和极具动感的夸张表现深深地吸引。其人物形象,整体大气,动势夸张,极具个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审美高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从造型手法及艺术价值两方面对画像石中的人物造型进行深入研究。 1 概念 画像石就是汉代的像石,是中国汉代的石刻画,产生与西汉,生于东汉,魏晋之际仅有个别实例,故称汉画像石。 ——范迪安[1]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系在石棺平面利用雕刻技法并施涂彩色制作的特殊壁画,用以嵌饰祠堂和墓室,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征,在世界其他地区中不见与之完全相同的艺术品。 ——杨泓[1] 通过广泛学习,综合诸多概念我了解到,“画像石”,顾名思义,石上的画像,也可以说是一种石刻绘画。因其形象塑造大多使用雕刻技法,所以,就其成型技术而言,属于雕刻艺术。但就其整体艺术形态和艺术风格而言,又与绘画极为一致,因此称为画像石。画像石艺术在我国汉代时期发展至高峰阶段,所以一般意义上的画像石就是指汉代画像石。 2 画像石中人物造型手法 2.1 高度概括和简化
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 所谓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金石学阶段、考古资料积累阶段和综合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为金石学阶段,时间上大体从北宋末年到二十世纪初。作为一种明显的地理标志,矗立在墓地中的汉代石祠堂、石墓阙及其画像,最先受到战争史家和地理学家的注意。东晋末年,戴延之在《西征记》中首次记载了今山东地区鲁恭墓前的石祠堂、石庙及其画像。北魏末年,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了今山东、河南南阳等地李刚、鲁峻、胡著等人的石祠堂及其画像。但是这些石祠堂及其画像,都是作者在记述地理形势和河川时作为地理标志而写进著作中的,还算不上是汉画像石的学术性著录。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地收集和著录汉画像石。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积累了大量金石铭刻拓片资料,著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十卷为跋尾,对藏品进行评论和考订,其中汉画像石拓片占了相当比重。书中首次著录了今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该书由于主观欣赏的比重远远超过客观研究,因此对画像石记述非常简略,使读者很难通过其描述了解画像的具体内容。真正意义上的汉画像石著述,始于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隶释》一书不仅收录了比《金石录》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对画像内容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和考证。在《隶续》中,收录摹写了包括武氏祠在内的山东、四川等地的大量汉代石祠堂、墓碑、墓阙上的画像,在汉画像石研究中首开摹录图象的先例。元明时期,学术废弛,金石学日衰,有关汉画像石的著作寥若晨星。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复兴,汉画像石也重新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 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资料主要来自未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零散画像石,大多数学者甚至只以收集的拓片为资料,因此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地面上散存的石祠堂、墓碑和墓阙的画像,墓室画像石几近于无;二是著录和研究偏重题榜铭刻文字和历史故事画像内容的考证,对大量无文字题榜的画像石则很少加以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使金石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对汉画像石作全面的、科学的考察。 第二个阶段约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一个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石资料的阶段。1907年,法国考古学家沙畹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关野贞分别调查了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代石祠堂、石墓阙及其画像,并出版了印制精美的图录;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等人调查了四川嘉陵江和岷江流域的汉代崖墓、石阙及其画像。在调查中,他们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测量和记录,从而使汉画像石的研究开始走出金石学家的狭隘书斋,进入到考古科学的庭院。1933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主持发掘了山东滕县的一座大型画像石墓——传曹王墓。与此同时,河南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也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30年和1937年,关百益和孙文青相继出版了《南阳汉画像集》、《南阳汉画像汇存》,南阳汉画像石的风貌开始为世人所知。抗日战争期间,撤往四川的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的部分学者,分别调查了四川彭山、乐山和重庆附近的汉代画像石阙及崖墓画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惜华将所收集的大量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拓片,编辑出版了
汉代画像石《楼阁拜谒图》研究
汉代画像石《楼阁拜谒图》研究 王红凯 概述 东汉祠堂画像石中《楼阁拜谒图》与旁侧《树木射鸟图》是研究汉代画像艺术史学价值的重要材料,笔者将从“形式主义分析、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三个角度切入分析,还原图像在汉代历史中的复杂含义与社会风俗。通过大量材料的分析比对,笔者认为《楼阁拜谒图》应该是前后关系的前室与后室;受拜谒者应该是墓主人;而《树木射鸟图》传承了自战国以来《采桑狩猎图或祭祀高媒》《后羿射乌图》的传统,融合了墓主人与子孙复杂的功力祈愿---射取爵禄、祈求长寿、繁衍子孙、死后升仙的多重愿望。 关键词:楼阁、拜谒、透视、射猎
腾固在1937年通过对汉代画像石与希腊石刻艺术的分析比较,精辟的指出:“浮雕亦有二种不同的体制,其一是拟雕刻的(高浮雕),希腊的浮雕即属于此类,在平面上浮起相当高的形象而令人感觉到有圆意;其二是拟绘画的(浅浮雕),埃及和古代亚细亚的遗品即属于此类,在平面上略作浮起,使人视之,但觉得描绘之物像携刻于其上。中国的石刻画像自然属于第二种,在佛教艺术以前,中国从未有过类似希腊的浮雕。但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有好几种,如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因为其底地磨平,阴刻的线条用得丰富而巧妙,所以尤近于绘画,像南阳石刻都是平浅浮雕而加粗率的线条阴勒,和绘画实在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对于中国汉代的石刻画像也想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此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属于这一类” [1]。 被腾固誉“拟绘画”的孝堂山和武梁祠的石刻不仅具有“生动之致,几于神化”的艺术与美学价值,而且也是众多美术史家研究汉代民俗、礼仪、制度、典章、服饰等等视觉艺术领域的重要材料。 从北宋伊始,金石学兴起,“以补正史、正诸儒之谬误”成为宋代史学界对于汉代时刻的基本理念。金石学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积累了大量金石铭刻拓片资料,著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十卷为跋尾,对藏品进行评论和考订,其中汉画像石拓片占了相当比重。书中首次著录了今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南宋洪适的《隶释》一书不仅收录了比《金石录》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对画像内容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和考证。在《隶续》中,收录摹写了包括武氏祠在内的山东、四川等地的大量汉代石祠堂、墓碑、墓阙上的画像,在汉画像石研究中首开摹录图象的先例。元明时期,学术废弛,金石学日衰,有关汉画像石的著作寥若晨星。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复兴,汉画像石也重新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 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将具有史学价值的武梁祠画像研究区分为三个部分“形式主义分析、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2]”。“对意义的探寻”一栏中巫鸿指出了一些石刻画像的重要图像的研究价值:诸如《楼阁拜谒图》、《桥头攻占图》、《泗水取鼎图》等。无论是图像尺寸还是图像位置,都表明对于它们的解读会是还原汉代画像石刻艺术史学价值的关键线索。 笔者就以武梁祠正壁中央下部的《楼阁拜谒图》来作为研究的重点,从“形式主义分析、对意义的探寻、考古学的启示”三方面来构筑起整个图像在东汉流行演变的轨迹。 《楼阁拜谒图》可以说具有严密的叙事性图像模型,整个图像在祠堂正壁画像区域核心位置,按历时性顺序分为《车马出行图》、《树木射鸟图》、《楼阁拜谒图》、《仙禽异兽图》。 图1、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龛室后壁 对此图像程序的阐释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楼阁拜谒图》,对于此类图像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黄明兰的“穆天子朝拜西王母”、土居淑子的“礼拜天帝使者”、长广敏雄的“礼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浅析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浅析 摘要:汉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的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在中国绘画艺术的长河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本文从画像砖、画像石产生的社会背景、艺术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希望能够进一步认识汉代形成的雄浑朴实的中国审美艺术。 关键词: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艺术 一、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浅析 古代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社会分工,在业余的工匠中产生了专业的画工。从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一位走上美术舞台的是民间画工,之后是宫廷画师和文人画家。可以说画工画是宫廷画和文人画根植的沃土。经过了千年绘画艺术的发展,到了汉代,已经达到了中国民间美术较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画像石、画像砖。画像石、画像砖可谓是中国时间最久、分布最广、作者众多、品种最丰、受众最多的艺术形式之一。 汉代汉王朝建立之初总结亡秦的教训,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奉行黄老哲学。汉初的各项政策,使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因此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汉初
经济和政治都有所发展和繁荣,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因此这一时期在政治、外交和思想上都达到空前的统一和繁荣。 画像砖、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服务于丧葬礼俗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所谓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画像砖则是用拍印和模印方法制成的图像砖。首先从材质和制作方法上来讲,二者有比较清楚的区别。画像石是汉民采集石料雕刻上图画形成的。画像砖则是用黏土为料,在烧制的前后进行印模压印、彩绘、雕刻等工序制作而成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使用于祠堂、碑阙、墓圹甚至是建筑。从功能上来看,二者既是建筑结构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室内装饰。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生动地记录了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民俗等诸多方面,完全可以视之为“汉代的百科全书”。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序》中,曾高度评价画像石、画像砖是“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形象。同时,在这个历史上,也在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 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鲁迅先生也称赞它“气魄深沉雄大”,并且多次高度评价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价值。 二、画像石、画像砖的产生
浅析汉代画像石的构图方式
浅析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及构图方式 010212139 朱琳汉代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从西汉初年的文、景或武帝时期画像石产生到东汉末年消失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尽管政治不断更迭,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但直到黄巾军大起义之前国家还是统一的,尚未出现封建军阀割据、势力纷争的局面,这有利于当时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在哲学思想等意识形态领域里,汉初至汉武帝统治之前崇尚老庄哲学,实行无为而治。之后,直到到东汉末年作为统治阶级巩固国家政权的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汉武帝以后统治阶级把“忠”、“孝”等作为人们加官进爵、跻身政治舞台的重要手段和作为人生礼制、道德等重要的品评准绳。加之经学昌盛,图谶流行,鬼神迷信,升仙信仰等风行到三江两地、五湖四海之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的厚葬风气①,促进了汉代画像石题材内容在全国各地的流行,正所谓“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 汉代画像石汉画像石画像砖的地理分布比较广泛,主要有四大区域:(1)山东的西部、南部以及苏北、皖北地区。(2)豫南、鄂北地区。(3)陕北以及晋西北地区。(4)四川、重庆地区,基于各地区不同的文化,画像石的题材风格甚至构图方式都各有差别,但是总体来说,不管以何种方式的分类,题材上还是大同小异的,无外乎社会现实生活,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祥瑞及装饰图案几个大的方面。下面以上述四大区域各取一例加以说明。 山东汉画像石画像砖的代表性祠墓主要是孝堂山郭氏祠、嘉祥武氏祠和沂南汉墓。嘉祥武氏祠题材内容以描绘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宣传儒家教义为主。代表作品有叙事性的东汉的《荆轲刺秦王》、《王陵母》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寓意阴阳形态的“异质同构”和生生不息。技法上采用剔地凸像的“薄肉雕”,以阴线表示面部或衣纹,人物形象多为正侧面角度,只见大略外形,具有剪纸般的装饰效果,简约、厚重、整体、大气。人物故事场景以穿插排列其间的边饰纹样作为空间分割和装饰陪衬。构图以“满”为胜,大量采用平行式构图。 南阳画像石画像砖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历史故事之外,多取材墓主人生前奢华生活场面和神话传说,另有对天文星座的表现如《阳乌负日》,南阳画像石的技法除阴刻线和平底浅浮雕之外,最具特点的是斜横纹衬底浅浮雕剔地并施以横斜衬纹,使主题凸出,再用简练的阴线条,刻画细部。造型简洁,神态生动,构思大胆奇巧,刀法粗犷有力、泼辣豪放,构成了南阳画像石独特的艺术风格。
汉画像石文献11
箫鼓东汉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出土 一辆车,用三匹化装了的马拉着。车上安装着建鼓。建鼓的中间插杆挂着缨穗缨络,最上面安个方座。 车上有五人,一人驾车,二人在前面吹箫,二人在后面举着缨络。而在车顶上的方座上,有一个小孩倒立其上,显出独特技艺。这是一辆出行的彩车,是带领乐舞队伍的。 骑马听乐图(作者收藏拓片) 骑马偶相遇,问君何所适,未及开口言,忽闻楼上有歌声,勒马细聆听,竟是年青别离曲。相顾人老两鬓白。
摇鼗鼓,山东沂南北寨出土 鼗是导也。摇鼗鼓,即在小鼓两侧有小珠以绳与鼓面相连,有一支长柄可用手捻动,使两侧小珠摆动而打击鼓面发声。在乐队开始演奏乐曲前,先摇鼗鼓,在演奏中不时穿插鼗鼓声,以烘托气氛。 抚琴,山东沂南北寨出土 汉代的琴,在众多乐器中,起着统帅作用。它声音和谐,音量大,却不喧哗。声音小时也能让人听到。它携带方便,因此成为不离身的乐器。 光武帝刘秀每次宴会上,都要让人鼓琴。可见琴在汉代是比较普及的一种乐器。 吹笙,山东沂南北寨出土 笙是以匏为底,在上面有规律的插上一定数量的竹管,再加金属的簧片。利用气流与簧片共振发音,每个竹管发出一个音,这音好像是从植物中发出的,的以叫笙。它是汉代乐器中的佼佼者。 “笙奏”是指全部乐器合奏的意思。
吹笛,山东沂南北寨出土 山东沂南北寨出土的画像石,有一人竖吹一乐器,它就是汉代的笛。 击铙 铙像铃,比铃大。使用时,以手执铙把,铙吕朝上,另一手拿小锥子敲击。 在汉代的乐队中,有四个人吹排箫,一人吹埙。为首的一人既吹排箫,并以锥击立于地上的铙,作为调节乐曲的节奏。 撞钟,山东沂南北寨出土 特钟,现存南阳汉画馆 上图是山东沂南北塞出土的画像石,一幅撞钟,它架子上悬挂两个钮钟。乐人用长棒撞之,棒上有一条带子,可见棒的分量不轻。 下图是特钟。它悬挂的是一个甬钟。在乐队演奏乐器前,首先要击特钟,作为乐曲的前奏之一,使乐队各种乐曲,同时开奏。二是在演奏乐曲过程中,击这特磬,可以加强乐曲的节奏。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文学院 10级1班宁夏学号:2010013666 摘要:汉代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汉代歌舞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画像石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乐舞图像将二者完美的结合,不仅再现了雄浑广博的大汉风韵,更体现了当时文化繁荣、气势恢弘的时代精神。近十年,随着汉代画像石的不断挖掘,对汉代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研究也日益繁盛。本文将从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地区分布及特征、乐舞类型、审美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对近十年来关于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研究进行整理。 关键字: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乐舞类型审美影响 一、汉代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及特征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汉画像石的分布十分广布,卫雪怡在《汉画像石的乐舞研究》中对汉乐舞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及特征进行了阐述。她将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分为四个大区域,分别是:画像石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的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中部的广大区域;以南阳为中心,包括湖北省北部地区在内的区域;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川渝地区和陕北、晋西地区。以山东为首的第一个分布区域受儒家文化和道家升仙思想影响颇深;以南阳为代表的第二个区域受楚文化影响最大,长袖细腰、轻盈飘逸的楚舞风格、小型乐队的表演艺术等形式是此区域汉乐舞画像石的主要艺术特征;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第三个区域深受巴渝文化影响,浓郁的西域文化风貌,手持鼗鼓和排箫的伏羲、女娲图以及独特的巴人民间舞蹈是本区乐舞汉画像石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陕北、晋西地区的乐舞画像石以剪影似的科化手法、鼓员敲击建鼓是动作缺乏舞蹈性、长袖舞伎人衣长袍、挥广袖舒缓而舞为主要艺术特征。除了以上四大汉乐舞画像石区域,卫雪怡还阐明散见于各省的画像石也不少,但数量有限、画面表现内容相对单一,不具有代表性和区域性特征[1]。关于汉乐舞画像石地域分布,吴金宝对于分布区域划分和特征描述与卫雪怡大致相同但稍有差异,他从深沉厚重的苏鲁豫皖边界区的艺术风格、迤逦灵动、迷离浪漫的南阳区乐舞艺术风格和博采众长、独具特色的四川去乐舞艺术风格对目前各地出土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内容、形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总结[2],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关于汉代乐舞画像石地区分布的研究梁宇在《从汉画像砖石上寻访汉代舞蹈》[3]中也有简单阐述,但是分类不如前两位清晰、描述也没有前两位详细。 除了对汉代乐舞画像石整体分布及特征的研究以外,对各代表区域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对南阳地区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研究最为突出:王松阳从图像学角度,以汉代画像入手,探讨了百戏中舞蹈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女乐歌舞表演的技术和韵味,“四夷”之乐与汉乐舞的融合与繁荣,以及汉代贵族间自娱性的即兴舞蹈和礼仪性舞蹈“以舞相属”风俗等方面对南阳汉代乐舞画像石进行了研究[4];黄茜文以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乐舞图像中的舞姿形态、表演形式以及对汉代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折射等方面来追溯汉代艺术的嬗变轨迹[5];田平以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为标准从六个方面欣赏汉画像乐舞艺术的审美内涵:飘逸轻盈奔放的舞技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用生动形象演绎出震人心弦的旋律美;舞蹈者妩媚动人的形象给人一种自然美的愉悦;夸张变形,出奇制胜;寓巧于拙,稚拙朴实之美;“形神兼备”——汉画乐舞具有传情达意的美学意蕴 [6];王蕊研究的是南阳汉画像石刻与汉乐舞融合所产生的双向审美效应的表现和内在成因与机制[7];王孟秋则是对南阳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几种乐舞形式——建鼓舞、长袖舞、盘鼓舞进行了探讨,讲述它们各自的舞蹈艺术特点,分析了汉代乐舞繁荣的原因。通过研究汉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上西王母图像分析
汉代画像石上西王母图像分析 论文摘要:汉代社会充满了神鬼迷信,随着道教在汉代的兴盛,其遵从的一些长生思想也逐渐普及,使得长生不死和死后升仙成为汉人皆有的愿望。西王母作为道教思想里的至上神,成为人们纷纷追捧的偶像。在人们意识到现实中的羽化成仙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渴望死后能达成愿望,于是纷纷于墓室中绘制一些能表现成仙愿望的图像,这时,西王母的形象便频繁出现。 关键词:西王母图式长生观念偶像崇拜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自战国中期至两汉发生了第二次重大的变化,一个新的宇宙构成部分——仙人世界终于被人们创造出来。汉代之所以神仙思想繁盛,是因为汉初主张推行黄老之学,讲究的是无为之治,与民休息;当时的新儒学形成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系统,还有社会上一直延续的巫祀行为仍有影响;方士神仙思想受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欢迎。再加上道教的影响,通过董仲舒推行的王道与天道合一,以阴阳五行统辖万物的学说成为稳定的专制政权的理论。以上种种,都推动了神仙思想的深入人心,而掌握着不死之药的西王母则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崇拜的神仙。 西王母形象的起源 西王母崇拜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在《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籍中均有西王母的记载,最初西王母的形象并不被人们认同,《山海经·西山经》记载说: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疠及五残。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述略同: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山海经·海内北经》云: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 记载中的“疠”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恶性传染病,另一种解释认为“疠”
汉代画像石砖的装饰艺术研究
汉代画像石砖的装饰艺术研究 袁恩培 〔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重庆400030〕 摘要:研究中国汉代画像石、砖的装饰艺术风格,探讨民族艺术形式、民族艺术装饰手法,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装饰文化。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砖;装饰艺术;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1-0100-05 Research on the Decoration Art of the Stones and Bricks with Pictures of the Han Dynasty YUAN En-p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Art,Chongging Uniuersity,Chongging400030,China)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coration art of the stones and bricks with pictures of the Han dynasty,discusses on the form of the nationaI art and the way of the nationaI art decoration,to inherit and deveIop the cuIture of the nationaI conventionaI decoration. Key words:the stones and bricks with pictures of the Han dynastyg decoration artg traditionaI cuIture 中国汉代艺术具有气魄深沉雄大、韵味醇厚质朴、骨力雄健奔放、气势高视阔步等特点,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体,形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汉代最重要、最丰富、最有时代特征的美术遗存是画像石、画像砖,它们的造型、布局、工艺制作及非凡的想象力和浑厚、宏大而又活泼的装饰风格都是空前的,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水平,对以后的装饰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我国的传统绘画里,自先秦两汉至今,虽然有时代风格之差异,但在重视装饰性这一点上总是一贯的。汉画像石、砖的装饰手法与以前相比,因其写实技法的提高,生活气息浓厚,显得生动活泼,而无呆滞之弊。与后世相比,它的装饰手法简练,整体感强,古朴庄重,富丽大方,而无繁琐细碎之感。在一贯重视装饰效果的我国传统绘画中,汉画像石、砖的装饰手法独具一格。为了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深入研究汉画像石、砖的艺术特色十分必要。 汉代以前的艺术着重于工艺美术的创造,如骨角、玉器、陶器雕刻或是商周的青铜器等,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汉画像石、砖继承了这些艺术遗产,但又突破了呆板的图案纹饰的束缚,因而显得生动活泼。不仅内容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而且艺术表现方面,写实的技法有很大提高,特别是人物的刻画由朴拙进而达到十分传神。“传神”是汉画像石、砖艺术的重要特征, “写形”是为“传神”服务的,为了能更充分地达到“传神”的目的,在造型手法上往住予以适当的取舍和夸张。画像石又称石刻画,有人又把它简称为“汉画”。一般是用在墓前石造享堂中作装饰,有时也用在墓室中作装饰。有时也用石刻画来装饰石棺或庙祠前的石阙。画像石装饰画的一般表现方法是在磨平的石面上先雕出人物形象等等,而将空余的地方薄薄雕去一层,使形象稍稍高出于底面。一些细部刻画则是用阴线刻,这些细部刻画比较简单,这种表现手法称为“减地浅浮雕”。《武氏石祠》上的装饰画就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此外,在表现手法方面,还有用线刻来表现的,即在平面上刻各种直线或曲线构成欲表现的图画,在这里把这种表现手法称为“阴线刻”。有时在线刻的画面上却把部分形象薄薄雕去一层,使它稍稍低于石面,在这里称它为“平面阴线阴刻”。 在汉代的画像石中, 《武氏石祠》具有自己独特的作风,它为装饰画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武氏石祠》在装饰艺术上具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它明确表现出装饰画与绘画不同,装饰画必须采用装饰性的表现手法。武氏祠的画像石是作为石室内的一种装饰,所以它要求所有作品有共同的作风,它不是单从某一个画面来考虑采用什么装饰手法,而是从石室整体的装饰 00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卷第1期 JOURNAL OF CHONGOING UNIVERSITY(SociaI Science Edition)VoI.11No.12005 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简介:袁恩培(1954-),男,重庆人,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教学研究。
民间信仰视域下的汉代祈财仪式图释读-中国汉画学会
民间信仰视域下的汉代祈财仪式图释读 郑先兴 【内容摘要】汉代人对于财富的崇拜,一是体现在汉画像所绘制大量的五铢钱形象,二是在四川等地出现了大量的青铜质地的摇钱树,其所传达的财富、长寿、平安、幸福等可以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诉求,可谓是溢于言表。汉画像的鱼儿,则借助于语音的相谐,表明人们对财富的诉求;捕鱼的画面则表明了财富可以源源不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鱼儿与莲花绘制在一起,则是一种纯自然的象征,即“连年有余”。汉画像中的天仓体现了普通民众那种能够不劳而获、得天而食的愿望;而汉画像中的各种工艺环节劳作场面,说明汉代人深刻地意识到,财富的获取只有通过勤奋的劳作,人们才能够必须的粮食、财富。 【关键词】汉画像;民间信仰;祈财;仪式图 【作者简介】郑先兴,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史、史学史。 财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依靠。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由此,作为民间信仰的五福内容之一,当然也体现在汉画像中,其主要的形式是摇钱树、莲鱼和天仓等等。 一、摇钱树:汉代祈财的时代特色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转折时期,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仅是在地域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文化方方面面实行了一体化。尤其是货币形态,统一采取了铜质与内方外圆的形制,即所谓的秦半两,汉承秦制,采用了五铢的形制。由此,汉代人对于财富的崇拜,集中体现在人们渴望拥有大量的五铢钱。今天能够看到的就是在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实用五铢钱、阴用冥钱。另外,在汉画像中,也绘制了大量的五铢钱形象。如图1,南阳汉砖画像,画面为模制图纹“大泉五十”,两两一组。如图2,南阳汉砖画像,画面为模制,上下各位菱形图案,中间为内方外圆的钱币,中间似乎有绳索穿起,可谓是“钱串”。[1]显然,这两幅画像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财富的渴望与膜拜。 图1 南阳汉砖画像“大泉五十”图2 南阳汉砖画像“钱串” 当然,汉代对于财富的崇拜,或者说拜金主义最大的表现,还是摇钱树的出现。根据考古发掘,在四川等地出现了大量的青铜质地的摇钱树。如图3,四川省博物院所展出的摇钱树,有1972年彭山县汉代崖墓出土一株144厘米的摇钱树,1983年广汉市东汉砖墓出土一株152厘米的摇钱树,绵阳东汉崖墓出土一株200厘米的摇钱树,等等。这些摇钱树的特征是青铜质地,如图4,其叶片为五铢钱样,配置有西王母、朱雀、佛、乐舞百戏等神话和生活场景。西王母是长寿的偶像,佛则是平安幸福的偶像,朱雀是汉代四灵的南方神,乐舞百 189
文物200503--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_刘云涛
·81· 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 刘云涛(莒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东莞镇位于莒县城北55公里。1993年5 月底,东莞镇文化站站长李永英在东莞村西南 约1.5公里处发现石刻一块。莒县博物馆闻讯 后派人前往察看,发现是一座古代墓葬,随即 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图一)。 该墓早年被严重破坏,墓上无封土,墓圹 已残。为一座长方形土圹竖穴砖石合建墓,方向南偏东15°。墓圹残长7.8、宽3.8、深1.7米,填土中夹杂着大量的残砖块。墓内的画像石表面全部用白灰涂抹,而且未发现随葬品。该墓共出土画像石10块,现分别介绍如下。1号石,顶残。高1.72、宽0.62、厚0.37米。四面皆刻画像。正面画像自上而下分为7层(图二)。第一 层是内饰卷云纹的拱形边框,框内刻朱雀和羽 人图案。第二层中间刻题记8行,每行13至18 字不等,惜已被后世造墓者凿残(图六)。题记 如下:“惟光和元年八月十日◆◆琅琊东莞◆ 孙熹 年六十四故世◆◆故◆◆诸曹(?)掾◆ 县主簿 ◆◆升离◆◆情意◆此大门阙◆◆ 归 于◆千秋万岁◆◆◆◆◆◆◆山◆◆◆ ◆◆◆◆有刻◆◆◆者游魂◆无不◆ 其 ◆◆◆◆◆◆◆◆◆◆◆◆孙◆ 东◆命行事 承◆◆升太知播惠康 ◆◆◆◆◆◆◆◆◆◆ ◆永无疆” 题记右侧一人,双手持盾,右向躬立,脑后 有榜题“门大夫”,其身前置一釜灶。题记左侧 为两层干栏式建筑,楼上楼下各坐一人。第三 层中间刻一圆坑,深6.5、直径13.5厘米。圆坑 右侧刻三人,其中右者荷物登梯,左者张弓射 之,二人中间立一小人。右下角有一榜,无题 。 图一墓葬位置示意图
·82··2005年第3期 文物图五2号石背面及右侧面画像拓片 图三1号石背面及右侧面画像拓片图二1号石正面及左 侧面画像拓片图四 2 号石正面及左侧面画像拓片
论东汉画像砖《庭院》图像
论东汉画像砖《庭院》图像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石棺画像、墓阙画像、崖墓画像在巴蜀地区留下大量的有关建筑的图像。几乎各县都有,尤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为甚。其中成都双流县牧马山出土,谓之《庭院》或曰《庄园》的一幅画像砖图像被《中国建筑史》等若干经典版本采用,并有大量文论阐述。尤可见此图在中国建筑史上的突出地位,即凡论中国古代建筑尤住宅者,不涉此案,皆有不成文章之嫌。此图究竟在中外相关著述上用了多少次,已无法统。 这些著作对于《庭院》图像见解大同小异卓有见地,特征为:主体厅堂三开间,并构成前庭后院院落。而次要的杂务,库贮部分则形成另一功能区。二者中有廊道分隔成一主一副两部分;四周则有廊道围合形成一方形庭院。谓之庭院或庄园等。 经长期观察与图像比较,似觉尚有一些现象值得进一步探讨,特絮述如下: 1坐北朝南庭院格局 牧马山《庭院》图像中的空间格局组合划分,是
四川古代农村民居中的必然,还是偶然。比如为什么要把核心居住主宅部分放在画面的右上角(西北方),而把厨房放在左下角(东南方)从而形成对角格局之状,显然,这不是偶然。 《庭院》描绘之地的川西平原,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主要受蒙古高原和阿留申低亚的影响,盛行北方,偏北方(东北方)吹来的强劲干冷的冬季风,甚至全年都吹此风,而夏季为太平洋高压和印度洋低压所控,也吹来南方暖湿夏季风,但相对微弱。我们审图看画而判,无论什么方向,庭院左下角的东南方最宜设置厨房,优点为全宅其他任何角度、位置所不能取代,因为此位是避开烟霾随风流向对庭院干扰的最佳角度选择,原因自然在厨灶一年到头大量使用的燃料上。 四川盆地古代不产煤,居民厨用燃料多木柴、秸秆之类。往往浓烟滚滚,污染严重。此况直到当代都是棘手问题。一个庭院,如果厨灶之房处理不当,包括灶位在厨房内的位置,其烟霾将熏染全宅,而烟霾的流动受风向的影响最大。若要躲避冬季东北风,夏季南风裹挟烟霾侵染全宅,最佳办法便是把烟污染控制在全宅的东南一隅,使其不能进入庭院内其他地区,此论当今拿到农村检验,古今一致,必东南方设厨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