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歧视与抗争中成长的黑人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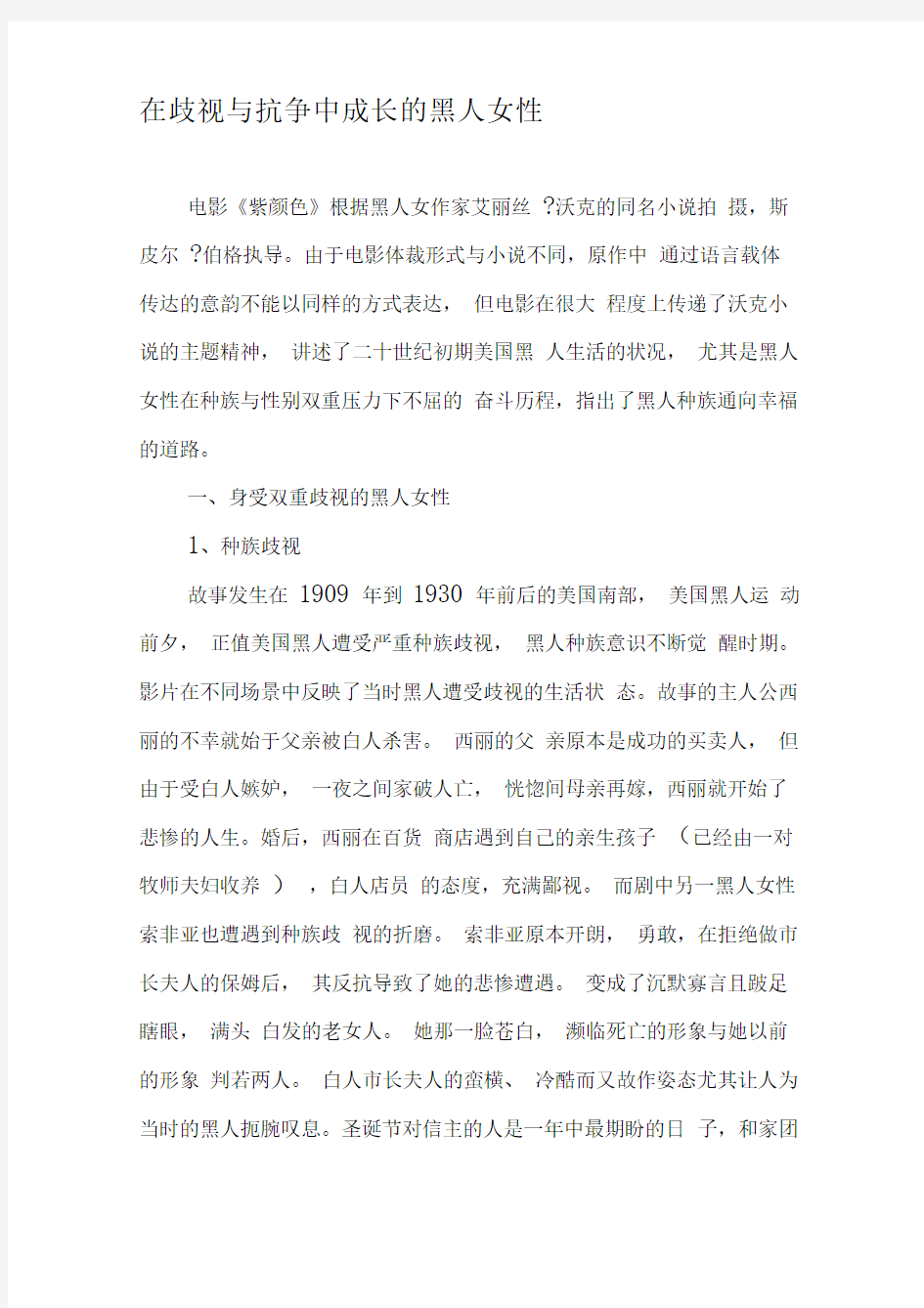

在歧视与抗争中成长的黑人女性
电影《紫颜色》根据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同名小说拍摄,斯皮尔?伯格执导。由于电影体裁形式与小说不同,原作中通过语言载体传达的意韵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但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传递了沃克小说的主题精神,讲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黑人生活的状况,尤其是黑人女性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力下不屈的奋斗历程,指出了黑人种族通向幸福的道路。
一、身受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
1、种族歧视
故事发生在1909 年到1930 年前后的美国南部,美国黑人运动前夕,正值美国黑人遭受严重种族歧视,黑人种族意识不断觉醒时期。影片在不同场景中反映了当时黑人遭受歧视的生活状态。故事的主人公西丽的不幸就始于父亲被白人杀害。西丽的父亲原本是成功的买卖人,但由于受白人嫉妒,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恍惚间母亲再嫁,西丽就开始了悲惨的人生。婚后,西丽在百货商店遇到自己的亲生孩子(已经由一对牧师夫妇收养),白人店员的态度,充满鄙视。而剧中另一黑人女性索非亚也遭遇到种族歧视的折磨。索非亚原本开朗,勇敢,在拒绝做市长夫人的保姆后,其反抗导致了她的悲惨遭遇。变成了沉默寡言且跛足瞎眼,满头白发的老女人。她那一脸苍白,濒临死亡的形象与她以前的形象判若两人。白人市长夫人的蛮横、冷酷而又故作姿态尤其让人为当时的黑人扼腕叹息。圣诞节对信主的人是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和家团
圆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权利和愿望,可是被迫沦为白人女仆的索非亚却只有得到主人的恩典,才得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整天”的许诺对她是奢侈品,须臾片刻已是万幸。而强占他人的市长夫人却以为这已是天大的恩惠,这极具讽刺意味。种族歧视还延伸到黑人的祖籍地――非洲。西丽的妹妹耐蒂跟随牧师一家来到非洲传教,亲眼目睹了白人如何毁掉奥林卡人世代生存的丛林。白人殖民者强占了他们的土地,拆掉了他们的房屋,砍倒了给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奥林卡人流利失所,逃向密林深处。奥林卡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这让前去传教的耐蒂认识到上帝也帮不了忙。作者通过故事向非洲的延伸向人们展示了美国黑人的民族之根,提醒世人不要忽视黑人的民族传统。实际上,不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中,艾丽丝?沃克和斯皮尔?伯格都对这种民族传统给予重视,比如莎格头上的彩色翎羽,莎格演唱的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等都充满了非洲黑人民族色彩。这种黑人文化的回归体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文艺运动的思想,即“强调黑人文化的灵魂和传统,寻求黑人文化的自觉性”。
2、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只是故事的大背景,故事的焦点在于一群无助且受父权压制的黑人妇女。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讲述了以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妇女从奴隶走向独立的人生历程。性别歧视是压在黑人妇女身上的另一座大山。正如贝尔?胡克斯指出的“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在这种传统的父权思想影响下,黑人妇女大都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剧中主人公
西丽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西丽跟随母亲改嫁,十四岁就受到了继父的
侮辱,并先后生下两子,不知去向。后西丽又被迫嫁给已有四个孩子的鳏夫。丈夫另有所爱,对西丽百般虐待。西丽像奴隶般劳作,但她受旧思想的影响,从不反抗。西丽没有话语权,她只给上帝写信。她在信里说,“可我不知道怎么斗争。我只知道怎么活着不死。”“我不斗,我安分守己。…‘我把自己变成木头。”她麻木地对待父权制度对她的迫害,逆来顺受忘却了在自己身上所承受的痛苦。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另一层面上,她又自觉地充当了旧制度的捍卫者。当索非亚,一个能为自己的尊严生活的人物出现时,西丽对哈波(索非亚的丈夫,阿尔伯特的儿子)的建议是“打她”。悲哀中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与西丽不同,索非亚生来不惧怕男人。她敢爱敢恨,永不肯低头。为了让索菲娅变得服服帖帖,哈波接受了西丽的建议,挑起了婚后的第一次家庭战争,最终以哈波的鼻青脸肿告终。索菲娅?巴特勒漂亮、聪明、强壮,从来都像一列勇往直前的军队那样充满霸气。但是,当自己深爱的丈夫第一次打了她,她的忧愁多过愤怒。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一生都在打架,跟父亲打,跟兄弟打,跟堂兄弟和叔叔伯伯打。一个女孩在一个男人统治的家里是不安全的。让她难过的是,没想到在自己家里也得
打一架。
索非亚与哈波家庭之战反映了性别歧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身受父权思想毒害的还有莎格。莎格是作者刻画的理想的黑人女性形象。她漂亮,开朗,勇敢。勇于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但她也是臭名昭
著的放荡的坏女人,连亲生父亲都不愿意承认她。为此,她不能和自己喜
欢的男人结婚(西丽的丈夫阿尔伯特),但她却生下了他的孩子,还被怀疑她的孩子是和不同男人生的。莎格生活中的不幸,可以说与父权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抗争沃克在陶洁译本的序中讲到,小说“强调人的发展成长,妇女间的团结以及男人成长产生变化的可能性。”电影体现了原作者沃克的表达意图。在抗争中,西丽得到了姐妹们的帮助,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走上了从经济到人格的独立道路。
1、西丽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独立真正改变西丽的是其丈夫的情人莎格。在美丽执著、大胆直率的布鲁斯歌手莎格的启发和帮助下,西丽学会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前半生的悲惨遭遇。她首先向上帝发出质问:“上帝为我干了哪些事?”“他无聊、健忘、卑鄙……以耳聋为荣”,“我告诉你,要是他肯听听可怜的黑女人的话,天下早就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伴随着对上帝的质疑,西丽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她不再对自己感到羞耻,不再对男人感到害怕。当丈夫又要揍她时,她针锋相对,“用餐刀扎他的手”。当丈夫讥讽她“你是个黑人,你很穷,你
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他妈的,你一钱不值”。她
反唇相向,发出振聋发聩的独立宣言:“我穷,我是个黑人,我
也许长得难看.... 不过我就在这里。”
西丽的独立从她离家出走开始。她跟随莎格来到孟菲斯,开始按自己的意愿从事。从学习做裤子到创立裤业公司,西丽完成了从人格到经济的完全独立,这标志着西丽最终摆脱了父权思想的束缚,成为独立自由
的新女性。
2、莎格对幸福生活的理解与追求莎格对生活有着独特的理解。她和西丽谈起“上帝是谁?” 在西丽眼中,上帝是个白人老头。可是,莎格说,上帝在你心里,你和上帝一起来到人间,但是只有在心里寻找它的人才能找到它。“上帝既不是她也不是他,而是它。”它不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当你因为有了这种想法而感到快乐的时候,你就找到它了。上帝喜欢有好东西大家一起享受。“你要是走过一块地没有注意到地里的紫颜色,上帝就会很生气。”当然,你眼睛里没有了男人,你才能看到一切。紫色代表高贵,代表美丽,代表平等,代表美好的生活。
三、完美大结局:男人与女人和谐幸福的生活影片的结局是圆满的。西丽最终战胜了思想和生活的枷锁,实现了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且与家人团圆,让人顿感从黑暗走向光明。索非亚与哈波的团聚,莎格与她父亲的相认,西丽的自醒都是圆满的。导演完全尊重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即寻求一种“献身于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主义”
在歧视与抗争中成长的黑人女性
在歧视与抗争中成长的黑人女性 电影《紫颜色》根据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同名小说拍摄,斯皮尔?伯格执导。由于电影体裁形式与小说不同,原作中通过语言载体传达的意韵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但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传递了沃克小说的主题精神,讲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黑人生活的状况,尤其是黑人女性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力下不屈的奋斗历程,指出了黑人种族通向幸福的道路。 一、身受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 1、种族歧视 故事发生在1909 年到1930 年前后的美国南部,美国黑人运动前夕,正值美国黑人遭受严重种族歧视,黑人种族意识不断觉醒时期。影片在不同场景中反映了当时黑人遭受歧视的生活状态。故事的主人公西丽的不幸就始于父亲被白人杀害。西丽的父亲原本是成功的买卖人,但由于受白人嫉妒,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恍惚间母亲再嫁,西丽就开始了悲惨的人生。婚后,西丽在百货商店遇到自己的亲生孩子(已经由一对牧师夫妇收养),白人店员的态度,充满鄙视。而剧中另一黑人女性索非亚也遭遇到种族歧视的折磨。索非亚原本开朗,勇敢,在拒绝做市长夫人的保姆后,其反抗导致了她的悲惨遭遇。变成了沉默寡言且跛足瞎眼,满头白发的老女人。她那一脸苍白,濒临死亡的形象与她以前的形象判若两人。白人市长夫人的蛮横、冷酷而又故作姿态尤其让人为当时的黑人扼腕叹息。圣诞节对信主的人是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和家团
圆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权利和愿望,可是被迫沦为白人女仆的索非亚却只有得到主人的恩典,才得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整天”的许诺对她是奢侈品,须臾片刻已是万幸。而强占他人的市长夫人却以为这已是天大的恩惠,这极具讽刺意味。种族歧视还延伸到黑人的祖籍地――非洲。西丽的妹妹耐蒂跟随牧师一家来到非洲传教,亲眼目睹了白人如何毁掉奥林卡人世代生存的丛林。白人殖民者强占了他们的土地,拆掉了他们的房屋,砍倒了给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奥林卡人流利失所,逃向密林深处。奥林卡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这让前去传教的耐蒂认识到上帝也帮不了忙。作者通过故事向非洲的延伸向人们展示了美国黑人的民族之根,提醒世人不要忽视黑人的民族传统。实际上,不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中,艾丽丝?沃克和斯皮尔?伯格都对这种民族传统给予重视,比如莎格头上的彩色翎羽,莎格演唱的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等都充满了非洲黑人民族色彩。这种黑人文化的回归体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文艺运动的思想,即“强调黑人文化的灵魂和传统,寻求黑人文化的自觉性”。 2、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只是故事的大背景,故事的焦点在于一群无助且受父权压制的黑人妇女。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讲述了以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妇女从奴隶走向独立的人生历程。性别歧视是压在黑人妇女身上的另一座大山。正如贝尔?胡克斯指出的“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在这种传统的父权思想影响下,黑人妇女大都忍气吞声,默默地承受。剧中主人公
哈莱姆文艺复兴背景下的新黑人女性成长三部曲-精选文档
哈莱姆文艺复兴背景下的新黑人女性成长三部曲 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又称黑人文艺复兴或者新黑人运动。大致起源于1919年, 1925至1928年间达到巅峰, 1932年逐渐停止,因发生于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黑人聚居区哈莱姆而得名。因其开创了一个民族回头探索自己过往历史的先例而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段文学繁盛时期还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及思想渊源,是这一时期黑人文学的发展出现相对沉默后的再度繁荣,是以被称作“哈莱姆文艺复兴”。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以往作品中塑造的汤姆叔叔型温顺的旧黑人艺术形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的精神,树立新黑人的形象,因此有人把这次文艺复兴称作新黑人文艺复兴(New Negro Renaissance)。 这一时期正值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宣告落幕。在这次运动中,“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1]这一时期的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表现出许多不同于黑人男性作家作品的特点,反映了黑人女性在白人主导和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积极构建种族身份、寻找女性自我的强烈愿望,她们的笔下呈现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女性形象。佐拉•尼尔•
赫斯顿既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她在 1937年发表的长篇代表作《他们眼望上帝》中塑造的黑人混血姑娘珍妮就成为新黑人女性的艺术经典。《他们眼望上帝》是赫斯顿第一部充分展示黑人女子内心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小说不仅打破了传统美国文学的禁区,也为后来黑人文学整体振兴铺平了道路。正如川大程锡麟教授所言,赫斯顿具有超前的女性主义意识,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完全不相适宜的[2]。 同时期的另一位美国男性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1908-1960)在1937年写的《他们眼望上帝》的书评中批评这部小说“没有主题、没有启示性、没有思想”。认为赫斯顿的作品只是风俗记事,描写了黑人的日常生活,毫无文学性。“在赖特阴影中赫斯顿和她的作品埋入了岁月的尘土之中,直到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发展壮大,才受到应有的重视。”[3]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出生于美国南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活跃分子,毕生为保持黑人文化传统而奋斗,是一位命运坎坷的非裔黑人女作家,从小浸润在丰富多彩的黑人民俗文化传统之中, 后师从美国人类学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博厄斯学习人类学,两次到南方进行民俗调查,所有这些孕育了赫斯顿强烈的黑人民俗文化意识,增强了她传播正宗的黑人民俗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她对20世纪许多黑人作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被包括艾丽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