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将考古学引入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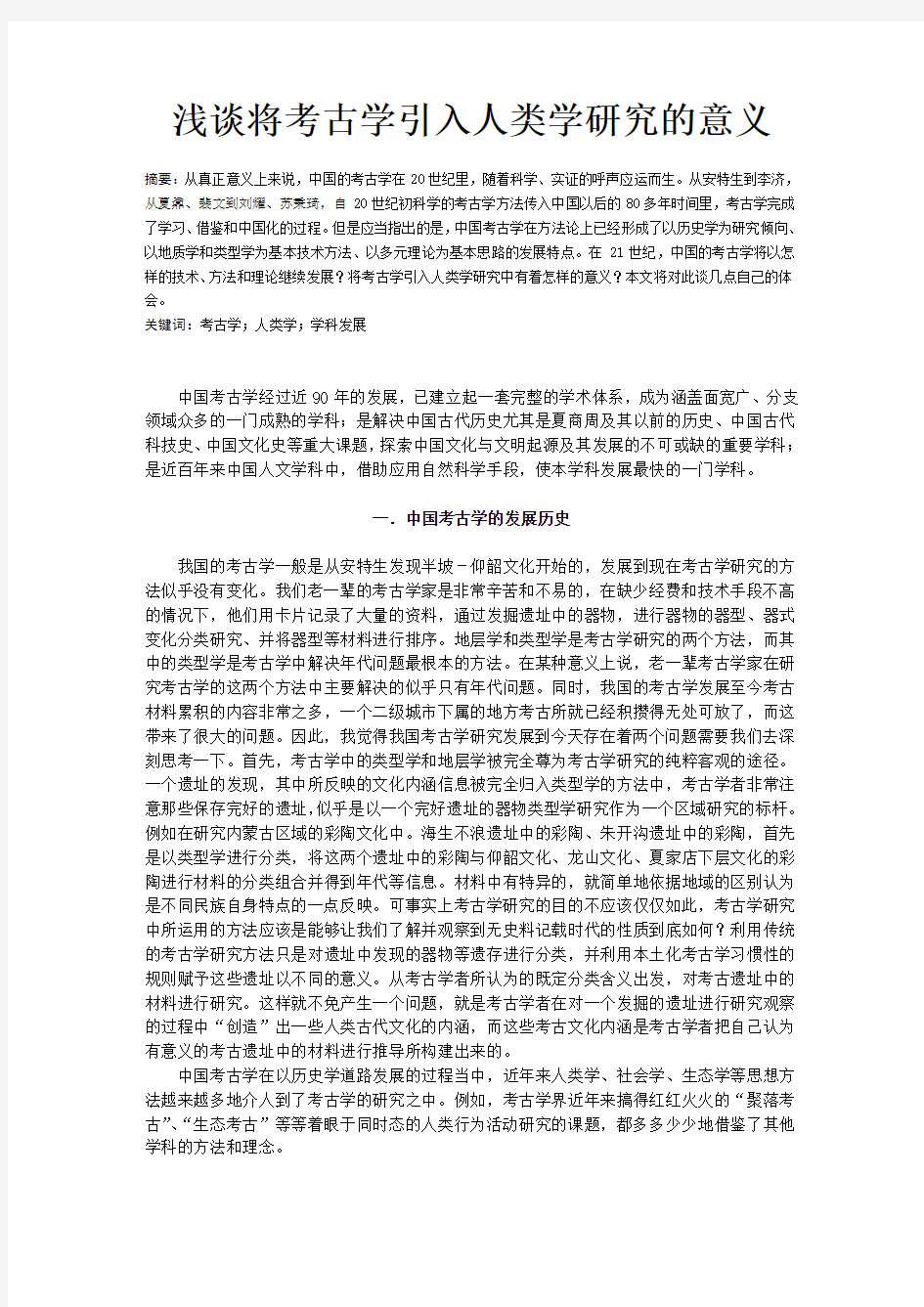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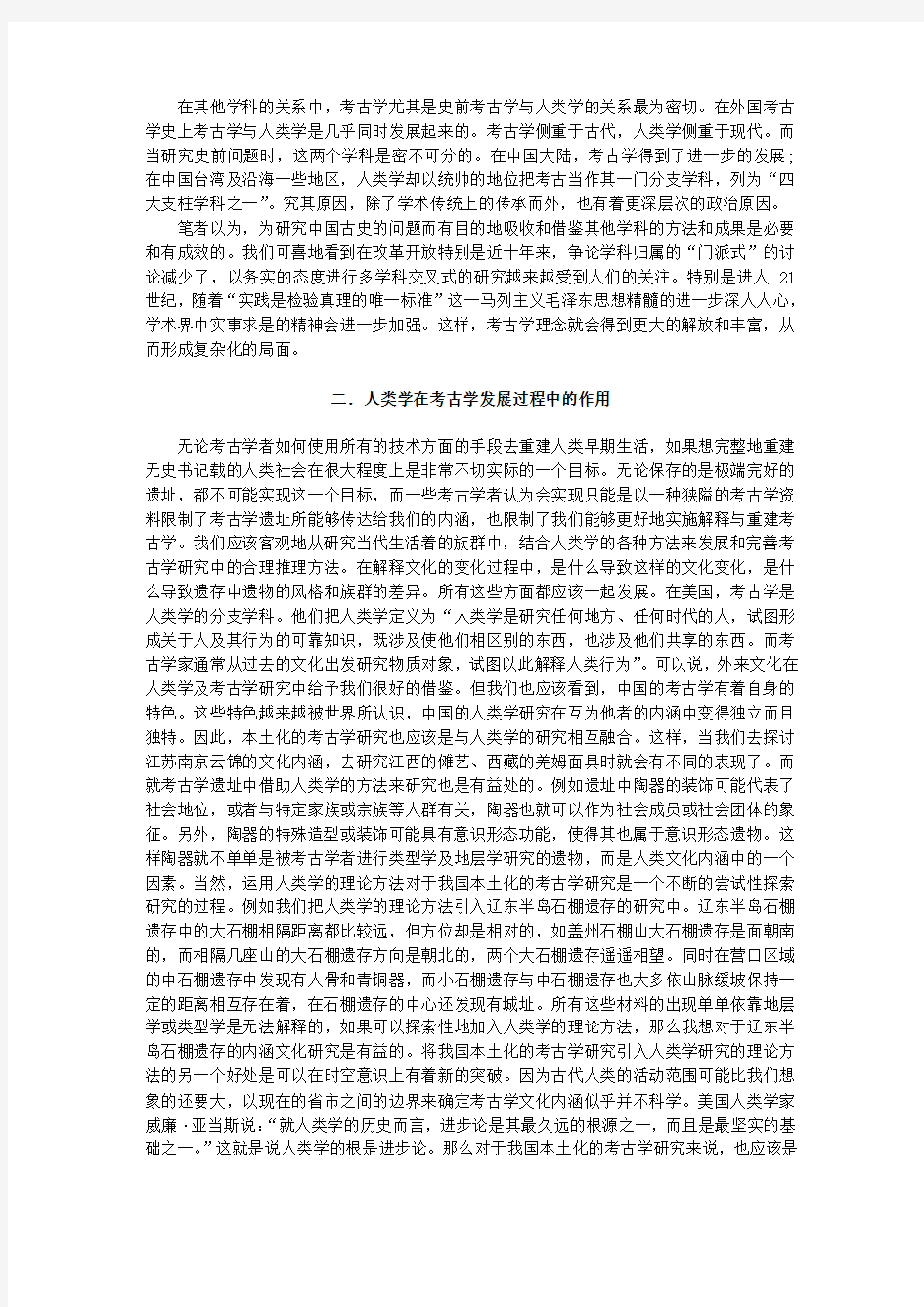
浅谈将考古学引入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摘要: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考古学在20世纪里,随着科学、实证的呼声应运而生。从安特生到李济,从夏鼐、裴文到刘耀、苏秉琦,自20世纪初科学的考古学方法传入中国以后的80多年时间里,考古学完成了学习、借鉴和中国化的过程。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考古学在方法论上已经形成了以历史学为研究倾向、以地质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技术方法、以多元理论为基本思路的发展特点。在21世纪,中国的考古学将以怎样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继续发展?将考古学引入人类学研究中有着怎样的意义?本文将对此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关键词:考古学;人类学;学科发展
中国考古学经过近90年的发展,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成为涵盖面宽广、分支领域众多的一门成熟的学科;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夏商周及其以前的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文化史等重大课题,探索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科中,借助应用自然科学手段,使本学科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考古学一般是从安特生发现半坡-仰韶文化开始的,发展到现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似乎没有变化。我们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是非常辛苦和不易的,在缺少经费和技术手段不高的情况下,他们用卡片记录了大量的资料,通过发掘遗址中的器物,进行器物的器型、器式变化分类研究、并将器型等材料进行排序。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两个方法,而其中的类型学是考古学中解决年代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老一辈考古学家在研究考古学的这两个方法中主要解决的似乎只有年代问题。同时,我国的考古学发展至今考古材料累积的内容非常之多,一个二级城市下属的地方考古所就已经积攒得无处可放了,而这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国考古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存在着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刻思考一下。首先,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和地层学被完全尊为考古学研究的纯粹客观的途径。一个遗址的发现,其中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信息被完全归入类型学的方法中,考古学者非常注意那些保存完好的遗址,似乎是以一个完好遗址的器物类型学研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的标杆。例如在研究内蒙古区域的彩陶文化中。海生不浪遗址中的彩陶、朱开沟遗址中的彩陶,首先是以类型学进行分类,将这两个遗址中的彩陶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陶进行材料的分类组合并得到年代等信息。材料中有特异的,就简单地依据地域的区别认为是不同民族自身特点的一点反映。可事实上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如此,考古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应该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并观察到无史料记载时代的性质到底如何?利用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只是对遗址中发现的器物等遗存进行分类,并利用本土化考古学习惯性的规则赋予这些遗址以不同的意义。从考古学者所认为的既定分类含义出发,对考古遗址中的材料进行研究。这样就不免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考古学者在对一个发掘的遗址进行研究观察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些人类古代文化的内涵,而这些考古文化内涵是考古学者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考古遗址中的材料进行推导所构建出来的。
中国考古学在以历史学道路发展的过程当中,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思想方法越来越多地介人到了考古学的研究之中。例如,考古学界近年来搞得红红火火的“聚落考古”、“生态考古”等等着眼于同时态的人类行为活动研究的课题,都多多少少地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念。
在其他学科的关系中,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在外国考古学史上考古学与人类学是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侧重于古代,人类学侧重于现代。而当研究史前问题时,这两个学科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大陆,考古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台湾及沿海一些地区,人类学却以统帅的地位把考古当作其一门分支学科,列为“四大支柱学科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学术传统上的传承而外,也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笔者以为,为研究中国古史的问题而有目的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是必要和有成效的。我们可喜地看到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争论学科归属的“门派式”的讨论减少了,以务实的态度进行多学科交叉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进人21世纪,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进一步深人人心,学术界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会进一步加强。这样,考古学理念就会得到更大的解放和丰富,从而形成复杂化的局面。
二.人类学在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无论考古学者如何使用所有的技术方面的手段去重建人类早期生活,如果想完整地重建无史书记载的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目标。无论保存的是极端完好的遗址,都不可能实现这一个目标,而一些考古学者认为会实现只能是以一种狭隘的考古学资料限制了考古学遗址所能够传达给我们的内涵,也限制了我们能够更好地实施解释与重建考古学。我们应该客观地从研究当代生活着的族群中,结合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来发展和完善考古学研究中的合理推理方法。在解释文化的变化过程中,是什么导致这样的文化变化,是什么导致遗存中遗物的风格和族群的差异。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一起发展。在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他们把人类学定义为“人类学是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试图形成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可靠知识,既涉及使他们相区别的东西,也涉及他们共享的东西。而考古学家通常从过去的文化出发研究物质对象,试图以此解释人类行为”。可以说,外来文化在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中给予我们很好的借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考古学有着自身的特色。这些特色越来越被世界所认识,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在互为他者的内涵中变得独立而且独特。因此,本土化的考古学研究也应该是与人类学的研究相互融合。这样,当我们去探讨江苏南京云锦的文化内涵,去研究江西的傩艺、西藏的羌姆面具时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了。而就考古学遗址中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也是有益处的。例如遗址中陶器的装饰可能代表了社会地位,或者与特定家族或宗族等人群有关,陶器也就可以作为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的象征。另外,陶器的特殊造型或装饰可能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使得其也属于意识形态遗物。这样陶器就不单单是被考古学者进行类型学及地层学研究的遗物,而是人类文化内涵中的一个因素。当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国本土化的考古学研究是一个不断的尝试性探索研究的过程。例如我们把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辽东半岛石棚遗存的研究中。辽东半岛石棚遗存中的大石棚相隔距离都比较远,但方位却是相对的,如盖州石棚山大石棚遗存是面朝南的,而相隔几座山的大石棚遗存方向是朝北的,两个大石棚遗存遥遥相望。同时在营口区域的中石棚遗存中发现有人骨和青铜器,而小石棚遗存与中石棚遗存也大多依山脉缓坡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存在着,在石棚遗存的中心还发现有城址。所有这些材料的出现单单依靠地层学或类型学是无法解释的,如果可以探索性地加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那么我想对于辽东半岛石棚遗存的内涵文化研究是有益的。将我国本土化的考古学研究引入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在时空意识上有着新的突破。因为古代人类的活动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以现在的省市之间的边界来确定考古学文化内涵似乎并不科学。美国人类学家威廉·亚当斯说:“就人类学的历史而言,进步论是其最久远的根源之一,而且是最坚实的基础之一。”这就是说人类学的根是进步论。那么对于我国本土化的考古学研究来说,也应该是
不断进步的,在理论方法的运用;遗存、遗物材料等现象的分类排序方法上;借鉴并融合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应该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只有这样,我国本土化的考古学研究才能更加深入发展,能够完成考古学的根本目的———探索并解决“在华夏文明之初的过去是怎么样的”。
三.小结
20世纪80年代,以苏秉琦、张忠培为代表的学术范式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爱国主义教育为基本内核的“中国考古学派”理论。这一理论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以区系类型、谱系理论和六大版块理论为框架的知识体系。
我认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在理论结构上除了以马列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以外,还应该强调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方面,是中国的史学传统。这一点不仅在历史时期的考古中十分必要,而且在史前时代的考古中也是应该强调的。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历史文物,不可避免地会有强烈的民族倾向。
第二方面,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视野。在研究中注重与国外材料的比较、学习和借鉴适合中国研究现状的方法。
对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现代化问题,我以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表现在考古学方法论上,就是要分清楚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侧重方向。在方法上学习和借鉴,形成交叉型、开放型的学科特色的同时还应该坚守和形成自己的学术领地。
参考文献:
[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一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第1版。
[2]李光漠《锄头考古学家的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英]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安志敏校《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4][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俞伟超《世纪之交话考古(五)》,《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7日
第三版。
[6]张忠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中国考古学—走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7]杨建华《赤峰东山嘴遗址布局分析及其相互关系》,《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
[8]李季《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摘要》,《考古》2001年第2期。
[9]张忠培《考古学的局限性》,《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10]例如二a.赵辉《考古中的地面及其清理》,《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
b.段天爆《基点·地面·层面—田野考古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 1999年6月19日第三版;
c.王炜林《考古地层学及其作用小议》,《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11]a.滕铭予(((中国地下文物基本情况数据库)数据说明》,《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b.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资料的信息化处理与(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年第6期。
[12][美l罗伯特·W·普鲁塞尔《考古学理论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年5月第1版。
[13]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吉林大学出版,1995年8月第1版。
[14]张光直《“浊大计划”与1972至1974年浊大流域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9月第1版。
[15]苏秉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考古》199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