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典芹: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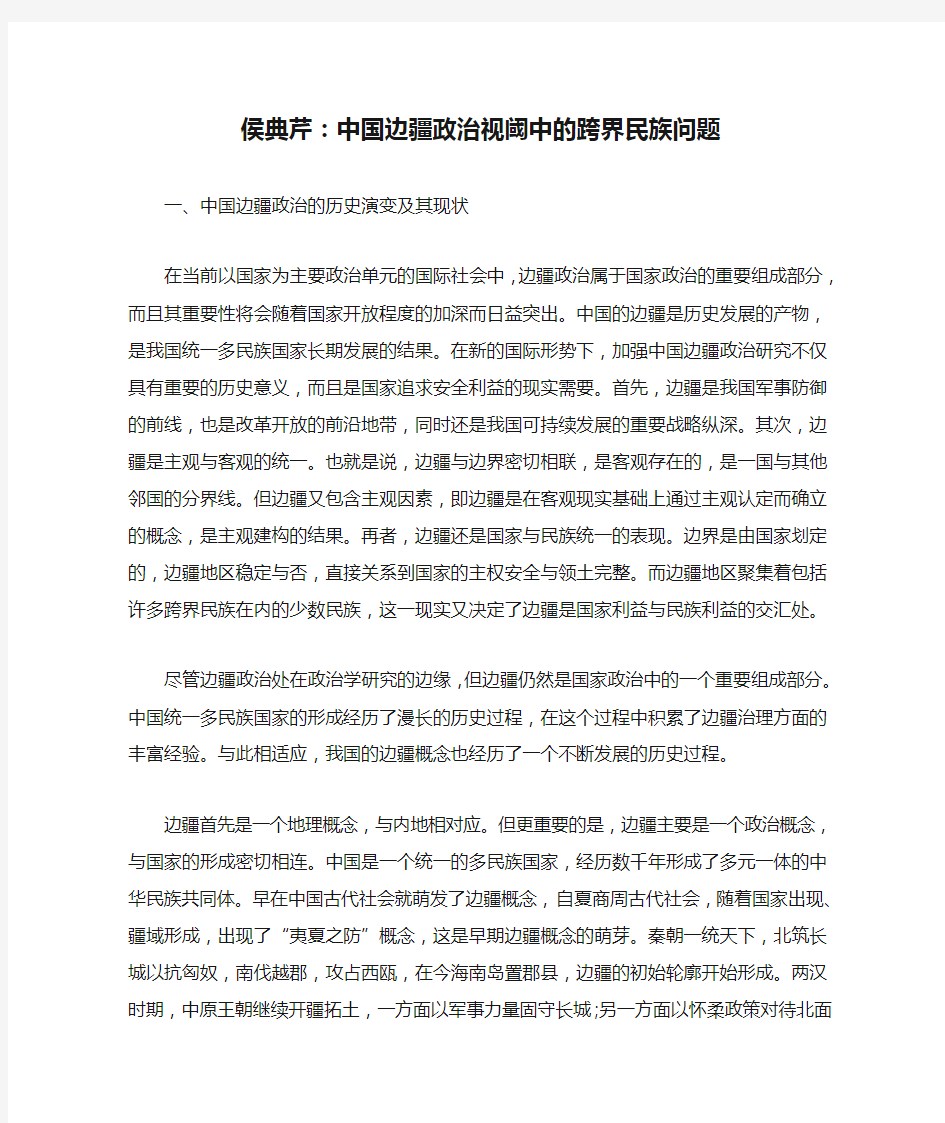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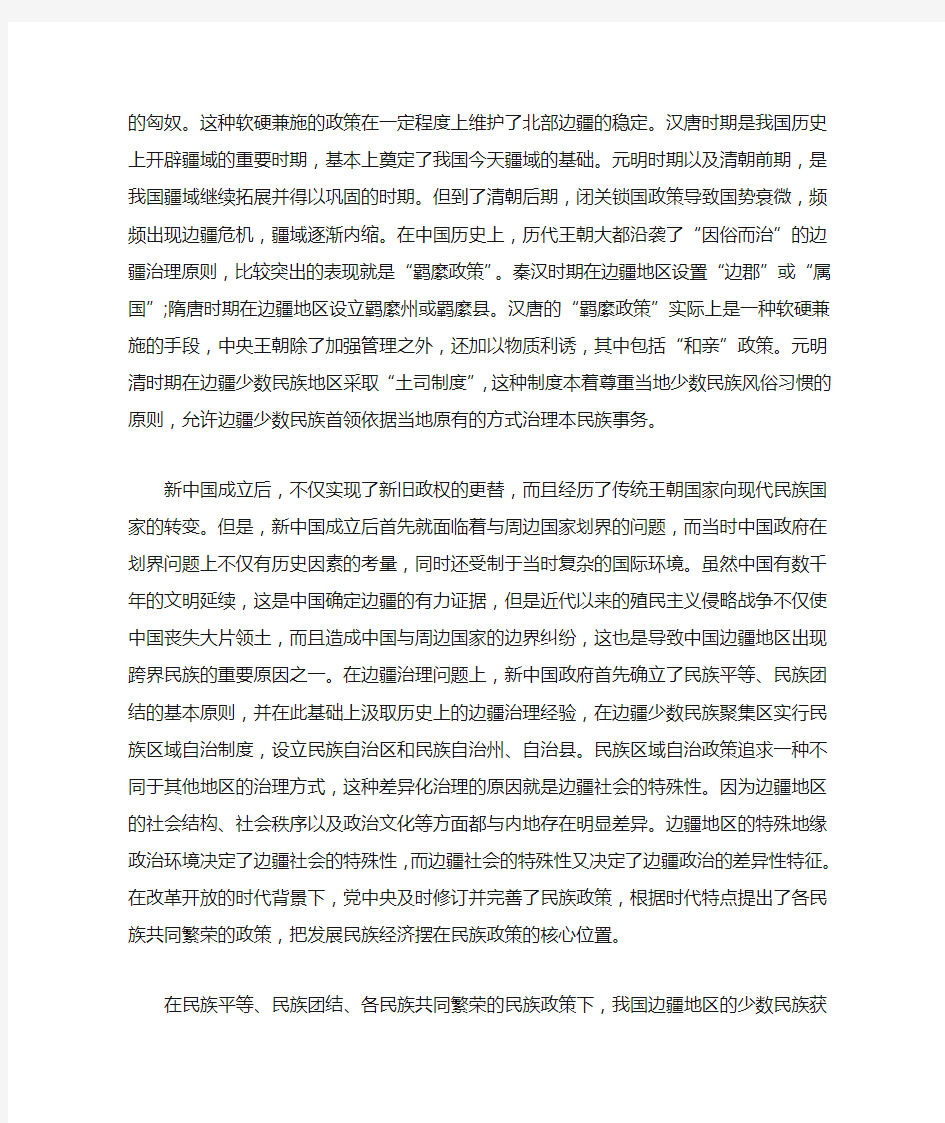
侯典芹: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
在当前以国家为主要政治单元的国际社会中,边疆政治属于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将会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加深而日益突出。中国的边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是国家追求安全利益的现实需要。首先,边疆是我国军事防御的前线,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同时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纵深。其次,边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说,边疆与边界密切相联,是客观存在的,是一国与其他邻国的分界线。但边疆又包含主观因素,即边疆是在客观现实基础上通过主观认定而确立的概念,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再者,边疆还是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表现。边界是由国家划定的,边疆地区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而边疆地区聚集着包括许多跨界民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这一现实又决定了边疆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交汇处。
尽管边疆政治处在政治学研究的边缘,但边疆仍然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边疆治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此相适应,我国的边疆概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
展的历史过程。
边疆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与内地相对应。但更重要的是,边疆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连。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数千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萌发了边疆概念,自夏商周古代社会,随着国家出现、疆域形成,出现了“夷夏之防”概念,这是早期边疆概念的萌芽。秦朝一统天下,北筑长城以抗匈奴,南伐越郡,攻占西瓯,在今海南岛置郡县,边疆的初始轮廓开始形成。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继续开疆拓土,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固守长城;另一方面以怀柔政策对待北面
的匈奴。这种软硬兼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汉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开辟疆域的重要时期,基本上奠定了我国今天疆域的基础。元明时期以及清朝前期,是我国疆域继续拓展并得以巩固的时期。但到了清朝后期,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国势衰微,频频出现边疆危机,疆域逐渐内缩。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大都沿袭了“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原则,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羁縻政策”。秦汉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置“边郡”或“属国”;隋唐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羁縻州或羁縻县。汉唐的“羁縻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中央王朝除了加强管理之外,还加以物质利诱,其中包括“和亲”政策。元明清时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土司制度”,这种制度本着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的原则,允许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依据当地原有的方式治理本民族事务。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实现了新旧政权的更替,而且经历了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就面临着与周边国家划界的问题,而当时中国政府在划界问题上不仅有历史因素的考量,同时还受制于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虽然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延续,这是中国确定边疆的有力证据,但是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不仅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而且造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纠纷,这也是导致中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边疆治理问题上,新中国政府首先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历史上的边疆治理经验,在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民族自治区和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追求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治理方式,这种差异化治理的原因就是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因为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与内地存在明显差异。边疆地区的特殊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边疆社会的特殊性,而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边疆政治的差异性特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及时修订并完善了民族政策,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把发展民族经济摆在民族政策的核心位置。
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下,我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自治权利,拥有民族发展、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自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边疆少数民族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大好机遇,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统计,从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少数民族地区的GDP增长达到10.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以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以来,他们充分利用跨界民族的特殊身份到韩国打工或经商,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总之,历史上形成了以中原汉族为中心、以周边少数民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版图。这种民族分布格局意味着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属于边疆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就是边疆民族问题,因而中国的民族政治实质就是边疆政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边疆地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跨界民族问题逐渐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中国跨界民族的分布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全面开放格局,国内、国际层面的跨界民族问题日益凸显,跨界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一个焦点。由于学术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关于“跨界民族”的概念问题仍有争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跨界民族”,有的从历史视角分析“跨界民族”,有的从形成原因来描述“跨界民族”,有的从跨界民族居住环境的政治地理现状进行定义。较早关注跨界民族问题的金春子、王建民等人认为,跨界民族既是指“紧靠边界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分居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又指在相邻国家的边界附近地区活动的那些同一民族。多数跨界民族分布地区是连在一起的,也有少数同一民族之间可能会有其他民族相隔,居住地没有直接相连”。吴鹏认为,“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刘稚总结了跨界民族的三个基本特征:历史上形成的原生形态民族;同一民族的人们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其最后得出结论: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葛公尚先生认为,跨界民族就是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它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特征:一是该民族被政治边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集地被政治疆界所分割。曹兴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对跨界民族进行了分析:狭义上讲就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吻合而跨国界居住
的民族;广义上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隔、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主动积极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尽管上述关于跨界民族的描述各不相同,审视的角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跨界民族因跨国界而分居在不同国家,这是跨界民族的基本现实要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形成了汉族聚居中心、少数民族大多聚居边疆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改变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也导致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许多跨界民族。中国在2.2万多公里的陆路边界线上与15个国家接壤,其中14个国家与中国拥有跨界民族。我国境内共有31个跨界民族,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西部和西南等边疆地区。
在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都属于跨界民族,他们分别居住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边疆地带,与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国等三国接界。朝鲜族是跨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居住的跨界民族;蒙古民族是跨中国、蒙古、俄罗斯而居的跨界民族;赫哲族(俄罗斯那乃族)、鄂温克族(俄罗斯埃文克族)、鄂伦春族等,则是跨中、俄边境而居的跨界民族。
在我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有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共6个跨界民族。除维吾尔族以外,其他5个跨界民族的主体都在境外。
在西部边陲,我国西藏自治区分别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接壤。中国除与巴基斯坦没有跨界民族外,与其他几国均有跨界民族。藏族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四国而居,其中绝大部分在中国;门巴族跨中国、不丹两国而居;珞巴族则跨中国、印度两国而居。在西南和南方,我国云南、广西两省与越南、缅甸和老挝三国接壤,这两省的跨界民族有17个,分别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和京族。除了京族是跨海疆而居的跨界民族外,其余16个都是跨陆地边界的跨界民族。其中,壮族(越南称岱依族、侬族)、布依族是跨中、越两国的跨界民族;景颇族(缅甸称克钦族)、怒族、阿昌族、独龙族、德昂族是跨中、缅两国的跨界民族;彝族是跨中、越、老三国的跨界民族;佤族、傈僳族均系跨中、缅、泰三国的跨界民族;布朗族跨中、缅、老三国而居;苗族、瑶族、哈尼族、拉祜族则是跨中、老、越、缅、泰五国而居的跨界民族;傣族是一个分布更广泛的跨界民族,跨中、老、越、缅、泰和印度六国而居。此外,还有在中国尚未确认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也是跨中、老、越、柬、缅、泰六国而居的共同体,在越南和老挝称之为“克目族”或“高目族”,其他国家均称之为克木人。
我国的跨界民族分布十分广泛,遍布从东北到西北、从西部
到西南的边疆地区。这些少数民族曾为我国的政权建设和边疆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边疆地区不仅是我国的边防前线,而且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同时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使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通过从事跨国经贸活动,跨界民族的经济收入迅速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的民族政策使边疆少数民族得到全面发展。但是中国的许多跨界民族,其主体在邻国,频繁的边境贸易活动使得我国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受到一
定削弱,同时可能会强化其民族认同意识。由于跨界民族问题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趋向,因此往往被某些国家和势力所利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外敌对势力以及国内的一些犯罪分子,有时利用跨界民族的特殊地位从事危害我国安全利益的活动,或进行跨国犯罪活动,给我国的政治安全和边疆稳定造成巨大威胁。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周边经济贸易活动迅速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很多问题通过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表现出来。当前,严重损害我国安全利益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除“疆独”和“藏独”势力外,“三蒙统一”势力也值得注意。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为“蒙古民主党”的组织提出“三蒙统一”,主张以蒙古国为中心,把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
共和国合并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这种思想显然受到了冷战结束以来泛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另外,在边疆跨界民族聚集地区,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包括偷渡、走私、贩毒、跨国犯罪、非法的跨国婚姻等。这些现象在各跨界民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三、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边疆政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边疆
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边疆与边界密切相连,边界是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边界的稳固也是国家领土完整的象征。同时,边界又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因为它涉及到与其他邻国的关系,所以“边界具有自己的地缘政治意义,它与权力和立国理由紧密相联,并可以在地面上划出来:它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如果想做的话,它可以变成一道严整的篱笆,无须考虑其他非地缘政治的变量”。边界的特殊政治意义使得边疆地区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十分突出。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发展趋势,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事业,对外交往日益频繁,跨界民族问题也不断出现,其在中国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安全是主权国家的首要基本利益,只有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才能谈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国家安全利益本身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而且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其外延也随着经济与社会的日益发展而不断扩大。领土完整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边疆安全尤为重要。边疆政治首先关注边疆安全与稳定,因为边疆安全不仅事关边疆地区的稳定,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边疆地区是各种利益交汇之处,包括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多数民族的利益和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央政府的利益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等。正是多种利益的交汇,使得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政治领域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跨界民族而言,国家政治边界形成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分隔线。但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单元的国际体系下,“现行政治疆界不变”、“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等国际关系理论或准则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应该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不能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来满足某个民族的个体利益。
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跨界民族跨国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直接影响到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而威胁国家的领土完整。跨界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同一个民族跨国界分居在不同的国家。而国界是一个国家领土的最外沿,它是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重要象征。因此,跨界民族问题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边疆安全密切相联。从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我国的民族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国家安全与边
疆稳定的高度关注。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来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
自治则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是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前提性理论。由于中国边疆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从而决定了中国边疆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民族政策。我国2.2万公里的陆路边界线,民族自治地方占1.9万公里;全国135个边境县,民族自治地方占107个。我国边疆安全与少数民族尤其是跨界民族的重要关系可见一斑。
我国的跨界民族与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又具有不同之处,尤其是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基本特征,使得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边疆政治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从国内政治方面来看,跨界民族问题事关我国的边疆安全、政治稳定和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一方面,我国跨界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边疆少数民族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边界两边的跨界民族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在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些边境地区的跨界民族利用身份和居住环境的便利条件,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和贸易活动,但也有不法之徒利用这种便利进行违法活动,甚至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破坏活动。比如中亚地区以“东突”为代表的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向我国新疆地区渗透,甚至多次派人潜入新疆进行暴恐活动。这不仅严重影响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威胁我国的领土安全和边疆政治稳定,对边疆地区
各族民众的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造成巨大损害。
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造成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也主要表现为“冷战”、“对峙”。在这种情形下,跨界民族之间的来往受到很大限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我国逐步实施并扩大对外开放,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与邻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传统安全的地位有所下降,非传统安全的地位上升。近来,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跨界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日益突出。在我国跨界民族较多的云南省,因为靠近世界三大毒品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直接影响到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金三角”位于缅甸、泰国、老挝三国交界处,不仅三国各自国内社会矛盾丛生,而且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尖锐,再加上这里有掸族、佤族、佬族、苗族、瑶族、克钦族、傈僳族、拉祜族、阿卡(哈尼)族、汉族等十几个跨界民族,国家间人员来往频繁,居民的国家和国籍观念淡漠。因此,“金三角”地区的现状有其历史的、地理的、经济和文化的因素,更有民族的因素,特别是大量跨界民族的存在。此外,该地区存在的跨国婚姻问题、偷渡问题、贩毒问题等,也会影响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全。
除了上述这些突出的安全问题以外,还存在一些潜在性问题。在一些欠发达的边疆地区,由于跨界民族分居在两个甚至更多的国家,相互之间存在一种暗自“攀比”的杠杆。当所在国的民族政策正确、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跨界民族的
境遇不断得到改善时,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基本上能够达成统一。否则,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与国家归属感就不一致,跨界民族的民族观念往往会超过国家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跨国婚姻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边疆地区的稳定,影响到我国跨界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以中国朝鲜族为例,自中韩建交以后,许多朝鲜族女青年通过各种渠道到韩国打工或经商,确实有一些年轻女性留在韩国,与韩国人结婚。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2年,中国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婚姻件数为54799件,占当时中国朝鲜族女性总数的20%。在朝鲜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延边自治州,1993-2001年间的涉外婚姻共有18885件,其中朝鲜族妇女18000人。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共同体的稳固。
第二,跨界民族问题影响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一方面,跨界民族问题可能会引起地缘政治的紧张态势;反过来,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有可能引发跨界民族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不能把跨界民族与地缘政治划等号。因为这里还要进一步从概念上区分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问题,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当然,跨界民族是产生跨界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有跨界民族就一定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是现存国家分隔力的产物,但跨界民族问题不单纯是现存国家分隔力的产物,而是现存国家政治分隔力和民
族向心力这两种相反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不仅如此,边疆地区还是一国的边界所在地区,边界的另一边就是其他国家。“边界不仅仅是指一国的边缘区域,而且还是不同政治体之间的交接地带,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区域国家权力网络密度较低,影响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还面临来自外部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克格勃人员煽动我国新疆地区的边民外逃,严重影响了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跨界民族问题属于民族问题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民族问题,至少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民族问题。跨界民族的特殊身份以及特殊的居住环境,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与地缘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与跨国关系密切相联。从某种意义上说,跨界民族问题也往往构成地缘政治的重要内容。葛公尚先生认为,跨界民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诱发地缘政治问题,从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利益:跨界民族通过国家的分隔力来影响地缘政治;跨界民族相互之间的联合力既产生了传统
民族的向心力,同时又造成了对相关国家的离心力,从而影响地缘政治;跨界民族诱发危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从而影响一个国家地缘政治中综合国力对比的格局;邻国跨界民族的相
互声援往往导致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此外,跨界民族通过泛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地缘政治。苏联解体后,中亚五个国家获得独立,民族意识迅速高涨。哈萨克斯坦为了弥补人口缺失
的问题,号召境外哈萨克族“回归故乡”。由哈萨克斯坦发起的这场“回归”运动在我国的哈萨克族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不仅影响了我国哈萨克族的发展,而且催化了中亚其他国家大民族主义的发展。这可能会对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影响该地区的地缘政治。
第三,从全球视野来看,随着中国逐渐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也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战略利益考虑,更加关注中国崛起后的未来发展方向,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巨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区、国际、教育等诸多领域相互纠缠在一起。”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美这对双边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状况。”但是,美国必然首先维护自身的全球霸权利益,当下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然有针对中国的成分。从近几年发生的南海争端、东海钓鱼岛事件以及台湾问题不难看出,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美国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利用全球化发展之势,高唱“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让渡”的论调,推行新干涉主义,借助民族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很难说美国不会利
用跨界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进而在战略上制衡中国。
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边疆稳定,为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国家必须加强边疆治理。作为国家的边防前哨,边疆地区除了加强和巩固“军”和“民防”外,更要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外,国家还要加强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加强对跨界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在国际层面上,我们要秉承“亲、诚、惠、容”的外交新理念,积极创造“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新格局,为我国边疆的稳定创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上海合作组织的良好运行充分表明,中、俄与中亚国家积极发展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有利于各国共同应对跨界民族问题。我们应积极推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合作共赢”新理念取代传统的“零和博弈”理念,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浅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一)
浅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一) 论文关键词:跨界民族;他者;认同;国际关系 论文摘要:民族认同是民族的自觉行为,表现为一种归属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最为敏感。因此,要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特别吸引世人眼球的国际社会现象,即围绕着民族有关的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地区争端或冲突,而且随着历史的继续演进,这些地区冲突有着进一步加剧之趋势。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冲突一方面涉及到“冷战期间被认为已经或趋于消失而在冷战结束后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焦点之一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还涉及到认同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存在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问题的地方更是如此。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Ethnic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政治范畴中的“边界或国界”。“边界或国界”一方面包含了作为社会文化层面的民族的地理居住地,这种居住地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为政治领域的民族的领土分界,这种分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为此,有学者将跨界民族定义为“那些原发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而在地域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见,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模式而言,“有的是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更多的国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发展(如外国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强迫手段)”。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所谓民族国家,即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变为‘国家’的政治形态。”它暗示了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什么是认同(Identity)?这是一个困扰学术界很久的难题,西方学者将它认为是无所不在同时又含义模糊的重要概念。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很难对其下一个科学和准确的定义,但是大家却一直都在高频率地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学术界围绕对认同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退。总结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述,但还是有这样一些共同或共通的地方,即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俞正梁则认为认同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共同特性基础上的、区别于他者的共有身份与形象,以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有两个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内生的认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认同,二是社会建构的认同,即自我与他者通过互动所造就的认同。” 由此可见,可以这样来对认同进行理论界定:(1)认同的发生首先是基于自我和他者的比较,在某种条件下上升为一种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差异或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并且这种差异或差别也获得他者的体认;(2)认同涉及的内容有形象、身份、符号、记忆、文化、传说和历史,并且表现为一种社会心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3)认同是一种心理意识,其表现形态取决于自我和他者对具体情势的认知、比照和判断,这种心理意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传承性;(4)认同并非是单一形态,通常是以复合形态出现在各种问题领域中的,且复合形态下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以上的界定为我们探讨跨界民族的认同提供基本的理论分析路径。我们以跨界民族认同的内容为标准,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等类型,显然,深入探讨这些认同的属性对深入理解和解决跨界民族问题提供必需的理论基础,是大有裨益的。 1民族认同 民族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认同在民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构成民族的六大要素之一。
跨界民族的类型
跨界民族的类型、属性及其发展趋势 刘稚 【专题名称】民族问题研究 【专题号】D5 【复印期号】2004年12期 【原文出处】《云南社会科学》(昆明)2004年05期第89~93页 【英文标题】On the Typ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LIU Zhi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Kunming,Yunnan,650034,China) 【作者简介】刘稚(1957-),女,云南昆明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云南昆明650034 【内容提要】作者对跨界民族定义、类型和性质、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与发展趋势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跨界民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一种是文化人类学范 畴的人们共同体;跨界民族的属性取决于该民族与国家结合的形式,不同类型的跨界民族有不同的 发展趋势。 The author discusses on such theoretical issues as definition. type,nature,course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She thinks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nowaday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one is human community in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and the other is human community in the category ot cultural anthropology.The nature of a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 depends on the form of combination of the group with the nation.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s. 【关键词】跨界民族/属性类型/发展趋势Cross-border ethnic group/Nature/Type/Development trend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4)05-0089-05 一、关于跨界民族的属性和定义 跨界民族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人们共同体的民族范畴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范畴交错重叠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一般来说,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构成了民族国家,但是由于民族过程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方向、范围不完全一致,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政治疆界不吻合的现象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大小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族多,国家少;多民族国家多,单一民族国家少。有人曾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上132个国家的民族结构进行过分析,发现在这些国家中,真正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仅有12个,约占9.1%,其他120个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其中拥有一个占本国人口50%以上的多数民族的国家有81个,约占国家总数的61.3%。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构不成多数民族的国家有39个,约占国家总数的29.5%。在这132个国家中,包含5个以上民族的国家达53个。[1]这种国家疆域与民族分布地域的交错重叠,使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即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个国家多种民族和一种民族多个国家,而后两种形式更为普遍,而且往往存在于同一区域,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民族的传统居住地域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割,成为跨国界而居的民族。 关于跨界民族的定义,学术界至今聚讼纷纭,而问题的症结首先在于如何定义“民族”,因为“跨界民族”是人们用“跨界”这一地理分布特点来修饰“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概念而形成的特定范畴,耍弄清什么是跨界民族,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族。笔者认为,正如对“民族”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一样,“跨界民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其存在和发展趋势取决于各国的民族过程、历史发展、民族观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要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来界定、解释世界各国、各地区所有的跨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跨界民族与边疆治理问题研究
中国民族报/2015年/11月/20日/第008版 理论周刊?纵深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跨界民族与边疆治理问题研究 刘稚 建设“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核心内涵在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地缘相邻、历史人文交往悠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为战略依托,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地缘政治新格局,打造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我国拥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与14个国家接壤,有30多个民族跨国界而居;相关各国边疆地区地处“一带一路”建设的通道前沿和关键枢纽,既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基地,同时也是国家间、区域间地缘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地缘战略利益交织、竞争的复杂地带。在全球化、区域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周边国家边疆民族问题的外溢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及“一带一路”建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有鉴于此,以国际视野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相关各国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本文试就“一带一路”视野下跨界民族与边疆治理问题的研究意义和主要内容提出一些见解。 一、研究价值和意义 有助于对跨界民族和边疆治理问题进行分类指导 从跨界民族与边疆治理的关系来看,我国拥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与14个国家接壤;从东北鸭绿江起,北至黑龙江、内蒙古,西至新疆、西藏,西南到云南、广西,在陆路边境地区有30多个民族跨国界而居。作为世界上邻国和跨界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跨界民族与中国的边疆问题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是影响我国边疆治理的重要因素,族际政治、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边疆问题和形势的面貌和走向。然而,由于跨界民族类型不同、境外同一民族情况不同,族际政治、地缘政治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各国各边疆地区治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有所不同。 在东北方向上,我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三国接壤,有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等5个跨界民族。蒙古族是跨中国、蒙古和俄罗斯三国的跨界民族,而且蒙古国是蒙古族的主权国家,蒙古族在中国和俄罗斯均有政治实体(共和国、自治区与自治州),以“三蒙统一”为号召的大蒙古主义对东北亚的政治稳定有潜在的影响。朝鲜半岛是朝鲜族主体聚居之地,目前又有两个主权国家:朝鲜和韩国。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及“大高丽主义”的喧嚣对东北地缘安全和我国朝鲜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西北方向上,我国的新疆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国接壤,其间存在着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7个跨界民族,其中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主体均在国外,且建有主权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主要受中亚的影响。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边疆民族问题具有“高政治”性。 在西南方向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大多数跨界民族主体在境内,且境外基本上不存在跨界民族政治实体。因此,西南方向上跨界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毒品、艾滋病泛滥、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族际政治、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边疆问题和形势的面貌,因此边疆治理的政策措施只有根据各地区跨界民族类型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侯典芹: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侯典芹: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 在当前以国家为主要政治单元的国际社会中,边疆政治属于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将会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加深而日益突出。中国的边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结果。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中国边疆政治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是国家追求安全利益的现实需要。首先,边疆是我国军事防御的前线,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同时还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纵深。其次,边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说,边疆与边界密切相联,是客观存在的,是一国与其他邻国的分界线。但边疆又包含主观因素,即边疆是在客观现实基础上通过主观认定而确立的概念,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再者,边疆还是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表现。边界是由国家划定的,边疆地区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而边疆地区聚集着包括许多跨界民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这一现实又决定了边疆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交汇处。 尽管边疆政治处在政治学研究的边缘,但边疆仍然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边疆治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此相适应,我国的边疆概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
展的历史过程。 边疆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与内地相对应。但更重要的是,边疆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连。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数千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萌发了边疆概念,自夏商周古代社会,随着国家出现、疆域形成,出现了“夷夏之防”概念,这是早期边疆概念的萌芽。秦朝一统天下,北筑长城以抗匈奴,南伐越郡,攻占西瓯,在今海南岛置郡县,边疆的初始轮廓开始形成。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继续开疆拓土,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固守长城;另一方面以怀柔政策对待北面 的匈奴。这种软硬兼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汉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开辟疆域的重要时期,基本上奠定了我国今天疆域的基础。元明时期以及清朝前期,是我国疆域继续拓展并得以巩固的时期。但到了清朝后期,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国势衰微,频频出现边疆危机,疆域逐渐内缩。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大都沿袭了“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原则,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羁縻政策”。秦汉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置“边郡”或“属国”;隋唐时期在边疆地区设立羁縻州或羁縻县。汉唐的“羁縻政策”实际上是一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中央王朝除了加强管理之外,还加以物质利诱,其中包括“和亲”政策。元明清时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土司制度”,这种制度本着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