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
读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的几点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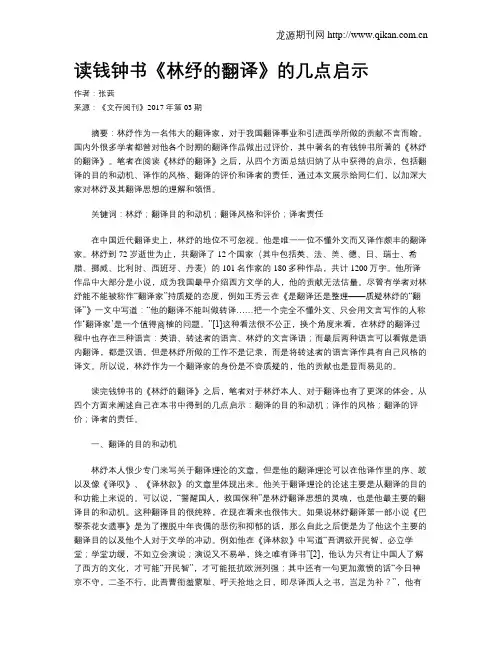
读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的几点启示作者:张茜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3期摘要:林纾作为一名伟大的翻译家,对于我国翻译事业和引进西学所做的贡献不言而喻。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曾对他各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做出过评价,其中著名的有钱钟书所著的《林纾的翻译》。
笔者在阅读《林纾的翻译》之后,从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从中获得的启示,包括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译作的风格、翻译的评价和译者的责任,通过本文展示给同仁们,以加深大家对林纾及其翻译思想的理解和领悟。
关键词:林纾;翻译目的和动机;翻译风格和评价;译者责任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林纾的地位不可忽视。
他是唯一一位不懂外文而又译作颇丰的翻译家。
林纾到72岁逝世为止,共翻译了12个国家(其中包括英、法、美、德、日、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丹麦)的101名作家的180多种作品,共计1200万字。
他所译作品中大部分是小说,成为我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学的人,他的贡献无法估量。
尽管有学者对林纾能不能被称作“翻译家”持质疑的态度,例如王秀云在《是翻译还是整理——质疑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他的翻译不能叫做转译……把一个完全不懂外文、只会用文言写作的人称作‘翻译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这种看法很不公正,换个角度来看,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也存在三种语言:英语、转述者的语言、林纾的文言译语;而最后两种语言可以看做是语内翻译,都是汉语,但是林纾所做的工作不是记录,而是将转述者的语言译作具有自己风格的译文。
所以说,林纾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身份是不容质疑的,他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读完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之后,笔者对于林纾本人、对于翻译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在本书中得到的几点启示:翻译的目的和动机;译作的风格;翻译的评价;译者的责任。
一、翻译的目的和动机林纾本人很少专门来写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但是他的翻译理论可以在他译作里的序、跋以及像《译叹》、《译林叙》的文章里体现出来。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翻译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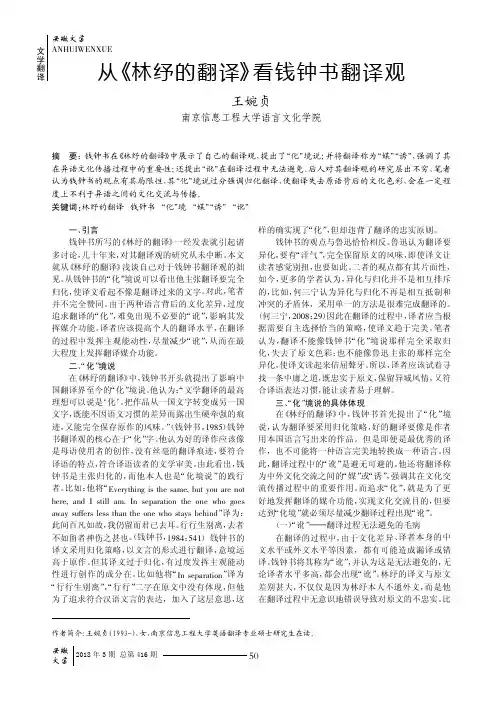
安徽文学ANHUIWENXUE 安徽文学2018年3期总第416期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翻译观王婉贞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摘要: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展示了自己的翻译观,提出了“化”境说;并将翻译称为“媒”“诱”,强调了其在异语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还提出“讹”在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
后人对其翻译观的研究层出不穷,笔者认为钱钟书的观点有其局限性,其“化”境说过分强调归化翻译,使翻译失去原语背后的文化色彩,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异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关键词院林纾的翻译钱钟书“化”境“媒”“诱”“讹”作者简介:王婉贞(1993-),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一、引言钱钟书所写的《林纾的翻译》一经发表就引起诸多讨论,几十年来,对其翻译观的研究从未中断。
本文就从《林纾的翻译》浅谈自己对于钱钟书翻译观的拙见。
从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看出他主张翻译要完全归化,使译文看起不像是翻译过来的文字。
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
由于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过度追求翻译的“化”,难免出现不必要的“讹”,影响其发挥媒介功能。
译者应该提高个人的翻译水平,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尽量减少“讹”,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翻译媒介功能。
二、“化”境说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开头就提出了影响中国翻译界至今的“化”境说。
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钱钟书,1985)钱钟书翻译观的核心在于“化”字。
他认为好的译作应该像是母语使用者的创作,没有丝毫的翻译痕迹,要符合译语的特点,符合译语读者的文学审美。
由此看出,钱钟书是主张归化的,而他本人也是“化境说”的践行者。
比如:他将“Everything is the same,but you are not here,and I still am.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译为: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
英汉互译国内著名翻译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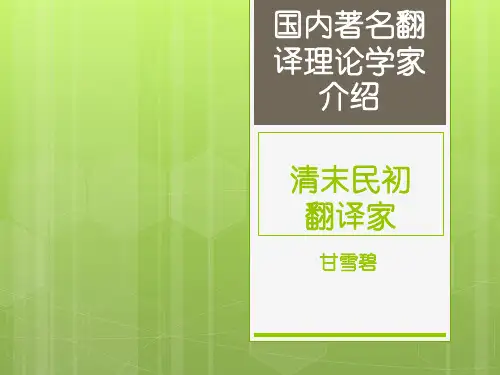
主要作品:
梁启超一生译介的西方书籍,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 克思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小说)。他流亡 日本后,对传播欧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流 派等特别感兴趣,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抉破罗网,造 出新思想。” 梁启超是提倡翻译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对于政治小说, 1898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首先大力提 倡翻译西洋政治小说,提高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这篇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呼唤我国 文学翻译高潮到来的先声。
主要作品:
十大著名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
《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吟边燕语》、《拊掌录》、《迦茵小传》、 《离恨天》、《现身说法》、《块肉余生述》、 《不如归》。 林纾被称为“译界之王”、“译才并世数严 林”,不懂外文,由别人在旁边口译,他边听 边以古文写作;30多人协助他口译,译出包括 英、美、法等十多国家的作品近200部。
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过程这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形似意似神似的理论问题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实质这实质上又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所谓等值的翻译理论无毫发出入应该是译者的最高追求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要求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达到所谓等效翻译的效果
主要作品:
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有
《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 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 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
翻译思想:
一、将翻译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马建忠谙熟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科学与文化。甲午战争 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提倡变法自强。欲知己知彼就必须全力发展翻译事业。。他 认为:第一,“翻译书院之设专以造就译才为主”,马氏所 说的造就“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的译才, 绝非一般外交外贸等洋务“通事”“舍人”之才,而是造就 担当翻译西学书籍,传播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肩负改造 社会重任的“国家栋梁之才”。 第二,译书乃“知己知彼” 之举,马建忠将应译之事拟分为三类:一是各国的时政,二 是居官者考订之书,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书。马建忠,其译 书主张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 要“知己知彼”,把西学的 “精髓”译介到中国来,维新自强,启迪民智,共赴救亡图 存大业。
林纾的翻译和近代文学思潮

第2 5卷 第 3期
新乡学院学报 ( 会科学版 ) 社
Jun f ix n nvrt( oi cecsE io ) o ra o ni gU i sy Sca S i e dt n l X a ei l n i
Jr 2 1 ua 0 1 .
Vo . 5 N . 12 o 3
一
、
林纾 其人
林纾 (82—12 ), 15 94 字琴南 , 号畏庐 , 自号冷 红生 , 晚年称补柳翁 、 践卓翁 , 福建 闽县人。林纾幼 年家境贫寒 , 靠母亲 、 姐姐做女工度 日。他幼 而好 学 , 闻强 记 , 博 自幼 嗜 书如命 ,熟 读 《 史记 》 《 、 左
传》 《 、汉书》 及唐宋名家作 品, 练就了一手优雅 、 凝 练 的中 国古文文 笔 。后林 纾 因家 中祖父 母 、 亲相 父 继去世 , 忧伤成疾 , 常咯血 , 但他仍刻苦学习 , 这一切 为林纾以后的创作 和翻译打下 了坚实 的基础。 林纾的功名道路并不顺畅 , 七次进京参加礼部 试, 皆未 得 中 。后 以教 书为 业 , 北京 任 中学教 员和 在 京 师大学 堂 教 习。林 纾 的性 格 刚 强 易怒 , 时怒 斥 时 他人 , 别人 甚感 难 堪 , 许 多 人 因 此 而与 他 疏 远 。 令 有 正 如他 自己所 说 :家贫 而 貌 寝 , 木强 多 怒 。 但 是 “ 且 ” 当别人有危难时 , 林纾却不惜奔走救助。林纾 的挚 友 王灼三 、 述庵 早逝 , 纾 毅然 把他 们 的孤儿 收养 林 林 在家十多年 , 衣食训诲备 至, 恩养一如 己子 , 亲授古 文 、 词。 诗 19 8 7年 , 纾 的夫 人 刘 琼 姿 病 逝 , 纾 时年 4 林 林 6 岁 。丧偶对 他刺 激很 大 , 他忧 郁难遣 。次年夏 天 , 林 纾 认识 了从 法 国归 来 的 王 寿 昌。 王 寿 昌对 他 说 : “ 吾请 与子 译一 书 , 可 以破 岑 寂 , 子 吾亦 得 以介 绍 一 名 著 于 中国 , 大胜 于蹙 额对 坐 耶 ? 于是 二 人 合译 法 ” 国小 仲马 的《 黎茶 花 女 遗 事 》 巴 。这 部 译 作 由 于 内 容新鲜 , 译笔凄婉且有情致 , 一时之间风靡海内。严 复说 :可怜一卷《 “ 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肠。 l1 , ”l J 翻译《 巴黎 茶花女 遗 事》 的大 获 成 功 , 开启 了林纾 的
浅析林纾翻译的历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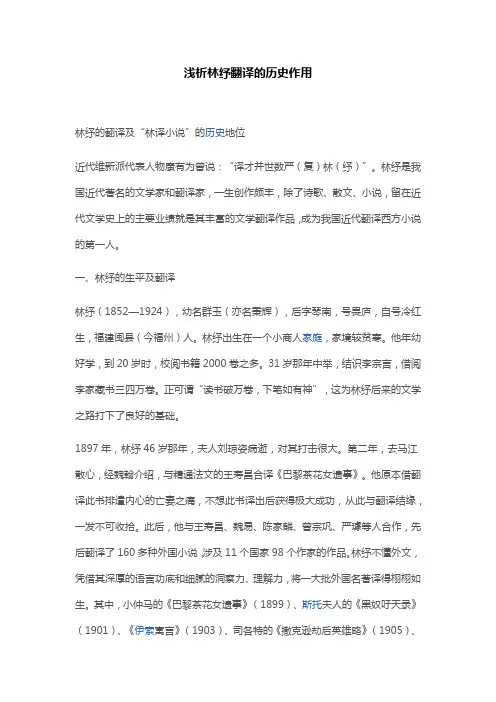
浅析林纾翻译的历史作用林纾的翻译及“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复)林(纾)”。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一生创作颇丰,除了诗歌、散文、小说,留在近代文学史上的主要业绩就是其丰富的文学翻译作品,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
一、林纾的生平及翻译林纾(1852—1924),幼名群玉(亦名秉辉),后字琴南,号畏庐,自号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
林纾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家境较贫寒。
他年幼好学,到20岁时,校阅书籍2000卷之多。
31岁那年中举,结识李宗言,借阅李家藏书三四万卷。
正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为林纾后来的文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97年,林纾46岁那年,夫人刘琼姿病逝,对其打击很大。
第二年,去马江散心,经魏翰介绍,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他原本借翻译此书排遣内心的亡妻之痛,不想此书译出后获得极大成功,从此与翻译结缘,一发不可收拾。
此后,他与王寿昌、魏易、陈家麟、曾宗巩、严璩等人合作,先后翻译了160多种外国小说,涉及11个国家98个作家的作品。
林纾不懂外文,凭借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细腻的洞察力、理解力,将一大批外国名著译得栩栩如生。
其中,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1901)、《伊索寓言》(1903)、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05)、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906)、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1908),十分具有代表性。
二、“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林纾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革时期。
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对林纾刺激很深,虽然他和翻译结缘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骨子里涌动着一股爱国热情的他最终走上外国文学的翻译殿堂却也有其必然性。
他与其妻刘琼姿感情甚笃,失妻后内心之痛易与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产生共鸣,加之借题发挥,译风飘逸哀婉、清新隽永,大受欢迎。
英汉翻译中的林纾现象

林纾现象林纾的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他不懂外语,由别人口授,46岁才开始译书,却译了184种,达一千万字以上。
“林译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
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
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那么,让我们来“玩味”一下,林译小说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可以从林译小说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从林纾的生平和林纾小说中,至少有六点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1.刻苦攻读,功底深厚林纾从幼年起就好学。
少年时家贫,无钱买书。
他到处搜罗求借。
有一次他在叔父家看到《毛诗》、《尚书》、《左传》、《史记》等书,就借来反复细读。
八岁便知发奋苦读,十一岁起即读欧阳修文、杜诗、《左传》、《史记》、《汉书》。
到十三岁时,已读书数万卷。
他自己说过,他曾用八年时间读《汉书》,八年时间读《史记》,至于韩愈的文章,前后用了四十年。
为了激发自己发奋苦读,他曾在墙壁上画了一口棺材,敞着盖,旁边画了一个人,写了两句话:“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他还说过:“果以明日死者,今日固已饱读吾书。
”他幼年启蒙于薜则柯先生。
薜的古文造诣很深,推崇欧阳修的文章和杜甫的诗。
林纾从师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
文学的深厚根基,为他后来的高速度翻译打下了基础。
他文笔洒脱,日写七八千字,翻译时,“耳听手追,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
2.源于原著,优于原著英国翻译家Arthur Waley认为“林纾翻译的迭更司作品优于原著”(《书林》1982年1 期)。
林译为什么“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读”呢?许渊冲先生把林译跟另外两位翻译大家董秋斯、张谷若所译的《大卫·科波菲尔》三个译本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林译富有文采”。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节选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节选英译
·文艺之窗·162余光中《翻译与创作》节选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节选英译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1 张栋【摘要】:余光中与钱钟书都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二人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在我国翻译史上影响深远。
余光中认为,翻译须用纯净的中文。
以散文形式写译论,熔知性和感性于一炉。
钟书则梳理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提出了在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化境”说。
【关键词】:余光中 翻译与创作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1 余光中《翻译与创作》 原文:翻译原是一种“必要之恶”,一种无可奈何的代用品。
好的翻译已经不能充分表现原作,坏的翻译在曲解原作之余,往往还会腐蚀本国文学的文体。
三流以下的作家,或是初习创作的青年,对于那些生硬,拙劣,甚至不通的“翻译体”,往往没有抗拒的能力,濡染既久,自己的“创作”就会向这种翻译体看齐。
译文: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necessary evil” originally, it’s not an alternative succedaneum. Even a good translating work can’t express the meaning of original work sufficiently, the bad translating work not only misinterpret the original work’s meaning ,but also do harm to the literaryform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hird rate writer and below ,or the youth at the beginning of leaning creation ,they don’t have the resist ability to the rigid、unskilled、and even unsmooth translating work. With the long-time influence of this kind of work ,their own translating work will follow this kind of translating work ‘s footsteps ,and be similar to this kind of translating work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原文: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浅谈《林纾的翻译》
浅谈《林纾的翻译》作者:王晓锐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7年第09期【摘要】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大家,其一生建树颇多,在译学方面也拥有杰出造诣。
本文通过浅析《林纾的翻译》一文,对钱钟书“化”、“讹”、“诱”三个主要翻译观点进行解读,且对其间接提出的译者所应具备的部分素质进行挖掘、借鉴。
【关键词】《林纾的翻译》化讹诱译者素质钱钟书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史上名震国际的大学者。
他既晓畅中国古经典籍,又精通多种语言与学术,著有《围城》、《管锥编》等重要作品,被盛誉为“文化昆仑”。
其实,关于译学的研究仅是钱钟书巍峨学识中的冰山一角,却在我国译学界熠熠生辉,影响巨大。
钱钟书所作《林纾的翻译》一文,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的翻译思想。
在该文章之初,钱钟书便巧妙引用了《说文解字》中的一段关于翻译的训诂来展开下文。
“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钱钟书利用这段丰富的意蕴,将翻译的最高境界“化”,难于避免的毛病“讹”以及所起的作用“诱”,都一一展示出来了。
第一点是“化”。
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但同时,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换言之,钱钟书只把“化”作为译者理应追求的翻译的最高境界,而非必须实现,且由于主客观因素,根本也不可能实现。
第二点是“讹”。
由于“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因此,译文在意义和口吻上总有失真之处,这就是“讹”。
在该文章中,钱钟书还进一步指明了“讹”的类别。
林纾和他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 事实。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 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 二岁时的大发现,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 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 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 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 探险小说。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 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 文文笔高明得多。”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 吾来十五年, 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 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 辱我令我肝肠颤!”
——林译 那格女士先狂笑而后嘤然以泣,为状至辛楚动人。疾呼曰:“十 五年来吾为此楼上下增光匪少。邀天之佑。”——言及此,力顿其左 足,复力顿其右足,顿且言曰:“吾未尝一日遭辱。胡意今日为此婢 所卖!其用心诡鄙极矣!其行事实玷吾侪,知礼义者无勿耻之。吾憎 之贱之,然而吾心伤矣!吾心滋伤矣!”
《剑底鸳鸯》,英司各特著,林纾、魏易合译(1907) 《神枢鬼藏录》[12],阿瑟毛利森(Arthur Morrison)原著。林纾、魏易合 译 《旅行述异》,英国华盛顿·欧文,林纾、魏易合译 《大食故宫余载》即《阿尔罕伯拉》,英国华盛顿·欧文,林纾、魏易合译 《空谷佳人》,英国博兰克巴勒著,林纾、魏易合译(1907) 《双孝子喋血酬恩记》,英国大隈克司蒂穆雷著,林纾、魏易合译 《孤星泪》,法国嚣俄(雨果)著,林纾、魏易合译(1907) 《旅行述异》,英国华盛顿·欧文,林纾、魏易合译(1907) 《爱国二童子传》,法国沛那,林纾、李世中合译(1907) 《花因》,几拉德原著,林纾、魏易合译(1907) 《藕孔避兵录》,菲利浦斯•奥本海姆原著,林纾、魏易合译 《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英国狄更斯,林纾、魏易合译(1908) 《贼史》,即《孤雏泪》英国狄更斯,林纾、魏易合译 《块肉余生录》,即《大卫·科波菲尔》,英国狄更斯,林纾、魏易合译 《块肉余生述后编》,英国狄更斯,林纾、魏易合译(1908) 《夏洛克奇案开场》,即推理小说《福尔摩斯》中的《血字的研究》,英柯 南达利著。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钱钟书翻译观
[钱钟书翻译观浅析]钱钟书翻译观钱钟书作为中国20世纪以睿智和博学著称的国学大师,不仅深谙中国古典文化,而且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也有着深刻的见解。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钱钟书的影响从学术界、知识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并在国内外形成了“钱学”这一文化现象。
本文从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着手介绍了其“化境”翻译观极其影响。
一、钱钟书小传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十岁在无锡东林小学就读,十三岁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他读书过目不忘,幼年时读了许多古代小说,并能流畅无碍的背出其中章节。
1929年,十九岁的钱钟书被破格录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突出。
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至1938年在欧洲留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围城》;翌年出版《谈艺录》。
1949年后,在清华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
1998年,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化境”翻译观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林纾的翻译》――钱钟书1、“化境”“化境”是钱钟书1964 年在一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的翻译主张,颠覆了以“信”为基本的传统翻译主张,开创了以追求“美”为标准的现代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的翻译思想,也为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2、“化境”在《林纾的翻译》中的体现文章开始,钱钟书叙述了许慎在《说文解字•诂林》的一节中关于翻译的话:�,译也。
从“口”,化“声”。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是同一个字。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林纾的翻译——钱锺书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1]。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
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3]。
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4],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
“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
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6]。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
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
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
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Uebelsetzer sind als geschaftige Kuppler anzusehen)——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抬高了它的声价[7]。
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得仔细、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
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法国十七世纪德·马露尔神父(Abbe de Marolles)的翻译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e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erams of against Martial)[8]。
许多人都能从自己的阅读经验里找出补充的例子。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9]。
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
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10]。
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
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四十年前[11],在我故乡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
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追寻。
因为翻来覆去地阅读,我也渐渐对林译发生疑问。
我清楚记得这个例子。
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第五章结尾刻意描写鳄鱼和狮子的搏斗,对小孩子说来,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紧张得使他眼瞪口开、气也不敢透的。
林纾译文的下半段是这样:“然狮之后爪已及鰐鱼之颈,如人之脱手套,力拔而出之。
少须,狮首俯鰐鱼之身作异声,而鰐鱼亦侧其齿,尚陷入狮股,狮腹为鰐所咬亦几裂。
如是战斗,为余生平所未睹者。
”狮子抓住鳄鱼的脖子,决不会整个爪子象陷在烂泥里似的,为什么“如人之脱手套”?鳄鱼的牙齿既然“陷入狮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狮腹”。
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家里的大人也解答不来。
而且这场恶狠狠的打架怎样了局?谁输谁贏,还是同归于尽?鳄鱼和狮子的死活,比起男女主角的悲欢,是我更关怀的问题。
书里并未明白交代,我真觉得心痒难搔,恨不能知道原文是否照样糊涂了事[12]。
我开始能读原文,总先找林纾译过的小说来读。
后来,我的阅读能力增进了,我也听到舆论指摘林译的误漏百出,就不再而也不屑再看它。
它只成为我生命里累积的前尘旧蜕的一部分了。
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
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
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一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一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
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当然,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也不失为一种消遣。
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
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象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13]。
但是,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举一两个例来说明。
《滑稽外史》第一七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险些气破肚子,回到缝纫室里,披头散发,大吵大闹,把满腔妒愤都发泄在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她手下的许多女孩子也附和着。
林纾译文里有下面的一节:“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
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
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这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逗得读者都会发笑。
我们忙翻开迭更司原书(第一八章)来看,颇为失望。
略仿林纾的笔调译出来,大致不过是这样:…“那格女士先狂笑而后嚶然以泣,为状至辛楚动人。
疾呼曰:…十五年来,吾为此楼上下增光匪少。
邀天之祐‟——言及此,力顿其左足,复力顿其右足,顿且言曰:…吾未尝一日遭辱。
胡意今日为此婢所卖!其用心诡鄙极矣!其行事实玷吾侪,知礼义者无勿耻之。
吾憎之贱之,然而吾心伤矣!吾心滋伤矣!‟”那段“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
他一定觉得迭更司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
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承认林纾颇能表达迭更司的风趣,但从这个例子看来,他不仅如此,而往往是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14]。
不妨从《滑稽外史》里再举一例,见于第三三章(迭更司原书第三四章):“司圭尔先生……顾老而夫曰:…此为吾子小瓦克福……君但观其肥硕,至于莫能容其衣。
其肥乃曰甚,至于衣缝裂而铜钮断。
‟乃按其子之首,处处以指戟其身,曰:…此肉也。
‟又戟之曰:…此亦肉,肉韧而坚。
今吾试引其皮,乃附肉不能起。
‟方司圭尔引皮时,而小瓦克福已大哭,摩其肌曰:…翁乃苦我!‟司圭尔先生曰:…彼尚未饱。
若饱食者,則力聚而气张,虽有瓦屋,乃不能閟其身。
……君试观其泪中乃有牛羊之脂,由食足也。
”这一节的译笔也很生动。
不过迭更司只写司圭尔“处处戟其身”,只写他说那胖小于若吃了午饭,屋子就关不上门,只写他说儿子眼泪是油脂(oillness),什么“按其子之首”、“力聚而气张”、“牛羊之脂,由食足也”等等都出于林纾的锦上添花。
更值得注意的是,迭更司笔下的小瓦克福只“大哭摩肌”,没有讲话。
“翁乃苦我”这句怨言是林纾凭空穿插进去的,添个波折,使场面平衡;否则司圭尔一个人滔滔独白,他儿子那方面便显得呆板冷落了。
换句话说,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
不由我们不联想起他崇拜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过去记传的润色或增饰[15]。
林纾写过不少小说,并且要采用“西人哈葛德”和“迭更先生”的笔法来写小说[16]。
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
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
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
方才引的一节算是改得好的,上面那格女士带哭带唱的一节就有问题。
那格确是一个丑角,这场哭吵也确有做作矫饰的成分。
但是,假如她有腔无调地“讴歌”起来,那显然是在做戏,表示她的哭泣压根儿是假装的,她就制造不成紧张局面了,她的同伙和她的对头不会把她的发脾气当真了,不仅我们读着要笑,那些人当场也忍不住要笑了。
李贽评论《琵琶记》[17]里写考试那一出说:“太戏!不象!”又说:“戏则戏矣,倒须似真,若真反不妨似戏也。
”林纾的改笔夸张过火,也许不失为插科打诨的游戏文章,可是损害了入情入理的写实,正所谓“太戏!不象!”了。
大家一向都知道林译删节原作,似乎没注意它也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增补原作。
这类增补,在比较用心的前期林译里,尤其在迭更司和欧文的译本里,出现得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