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社会发展角度解读梅丽迪恩对自我身份的追寻
从“迷失自我”到“彰显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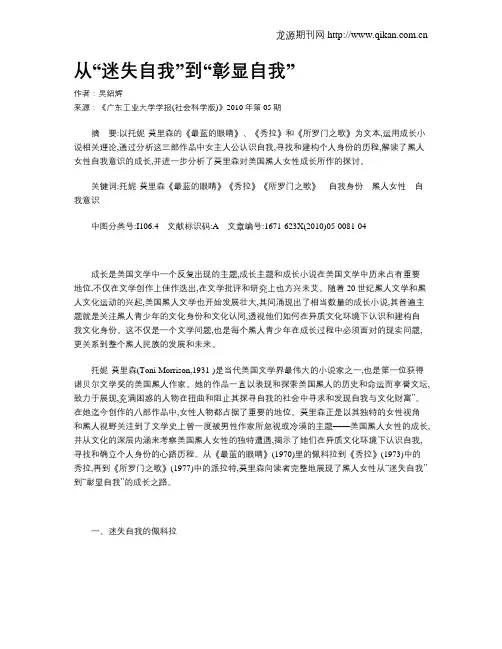
从“迷失自我”到“彰显自我”作者:吴绍辉来源:《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5期摘要:以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为文本,运用成长小说相关理论,通过分析这三部作品中女主人公认识自我,寻找和建构个人身份的历程,解读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并进一步分析了莫里森对美国黑人女性成长所作的探讨。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自我身份黑人女性自我意识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0)05-0081-04成长是美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成长主题和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迭出,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上也方兴未艾。
随着20世纪黑人文学和黑人文化运动的兴起,美国黑人文学也开始发展壮大,其间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成长小说,其普遍主题就是关注黑人青少年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透视他们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下认识和建构自我文化身份。
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每个黑人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关系到整个黑人民族的发展和未来。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
她的作品一直以表现和探索美国黑人的历史和命运而享誉文坛,致力于展现,充满困惑的人物在扭曲和阻止其探寻自我的社会中寻求和发现自我与文化财富”。
在她迄今创作的八部作品中,女性人物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莫里森正是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黑人视野关注到了文学史上曾一度被男性作家所忽视或冷漠的主题——美国黑人女性的成长,并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考察美国黑人女性的独特遭遇,揭示了她们在异质文化环境下认识自我,寻找和确立个人身份的心路历程。
从《最蓝的眼睛》(1970)里的佩科拉到《秀拉》(1973)中的秀拉,再到《所罗门之歌》(1977)中的派拉特,莫里森向读者完整地展现了黑人女性从“迷失自我”到“彰显自我”的成长之路。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认知失调的自我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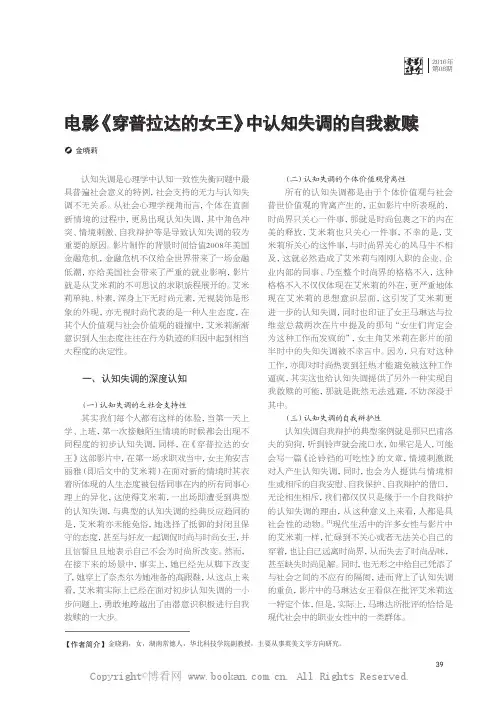
2016年第08期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中认知失调的自我救赎认知失调是心理学中认知一致性失衡问题中最具普遍社会意义的特例,社会支持的无力与认知失调不无关系。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而言,个体在直面新情境的过程中,更易出现认知失调,其中角色冲突、情境刺激、自我辩护等是导致认知失调的较为重要的原因。
影片制作的背景时间恰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给全世界带来了一场金融低潮,亦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就业影响,影片就是从艾米莉的不可思议的求职旅程展开的。
艾米莉单纯、朴素,浑身上下无时尚元素,无视装饰是形象的外现,亦无视时尚代表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在其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碰撞中,艾米莉渐渐意识到人生态度往往在行为轨迹的归因中起到相当大程度的决定性。
一、 认知失调的深度认知(一)认知失调的乏社会支持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第一天上学、上班,第一次接触陌生情境的时候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初步认知失调,同样,在《穿普拉达的女王》这部影片中,在第一场求职戏当中,女主角安吉丽雅(即后文中的艾米莉)在面对新的情境时其衣着所体现的人生态度被包括同事在内的所有同事心理上的异化,这使得艾米莉,一出场即遭受到典型的认知失调,与典型的认知失调的经典反应趋同的是,艾米莉亦未能免俗,她选择了抵御的封闭且保守的态度,甚至与好友一起调侃时尚与时尚女王,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不会为时尚所改变。
然而,在接下来的场景中,事实上,她已经先从脚下改变了,她穿上了奈杰尔为她准备的高跟鞋,从这点上来看,艾米莉实际上已经在面对初步认知失调的一小步问题上,勇敢地跨越出了由潜意识积极进行自我救赎的一大步。
(二)认知失调的个体价值观背离性所有的认知失调都是由于个体价值观与社会普世价值观的背离产生的,正如影片中所表现的,时尚界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时尚包裹之下的内在美的释放,艾米莉也只关心一件事,不幸的是,艾米莉所关心的这件事,与时尚界关心的风马牛不相及,这就必然造成了艾米莉与刚刚入职的企业、企业内部的同事、乃至整个时尚界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不仅仅体现在艾米莉的外在,更严重地体现在艾米莉的思想意识层面,这引发了艾米莉更进一步的认知失调,同时也印证了女王马琳达与拉维兹总裁两次在片中提及的那句“女生们肯定会为这种工作而发疯的”,女主角艾米莉在影片的前半时中的失知失调被不幸言中。
无声告白读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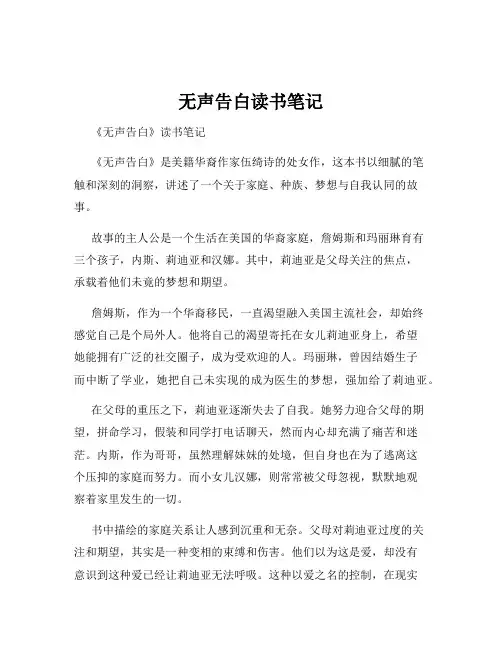
无声告白读书笔记《无声告白》读书笔记《无声告白》是美籍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处女作,这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庭、种族、梦想与自我认同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家庭,詹姆斯和玛丽琳育有三个孩子,内斯、莉迪亚和汉娜。
其中,莉迪亚是父母关注的焦点,承载着他们未竟的梦想和期望。
詹姆斯,作为一个华裔移民,一直渴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却始终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
他将自己的渴望寄托在女儿莉迪亚身上,希望她能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子,成为受欢迎的人。
玛丽琳,曾因结婚生子而中断了学业,她把自己未实现的成为医生的梦想,强加给了莉迪亚。
在父母的重压之下,莉迪亚逐渐失去了自我。
她努力迎合父母的期望,拼命学习,假装和同学打电话聊天,然而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迷茫。
内斯,作为哥哥,虽然理解妹妹的处境,但自身也在为了逃离这个压抑的家庭而努力。
而小女儿汉娜,则常常被父母忽视,默默地观察着家里发生的一切。
书中描绘的家庭关系让人感到沉重和无奈。
父母对莉迪亚过度的关注和期望,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束缚和伤害。
他们以为这是爱,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爱已经让莉迪亚无法呼吸。
这种以爱之名的控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很多父母将自己的梦想和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却忽略了孩子本身的兴趣和需求,从而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这本书也揭示了种族问题在美国社会的根深蒂固。
詹姆斯作为华裔,尽管他努力融入,却依然遭受着来自外界的歧视和偏见。
这种种族的差异和不平等,不仅影响了詹姆斯的一生,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他的家庭和孩子。
此外,书中对于自我认同的探讨也令人深思。
莉迪亚在迎合父母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她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最终无法承受压力而选择了走向湖中心。
这让我们意识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是多么重要。
只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在各种期望和压力中寻找着自我呢?我们或许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选择了不喜欢的专业;或许为了迎合社会的标准,从事了不热爱的工作。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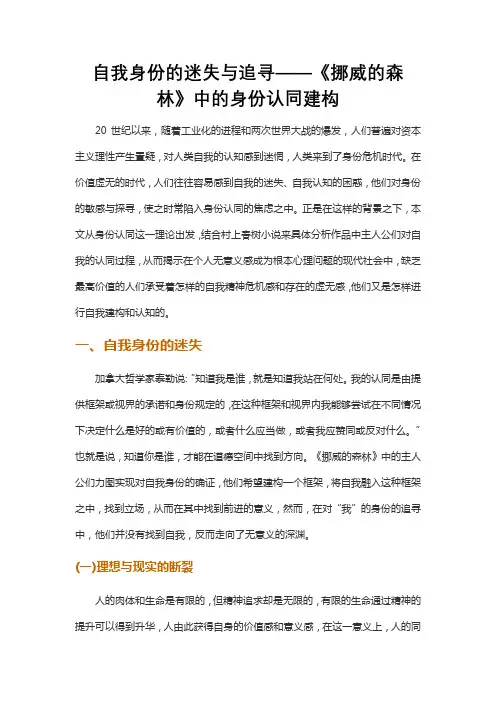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理性产生置疑,对人类自我的认知感到迷惘,人类来到了身份危机时代。
在价值虚无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感到自我的迷失、自我认知的困惑,他们对身份的敏感与探寻,使之时常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从身份认同这一理论出发,结合村上春树小说来具体分析作品中主人公们对自我的认同过程,从而揭示在个人无意义感成为根本心理问题的现代社会中,缺乏最高价值的人们承受着怎样的自我精神危机感和存在的虚无感,他们又是怎样进行自我建构和认知的。
一、自我身份的迷失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说:“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
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
”也就是说,知道你是谁,才能在道德空间中找到方向。
《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们力图实现对自我身份的确证,他们希望建构一个框架,将自我融入这种框架之中,找到立场,从而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意义,然而,在对“我”的身份的追寻中,他们并没有找到自我,反而走向了无意义的深渊。
(一)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人的肉体和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有限的生命通过精神的提升可以得到升华,人由此获得自身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同一性或认同具有形而上的向度。
正是借助这种超越的本性,人不断朝理想的、可能性的生活奋进,力图追求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自我认同恰恰体现在对这种总体性自我的理解和把握中,亦即体现为意义感的追寻过程之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已不再是唯一的奋斗目标,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生存的意义和本质。
《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们在对这冷漠社会的观照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价值。
他们讨厌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生活,可是身边到处都是“学生服”与“敢死队”那样的迂腐之人,不懂变通。
2024年《人生由我》读后感5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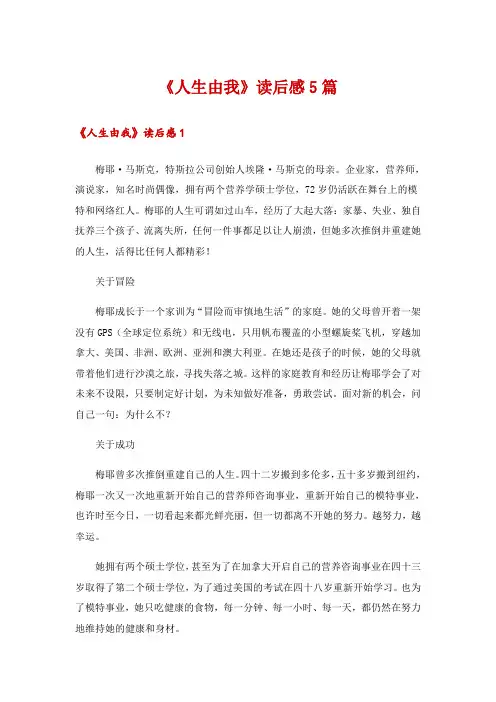
《人生由我》读后感5篇《人生由我》读后感1梅耶·马斯克,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母亲。
企业家,营养师,演说家,知名时尚偶像,拥有两个营养学硕士学位,72岁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模特和网络红人。
梅耶的人生可谓如过山车,经历了大起大落:家暴、失业、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流离失所,任何一件事都足以让人崩溃,但她多次推倒并重建她的人生,活得比任何人都精彩!关于冒险梅耶成长于一个家训为“冒险而审慎地生活”的家庭。
她的父母曾开着一架没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和无线电,只用帆布覆盖的小型螺旋桨飞机,穿越加拿大、美国、非洲、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
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带着他们进行沙漠之旅,寻找失落之城。
这样的家庭教育和经历让梅耶学会了对未来不设限,只要制定好计划,为未知做好准备,勇敢尝试。
面对新的机会,问自己一句:为什么不?关于成功梅耶曾多次推倒重建自己的人生。
四十二岁搬到多伦多,五十多岁搬到纽约,梅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自己的营养师咨询事业,重新开始自己的模特事业,也许时至今日,一切看起来都光鲜亮丽,但一切都离不开她的努力。
越努力,越幸运。
她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甚至为了在加拿大开启自己的营养咨询事业在四十三岁取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为了通过美国的考试在四十八岁重新开始学习。
也为了模特事业,她只吃健康的食物,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仍然在努力地维持她的健康和身材。
关于教育梅耶有一句话这样说:对孩子最有用的教育,就是让他们看见你在努力地称为更好的自己。
“我从未像对待小宝宝那样对待他们,也从未责骂他们,或告诉他们应该学习什么。
他们只需要让我知道他们正在学习什么或者没学什么就行。
我不会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因为那是他们的责任。
我们没有必要对孩子们过度保护,这只会造成他们与现实和责任脱节。
”一切皆有可能,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
有时我们缺乏的是改变的勇气、制定计划并遵从计划的决心、面对未知的准备和对学习的坚持。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女性自我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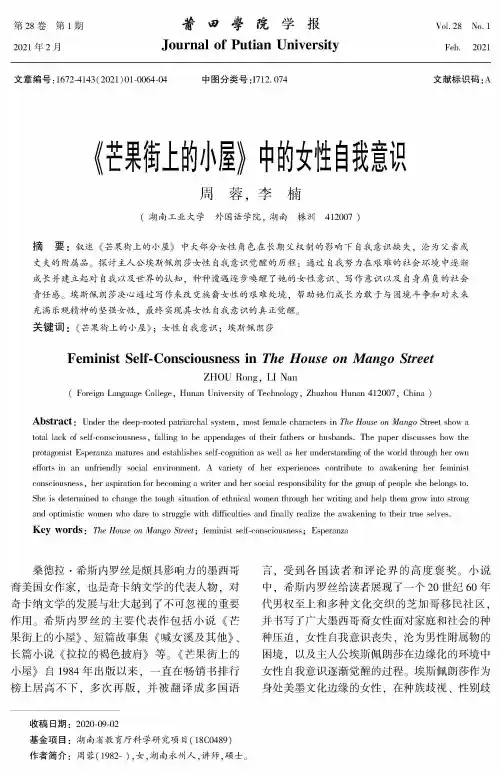
第28卷第1期普设每院学报Vol. 28 No. 1 2〇2i 年 2月Journal of Putian University F eb.2021文章编号:1672-4143(2021)01-0064-04 中图分类号:I712. 074文献标识码:A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女性自我意识周蓉,李楠(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摘要:叙述《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大部分女性角色在长期父权制的影响下自我意识缺失,沦为父亲或丈夫的附属品。
探讨主人公埃斯佩朗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历程:通过自我努力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逐渐成长并建立起对自我以及世界的认知,种种遭遇逐步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写作意识以及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感。
埃斯佩朗莎决心通过写作来改变族裔女性的艰难处境,帮助她们成长为敢于与困境斗争和对未来充满乐观精神的坚强女性,最终实现其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
关键词:《芒果街上的小屋》;女性自我意识;埃斯佩朗莎Feminist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House on M ango StreetZHOU Rong,LI Nan(Foreign Language Colleg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 Abstract:Under the deep-rooted patriarchal system,most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show a total lack of self-consciousness,falling to be appendages of their fathers or husbands.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protagonist Esperanza matures and establishes self-cognition as well as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her own efforts in an un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A variety of her experiences contribute to awakening her feminist consciousness,her aspiration for becoming a writer and h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roup of people she belongs to.She is determined to change the tough situation of ethnical women through her writing and help them grow into strong and optimistic women who dare to struggle with difficulties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awakening to their true selves. Key words: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feminist self-consciousness;Esperanza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是颇具影响力的墨西哥 裔美国女作家,也是奇卡纳文学的代表人物,对 奇卡纳文学的发展与壮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
追寻作为黑人妇女的自我身份
追寻作为黑人妇女的自我身份作者:唐俊芳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29期摘要:小说《紫色》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经典代表作,小说通过曲折情节展现了主人公茜丽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从饱受折磨蜕变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黑人女性商人的故事。
小说通过茜丽从饱受压迫、深受种族歧视与区别对待到自我奋斗,不断摆脱社会的固有观念,形成独立身份与人格的过程,展现了一位黑人女性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反抗种族歧视的精神。
这种精神对当今社会也有着重要意义,人作为社会主体受到各种因素困扰,要不断寻求自身价值。
关键词:小说《紫色》;黑人妇女;成长小说[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9--01《紫色》小說是美国著名黑人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经典代表作,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项与全国图书奖。
小说描述了主人公茜丽成长过程的中经受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等社会问题。
小说展示了茜丽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不断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
《紫色》中主人公的成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童真的幻灭阶段—主人公的成长阶段—追求自我价值阶段。
本文主要结合小说以及主人公成长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童真的幻灭阶段小说《紫色》是一部书信体小说,文中的主要情节通过书信语言的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
整部小说共包括92封信件。
92封信件中70封为主人公茜丽自己撰写,22封信件由主人公妹妹聂蒂所写[1]。
在茜丽所写的70封信件中,通过前20封信件可以看出当时茜丽是一个没有自主人格,天真懵懂、任人欺凌的黑人小女孩,喜欢紫色、与其他孩子一样喜欢打闹。
好景不长,茜丽的继父奸污了她,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他则会杀了他的母亲。
缺乏社会经验的茜丽生下一儿一女后,母亲因为承受不住打击撒手人寰,缺少庇护的茜丽被迫嫁给带有四个儿女的鳏夫,并忍受凌辱。
在此阶段中,茜丽自我意识尚未觉醒,没有形成独立人格,也并未意识到自己受迫害的根源所在,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心存怨恨,但无力改变眼前的现实。
从心理社会发展角度解读梅丽迪恩对自我身份的追寻(1)
从心理社会发展角度解读梅丽迪恩对自我身份的追寻梅丽迪恩是美剧《初为人母》中的主角,她是在自我身份寻找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从心理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梅丽迪恩在心理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经历了相应的问题和转换,这些问题和转换帮助她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人们开始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在这个阶段,梅丽迪恩主要面对的问题是发展自尊和形成个人身份。
在剧中,梅丽迪恩在这个阶段的身份认同也是不稳定的,她常常感到自己被孤立和无助,同时她也很难和她的家庭保持亲密的关系。
因此,她尝试着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来寻找自己的身份,比如参加学校的戏剧表演以及创作音乐。
这些活动使她感受到了成就感,从而帮助她建立了自信心和身份意识。
在青春期,人们开始经历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发展,在这个阶段,梅丽迪恩开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期望。
她开始受到社会对她的外貌和行为的期望和压力。
尽管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流行女孩,但她却因自己的马尾辫和穿着失去了自信。
此外,她的父母常常给她施加压力让她追求传统的女性角色,并把她的热情当作“小女孩的幻想”。
所有这些都让梅丽迪恩感到混乱和焦虑,她开始寻求自己的身份,并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梦想,这是她的坚守和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方式。
从成年到中年期,人们渐渐地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目标和责任。
在剧中,梅丽迪恩面对着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为自己的前程和家庭作出贡献的女性这些职责、任务和诉求。
尽管她有时会感觉自己被困在自己的角色中,并且她的角色和价值观似乎与她的丈夫不同,但她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事业。
她不是希望做一个“完美的”母亲,而是希望追求自己的个人梦想。
在这个阶段,梅丽迪恩的追求自我身份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她不再寻求他人的认可,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需要。
最后,在老年人的阶段,人们通常会面对对死亡和生命的反思。
在这个阶段,梅丽迪恩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深刻,包括生命的意义,如何解决人际关系,如何完成其余时间的目标。
试析梅瑞狄斯《利己主义者》中的巧合艺术
试析梅瑞狄斯《利己主义者》中的巧合艺术《利己主义者》是英国作家梅瑞狄斯所著的一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巧合艺术而闻名。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巧合情节,这些巧合情节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也向读者展示了人生的无常和机遇的重要性。
下面将从情节安排、人物关系以及小说主题等方面来分析这种巧合艺术。
巧合情节在小说中的安排非常精妙,既让读者感到意外,又让故事发展得更加紧凑。
在小说中,主人公海伦娜在婚礼当天遇到了亨利,在没多久后又遭遇了车祸,这些突如其来的巧合情节使得海伦娜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后,小说中还出现了许多巧合情节,例如海伦娜在职业领域的成功与亨利的出现以及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
这些情节的巧合不仅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也使得读者在阅读中感到有趣和享受。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是巧合艺术的重要体现。
海伦娜在小说中遇到的人物几乎都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
她与她的妹妹和弟弟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且她的前夫亚瑟和改嫁对象亨利也与她的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既是由于巧合的安排,同时也展现了命运和机遇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些关系不仅让故事更加曲折有趣,也使得读者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巧合艺术也体现在了小说的主题上。
《利己主义者》通过描绘主人公海伦娜的故事,探讨了利己主义的概念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小说中的巧合情节和人物关系展示了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常常受到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影响,并对人们的人生轨迹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种对于命运和机遇的重视揭示了小说中的主题,即在现实社会中,个体的选择和努力只是命运和机遇中的一部分。
巧合情节和人物关系让读者深思,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和他人的影响。
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通过巧合情节和人物关系展示了其独特的巧合艺术。
这种艺术使得小说充满了悬念和挑战,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无常和机遇的重要性。
通过这种艺术手法,梅瑞狄斯成功地将读者吸引到故事中,使他们在阅读中找到愉悦和思考的乐趣。
《又来了,爱情》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呈现与身份建构
《又来了,爱情》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呈现与身份建构
殷文朔
【期刊名称】《新乡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41)1
【摘要】《又来了,爱情》是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晚年代表作品,它充满着现实主义风格,文风简洁而思想深邃、观点犀利。
人的身份是可以建构的,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不断变迁。
文化身份是人们在社会中立足的标签,而身份的建构是人们摆脱主流文化排斥和摆脱被边缘化的途径。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萨拉和朱莉面临的身份危机与建构,能够给女性以启示:女性应该全面地了解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动态,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
【总页数】4页(P45-48)
【作者】殷文朔
【作者单位】蚌埠工商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相关文献】
1.爱情来了,女性的自由在哪里——基于伊利格瑞的理论解读《又来了,爱情》中莱辛的女性观
2.论《好女人的爱情》中女性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建构
3.观赏石收藏的精品意识
4.女性主体意识的呈现与独立身份建构——笛安《景恒街》中的女性书写研究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从心理社会发展角度解读梅丽迪恩对自我身份的
追寻
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心理分析学家,他在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学说的基础上,于1950年提出了解释整个生命历程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Theory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危机。
艾瑞克森强调文化及社会环境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发展包括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变化过程,此过程有八个发展阶段组成,每一阶段都有一个发展(developmental crisis)或中心任务必须解决,成功地解决每一个阶段的危机,人格才会顺利发展。
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特定的心理社会任务需要解决。
小说《梅丽迪恩》中同名主人公梅丽迪恩6岁以前的故事作者没有叙述,所以运用艾瑞克森的八阶段理论分析梅丽迪恩的自我追寻过程时,从6岁以后的成长阶段开始。
学龄期:指6—12岁发展阶段此期发展的危机是勤奋对自卑危机。
学龄期的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
此期儿童的活动场所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主要精力集中于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能,学习与同伴合作,竞争和遵守规则。
学
龄期是养成有规律的社会行为的最佳时期。
在学业上的成果体验会促进勤奋感的建立。
反之失败的经历多于成功,则会产生自卑感。
对学龄期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是父母、老师、同学等。
这个阶段自我概念变的比较复杂,影响自尊。
梅丽迪恩七岁时的一天,她玩耍的时候,发现了一块黄色的亮晶晶的金属。
她特别高兴地认为自己找到了电影里看到的黄金,便兴冲冲地去告诉母亲,可是母亲在忙碌,并不理她。
梅丽迪恩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家人的关注,她自始至终与一种无名的罪恶感相斗争。
起初,她认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个罪过,因为她感到“破坏了母亲的宁静,毁灭了母亲的前程,但她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是她的过错。
”
青春期:指12—18岁发展阶段此阶段发展的危机是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
身体上性生理的成熟,使之具有性冲动的压力。
由于性知识的缺乏及社会的禁忌,使之不知如何处理因性冲动而出现的困惑和压力。
梅丽迪恩的母亲是一个深受本能折磨的母亲,她虽然质疑黑人母亲身份这个女性神话,但是并不敢提出反抗。
她视孩子为一个负担,既没有鼓励梅丽迪恩发展自己独特的才能,也没有告诉她有关性的知识,任其自由发展。
她12岁时,每个周六的下午都去达克斯殡葬之家。
达克斯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他每次都对
梅丽迪恩进行猥亵,而梅丽迪恩并不反感,因为她能得到一些糖果。
她15岁左右时,达克斯更加肆无忌惮,他不在时,他的助手也骚扰梅丽迪恩,而梅丽迪恩似乎对此很痴迷。
假如梅丽迪恩的母亲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会传授给女儿一些基本的性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梅丽迪恩在青春期阶段对性意识的模糊也造成日后她婚姻的不幸。
虽然她和丈夫艾迪不是一见钟情,和他交往后,梅丽迪恩放弃了达克斯和他的助手,但是她一直心怀愧疚,性生活中她也找不到真正的快乐。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竟然怀孕了。
而未婚妈妈在当时美国社会是不被接受的。
因此,她不得不放弃学业而走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她对艾迪并不是真爱,嫁给埃迪只是满足于艾迪所提供给她的物质保障,为她的生存进行道德上的辩护。
而艾迪却把征服女人的身体视为男子汉气概的表现,把梅丽迪安当作其发泄性欲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
他要求梅丽迪安无条件地满足他的性欲望而无视其感情上的需求。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到:“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
”做饭、洗衣服、无爱的性生活使梅丽迪安苦不堪言。
正如沃克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庆祝婚姻
就像庆祝自己被卖成奴隶一样”,梅丽迪恩17岁时,艾迪便以她对性生活冷淡为借口在外面另觅新欢,到最后像扔掉旧衣服一样把梅丽迪安母子抛弃了。
梅丽迪安变成了一个精神抑郁的单身母亲,“梅丽迪安的生活过得完全没有朝气,每天通过看电视来消磨时间,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离。
”此时,她的生活拘囿于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也没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公正的命运的安排。
因此,我们说此时她属于一个丧失了主体性的人,属于沃克所划分的“被悬吊起来的女人”(“她们被悬掉在历史的时空中,她们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自杀,要么被男人、孩子或各种各样的压力耗尽一生。
她们走投无路。
她们根本动弹不得,直到她们有了可进入的空间。
”)自我认同(ego identity)是人格上自我一致的感觉,青少年需要从周围世界中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选择人生的目标。
由于过早的走入婚姻,成为母亲,梅丽迪恩在此阶段发展并不顺利。
青年期指18-35岁发展阶段,此期发展的危机是亲密对孤独。
青年期已经建立了自我认同感,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价值观念及人生目标。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发展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友谊、爱情和婚姻关系,从而建
立亲密感。
艾瑞克森认为真正的亲密感是指两人都愿意共同分享和相互调节生活中一切重要的方面,只有在建立自己的认同感之后,也就是解决了上一期自我认同和角色紊乱的矛盾冲突后,才能别人的共享中忘记自我,否则很难达到真正的感情共鸣,会产生与同龄人,社会及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孤独感。
梅丽迪安的第二次恋爱同样让她深切地感到自我成长的失败。
她的第二任男友是个叫特鲁曼( Truman)的黑人艺术家。
特鲁曼读过大学,到过法国,也参加过民权运动。
他比艾迪接受过更高的教育,见识更广。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他与艾迪没有多大的差别,正如他的名字所示( Truman与true man谐音,中文意为真正的男人),他也是男权价值观念的代言人。
与其他的男性一样,特鲁曼所欣赏的只是那些肉体上有魅力而精神上很幼稚的睡美人。
他希望梅丽迪安是个有魅力,但处于睡眠状态的女人。
与特鲁曼的性爱关系中,梅丽迪安没有获得精神的自由。
相反,她却总是感受到自我的分离只要他在旁边,她就想与他做爱。
热烈、迅速而不用脑子;她只能将思想关闭,(让)她的身体自动地投入他的怀抱。
根据艾瑞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人在中年期(35-65岁)遇到的主要危机是创造对停滞。
成年人建立了与他人
的亲密关系,进入中年期关注的重点是工作、家庭和养育下一代,以及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中年人知识的积累日益丰富,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看待问题;并且会努力工作,脚踏实地地创造未来。
小说主人公梅丽迪安为了能上大学走出自我解放的第一步,抛弃了她的孩子。
当她把孩子送走时,她的心情并不轻松。
她没回头,认为自己拯救了一个小生命。
她的心情很矛盾:母亲代表了受害者,不自由的妇女殉道者。
成为一个母亲,那么她很可能淹没在做不完的家务里,梅丽迪安选择了自由,后来结扎了输卵管彻底放弃了生育功能,献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对种族、阶级、性压迫的社会斗争。
沃克设计梅丽迪安这样一个勇敢热情的女性形象呼召广大女性的觉醒和投入,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在梅丽迪安心里做母亲的渴望和追求幸福自由的理想二者之间的纠缠斗争。
梅丽迪安最后的选择值得读者深思:她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并且将自己的输卵管结扎,终结了当母亲的角色;她不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根据艾瑞克森的理论,梅丽迪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青年期发展不顺利。
她选择成为一名妇女主义者喜欢和偏爱女人的文化、女人的感情变化和女人的力量,以整个种族(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生存和
完整为己任。
从这一点来说,梅丽迪恩的人生并不完整,也就是她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并未成功。
最后,梅丽迪安在黑人教堂中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
可是,她接受的是“教堂”,而不是基督教。
那里古老的圣歌使她振奋,因为她听到了“人民的歌声,那歌声使他们团结一致”。
梅丽迪安在黑人圣歌中找到了“再生的力量”,她对黑人的事业又充满了希望。
小说结尾处,梅丽迪安打起了行装,踏上新的征程,她又要去漂泊,但何处是归途?在生活和文学中,还没有既摆脱婚姻与孩子的束缚,又能在父系社会成功地生存的角色模型可作她们前进的方向。
虽然梅丽迪安比她的母亲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她也为选择付出了代价,那便是心灵和肉体的痛苦。
她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孩子和丈夫。
在通往自我的旅途上,她是孤独的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