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里的石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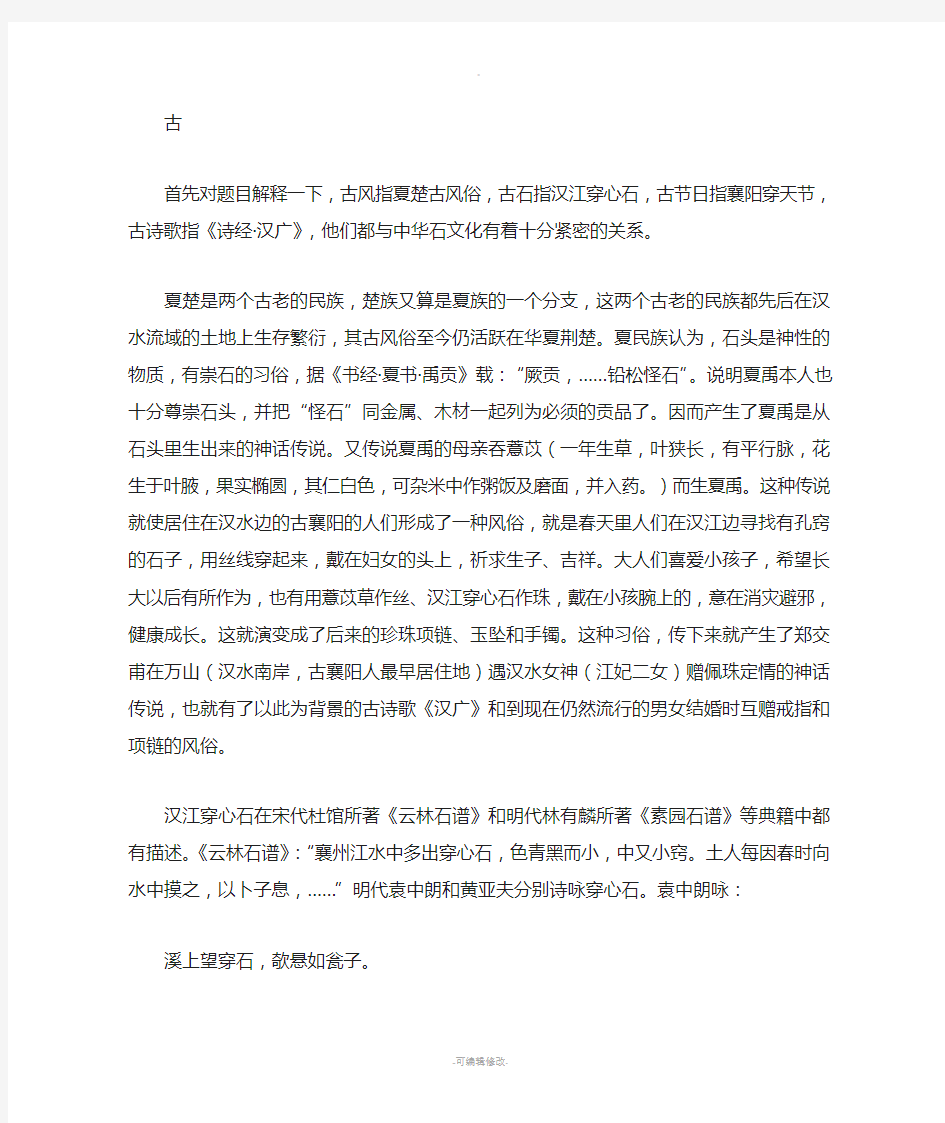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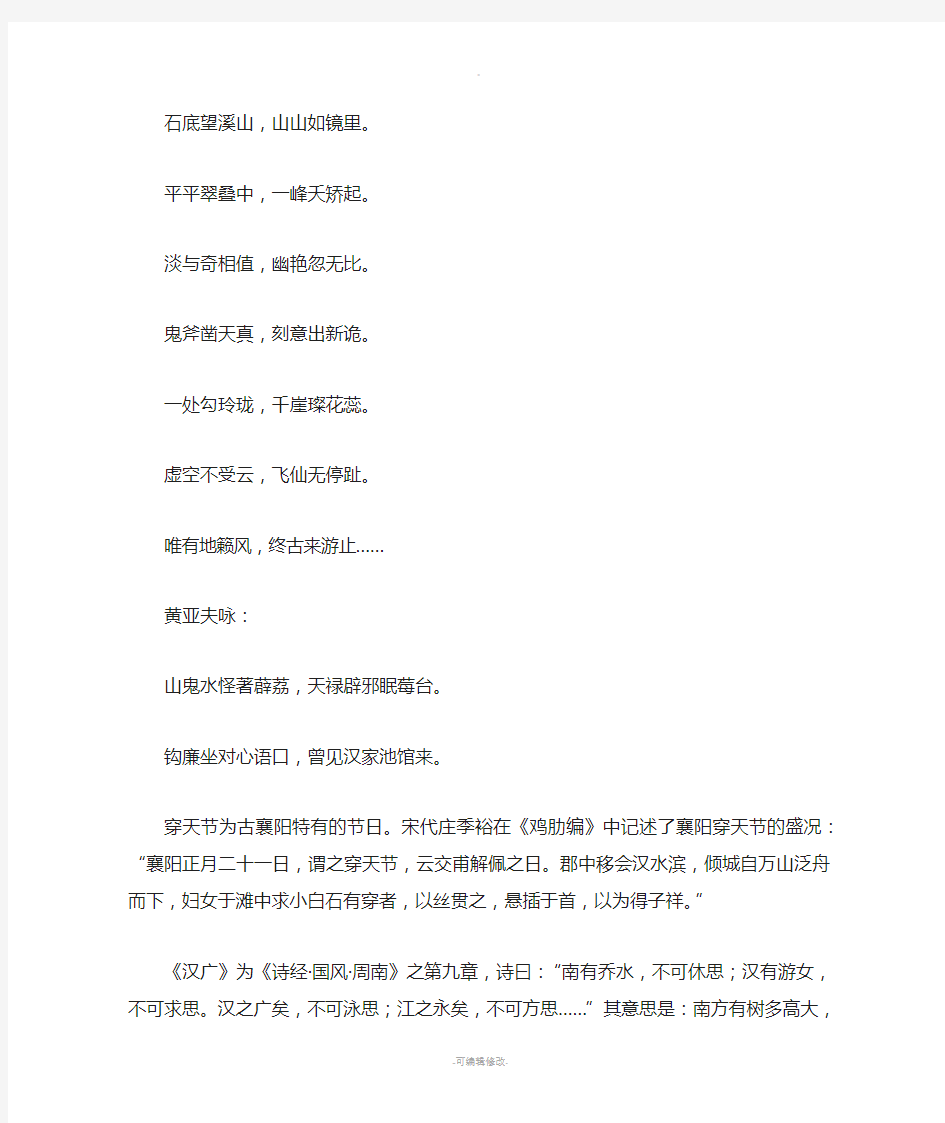
。
古
首先对题目解释一下,古风指夏楚古风俗,古石指汉江穿心石,古节日指襄阳穿天节,古诗歌指《诗经·汉广》,他们都与中华石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夏楚是两个古老的民族,楚族又算是夏族的一个分支,这两个古老的民族都先后在汉水流域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其古风俗至今仍活跃在华夏荆楚。夏民族认为,石头是神性的物质,有崇石的习俗,据《书经·夏书·禹贡》载:“厥贡,……铅松怪石”。说明夏禹本人也十分尊崇石头,并把“怪石”同金属、木材一起列为必须的贡品了。因而产生了夏禹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话传说。又传说夏禹的母亲吞薏苡(一年生草,叶狭长,有平行脉,花生于叶腋,果实椭圆,其仁白色,可杂米中作粥饭及磨面,并入药。)而生夏禹。这种传说就使居住在汉水边的古襄阳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风俗,就是春天里人们在汉江边寻找有孔窍的石子,用丝线穿起来,戴在妇女的头上,祈求生子、吉祥。大人们喜爱小孩子,希望长大以后有所作为,也有用薏苡草作丝、汉江穿心石作珠,戴在小孩腕上的,意在消灾避邪,健康成长。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珍珠项链、玉坠和手镯。这种习俗,传下来就产生了郑交甫在万山(汉水南岸,古襄阳人最早居住地)遇汉水女神(江妃二女)赠佩珠定情的神话传说,也就有了以此为背景的古诗歌《汉广》和到现在仍然流行的男女结婚时互赠戒指和项链的风俗。
汉江穿心石在宋代杜馆所著《云林石谱》和明代林有麟所著《素园石谱》等典籍中都有描述。《云林石谱》:“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又小窍。土人每因春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明代袁中朗和黄亚夫分别诗咏穿心石。袁中朗咏:
。溪上望穿石,欹悬如瓮子。
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镜里。
平平翠叠中,一峰夭矫起。
淡与奇相值,幽艳忽无比。
鬼斧凿天真,刻意出新诡。
一处勾玲珑,千崖璨花蕊。
虚空不受云,飞仙无停趾。
唯有地籁风,终古来游止……
黄亚夫咏:
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莓台。
钩廉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家池馆来。
穿天节为古襄阳特有的节日。宋代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记述了襄阳穿天节的盛况:“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滨,倾城自万山泛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穿者,以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祥。”
《汉广》为《诗经·国风·周南》之第九章,诗曰:“南有乔水,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其意思是:南方有树多高大,谁有福分在树下;汉水游女好美貌,只是不能追求到,汉水波涌江面宽,怎么游水到岸边!长江源远又流长,如何并行结成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创作年代距今约两千五百年左右。由此可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在汉水之滨的古襄阳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寻找奇石的风潮。
THANKS !!!
致力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合同协议,策划案计划书,学习课件等等
打造全网一站式需求
欢迎您的下载,资料仅供参考
《诗经》的文化底蕴
《诗经》的文化底蕴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中心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内容提要 (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2) 绪论 (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8) 总结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前期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作,因所配乐曲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题材相当广泛,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民间的日常生活,都有所涉及,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古朴自然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以及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同时,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 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从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到《雅》、《颂》的抒情诗中沉潜着的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这不仅仅表现着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同时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乃是我们古老祖先们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 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 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原因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 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 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复习进程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
浅析《诗经-关雎》文化内涵的当代意义《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从春秋乃至更古老的时代流传至今,是中华文化中分量最重的瑰宝之一,古来文人从启蒙开始便都要接触研习《诗经》,从而在文人心中有着重大意义。而《关雎》则是这部诗歌总集的第一篇,可以说绝不是随意而为之的。作为《诗经》的首篇诗歌,历代学者对此诗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此诗歌颂“后妃之德”。汉代毛亨《毛诗诂训传》认为诗中“君子”指代周文王,“淑女”借喻太姒,中心是褒扬“后妃之德”。《毛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2)认为此诗就是一首单纯的男女恋歌。“是一个青年热恋采集荇菜女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一曲单纯的爱情颂歌,以最为朴素明净的民歌语言,最为热烈真挚的相思情怀讲述着中国上古时代的爱情传说。”(3)《关雎》是一首婚歌。如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论《桃夭》说:“盖此(指《桃夭》)亦咏新婚诗,与《关雎》同为房中乐,如后世催妆坐筵等词。特《关雎》从男求女一面说,此从女归男一面说,互相掩映,同为美俗。”(《诗经原始》) 虽然各个时代的不同学者们各持己见,但《关雎》之中丰富的文化内蕴是受到代代文人学者所公认的。不论解读如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都值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细细品读。即使是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对于当代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就试着就《关雎》的几点文化内涵,浅谈一下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发乎于情,止乎于理。 有记载的最早对《关雎》一诗进行阐述的是孔子,他写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这首诗抒发快乐的感情,但没有过分,抒发哀怨的感情,但不致损伤。《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这便是我国能找到的最早的爱情故事了,相比于当今社会各种充斥在市面上的爱情小说、影视里所描写的故事,似乎平平无奇。但是《关雎》流传至今还依旧受到文人们的喜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诗经》第一篇的虚名,而是因为他表达出来的那种真挚美好的感情。人与动物的区别便在于丰富的感情,而爱便是感情中最为炽热的一种。试问谁不曾在自己年轻时憧憬过,歌颂过爱情。但是《关雎》在描绘男女之间的感情时,并没有像现代爱情故事那样把爱描写的那么看似浓烈丰富实则赤裸和肤浅。男子对女子爱的表达是真诚坦然的,对爱的追求也无不动人,对爱的期待是那么可爱而真实。但正如孔子所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男子对爱情对女子的追求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困扰,并没有做出任何过分之事。无论是苦恼也好,喜悦也罢,都是在一个很适当的范围内,没有越轨。这对于当下追求或者想追求爱情的年轻人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用来生活而不是时时刻刻为了生存为了果腹而挣扎。古语有云:饱暖思淫欲。丰富的精神生活建立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上。现代人们有着充裕的时间,自然而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精神产物。这也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间。爱情作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产物,自然而然的被人们拿出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和文化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诗经里的石文化
古 首先对题目解释一下,古风指夏楚古风俗,古石指汉江穿心石,古节日指襄阳穿天节,古诗歌指《诗经·汉广》,他们都与中华石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夏楚是两个古老的民族,楚族又算是夏族的一个分支,这两个古老的民族都先后在汉水流域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其古风俗至今仍活跃在华夏荆楚。夏民族认为,石头是神性的物质,有崇石的习俗,据《书经·夏书·禹贡》载:“厥贡,……铅松怪石”。说明夏禹本人也十分尊崇石头,并把“怪石”同金属、木材一起列为必须的贡品了。因而产生了夏禹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话传说。又传说夏禹的母亲吞薏苡(一年生草,叶狭长,有平行脉,花生于叶腋,果实椭圆,其仁白色,可杂米中作粥饭及磨面,并入药。)而生夏禹。这种传说就使居住在汉水边的古襄阳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风俗,就是春天里人们在汉江边寻找有孔窍的石子,用丝线穿起来,戴在妇女的头上,祈求生子、吉祥。大人们喜爱小孩子,希望长大以后有所作为,也有用薏苡草作丝、汉江穿心石作珠,戴在小孩腕上的,意在消灾避邪,健康成长。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珍珠项链、玉坠和手镯。这种习俗,传下来就产生了郑交甫在万山(汉水南岸,古襄阳人最早居住地)遇汉水女神(江妃二女)赠佩珠定情的神话传说,也就有了以此为背景的古诗歌《汉广》和到现在仍然流行的男女结婚时互赠戒指和项链的风俗。 汉江穿心石在宋代杜馆所著《云林石谱》和明代林有麟所著《素园石谱》等典籍中都有描述。《云林石谱》:“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又小窍。土人每因春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明代袁中朗和黄亚夫分别诗咏穿心石。袁中朗咏: 溪上望穿石,欹悬如瓮子。 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镜里。 平平翠叠中,一峰夭矫起。 淡与奇相值,幽艳忽无比。 鬼斧凿天真,刻意出新诡。 一处勾玲珑,千崖璨花蕊。 虚空不受云,飞仙无停趾。 唯有地籁风,终古来游止…… 黄亚夫咏: 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莓台。 钩廉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家池馆来。
《诗经》中的服饰文化
《诗经》中的服饰文化 摘要:我国服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要了解我国服饰文化的发展进程,对夏商周时期的服装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诗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平台。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服装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本文通过服装原料、服装种类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几方面对西周、春秋时期的服饰文化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服装;春秋;诗经 一、服装原料 古代的服装可利用的原材料有限,人们多数利用的是自然生长的植物或动物皮毛,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从只知道单纯的利用野生动植物到学会自己种植、养殖,大大增S加了服装原料的数量。 (一)葛的应用 在《诗经》中“葛”出现次数频繁,有四篇以此为题。这说明葛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它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来源之一。如,《诗经.王风.采葛》说:“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就证明了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诗经.国风.葛覃》)。这说明了葛生长的状态和地点,它是一种蔓生植物,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葛用煮法可抽出纤维用作织布原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诗经.国风.葛覃》),这说明当时葛衣也分几种,有“絺、綌”只分,絺为细葛布,綌为粗葛布。另外,还有比絺还细的葛布,称为绉。“蒙彼绉絺,是紲袢也。”(《诗经.鄘风.君子偕老》)这句诗就说明了绉的存在。 (二)麻的应用 除葛以外,苎麻也是当时可利用的重要的服装原料。《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中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纻……”这是说古人利用“沤”的办法使麻纤维脱胶用以织布。在《诗经》中“麻”字出现多次,如“丘中有麻”(《诗经.王风.丘中有麻》)。“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诗经.陈风.东门之枌》)等等。说明在西周时期,我国麻的种植已经相当的普遍了,当时的劳动人民用它来做衣服、鞋子。 (三)蚕丝的应用 就在葛布和麻布盛行之时,另一种更珍贵、更美丽的衣料出现了。这就是我国一直应用至今的独特的布料——丝绸。从《诗经》中可以看出,此时,我国劳动人民已懂得自己栽培桑树,饲养家蚕。当然这也是经过了一个由利用野生蚕丝到自觉的家养蚕丝的发展过程。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个丝茧,经鉴定为野生蚕茧,而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丝和丝织品,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1]。这表明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懂得利用野生蚕丝,并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进行家蚕的饲养。到了春秋时期,我国的蚕桑养殖已
诗经里的石文化
。 古 首先对题目解释一下,古风指夏楚古风俗,古石指汉江穿心石,古节日指襄阳穿天节,古诗歌指《诗经·汉广》,他们都与中华石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夏楚是两个古老的民族,楚族又算是夏族的一个分支,这两个古老的民族都先后在汉水流域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其古风俗至今仍活跃在华夏荆楚。夏民族认为,石头是神性的物质,有崇石的习俗,据《书经·夏书·禹贡》载:“厥贡,……铅松怪石”。说明夏禹本人也十分尊崇石头,并把“怪石”同金属、木材一起列为必须的贡品了。因而产生了夏禹是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话传说。又传说夏禹的母亲吞薏苡(一年生草,叶狭长,有平行脉,花生于叶腋,果实椭圆,其仁白色,可杂米中作粥饭及磨面,并入药。)而生夏禹。这种传说就使居住在汉水边的古襄阳的人们形成了一种风俗,就是春天里人们在汉江边寻找有孔窍的石子,用丝线穿起来,戴在妇女的头上,祈求生子、吉祥。大人们喜爱小孩子,希望长大以后有所作为,也有用薏苡草作丝、汉江穿心石作珠,戴在小孩腕上的,意在消灾避邪,健康成长。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珍珠项链、玉坠和手镯。这种习俗,传下来就产生了郑交甫在万山(汉水南岸,古襄阳人最早居住地)遇汉水女神(江妃二女)赠佩珠定情的神话传说,也就有了以此为背景的古诗歌《汉广》和到现在仍然流行的男女结婚时互赠戒指和项链的风俗。 汉江穿心石在宋代杜馆所著《云林石谱》和明代林有麟所著《素园石谱》等典籍中都有描述。《云林石谱》:“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又小窍。土人每因春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明代袁中朗和黄亚夫分别诗咏穿心石。袁中朗咏:
。溪上望穿石,欹悬如瓮子。 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镜里。 平平翠叠中,一峰夭矫起。 淡与奇相值,幽艳忽无比。 鬼斧凿天真,刻意出新诡。 一处勾玲珑,千崖璨花蕊。 虚空不受云,飞仙无停趾。 唯有地籁风,终古来游止…… 黄亚夫咏: 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莓台。 钩廉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家池馆来。
浅谈诗经中的文化现象
浅谈《诗经》中的文化现象及文化精神 刘懿慧 摘要:《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及其内涵是丰富而广泛的,是从远古社会到周代深厚的文化沉淀。因此,充分挖掘其深层文化现象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商业观念占卜文化女性审美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一直被称作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亮点。其实,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诗经》所记录的宗教祭祀活动、田间地头的劳作和宴饮觥筹中所见的宗法等级关系等等,都是在诗以它的美好节律向我们透露着那一个时代的信息。闻一多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向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①在这里,主要谈谈《诗经》的几个文化现象,及其所反映的文化精神。 一.浓厚的农业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诗经》便是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在《诗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以描述农事为主题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高度重视农业,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利用。按照郭沫若的说法,其中的农事诗,即《国风》中的《豳风?七月》,《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周颂》中的《思文》、《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等十一篇②。 其中,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是《豳风?七月》这首诗。诗从七月写起,物象纷繁流转,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展开了各个画面把周人一年四季的辛勤劳动贯穿了起来。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为开篇,而后“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绘声绘色地表现了一幅农民四季流转,辛勤事农的图景。 在这首诗中,显示出一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农业过程,也就是在这以过程中,可以看出,周人的农业活动显示出季节性的差异,“春耕,夏耘,秋收,春藏”,各项工作因时制宜。 在周的这种浓厚的农业观念中,具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怀。表现为《诗经》中相当篇幅的作品中的眷恋故土的情怀。以农业为根基的周朝社会,人们热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热爱和平舒适的田园生活,安土重迁在他们的思想中极为牢固。因此他们对战争,对徭役,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万分痛恨。战争、徭役迫使他们离开故土,是他们最痛苦的事。 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首诗表现的是在家中的妻子日日夜夜地盼望丈夫从军的归来,反复吟咏,日思夜念,看到家鸡的归窝,看到牛羊的下山,心生悲伤,为什么她的丈夫还不
《诗经》中鹿的文化寓意及其演变
《诗经》中鹿的文化寓意及其演变 吴崇明 《诗经》中与鹿相关的诗有多篇,其中关于鹿的描写折射出丰厚的文化寓意,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特色和风貌。 一、鹿是爱情的象征 《诗经?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 NFDFB ,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据研究者考证,麕指小獐,是鹿一类的兽。而李善《文选》注认为,麕也就是鹿,“今江东人呼鹿为麕”(程俊英《诗经注析》)。故“野有死麕”与“野有死鹿”是一回事。《野有死麕》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恋爱的诗。写恋爱,为何要以“野有死麕”起兴?今天看来,“野有死麕”和“野有死鹿”不仅与爱情无关,而且“死麕”和“死鹿”这样的字眼,甚至让人觉得不美、不吉利。但是,在古代却不然,因为鹿是与爱情婚姻相关的一种礼物。古人婚礼纳徵,用鹿皮为贽。《仪礼?士婚礼第二》:“纳徵,玄 NFC51 束帛,俪皮。如纳吉礼。”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曰:“俪,两也。”“皮,鹿皮。”又《仪礼?士婚礼第一》:“主人酬宾,束帛俪皮。”郑玄注曰:“俪皮,两鹿皮也。”许慎《说文解字?鹿部》也认为:“[FJF]丽[FJJ]……从鹿丽声,礼[FJF]丽[FJJ]皮纳聘,盖鹿皮也。”由此可见,鹿皮是古人婚礼当中的重要贽礼,是年轻人结婚时少不了的东西。闻一多先生则据《野有死麕》进一步推论:“上古盖用全鹿,后世苟简,乃变用皮耳。”(《诗经研究》) 弄清了古人婚礼纳徵,用鹿皮为贽的礼俗,便能明白:《野有死麕》这首诗以“野有死麕”起兴,不是与题旨无关的信口开河,也不是随随便便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它实际上是作者精心的安排,寓有深意。它说的是:那位多情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于是跑到树林里打死了一只鹿,送给这位同样对他一往情深的姑娘。到了第二章,“又言取薪木照明之物与鹿肉为礼,想娶此如玉之女”(《陈子展《诗经直解》上,卷二)。古代人结婚时要砍柴作火把。清代胡承珙《毛诗后笺》:“《诗》于婚礼,每言析薪。古者婚礼或本有薪刍之馈耳。”可见,诗写“林有朴 NFC54 ”、“野有死鹿”,也都是围绕着爱情和婚姻这个话题
诗经中的婚俗文化
结合《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婚俗探析周朝社会概况 作者:郭巧玉 指导老师:高梓梅 摘要:《诗经》中婚恋诗的大量出现,可以说是对周朝社会面貌的真实再现。通过列举《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若干婚俗,进一步去探析当时社会背景,如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出现“上巳之恋”,还有重视对女子施教和对女子生育能力的强调,从而发现周朝婚姻中礼俗并举的现象,并了解当时社会进入了名义上一夫一妻制而实际上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统治时期。 关键词:《诗经》;国风;婚恋诗;婚俗;周朝;社会概况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其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从民俗学角度列举《诗经·国风》婚恋诗中的若干婚俗不仅可以发现周朝婚姻礼俗并举的现象,而且能够探析到周朝是宗法制下一个名义上进入一夫一妻制,又有着男尊女卑不平等观念的父权制社会。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上巳之恋所体现出的周朝婚 姻礼俗并举现象 《国风》时代婚恋诗中的婚俗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性,既有远古社会的遗风流俗,也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出现的新内容: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也有上巳之恋的自由;既有繁琐的婚礼程序,又有简便的嫁娶方式。周朝一方面对婚嫁实行了一整套严格的规范程序来维护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又由于地域的差别,离政治中心区域较远的地方受周礼影响较弱却还保留着自己的古老婚俗。从《诗经·国风》采集来的表现各地民俗风情的婚恋诗中可以明确发现周朝婚姻中
礼与传统民间习俗并存的现象。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礼记》一再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昏义》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可见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在当时是不合礼、不合法的,是得不到家庭、家族及社会他人所认可的。在这种择偶方式下,男女双方本人几乎没有经过自由恋爱而决定婚姻幸福的权利。我们可以从《诗经·国风》婚恋诗篇章中体会当时人们对这一婚俗的重视。首先看父母在婚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1]。作为“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大事,其缔结当然要从家族利益出发,因此男女双方在成婚以前必须经由父母同意、认可。如《齐风·南山》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说明父母之命的重要;《郑风·将仲子》“岂取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命,亦可畏也”,表现了对父母之命的遵从;《鄘风·柏舟》“母也不只,不谅人只”,诗中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青年,她的母亲强迫她嫁给别人,她誓死不肯。可以看出在婚姻包办制度下待嫁女处于被动地位,她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爱人的权利;还有《鄘风·蝃蝀》“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这首诗是对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破坏婚姻礼制的女子的强烈痛斥和指责。此外,媒人在成亲过程中也有着重要作用,无论男子或女子需要结婚,都要通过媒人这一关。如果没有媒人的介绍,那么男女成婚就失去了所依据的重要条件。周代婚俗中的“匪媒不得”就是最好的说明,如弃妇诗《卫风·氓》中“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这句话揭示了女子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良媒”,不具备成婚的所需条件;《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反复强调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还有《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娶妻必有媒。从上面列举的《诗经》婚恋诗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婚制制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偶方式,如果缺少这一成婚条件,就会受到谴责或酿成悲剧。 (二)上巳之恋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阅读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阿维斯塔》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1.下列对“圣诗”与“俗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圣诗与俗诗是学者运用当今的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来研究诗歌起源时似可区分出来的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源头。B.圣诗与俗诗虽然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C.俗诗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超过了圣诗。D.圣诗是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即属于此类。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A.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探讨诗歌的起源,虽然可以避免不少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但还不能很肯定地说彻底解决了诗歌起源的问题。B.《阿维斯塔》、《阿维斯塔》、《艾努玛·艾利什》等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大部分记载下来并得以流传,可能是因为它在初民意识形态中有着较高的地位。C.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安德鲁·兰的观点恰好说明诗歌的起源有“圣”与“俗”的区别。D.圣诗与俗诗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从固定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变成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性的俗诗。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从理论上说,俗诗与圣诗起源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它们都以人类的语言能力的产生为前提,但圣诗源于宗教文化,俗诗源于世俗文化。
诗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
[诗经,社会文化,婚恋]试论《诗经》中的婚恋诗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意义
试论《诗经》中的婚恋诗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爱情诗 宋代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由此可见,歌咏爱情是《诗经》创作的重要主题。而《诗经》中的爱情诗写得真实、细腻、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里有男女互相爱慕的诉语;有相爱男女之间的热烈、激情;也有恋爱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先秦时期礼教初设,礼教的兴起使得伦理道德思想开始占据人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充满禁锢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自由的。但原始社会的某些残留影响尚存在,甚至当时的一些礼教也建立在民间的风俗之上,略微宽松的社会环境也给予了男女感情发展的土壤。 表现男女之间的相恋和相思,是《诗经》中爱情诗最主要的部分。如《邶风静女》中就描绘了男女相会的恋爱场景: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躇。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非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这首诗描写了相恋的男女幽会的场景,从男方的视角表达了对女子美好的德行以及美丽的外表的称颂,使得一位活泼善良的女子形象跃立于前。而诗中也句句体现了男子对静女的爱恋之情,表现出男子沉浸在爱情的美好之中,整首诗都透露着热烈欢快、真挚动人的情感。 《诗经》中不仅描写了男女情投意合的美好,也描写了在相恋过程中的矛盾与惆怅,如《郑风遵大路》中就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矛盾。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诗作刻画了相恋多年的男女,男子反目离开,女子抓住男子的衣袖苦苦哀求他留下的场面。整首诗没有头尾,只刻画了这么一个场面,但却活灵活现,仿佛就能看到这样一对男女正在路边拉扯,大片的留白寄予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使这首诗有着意味绵长的风韵。《诗经》中的爱情诗丰富多彩,除了以上的内容,还有许多优秀的篇章。如《周南关雎》表露了男子对一个淑女的日夜思念;《王风木瓜》体现了男女之间对对方深情的心意的报答;如《曹风候人》反映了女子苦苦的单相思等。《诗经》中的丰富多彩的爱情诗,生动的再现了先秦时代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展现了质朴而又自由的民风,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精神文化发展初期的面貌。 然而先秦时期礼教初设,伦理思想的禁锢一定程度上桎梏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自由追求。《诗经》时代的青年男女的感情,已经开始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压迫,少有能自由择偶的权利了。如《郑风将仲子》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这首诗表达了女子对心上人仲子的劝告,担心这样的幽会会被父母兄弟及邻里发现,受到他们的指责和社会舆论的压迫。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经》时代人们的爱情开始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和禁锢,也使得千百年以来,青年男女逐渐直至完全失去了追求爱情的自由。但《诗经》中还描写了受到压迫的青年男女们为了追求自由爱情发出的反抗,如《鄘风柏舟》中,女子对于不能自主择偶,嫁给心上人而喊出了反抗的呼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更有写那些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下幽会甚至私奔的篇章,如《鄘风蝃蝀》中讽刺了一位不顾母命,携郎私奔的女子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这些都是爱情诗篇中最具有思想价值的诗篇,表达了人们不畏强权的自由抗争思想。
诗经的文化精神
诗经的文化精神 集团公司文件内部编码:(TTT-UUTT-MMYB-URTTY-ITTLTY-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