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与消费综述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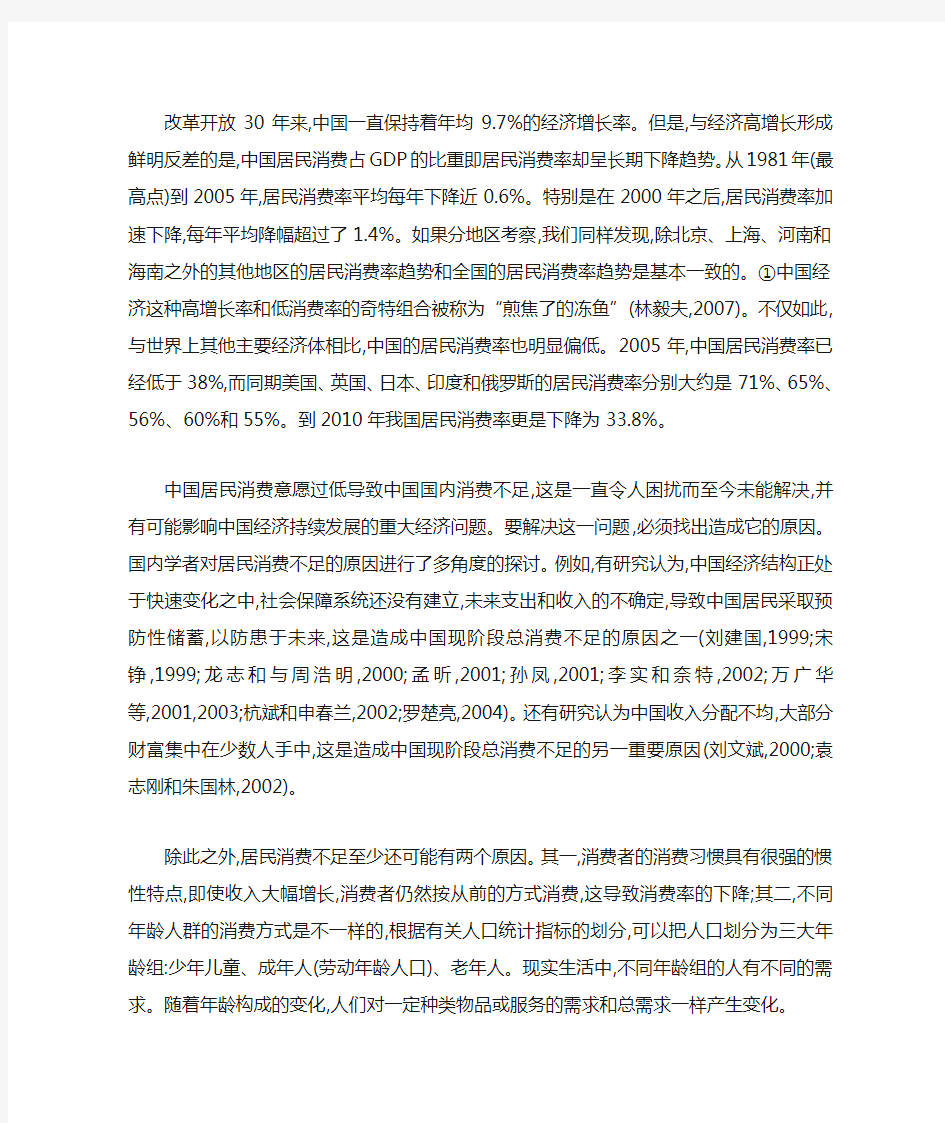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年均9.7%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与经济高增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却呈长期下降趋势。从1981年(最高点)到2005年,居民消费率平均每年下降近0.6%。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率加速下降,每年平均降幅超过了1.4%。如果分地区考察,我们同样发现,除北京、上海、河南和海南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趋势和全国的居民消费率趋势是基本一致的。①中国经济这种高增长率和低消费率的奇特组合被称为“煎焦了的冻鱼”(林毅夫,2007)。不仅如此,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也明显偏低。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已经低于38%,而同期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居民消费率分别大约是71%、65%、56%、60%和55%。到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更是下降为33.8%。
中国居民消费意愿过低导致中国国内消费不足,这是一直令人困扰而至今未能解决,并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找出造成它的原因。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例如,有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社会保障系统还没有建立,未来支出和收入的不确定,导致中国居民采取预防性储蓄,以防患于未来,这是造成中国现阶段总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刘建国,1999;宋铮,1999;龙志和与周浩明,2000;孟昕,2001;孙凤,2001;李实和奈特,2002;万广华等,2001,2003;杭斌和申春兰,2002;罗楚亮,2004)。还有研究认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造成中国现阶段总消费不足的另
一重要原因(刘文斌,2000;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
除此之外,居民消费不足至少还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具有很强的惯性特点,即使收入大幅增长,消费者仍然按从前的方式消费,这导致消费率的下降;其二,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方式是不一样的,根据有关人口统计指标的划分,可以把人口划分为三大年龄组:少年儿童、成年人(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现实生活中,不同年龄组的人有不同的需求。随着年龄构成的变化,人们对一定种类物品或服务的需求和总需求一样产生变化。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微观、宏观两种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率或储蓄率。微观方面,根据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以下简称LCH),消费者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劳动人口的收入除了用于自己消费以外,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一部分储蓄起来用于退休后的生活。劳动人口对应正储蓄,而儿童和退休人口对应负储蓄,因此,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时,该国总储蓄率应该是上升的。反之,当儿童和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时,总储蓄率会下降。但LCH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Hurd,1990;Carroll and Summers,1991;Haque et al.,1999)。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重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
而增加消费,这会部分抵消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另一个微观机制是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ousehold saving demand model,以下简称HSDM)(Samuelson,1958;Neher,1971)。孩子被认为是储蓄的替代物,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可以相应减少;而家庭孩子数量较少时,父母会增加储蓄以防老。另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减少时,父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Becker,1981)。因此,与LCH 相同,HSDM也预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或消费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还可以通过宏观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率(Cutler et al.,1990;Hock and Weil,2006;Weil,1999)。例如,当劳动人口逐步减少时,如果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不变,因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人均消费水平上升;生育率的下降通常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但后者上升的幅度通常会小于前者下降的幅度,如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加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则社会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反之则相反。
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对人口结构与消费/储蓄的关系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老龄化有利于消费增长。Leff( 1969) 使用74 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通过计量检验,认为较高的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和总负担系数不利于储蓄率的提高,换言之,有利于消费增长。舒尔茨( 2005) 在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基础上,使用16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
采用多种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计量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其研究结论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但老龄化对储蓄率产生的影响比较微弱。王宇鹏( 2011) 的研究表明: 人口老龄化因素显著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 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
第二,老龄化不利于消费增长。Modigliani &Cao( 2004) 采用中国1953 ~2000 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结论。Clark &Spengler( 1980) 对美国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政府支付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是青少年人口的 3 倍。一般地,与青少年不同,老年人的抚养费用属于纯消费性支出,因此,政府支出较多的用于老年人,有可能降低未来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李通屏、李建民( 2006) 指出: 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结构的消费性下降和生产性上升,虽然产生了人口红利,但却不利于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率的提高,即人口转变过程中,消费率下降具有其内在必然性。王金营、付秀彬( 2006) 建立了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消费函数,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了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使得收入增长导致的消费水平增速出现减小; 老龄化将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率。
第三,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 2008) 利用1989 ~2004 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 估计
方法,研究发现: 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比较微弱; 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他们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
第四,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变化性: 在人口老龄化的初始阶段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中期阶段为负效应,晚期阶段表现为零效应。于潇、孙猛( 2012) 指出: 中国当前处于人口老龄化初期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在老年人消费系数高于少儿消费系数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正效应; 当老龄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时将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效应。
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储蓄率的文献考察了人口结构变量,但只是间接说明人口结构特征与消费的关系,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民消费率的影响学界鲜有研究。一方面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部分(2008年比重为53.32%),但其仅消费了全国大约1/3的商品,农村市场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国家统计局,2008)。李响、王凯(2010)对1993—2007年中国人口年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与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都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还有李春琦(2010)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利用1978—2007年中国宏观年度数据考察了人口结
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陈冲(2011)在生命周期理论假说框架下,利用1993—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有关宏观数据对理论模型做实证检验,认为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均具有负的影响,即当前我国少儿抚养系数的下降提高了农村居民消费率,而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另外,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非常稳定,伴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正负效应分析对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作用结果,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并不相同。结合作用机制,可以将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正向作用
(1) 补偿性消费。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人在劳动年龄阶段时,家庭负担沉重,消费欲望压低。一般而言,老年人有了充足的时间、储蓄以及强烈的愿望去实现自己以前未曾圆的理想或者梦想。比如,大部分老年人对旅游消费的挚爱便是补偿性消费的体现。这些梦想实现的过程促进了消费需求提升。
(2) 利他性消费。利他性消费对消费需求有正向拉动效应。老年人利他性主要表现为为子女操办婚事、为子女出资购房、照看孙辈等。这在客观上提升了我国老年人的利他性消费。同时,利他性消费还会提升老年人身边亲人的消费水平。
(3) 医疗消费需求。相对于其他年龄段人群,老年人身体机能明
显衰弱,有更高的染病可能性。医疗保健消费需求明显要高,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负向作用
(1) 购买力下降。养老金、子女提供的抚养金等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与在职工资收入相比有着较大差距,因此,他们的购买力相对下降,可用于消费的支出也呈下降态势。
(2) 消费习惯和消费欲望制约。受传统消费思想和习惯制约,老年人更为勤俭节约,可能会抑制其自身消费需求,阻碍消费水平提升。
(3) 利他性消费抑制了自身消费水平提升。农村老年人“利他性”消费心理比较严重。加之,由于能省钱就省钱的想法比较突出,老人“零消费”严重。农村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利他性”消费心理、无养老保障等因素是造成农村老人“零消费”的重要原因。
(4) 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年龄老化,可能导致生产技术得不到更新,不利于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与推广。人口老龄化通过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拉低消费水平提升速度。
(5) 储蓄率下降。生命周期理论显示,老年人由于收入下降,开始动用以前的积蓄,储蓄不断减少。当全社会老龄化加重时,国民储蓄率也会受到影响。储蓄率下降意味着资本积累相对下降,这不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速下降最终会导致国民收入水平增速下降,并作用于消费需求水平。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总效应取决于老龄化正负效应的大小。老龄化正负效应不确定,因此,老龄化总效应的正负也无法判别。在老龄
化初期,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储蓄率的影响有限,对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影响不大,此时老龄化的总效应可能表现出正效应。反之,如果老龄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储蓄率下降幅度过大,这势必影响整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从而使老龄化的总效应为负值。
发现不同年龄人群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 少儿在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和衣着方面的支出较高,成人在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以及居住方面的支出较高,老人在食品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较高。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必然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根据2013 ~2030 年的人口预测数据,从人口老龄化的视角考察了未来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当剔除收入效应、财富效应和偏好转变等因素时,老龄化将导致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居住的消费比重上升,衣着、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下降。但即使考虑收入效应后,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仍将快速增长,而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占比仍将较快下降。这说明人口结构变迁将从需求层面对这些部门造成冲击。政府尤其需要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下医疗需求膨胀、教育需求萎缩的准备,以避免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而教育资源供给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