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注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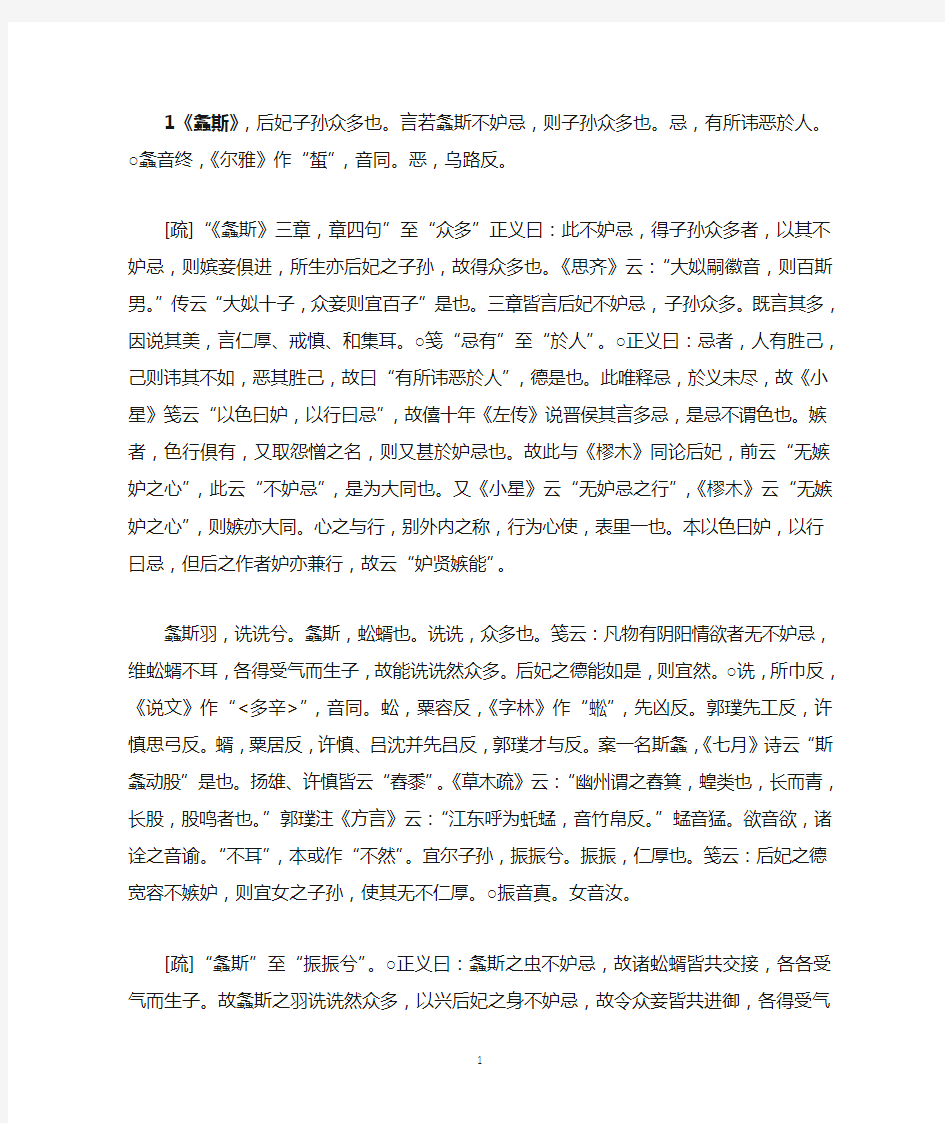

1《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忌,有所讳恶於人。○螽音终,《尔雅》作“蜤”,音同。恶,乌路反。
[疏]“《螽斯》三章,章四句”至“众多”正义曰:此不妒忌,得子孙众多者,以其不妒忌,则嫔妾俱进,所生亦后妃之子孙,故得众多也。《思齐》云:“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传云“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妒忌,子孙众多。既言其多,因说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笺“忌有”至“於人”。○正义曰:忌者,人有胜己,己则讳其不如,恶其胜己,故曰“有所讳恶於人”,德是也。此唯释忌,於义未尽,故《小星》笺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传》说晋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谓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则又甚於妒忌也。故此与《樛木》同论后妃,前云“无嫉妒之心”,此云“不妒忌”,是为大同也。又《小星》云“无妒忌之行”,《樛木》云“无嫉妒之心”,则嫉亦大同。心之与行,别外内之称,行为心使,表里一也。本以色曰妒,以行曰忌,但后之作者妒亦兼行,故云“妒贤嫉能”。
螽斯羽,诜诜兮。螽斯,蚣蝑也。诜诜,众多也。笺云: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维蚣蝑不耳,各得受气而生子,故能诜诜然众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则宜然。○诜,所巾反,《说文》作“<多辛>”,音同。蚣,粟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许慎思弓反。蝑,粟居反,许慎、吕沈并先吕反,郭璞才与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诗云“斯螽动股”是也。扬雄、许慎皆云“舂黍”。《草木疏》云:“幽州谓之舂箕,蝗类也,长而青,长股,股鸣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东呼为虴蜢,音竹帛反。”蜢音猛。欲音欲,诸诠之音谕。“不耳”,本或作“不然”。宜尔子孙,振振兮。振振,仁厚也。笺云:后妃之德宽容不嫉妒,则宜女之子孙,使其无不仁厚。○振音真。女音汝。
[疏]“螽斯”至“振振兮”。○正义曰:螽斯之虫不妒忌,故诸蚣蝑皆共交接,各各受气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诜诜然众多,以兴后妃之身不妒忌,故令众妾皆共进御,各得受气而生子,故后妃子孙亦众多也。非直子多,则又宜汝之子孙,使之振振兮无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虫,故举羽以言多也。○传“螽斯,蚣蝑”。○正义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虽颠倒,其实一也。故《释虫》云:“蜤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谓舂黍也。”陆机《疏》云:“幽州人谓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类也。长而青,长角,长股,肱鸣者也。或谓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瑇瑁叉,五月中,以两股相切作声,闻数十步是也。”此实兴也。传不言兴者,《郑志》答张逸云:“若此无人事,实兴也,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众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传不言兴也。传言兴也。笺言兴者喻,言传所兴者欲以喻此事也,兴、喻名异而实同。或与传兴同而义异,亦云兴者喻,《摽有梅》之类也。亦有兴也,不言兴者,或郑不为兴,若“厌浥行露”之类。或便文径喻,若“褖衣”之类。或同兴,笺略不言喻者,若《邶风》“习习谷风”之类也。或叠传之文,若《葛覃》笺云“兴焉”之类是也。然有兴也,不必要有兴者,而有兴者,必有兴也。亦有毛不言兴,自言兴者,若《四月》笺云“兴人为恶有渐”是也。或兴喻并不言,直云犹亦若者。虽大局有准,而应机无定。郑云喻者,喻犹晓也,取事比方以晓人,故谓之为喻也。○笺“凡物”至“宜然”。○正义曰:昭十年《左传》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是有情欲者无不妒也。序云“若螽斯不妒忌”,则知唯蚣蝑不耳。○传“振振,仁厚”。○正义曰:言宜尔子孙,明子孙皆化。后妃能宽容,故为仁厚,即宽仁之义也。《麟趾》、《殷其雷》传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雷》其妻劝夫以义,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为信厚也。○笺“后妃”至“仁厚”。○正义曰:此止说后妃不妒,众妾得生子众多,而言孙者,协句。且孙则子所生,生子众则孙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孙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乱者,此诗人盛论之,据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薨薨,众多也。绳绳,戒慎也。○薨,呼弘反。螽
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揖揖,会聚也。蛰蛰,和集也。○揖,子入、侧立二反。蛰,尺十反,徐又直立反。《螽斯》三章,章四句。
2《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老而无妻曰鳏。○“桃夭”,於骄反。桃,木名。《说文》作“枖”,云“木少盛貌”。<鱼睘>,本亦作“鳏”,古顽反。
[疏]“《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鳏民”。○正义曰:作《桃夭》诗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内脩其化,赞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礼,昏娶不失其时,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妒忌,则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过限,昏姻以时,行不逾月,故周南之国皆无鳏独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虽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内赞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妒忌后,言其所致也。且言致从家至国,亦自近致远之辞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时,下二句是也。国无鳏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经无所当也。○笺“老而”至“曰鳏”。○正义曰:刘熙《释名》云“无妻曰鳏”者,“愁悒不寐,目恒鳏鳏然,故其字从鱼,鱼目不闭也。无夫曰寡。寡,踝也,单独之名”。鳏或作“矜”,同。盖古今字异。《王制》曰:“老而无妻谓之矜,老而无夫谓之寡。”则鳏、寡,年老不复嫁娶之名也。《孝经》注云:“丈夫六十无妻曰鳏,妇人五十无夫曰寡也。”知如此为限者,以《内则》云“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则妇人五十不复御,明不复嫁矣,故知称寡以此断也。《士昏礼》注云“姆,妇人年五十出而无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为昏。妇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复娶,为鳏、寡之限也。《巷伯》传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间居”,谓妇人也。《内则》曰“唯及七十,同藏无间”,谓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鳏之言鳏,鳏无所亲”,则寡者少也,言少匹对耳,故《鸿雁》传“偏丧曰寡”,此其对例也。妇人无称鳏之文,其男子亦称寡,襄二十七年传曰:“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故《小雅》云:“无夫无妇并谓之寡。丈夫曰索,妇人曰釐。”又许慎曰“楚人谓寡妇为霜”,并其异名也。鳏、寡之名,以老为称,其有不得及时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无鳏民,谓年不过时,过则谓之鳏,故舜年三十不娶,《书》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唐》传:“孔子曰:‘舜父顽母嚚,不见室家之端,故谓之鳏。’”是三十不娶称鳏也。又《何草不黄》云“何人不矜”,尚从军未老,不早还见室家,亦谓之矜。《易·大过》“九二,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彼郑注云:以丈夫年过娶二十之女,老妇年过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妇五十犹得嫁娶者,《礼》:“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是年过可以改娶,则妇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鳏寡,据其不得嫁娶者耳。传言崔杼为寡,则有子亦称寡。鳏寡据其困者多是无子,故《王制》及《周礼》皆云“天民之穷而无所告者”。
传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壮宜其室家为不逾时,则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时也。但传说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摽有梅》卒章,《传》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礼会而行之”,谓期尽之法,则男女以正,谓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时行,则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则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东门之杨》传曰“男女失时,不逮秋冬”,则秋冬嫁娶正时也。言宜其室家无逾时,则三章皆为秋冬时矣。郑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为昏,是礼之正法,则三章皆上二句言妇人以年盛时行,谓二十也,下句言年时俱当,谓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兴也。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笺云:兴者,逾时妇人皆得以年盛时行也。○少,诗照反。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无逾时者。笺云:宜者,谓男女年时俱当。○当,丁浪反。
[疏]“桃之”至“室家”。○毛以为少壮之桃夭夭然,复有灼灼然。此桃之盛华,以兴有十五至十九少壮之女亦夭夭然,复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归嫁於夫,正得善时,宜其为室家矣。○郑唯据年月不同,又宜者,谓年时俱善为异。○传“桃有
华之盛者”。○正义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华之盛。桃或少而未华,或华而不少。此诗夭夭、灼灼并言之,则是少而有华者,故辨之。言桃有华之盛者,由桃少故华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笺“时妇”至“时行”。○正义曰:此言年盛时,谓以年盛二十之时,非时月之时。下云“宜其室家”,乃据时月耳。○笺“宜者”至“俱当”。○正义曰:易传者以既说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归”,后言“宜其室家”,则总上之辞,故以为年时俱当。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蕡,实貌。非但有华色,又有妇德。○蕡,浮云反。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家室,犹室家也。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体至盛也。○蓁,侧巾反。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尽以为宜。笺云:家人,犹室家也。○尽,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疏]笺“家人犹室家”。○正义曰:易传者以其与上相类,同有“宜其”之文,明据宜其为夫妇,据其年盛,得时之美,不宜横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传》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谓夫妇也。此云“家人”,家犹夫也,人犹妇也,以异章而变文耳,故云“家人犹室家”也。《桃夭》三章,章四句。
3《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菟罝,菟又作兔,他故反;罝音子斜反,《说文》子余反。好,呼报反。[疏]“《兔罝》三章,章四句”至“众多”。○正义曰:作《兔罝》诗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关雎》之化行,则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贤人众多。由贤人多,故兔罝之人犹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经三章皆言贤人众多之事也。经直陈兔罝之人贤,而云多者,笺云:罝兔之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则是贤人众多。是举微以见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芣苡》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而设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后,《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则论天下昏姻得时,为自近及远之辞,故云所致也。此《兔罝》又承其后,已在致限,故变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芣苡》以后妃事终,故总言之美。其实三者义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妒忌,此言《关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说昏姻男女,故言不妒忌,此说贤人众多,以《关雎》求贤之事,故言《关雎》之化行。《芣苡》则妇人乐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随义立文,其实总上五篇致此三篇。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肃肃,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声也。笺云:罝兔之人,鄙贱之事,犹能恭敬,则是贤者众多也。○椓,陟角反。丁,陟耕反。罟音古,罔也。杙,本又作弋,羊职反,郭羊北反。《尔雅》云“枳谓之杙”,李巡云:“橛也。”枳音特。橛音其月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干,扞也。笺云:干也,城也,皆以御难也。此罝兔之人,贤者也,有武力,可任为将帅之德,诸侯可任以国守,扞城其民,折冲御难於未然。○赳,居黝反,《尔雅》云:“勇也。”干如字,孙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旧户旦反,沈音幹。扞,户旦反。御,鱼吕反。难,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将,子匠反。帅,色类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鸩反,后不音者放此。守,手又反。折,之役反。冲,昌容反。[疏]“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至“干城”。○毛以为肃肃然恭敬之人,乃为兔作罝,身自椓杙。其椓杙之声丁丁然,虽为鄙贱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肃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为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为之防固也。○郑唯干城为异。言此罝兔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国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冲御难於未然也。谓公侯使之与民作扞城也。○传“肃肃”至“杙声”。○正义曰:“肃肃,敬也”,《释训》文。此美其贤人众多,故为敬。《小星》云“肃肃宵征”,故传曰:“肃肃,疾貌。”《鸨羽》、《鸿雁》说鸟飞,文连其羽,故传曰:“肃肃,羽声也。”《黍苗》说宫室,笺云:“肃肃,严正之貌。”各随文势也。《释器》云:“兔罟谓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径路,张罝捕之也。”《释宫》云:“枳谓之杙。”李巡云:“杙谓鬘也。”此“丁丁”连“椓之”,故知椓杙声,故《伐木》传亦云:“丁丁,伐木声。”○传“干,扞也”。○正义曰:《释言》文。孙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传曰:“可以制断,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为腹心。则好仇者,公侯自
以为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为扞城。言以武夫自固,为扞蔽如盾,为防守如城然。○笺“干也”至“未然”。○正义曰:笺以此武夫为扞城其民,易传者以其赳赳武夫,论有武任,明为民扞城,可以御难也。言未然者,谓未有来侵者,来则折其冲,御其难也。若使和好,则此武夫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肃肃兔罝,施于中逵。逵,九达之道。○施,如字。逵,求龟反。杜预注《春秋》云:“涂方九轨。”[疏]传“逵,九达之道”。○正义曰:《释宫》云:“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达谓之剧旁。”孙炎云:“旁出歧多故曰剧。”“四达谓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达谓之康。”孙炎云:“康,乐也,交会乐道也。”“六达谓之庄。”孙氏云:“庄,盛也,道烦盛。”“七达谓之剧骖。”孙氏云:“三道交,复有一歧出者。”“八达谓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达谓之逵。”郭璞云:“四道交出,复有旁通者。”庄二十八年《左传》“楚伐郑,入自纯门,及逵市”。杜预云:“逵并九轨。”案《周礼》“经涂九轨”,不名曰逵,杜意盖以郑之城内不应有九出之道,故以为并九轨,於《尔雅》则不合也。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笺云:怨耦曰仇。此罝兔之人,敌国有来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贤也。[疏]“赳赳”至“好仇”。○毛以为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为公侯之好匹。此虽无传,以毛仇皆为匹,郑唯好仇为异。肃肃兔罝,施于中林。中林,林中。○施如字,沈以豉反。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可以制断,公侯之腹心。笺云:此罝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为策谋之臣,使之虑无,亦言贤也。○断,丁乱反。[疏]“公侯腹心”。○毛以为兔罝之人有文有武,可以为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谋事,能制断其是非。○郑以为此罝兔之人贤者,若公侯行攻伐时,可使之为腹心之计,谋虑前事。○传“可以”至“腹心”。○正义曰:解武夫可为腹心之意。由能制断,公侯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己腹心。○笺“此罝”至“言贤”。○正义曰:笺以首章为御难,谓难未至而预御之。二章为和好怨耦,谓己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谓行攻伐,又可以为策谋之臣,使之虑无也。虑无者,宣十二年《左传》文也,谋虑不意之事也。今所无,不意有此,即令谋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谋,明自往攻伐,非和好两军,与二章异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天下和,政教平也。○芣苡,音浮。苡,本亦作“苡”,音以。《韩诗》云:“直曰车前,瞿曰芣苡。”郭璞云:“江东呼为虾蟆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谓之牛舌,又名当道,其子治妇人生难。”《本草》云:“一名牛遗,一名胜舄。”《山海经》及《周书·王会》皆云:“芣苡,木也,实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卫氏传及许慎并同此。王肃亦同,王基已有驳难也。舄音昔。[疏]“《芣苡》三章,章四句”至“有子”。○正义曰:若天下乱离,兵役不息,则我躬不阅,於此之时,岂思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妇人始乐有子矣。经三章,皆乐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上无“天下”二字,据笺,则有者误也。○笺“天下和,政教平”。○正义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称王,王必以天下之辞,故《驺虞序》曰“天下纯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实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图瑞毕至,故曰太平。虽武王之时,亦非太平也,故《论语》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注云:“谓未致太平。”是也。武王虽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贡职,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称太平,故《鱼丽》传、《鱼藻》笺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之时,其实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据颂声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鱼》、《既醉》、《维天之命》序及《诗谱》皆言太平。惟郑《康诰》注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洽时和,乃得称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时妇人乐有子者众,故频言采采,见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须。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辞;有者,已藏之称,总其终始也。二章言采时之状,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成之处,或袺之,或襭之。首章采之,据初往,至则掇之、捋之,既得则袺
之、襭之,归则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妇人乐采而有子,故与采之为对,所以总终始也。六者本各见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捋事殊,袺、襭用别,明非一人而为此六事而已。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非一辞也。芣苡,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任焉。薄,辞也。采,取也。笺云:薄言,我薄也。[疏]传“芣苡,马舄”。○正义曰:《释草》文也。郭璞曰:“今车前草大叶长穗,好生道边。江东呼为虾蟆衣。”陆机《疏》云:“马舄,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也。今药中车前子是也。幽州人谓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妇人难产。王肃引《周书·王会》云:‘芣苡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駮云:‘《王会》所记杂物奇兽,皆四夷远国各赍土地异物以为贡贽,非《周南》妇人所得采。’是芣苡为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怀任者,即陆机《疏》云所治难产是也。○笺“薄言,我薄也”。○正义曰:毛传言“薄,辞”,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训经“言”也,“薄”还存其字,是为“辞”也。言“我薄”者,我薄欲如此,於义无取,故为语辞。传於“薄汙我私”不释者,就此众也。《时迈》云:“薄言震之。”笺云:“薄犹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笺云:“王始言饯送之。”以“薄”为“始”者,以《时迈》下句云“莫不震叠”,明上句“薄言震之”为始动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絷其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时将行,王始言饯送之。《诗》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为“始”,馀皆为“辞”也。采采芣苡,薄言有之。有,藏之也。采采芣苡,薄言掇之。掇,拾也。○掇,都夺反,一音知劣反。拾音十。采采芣苡,薄言捋之。捋,取也。○捋,力活反。采采芣苡,薄言袺之。袺,执衽也。○袺,音结。衽,入锦反,又而鸩反,衣际也。采采芣苡,薄言襭之。扱衽曰襭。○襭,户结反,一本作“撷”,同。扱,初洽反。[疏]传“袺执”至“曰襭”。○正义曰:《释器》云:“执衽谓之袺。”孙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谓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带。”衽者,裳之下也。置袺,谓手执之而不扱,襭则扱於带中矣。《芣苡》三章,章四句。
4《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纣时淫风遍於天下,维江、汉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汉广,汉水名也。《尚书》云:“嶓冢导漾水,东流为汉。”被,皮义反。纣,直九反。殷王也。遍,边见反。[疏]“《汉广》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正义曰:作《汉广》诗者,言德广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苡》之化,今被於南国,美化行於江、汉之域,故男无思犯礼,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广所及然也。此与《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赞,於此言文王者,因经陈江、汉,指言其处为远,辞遂变后妃而言文王,为远近积渐之义。叙於此既言德广,《汝坟》亦广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国则六州,犹《羔羊序》云“召南之国”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广,故直言南。彼论诸侯,故止言召南之国。此“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总序三章之义也。○笺“纣时”至“教化”。○正义曰:言先者,以其馀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以江、汉之域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经、序有江、汉之文,故言之耳。其实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汉独先也。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兴也。南方之木,美乔上竦也。思,辞也。汉上游女,无求思者。笺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叶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兴者,喻贤女虽出游流水之上,人无欲求犯礼者,亦由贞絜使之然。○乔木,亦作“桥”,渠骄反,徐又纪桥反。休息并如字,古本皆尔,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尔。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汉水”。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潜行为泳。永,长。方,泭也。笺云:汉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潜行乘泭之道。今以广长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贞絜,犯礼而往,将不至也。○泳音咏。泭,芳于反,本亦作“氵符”,又作“桴”,或作“柎”,并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谓之,谓之筏。筏,秦、晋通语也。”孙炎注《尔雅》云:“方木置水为柎筏也。郭璞云:“水中筏
也。”又云:“木曰,竹曰筏,小筏曰泭。”音皮隹反。柎、筏同音伐。樊光《尔雅》本作“柎”。[疏]“南有”至“方思”。○正义曰:木所以庇荫,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乔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兴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时,今汉上有游女,以贞絜之故,不可犯礼而求。是为木以高其枝叶,人无休息者;女由持其絜清,人无求思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则在室无敢犯礼可知也。出者犹能为贞,处者自然尤絜。又言水所以济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汉之广阔矣,江之永长矣,不可潜行乘泭以求济,以兴女皆贞絜矣,不可犯礼而求思。然则方、泳以渡江、汉,虽往而不可济,喻犯礼以思贞女,虽求而将不至。是为女皆贞絜,求而不可得,故男子无思犯礼也。定本游女作游。○传“思辞”至“思者”。○正义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为义,故为辞也。经“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传解“乔木”之下,先言“思,辞”,然后始言“汉上”,疑经“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则?诗之大体,韵在辞上,疑休、求字为韵,二字俱作“思”,但未见如此之本,不敢辄改耳。《内则》云:“女子居内,深宫固门。”此汉上有游女者,《内则》言“阍寺守之”,则贵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则执筐行馌,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无求者。定本“乔上竦”,无木字。○笺“不可”至“之然”。○正义曰:笺知此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据男子之辞,若恒不可,则不应发“不可”之辞,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笺与下笺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总解经“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笺下言渡江、汉有潜行、乘泭之道,不释“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风大行之时,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絜。此云絜者,本未必已淫,兴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荫,水可方、泳,犹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广长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时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叶”,解传言“上竦”也。言女虽出游汉水之上者,对不出不游者言。无求犯礼者,谓男子无思犯礼,由女贞絜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贞而男始息者,以奸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严於女,法缓於男,故男见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贞信,尚有强暴之男是也。○传“潜行”至“方泭”。○正义曰:“潜行为泳”,《释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七里。“永,长”,《释诂》文。“方,泭”,《释言》文。孙炎曰:“方,水中为泭筏也。”《论语》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编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笺“汉也”至“不至”。○正义曰:此江汉、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风》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虽深,不长於江、汉故也。言“将不至”者,虽求之,女守礼,将不肯至也。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薪貌。错,杂也。笺云:楚,杂薪之中尤翘翘者。我欲刈取之,以喻众女皆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翘,祁遥反,沈其尧反。“尤高絜”者,一本无“絜”字。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秣,养也。六尺以上曰马。笺云:之子,是子也。谦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原秣其马,致礼饩,示有意焉。○秣,莫葛反。《说文》云:“食马穀也。”上,时掌反,下文同。饩,虚气反,牲腥曰饩。[疏]“翘翘”至“其马”。○正义曰:翘翘然而高者,乃是杂薪。此薪虽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杂薪之中,尤翘翘而高故也。以兴贞絜者乃是众女,此众女虽皆贞絜,我欲取其尤贞絜者。又言是其尤絜者,之子若往归嫁,我欲以粟秣养其马,乘之以致礼饩,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传“翘翘,薪貌”。○正义曰:翘翘,高貌。传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翘翘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翘翘连言错薪,故为薪貌。《鸱鸮》云“予室翘翘”,即云“风雨所漂摇”,故传曰:“翘翘,危也。”庄二十二年《左传》引逸诗曰“翘翘车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远,故服虔云:“翘翘,远貌。”○笺“楚杂”至“絜者”。正义曰:薪,木称,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谓之薪。”下章蒌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学记》注以楚为荆,《王风》、《郑风》并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杂薪之中尤翘翘”,言尤明杂薪亦翘翘也。○笺“之子”至“意焉”。正义曰:《释训》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论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则‘之’为语助,人言之子者,犹云是此子也。《桃夭》传云嫁子,彼说嫁事,为嫁者之
子,此则贞絜者之子,《东山》之子言其妻,《白华》之子斥幽王,各随其事而名之。”言“谦不敢斥其適己”,谓云往嫁,若斥適已,当言来嫁,所以《桃夭》、《鹊巢》、《东山》不为谦者,不自言己,说他女嫁,故不为谦也。言“致礼饩”者,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问名、纳吉皆如之。纳徵用玄纁、束帛、俪皮,是士礼也。《媒氏》云“纯帛无过五两”,谓庶人礼也。欲致礼,谓此也。饩,谓牲也。昏礼不见用牲文,郑以时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执谦,不敢斥言其適己。言养马,是欲致礼饩,示有意求之,但谦不斥耳。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蒌。蒌,草中之翘翘然。○蒌,力俱反,马云:“蒌,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疏]传“蒌,草中之翘翘然”。○正义曰:传以上楚是木,此蒌是草,故言草中之翘翘然。《释草》云:“购,蔏蒌。”舍人曰:“购一名蔏蒌。”郭云:“蔏蒌,蒌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东用羹鱼也。”陆机《疏》云:“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馀。好生水边及泽中,正月根牙生,旁茎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叶又可蒸为茹。”是也。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五尺以上曰驹。[疏]传“五尺以上曰驹”。正义曰:《廋人》云:“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故上传曰“六尺以上曰马”。此驹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笺云“六尺以下曰驹”是也。《辀人》注国马谓种、戎、齐、道,高八尺。田马高七尺,驽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龙、騋、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龙”不合《周礼》也。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广》三章,章八句。
5《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言此妇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坟,符云反。《常武》传云:坟,涯也。能闵,密谨反,伤念也。一本有“妇人”二字。被,皮义反。[疏]“《汝坟》三章,章四句”至“以正”。○正义曰:作《汝坟》诗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念其君子,犹复劝勉之以正义,不可逃亡,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诸叙“言道”者皆为“言”,不为“道”耳。上云“德广所及”,先德后道,事之次也。言汝坟之国,以汝坟之厓,表国所在,犹江、汉之域,非国名也。闵者,情所忧念。勉者,劝之尽诚。欲见情虽忧念,犹能劝勉,故先闵而后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惮劳,虽则勤苦,无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闵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闵”上无“妇人”二字。遵彼汝坟,伐其条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坟,大防也。枝曰条,榦曰枚。笺云:伐薪於汝水之侧,非妇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贤者,而处勤劳之职,亦非其事。○枚,妹回反,榦也。未见君子,惄如调饥。惄,饥意也。调,朝也。笺云:惄,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纣心}本又作“惄”,乃历反,《韩诗》作“溺”,音同。调,张留反,又作“輖”,音同。[疏]“遵彼”至“调饥”。○正义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侧,伐其条枝枚榦之薪。以为己伐薪汝水之侧,非妇人之事,因闵己之君子贤者,而处勤劳之职,亦非其事也。既闵其劳,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见君子之时,我之思君子,惄然如朝饥之思食也。○传“汝水”至“曰枚”。○正义曰:《释水》云:“汝为濆。”传曰“济汝”,故知是水名也。“坟,大防”,《释丘》文。李巡曰:“坟谓厓岸状如坟墓,名大防也。”故《常武》传曰:“坟,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坟。”则此坟谓汝水之侧厓岸大防也。若然,《释水》云“水自河出为灉,江为沱”,别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诗》云遵彼汝濆”,则郭意以此汝坟为濆,汝所分之处有美地,因谓之濆。笺、传不然者,以彼濆从水,此坟从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濆汝之间故也。枝曰条,榦曰枚,无文也。以枚非木,则条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对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条而已。枚,细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礼》有《衔枚氏》,注云“枚状如箸”,是其小也。《终南》云:“有条有梅。”文与梅连,则条亦木名也。故传曰“条、槄”,与此异也。下章言“条肄”,肄,馀也,斩而复
生,是为馀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传》曰:“晋国不恤宗周之阙,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馀也。”是肄为复生之馀。○笺“伐薪”至“其事”。○正义曰:知妇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妇人能闵其君子”,则闵其君子者,是汝坟之国妇人也。经言“遵彼汝坟”,故知妇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为命妇,而伐薪者,由世乱时劳,君子不在。犹非其宜,故云非妇人之事。妇人之事,深宫固门,纺绩织纴之谓也。不贤而劳,是其常,故以贤者处勤为非其事也。○传“惄,饥意”。笺“惄,思”。○正义曰:《释诂》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释言》云:“惄,饥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饥也。”然则惄之为训,本为思耳。但饥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为饥。惄是饥之意,非饥之状,故传言“饥意”。笺以为思,义相接成也。此连调饥为文,故传以为饥意。《小弁》云“惄焉如捣”,无饥事,故笺直训为“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笺又云:“如朝饥之思食。”遵彼汝坟,伐其条肄。肄,馀也。斩而复生曰肄。○肄,以自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复,扶富反。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既,已。遐,远也。笺云:己见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见之,知其不远弃我而死亡,於思则愈,故下章而勉之。○思,如字,又息嗣反。[疏]“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正义曰: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古之人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妇人以君子处勤劳之职,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觊君子事讫得反。我既得见君子,即知不远弃我而死亡,我於思则愈。未见,恐其逃亡;既见,知其不死,故忧思愈也。○笺“已见”至“勉之”。○正义曰:言不远弃我,我者,妇人自谓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复得见,为远弃我。今不死亡,已得见之,为不远弃我也。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义,不避劳役,不由於妇人,然妇人闵夫之辞,据妇人而言耳。郑知不直远弃己而去,知为王事死亡者,以闵其勤劳,岂为弃己而忧也。下章云“父母孔迩”,是勉劝之辞,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笺之下云“己见君子,君子反也,於己反得见之”,俗本多不然。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赪,赤也,鱼劳则尾赤。燬,火也。笺云:君子仕於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鲂,符方反,鱼名。赪,敕贞反,《说文》作“<赤巠>”,又作“赪”,并同。燬音毁,齐人谓火曰燬。郭璞又音货。字书作“ 尾”,音毁,《说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齐人曰燬,吴人曰 尾,此方俗讹语也。瘦,色救反。酷,苦毒反。虽则如燬,父母孔迩。孔,甚。迩,近也。笺云: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於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辟此”,一本作“辞此”。处,昌虑反。为踈,于伪反。踈亦作疏。[疏]“鲂鱼”至“孔迩”。○正义曰:妇人言鲂鱼劳则尾赤,以兴君子苦则容悴。君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炽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虽则如火,当勉力从役,无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自思念,以免於害,无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谓勉之以正也。○传“赪,赤”至“燬火”。○正义曰:《释器》云:“再染谓之赪。”郭云:“赪,浅赤也。”鲂鱼之尾不赤,故知劳则尾赤。哀十七年《左传》曰:“如鱼赪尾,衡流而彷徉。”郑氏云:鱼肥则尾赤,以喻蒯瞶淫纵。不同者,此自鲂鱼尾本不赤,赤故为劳也。郑以为彼言彷徉为鱼肥,不指鱼名,犹自有肥而尾赤者。服氏亦为鱼劳。“燬,火”,《释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孙炎曰:“方言有轻重,故谓火为毁也。”○笺“君子”至“纣存”。○正义曰:言君子仕於乱世,不斥大夫士。王肃云:“当纣之时,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坟之大夫久而不归。”乐详、马昭、孔晁、孙毓等皆云大夫,则笺云仕於乱世,是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伤悲”,《伯兮》则云“甘心首疾”,忧思昔在於情性,岂有劝以德义,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称“勉之以正”,则非庶人之妻。言贤者不宜勤劳,则又非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雷》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其妻劝以义。此引父母之甚近,伤王室之酷烈,闵之则恐其死亡,勉之则劝其尽节,比之於《殷其雷》,志远而义高,大夫妻於是明矣。虽王者之风,见感文王之化,但时实纣存,文王率诸侯以事殷,故汝坟之国,大夫犹为殷纣所役。若称王以后,则不复事纣,六州,文王所统,不为纣役也。
笺以二《南》文王之事,其衰恶之事,举纣以明之。上《汉广》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时,言纣时淫风大行。此云“王室如燬”,言是时纣存。《行露》云“衰乱之俗微”,言纣末之时,《野有死麕》云“恶无礼”,言纣时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纣时。法有详略,承此可知也。《汝坟》三章,章四句。
6《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关雎》之时,以麟为应,后世虽衰,犹存《关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犹尚振振然,有似麟应之时,无以过也。○麟之趾,吕辛反,瑞兽也。《草木疏》云:“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员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锺吕,行中规矩,王者至仁则出。”服虔注《左传》云:“视明礼脩则麒麟至。”麕,音俱伦反。序本或直云“麟趾”,无“之”字。“止”本亦作“趾”,两通之。应,应对之应,序、注及下传“应礼”同。[疏]“《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时”。○正义曰:此《麟趾》处末者,有《关雎》之应也。由后妃《关雎》之化行,则令天下无犯非礼。天下既不犯礼,故今虽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时,信厚无以过也。《关雎》之化,谓《螽斯》以前。天下无犯非礼,《桃夭》以后也。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此篇三章是也。此篇处末,见相终始,故历序前篇,以为此次。既因有麟名,见若致然,编之处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时,不为有《关雎》而应之。大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岂一人作诗,而得相顾以为终始也?又使天下无犯非礼,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难化於天下,岂其然乎!明是编之以为示法耳。○笺“关雎”至“以过”。○正义曰:笺欲明时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关雎》之时,以麟为应,谓古者太平,行《关雎》之化,至极之时,以麟为瑞。后世虽衰,谓纣时有文王之教,犹存《关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应之时,无以过也。信厚如麟时,实不致麟,故张逸问《麟趾》义云:“《关雎》之化,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时。笺云喻今公子亦信厚,与礼相应,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时,《关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谓当文王与纣之时,而周之盛德,《关雎》化行之时,公子化之,皆信厚与礼合,古太平致麟之时,不能过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郑言古太平致麟之时者,案《中候·握河纪》云:“帝轩题象,麒麟在囿。”又《唐》传云:“尧时,麒麟在郊薮。”又《孔丛》云:“唐、虞之世,麟凤游於田。”由此言之,黄帝、尧、舜致麟矣。然感应宜同,所以俱行《关雎》之化,而致否异者,亦时势之运殊。古太平时,行《关雎》之化至极,能尽人之情,能尽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时,殷纣尚存,道未尽行,四灵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时,天下太平,亦应致麟,但无文证,无以言之。孔子之时,所以致麟者,自为制作之应,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难此也。三章皆以麟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兽,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从下而上,次见其额,次见其角也。同姓疏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与“定”为韵,故先言之。麟之趾。振振公子,兴也。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笺云:兴者,喻今公子亦信厚,与礼相应,有似於麟。○振,音真。相应,音鹰,当也。于嗟麟兮!于嗟,叹辞。[疏]“麟之”至“麟兮”。○正义曰:言古者麟之趾,犹今之振振公子也。麟之为兽,属信而应礼,以喻今公子亦振振然信厚,与礼相应。言公子信厚,似於麟兽也,即叹而美之,故于嗟乎叹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时兮,虽时不致麟,而信与之等。反覆嗟叹,所以深美之也。○传“麟信”至“信厚”。○正义曰:传解四灵多矣,独以麟为兴,意以麟於五常属信,为瑞则应礼,故以喻公子信厚而与礼相应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兽,以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应礼,则与《左氏》说同,以为脩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传》服虔注云:“视明礼脩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扰,言从义成则神龟在沼,听聪知正而名山出龙,貌恭体仁则凤皇来仪。”《驺虞》传云“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是与《左传》说同也。说者又云,人
臣则脩母致子应,以昭二十九年《左传》云水官不脩则龙不至故也。人君则当方来应,是以《驳异义》云“玄之闻也,《洪范》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属金,孔子时,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可从,故天应以金兽之瑞”,是其义也。笺“公子信厚,与礼相应,有似於麟”,申述传文,亦以麟为信兽。《驳异义》以为西方毛虫,更为别说。○传“于嗟,叹辞”。○正义曰:此承上信厚,叹信厚也。故《射义》注云:“‘于嗟乎驺虞’,叹仁人也。”明此叹信厚可知。麟之定。振振公姓,定,题也。公姓,公同姓。○定,都佞反,字书作“顁”,音同。题,徒兮反,郭璞注《尔雅》:“额也。”本作“颠”,误。于嗟麟兮![疏]传“定,题”。○正义曰:《释言》文。郭璞曰:“谓额也。”传或作“颠”。《释畜》云:“的颡,白颠。”颠亦额也,故因此而误。定本作“题”。○传“公姓,公同姓”。○正义曰:言同姓,疏於同祖。上云“公子”,为最亲。下云“公族”,传云“公族,公同祖”,则谓与公同高祖,有庙属之亲。此“同姓”,则五服以外,故《大传》云“五世袒免,杀同姓”是也。《大传》注又云“外高祖为庶姓”,是同高祖为一节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对例为然。案《杕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不如我同姓。”传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为异。彼为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无异称,故为一也。且皆对他人异姓,不限远近,直举祖父之同为亲耳。襄十二年《左传》曰:“同姓於宗庙,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又曰“鲁为诸姬,临於周庙”,谓同姓於文王为宗庙也。“邢、凡、蒋、茅、胙、祭,临於周公之庙”,是同宗於祖庙也。同族谓五服之内,彼自以五服之外远近为宗姓,与此又异。此皆君亲,非异国也。要皆同姓以对异姓,异姓最为疏也。麟之角。振振公族,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笺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象”。于嗟麟兮![疏]传“麟角”笺至“不用”。○正义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笺申说传文也。《释兽》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传曰:“麟,麕身,牛尾,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陆机《疏》:“麟,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员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锺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入陷阱,不罹罗网。王者至仁则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应麟也。故司马相如赋曰‘射麋脚麟’,谓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国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召南鹊巢诂训传第二
7《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起家而居有之,谓嫁於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鸤鸠然,而后可配国君。○鹊,七略反,《字林》作“<昔隹>”。行,下孟反,下注同。尸鸠,本又作“鸤”,音同。《尔雅》云:“鸣鸠,鴶鵴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东呼获穀。”《草木疏》云:“一名击穀。”案:尸鸠有均一之德,饲其子,旦从上而下,暮从下而上,平均如一,杨雄云:“戴胜也。”[疏]“《鹊巢》三章,章四句”至“配焉”。○正义曰:作《鹊巢》诗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国君积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来居处共有之,由其德如鸤鸠,乃可以配国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经三章皆言起家而来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为诸侯,而言国君者,《召南》诸侯之风,故以夫人国君言之。文王继世为诸侯,而云“积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为难,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显夫人之德,非谓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兴也。鸠,鸤鸠,秸鞠也。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笺云: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寝也。○秸,古八反,又音吉。《尔雅》作“鴶鞠”,音菊。《尔雅》作“鵴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百两,百乘也。诸侯之子嫁於诸侯,送御皆百乘。笺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鸤鸠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车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讶”,又作“迓”,同。王肃鱼据反,云“侍也”。乘,绳证反,下
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疏]“维鹊”至“御之”。○正义曰:言维鹊自冬历春功著,乃有此巢窠,鸤鸠往居之,以兴国君积行累功勤劳乃有此爵位维,夫人往处之。今鸤鸠居鹊之巢,有均壹之德,以兴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国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鸤鸠之德,其往嫁之时,则夫家以百两之车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礼迎具备。○传“鸤鸠,秸鞠”。○正义曰:序云“德如鸤鸠”也,《释鸟》云“鸤鸠,秸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东呼获穀。”《埤仓》云“鴶鵴”,《方言》云“戴胜”,谢氏云“布穀类也”。诸说皆未详,布穀者近得之。○笺“鹊之”至“燕寝”。○正义曰:《推度灾》曰:“鹊以复至之月始作室家,鸤鸠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复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鹊始巢”,则季冬犹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与《月令》不同者,大率记国中之候,不能不有早晚,《诗纬》主以释此,故依而说焉。此以巢比爵位,则鸤鸠居巢,犹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谓以室比巢。燕寝,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寝。下传言“旋归,谓反燕寝”,亦是也。○传“百两”至“百乘”。○正义曰:《书序》云“武王戎车三百两”,皆以一乘为一两。谓之两者,《风俗通》以为车有两轮,马有四匹,故车称两,马称匹。言诸侯之女嫁於诸侯,送迎皆百乘者,探解下章“将之”,明此诸侯之礼,嫁女於诸侯,故迎之百乘;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虽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为礼也。此夫人斥大姒也,《大明》云“缵女维莘”,莘国长女,实是诸侯之子,故得百乘将之。○笺“家人”至“盛”。○正义曰:此申说传送迎百乘之事。家人,谓父母家人也。《左传》曰:“凡公女嫁於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公子则下卿送之。於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谓夫也。《昏礼》曰:“衽良席在东。”注云:“妇人称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将瞷良人所之。’”《小戎》曰:“厌厌良人。”皆妇人之称夫也。《绸缪》传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对“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礼,人伦之本,以象国君有百官之盛。诸侯礼亡,官属不可尽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举全数,故云百官也。《士昏礼》“从车二乘”,其天子与大夫送迎则无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车,故郑《箴膏肓》引《士昏礼》曰:“主人爵弁纁裳,从车二乘,妇车亦如之,有供。”则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车也。又引此诗,乃云:“此国君之礼,夫人自乘其家之车也。”然宣五年“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反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车,故郑《箴膏肓》又云:“礼虽散亡,以诗义论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车反马之礼。”故《泉水》云“还车言迈”,笺云“还车者,嫁时乘来,今思乘以归”,是其义也。知夫人自乘家车也。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车迎之;送之,则其家以车送之,故知婿车在百两迎之中,妇车在百两将之中,明矣。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也”,一本无“之”字。之子于归,百两将之。将,送也。○将,如字,沈七羊反。维鹊有巢,维鸠盈之。盈,满也。笺云:满者,言众媵侄娣之多。○媵音孕,又绳证反。国君夫人有左右媵。侄,待结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侄。谓吾姑者,吾谓之侄。娣,徒帝反,女弟也。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能成百两之礼也。笺云:是子有鸤鸠之德,宜配国君,故以百两之礼送迎成之。[疏]笺“满者”至“之多”。正义曰:《公羊传》曰“诸侯一娶九女,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凡有八人,是其多也。又曰:“侄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传“能成百两之礼”。正义曰:传言夫人有鸤鸠之德,故能成此百两迎之礼。笺以迓为迎。夫人将之,谓送夫人;成之,谓成夫人,故易以百两之礼送迎成之。《鹊巢》三章,章四句。
8《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职者,夙夜在公也。○蘩音烦,本亦作“繁”,孙炎云“白蒿”。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谿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荇菜也。笺云:于以,犹言“往以”也。“执蘩菜”者,以豆荐蘩菹。○沼,之绍反。沚音止。皤,薄波反,白也。蒿,好羔反。谿,苦兮反,杜预云
“涧也”。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之事,祭事也。笺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荐此豆也。[疏]“于以”至“之事”。○正义曰:言夫人往何处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为菹,夫人往何处用之乎?於公侯之宫祭事,夫人当荐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论其祭事。○传“蘩,皤蒿”。○正义曰:《释草》文。孙炎曰:“白蒿也。”然则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谓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涧之中,亦谓於曲内,非水中也。○传“公侯”至“荇菜”。正义曰:言执蘩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为祭用,既言公侯夫人执蘩菹,嫌王后尊,不可亲事,故因明王后则亲执荇菜也。言不求备者,据诗举荇菜,非其备者,其实祭则备物,故《关雎》传云“备庶物以事宗庙”,是也。《左传》曰:“荀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可荐於鬼神。”彼言毛,此传言草,皆菜也。○笺“于以”至“蘩菹”。正义曰:经有三“于”,传训为“於”,不辨上下。笺明下二“于”为“於”,上“于”为“往”,故叠经以训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训为“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荐蘩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实”,皆有菹,菹在豆,故知以豆荐蘩菹也。《特牲》云“主妇设两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两鉶鉶芼设于豆南,南陈”,即主妇亦设羹矣。知蘩不为羹者,《祭统》云“夫人荐豆”,《九嫔职》云“赞后荐,彻豆笾”,即王后夫人以豆为重,故《关雎》笺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为羹。《采蘋》知为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故知为羹。且使季女设之,不以荐事为重,与此异也。○传“之事,祭事”。○正义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庙,故下云“宫”,互见其义也。于以采蘩?于涧之中。山夹水曰涧。○涧,古晏反。夹,古洽反,一音古协反。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宫,庙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饰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笺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谓视濯溉饎爨之事。《礼记》:“主妇髲髢。”○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直角反。溉,古爱反。饎,昌志反,酒食也。爨,七乱反。髲,皮寄反,郑音发。鬄,本亦作髢,徒帝反,刘昌宗吐历反,沈汤帝反,郑注《少牢礼》云“古者或剔贱者、刑人之发以被妇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为吕姜髢”,是也。紒音计。被之祁祁,薄言还归。祁祁,舒鷃也,去事有仪也。笺云:言,我也。祭事毕,夫人释祭服而去髲髢,其威仪祁祁然而安舒,无罢倦之失。我还归者,自庙反其燕寝。○祁,巨私反。罢音皮,本或作“疲”。[疏]“被之”至“还归”。○正义曰:言夫人首服被鬄之饰,僮僮然甚竦敬乎!何时为此竦敬?谓先祭之时,早夜在事,当视濯溉饎爨之时甚竦敬矣。至於祭毕释祭服,又首服被鬄之释,祁祁然有威仪。何时为此威仪乎?谓祭事既毕,夫人云薄欲还归,反其燕寝之时,明有威仪矣。○传“被,首饰”。○正义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饰。笺引《少牢》之文,云“主妇髲鬄”,与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读为髲鬄。古者或剔贱者、刑者之发,以被妇人之紒为饰,因名髲鬄焉。此《周礼》所谓次也。”又“追师掌为副编次”,注云“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髲髢”,即与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妇纚笄”,《少牢》云“被锡纚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礼》之次也。此言被,与髲鬄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鬄,同物而异名耳。《少牢》注读“被锡”为“髲鬄”者,以剔是翦发之名,直云“被锡”,於用发之理未见,故读为“髲鬄”,鬄,剔发以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读,故此及《追师》引经之言髲鬄也。定本作“髲髢”,与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妇衣侈袂”,注云“衣绡衣而侈其袂耳”。侈者,盖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此夫人首服与之同,其衣即异。何者?夫人於其国,与王后同,展衣以见君,褖衣御序於君。此虽非正祭,亦为祭事,宜与见君相似,故《丝衣》士视壶濯犹爵弁,则此夫人视濯溉,盖展衣,否则褖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听祭报”,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当配耳,故下笺云“夫人祭毕,释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侈绡衣之袂,《追师》注引《少牢》“衣侈袂”以为侈褖衣之袂。不同者,郑以《特牲礼》士妻绡衣,大夫妻言侈袂,对士而言,故侈绡衣之袂。以无明文,故《追师》之注更别立说,见士祭玄端,其妻绡衣,
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与士异,故为侈褖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为异者,以助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褖衣之袂。此“主妇髲鬄”,在《少牢》之经,笺云“《礼记》曰”者,误也。○传“僮僮,竦敬”。○正义曰:知僮僮不为被服者,以下祁祁据夫人之安舒,故此为竦惧而恭敬也。○笺“早夜”至“之事”。○正义曰:早谓祭日之晨,夜谓祭祀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后夜,便文耳。夜在事,谓先夕视濯溉。早在事,谓朝视饎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视濯溉饎爨之事,所谓不失其职也。郑何知非当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为视濯者,以“被之祁祁,薄言还归”据祭毕,即此“被之僮僮”为祭前矣。若为自夙至夜,则文兼祭末,下不宜复言祭末之事,故郑引髲鬄与被为一,非祭时所服,解在公为视濯,非正祭之时也。经言夙夜在公,知是视濯溉饎爨者,诸侯之祭礼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陈鼎於门外,宗人升自西阶,视壶濯及笾豆”,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兴,主妇亲视饎爨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约之以为濯溉饎爨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注云“濯,溉也”,即濯、溉一也,郑并言耳。《特牲》宗人视濯,非主妇,此引之者,诸侯与士不必尽同,以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约彼夙夜所为之事以明之。不约《少牢》者,以《少牢》先夕无事,所以下人君祭之日,朝乃饔人溉鼎,廪人溉甑,无主妇所视,无饎爨之文,故郑不约之。士妻得与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诸侯礼,故夫人视濯。天子则大宗伯视涤濯,王后不视矣。○传“祁祁”至“有仪”。○正义曰:言去事有仪者,谓祭毕去其事之时有威仪,故笺云“祭毕,释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髲鬄,其威仪祁祁然而安舒”,是有仪也。定本云“祭事毕,夫人释祭服而髲髢”,无“去”字。知祭毕释祭服者,以其文言“被”,与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毕皆释祭服矣。○笺“我还”至“燕寝”。○正义曰:言此者,以庙寝同宫,嫌不得言归,故明之燕寝,夫人常居之处。
《采蘩》三章,章四句。
毛诗正义
1.诗教指以《诗经》来教化人,教化的目的在于使人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一种受推崇的性格修养和礼节品质。 2.毛传指为传授诗经所写的注解,毛传由大毛公毛亨开始,再传给和小毛公毛苌完成的。对后世影响很大,对解读诗经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郑笺汉·郑玄所作《〈毛诗传〉笺》的简称。郑玄兼通经今古文学,对毛诗进行注解,谦虚而称为笺 4主文而谲谏,主文指不直接陈述而用比喻的手法叫做主文,委婉讽刺叫做“谲谏” 5四始六义“四始者,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6兴观群怨?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可以激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 7三纲领,八条目 三:明德,新民,至善。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8中庸章句: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 9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君子尊崇天赋予的道德本性,又通过求教和学习,使自己的知识既进入宽广博大的境界,又深入到精微细妙之处;使自己到德行既高尚文明,又能遵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10史迁司马迁;体例;历史地位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笔法孔子首创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通过叙述事实来表现思想倾向而不是直白的议论性文辞;秉笔直书秉笔直书,指写 指《史记》、《汉书》等以文章不隐瞒、不夸大,真实地反映情况。;正史 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 11厚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12含章可贞 有美德而不显耀,
弟子职注音版
先xiān生sheng施s hī教jiào,弟dì子zǐ是s hì则zé。温wēn恭gōng自zì虚xū,所suǒ受shòu是s hì极jí。见jiàn善shàn从cóng之z hī,闻wén义yì则zé服fú。温wēn柔róu孝xiào悌tì,毋wú骄jiāo恃s hì力lì。志z hì无wú虚xū邪x ié,行háng必bì正zhèng直z hí。游you居jū有yǒu常cháng,必bì就j iù有yǒu德dé。颜yán色sè整zhěng齐qí,中zhōng心xīn必bì式s hì。夙sù兴xīng夜yè寐mèi,衣yī带dài必bì饬c hì。朝zhāo益yì暮mù习xí,小xiǎo心xīn翼yì翼yì。一yī此cǐ不bù解x iè,是s hì谓wèi学xué则zé。 少shǎo者zhě之z hī事s hì,夜yè寐mèi蚤zǎo作zuò。既jì拚pīn盥guàn漱shù,执z hí事s hì有yǒu恪kè,摄shè衣yī共gòng盥guàn,先xiān生sheng乃nǎi作zuò。沃wò盥guàn彻chè盥guàn,汛xùn拚pīn正zhèng席xí,先xiān生sheng乃nǎi坐zuò。出chū入rù恭gōng敬jìng,如rú见jiàn宾bīn客kè。危wēi坐zuò乡xiāng师s hī,颜yán色sè毋wú怍zuò。 受shòu业yè之z hī纪jì,必bì由yóu长zhǎng始s hǐ;一yì周zhōu则zé然rán,其qí馀yú则zé否fǒu。始s hǐ诵sòng必bì作zuò,其qí次cì则zé已yǐ。凡fán言yán与yǔ行háng,思sī中zhōng以yǐ为wéi纪jì。古gǔ之z hī将jiāng兴xìng者zhě,必bì由yóu此cǐ始s hǐ。后hòu至z hì就j iù席xí,狭x iá坐zuò则zé起qǐ。若r uò有yǒu宾bīn客kè,弟dì子zǐ骏jùn作zuò。对d uì客kè无wú让ràng,应yìng且q iě遂s uì行xíng。趋qū进jìn受shòu命mìng,所suǒ求q iú虽s uī不bú在zài,必bì以yǐ反fǎn命mìng,反fǎn坐zuò复fù业yè。若r uò有yǒu所suǒ疑yí,捧pěng手shǒu问wèn之z hī。师s hī出chū皆j iē起qǐ。 至z hì于yú食s hí时s hí,先xiān生sheng将jiāng食s hí,弟dì子zǐ馔zhuàn馈k uì。摄shè衽rèn盥guàn漱shù,跪g uì坐zuò而ér馈k uì。置z hì酱jiàng错cuò食s hí,陈chén膳shàn毋wú悖bèi。凡fán置z hì彼bǐ食s hí,鸟niǎo兽shòu鱼yú鳖b iē,必bì先xiān菜cài羹gēng。羹gēng胾zì中zhōng别b ié,胾zì在zài酱jiàng前qián,其qí设shè要yào方fāng。饭fàn是s hì为wéi卒zú,左zuǒ酒j iǔ右yòu酱jiàng。告gào具jù而ér退t uì,捧pěng手shǒu而ér立lì。三sān饭fàn二èr斗dòu,左zuǒ执z hí虚xū豆dòu,右yòu执z hí挟x ié匕bǐ,周zhōu还xuán而ér贰èr,唯wéi嗛qiàn之z hī视s hì,同tóng嗛qiàn以yǐ齿c hǐ。周zhōu则zé有yǒu始s hǐ,
《毛诗序》全文翻译及释义
毛诗序: 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毛诗》于汉末兴盛,取代前三家而广传于世。《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毛诗》讲《诗经》的总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能经过东汉经学家卫宏修改。 《毛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毛诗大序》原文及注解
《毛诗大序》 【原文】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大序》① 《关雎》②,后妃之德也③,风之始也④,所以风天下⑤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⑥,用之邦国焉⑦。风,风也,教也;风以动⑧之,教以化⑨之。 【注解】
①毛诗序: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毛诗于古《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总序。 ②《关睢》:《诗经·国风·周南》第一首诗的篇名。 ③后妃之德也:后妃,天子之妻,旧说指周文王妃太姒。此处说《关雎》是称颂后妃美德的。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性行合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 ④风之始也:本指《关雎》为《诗经》的国风之首之意。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 ⑤风:读去声,用作动词,教化之意。 ⑥用之乡人焉:相传古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人”,指百姓。《礼记·乡饮酒礼》载: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所以《正义》释“用之乡人”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 ⑦用之邦国焉:《仪礼·燕礼》载:诸侯行燕礼饮燕其臣子宾客时,歌乡乐《关雎》、《葛覃》等。故《正义》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 ⑧动:感动。 ⑨化:感化。 诗者,志之所之也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黄贞权①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 内容提要: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 所忽略。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 论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孔颖达 毛诗正义 诗缘政 风雅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76-81 诗歌的本质是什么?历来聚讼纷纭,源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和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被后世的文艺理论家所津津乐道,以至于在现当代出现了朱志清的《诗言志辨》、裴斐的《诗缘情辨》、王文生的《诗言志———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等经典著作。[1]可是他们却都忽略了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却存着“诗缘政”的诗学命题。唐初,著名文学家孔颖达在对《诗》的阐释过程中,囿于时代、政治、历史文化语境的原因,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从此把中国传统诗歌作为“言情”、“言志”的本质观做了一次大胆的解构,把文学与政治做了嫁接,使唐代的诗学具有前所未有的批判战斗精神,也开启了唐代诗歌的批判写实主义风气。 一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出“诗缘政”这一富有时代烙印的诗学命题。如: 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故《七月》之篇备有风、雅、颂。[2]诗者缘政而作,风、雅系政之广狭,故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此风、雅之作,本自有体,而云贬之谓风者,言当为作雅,犹贬之而作风,非谓采得其诗乃贬之也。[3] 言秦仲国大将兴,是其土地广宽,虽未得爵命,而大于邾、莒,诗者缘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诗也。且秦于襄公之后,国大而录其诗,因秦仲先已有诗,故并录之耳。[4] 自然大雅为天子之乐可知。若然,小雅之为天子之政,所以诸侯得用之者,以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故不得作诗。而诗为乐章,善恶所以为劝戒,尤美者可以为典法,故虽无诗者,今得而用之,所以风化天下。[5] 《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到“诗缘政”这个诗学命题,在孔颖达看来,不是简单的术语罗列,也不是对《毛诗序》的“主文而谲谏”式教化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对传统诗学的充分理解之后,囿于唐代政治主张,是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一场“诗学革命”。理解“诗缘政”这一诗学命题,我们必须要溯回到孔颖达时代的历史文化语 ①作者简介:黄贞权(1976--),河南商城人,文学硕士,现为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008-ZX-143)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 -唐初,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思想,决定弘扬儒学,通过明经科来选拔人才,由于当时经学异学颇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本,必须选人来编一套全国统一考试的指定“教材”,以便于“考生”使用。据《旧唐书·儒学》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1]《毛诗正义》于 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令天下。正是在这种政治和多元的文化格局当中,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占据了国家权力话语的中心位置。“《毛诗正义》被作为封建政治伦理教育的国定教科书,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学童、士人和官吏人人诵习的经书。随着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诗经》在全国空前地广泛流传。”[2]《毛诗正义》成为唐人取仕必读的教材,其中的诗学思想或显或隐的对他们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孔颖达对《诗》的爬罗剔抉的阐释中,提出“情志一也”、“兴象”、“诗缘政”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揭示出诗歌的功用、诗歌创作方法及诗理,启蒙了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一、“情志”论 “情志”论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核心,包含着丰富的 理论内涵。关于诗歌的本质到底是“言志”还是“言情”,唐以前聚讼纷纭,从《尧典》、孔子、《毛诗序》及陆机、刘勰、钟嵘都在阐释这一富有生命力的诗学命题。而孔颖达在前人诗学思想基础上作了审美超越,把诗歌到底是“言志”还是“缘情”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言志”也即“言情”,是二而为一的关系。孔氏在《毛诗正义·诗序》中云:“诗者,人志意之抽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3]孔颖达在这里给“情志”下了定义,也给“诗”下了定义。“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这是给“志”下的定义。从“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几句看,他所说的“志”也就是“悦豫”、“哀伤”之类的“情”。在《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则鲜明地提出“情志一也”。“民有六志……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4]而这种情志从何而出呢?就是“情缘物动,物感情迁”[5]的结果。“外物”是激起“悦豫”、“哀伤”之情的外界的客观事物,包括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孔氏在《礼记正义》中对“外物”作了很好的诠释:“物,外境也。言乐初所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也……若外境痛苦,则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声必踧速杀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欢乐,欢乐在心,故声必随而宽缓也。”[6]孔氏所说的“外物”、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收稿日期:2009-09-06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孔颖达〈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研究》成果之一(2008-ZX-143)作者简介:黄贞权(1976-),男,河南商城人,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孔颖达对《诗》的阐释绾合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剥去历代对《诗》阐释的陈垢,对传统《诗》学的接受做出取舍并加以创新和超逸,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提出了“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关键词:孔颖达;毛诗正义;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2-0144-04 黄贞权 2010年第2期(复总第76期) 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2,2010(rest.tot No.76) 144
_毛诗正义_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
《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 白长虹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辽宁鞍山 114005) 摘要:《毛诗正义》虽作为《诗经》注疏史上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但其撰者及编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本文详细考辨了《毛诗正义》的编撰、修订次数及具体时间,缕析了《毛诗正义》的各次参撰者,以期有益于对《毛诗正义》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毛诗正义》;撰者;编撰时间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6-0079-06 《毛诗正义》作为《五经正义》〔1〕之一,其编撰是与《五经正义》连在一起的。《五经正义》通常题为孔颖达撰,其实编撰者并非孔颖达一人,这在《旧唐书?孔颖达传》本传、 《五经正义》各序、长孙无忌《上五经正义表》等中都有相关记载。但由于记载分散,历代截取、转录〔2〕,造成对《五经正义》撰者记载参差不清的局面。另外,其编撰时间史料记载也不很明确,加之几经讨论、刊定,学者们对《五经正义》的编撰时间更是提之笼统,彼此不一〔3〕。日本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4〕,台湾张宝三先生《五经正义研究》〔5〕对《五经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论述较为详细,但仍值得继续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经正义》的撰者及编撰时间进一步加以探讨,通过对史料的综合分析尽量明确《五经正义》编撰各阶段的起讫时间,并对参撰者作以统计和分析,尤其是将由于马嘉运掎摭所作的修订与贞观十六年的初次修订区分为两次不同的修订。 《五经正义》编撰的起始之年,《两唐书》、 《贞观政要》及孔颖达碑都不见明确记载〔6〕。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认为:“《唐会要》系之于贞观十二年,盖有所据。”,张宝三先生《五经正义研究》认为《唐会要》“言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在贞观十二年,盖指受诏始修之年,非谓其已成一百七十卷也,会要乃合其终始言之。” 《贞观政要?崇儒学》云:“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可见《五经正义》是在《五经定本》完成以后开始修撰的。《五经定本》的完成时间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其颁行,《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载:“七年……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可见《五经定本》的完成最晚不迟于贞观七年。据《旧唐书?孔颖达传》,与孔颖达一同受诏的还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据《旧唐书?司马才章传》和《册府元龟》,才章、王恭、王琰等人是贞观六年才被太宗征引的〔7〕,据此《五经正义》的编撰也不应早于贞观六年。 《贞观政要》将颜师古排在受诏编撰者的第一位,其次才是孔颖达,可是《两唐书》尤其是《颜师古传》中都不见颜师古主持《五经正义》的记载。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认为:“《政要》以为颜师古主之。然各经序皆颖达撰。《新旧唐书》、 《唐会要》、 《册府元龟》等俱以为孔颖达主之。长孙无忌上表,亦特言以颖达宏材硕学,名振当时,奉诏修撰。则颖达尤致力于撰定可无疑也。”从颜师古的经历看,他更有可能主要继续从事文字辨析方
经学中的文学因素——析《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1)
经学中的文学因素——析《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1) 论文关键词:《毛诗正义》章法结构用韵赋比兴 论文摘要:《毛诗正义》虽属传统的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艺术表现特征的总结引人注目。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它对《诗经》章法结构、用韵情况和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八的分析与总结。 《毛诗正义》作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者,其说诗模式虽然仍未跳出重在发掘政治教化与美刺功能的传统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在章法结构、用韵和赋比兴手法等艺术表现特征方面所进行的系统总结却颇为引人注目。这一成就超越了此前魏晋六朝文学自觉时代的《诗经》研究成就。 一、《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出发点 文学是情感的产物,肯定文学创作中的个人情感抒发,是重视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基本前提。孔颖达等人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于儒家文论中第一次明确主张“情志一也”。《毛诗正义》中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情志合一的意思: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日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
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此处所谓“心”,即上文所谓“情”;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即上文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可见,这段阐释,其实也正是主张情志合一,肯定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根本地位。 那么,直接将心中之情感说出来就能够成为一首诗吗?孑L疏明确提出了“直言非诗”的理论主张。孔疏认为,《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的意义重在强调“直言者非诗,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接着又说:“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既然他认为“直言非诗”,那么运用各种语言艺术形式来言志作诗就是逻辑的必然。从实现诗歌抒情意图发,孔颖达强调要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手段以强化诗人“申志”“舒愤”之目的。这种认识为其深入探讨《诗经》的创作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他关注《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发点。 二、对章法结构的分析 孔疏在《诗经》首篇《关雎》之后,用了字数是《诗大序》倍的篇幅,对《诗经》的字句篇章作了集中讨论,成为
毛诗序》全文翻译及释义
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毛诗》于汉末兴盛,取代前三家而广传于世。《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 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毛诗》讲《诗经》的总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
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1)
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1) 论文关键词:《毛诗正义》引书成书特征经学性论文摘要: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集大成的 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撰征引了自汉魏以来以迄初唐的学术著作 292 种。《毛诗正义》引书彰显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从取材看, 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即使 是引用文学典籍,亦不违此,甚至不惜牺牲对诗的审美观照;从方法 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谶纬解释经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诗正 义》文本的经学特征,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 面。 在现代《诗经》学研究中,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国 学热的兴起,《毛诗正义》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主要侧重于文 学、文献及其学术史的地位等方面的探讨。在引书方面,自唐代以 来,学者多有关注,而由于《毛诗正义》文本本身在内容上的博大浩 繁,难以卒读,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对其文本引文进行细致考索, 因此,《毛诗正义》引书的价值便湮没无闻。本文不揣谫陋,对其 引文进行细致的爬梳,然后分门别类,多向比较。我们发现,《毛 诗正义》在其驳杂的引书中,彰显出鲜明的成书特征。这一发现,对 于我们今后研究《毛诗正义》提供了一种较有价值的参照。本文认 为,《毛诗正义》通过引书能够体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一、《毛诗正义》取材极为广泛,较少学术成见《毛诗正义》 广泛继承了唐以前的文化遗产,从时间上来看,绝大部分是两汉以来
的作品,所引著述包括经、史、子、集各个门类。除按照《隋书?艺文志》,《孟子》归人“子部”外,《毛诗正义》引用了儒家的所有经典及其大量传注,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流派都包括在内,如两汉的今古文学派,魏晋的郑王学派,以及玄学代表王弼的《周易》注,南北对峙时的南学和北学,而且,汉魏时期的纬书也有大量征引。史部引用了《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主要的史学著作和传注,以及其他著述28 种之多。子部引书26种,不仅有儒家的《孟子》、《苟子》,而且还有《老 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墨子》、《吕氏春秋》、《孙子兵法》、《尸子》、《九章算术》、《本草》等,几乎引用了春秋以来诸子百家的主要著述。集部以战国以来的诗歌和辞赋为多,如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三国曹植,晋代的张衡和潘岳的作品等。马宗霍赞道:“其实唐人义疏之学,虽得失互见,而瑕不掩瑜,名宗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破门户之习。今就而论之 《诗》则训诂本诸《尔雅》,而参以犍为舍人、樊光、李巡、孙叔然渚家之注,使《尔雅》古义,赖是以存。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亦间及焉。制度本诸群经,而益之以王肃之难,王基之驳,孙毓之评,崔灵恩之集注,佐之以郑氏易注书注,贾服左传注,他若《郑志》驳《五经义疏》诸书,亦咸萃焉。虽有二刘在前,足备采择,而取舍之间,实具卓识。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固其宜也。”口由此可见,《毛诗正义》的编撰者俯察历史,不抱学术成
毛诗正义之硕鼠
《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於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硕音石。敛,吕验反,下 同。[疏]“《硕鼠》三章,章八句”至“大鼠”。○正义曰:蚕食者,蚕之食桑,渐渐以食,使桑尽也。犹君重敛,渐渐以税,使民也。言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硕鼠为喻之意,取其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经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敛,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敛,不修其政,故下四句言将弃君而去也。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贯,事也。笺云:硕,大也。 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无复食我黍,疾其税敛之多也。我事女三岁矣,曾无教令恩德来眷顾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贯,古乱反,徐音官。复,扶又反。税,始锐
反。比,毗志反。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笺云:逝,往也。往矣将去女,与之诀别之辞。乐土,有德之国。○乐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诀,古穴反。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笺云:爰,曰也。[疏]“硕鼠”至“得我所”。○正义曰:国人疾其君重敛畏人,比之硕鼠。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犹言国君国君,无重敛我财。君非直重敛於我,又不修其政。我三岁以来事汝矣,曾无於我之处肯以教令恩德眷顾我也。君既如是,与之诀别,言往矣将去汝之彼乐土有德之国。我所以之彼乐土者,以此乐土,若往则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将去汝者,谓我往之他国,将去汝国也。○传“贯,事”。○正义曰:《释诂》文。○笺“硕大”至“是徙”。○正义曰:“硕,大”,《释诂》文。《释兽》於鼠属有鼠,孙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
豆,关西呼(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诗,以硕鼠为彼五技之鼠也。许慎云:“硕鼠五技,能飞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绿不能穷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谓五技。”陆机《疏》云:“今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两脚於颈上跳舞,善鸣,食人禾苗。人逐则走入树空中。亦有五技,或谓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 魏国,今河北县是也。言其方物,宜谓此鼠非鼠也。”按此经作“硕鼠”,训之为大,不作“鼠”之字,其义或如陆言也。序云“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为斥君,亦是兴喻之义也。笺又以此民居魏,盖应久矣。正言“三岁贯汝”者,以古者三岁大比,民或於是迁徙,故以三岁言之。《地官·小司徒》及《乡大夫职》皆云三年则大比。言比者,谓大校,比其民之数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时民或得徙。《地官·比长职》曰:“徙於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
《毛诗正义》讲义
《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案1《漢書·藝文志》《毛詩》二 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2 其名。《後 漢書·儒林傳》始雲:“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 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雲:“孔子刪3 《詩》授卜商, 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4 ,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 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據是二書,則 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雲大毛公為其 《傳》,由小毛公而題5 毛也。 (1)案:根据 (2)著:记载,登记 (3)删:删节 (4)曾申:曾子,曾参之子(5)题:写上,签署
《隋志》所雲,殊為舛誤6 。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 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7 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尤為於古無據。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 8 傳授9 《毛詩》,淵源有自 10 ,所言必不誣 11 也。鄭氏發明毛義, 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12 是此 郡人,故以為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13 用記,郡將 14 用箋 之意。 (6)舛誤:错误 (7)《毛诗训诂传》:“训”诂最初单称为“训”(故),汉代以来“训诂”曾合称,又称“故训”,“训诂”合称始于汉 代《毛诗训诂传》(《毛传》作者毛亨) (8)并:相继 (9)传授:讲解,教授,学问,记忆 (10)自:起源 (11)诬:言语不真实,欺骗 (12)康成:郑玄 (13)公府:中央一级行政单位 (14)郡将:郡守
毛诗正义 目录 毛诗序 诗谱序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目录毛诗序诗谱序《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目录毛诗序诗谱序《毛诗正义》序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毛诗诂训传》西汉•毛公传 □《毛诗传笺》东汉•郑玄笺 □《毛诗正义》唐•孔颖达疏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 汉人传诗本有四家,称为四家诗。《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至战国初期,研究讲习《诗》者,有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苌(据现在有关学者考证推断,毛亨与毛苌为叔侄关系)。 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又被称为三家诗,皆采用今文,被称为今文经学,在东汉被立于学馆。毛诗晚出,属古文经学。
毛诗训诂简明,东汉时受到重视,允许在朝廷公开传授。东汉末年兼通今古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作《毛诗传笺》,主要为毛氏《诗故训传》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提要》说:“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郑玄《六艺论》说:“诗宗毛义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郑玄的《六艺论》现在已经佚失,这些话是根据孔颖达《毛诗正义》所引出的。三家诗自此渐渐衰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毛苌所讲的《诗》,世称“毛诗”。现在读到的《诗经》,即是由毛亨、毛苌流传下来的。《礼记》中的《经解》称《诗》《书》(尚书)《仪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南宋称《诗》为《诗经》。 唐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574~648),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 ”“笺”被称为“注”,
毛诗正义读书笔记
《毛诗正义》读书小记 《毛诗正义》是我开学以来接到的的第一项读书任务。本来没有阅读大部头的经历,现在却要在十几天内读完它,还要简单谈谈感想,着实难也。无奈之下,只好匆匆走马观花,略有感触,便急急下笔,以此权充挂一漏万之文字也。 在这篇小记中,我主要想谈谈对于诗序、诗谱序和毛诗正义的价值、特色的一点看法。 《毛诗正义》开篇为序。序言简短却包罗丰富,实在有总括之妙。我认为读序可知诗经大义。序中指出,诗的作用在于抒发情感,警诫当朝。这一点可以体会得到,因为我在相当一部分篇目的注疏中都可以见到类似于“刺幽王也”的字样。诗在手法上多以草木花鸟为象征,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比兴手法。我大略翻过的诗经篇目中,有大量诗作都具备这一特点。例如《关雎》、《蒹葭》、《青蝇》等。我认为由此也可一窥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人文与自然关系之密切。情生于万物,感发于一草一木。 诗序后紧随的是诗谱序。诗谱序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陈述诗歌主题和内容的随时代变化,与政治密切相关。实在让人感到,无一诗不为时代所需,无一诗不染时代色彩。通过阅读诗谱序,我可以感觉到,《毛诗正义》似乎极推重诗经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在很多诗的疏文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给我印象颇深的是《关雎》《葛蕈》的注疏。《毛诗正义》都将其诠释为后妃之德,夫妇之道,由君至臣,以化天下民。这不似今人通行的解释更偏向于男女之情,显得随性自然。至于为何如此,是否与作者所处时代有关,值得日后进一步探究。 如此煌煌巨著,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价值丰厚。我认为毛诗正义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在训诂学方面。此书对于诗意的诠释相当详尽,从字音字义到词义再到句义,古今变化,古代文化常识,逐一解释,抽丝剥茧。稍有分歧,定要追本溯源,将不同观点加以比较分析,最终所持意见总是有所保留,不厌其烦。如此一来再晦涩的诗句也能讲解得透彻明晰。特别是许多意象的象征义,因为时代久远,今人一读极易云里雾中,所以毛诗对于象征义的查考和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毛诗正义是一部多元化的作品,不局限于训诂,在解释诗意的同时,往往对主旨大义作深入剖析,这就又增加了文学鉴赏方面的价值。 我从《毛诗正义》中收获的第二类价值是治学的思路、方法和态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研读诗经,自然以公认的学术性著作为上等。在书的选择和价值取向上,势必要与普通吟咏风雅的读者有所不同。毛诗的训诂规则是在阐述前人观点、古籍言论的基础上陈述新看法、新见解。所以疏文通常篇幅较长,洋洋洒洒,动辄千字。有人批评唐人义疏多繁言赘语,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代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再细枝末节处也须有据察考,涉卷无数,不辞辛劳。编者实在非学识精深,沉心为学者不能胜任。毛诗正义引用典籍之丰富广博,令人惊叹折服。我国文化宝库卷帙浩繁,考据何其不易!我读此书时也常常不由得一声叹息:治学难也!因此我认为,初涉学问者必读《毛诗正义》,研究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能见识一番学问之道。甚至可以以此为标杆,培养自己的一点专业素养和学术气质。 以上就是我此次读《毛诗正义》的一点感想。匆匆下笔,难免浅陋。希望自己日后能继续细细研读,从中有所学习,有所进益。
《毛诗正义》诗谱序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疏]正义曰:郑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谓神农时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者,为田报祭。案《易·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若然,《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而《六艺论·论诗》云:“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於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彼书契之兴既未有诗,制礼之后始有诗者,《艺论》所云今诗所用诵美讥过,故以制礼为限。此言有诗之渐,述情歌咏,未有箴谏,故疑大庭以还。由主意有异,故所称不同。礼之初与天地并矣,而《艺论·论礼》云“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亦谓今时所用之礼,不言礼起之初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义曰:《虞书》者,《舜典》也。郑不见《古文尚书》,伏生以《舜典》合於《尧典》,故郑注在《尧典》之末。彼注云:“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彼《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故言《诗》之道也。“放於此乎”,犹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隐二年《公羊传》文。言放於此者,谓今诵美讥过之诗,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讴歌始於此也。《益稷》称舜云:“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乘之庸之,否则威之。”彼说舜诫群臣,使之用诗。是用诗规谏,舜时已然。大舜之圣,任贤使能,目谏面称,似无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诗”者,《六艺论》云情志不通者,据今诗而论,故云“以诵其美而讥其过”。其唐虞之诗,非由情志不通,直对面歌诗以相诫勖,且为滥觞之渐,与今诗不一,故《皋陶谟》说皋陶与舜相答为歌,即是诗也。《虞书》所言,虽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尧,明尧已用诗矣,故《六艺论》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亦指《尧典》之文。谓之造初,谓造今诗之初,非讴歌之初。讴歌之初,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然讴歌自当久远,其名曰诗,未知何代。虽於舜世始见诗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时也。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