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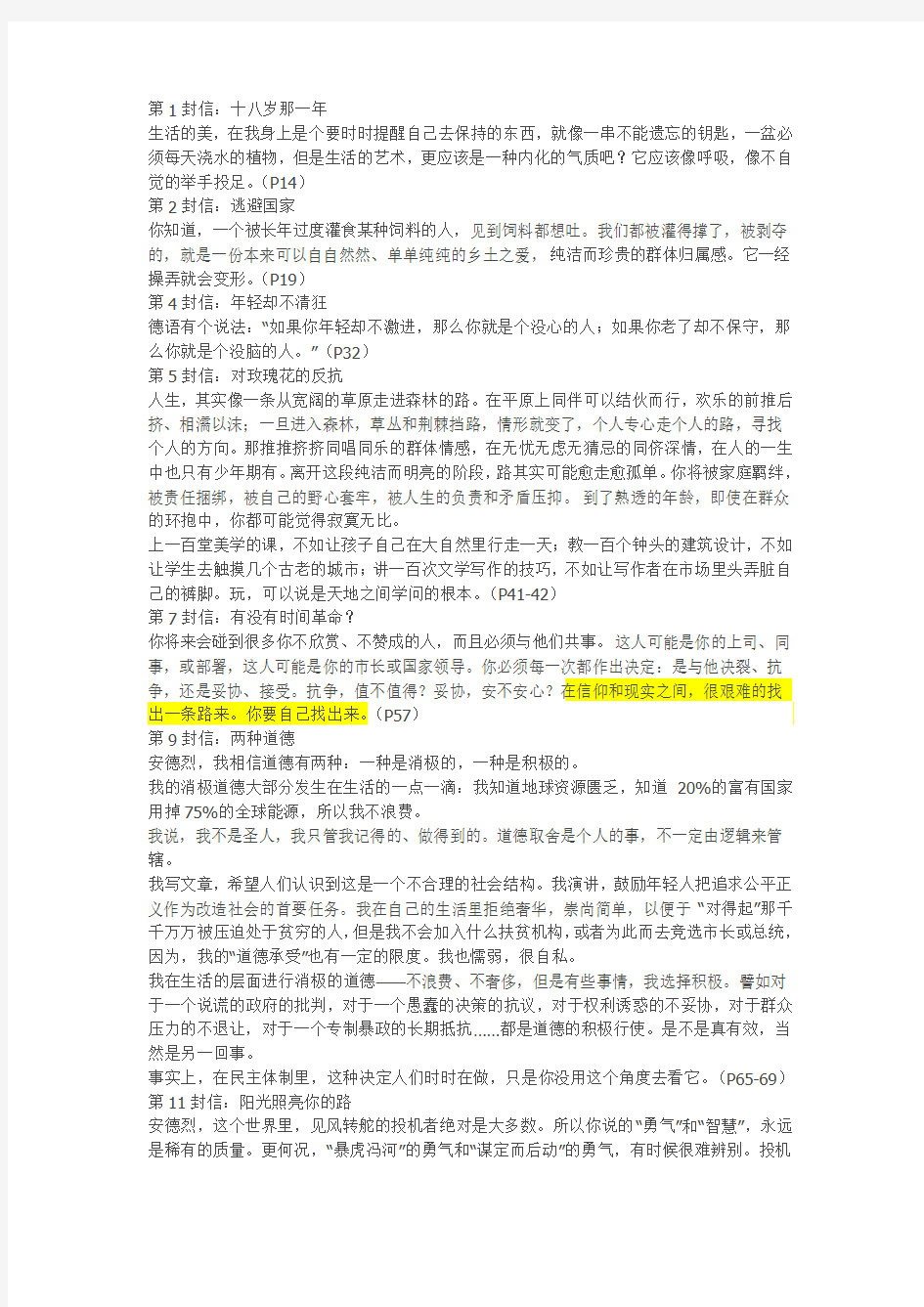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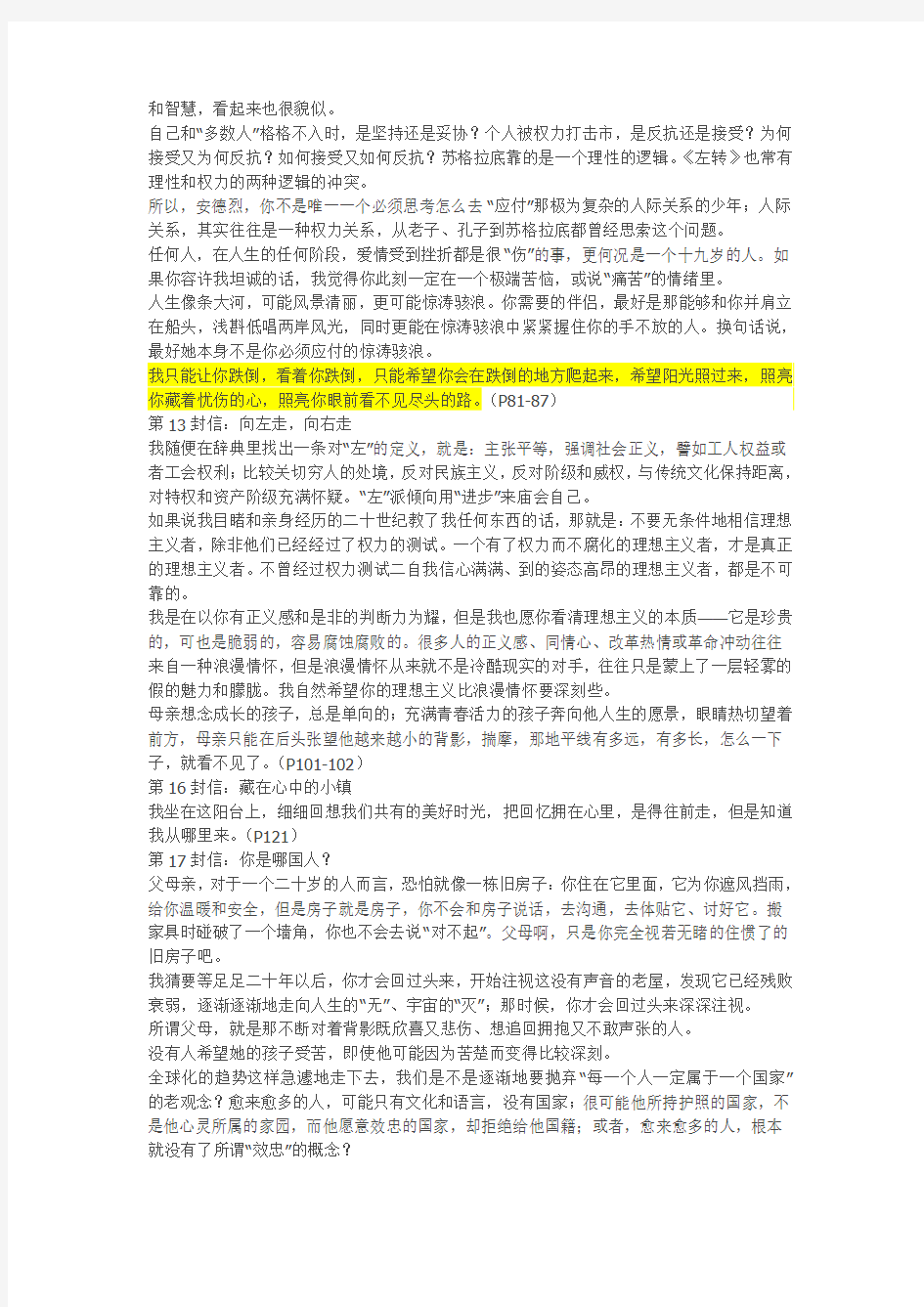
第1封信:十八岁那一年
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的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P14)
第2封信:逃避国家
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P19)
第4封信:年轻却不清狂
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P32)
第5封信:对玫瑰花的反抗
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草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的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在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单。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负责和矛盾压抑。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环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头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P41-42)
第7封信:有没有时间革命?
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署,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的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P57)
第9封信:两种道德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
我说,我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压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懦弱,很自私。
我在生活的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利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P65-69)第11封信:阳光照亮你的路
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是稀有的质量。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
和智慧,看起来也很貌似。
自己和“多数人”格格不入时,是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市,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何接受又为何反抗?如何接受又如何反抗?苏格拉底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转》也常有理性和权力的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是一种权力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这个问题。
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十九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在一个极端苦恼,或说“痛苦”的情绪里。
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我只能让你跌倒,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P81-87)
第13封信:向左走,向右走
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正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庙会自己。
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二自我信心满满、到的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
我是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魅力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P101-102)
第16封信:藏在心中的小镇
我坐在这阳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是得往前走,但是知道我从哪里来。(P121)
第17封信:你是哪国人?
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经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注视。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变得比较深刻。
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抛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国家这种单位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有了或没了,兴盛了或灭亡了,变大了或变小了,安德烈,小镇不会变。泥土和记忆不会变。(P123-129)
第21封信:文化,因为逗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孤独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着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安德烈,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第25封信:孩子,你喝那瓶奶?
贫穷是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降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P192)
第27封信:给河马刷牙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是否有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社会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被人逼,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P208-209)
第30封信: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P230)
第32封信:人生诘问
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会不了头。(P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