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校勘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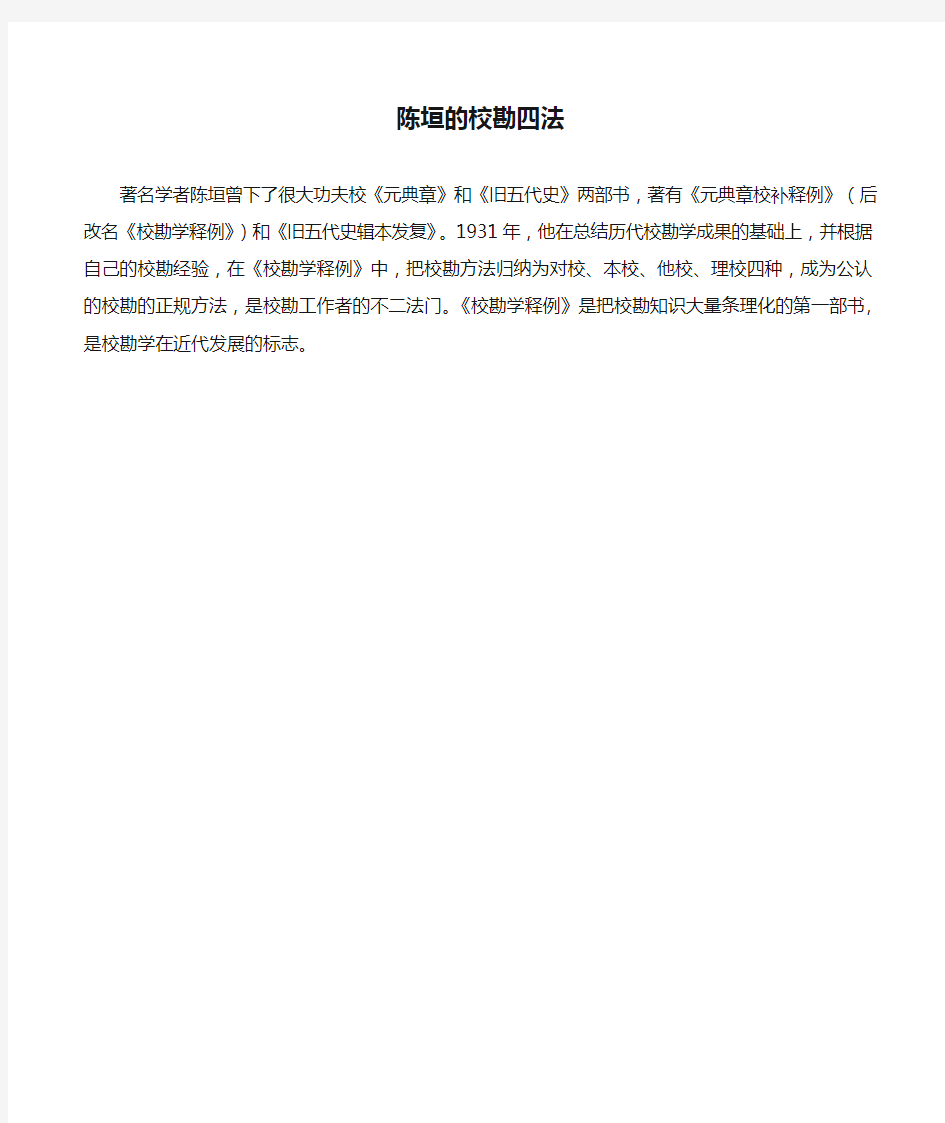
陈垣的校勘四法
著名学者陈垣曾下了很大功夫校《元典章》和《旧五代史》两部书,著有《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和《旧五代史辑本发复》。1931年,他在总结历代校勘学成果的基础上,并根据自己的校勘经验,在《校勘学释例》中,把校勘方法归纳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成为公认的校勘的正规方法,是校勘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校勘学释例》是把校勘知识大量条理化的第一部书,是校勘学在近代发展的标志。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冶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着,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核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籍未由也。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今复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请,就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八千余轴,分别部居。稽覈同异,编为目录,号曰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书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垂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胜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他如佛说诸经杂缘喻田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共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孟子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探析
《孟子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探析-哲学 《孟子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探析 刘瑾辉吴秋雅 【摘要】 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孟子注疏校勘记》,是清代《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它广收当时可见的诸多版本,对宋代孙奭的《孟子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有效地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等传统校勘方法,校勘态度严谨,引征广博,乃属精审详实之作。 关键词 《孟子》;《孟子注疏》;《孟子注疏校勘记》 中图分类号:B22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118-05 作者简介:刘瑾辉,江苏淮阴人,文学博士,(扬州225002)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秋雅,江苏宜兴人,(扬州225002)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称清代校勘的典范之作,其中的《孟子注疏校勘记》亦是清代《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孟子注疏校勘记》广收当时可见的诸多版本,对宋代孙奭的《孟子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校勘态度严谨,引征广博,乃属精审详实之作,是后人研治《孟子》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孟学史上不可忽略的孟学著作。 校勘是对文献的校对勘正。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在总结前人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将历代校勘古籍的方法归纳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作为校勘
史上的经典之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有效地运用了各种传统校勘方法,并根据具体校勘需要,综合运用传统校勘方法,使校勘结果更精准。本文旨在考察《孟子注疏校勘记》对传统校勘方法的运用。 一、对校法:校异同,清源正本 一著的传世版本不止一种。对校法就是将这几个版本放在一起进行对校,遇到不同的地方,就把异文记录在底本上,这样人们看到校本的同时,也能对其他本子有所了解。对校是一个获得异文资料、发现错误的过程。陈垣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 “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说明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法是第一位的,这是包括陈垣在内的前贤在校勘实践中的深切体会。《孟子注疏校勘记》娴熟地运用了此种校勘方法。 《孟子注疏》云:“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按宋高宗御书《孟子》石经残本篇题并顶格,不空字。十行本正与之合,盖犹是旧欵。闽、监、毛三本并低一字,非,又篇题下近孔继涵、韩岱云所刻,经注本及《考文》古本无凡几章字,《音义》及足利本有。《孟子》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缪公。’信乎?”《孟子注疏》引赵岐注云:“人言百里奚自卖五羖羊皮,为人养牛,以是而要秦缪之相,实然不?” 《孟子注疏校勘记》云:
校勘发展简史
校勘发展简史 摘要:校勘是我们在学习古典文献学必不可少会用到的一个科目,作为文献学最古老的科目之一,它究竟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关键词:校勘,校雠,发展 校勘,在《汉语大字典》中这样释义: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校勘,在发展之初叫做校雠,校,有查对、订正之意,雠,有两者相对之意。雠字,《说文》: "犹讐也。" ?玉篇?: "对也。"《正字通》:“言相贵在对也”。《韵会》:“雠,犹较也。谓两不相覆校,如雠仇也”。《尔雅》:"匹也。郭注:“雠犹俦等类也”。《方言》: "予赖雠也,秦、晋曰雠据上所引诸说看来,是雠字有角比检考之意,与校可以互训。有说“一人独校为校,二人对校为雠”,校雠就是二人相对,各自手持定本或校本,找出二者互相不一致的地方。汉以后,一般是一个人根据不同的本子参照比较,不再采取一人读书、一人持本的做法。中国古籍的校勘,根据近代学者的研究,一般采取以下四种方式:①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这是校勘的最初阶段,也是最基本的程序;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前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日:“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则又由校雕目录之学,进而为学术史底探讨了。章氏特著《宗刘》一篇于《校佛通义》中,于《刘略》、《班志》特致推崇;我们试就《汉志》加以检讨,看它们如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志》首列一段总叙,述秦代焚书,汉代求书校书底经过;次乃分述六略。此六略中,每一小类书目条列既定,总计家数篇数之后各有小序一段;每一略各小类完后,又总计此略之家数篇数,又有撮述此一略之序文;六略俱完,又总计种数(即小类数)部数及篇数。《汉志》组织,大致如此。章氏所谓辨学术,考源流者,即是指《汉志》中之序文而言。《六艺》、《诸子》二略尤足以见学术之渊源。今录《六艺略》各类小序,以见一斑。1 关于校勘的最早记载, 见于《国语·鲁语》。鲁国大夫闵马父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 以《那》为首。此事又见于《诗经·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 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 通“父”) 者, 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 以《那》为首。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商颂谱疏》对此事有个解释:韦昭( 注《国语》者) 云:“名《颂》, 颂之美者。”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郑玄《诗谱·商颂谱》曾言:宋戴公时r一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宋为商王封兄微子启所封,故尚存有《商颂》。自启至戴公已七世,所存商颂十二篇已有错乱讹误,故以周太师所藏者校之,定其次序,以《那》‘篇为首。这已是校勘编次的工作了。3校雠目录学纂要蒋伯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史记·孔子世孔子的弟子卜商, 字子夏, 也留下了一则校勘事例。《吕氏春秋·慎行·察传》载:子夏之晋, 过卫。有读史记者, 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 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 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因“亥”与“豕”,“己”与“三”写法相近。)子夏指出卫国人读错两个字,其原因是字形近似。虽然这里未说明是卫国人读别字, 还是简帛所写的文字错误。但这事的性质可算属于校勘范围,也可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许守泯 (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台南) 一、经历简介 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萧教授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班汉姆(E. Bern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干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萧教授在姚先生的教导熏陶之下,选择以蒙元史为研究领域。1959年完成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并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仍跟随姚先生研习蒙元史。1963年提交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同年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在哈佛大学,萧教授主要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与杨联升两位先生。杨联升先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其治学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和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柯立夫先生则师承二十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萧教授在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并由哈佛大学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萧教授于1969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先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1974年转任新加坡学历史系。1994年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返台任教,讲授“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退休,荣聘为清华大学历史所梅贻琦荣誉讲座教授至今。 二、研究取径与重心 萧启庆教授认为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着重纵向分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萧教授的研究重心,早年较重视第一条主轴,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但萧教授也体认到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中的地位。 三、出版著作 截至目前,萧教授已经出版专书两册,联合编着三种,论文集五册,分别是:专书《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联合编着方面,与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陈学霖两位教授合着《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历史学近百年来各个学科的大牛们(附任教学校)
一.先秦史 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夏鼐(考古,北大),吕振羽(吉林大学),吕思勉,许倬云(台湾中央研究院),费孝通(考古,社科院),张光直(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尹达(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苏秉琦(北大),林耀华(中央民族大学),徐中舒(史前和三王,四川大学),翦伯赞(先秦和秦汉,北大),齐思和(先秦史、世界中古史和中国近代史,北大),马非百(中国历史博物馆),赵光贤(西周史和孔子研究,北师大),束世徵(华东师范大学),王玉哲(南开大学),唐兰(北大),李亚农(上海历史研究所),杨宽(复旦大学),童书业(山东大学),黄子通(北大)金景芳(吉林大学),田昌五(山东大学),吴荣曾(北大),徐修鸿(复旦大学),赵锡元(吉林大学),杜水生(北师大),张广智(青海师范大学),李学勤(清华),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晁福林(北师大),刘泽华(南开大学),王震中(社科院),江林昌(烟台大学),朱凤瀚(南开大学),罗新慧(北师大),韩巍(北大),陈伟(先秦及秦汉考古,武汉大学) 二.秦汉史 钱穆(秦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北大),林剑鸣(西北大学),顾颉刚田余庆(秦汉及魏晋史,北大),邢义田(台湾中央研究院),余英时(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林甘泉(人大),田人隆(社科院),李祖德(社科院),安作璋(山东大学),朱绍侯(秦汉和魏晋史,河南大学),陈苏镇(秦汉和魏晋史,北大),王子今(秦汉和魏晋史,北师大),李开元(北大),刘庆柱(秦汉考古,社科院) 三.魏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北大),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武汉大学),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厦门大学),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山东大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北大),贺昌群(魏晋南北朝和汉唐史,社科院),尚钺(魏晋史、先秦史、中国古代通史,人大)何兹全(北师大),齐涛(山东大学),朱大渭(社科院),陈爽(社科院),阎步克(北大),罗新(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西域史,北大),赵克尧(魏晋史和汉唐史) 四.隋唐五代史(不计前面重复的) 胡如雷(河北大学),陶懋炳(五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吴宗国(北大),荣新江(北大),薄小莹(北大),王小甫(唐宋史,北大),郑学檬(唐史、古代经济史等,厦门大学),陈明光(汉唐史,厦门大学) 五.宋辽夏金元史 邓广铭(宋史,北大),漆侠(宋辽夏金史,河北大学),黄现蟠(宋元史及民族史,广西大学),韩儒林(西夏史和元史,北师大),吴天墀(西夏史,四川大学),陈述(辽史,社科院),张博泉(辽金史,吉林大学)舒焚(辽史,湖北大学),陈振(宋史,南京师范大学),周宝珠(宋史,华中师范大学),杨树森(辽宋金史,吉林大学),汝企和(宋史,北师大),邓小南(宋史、唐宋妇女史,北大),张希清(辽宋夏金史,北大),张帆(宋史,北大),刘浦江(辽金史,北大),李锡厚(辽金史,社科院) 六.明清史 吴晗(明史,清华),郑天挺(南开大学),谢国桢(南开大学),韦庆远(人大),邓之诚(北大),戴裔煊(明史、民族史、澳门史,中山大学),王毓铨(明史,社科院),梁方仲(明
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_从_做官_与_做馆_谈起
收稿日期:2008-02-18 作者简介:陈美林,男,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 ———从“做官”与“做馆”谈起 陈美林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儒林外史》齐补本将卧本“做官”改为“做馆”,并无版本依据,可见刘红军文中 肯定齐补本所改,显系对《儒林外史》原文的误读。因此,保存卧本原真是必要的。 关键词:校勘 解读 做官 做馆 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2-011-08 我国古籍汗牛充栋,在长期流传中,“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现象屡屡有之,以致不少古籍失去原来面貌,从而有校勘之必要,以“克复其旧”、“归其真正”[1] 。 古籍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史、哲、经、农、医、理、工等学科无不有大量古代著作传世,它们都是先贤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经验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在解读各类古籍时,自然也必需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即使文、史两类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有很大差异。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史学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文学容许虚构,而史学则不能有违史实。虽然文史可以互证,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在二者互证时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免混淆而致误读。 刘红军《“做官”还是“做馆”———兼论迟衡山武书的结局》(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下 称“刘文”)一文既缺少必要的校勘,又未曾将文、史二者分辨清楚,以致误读文学作品,因此,该文的结 论仅可视为一家之言,而不能成为定论。 一 刘文根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之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下称齐补本)六十回本之第五十二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文中所叙及的“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来校正早于此本的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下称卧本),卧本第四十八回(回目文字与齐本五十二回同)中的文字为“迟衡山、武正字到远处做官去了”。刘文认为卧本“做官”误,而齐补本“做馆”是,但缺少必要的校勘根据。 由于《儒林外史》并无作者吴敬梓的稿本传世,自然无法与之对校;同时,在其他文献载籍中又寻不到有关《儒林外史》原作的辑录,也无法进行他校。但《儒林外史》全文俱在,可以进行本校,提出本证,而刘文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仅凭自己的识见予以推断,未免偏颇。 2008年6月 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 mal University Jun .,2008No .2
北京师范大学项目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项目介绍 一、公司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大学,以其在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的绝对优势而蜚声海内外。北京师范大学以其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的深厚底蕴和不断创新,一直作为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智慧源泉,引领着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首批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是首批列入"211工程"建设计划的名校之一,也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北京地区四所"建设世界一流名校"的成员校之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百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胡先骕、汪堃仁、周廷儒等为代表,一大批名师先贤在这里弘文励教。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形成了"治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 为适应国家教育改革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积淀的丰厚教育资源,促进大学的教学、科研成果能够更有效的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得到实践和发扬,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专门面向中国基础教育第一线的直属教育服务机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致力于弘扬北京师范大学优良的治学传统和先进的教育理念,积极推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为地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全面支持和优质服务。中心以其教育服务的全方位、专业化、系统性、精细化、个性化和高质量等特点,成为行业标杆。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支持地方、服务地方的重要窗口和输出平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主要从事以下方面的工作及相关的教育产业的发展:
陈垣故居观后感
陈垣故居观后感 他,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为反清反帝的斗争竭尽力量;他,是我们中国的国宝!这位伟大的学者——陈垣。今日我有幸来到陈垣先生的的故居,欣赏那精雕细造的陈垣先生的石像,感悟那段坎坎坷坷的拼搏历程。尽管这位伟大的学者已经与世长辞,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神遗产,也永远地铭刻在历史上。1880年,在那个并不十分太平的世纪,陈垣出生在新会石头村这片黄土地上,这似乎也注定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坚持。 陈垣先生的故居亦因为时间的洗礼而长出层层青苔;那坚实的梁柱犹在坚守它的职责;波光潋滟的小溪缓缓流动;亭亭净直的竹子轻轻摇晃。这水木明瑟的胜境,陪伴了陈垣先生晚年的地方,给予了陈垣最后的幽静。 我在故居里的天井徘徊,迎接着从附近流动的风,感受陈垣先生所遗留的书香气息。走在古色古香的走廊和大厅,想象着这个坚韧不屈的学者是如何研究《四库全书》的情景。说起这《四库全书》,倒也令我也感受到陈垣先生的劳累。陈垣从北京城内西南角到京师图书馆来回三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便去了,却是等夕阳染红了天边才回来,这合算起来,竟读了10小时! 陈垣先生博学多才,难怪被称为国宝。陈垣一生研究多种学科,包括历史,元史,考古学等,而他所写的书更是家喻户晓。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于宋人,清人所避讳史作,又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合编成《史讳举例》一书。 陈垣先生一生奔波劳碌,为了祖国而奋斗不停。他一生担任过各科教师和校长,一生都离不开学术与文化。他为国为民,可谓“忧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他的精神是我们的学习标榜,我们应该像陈垣先生一样,为学业奋发图强,将来也像他一样为祖国做出奉献。 故居因陈垣的辞世而变得荒凉,在风花雪月中故居也黯然褪色,但依旧山辉川媚,鸟语花香,陈垣校长依旧屹立在故居门前。陈垣校长的精神也影响我们这里,我们的江门,蓬江,新会更加的光彩夺目。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简介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试论陈垣对古典文献学的贡献
文献学山东图书馆季刊2006年第3期 试论陈垣对古典文献学的贡献 邹应龙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陈垣在古籍整理中,保护与整理了大批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并做了大量的编目工作,使我国古典文献学逐步走 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开辟和规整了目录学新的编撰体式,建立了科学完整的校勘学理论与方法论。 [关键词]陈垣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 [Ab stra ct]In a rrange anc i ent Chi nese c l assics,Chen Yuan pretects and arranges a l ot of prec i ous arch i ves and da tas,m akes a l a rge var i e t y of cata lo gues,which m akes anc i ent docu m en t sc ience i n sc ientific deve l opi ng road; i n i tiates and nor m s new co mp ili ng syste m s i n Ca talog ue Science;estab li shs scien tifica,l whole theory and m ethods i n Jiao2kan sc i ence. [K ey wor ds]Chen Yuan anc i ent docu m en t sc ience cata l ogue ed ition Ji ao2kan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别号圆庵居士,书斋号励耘,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史学家、古典文献学家、教育家。作为史学家,其学术博大精深,被/称之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0。[1]作为教育家,他一生教书育人,推动了我国高师教育的发展。而作为古典文献学家,他研究精深,集古典文献学之大成,为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文献保护与编目整理 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到近代,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型,学术范式也随之而产生新变,无论是宏观观照如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还是微观探索如史料的整理与保存,陈垣都能得风气之先,钻研精深,对古典文献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于1922年春到6月和1928年5月到次年5月,两任京师图书馆(案:后改名北平图书馆)馆长一职,并长期任馆委会委员,为图书馆的筹建、建制等竭忠尽智,出谋划策,筚路蓝缕,居功至伟。尤其是,他曾多方游说,积极争取,获准将中南海居仁堂拨为馆舍,扩大了图书馆的规模,在北图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2]期间,还极力阻止美国庚款基金会的介入,保证了北图主权在我的局面。为更好地保护清代的文物典章,陈垣为故宫博物院购买了清湖广总督端方的档案600余册。[3]成功游说当时北洋政府,将辛亥革命后接受的无人管理的清军机处档案移交故宫博物院,为清史研究保存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原始档案材料。他对懋勤殿陆续发现的珍贵文书档案5教王禁约6、5康熙谕西洋人6等及时加以保护,并进行校释,将没有注明年月的10件档案一一考订清楚。[4]此事汉文记载极少,陈垣的整理校释填补了研究康熙与罗马交往关系的空白。1933年,陈垣主持筹备5宋会要6编印工作,合徐星伯本和清本,定名为5宋会要辑稿6,使艰难传世几经湮没的仅存的5宋会要6得以整理流传,成为多年来宋史研究的重要资料。1939年,5嘉兴藏6在故宫被发现,陈垣亲自加以整理,发现了200多种清初僧人语录和大量塔铭,很多已成为海内孤本,同时利用5嘉兴藏目录6与5嘉兴藏6的实际收书进行校对,钩稽出5目录6未载之书,开辟了史学研究新资源。特别是陈垣在蠶藻堂意外发现了5四库萃要6,武英殿刻书处发现了四库应毁而未毁书,/有李清5诸史同异表6,周亮工5读画录6等的残本,都是很难看到的书0。[5]正是陈垣的妥善保管,诸书才避免了霉烂虫噬之厄。 陈垣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整理工作。1930年,陈垣用五种5元典章6本子,与沈刻本加以对校,/如是整理有数越月,凡得讹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定名5沈刻<元典章>校补60[6]成为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故杨志玖说:/若无5校补6而冒然利用沈刻本,对其中年代、人名、地理、名物制度等的种种错刻毫无察觉,势必影响对元代典制史事的正确理解。0[7]1922年,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藏敦煌唐人写经8679卷,/知其 # 75 #
古籍校勘
校勘记校勘记 notes of collation 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在中国,比较完整的校勘记以隋唐之间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最早。此书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14种当时称作经典的书籍作注释和校勘,共31卷。宋代校勘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著名的校勘记著作有张淳的《仪礼识误》3卷,方崧卿的《韩集举正》10卷,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10卷,岳珂的《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清代校勘学更为发展,对中国古代书籍,除了传统的经书以外,还对不少哲学、历史、地理、诗文集作了校勘,写成不少有价值的校勘记。这些校勘记大部分附于所校的书内,有的则单独刻刊,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卢文□《群书拾补》等。 校勘记的书写没有固定的格式,习惯上大致有这样几种方式:①凡文字有不同的, 写为:“某, 一本作某”(一般应具体写明版本名称)。②凡脱离文字的, 写为:“某本某下有某字。” ③凡文字有衍文(即多余的),写为:“某本无某字。”或“某字衍。”④凡文字颠倒而可以通的,写为:“某本某某二字互乙”;或颠倒而不通的,写为:“某某二字衍,当从某本作某某。” ⑤凡文字可判断其错误的,写为:“某当作某。”凡不能定其误的,写为:“某疑当作某。”⑥文句前后倒置的,写为:“某本某句在某句下。”中华书局于60~70年代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于每一史书的每一卷后面都附有校勘记,体例较为完善。 (傅璇琮) 校勘记是校勘成果的文字表达形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撰写切实简明的校勘记,"可以使校正者有据,误校者留迹,两通或多歧者存异。" 它通过条列校勘异同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校书者对古籍校勘整理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校勘记的撰写,已成为校勘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和掌握校勘记的撰写原则与基本方法。 一.古医籍的校勘与校勘记的撰写概况 校勘记又名校记、考异、考证。校勘记作为校勘成果的文字表达形式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校勘工作和校勘学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 古籍的校勘工作,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周代已有正考父校《商颂》,如《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其后有孔子校勘"六艺"、子夏校勘古《史记》。而官方组织的大规模校书活动,则始自于汉成帝河平年间的刘向校书。 古医籍的校勘是否起自先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出土的医学文献中可见,早在汉或汉以前的医籍中,已有较多异文出现。今存《素问》、《灵枢》两书中,也收录了部分异文。如《素问·缪刺论》:"其状若尸,或曰尸厥。"《灵枢·口问》:"故曰噫,补足太阴阳明。一曰补眉本也。"这些异文说明古人在整理编纂时,已注意到对原文的校勘。 有明确记载的古医籍校勘工作,当始自西汉李柱国校方技之时。《汉书·艺文志》云:"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据前人总结,刘向校书之时,曾备众本、订脱误、删复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序叙、述疑似、准经义、徵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作过大量的校勘工作。如《战国策书录》云:"所校中《战国策》……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者多。"《列子书录》云:"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由此推知,李柱国亦必对医书进行过兼备众本、比勘文字、篇第审定、定立书名、厘定部居、叙述源流等工作。虽然所校医书早佚,其医籍校勘
史源学
史源学简介 一、定义 什么是史源学?简而言之,史源学就是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陈垣认为,研究史著,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他常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己。”并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达到“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可以说,史源学是他在长期治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创新。 二、方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为了传授史源学之精神,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 这门课的讲授方法是: 其一,选定教材。他认为最好是选用近代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其理由一是名作可使学生从中得到更大教益;二是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寻考其史源,如能发现名家大师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会大大激发起他们研究的兴趣,增强他们研究的自信心,并体会到即使是名家大师之作,也不可盲目迷信。 其二,寻考史源。陈垣每次上课,都要从所选定的名著中抽出一二篇,交学生“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他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 一是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这一条是强调通过史源学考察史料的可信程度。例如,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陈垣以史源学的方法,从版本异同上发现《提要》所据版本之谬;而《广弘明集》原本并不误,以高丽本为证,其书唐高宗者皆作“今上”。穷史料之根源,不仅为了判断史料正误,还可以厘定各史料间的“父子”、“兄弟”关系,以明史料之优劣。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考贯云石事迹,就从《元史》本传追寻史源,发现本传乃采自欧阳玄《贯公神道碑》,且神道碑记载更详;确定两种史料的“父子”关系后,陈垣舍《元史》本传而用神道碑,证明了贯云石学佛之事。 二是看其引证是否充分。考证前史所下结论往往需要追踪史源,看其对史料的引证是否充分。清代史家曾争论一历史公案,即楚汉战争中项羽拘刘邦家属为人质,究竟所拘为何人?顾炎武《日知录》据《汉书·高帝纪》所载“太公吕后”,认为只有刘邦之父及妻。赵翼《廿二史札记》据《史记·高祖纪》所记“父母妻子”,认为除太公、吕后外,还有刘邦母及刘邦子。陈垣遍查《史记》、《汉书》,发现顾、赵二人引证皆不充分,因为两种提法史、汉二书皆曾多处用过,可证此两语乃家属通称,不必拘泥于具体人物的考辨。 三是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前人采集史料或有疏忽,故造成结论之谬。 四是看其判断是否准确:计算、比例、推理。追根史源,还应注意核对前人的判断是否准确。比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考证《后汉书·光武帝纪》时,认为光武帝年岁应为64岁。陈垣以年代学进行核算,指出凡“一年有两纪元之例,中间须少算一年”。光武帝在建武三十二年改元建武中元元年,赵翼未注意一年之中有两纪元之例,将光武帝即位时年岁,累加建武三十二年、中元二年而未减一年,计算上失误。光武帝去世时实为63岁。 陈垣认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也无由知其致误之原。”如在一次《史源学实习》课中,陈垣通过“读《廿二史札记》所得教训”,让学生从六个方面举例说明之:“一、读书不
校勘整理通则
校勘整理通则 1 术语和定义 本通则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1.1 版本 版本是指一书经过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 1.2 善本 善本特指抄刻时代较早、内容完整、字迹清晰、错误较少的版本。 1.3 校勘 校勘是指利用古籍的不同版本和其他相关资料,通过对比分析、考证推理,指出和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字句、篇章上的不同和错误。 1.4 校勘记 校勘记是对校勘结果的文字记录。古籍的校勘,在完成误、脱、衍、倒等异文分析和审定正误后,需系统、扼要、准确地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这样一些文字称为“校勘记”。 1.5 校注 校注表示前人校勘注释的文字内容。 1.6 眉批 表示在书眉处的批注、评语、订误、校文、音注、题名等文字。有作者自加者,也有后人所加者。有已雕版上书者,也有刊印后书写者。 1.7 点校说明 点校说明是对点校整理工作的研究所得、原书的版本源流、校勘的方法体例等加以详尽说明。 1.8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是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思想等基本情况。 2 符号与约定 2.1 □ 表示古籍缺文,空围数与缺文字数相等。
□……□表示古籍缺文,但字数不清。 2.2 ■ 表示电脑无法输入的文字。如以组合方式自造字,则以【】标注。如:■【骨干】 2.3 ( ) 表示文中夹注、当作小字的内容。 3 古籍版本的选择 3.1 底本的确定 选择善本作为底本。 选择原则:(1)祖本或早期刊本;(2)内容完整无残缺的足本;(3)前人整理过的精校精刻本。 3.2 校本的确定 同书底本以外的其他版本。版本较多者,不必全选,应选择有代表性、质量较好者为校本。 3.3 他校本的确定 文义不安又无别本可作校资,应考虑他校。 4 古籍的校勘 4.1 校勘术语 4.1.1 是非校勘语 用于说明有明确依据的校改内容。常用的有:“据改”、“据补”、“据删”、“乙正”等。 4.1.2 倾向校勘语 用于说明没有确凿校改依据,但校者有倾向性意见者。常用的有:“疑误”、“疑脱”、“疑衍”、“疑倒”、“当作”、“当改”、“当删”、“义长”等。 4.1.3 异同校勘语 用于说明是非难定,校者亦无倾向性意见的异文。常用的有:“某本(或某书)作某”、“某本(或某书)有某”、“某本(或某书)无”。 4.1.4 存疑校勘语
古籍校勘中的形讹与借字辨析
古籍校勘中的形讹与借字辨析 谈莉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四期) 【内容提要】古书用字相当复杂,流传至今又难免存在讹误。在古籍整理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把握汉字的形体演变和语音的古今差异,将通假字以及因避讳而导致的字形替代等文字借用现象与字形错讹区分开来,以便更好地阅读和校勘古籍。 【关键词】古籍校勘形讹古音通假避讳字形替代 辨正古书中的讹字是古籍校勘的重要内容。而古书中的用字现象又相当复杂,尤其有大量的借字,包括常说的通假字,以及书写者出于各种原因有意识地使用的临时代用字。汉字的形体演变和语音的古今差异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判断是作者借字而用还是后人传抄致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不明借字而导致形讹也是常有的现象,《战国策·赵策》:“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其中“揖”《史记·赵世家》则作“胥”。“胥”通“须”,意为“等待”,可见“揖”当是“胥”字传写之误。看来在古籍校勘中分清讹字和借字是很有必要的。 一 古书中的错讹多种多样,首先表现为字形的讹误。典籍中存在的形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形似而误。洪迈《容斋四笔》卷二谈“抄传文书之误”云:“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版,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無)千岁(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
古籍校勘解读中语言学研究运用.docx
古籍校勘解读中语言学研究运用 一、引言 《墨子•备城门》中有如下句子:(1)适(敌)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选本,迎而穴之,为之且(具)内弩以应之。(《备城门》)句中“选本”之“本”为讹字,王念孙以为“选本”当为“选士”,孙诒让则说“‘本’与‘卒’隶书亦相近,后文‘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今本讹为‘本’,可证。王定为‘士’之讹,未知是否。”[1]可见,孙诒让更倾向“本”是“卒”之讹。吴毓江《墨子校注》兼列王、孙二说,并未下案己见[2]。究竟是“选士”还是“选卒”,在今天的译注本中,多取王说。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此句即取“我亟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3,p23]。姜宝昌《墨守训释》引王念孙说,认为“士”字“义形近讹作‘本’”,“王校是,今从之”,释“士”为“士卒,甲士,军士”,将此句译为“守方应急令专务凿穴之工师挑选得力士卒,相迎挖掘穴道”[4]。孙以楷、甑长松译《墨子全译》附《墨子》原文,注“‘本’当作‘士’”[5,p448],并译为“我方立即令坑道师挑选士兵,迎头挖坑道”[5,p212]。孙中原作“我急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6,p421],译为“我方急使精于掘隧道的工师挑选士卒,迎面掘隧道”[6,p428]。方勇对此句“选本”亦采“选士”说,并专门注释为“精兵”,译为“我方即刻派遣善于挖掘的精兵,迎头挖好深沟”[7,p477]。综观诸家注译,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字校勘多取王
说,认为是“选士”,仅孙诒让提出或为“选卒”;二是对“选士”译文,多看作动宾式,即“选”是动词。唯方勇解为偏正式,即认为“选”作定语修饰“士”。本文尝试从“士”“卒”两词词义与使用的细微差别来探讨例(1)中“本”究竟是“士”还是“卒”;同时结合文意,辨析“我亟使穴师选本”句的句法、语义,看“选本”究竟是动宾结构还是偏正结构。二、“本”为“士”还是“卒” 《王力古汉语字典》对“士”与“卒”作出辨析,“‘士’和‘卒’分别是:作战时,士在战车上面,卒则徒步”[8]。在战车上还是徒步,体现两者身份、地位的差异,显然“士”比“卒”身份要特殊、地位要高,“卒”处于军队最基层。观察例(1)“我亟使穴师选本,迎而穴之”,“迎而穴之”即挖掘隧道。这样基础性的体力工作,“卒”更为适宜,且例(1)句上一段中有相似语境使用了“卒”,可加以佐证:(2)复使卒急为垒壁,以盖瓦复之。(《备城门》)这一句内容句式与例(1)较为相似,“卒”被差使做具体的防御工事。可见,例(1)中“卒”从事挖掘隧道这种基础性体力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与“卒”的使用语境不同,《墨子》中“士”见用的语境都不重在具体的基础性工作,其使用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考察《备城门》等城守各篇,“士”一般有表示身份性质的定语修饰,如:(3)城上十人一什长,属一吏士。(《备城门》)(4)敢问客众而勇,堙次吾池,军卒并进,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