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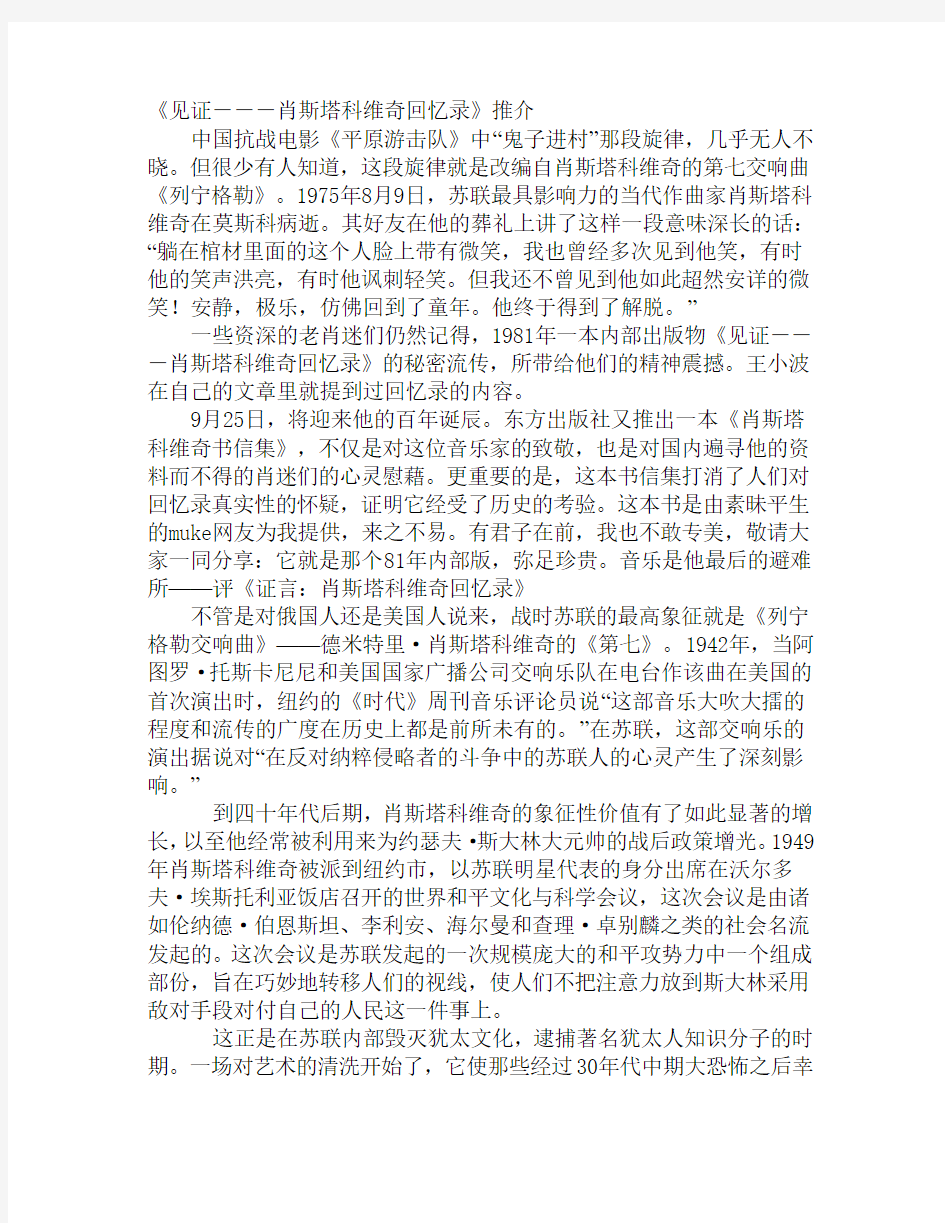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推介
中国抗战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鬼子进村”那段旋律,几乎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旋律就是改编自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1975年8月9日,苏联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病逝。其好友在他的葬礼上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人脸上带有微笑,我也曾经多次见到他笑,有时他的笑声洪亮,有时他讽刺轻笑。但我还不曾见到他如此超然安详的微笑!安静,极乐,仿佛回到了童年。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一些资深的老肖迷们仍然记得,1981年一本内部出版物《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秘密流传,所带给他们的精神震撼。王小波在自己的文章里就提到过回忆录的内容。
9月25日,将迎来他的百年诞辰。东方出版社又推出一本《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不仅是对这位音乐家的致敬,也是对国内遍寻他的资料而不得的肖迷们的心灵慰藉。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信集打消了人们对回忆录真实性的怀疑,证明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本书是由素昧平生的muke网友为我提供,来之不易。有君子在前,我也不敢专美,敬请大家一同分享:它就是那个81年内部版,弥足珍贵。音乐是他最后的避难所——评《证言: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说来,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列宁格勒交响曲》——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1942年,当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队在电台作该曲在美国的首次演出时,纽约的《时代》周刊音乐评论员说“这部音乐大吹大擂的程度和流传的广度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苏联,这部交响乐的演出据说对“在反对纳粹侵略者的斗争中的苏联人的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
到四十年代后期,肖斯塔科维奇的象征性价值有了如此显著的增长,以至他经常被利用来为约瑟夫·斯大林大元帅的战后政策增光。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被派到纽约市,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分出席在沃尔多夫·埃斯托利亚饭店召开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诸如伦纳德·伯恩斯坦、李利安、海尔曼和查理·卓别麟之类的社会名流发起的。这次会议是苏联发起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和平攻势力中一个组成部份,旨在巧妙地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不把注意力放到斯大林采用敌对手段对付自己的人民这一件事上。
这正是在苏联内部毁灭犹太文化,逮捕著名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时期。一场对艺术的清洗开始了,它使那些经过30年代中期大恐怖之后幸
存下来的作家和作曲家们的命运又处于生死存亡的地位。在音乐领域中,主要的攻击目标是肖斯塔科维奇。尽管他得过不少斯大林奖金,现在却被称为“非苏维埃的、不健康的、荒诞的、没有韵调的”作品的作者。他知道该怎么办。1936年为了他写的一部惹恼了斯大林的歌剧,在受到了当众“鞭笞”之后他差点儿丢了命。在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通过一项谴责他的决议之后,他为能指出他的缺点而对苏共公开地表示“深切地感恩戴德”。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对逗留在沃尔多夫饭店里的肖斯塔科维奇加以细致观察,就可以发生他根本不适合承担分配给他的作斯大林的宣传员的角色。坐在该饭店“星光屋顶”的高台上的他,给人一种令人惊异的虚弱感,人们可以看到他用抖动着的手拿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的面部经常习惯性地抽搐着,嘴唇也拉成一种令人狐疑的微笑。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这个发言既攻击了美国战争贩子,也攻击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与此同时对“苏联音乐文化达到的空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加以赞扬。在发言稿的整个宣读过程中,从这位作曲家嘴角和面颊的不停抽动中可以看出,他的坐立不安已达到了一种难以控制的程度。
不过,对大多数人说来,肖斯塔科维奇确实是像他自己说自己的那样,是苏联国家和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对其他人说来,他代表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他说的那些话过了许多年都难以被人忘记。随着这本书的问世,构成他人格的这两种形象都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是在他1975年(68岁)去世前四年之内,对音乐研究家所罗门·沃尔科夫口授的。这些手稿被偷运到国外,每一章上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的亲笔签名。之后沃尔科夫移居到了美国,他对手稿进行了编辑并加上注释。这本回忆录既然已经出版了,对这位作曲家生涯中的每一个插曲都不能用过去那种眼光看了,对他的每一部音乐作品也必须用新的、不同的方式去理解。
在沃尔多夫开的这次会就是一个例子。正像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参加这次会就像参加一种可怖的字谜游戏,戏中主要演员的脸孔实际上是一种对愤怒的掩盖,他的微笑是一种恐惧的苦笑。西方对斯大林所发动的一场对文艺上的“腐败的形式主义堕落”(即实验主义)的攻势反应冷淡,这曾使得斯大林很失望。“不要担心,他们会把它咽下去的。”这位独裁者说。把肖斯塔科维奇派到纽约来,就是他所使用的填鸭式的方式。“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肖斯塔科维奇说道。“这十足是他
的风格。”这位作曲家对美国人甘愿受骗上当一事除了表示蔑视之外别无它法。
回忆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因恐惧而吓傻了的,骄傲、颖悟过人和有教养的人。“你感到想喊叫出来,但是你控制住自己,结果就只是哼叫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来”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在无论什么声明上都签字,做给他准备好了的无论什么内容的讲话。但是在那些胡言乱语的后面藏着另一个肖斯塔科维奇,他的主导激情就是愤怒。想到在苏联政权对他的音乐采取种种手段之后人们对他的冷漠与威胁,他就久久不能平静。他埋在心头的最大愤怒是对着斯大林的,他的最大悲伤则留给这个独裁者的牺牲者了。
这些态度与人们通常所了解到的他的态度是如此惊人地不同,以致于将来会有那么一些人会怀疑他是不是在生活的最后年代在信仰上
发生了改变,并为后代着想而修改了他的回忆录。对这个总是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不过这本书的诚心诚意是显然的,不难使大多数读者信服。
由于不能用语言发汇他的愤怒,作曲家把它表现在自己的音乐里。“我的大数交响乐都是墓碑。”他说道。“我们的人民死掉的太多了,他们被埋葬在一些谁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很愿意为每一个牺牲者写
一部作品,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音乐奉献给他们所有的人的缘故。”他说,对第七交响曲的构思始于战前,该作品中用吓人的膨胀极强音演奏的所谓侵略主题,与纳粹的进攻毫无关系。“当我写下这一主题时,我考虑的是人类的其他敌人。”使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成名的第五交响曲,本来是旨描述斯大林在1936-37年的大恐怖的。在斯大林死后的时期,他的第十三交响曲是用以表示对反犹太主义的抗议的,第十四交响曲则是为古拉格恐怖敲起警钟。
就是他对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所作的有力的重新配器,也是为了突出该歌剧的这样一种启示:即一个“反人民的政府”在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是罪恶的。作曲家想念歌剧的总谱比根据普希金的剧本改写出的歌剧脚本更清楚地突出了这一主导思想。“对我说来,这种抽象的艺术——音乐——更为有效”,他说。“音乐把一个人从头到脚彻底照亮,同时那也是他最后的希望的最后的避难所。
对肖斯塔科维奇说来,音乐对一个精神上受到凌辱但又长期不能表达出来的人确实是最后的希望和最后的避难所。不过要想使斯大林或任何其他人能够了解他所写的音乐的涵义,不亚于水中捞月。斯大林像所有其他的俄国暴君一样,其对文艺的态度可以用十九世纪讽刺作家米哈伊尔·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一篇小说中一个官僚所说过的话来概括:
“凡是我不懂的东西对这个国家说来都是危险的。”
这位作曲家兼历史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过去从未拿出过来的描
绘近55年来苏联音乐生活的图画。他对他的老师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亲切而情趣横生的回忆勾勒了音乐文献中一幅最动人的作曲家画像。肖斯塔科维奇冥想着他的那些亲密朋友们的命运,导演伏赛瓦洛德·梅耶荷德,红军元帅米哈伊米·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人物:作曲家们、一位管风琴师、一位音乐研究家。所有这些人都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死掉了。“当我开始一个个回忆起我那些朋友和熟人们一生经历时,“他对沃尔科夫说,“我所看到的全是尸体,一座座用尸体堆起来的山。”
也许最动人的一段就是哀痛民间音乐在苏联绝种了的那段。肖斯塔科维奇讲述了一个关于民间盲人歌手的故事,这些人叫利尔尼基和班杜里斯蒂,他们从记不清多久以前的时代就开始沿着乌克兰乡村的道路游荡了。在三十年代中期,这些歌手们被召集起来去参加在乌克兰举行的一次官方的民族音乐代表大会。那些来自乌克兰各地,包括来自最小的偏僻村庄的歌手们一共聚齐了几百人。肖斯塔科维奇说:“那简直是个活的博物馆,是这个国家的活的历史,代表了它所有的歌曲、所有的音乐和诗。而他们却几乎全被枪毙了,差不多所有那些可怜的盲人全被杀死了。
为什么?肖斯塔科维奇答道:“就是要这样,这样他们就不会碍事了。”那些盲人唱的歌曲并没有得到检查官的通过。“在那儿干的那些事太积德了,”他用愤怒的挖苦补充道,“全面的集体化开始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被他们消灭了,而这些盲人却在这儿转来转去,唱着一些内容可疑的歌曲。”肖斯塔科维奇起誓说,“总有一天人们会找这些干了这件坏事的和其它类似坏事的人算帐的,但愿他们的子孙会找他们。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活着就没意思了。”
肖斯塔科维奇为那部卓越的苏联影片《哈姆雷特》写了音乐。那是他最喜欢的剧作之一,其中有一段哈姆雷特说的话他是特别欣赏的:“你愿意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尽管你可以使我烦恼,但你永远利用不了我。”现在我们才知道,那本来是可以作肖斯塔科维奇的墓志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