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野鸭》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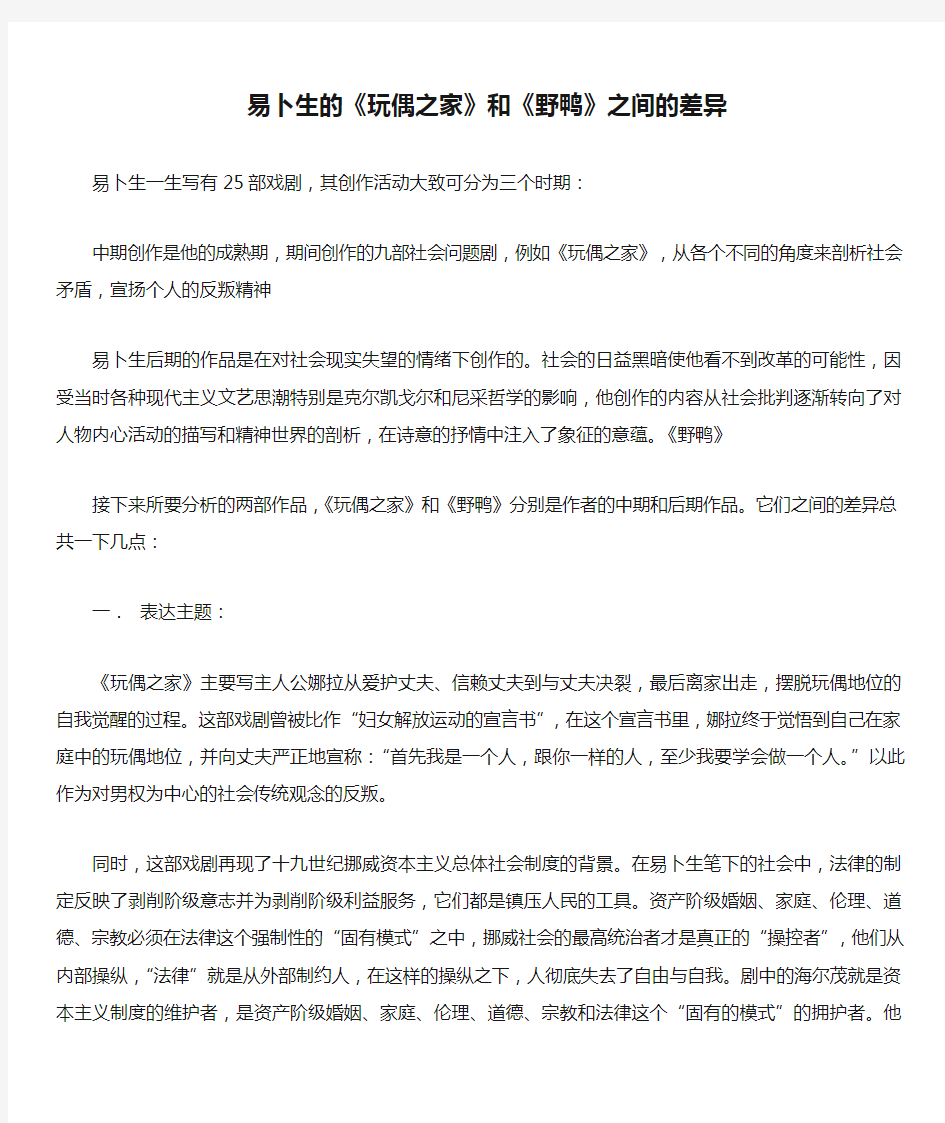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野鸭》之间的差异
易卜生一生写有25部戏剧,其创作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中期创作是他的成熟期,期间创作的九部社会问题剧,例如《玩偶之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剖析社会矛盾,宣扬个人的反叛精神
易卜生后期的作品是在对社会现实失望的情绪下创作的。社会的日益黑暗使他看不到改革的可能性,因受当时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特别是克尔凯戈尔和尼采哲学的影响,他创作的内容从社会批判逐渐转向了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和精神世界的剖析,在诗意的抒情中注入了象征的意蕴。《野鸭》
接下来所要分析的两部作品,《玩偶之家》和《野鸭》分别是作者的中期和后期作品。它们之间的差异总共一下几点:
一.表达主题:
《玩偶之家》主要写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的过程。这部戏剧曾被比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在这个宣言书里,娜拉终于觉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并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会做一个人。”以此作为对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
同时,这部戏剧再现了十九世纪挪威资本主义总体社会制度的背景。在易卜生笔下的社会中,法律的制定反映了剥削阶级意志并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它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宗教必须在法律这个强制性的“固有模式”之中,挪威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操控者”,他们从内部操纵,“法律”就是从外部制约人,在这样的操纵之下,人彻底失去了自由与自我。剧中的海尔茂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是资产阶级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宗教和法律这个“固有的模式”的拥护者。他复杂多变失去了自我的性格特征,顺应了”适者生存”人的两难处境。娜拉却是争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挣脱“固有模式”活在真实中的自由人。它表现了易卜生《玩偶之家》戏剧的社会讽刺性,凸现反社会性,并希望以此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法律、道德、宗教和受金钱支配的结构进行严厉的判决
《野鸭》这部五幕悲喜剧围绕威利和艾克达尔两家的背景展开,是一部看似平常的家庭悲剧,实际上却是易卜生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象征主义戏剧。在缓缓的叙述中揭示出理想生活和庸俗生活的矛盾,不经意地表现了幻想对人的全部意义。
这部戏剧也是易卜生所有戏剧创作中颇为令人困惑和茫然的一部。这部剧中似乎传达着这样一个主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时时处处都充盈着由各种谎言和假象所构成的幻景;我们陶醉和浸淫其间,只要没有人来捅破它的虚幻性,生活还是可以平静而快乐的,拿剧中清醒者瑞凌医生的话来讲,那就是,“只要我们有法子甩掉那批成天向我们穷人索要‘理想的要求’的讨债鬼,日子还是很可以过下去的。”
这个剧本的写作意图也并没有《玩偶之家》那么明显,批评家评论说,“人们竭尽所能地要去弄明白易卜生的意图,却茫然不知其所向。“易卜生似乎已经料到了这种情况。他在该剧发表之前写给他的出版人的信中就提到:他的《野鸭》,无论是主题还是技巧,都有新的突破,会给年轻的戏剧家们以新的滋养,也会给批评家们以争论和评析的新材料;而这正是他所期望和喜悦的。
全剧的基调是灰色的,貌似喜剧的结尾更是黯然,大大消除了此剧的批判性。迷茫悲观的易卜生似乎无法定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庸俗生活压倒性地战胜高尚理想。哪怕老威利遭到了报应,眼睛要瞎了,那又怎样呢?除了无辜的海特维格过早的离开人间,一切都恢复了原样。雅尔马夫妇在无奈中已经和解;格瑞格林被瑞凌说服,只好接受自己的命运,他说:“我的命运像现在这样,倒也很好。”维持庸俗生活的现状,保持幻想,继续过自欺欺人的日子,这个发展成喜剧的结局其实是相当悲凉、淡漠的,合乎现实生活的常理,显示了易卜生晚期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也反映了易卜生从乐观到消极的心路历程。
二.表现手法:
《玩偶之家》中通过对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
《玩偶之家》中通过人物群像的刻画,确立了以娜拉与海尔茂矛盾冲突为主线,围绕着“冒名签字”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为副线。主线、副线在剧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纠缠,副线又对主线起着推波助澜作用。每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的矛盾冲突都尽可能展示到极致,他们的悲剧命运和娜拉的悲剧给合在一起,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揭露
而《野鸭》:则展现了易卜生对戏剧冲突的全新认识:
与其以往的剧作所不同的是,《野鸭》易卜生设置的戏剧冲突并不激烈,他对剧中人物的讽刺也温和,却将关注的焦点由外部动作转向内心冲突,而呈现给观众和读者的却是一幅多层面的芸芸众生心态画像。事实上,《野鸭》是一部关于心灵的戏,一部关于何谓健康心灵并如何获取它的戏。
另外一个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该剧贯穿始终的象征手法的运用。
全剧始终笼罩在悲伤地“野鸭”气息之中,野鸭可以说是剧中主要人物的象征。这样的特点首先表现在《野鸭》中的雅尔马身上。
通过格瑞格斯之口,易卜生两次指出他很有几分“野鸭”气息。“野鸭总是这样子。它们使劲扎到水底下,死啃住海藻海带——和水里的那些脏东西。它们再也钻不出来了”雅尔马昏聩无能唯唯诺诺,在外人面前生怕寒酸的老父亲给自己难堪,不敢上前相认,在家人面前又装腔作势,颐指气使,整天沉浸在当发明家的幻想之中,其精神也在虚幻的梦想中渐趋麻木,十五年来一直受着自己妻子当年的情夫老威利的恩惠过日子,他就像是那只被养在水槽里的野鸭,过着暗淡无光的日子。
三.角色塑造:
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角色塑造中,虽然她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理想很难实现,但易卜生对她的这种行为,这种精神却是赞赏的,所以说娜拉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比较鲜明的,也带有一些催人警醒的作用。然而,在《野鸭》中,易卜生将他的笔触深入到他所说的“灵魂的最后一条皱纹”,竭尽其想象与洞察,酣畅而无情地拷问剧中那一个个扭曲的灵魂,试图探究它们染病的根源,为病态的灵魂做一个睿智的诊断。
作者一反以前鲜明的人物形象,在《野鸭》中描写了一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人物,并将同情的笔触加在其形象描绘上。这个人物就是剧中的雅尔马。
雅尔马显然是易卜生颇为同情和钟爱的人物。他是一个在其成长过程中遭受过打击和创伤的“受挫儿童”,明显地不适应成人世界的生活;他的所作所为总是在逃避责任和挑战。他似乎永远也不会长大:从思维方式到言行举止都显出幼稚和低能。医生瑞凌对这样的一个人物看得很清楚:“如果他曾经有过你所谓个性的不正常发展的倾向,那种倾向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别人铲除干净了。”他就停留在那个孩提时代,他的生活其实也其乐融融的。瑞凌认为,造成雅尔马今天这种状态的罪魁是他的两个姑姑,也就是易卜生眼中挪威传统文明的代表,它已经在他十几岁时就将他身上的血气和意志“铲除干净了”!雅尔马显然是一个已被现代文明“去势”的“染病的人”,是易卜生心目中现代人的代表,满身的“野鸭气息”。尽管如此,瑞凌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生活还是得照样过下去。
综上我们所论述的,随着作者社会阅历的增长,作者已经不能满足于过去的那种简单地批判呐喊,面对这日益黑暗的现实社会,他希望做得更多,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真正地有所改变,但是,究竟是时间改变了他,还是他最终妥协了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作者的心境始终还是随着对现实世界的愈加失望而越发消沉,在越发黑暗的现实社会中,改革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作者在创作《野鸭》这部剧时想必也还没有找到答案,这也是这两部剧中作者创作心态上的巨大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