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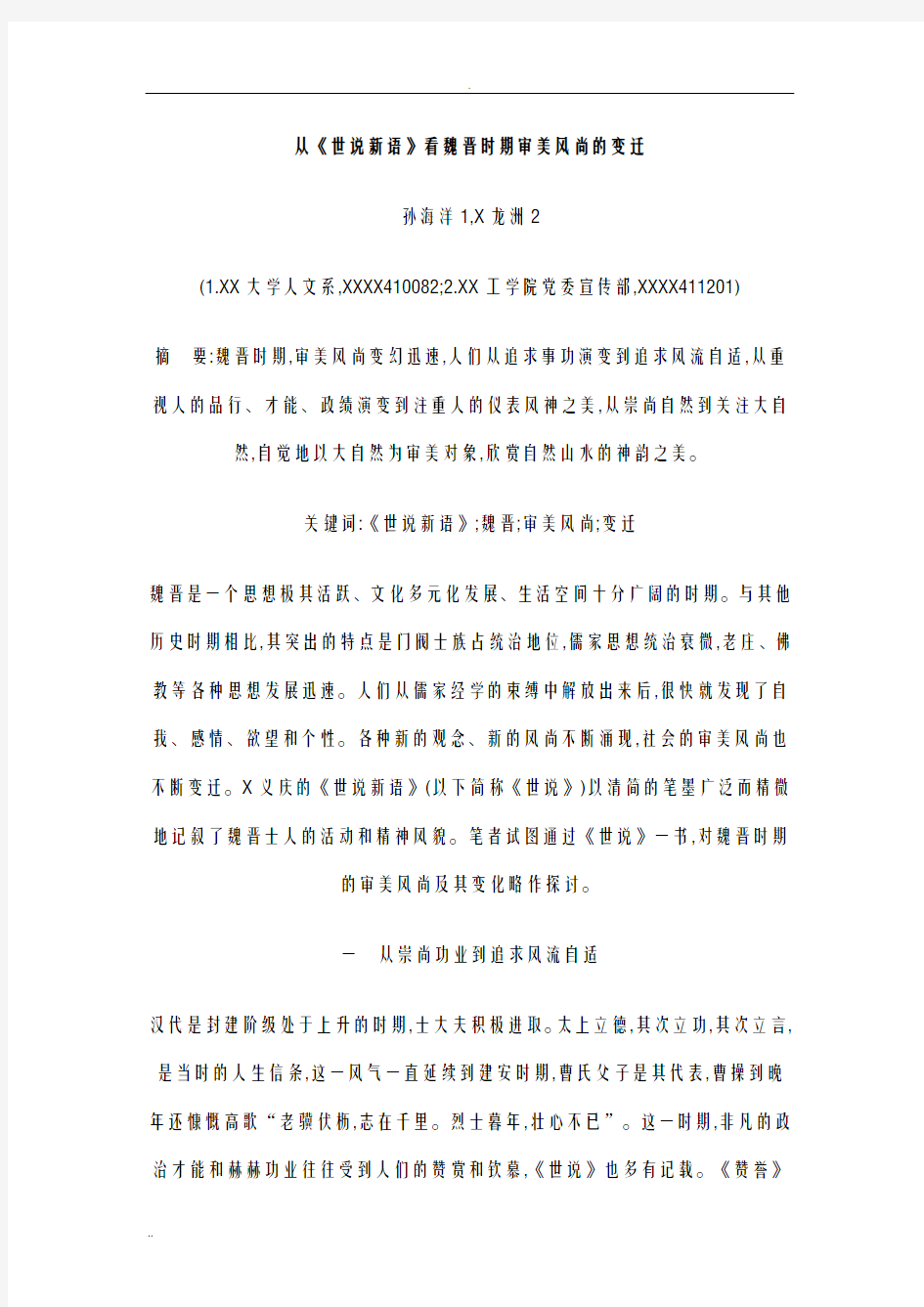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孙海洋1,X龙洲2
(1.XX大学人文系,XXXX410082;2.XX工学院党委宣传部,XXXX411201)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X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
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
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X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X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诸">诸君何为入我巾军中?’”“X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X翰后来当齐王东曹椽,见东风起,即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羹和胪鱼脍,说:“人生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官数 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挂冠而归。 放纵是追求自适在生活上的表现,而魏晋人的清谈则是一种审美活动。《世说·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X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听众“咨嗟称快”,并不是因为谈论多么高妙深奥,而是因为谈论者才华丰茂,辩诘精彩,辞采华赡,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有一种美的享受。又支道林、许询等人在会稽王斋头开讲,“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同上)。支许二人都通佛理,二人主讲,定然掺杂许多佛理,在座众人未必都懂,但反应却那么强烈,主 要还是两人的口才、文辞吸引了他们。又:“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支道林为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也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已”。谈者、听者都是在追求一种情趣,从清谈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情上的满足。因而当时之人乐此不疲,有的人甚至不顾性命,沉迷其中,《世说·文学》载:“卫王介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王介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王介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适意,作为魏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那个充满忧患,充满不和谐的时代的产物。士人们从儒家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从而追求适意这一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的出现,并得到自觉的认可,表明魏晋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达到了一 定的哲学高度。 二从注重德行到重视人体自身的美 人物品评肇自东汉后期,其时,士人与宦官斗争激烈,一些士人退居乡野,批评朝政,指斥阉竖,臧否人物,形成风气。当时品评人物的内容主要是朝廷官员或士人的品行、才能、政绩等,这在《世说》的《言语》、《赏誉》、《德行》诸篇中多有记载。如《德行篇》说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X,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又记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地,“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人们遂以此定优劣。又《识鉴篇》载乔玄评曹操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汉末人也注重人的 外表风度,但往往将外表风度与德行相联系,《德行篇》评李膺“风格秀整”,就是与其“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相关联的。诗人徐干说:“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君子)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声气可X,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1]认为仪表是德行情操的外在表现,以合符儒家礼仪为美。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但他的思想显然属于前代。建安人多尚通脱,不十分注重容止,故《世说·容止篇》很少有建安及建安以前人的事迹,但也有部分建安人开始注意到个人容止,《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X王圭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至魏晋之际,士人们就非常注重外貌举止了,人们也多所品评,而且审美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曹操认为自己长得不高大,不雄壮,不足以雄远国,所以让人顶替来接见外国使节。而魏末西晋,人们更欣赏人物面容的整丽和闲雅的风度。《世说·容止》云:“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口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面如傅粉,肤色皎然,当时被认为是“美姿仪”。这是一种柔弱之美,时人就以这种柔弱的女性美为尚。《容止篇》所写的其他美男子也多属此类。如“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XX’”。“蒹葭”、“XX”都属柔弱之美。又说:“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又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当时所称颂的美男子多为奶油小生一类,可见时人对人物的审美观多少有些病态。 南渡以后,审美风尚又有所改变,名士们从南渡初的放纵逐渐转向追求宁静、闲适,追求一种潇洒的风神,开始注重人的气质、风貌,尤其注意人的所谓“神韵”。《容止篇》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此语本指王羲之的字非常潇洒,但同时也指其人。《赏誉篇》“殷中军道王右军”条X孝标注引《文章志》就说:“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赏誉》又载:“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谢曰:‘身不潇洒。君道心最得,身正自调畅。’”“调畅”即风神潇洒之意。X注引《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王献之称赞谢安真正潇洒,谢安则回赞王献之养身得道,风神调畅。“风神调畅”,这是当时对人的很高的赞赏,潇洒主要是指外在风姿的美,举止的闲雅。而“风神”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当时对人物美的最高评价“神朗”,“神朗”既包含气质的清爽,更有内在精神的明澈。如《赏鉴篇》中,王戎称赞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衍则赞裴楷“精明朗然,笼盖人上”。支道林外貌本不佳,但王羲之却赞叹他“器朗神隽”。是知东晋士大夫对人物的审美多注重精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反映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西晋,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容止》载:“裴令公(楷)有隽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至,强回视之。王出语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劲,体中故有小恶。’”裴楷病得本来不轻,连翻身都很困难,只是勉强回头见客,王衍却从他闪闪有神的目光中看出他得的不是什么大病。东晋人更精于通过眼睛来品评人物的风貌,《容止篇》亦多有记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谢公云:‘见林公(支道林)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眼如点漆”、‘黯黯明黑”,这在黄眼睛的中国男子中确实很特别,这种眼睛显得很聪 慧、有精神,所以受到赞美。裴楷又说“王安丰眼如岩下电”(同上),则这又与裴楷本人一样,属于目光锐利的那一种,其内在精神自不待言。 东晋士大夫品人更多地是将才貌、才情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推崇神明与风姿相统一的人格美。《世说·言语》“周仆射雍容好仪容”条X注引《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イ免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世说·赏誉》又载:“(X)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会,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语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雅服。”《容止篇》所说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手与麈尾的白玉柄一样洁白等等,都是将才情、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品赏。人们评X伶也说他“身长六尺,貌甚丑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同上),是说他外貌既丑,精神又萎顿,简直是土木形骸。又说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既矮又粗胖,且精神萧散。对二人的评价也是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晋人开始以人自身的形体为审美对象,这是人的觉醒的直接产物。这一时期对人体的审美又经历了从单纯的重外貌的整丽,到重视风度气质和内在精神,再到追求内外统一的人格美的过程,进步之速,发展之快,是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所不及的,只有在多元化文化的魏 晋时代才有这种可能。 三从崇尚“自然”到关注自然,到欣赏大自然之美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老庄思想也乘儒学衰微之机而迅速扩大其影响,一些士大夫开始习老庄,崇尚自然。后汉郭林宗云:“天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2]据《太平御览》卷602页引《抱朴子》说,蔡邕曾到江东,回来后,“诸儒觉其谈论更远”。所谓“更远”,是说他谈论义理有些玄远。建 安时的曹丕也开始谈及道家的淡泊、无为、自然等,只是还不集中。正始时期,玄风大畅,开始是XX有何晏、王弼等一批名士聚党而清谈,正始中期,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又形成了一个清谈群体。阮、嵇为反抗名教而公开标榜“自然”,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并且投身自然,优游山林。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赞颂,阮籍《咏怀诗》云:“登高远望,周览八隅。山川悠邈,长路乖殊。感彼墨子,怀此杨朱。抱影鹄立,企首踟蹰。仰瞻翔鸟,俯视游鱼。丹林云霏,绿叶风舒。”[3]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欣爱之情。正始以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大自然之美,左思《归隐诗》言:“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自然山水开始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名士们优游于青山秀水之中,品赏大自然之美,石崇《金谷诗叙》述说道:“有别庐在XX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 欢欣之物备矣。”[4] 西晋人对自然山水的依恋还只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而东晋士大夫对山水的喜爱则已正式进入美学的层次了。东晋偏安江南,名士多聚居于风光秀丽的会稽,江南秀美的山水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山水审美情趣。东晋名士之于山水,首先是审美娱乐的需要,其次是藉山水以悟道。《世说·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林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又“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表明,士大夫们已经在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山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并在审美活动中领悟茫茫宇宙万物 混一,本无区别的哲理,达到主客体相统一,人与大自然合一的境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这一境界的具体写照。 自然山水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象后,又进一步使主体积累了审美经验,使人们对山水的审美不断向纵深发展。首先是寄情山水,观赏山水日益成为东晋名士一项重要的审美活动。他们安排活动往往选一风和日丽的日子,选一优美的处所进行。《容止篇》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王羲之、谢安、许询等人则经常在山阴集会,据王羲之《XX序》载,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他们选择了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山阴兰亭相聚修禊,饮酒赋诗。和尚们也不例外,据《晋诗》卷二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载,隆安四年仲春释法师与三十多名僧徒专门游览庐山石门风光。当时人甚至认为只有喜爱山水,懂得品赏山水之美的人才能作文。《赏誉篇》载:“孙兴公(绰)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 其次,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和描绘逐渐由形入神,从以貌写貌到捕捉、描写和品味自然山水的神韵。自然山水在建安时代及其以前人的笔下多为抒情表意的凭借物,即使曹操著名的《观沧海》也是如此。至东晋前期,人们开始注意自然山水,描山绘水的作品不少,但写法比较粗糙,如潘岳《金谷集作诗》写金谷之景:“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木卑。灵圃繁石榴,茂林列芳梨。”[5]罗列景物层层铺写,虽词采华丽,但画面凝重,缺少生气。东晋前期的山水文学略有进步,景物描写较有生气,画面较活泼,如谢万《兰亭诗》:“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 条鼓鸣音。”[6]景物明丽,但乏灵气,没有什么意境。当时的人多从览观大自然中去悟理,以止水之心,宁静之态去观照客体,主体与客体保持着距离,缺乏感情上的 交流。 东晋后期,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然山水的神韵并品赏其神韵美。神韵是我国古典美学中一个特殊的审美X畴,它的出现,与佛教很有关系。佛教贵神贱形,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云:“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数有粗精,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理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7]认为“神”是很精妙的东西,但是客观存在的,是万物之灵而寄寓于万物,它化自情感而又是情感的根本。对万物之“神”,画家们最先感受到,《世说·巧艺》云:“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隽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又:“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故。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人物脸上加画三根毛,就显得有识度。而这识度又是人物之“神”;谢鲲飘逸,喜好山水,飘逸这种风神很难通过画人物肢体或面部表情来表现,于是将人物置之丘壑之中,通过环境衬托出来。晋宋之际的画家宗炳则正式从理论上阐述了审美意义上的“神”,其《画山水序》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8]。“神”看不见,摸不着,但随处都在,只要会心应目,理入影迹,就可妙写。也就是主X主体与客体相契合,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观察山水时移神于山水,这样,山水也就有了灵气———神韵。因此,他说:“山水质而有趣灵。”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说的:“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9] 宗炳虽然对神韵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但他在创作上仍是主X“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而诗人们却能领会大自然的神韵,陶渊明写山水田园,以意会形,写形传神,常常情景交融,气韵生动:“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等[10],都意境幽远,韵味深长。对自然山水的神韵,精于佛学的谢灵运认识和感受得更具体、更确切。谢氏写山水景物多形似,但开始朝物我交融方向发展,他往往以欣喜之情,佛学的眼光去观察、看待山水草木,极力体味自然山水所含的美质,因而其笔下的自然山水富有灵气和禅佛意境,如:“白云抱幽石,绿波媚清涟。”(《过始宁别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11]水云竹石、芰荷蒲稗仿佛都具有生命、情感。诗人把握了自然景物的生命状态,故能传达出景物的神韵,景物 也就具有神思韵味,具有浓郁的意境。 《世说新语》所展示的魏晋审美风尚远非上述三个方面,但窥一斑可见全豹,从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由于儒家经学束缚的解除和老庄、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魏晋名士这个特殊文化群体的积极推动下,社会审美风尚急速变迁,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向深层次,向高雅,向内在情感和内在精神演进。这种高雅的情趣成了后世士大夫一种主要的审美情趣,其审美思想如对神韵的推崇等对后世美学和诗歌创作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1] 徐干.中论·法象[M].:中华书局,1989. [2] 晋葛洪.抱朴子·外篇·正郭[M].:中华书局,1979. [3] 逯钦立.魏诗(卷十)[M].:中华书局,1983. [4] 丁福保.全晋文(卷三三)[M].:中华书局,1958. [5] 逯钦立.晋诗(卷五)[M].:中华书局,1983. [6] 逮钦立.晋诗(卷十四)[M].:中华书局,1983. [7] 梁僧佑.弘明集(卷十二)[M].XX:XX古籍,1986. [8] 丁福保.全晋文(卷二十)[M].:中华书局,1958. [9]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A].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C].XX:岳麓书 社,1996. [10] 逯钦立.晋诗(卷十七)[M].:中华书局,1983.[11] 逯钦立.宋诗(卷二、卷 三)[M].:中华书局,1983.6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意境,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以及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如果典型是以单个形象而论的话,意境则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故而美学与意境就有了那么一层深厚的关系。美学里的意境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绘画中是作品通过时空境象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後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 意境理论最先出现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中有“意象”说和“境界”说。唐代诗人王昌龄和皎然提出了“取境”“缘境”的理论﹐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艺理论界对“境界”说的阐述虽然众说纷纭,为轩为轾,但有一个地方却出人意外,绝大多数评论者都把“境界”和“意境”等同起来。称之为“文学形象”、“作品中的世界”。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境界”一词作为一般习惯用法,如云“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泛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界域而言者。又如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修养造诣之各种不同的阶段而言者。又如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日夜流’、‘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此处之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作者所描写的景物而言者。 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美学命题和范畴。“意境”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学范畴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辩证统一性;美学范畴的动态变异性;“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哲学认知和审美认知方式交融的艺术观照方式。“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的范畴,这是从美学范畴说,这个范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炼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历代许多艺术家有意识去追求的。 中国民俗艺术的审美特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纵贯古今,汪洋恣肆,灿烂辉煌,照耀在世界文明的天空。在民族文化的沃野上,中国民俗艺术宛如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含苞怒放,以其特有的民族风格,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坚韧不拔的艺术追求,在人类艺术史上谱写了雄奇壮美的篇章。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在各式各样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它不但没有凋谢飘零,反而更加艳丽芬芳,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它的奥秘和真谛。 民俗艺术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相袭成俗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也就是在民俗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艺术形式的总称,其中包括民俗音乐、歌舞、戏曲、曲艺、杂技、绘画、剪纸、雕塑、建筑以及其他各种民间工艺美术等。 民俗艺术和民间艺术是两个含义十分近似的概念,有时甚至可以通用,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民俗艺术是民间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艺术除了包括民俗活动中的各种艺术形式之外,还应该包括来自民间艺术家的单独而非共同的创作,并不在民间广为流传和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和形式。民俗艺术和民族艺术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俗艺术必定是民族艺术,但民族艺术主要是针对其他民族而言的,所包含的内容自然要广泛得多。 在民俗美学的范畴中,衣食往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节日习俗等文化现象均属于现实美,其美学的原始表达无不与其实用功利和象征性联系在一起,而民俗艺术则逐渐脱离了现实的世界,进入了纯粹的审美精神领域,其审美本质也日益显露和丰富。虽然民俗艺术仍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并以此作为创作素材和表现对象,但它却是对现实生活提炼加工后的产物,比现实世界更具有审美价值。 在艺术美的世界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最完美的表现。 中国民俗艺术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民俗艺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与探讨,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种典型而鲜明的艺术特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一)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改革,不仅造就了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结构性变异,同时,它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从总的方面来看,90年代、尤其是最近几年间,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呈现出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个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大的改变。 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在它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潜在着一种相当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在放弃"政治──道德一体化"的文化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充分张扬大众意志的生活享受权利及其现实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追求个人基本生活利益的直接满足。很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出现,是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变革和文化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本身处在一种不断趋近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充分体现出"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 性,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来说,把现实活动的基本目标落实到物质生活积累和占有的过程中,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日常享受之上,便是一个应和了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且又非常实际的价值前景。它表明,在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中,"以经济为中心"既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政治纲领,同时,在现实活动层面上,它也是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生活改造和提高的基本力量。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正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的。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审美风尚总是体现了这个时代基本的文化存在状况及其价值取向,那么,90年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风尚正体现了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大众对自身生活的一种新的、自觉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根本之处,便在于它充分强调了现实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强调了通过物质占有和消费实现大众生活享受的直接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进程之上的生活"审美化"图景,已经非常具体地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的总体面貌。"审美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直观现实。 概而言之,这种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第一,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既是整个文化建构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大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直接规定;第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了一种向感性"享乐"动机的充分归趋,大众生活过程呈现出十足的娱乐享受形态,洋溢着现实感性的快乐情调;第三,大众生活过程不再追求自身的历史 中国古典美学 悠悠华夏五千年,世界上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古典美学则是中国历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人们所称道。 中国古典美学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构建中国古典美学框架的主要思潮和派别之一,其形成和发展直接与儒家相关。“仁义”是中国古代人民一直很推崇的一种道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认为仁时一种美。“仁”是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互相友爱、互助、同情等。1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2百行以孝为先,这是一种仁爱。在儒家思想中孝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敬爱父母、笃爱兄长,这是“仁”的基础。假如一个家庭父母不和睦,妻离子散,而家庭成员整天都心烦意乱,事事不顺心,那么又何来“美学”之说呢?孔子的美学思想,以仁学为基础,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沉思美之所在,强调唯有遵循仁义之道,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中才能获得自由,进入美的境界,所以“仁”时一种美。 “忠孝两全”一直是中国古典美所提倡的一种美德。“孝”是仁的一种,而忠则是义中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里“忠”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挚情感,其行为指的是舍己,即要求人们为忠诚对象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这一概念极其鲜明地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对象“伦理型”特征。“忠”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忠信、忠义、忠告、忠言等词,一直都广为流传。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公孙丑问孟子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3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指的就是融合了道德思想,渗透着情感意义。为实现一定的伦理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精神。“孔孟”之一的孟子高度赞美了这种为理想实现而自我牺牲的一切精神。那种“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在社会美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影响和鼓励着一代代的人们为之学习和努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5的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在金人的诱惑和威胁下不为所动,“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6的边疆将士勇敢无畏,“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7的清朝诗人于谦在诱惑面前洁身自好。 而对中国古典美学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的道家学派,则主张“道”作为宇宙的终极始因,把体道作为人得的存在的最高价值境界,道是道家思想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的出现,将先秦时代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具有人格化意味的“天”的观念,引向初具形而上色彩的抽象的理论层次。“道,可道也,非恒道也。”8“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9在老子的哲学中,道在宇宙的意义上被称为宇宙动力学始点而近于“一”,或在本论意义被作为万有物的终极本体而近于“无”,道即一即无,道不可道,道即是从自然运作中抽象出来的统摄万有的无为无不为的最高宇宙法则。10但老子的思想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朦胧而深奥,而作为“老庄”之一的庄子继承了老子之道,并认为谈天轮道目的在于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种有宇宙的色彩和本体论意味的绝对价值境界,因为庄子哲学哲学中引入了“天”、“人”、“吾”、“我”四者的关系。“无为为之之谓天”11,“天”在庄子的哲学中表达了“天帝”、“天帝”等人格化或宿命的意义,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的本然状态和生命的本真状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儿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 简析中国传统美学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研习中国书画的一名学生,也许对中国的传统美学体会更多更深刻一些,兴趣也更浓。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下面从以下几点试析:人生哲学,独特性,人生美艺术美,其价值。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已。 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体现在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这种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其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360docs.net/doc/8e5973539.html,/view/3510067.htm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录 (v) 第一章绪论 (1) 1.1选题背景 (1)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2) 1.3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4) 1.4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5) 1.5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6) 第二章女子妆饰的出现和发展 (7) 2.1女子妆饰的概念和起源 (7) 2.1.1女子妆饰的概念 (7) 2.1.2女子妆饰的雏形 (8) 2.2女子妆饰的基本内容 (9) 2.2.1面妆与面饰 (9) 2.2.2眉眼妆 (11) 2.2.3唇妆 (12) 2.2.4发式与发饰 (13) 2.3社会审美风尚对女子妆饰的影响 (15) 第三章唐代女子妆饰发展及审美风尚的变迁 (17) 3.1阔眉高髻:初唐女子妆饰的简约之风 (17) 3.1.1承上启下的初唐妆饰 (17) 3.1.2清新健康美:初唐女子妆饰概观 (19) 3.2红妆若醉:盛唐女子妆饰的突破与自由 (20) 3.2.1丰腴大气美:盛唐女子妆饰的流行时尚 (21) 3.2.2西来之妆:盛唐时期的胡风盛行 (24) 3.3懒倚楼台妆如泣:中晚唐女子妆饰审美风尚的转变 (25) 3.3.1中晚唐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审美风尚的影响 (26) 3.3.2奢华委婉美:中晚唐对于“病态美”的追求 (27) 第四章唐代女子妆饰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审美关联 (30) 4.1红袖与巾帼:唐代女子妆饰中女性审美意识的起落 (30) 4.2唐代儒道佛对女子妆饰的审美影响 (32) 4.3唐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子妆饰 (34) 4.3.1文学作品中对女子妆饰的描写 (34) 4.3.2艺术作品中对女子妆饰的展示 (37) 第五章当下唐代女子妆饰元素的再流行 (42) 5.1复古即流行:现代流行时尚对于唐代女子妆饰元素的运用 (42) 5.2继承与回归:现代审美风尚对传统美的追寻 (44) 结论 (47) 参考文献 (1)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5) 致谢 (1)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浅谈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当代的传承 ——以电影《黄土地》为例 摘要:《黄土地》是导演陈凯歌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深刻、意蕴深远,是中国不可多得的艺术片,通过对这部电影的镜头、场景、画面、造型、等一系列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和“意境说”的审美思想。从而揭示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当代的价值。 关键词:审美文化黄土地天人合一意境说 诞生于 19 世纪末、崛起兴盛于 20 世纪的电影经过百年历史的发展,凭着现代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以它生动逼真的视觉形象向我们展示着这个变幻多姿的世界,并在展现视觉形象的同时触动着我们的灵魂,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 自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京剧老旦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的部份场面。由此拉开了中国电影史的大幕。中国电影在中国传统审美的背景和基础上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审美文化在影视创作中显示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 一、“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儒家学派审美的最高境界。这种观点萌芽于西周时期的天命论。战国时期,孟子和庄子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种观点。再经过各朝各代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天人合一的观点几乎为各派哲学家所接受。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一种天人和谐的审美境界,在人与自然亲密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关的文化心理。这是人们以诗意的情怀去体悟自然的结果。自然万物是怡情悦性的对象,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中国美学正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中,即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中寻求美。用生命的意识去审美,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思维方式。在审美的层面上,人既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人即自然,自然即人。 1984年拍摄的电影《黄土地》,是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开山之作。同时,《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内容提要本文对华夏审蓑风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阐释,对华夏审美风尚的特征与个性及形成这些特征与个性的原因作了漾入的分析。 关键词华夏审美风尚发展 一、演进与发展脉络 华夏文明八千余年,从凿石为斧的初级加工工具阶段,到精镂细刻的宫廷艺术,审美风尚不仅绵延有序地发展,而且其发展呈现出某种自在的规律性。 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之际是华夏审美风尚的一个发轫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各民族的审美意识开始形成距今约一万八千多年前,山顶洞人就打造出了造型均匀规整、磨制光滑的石制工具,已有了被考古学家称为“装饰品”的小砾石、石珠、贝壳等。它们之中有的被赤铁矿粉染红,呈现红色最初的美感已在原始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形式和功能相同的原始舞蹈和原始绘画(1)。而分布更广的史前岩画,从广西左江和云南苍源到新疆、内蒙古的北方山区都有生动而丰富的展示。 在中国的审美风尚演化过程中,这种史前文化的审美特征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北方草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审美风尚就有地域造成的差别我们只能用主体文化所内涵的主要特征来概括其性质,并寻找其千年延续发展的脉络。我们用“龙腾凤起”来概括华夏审美风尚的原始特征,这是有人类学的根据的。 l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了一座仰韶文化墓葬。壮年墓主两侧,有用白色蚌壳精心摆塑而成的两个动物图形——龙与虎的图形。西水坡蚌塑开风气之先,众多具有特定内涵的意象符号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不断涌现,在部落兼并、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相互涵化、定型、沉积和简约化,终于凝结为具有震慑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一各种龙纹的变形图纹,如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红山文化的“玉龙形器”。 龙的腾飞对华夏审美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为古代中国人感受、体验、想象自然和人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价值框架,并成为殷商之际审美风尚的主流标识。从先民活泼而愉快的陶器纹饰到神秘沉重的青铜器的“狞厉之美”,体现出华夏审美文化中神权意志的威严和力量。而从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等饰纹可以看出:龙的腾飞使华夏审美意识有了一个真幻互融、神人相依的神话-审美心理模型.它激发了华夏民族的审美想象。 经历了最初的自由活泼的艺术想象阶段.经过夏商之际的过渡,终于.以先秦的人文伦理价值为核心的华夏审美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框架以德为本,美善一体,周初的“天命观”给秦汉审美风尚开辟了历史路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尚书·诏告》中说:“自成汤至于帝乙,因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义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在周初的文诰里,一个反复吟诵的主题就是敬德。从敬王丽敬德.自周开始,华夏文化的审美眼光已转向“人事”而非鬼神而从这一点出发,衡量人格美的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人格而至教化,由教化而至礼乐有序,终于形成一种以血缘伦理为核心。以“敬德”为内容的伦理审美精神,并成为稳定的“尊卑、男女、老幼”这一亘古不变的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机制。 华夏审美风尚从美善不分到获得美的自觉,魏晋是一个特殊的转换阶段。鲁迅曾以“文学的自觉”来概括汉末魏初的文化气质,因为这个时代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即“诗赋不必寓教训”的主张,使审美精神从道德和政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魏晋的文学风格,成为“几百年问精神上大解放,人格思想上大自由的时期”(3)。 从审美精神的发展看,魏晋时期是华夏审美文化真正的成熟期一一它使美与道德从属的关系疏远并形成了自己的属性和品格。在社会动荡不安、统一政权不复存在的魏晋时期,文化、艺术和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和个性,在这种环境里文士学者可以直抒胸臆丽不必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将自己的真情实感隐藏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尚通脱”,即可以写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4)。 这种个性化的精神自由,经过郭象“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的阐释,成为“独化于玄冥之境”(5)的独立自足的审美框架,所谓“《六经》礼乐本求致用,《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6),标志着审美 论《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高 娴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4)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它回避了魏晋时代黑暗的政治斗争,集中描绘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画卷。小说并不能消解历史的沉重,却从侧面反映魏晋时代社会主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让一个沉重的时代被软化和美化。《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具有尚情特质,其本质在于并非入世也未能超世的在世情怀。他们将个体精神价值置于社会价值观之上,注重精神世界的交流融汇,以情为纽带,以真为准则。在悬置了道德规范的主体意识下,他们表现出了超乎特定时代道德,又合乎人性本质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关键词:人情;在世;生命本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7)12-0008-03 收稿日期:2007-10-23 作者简介:高娴(1983-),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准则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被归纳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关系。《汉书?艺文志》中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宗法等级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模式和统治者的维持国家秩序的核心依据。作为统治的工具,它排除了人与人关系处理中的情感因素,而将其理智化为等级模式并作为礼法固定下来。真情的价值在其中泯灭,礼制让虚伪者轻易的叩开了方便之门。情与真本质上就有着重要的联系,“情”的初义就是“真”。“民之情伪尽知之 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情伪相感”(《易?系辞》 )中的情和伪相对,即是真的意思。从这样的字义变化中,我们认识到情的本质价值在于真。这恰好和礼所推崇的人为的“伪”的一面形成了对立。魏晋士人明显取了前者。 三种基本人伦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在《世说新语》都得到了表现。我们不妨以此来认识和探讨魏晋士族对功利价值观的超越,对个体精神的维护、以及对生命本质价值的演绎。 一、亲情:情至深处,不法常礼 亲子关系是生命降生所带来的最基本关系,鹁鸽护雏,乌鸦反哺,自然界都遵循着这样的生命关系。周代制礼将孝道作为人的最基本品德,孝成为古代中国立家立国的根本。“五伦”中首要的是“父子有亲”。作为道德标准的“孝”,只强调了子对父的义务,突出父子从属关系和地位差别;而发乎自然的情感没有等级区分。 当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那是怎样心情,《世说新语》中恰有一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 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这里的呼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句,已经被后人当作了魏晋士人尚情的宣言。王戎不标榜圣人,不是鄙人,他承认自己这一个凡夫俗子是有感情的人,并且是钟情的人。这样的坦诚和真情打动了山简,山简之前用“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来劝解王戎。且不说史书记载王戎的儿子绥19岁早逝,已经不是“孩抱中 物”[1] ,那一句“何至于此”的劝解之辞,正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中 父对于子的应有态度。这是一种违反自然人性的虚伪态度,王戎的真情表露击破了它。看到了情的深刻,礼的肤浅,山简“服其言”。 当礼成为了一种行为规范而被程式化并且这种程式在生活中被反复复制的时候,慢慢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而真情是无价的。不法常礼的行为方式虽然会被社会所误解,其实质却是为了维护真情的价值。阮籍的故事尤其体现了情和礼的对抗。这种对礼的冷漠,对世俗观念的叛逆,表现了情的深刻: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 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这第一则故事里,阮籍在母亲的丧期依旧参加社交活动,并且饮酒吃肉。他在行为受到他人的指责后,依然神色自若。文王用“有疾”给阮籍解围。固然如文王所说,阮籍服食五石散成疾,在饮食、行为要遵守诸多规范,必须饮酒吃肉,不能有大喜大悲[2],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礼的地位已经从无上崇高滑落到要给服食五石散的有疾人让路。阮籍真的因为服食而把母亲的丧事抛在脑外了吗?第二则故事让我们看到事实。服药者不能有大喜大悲,这里的阮籍却“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真情所致,哪里还顾及得到自己的服食禁忌。两则故事贯通来看,服食的重要性大于礼,然真情不得不发,不受任何束缚,服食禁忌已经无暇顾及。 比起无条件的对礼的服从,魏晋士人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于礼的价值取向。服食的本质在于追求无限的人生,后来泛化为魏晋士人的生活时尚。当魏晋士人们怀着超世的梦想追求仙风道骨而服食的时候,也同样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一 ? 8?2007年12月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Dec.2007第24卷第12期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Vol.24 No.12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8e5973539.html, 中国戏曲艺术与审美文化传统及其对中华总体美学的意义 作者:程宏宇 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35期 摘要:认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必须对古典戏曲的原生态历史进行总结,论析中国戏曲与审美艺术传统的相关问题,从戏曲艺术学科自身发展着眼,扫描中国戏曲美学总体发展及其趋势,揭示其对中华总体美学的深远意义和多元化价值。本文是一篇专题研究中国戏曲艺术与审美文化传统的论文,笔者扫描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对古典戏曲的原生态历史进行了小结,析论了中国戏曲与审美艺术传统的相关问题,进而从戏曲艺术学科自身发展来看,统观中国戏曲美学总体发展及其趋势。 关键词:中国戏曲审美传统传承创新 一、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戏曲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戏曲经历了萌芽、滋长、发展、成熟等几个重要阶段。13世纪初步进入成熟时期。20世纪中叶,基于我国戏剧将曲词、说唱、舞蹈、音乐、表演甚至杂技、武术、美术等有机地融为一体的高度综合性的艺术特征,戏剧史研究者将宋元间流行的“戏曲”一语,作为我国传统戏剧的统称,包括宋金以来的杂剧、南戏、传承和各种地方戏曲在内。 关于戏曲的起源,学术界历来有巫优说、原始歌舞说、百戏说、傀儡说及外来说等多种观点,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说来。我国戏曲既然是一种不断积淀创新而成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样式,其兴起因素就不应当是单一和孤立的,而应该是诗歌、音乐、舞蹈、表演、说唱等多种艺术成分长期交融聚合的结果。如果要发掘我国戏曲来源,则需从先秦歌舞、两汉百戏、六朝俗讲等一路寻索而来,同时也要兼顾诗词、歌赋、史传、说话等雅俗文艺样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驱鬼驱灾的傩仪也与戏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汉代民间流行的角抵戏《东海黄公》便是从傩仪中派生出来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祭神鬼活动之中的戏剧表演成分逐渐增加,其中的歌舞和技艺表演大有挣脱宗教仪式的外壳而风行于世的趋势。以科白、滑稽为主的参军戏源于后汉,至唐渐成格局。参军戏起源于后汉,至唐渐成格局。参军戏是与歌舞并行的一种滑稽表演。它与上古以来的优戏有内在的血缘关系。 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将近百年的战乱分裂局面,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作为宋代文化全面繁荣的重要标志,传统的雅文化与新兴的都市文化交相争辉,砥砺磨合,进而在广泛的艺术领域中并行突进。这种文化氛围,为结胎滋生于随唐之间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中国民俗艺术的审美特征.pdf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一)
(完整版)中国古典美学
简析中国传统美学的意义与价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唐代审美风尚变迁下的女子妆饰发展研究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
浅谈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在当代的传承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中国古代审美风尚
论_世说新语_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中国戏曲艺术与审美文化传统及其对中华总体美学的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