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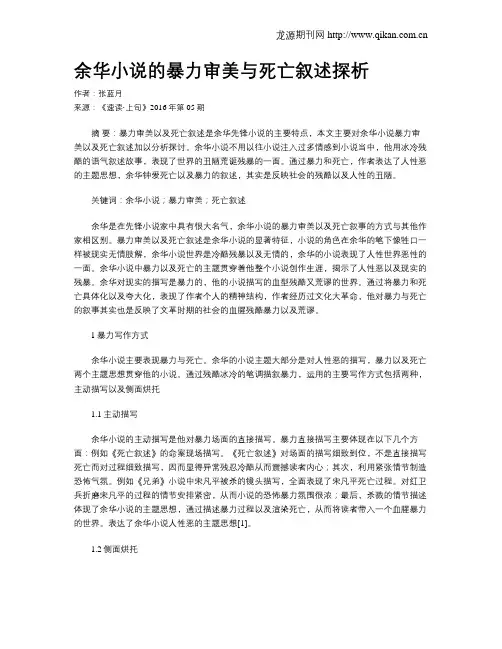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探析作者:张蓝月来源:《速读·上旬》2016年第05期摘要:暴力审美以及死亡叙述是余华先锋小说的主要特点,本文主要对余华小说暴力审美以及死亡叙述加以分析探讨。
余华小说不用以往小说注入过多情感到小说当中,他用冰冷残酷的语气叙述故事,表现了世界的丑陋荒诞残暴的一面。
通过暴力和死亡,作者表达了人性恶的主题思想,余华钟爱死亡以及暴力的叙述,其实是反映社会的残酷以及人性的丑陋。
关键词:余华小说;暴力审美;死亡叙述余华是在先锋小说家中具有很大名气,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以及死亡叙事的方式与其他作家相区别。
暴力审美以及死亡叙述是余华小说的显著特征,小说的角色在余华的笔下像牲口一样被现实无情肢解,余华小说世界是冷酷残暴以及无情的,余华的小说表现了人性世界恶性的一面。
余华小说中暴力以及死亡的主题贯穿着他整个小说创作生涯,揭示了人性恶以及现实的残暴。
余华对现实的描写是暴力的,他的小说描写的血型残酷又荒谬的世界。
通过将暴力和死亡具体化以及夸大化,表现了作者个人的精神结构,作者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对暴力与死亡的叙事其实也是反映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的血腥残酷暴力以及荒谬。
1暴力写作方式余华小说主要表现暴力与死亡。
余华的小说主题大部分是对人性恶的描写,暴力以及死亡两个主题思想贯穿他的小说。
通过残酷冰冷的笔调描叙暴力,运用的主要写作方式包括两种,主动描写以及侧面烘托1.1主动描写余华小说的主动描写是他对暴力场面的直接描写。
暴力直接描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例如《死亡叙述》的命案现场描写。
《死亡叙述》对场面的描写细致到位,不是直接描写死亡而对过程细致描写,因而显得异常残忍冷酷从而震撼读者内心;其次,利用紧张情节制造恐怖气氛。
例如《兄弟》小说中宋凡平被杀的镜头描写,全面表现了宋凡平死亡过程。
对红卫兵折磨宋凡平的过程的情节安排紧密,从而小说的恐怖暴力氛围很浓;最后,杀戮的情节描述体现了余华小说的主题思想,通过描述暴力过程以及渲染死亡,从而将读者带入一个血腥暴力的世界。
死亡的风景--余华、莫言暴力叙述现象研究

论述题:余华暴力叙事变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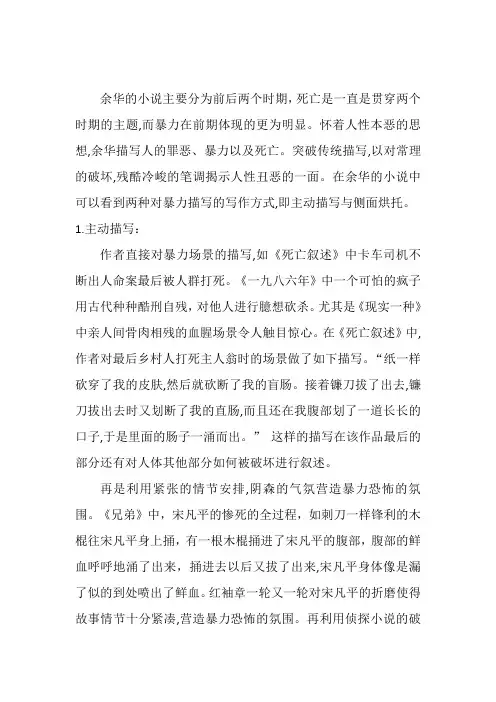
余华的小说主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死亡是一直是贯穿两个时期的主题,而暴力在前期体现的更为明显。
怀着人性本恶的思想,余华描写人的罪恶、暴力以及死亡。
突破传统描写,以对常理的破坏,残酷冷峻的笔调揭示人性丑恶的一面。
在余华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两种对暴力描写的写作方式,即主动描写与侧面烘托。
1.主动描写:作者直接对暴力场景的描写,如《死亡叙述》中卡车司机不断出人命案最后被人群打死。
《一九八六年》中一个可怕的疯子用古代种种酷刑自残,对他人进行臆想砍杀。
尤其是《现实一种》中亲人间骨肉相残的血腥场景令人触目惊心。
在《死亡叙述》中,作者对最后乡村人打死主人翁时的场景做了如下描写。
“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
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
”这样的描写在该作品最后的部分还有对人体其他部分如何被破坏进行叙述。
再是利用紧张的情节安排,阴森的气氛营造暴力恐怖的氛围。
《兄弟》中,宋凡平的惨死的全过程,如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往宋凡平身上捅,有一根木棍捅进了宋凡平的腹部,腹部的鲜血呼呼地涌了出来,捅进去以后又拔了出来,宋凡平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
红袖章一轮又一轮对宋凡平的折磨使得故事情节十分紧凑,营造暴力恐怖的氛围。
再利用侦探小说的破案的手法,一层层地向读者揭开人头之谜。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及人物的生活都是非常态的。
在小说《现实一种》中,暴力表现得十分突出。
显然,这种对家庭的描述是反传统也是可悲的。
以上对杀戮情节的描述,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认识。
对于这样直接描写暴力,即是直接对死亡的描写和对死亡氛围的渲染。
让读者直面暴力,带领其进入一个血腥死亡的世界发觉人性恶的一面。
2.侧面烘托。
作者通过读者内心对事件的猜测,从侧面烘托出暴力叙事达到的效果。
比如在《河边的错误》里,从开头描写么四婆婆赶鹅到人们惊慌失措的逃离再到小孩的得意,终于进入正题的发现了人头。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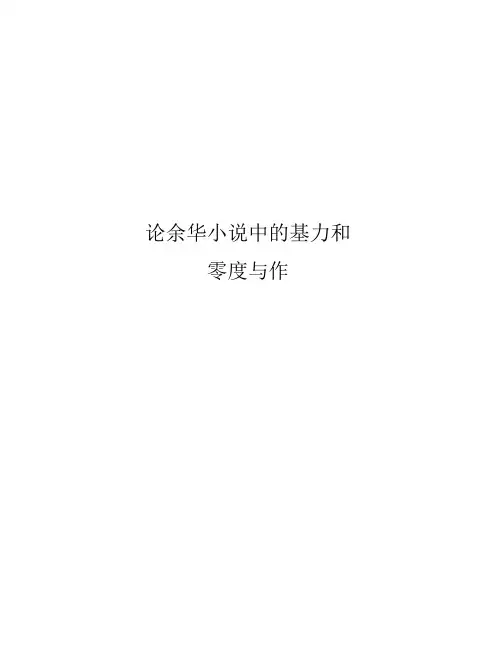
余华在创作《现实一种》时,他以零度的笔触中性客观的描述着山岗 山峰一家。鲜血横飞在这个冷漠的家庭里,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被亲人 残酷的夺走。在这个大家庭里,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最终全部走向毁灭 的命运。赵毅横先生称之为“对中国的家庭伦理的无情颠覆”。⑴难道 余华写作时就没有一幺幺情感吗,他变得麻木了吗?自然不是,余华在进 行写作时,是幣铸了丰富而恢弘的情感的。他只是把内心的情绪压在理 性的脚下。将这桩事件客观,冷静的叙述出来。他相信,最真实的才是 自己作品所追求的。他的文字是疯狂的,而是最真实的,因为这一切都 源于内心。他自称“《现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 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汹涌般涌动着,这是从丽梦出发抵达 梦魇的叙述。"⑻
前言
“零度写作”究竟有何等魅力,何以吸引众多文人在它的指导下潜心 创作?先锋小说家余华是怎样借用“零度写作”,融进自己的小说暴力 写作?解开这两个谜团,我们便知道余华小说暴力的另一侧正是“零度写作”的牵引。一起感受余华小说的暴力美学,领会“零度写作”的独 特魅力。
一、“零度写作”的起源和传播
㈠、“零度写作”的起源
colours to a them ,violent,
zero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analyzes violence, blood, death in its work in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nd reveals the "zero writing" the great charm.
生命末日的言说——余华小说“死亡叙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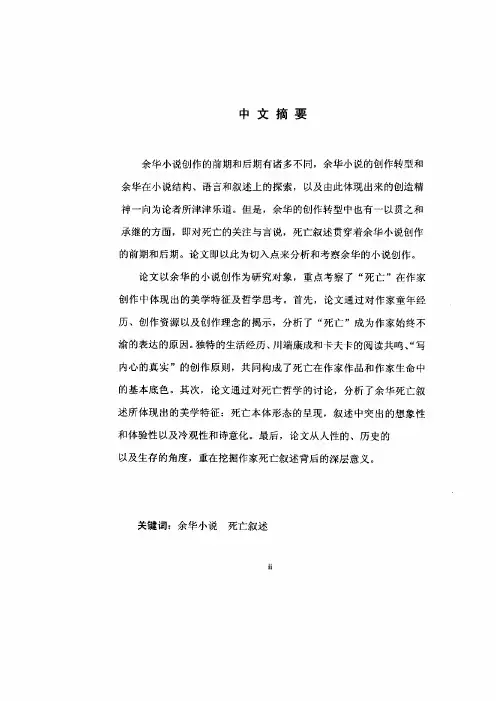
中文摘要余华小说创作的前期和后期有诸多不同,余华小说的创作转型和余华在小说结构、语言和叙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精神一向为论者所津津乐道。
但是,余华的创作转型中也有一以贯之和承继的方面,即对死亡的关注与言说,死亡叙述贯穿着余华小说创作的前期和后期。
论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和考察余华的小说创作。
论文以余华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死亡”在作家创作中体现出的美学特征及哲学思考。
首先,论文通过对作家童年经历、创作资源以及创作理念的揭示,分析了“死亡”成为作家始终不渝的表达的原因。
独特的生活经历、川端康成和卡夫号的阅读共鸣、“写内心的真实”的创作原则,共同构成了死亡在作家作品和作家生命中的基本底色。
其次,论文通过对死亡哲学的讨论,分析了余华死亡叙述所体现出的美学特征:死亡本体形态的呈现,叙述中突出的想象性和体验性以及冷观性和诗意化。
最后,论文从人性的、历史的以及生存的角度,重在挖掘作家死亡叙述背后的深层意义。
关键词:余华小说死亡叙述AbstractYuHua(1960.),theeminentnovelisttodayinChina,hasshifteddistinctlyinthenarrativestyle.Unlikeotherresearchers,whopaytheirattentiontothedifference,thepresentdissertationpurportstofocusontheperpetuatedartisticpracticeinhisnovelcreative,thatis,DeathNarrative.PaperemphasizesontheaestheticandmetaphysicalcharacterexpressedintheDeathNarrative.Chapter1summarizesthreecausesofthedeathnarrative,thatis,thespecialexperienceinhischildhood,thespecialexperimentofhispre-readingffranzKatka,theJuristnovelist,andYasunariKawabata,theJapanesegreatliteraturemaster),andthelastcausesishisto-write—the·heart—realitycreativeprinciple.ThosetangledtogethertoimpelYuHuacreatingvividly.Chapter2dealswiththeproblemofdearthinthephilosophicaestheticsphere,andanalyzestheaestheticfeatureoftheDeathNarrationinhisnovels.Thatis,thedeathnoumenalform,thesignificantimaginativestyle,andtheeminentdispassionateandpoeticexpression,Finally,inthethirdchapter,wetrytOfurtherdiscussthedeepvalueofhisdeathnarrativeinawidenhorizonofhumanity,historyandexistence.Keywords:YuHua’Snovel,DeathNarrative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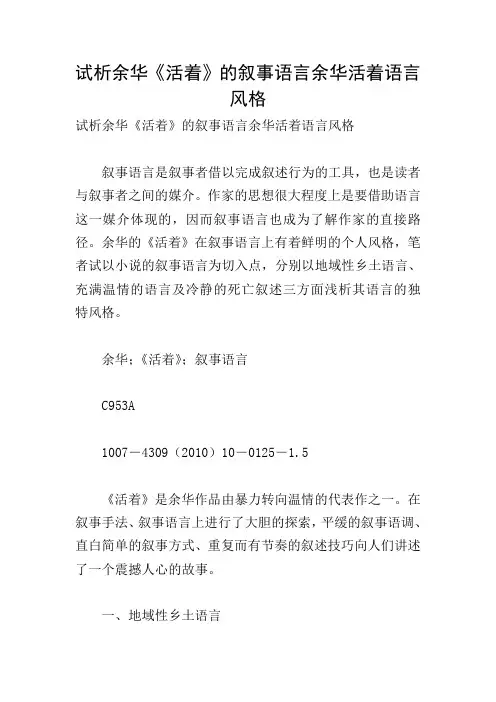
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试析余华《活着》的叙事语言余华活着语言风格叙事语言是叙事者借以完成叙述行为的工具,也是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媒介。
作家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语言这一媒介体现的,因而叙事语言也成为了解作家的直接路径。
余华的《活着》在叙事语言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笔者试以小说的叙事语言为切入点,分别以地域性乡土语言、充满温情的语言及冷静的死亡叙述三方面浅析其语言的独特风格。
余华;《活着》;叙事语言C953A1007―4309(2010)10―0125―1.5《活着》是余华作品由暴力转向温情的代表作之一。
在叙事手法、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平缓的叙事语调、直白简单的叙事方式、重复而有节奏的叙述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一、地域性乡土语言对作家而言,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别具一格的风格固然与作家独有的个人感悟、思维方式、表达技巧等内在的因素有关,同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地域等外在因素也相关。
被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评价为写出了“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余华,其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始终是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有着吴越文化的精神,有着乡土文化的特质。
《活着》所蕴含的地域性乡土语言使文本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它将江南农村生活、乡土人情等都浓缩到文本中,清晰地再现了浙江一带的乡村风貌;且小说以老人讲故事的口述形式展开,语言高度口语化的同时质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气息和浓烈的乡土韵味。
小说中的人物,从福贵的父亲到小孙子苦根都具有个性化的语言。
作家巧妙地结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社会大环境、等等,给每一人物特定的言语措辞。
透过语言的表层我们读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农民。
作为故事的讲述者福贵,作家给予他最简洁最朴素也是最粗俗的措辞。
余华说“福贵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民,而且他的一生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来完成的,让这样一个人来讲述自己,必须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写,必须时刻将叙述限制起来,所有的词语和句式都为他而生,因此我连成语都很少使用,只有那些连孩子们都愿意使用的成语,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去使用。
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
44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韩晓濛 山东行政学院摘要:在中国,余华是八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先锋派代表作家的姿态异军突起。
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最具特点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对“暴力”“死亡”的关注,这使余华在文坛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叙事方法成为当代文学中颇具争议性的文学现象之一。
余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于暴力、死亡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受与理解。
其作品打破以往的传统,将死亡的过程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表现他对死亡的认知,从而达到唤醒人性的目的。
关键词:暴力;死亡;人性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充斥着暴力、血腥、恶与死亡,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死亡气息,笼罩着让人战栗的死亡阴霾。
他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创作手法,颠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历史、常识。
在他的特定情境下,父子之间不再是“血浓于水”,夫妻之间不再是“举案齐眉”,朋友之间不再是“温情脉脉”,通过亲人、朋友间的争执与互相残杀否定了世俗所认同的纯真感情,证明冷漠与仇恨始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本文将结合余华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其多部作品中关于暴力的描写和对现实的指正分析,解读其暴力叙事的成因及对暴力叙事的情感态度与思考。
一、余华暴力叙事的个体成因(一)成长背景约瑟夫·洛斯奈曾指出 “儿童在幼年期间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影响成长后的生活方式。
”[1]也就是说一个人童年时期的行为习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转变成早期的经验在人的潜意识中被保留,成为自己独有的行为习惯,并在之后的生活中不自觉的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余华童年时期因为父母的工作而长期处在充满着血腥与死亡的医院环境中,使他经历了异于常人的恐惧、焦虑和痛苦。
这些经历在他长大后依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的创作活动,“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
当时我们家的后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
论余华小说对“死亡”的叙述
论余华小说对“死亡”的叙述摘要: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
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
Summary:Yu Hua's concern about violence as a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f the violence in Yu Hua's novel reveals the human aesthetic aesthetic behavior on the other side, then it concerns the death of human life is showing another pole. In Yu Hua's novel, the life and death as the two poles of life constitute a fate-like circle of death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life is not only the end of life, but also the sustenance of life, death and the moment the process is a focal point for the fate of life .关键词:余华;小说解读;死亡叙述;死亡意义Keywords: Yu Hua; Novels; death narrative; the meaning of death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由父亲安排他成为一名牙科医生。
但余华对医生这个职业感到很不适应,他认为当医生太严格,生活有些呆板。
论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事
Vo 1 . 3 0
第 7期
No . 7
兰州教 育 学院 学报
J OU RNAL OF L AN Z H0U I NS T I T UT E O F E DUC AT I ON
2 0 1 4年 7月
J u 1 .2 0 1 4
论余华小说 中的死 亡叙事
陈 侠
( 西南大学 , 重庆 4 0 0 7 1 5 )
[ 摘
要 ]余华是上世 纪 8 0年代 先锋 派的代表作 家, 他在创 作伊 始, 就走 了一条 与 当代作 家完全不 同的叙述路 线。风
格转 变之后 , 依 然不 同流俗 , 沉迷 于暴力、 鲜血 、 死亡等冷 色调 的意象。他笔 下的死亡叙述 蒙上 了一层宿命 和暴 力的面
一
种 高度 的概括 , 概 括成 了一 种 比较完 美 的形 式 。 ”
始 使用 一种 虚伪 的形 式 , 这种 形 式 背离 了现 状 世界 提 而余华 正是 一 个 可 以充 分 利 用 宿命 这 种超 自然 东 西
供给我 的秩序和逻辑 , 然而却 自由地接近 了真实 。 ” _ 2 J 的作 家 , 不 仅 使 死 亡 以更 加 令 人 玩 味 的形 式 出现 , 还 余华所采用 的这种“ 虚伪 的形式” 大多是 以宿命为载 借助 宿命 这 一 虚 伪 的形 式 来 趋 近作 家 表 述 的真 实— — 那就是 人 性 的趋 私趋 恶 。 体, 宿命 是 不可 理解 的 , 但 必须 是绝 对相 信 的东西 。
在 中 国的 民间意识 中 , 非 现实 的宿命 观念 是 被 当 作现 实来 看待 的。余华 偏爱 宿 命 , 他 总是 把 宿 命 与荒
二、 “ 文革 ”: 疯 狂暴 力 的死 亡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胡姗姗13011407余华所强力推崇的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
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理念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性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
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
余华对它们的执迷,从创作主体的原始动机来看,可能是他觉得这种人性状态更容易传达他对现实文明的不信任和反感,也更能够直接地展示他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
但是,随着叙事话语的自然流淌,以及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余华又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之中,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某种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
前言余华小说具有哟中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犹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
一、暴力与死亡(一)暴力从动物的本能上说,暴力无疑使人的一种攻击性本能。
攻击性或者说暴力作为人性本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或者攻击性有事一种潜力意志的体现,它渗透在政治,文化等等诸多领域。
暴力只要诉诸一个更大的叙事,诸如真理,现代化,历史进步等等,它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隐秘部位,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
因此余华的解释是,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让奴隶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场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
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的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
人类文明的更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时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
然而拳击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及时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句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
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利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胡姗姗13011407余华所强力推崇的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沉醉式表达。
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理念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性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
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
余华对它们的执迷,从创作主体的原始动机来看,可能是他觉得这种人性状态更容易传达他对现实文明的不信任和反感,也更能够直接地展示他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
但是,随着叙事话语的自然流淌,以及故事情节的自然发展,余华又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之中,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某种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
前言余华小说具有哟中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犹如身不由己地加入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
一、暴力与死亡(一)暴力从动物的本能上说,暴力无疑使人的一种攻击性本能。
攻击性或者说暴力作为人性本能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从社会伦理上说,暴力或者攻击性有事一种潜力意志的体现,它渗透在政治,文化等等诸多领域。
暴力只要诉诸一个更大的叙事,诸如真理,现代化,历史进步等等,它就可以获得合法性,因此,暴力在社会伦理的隐秘部位,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
因此余华的解释是,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让奴隶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场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
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的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
人类文明的更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行为时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的。
然而拳击取而代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及时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句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
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利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
当余华以反理性,反逻辑的手段赋予暴力合法性的同时,暴力本身也成为一种解构现实秩序的工具,而且这种解构始终披着“命运”的外衣,呈现出无法理喻的必然性特征,也使余华的叙事在广泛的欲望宣泄中成为某种话语的隐喻。
譬如在《劫数难逃》中,余华就一反常态地将暴力引入婚姻,友情与隐秘的欲望冲动之中,他以命运的一次次暗示作为叙事前进的内在动力,不断地让人物进入各种预设的暴力场景中,成为各种人性欲望的欲望的牺牲品。
像露珠对东山占有之后的冷静毁容,广佛对窥视自己与彩蝶偷情的孩子的杀戮,森林一看到女人漂亮的裤子便用刀片将之割破,沙子则对女人的辫子有着不可控制的占有欲......他们看起来是被命运推来搡去,而实质上却是欲望狂欢的结果。
余华乐于充当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幸灾乐祸观看他的人物发出一个个暴力动作,东山对露珠大打出手,沙子玩弄剪刀,千佛的残暴直至彩蝶的坠楼......这一切大小暴力行径,全无凶狠的特征,而具有艺术性优雅,正是在描述这些反常怪诞的行为时,余华的叙述创造出了一种奇怪而又陌生的绝对真实。
余华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奇异的领域,在这里,人们走向自己的墓地就像兴高采烈去参加某个假面舞会,人们生活在阴谋和危险的边缘却心安理得,甚至从容不迫。
《世事如烟》也是将叙事的内驱力建立在某种命运之中,其中算命先生作为一种权利意志的象征,不仅成功地操纵周围人群的命运,使自己的暴力意志不断地通过他人的死亡获得延伸,而且还直接以暴力手段,从一个个少女哪里获得所谓的生命精气。
无论是汽车司机,灰衣女人,等等,他们看起来都没有遭受多少直接的暴力伤害,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身体暴力形式,在他们的生命中承受得并不多,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无处不遭受着暴力的无情折磨。
《往事与刑罚》也同样如此。
余华随便挑了几个时间记忆作为一种命运的符号,便将暴力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物对接起来。
它们有刑罚专家这个权利意志的代表所设定,并明确地指向不同的暴力形式。
余华的这些小说之所以充满了某种忧郁,残忍的血腥气息,甚至洋溢着某种隐约的狂欢气息。
无论是出自于自虐,他虐,还是为了复仇,反抗,在具体的叙述方式,让施暴者,受难者,旁观者从多角度集体性地参与到叙事话语。
(二)死亡叙述无论是显性暴力还是隐性暴力,它们对生命影响的终极结果都是一样——死亡。
正是这种显性暴力和隐性暴力的多重渗透,使人物的死亡成为一种无法遏制的结局。
所以,在余华的首次先锋出击中,死亡不仅大面积地出现在故事中,而且成为暴力发生,发展乃至自行终结的一种必然性状态。
余华的人物早已蒙上宿命的阴影,他们面临危险,切近死亡却浑然不知,他们如此麻木地走向灾难确实另人惊异不已。
由于余华的故事从来没有历史性,他笔下的死亡也很少负载着某种政治,文化,历史等宏大的社会内涵,而只是欲望的产物。
呈现出大量的偶然性和随意性。
院的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的死亡都是非自然死亡。
二、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一)肉体的死亡在余华创作的小说中,对于个体正常死亡的叙述很典型,在“生在死后出现”、“没有生死间隔”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他对人生老病死的常态注入了自己的体会,加以夸张和戏谑,消解了由病到死亡的悲剧过程,在死亡过程中完成了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
在余华作品中,正常死亡常常表现为老死和病死两种形式。
余华关注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其对老死的刻意描述,表现了死的必然。
《现实一种》中老太太的死纯属自然死亡。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她“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
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死从脚趾往上爬“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
在《活着》中,福贵的爹在卖掉家产替福贵还清赌债后,“像往常那样,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向村口的粪缸走去。
”他从粪缸掉下了,“嘿嘿笑了几下,笑完后闭上了眼睛,脖子一歪,倒带顺着粪缸滑到了地上。
”这个可怜的老人在失去了他的屋子即将死亡的时刻,选择了依旧属于自己的粪缸,笑着离开了人世。
这笑中含着对不能死在自己屋子的遗憾。
他就这样带着一点点欣慰又凄凉的感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余华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死的独特思考,在他平淡的叙述中,死亡是那么“胡作非为”,对诡异的死亡意象的营造,使得我们感到了一种外在无形的隐秘力量的作用。
但在其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别样的东西,女儿难产的直接根源是“文革”医生被批斗,吃馒头给撑死了;儿子被抽死,因为县长的爱人生孩子大出血;外孙被撑死是因为太饿了,虽然死神无法预知,其中的人为的因素不能不说没有,余华实则通过对死亡的神秘书写揭示的是直面生命、直面现实的思考。
(二)精神的死亡除了直接对个体群体生命死亡的描述,余华还刻画了这样一组人,他们是活着的,但是在他们大都或疯癫或白痴,无法独立思考,在人的精神层面上讲,他们已经死亡。
这些活着的人已经没有了生存的意义,但透过他们有别于常人的视角,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本身的一些问题。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我”是个傻子,他原本有自己的名字,叫来发,但别人是按他们的想法叫他,因此这个有名的人就如同无名。
他父亲死了独自一人生活,以挑煤为生,周遭的人看他是傻子,总以取笑他为乐。
同样在生活底层的人,又把人分出阶层,最底层就成为其他人取笑的对象,这里就有了阿Q的思想,自己本身就无法自足,偏要去欺负比他更卑微的小尼姑。
而一个底层傻子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他甚至没有一个作外号的名字,靠干最苦最累的活生存,这就是这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境况,触人目,惊人心,鲁迅说人竟如虫豸,这里的傻子何尝不是如此。
小说《一九八六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曾经历文革变得有些疯癫的历史教师,他在教书期间研究过古代刑罚,尤对酷刑颇有研究,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自虐和他虐倾向,每日幻想着对他人的臆想砍杀,最后却用古代种种酷刑自戕。
在这里,虽然作为人的生命迹象还存在,但是他的精神早就崩溃,活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空壳。
出于对那段历史的绝望和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否认,他开始一种最为极端的精神境遇,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牢笼。
他把自己幻想成世界的主宰,对人类施加惩罚。
可是,这些不过是他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作为活着的人他已找寻不到任何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小说,作家通过对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的侧面展现,把人类生存的意义思考摆在读者面前,也传达出作者对社会的控诉。
余华对于精神死亡关注主要集中在傻子和疯子两类人身上,他们有呼吸有心跳,是活生生的人,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空缺的,是无序的,导致了他们的生如同“死”。
余华着力刻画这类人的精神死亡,表达了他对于活着意义的思考。
在死亡面前,活着是比死亡更有意义,但是,精神上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丧失了活着的价值。
不管是精神死亡抑或肉体死亡,只要是死亡,就意味着毁灭与衰败。
肉体的死亡是彻底结束,精神死亡又何尝不如此?傻子被人欺负,疯子渴望杀人,正常人也时常失去理性,变成了野兽,而即便平静活着的人又总是遭遇不可捉摸的意外致死,余华在对死亡意象的书写中,他写出了死的神秘莫测,通过这样的描写告知读者:死之不可测其实也是生之不可测。
死的不可预测是因为人类本身卑微,而卑微的人们又任意放任这种卑微,人类无法自救,也不愿意自救,于是就万劫不复。
三、余华创造暴力与死亡动因(一)医院里的风景余华是胆小的,伴随着胆小而来的,自然是恐惧以及对恐惧本身的高度敏感。
然而生活却偏偏为余华安排了一个充满恐惧意味的生存环境——医院。
对于没有多少人生经验的小孩来说,鲜血、疾病和死亡......这些概念的真实内涵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并不一定引发他们的恐惧。
余华的父母本身就是医生,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的生与死,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使他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环境。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
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胸前血迹斑斑。
”也许他早已习惯了医生对待生命的自然状态,使他在叙述死亡时,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平静。
(二)川端康成的启蒙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并非只是叙事上的处理,川端认为“对现实的表象和现实的界限过分轻信,就不能产生深刻的艺术”所以他认为,作家是要透过现实的表现公布,达到现实的彼岸,去窥探灵魂的深渊。
余华的叙述远离了对生命的自然尊重,对死亡的基本恐惧,给人以情感上的极度惊悚,而这就是受川端康成的对细节的精巧处理,他使余华学会了从容地描述一种场景。
余华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中——他不再轻易地屈服于日常伦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不再拘泥于对故事情节的逻辑的建构,让叙事直接进入人物的精神领域,不断地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生存境遇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以此来凸显荒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