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浅论余华作品的暴力写作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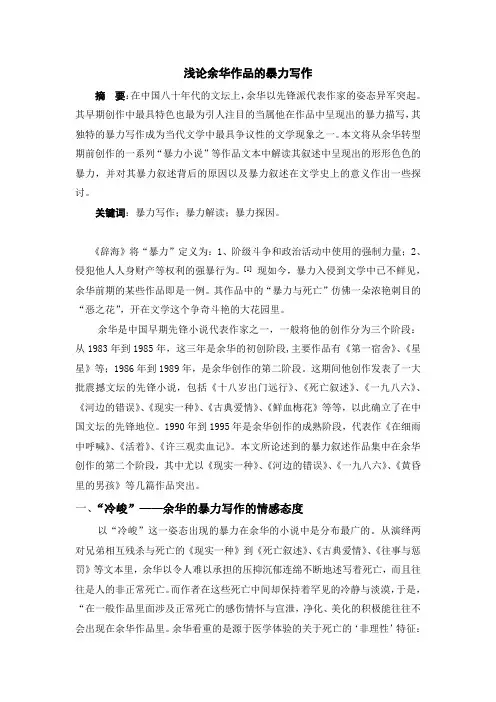
浅论余华作品的暴力写作摘要: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上,余华以先锋派代表作家的姿态异军突起。
其早期创作中最具特色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他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暴力描写,其独特的暴力写作成为当代文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文学现象之一。
本文将从余华转型期前创作的一系列“暴力小说”等作品文本中解读其叙述中呈现出的形形色色的暴力,并对其暴力叙述背后的原因以及暴力叙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作出一些探讨。
关键词:暴力写作;暴力解读;暴力探因。
《辞海》将“暴力”定义为:1、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中使用的强制力量;2、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
[1]现如今,暴力入侵到文学中已不鲜见,余华前期的某些作品即是一例。
其作品中的“暴力与死亡”仿佛一朵浓艳刺目的“恶之花”,开在文学这个争奇斗艳的大花园里。
余华是中国早期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一般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从1983年到1985年,这三年是余华的初创阶段,主要作品有《第一宿舍》、《星星》等;1986年到1989年,是余华创作的第二阶段。
这期间他创作发表了一大批震撼文坛的先锋小说,包括《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等,以此确立了在中国文坛的先锋地位。
1990年到1995年是余华创作的成熟阶段,代表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本文所论述到的暴力叙述作品集中在余华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其中尤以《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黄昏里的男孩》等几篇作品突出。
一、“冷峻”——余华的暴力写作的情感态度以“冷峻”这一姿态出现的暴力在余华的小说中是分布最广的。
从演绎两对兄弟相互残杀与死亡的《现实一种》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往事与惩罚》等文本里,余华以令人难以承担的压抑沉郁连绵不断地述写着死亡,而且往往是人的非正常死亡。
而作者在这些死亡中间却保持着罕见的冷静与淡漠,于是,“在一般作品里面涉及正常死亡的感伤情怀与宣泄,净化、美化的积极能往往不会出现在余华作品里。
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开题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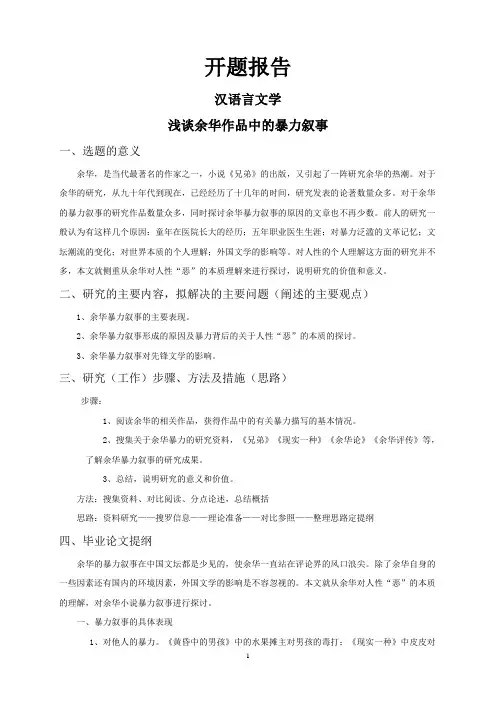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一、选题的意义余华,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小说《兄弟》的出版,又引起了一阵研究余华的热潮。
对于余华的研究,从九十年代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发表的论著数量众多。
对于余华的暴力叙事的研究作品数量众多,同时探讨余华暴力叙事的原因的文章也不再少数。
前人的研究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童年在医院长大的经历;五年职业医生生涯;对暴力泛滥的文革记忆;文坛潮流的变化;对世界本质的个人理解;外国文学的影响等。
对人性的个人理解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就侧重从余华对人性“恶”的本质理解来进行探讨,说明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观点)1、余华暴力叙事的主要表现。
2、余华暴力叙事形成的原因及暴力背后的关于人性“恶”的本质的探讨。
3、余华暴力叙事对先锋文学的影响。
三、研究(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思路)步骤:1、阅读余华的相关作品,获得作品中的有关暴力描写的基本情况。
2、搜集关于余华暴力的研究资料,《兄弟》《现实一种》《余华论》《余华评传》等,了解余华暴力叙事的研究成果。
3、总结,说明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方法:搜集资料、对比阅读、分点论述,总结概括思路:资料研究——搜罗信息——理论准备——对比参照——整理思路定提纲四、毕业论文提纲余华的暴力叙事在中国文坛都是少见的,使余华一直站在评论界的风口浪尖。
除了余华自身的一些因素还有国内的环境因素,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就从余华对人性“恶”的本质的理解,对余华小说暴力叙事进行探讨。
一、暴力叙事的具体表现1、对他人的暴力。
《黄昏中的男孩》中的水果摊主对男孩的毒打;《现实一种》中皮皮对堂弟的扇耳光后获得的快感,以及山岗和山峰两兄弟的自相残杀,以及医院中的一系列的解剖;《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反复杀人,隐含着人的暴力本能,马哲杀疯子何尝不是人的暴力本能的表现。
因此暴力是人性的一种本能,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性中的“恶”的具体表现。
从《现实一种》看余华小说的暴力叙事蕴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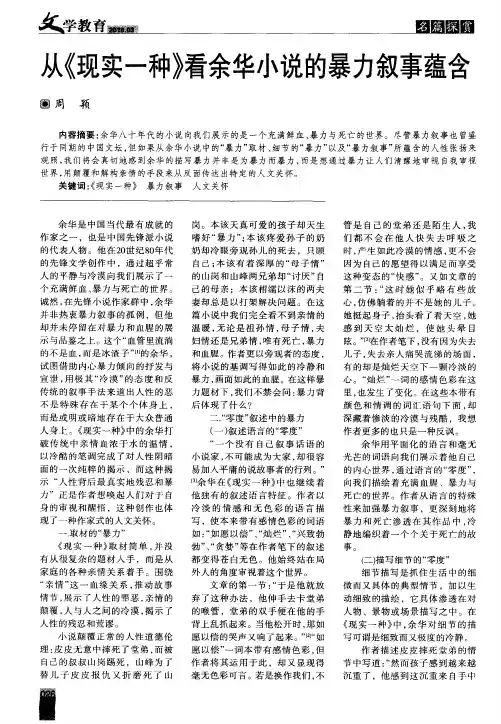
[31余 华在 《现实 一 种》中也继 续 着
他 独有 的叙 述语 言特征 。作者 以
冷 淡 的情 感 和 无 色 彩 的语 言描
写 ,使 本 来 带 有 感 情 色 彩 的 词 语
如 :“如 愿 以 偿 ”、“灿 烂 ”、“兴 致 勃
勃 ”、“贪婪 ”等在 作者笔下 的叙述
都 变 得 苍 白无 色 。 他 始 终 站 在 局
关键词 :《现实一种》 暴力叙事 人文关怀
余 华 是 中 国 当 代 最 有 成 就 的 作 家 之 一 ,也 是 中 国 先 锋 派 小 说 的代 表 人 物 。 他 在 20世 纪 80年 代 的先 锋 文 学 创 作 中 ,通 过 超 乎 常 人 的 平 静 与 冷 漠 向 我 们 展 示 了 一 个充 满鲜血 、暴力 与死亡 的世界 。 诚 然 ,在 先 锋 小 说 作 家 群 中 ,余 华 并非 热衷暴力 叙事 的孤例 ,但 他 却并未 停 留在 对暴力 和血腥 的展 示 与 品鉴 之 上 。这 个 “血 管 里 流 淌 的不 是 血 ,而 是 冰 渣 子 ”…的 余 华 , 试 图 借 助 内心 暴 力 倾 向 的抒 发 与 宣 泄 ,用 极 其 “冷 漠 ”的 态 度 和 反 传 统 的 叙 事 手 法 来 道 出 人 性 的 恶 不 是特 殊 存在 于 某个 个体 身 上 , 而 是 或 明 或 暗地 存 在 于 大 众 普 通 人身上 。《现实~种 》中的余华 打 破 传 统 中 亲 情 血 浓 于 水 的 温 情 , 以 冷 酷 的 笔 调 完 成 了对 人 性 阴 暗 面 的 一 次 纯 粹 的 揭 示 ,而 这 种 揭 示 “人 性 背 后 最 真 实 地 残 忍 和 暴 力 ”正 是 作 者 想 唤 起 人 们 对 于 自 身的 审视 和醒 悟 ,这种 创作也 体 现 了 一 种 作 家 式 的人 文关 怀 。
浅论余华《兄弟》的暴力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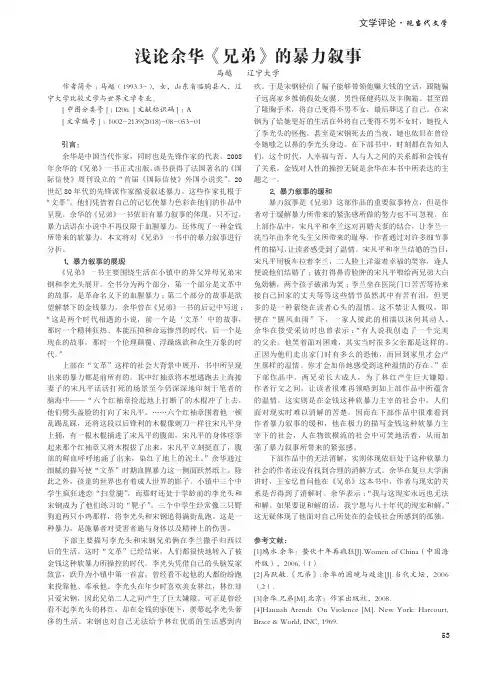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浅论余华《兄弟》的暴力叙事马越 辽宁大学作者简介:马越(1993.3-),女,山东省临朐县人,辽宁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8-053-01引言:余华是中国当代作家,同时也是先锋作家的代表。
2008年余华的《兄弟》一书正式出版,该书获得了法国著名的《国际信使》周刊设立的“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
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酷爱叙述暴力。
这些作家扎根于“文革”,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记忆使暴力色彩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
余华的《兄弟》一书依旧有暴力叙事的体现。
只不过,暴力话语在小说中不再仅限于血腥暴力,还体现了一种金钱所带来的软暴力。
本文将对《兄弟》一书中的暴力叙事进行分析。
1、暴力叙事的展现《兄弟》一书主要围绕生活在小镇中的异父异母兄弟宋钢和李光头展开。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文革中的故事,是革命名义下的血腥暴力;第二个部分的故事是欲望解禁下的金钱暴力。
余华曾在《兄弟》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两个时代相遇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时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时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上部在“文革”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展开,书中所呈现出来的暴力都是前所有的。
其中红袖章将本想逃跑去上海接妻子的宋凡平活活打死的场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刻于笔者的脑海中——“六个红袖章捡起地上打断了的木棍冲了上去,他们劈头盖脸的打向了宋凡平。
……六个红袖章围着他一顿乱踢乱踩,还将这段以后锋利的木棍像刺刀一样往宋凡平身上捅,有一根木棍捅进了宋凡平的腹部,宋凡平的身体痉挛起来那个红袖章又将木棍拔了出来,宋凡平立刻挺直了,腹部的鲜血呼呼地涌了出来,染红了地上的泥土。
”余华通过细腻的描写使“文革”时期血腥暴力这一侧面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孩童的世界也有着成人世界的影子。
余华小说作品中的暴力元素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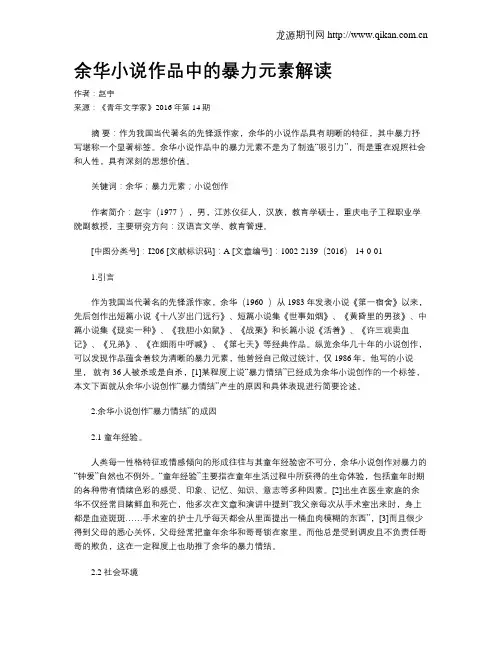
余华小说作品中的暴力元素解读作者:赵宇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14期摘要: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小说作品具有明晰的特征,其中暴力抒写堪称一个显著标签。
余华小说作品中的暴力元素不是为了制造“吸引力”,而是重在观照社会和人性,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余华;暴力元素;小说创作作者简介:赵宇(1977-),男,江苏仪征人,汉族,教育学硕士,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1.引言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先锋派作家,余华(1960- )从1983年发表小说《第一宿舍》以来,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我胆小如鼠》、《战栗》和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等经典作品。
纵览余华几十年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作品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暴力元素,他曾经自己做过统计,仅1986年,他写的小说里,就有36人被杀或是自杀,[1]某程度上说“暴力情结”已经成为余华小说创作的一个标签,本文下面就从余华小说创作“暴力情结”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进行简要论述。
2.余华小说创作“暴力情结”的成因2.1 童年经验。
人类每一性格特征或情感倾向的形成往往与其童年经验密不可分,余华小说创作对暴力的“钟爱”自然也不例外。
“童年经验”主要指在童年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
[2]出生在医生家庭的余华不仅经常目睹鲜血和死亡,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到“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手术室的护士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3]而且很少得到父母的悉心关怀,父母经常把童年余华和哥哥锁在家里,而他总是受到调皮且不负责任哥哥的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余华的暴力情结。
论余华作品中的暴力与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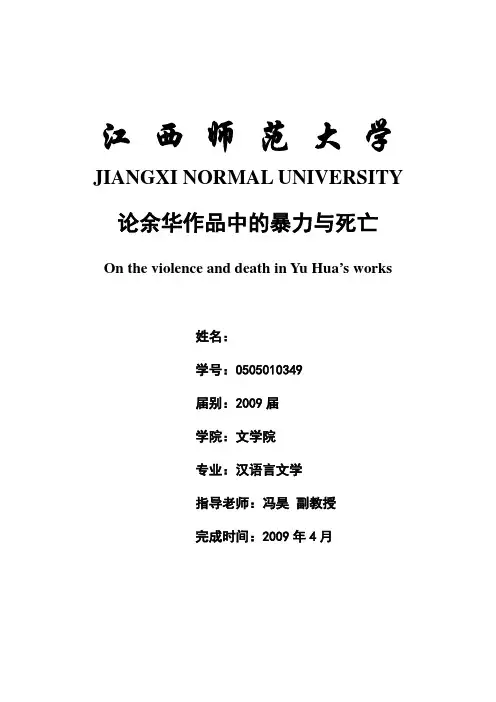
江西师范大学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论余华作品中的暴力与死亡On the violence and death in Yu Hua’s works姓名:学号:0505010349届别:2009届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指导老师:冯昊副教授完成时间:2009年4月目录中文摘要 (Ⅰ)英文摘要 (Ⅱ)引言 (1)一、生活积累与阅读积累 (2)(一)生活积累 (2)(二)阅读积累 (4)二、余华作品中的暴力 (5)(一)暴力源自现实之恶 (5)(二)以暴力反映人性之恶 (6)三、余华作品中的死亡 (8)(一)死亡的外表 (9)(二)对死亡的思考 (10)(三)对传统的颠覆和回归 (11)(四)死亡叙述中的人文关怀 (13)结语 (15)参考文献 (16)致谢 (17)论余华作品中的暴力与死亡摘要: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余华在其作品中对暴力和死亡的描写是其作品的突出特色,谋杀、死亡是他小说中的常见主题。
余华早年经历使其对暴力与死亡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艺思潮涌入中国。
在这双重影响下,余华开拓了创作手法,走上了全新的创作道路。
余华支持“性恶论”。
他以暴力反映现实和人性之恶。
余华打破传统,他善于将死亡过程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在多种死亡外表之下反映其对死亡的思考,达到唤醒人性的目的。
在余华后期的作品中,也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叙述中含有温情的一面。
这一时期的作品叙述语言趋于平和,人性善重新回到小说主题中来。
余华前期作品的“零度叙述”和后期的“温情叙述”都体现了人文关怀。
余华始终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以平静的心态去叙述真实的生活,在当代文坛独领风骚。
关键词:余华;暴力;死亡;人文关怀On the violence and death in Yu Hua’s worksAbstract:Yu Hua is one of “the cutting edge literatures”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1980s.His works’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is the describe of the violence and the death. In his novels, the common subject is the murder and death.Yu Hua's early experience made him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from ordinary people about violence and death.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western artistic ideas rushed into China. In this double influence, Yu Hua has opened up a creative way and embarks on a new creative path. Yu Hua supports the "theory of evil human nature." He reflects evil of reality and human nature. Yu Hua has broken up the tradition and shown the process of death perfectly, under varieties appearances of death also reflected his thinking on death,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wakening humanity.Yu Hua's late works, also have a tendency to return to the tradition, narrative contained in the side of warmth. The describing language of this period of works tends to be calm and returns to the subject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The early works of Yu Hua's "zero narrative", and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armth described" all embody the humanistic care. Yu Hua h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he described a calm attitude to real life,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cene.Key words: Yu Hua;Violence;Death;Humanities concern引言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盐人。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余华在创作《现实一种》时,他以零度的笔触中性客观的描述着山岗 山峰一家。鲜血横飞在这个冷漠的家庭里,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被亲人 残酷的夺走。在这个大家庭里,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最终全部走向毁灭 的命运。赵毅横先生称之为“对中国的家庭伦理的无情颠覆”。⑴难道 余华写作时就没有一幺幺情感吗,他变得麻木了吗?自然不是,余华在进 行写作时,是幣铸了丰富而恢弘的情感的。他只是把内心的情绪压在理 性的脚下。将这桩事件客观,冷静的叙述出来。他相信,最真实的才是 自己作品所追求的。他的文字是疯狂的,而是最真实的,因为这一切都 源于内心。他自称“《现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 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汹涌般涌动着,这是从丽梦出发抵达 梦魇的叙述。"⑻
前言
“零度写作”究竟有何等魅力,何以吸引众多文人在它的指导下潜心 创作?先锋小说家余华是怎样借用“零度写作”,融进自己的小说暴力 写作?解开这两个谜团,我们便知道余华小说暴力的另一侧正是“零度写作”的牵引。一起感受余华小说的暴力美学,领会“零度写作”的独 特魅力。
一、“零度写作”的起源和传播
㈠、“零度写作”的起源
colours to a them ,violent,
zero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analyzes violence, blood, death in its work in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nd reveals the "zero writing" the great charm.
论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
论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界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死亡与暴力为主题,铸就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他的小说中,死亡与暴力作为关键元素,常常掀起人们思考生命的深刻哲学反思。
本文将通过分析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探讨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意义。
一、余华小说中的死亡表达了生命的真谛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不是为了衬托生命的价值而存在的,而是将死亡置于生命存在的必然性中,从而表达了生命的真谛。
例如,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无数磨难,虽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他始终坚持着活下去。
在生命的边缘,他看到了生命的可贵,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福贵的生命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而是在生存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生命的价值,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小说中,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是重生和自我认识的开端。
二、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余华小说中的暴力经常表现为人类对于生命的残忍和贪婪,暴力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
例如,在小说《兄弟》中,主人公与他的兄长相爱相杀,残杀无辜的人,突显出人性的残忍和狠毒。
在小说中,暴力表现出作为人的双重性,即具有善良和恶行两面性的现象,深刻揭示了人性的种种弱点和缺陷。
三、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呼唤着人的关注和反思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呼唤着人们对于生命和人性的关注和反思。
只有从对死亡和暴力中发现的人性问题出发,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
这使得读者深思,不仅仅仅是故事本身的安排,更是人们在接受和反思小说时,内心深处的探求和反思。
因此,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和暴力并非简单的文学创作,而是呈现人性矛盾,探索人类普世话题的一种方式。
综上所述,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不仅仅只是小说内容,更是文学作品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
余华作品中对于生命与死亡、人性与道德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度和厚度。
它们正是从小说中的暴力和死亡中提炼出人性探题和人类社会的内涵,从而引领了人们对于生命和人性的关注和反思。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事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事作者:吴喆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04期摘要:文章以余华小说《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中的暴力叙事为例,分析其作品中暴力叙事的展现形式——鲜血和死亡,进而探究其热衷于暴力叙事的种种原因,诸如童年经历、牙医经历、西方死亡叙述的影响等。
余华小说以现实和历史为其暴力叙事的对象,用一种极端的手法——死亡来引起我们对人类现有的生存状态的高度反思和警醒。
关键词:余华;小说;暴力叙事余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震惊文坛,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贯穿其作品中的“暴力”叙事,从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就有了“暴力”叙事的苗头,到后来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一九八六年》等作品中更是充斥着“暴力”叙事。
一、余华“暴力”叙事的现象分析在余华众多“暴力”叙事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鲜血和死亡的意象。
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他应该是一个最热衷于描写死亡的作家。
“仅1986年,他写的小说里,就有36人被杀或自杀。
”①而小说《现实一种》更是将死亡展现到了极致,可以说是暴力和死亡的连锁反应。
故事开始于四岁的皮皮无意中摔死了自己的堂弟,结果被叔叔山峰惩罚,先是舔堂弟留在地上的血迹,后又被山峰活活踢死。
山岗为了给儿子皮皮报仇,在其无意识的情况下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将山峰折磨至死。
而山岗则被执行枪决,但山峰的妻子仍不解气,假借山岗妻子的身份将其尸体捐给国家,于是山岗的尸首被一群形形色色的医生给肢解瓜分了。
这一连串的死亡和被死亡中,无不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甚至恶心的血腥、冷酷的气息,暴力场面更是比比皆是,如山峰踢死皮皮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
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
”②而最后医生肢解山岗尸体的情景更是让人发指:“她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上凹一刀切进去,然后往下一直切到腹下。
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
44浅谈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叙事韩晓濛 山东行政学院摘要:在中国,余华是八十年代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先锋派代表作家的姿态异军突起。
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最具特点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其对“暴力”“死亡”的关注,这使余华在文坛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叙事方法成为当代文学中颇具争议性的文学现象之一。
余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于暴力、死亡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受与理解。
其作品打破以往的传统,将死亡的过程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表现他对死亡的认知,从而达到唤醒人性的目的。
关键词:暴力;死亡;人性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充斥着暴力、血腥、恶与死亡,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死亡气息,笼罩着让人战栗的死亡阴霾。
他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创作手法,颠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历史、常识。
在他的特定情境下,父子之间不再是“血浓于水”,夫妻之间不再是“举案齐眉”,朋友之间不再是“温情脉脉”,通过亲人、朋友间的争执与互相残杀否定了世俗所认同的纯真感情,证明冷漠与仇恨始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本文将结合余华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其多部作品中关于暴力的描写和对现实的指正分析,解读其暴力叙事的成因及对暴力叙事的情感态度与思考。
一、余华暴力叙事的个体成因(一)成长背景约瑟夫·洛斯奈曾指出 “儿童在幼年期间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影响成长后的生活方式。
”[1]也就是说一个人童年时期的行为习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转变成早期的经验在人的潜意识中被保留,成为自己独有的行为习惯,并在之后的生活中不自觉的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余华童年时期因为父母的工作而长期处在充满着血腥与死亡的医院环境中,使他经历了异于常人的恐惧、焦虑和痛苦。
这些经历在他长大后依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的创作活动,“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
当时我们家的后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
这种倾向与他的童年记忆、阅读经验以及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有关。
对暴力的残酷书写决非余华内心的真正向往,实是作者采取极端和隐喻的方式对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和对人生苦难的痛切关注。
关键词:余华;鲜血;暴力;死亡;人文关怀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余华通过冷漠残酷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死亡的世界。
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小说的潜在主题依然与暴力有关。
这种极端而强硬的叙述方式其实隐喻了作者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
令许多读者关注的是,余华为什么这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书写?或许,只有解开了这个谜底,余华精神世界的最后一道大门才会向我们真正敞开。
<一>余华对鲜血的钟情由来已久。
在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血莫不与道义、气节联系在一起,而余华笔下的血已无关宏旨。
“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名作里,余华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鲜红的血液稀释成了“眼泪”,第一次向读者显示了他冷酷的一面。
而在那篇以《鲜血梅花》(1989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命名的小说里,他就兴趣盎然地玩味道:“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
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
”到了《死亡叙述》,余华则是这样描述鲜血的:“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的洗脚水似的。
”而“我”却以欣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地面留下的印痕,毫无痛惜之感。
余华曾经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①[P162]对暴力的迷恋,使余华在描写鲜血时,禁不住会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欣赏的眼光来打量,甚至以华丽的语言来不厌其烦地精描细写。
如在《一九八六》里,余华这样写道:“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
”在这里,鲜血四溢的视觉冲击,给人的不再是惊心动魄的畏惧,而是豪奢的感官盛宴。
与此同时,余华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结也愈来愈清晰地展现给了读者。
“暴力”也是贯穿和理解余华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词语。
早期如《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希望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转寓“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
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但它们的潜在主题其实依然与暴力有关。
以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为例,尤其能够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
这篇小说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
暴力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
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可是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暴力来获取快乐——“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
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了一个耳光。
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
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儿,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
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
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来,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接着,皮皮抱着堂弟到屋外去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感到轻松自在”。
就这样,暴力的旋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
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旋涡中。
成人世界的暴力一旦展开,可绝不像孩童世界那样是非理性的,它是有计划、有安排、有目标的,它要求每一个人都用暴力来还击暴力,否则你就无法继续获得做人的尊严。
比如,山岗开始时对自己儿子的死有点漠然,但他立刻受到了妻子的谴责:“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这个世界似乎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对暴力坐视不管,他必须反击,可是,除了暴力本身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制止和惩罚暴力呢?于是,报复性的暴力活动就在山岗和山峰一家展开了,它像一阵暴风,将每一个人的内心启动,似乎就无法停下来了,直到把所有人都席卷了进来。
结果,每个人都具有了双重角色: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而暴力作为一种力量,一旦在人的内心启动,似乎就无法停下来了,直到把所有人都带进毁灭之中。
这也说明,暴力不是一种外在的手段,它其实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一有机会,它就会奔泻而出,甚至最终主宰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
作为暴力的一种极端方式和结果,余华的小说几乎都涉及到了屠杀和死亡。
如《一九八六》里的疯子自戕,《古典爱情》里的吃人场面,死亡简直与人同在,如影随形。
即使在题为《活着》的小说里,余华也多次写到死亡:福贵的儿子有庆为救活县长太太抽血过多而死;哑女凤霞因难产流血过多而死;媳妇家珍因丧女、贫困与疾病而死;偏头女婿二喜因意外被砸死;外孙苦根因饥饿饱食被撑死;以及战友老全,冤家龙二,县长(亦为战友)春生先后以不同的方式死去,故事主人公福贵则在尘世以送别的姿态默默地活着。
在目睹和耳闻的死之中,活着竟变得悲壮起来。
仿佛正因为此,活着才显得难能可贵,“似乎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成了唯一的目的和理由”。
②[P293]然而,令许多人关注和好奇的是,余华何以在内心积淀如此深厚的暴力情结呢?<二>对于这样的疑问,余华曾经声称“这是作家的难言之隐”,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不过他却提出反问:“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死亡和暴力”呢?尽管如此,我们从余华的《现实一种》(1997年意大利版)的前言里,仍然不难发现,余华对鲜血和死亡的迷恋,其实与他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
他在这篇序言里写道:“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
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
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
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
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
”③[P232]余华在序言里还提到,童年时他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常常在炎热的夏天独自一人跑进里面乘凉。
那时的余华几乎听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哭声,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
时间长了,面对亡者亲属的哭声,他渐渐失去了常人所有的恐惧与震撼,以至于竟然“觉得那已经不是哭泣了,它们是那么的漫长持久,那么的感动人心,哭声里充满了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
”④[P233]此外,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余华被动地接受了当时的语言暴力,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可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血腥场面,从而造成了他童年生活中的信任破灭。
这就使余华产生了一种认识,即惟一能够确证自身存在、力所能及并能带来快感的东西,便是暴力。
当然,童年经历和儿时记忆决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的全部原因。
余华的创作风格之所以迥异于其他作家,还与他的阅读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余华在谈到写作过程中对材料处理的感觉时曾经坦言:这样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阅读的体验。
余华还说,他主要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
在这些外国作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在中国作家中,则只有鲁迅一人。
“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
”川端康成曾经这样描写一个母亲凝视死去的女儿时的感受。
正是“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
”后来,“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
”“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⑤[P146-147]我们可以发现,是川端康成教会了余华如何写作,卡夫卡则给了他想象和勇气,使他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扭曲的变形的原始的罪恶)有了特殊的敏感。
此外,陀斯妥耶夫斯基暴力叙述的慢镜头特写和鲁迅的冷峻笔法则使余华在进入血腥的暴力世界时,能够不动声色游刃有余。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能完全脱离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
余华的极端叙事方法也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有着必然的联系。
尽管当时的中国文坛已相继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系列创作潮流,然而文学自身的革命仍然无动于衷。
到了80年代中叶,先锋文学实验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马原、莫言、残雪等作家的先锋创作一开始就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
这些作品“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
⑥[P291]在当时诸多的文学思潮中,中国作家对人的关注,还多是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则几乎是一个空洞。
而人文领域里人道主义关怀的泛滥,却已渐渐沦落成为一种假惺惺的虚拟口号。
正是在这个时候,余华脱颖而出,他继承发展了先锋派作家残雪等人对“人的存在”的探索,作品很快引起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因为余华一出场就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真实的书写,而是采用极端残酷的书写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以彻底改写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构。
余华渴望冲破日常经验的藩篱,以更自由的形式去接近真实。
但他指的是想象中的真实。
“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他的精神。
”“当我不再相信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⑦[P46]所以,我们在余华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常态的现实生活,一切都是非常态的。
《现实一种》里的家庭杀戮,《鲜血梅花》里的江湖恩怨、《一九八六》里沉浸于暴力幻想的疯子,《世事如烟》里飘忽的人物关系和无常的宿命等等,处处都显示出一种与现实极度紧张的关系。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早期的先锋实验,还是90年代转型后的创作,余华一直紧紧握住的都是人和人性的基本母题。
他握住的其实是文学中恒常的部分,而不是像一些作家,在语言和形式革命上用力过猛,以致最终在思想上却显得空洞而贫乏,徒剩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
《三》由此可见,理解余华小说中的人文立场,是进入他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
在荒诞的故事背后,我们却发现了感人的真实。
余华的创作其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的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
正如他所说,极端的暴力书写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它隐喻着他所发现的“另一部分的真实”——从古老的奴隶角斗,到现在的拳击甚至南方人的斗蟋蟀,余华都从中看到了“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意识到“暴力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事实上,早期的先锋作品里,余华眼中的人大多都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