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读书笔记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读书笔记《丰乳肥臀》是一部讲述上官家从建立到走向灭亡的曲折过程的历史性小说。
故事从抗日战争一直持续到中国改革开放。
下面XX给大家带来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读书笔记1莫言的这本书是标题党的最佳代表,“丰乳肥臀”让人联想到野性女人在花花世界中的无羁生活。
而“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寄语,使得读者建立了“丰乳肥臀”与“母爱”的联系。
看完整本书,除了魔幻现实主义带给你的震感外,更多的是被母爱的崇高与伟大动容。
从抗战前夕到解放以后的时间跨度内,母亲上官鲁氏生养了九个儿女,四个孙辈,历经日本屠杀、自然灾害、炮火硝烟、文化革命种种磨难,用自己的乳汁滋养儿孙、以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
丰乳肥臀——悲苦的命运“母亲”有着与旧社会审美标准相匹配的小脚,有着女人生育能力象征的“丰乳肥臀”,但却演绎着旧社会妇女的悲苦命运。
下嫁不能生育的上官寿喜迫使母亲向多位男人借种生子来延续上官家血脉,最终与牧师的爱情结出了上官后代中唯一的男人——上官金童。
八个女儿继承了母亲的丰乳肥臀体态特征,来弟、招弟、领弟、盼弟、想弟、念弟、求弟和玉女各个命运多舛,生之悲苦——死了、疯了、卖了,没有你想不到的苦,只有你无法体验的悲。
这种悲是旧社会女人的写照,是对中国社会人性丑恶的揭露。
即使拥有丰乳肥臀,女人充其量也只是生产的工具,生产力越高所受的剥削也就越深,女人的价值也仅仅体现为生男生女。
丰乳肥臀作为底层劳动人民延续血脉的工具,数千年的生产着悲苦的女人。
丰乳肥臀——生命的抗争每读到一个女儿的命运就不禁感叹上官家女儿的不屈精神,抗争力量。
母亲的被借种、被__、被暴打也不向生命低头,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悲情戏码,也没有孤单流泪、自怨自艾的怜悯情怀。
生活永远坦坦荡荡,即使身体遭受无尽践踏,灵魂也始终保持纯净。
上官家的八个女儿同样延续了母亲的坚毅性格,不管成仙、成妖还是卖身卖命,都无怨无悔,热情荡漾。
浅谈莫言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的特征及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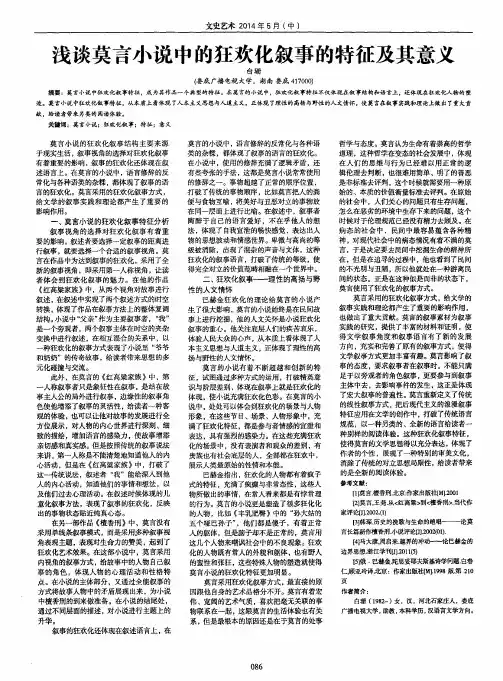
莫言小说 的狂 欢化叙 事特 征 分析 叙 事视 角的选 择对狂 欢化 叙事有 着重 要的影 响, 叙述者要选择一定叙事的距离进 行叙事 , 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叙事 视角。莫 言在作 品中为达到叙事的狂欢化 , 采用 了全 新 的叙事视角 ,即采用第一人称视角 , 让读 者体会 到狂欢化 叙事 的魅力 。在他 的作 品 《 红高粱家族 》中 , 从两个视角对故 事进行 叙述 , 在叙述 中实现了两个叙述方式的时空 转换 , 体现了作 品在叙事方法上的整体复调 结构。 小 说中 “ 父亲 ” 作为主要叙事者 ,“ 我” 是一个旁观者 , 两个叙事主体在时空的夹杂 变换中进行叙述 ,在相互混合 的关 系中,以 种狂欢化的叙事方式表现了小说 里 “ 爷爷 和奶奶”的传奇故事 ,给读者带来思想的多 元化碰撞与交 流。 此外 , 在莫言 的 《 红高粱家族 》中,第 人称叙事者只是象征性在叙事 , 是站在故 事主人公的局外进行叙事 , 边缘性的叙事角 色使他增添了叙事 的灵活性 , 给读者一种客 观 的体验 , 也可以让他对故事 的发展进行全 方位展示 , 对人物 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刻 、 细 致的描绘 ,增加语言 的感染力 , 使故事增添 亲切感 和真实感 。 但是按照传统的叙 事说 法 来讲 , 第一人称是不能清楚地知道他人的内 心活动 ,但是在 《 红 高粱家族 》中 , 打破 了 这一传统说法 , 叙述者 “ 我”能给深入到他 人的内心活动 ,知道他们 的事情和想法 ,以 及他们过去心理活动 。 在叙述时候体现的儿 童化叙事方法,表现了叙事 的狂欢化 ,反映 出的事物状态贴近纯真心态 。 在另一部作 品 《 檀香刑 》中,莫言没有 采用单线条叙 事模式 , 而是采用多种叙事视 角表现主题 , 表现对生命 力的赞美 , 起到 了 狂欢化艺术效果。在这部小说中 , 莫言采用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

一、多视角叙述
莫言的小说常常采用多视角叙述的方式,这种叙事方式使故事具有更强的立体 感和真实感。例如,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开始,描述 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所见所闻,然后转向第三人称视角,深入描绘了各 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这种多视角叙述方式,让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故事,增强了故事的复 杂性和深度。
谢谢观看
综上所述,莫言小说的结构艺术是其作品独特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他通过复 杂多层次的时间结构、交错穿插的叙事结构、魔幻与现实交织的超现实主义结 构和地方色彩浓郁的地域文化结构等手法,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和表现方式,
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了不同的文学魅力。这些结构艺术不仅丰富了小说 的内容,也使得他的作品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
二、交错穿插的叙事结构
莫言小说的叙事结构往往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多角度、多视点、多 层次的叙述方式,让读者在不断变换的视角中体验故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檀香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以一个刽子手的角度展开叙述,但 同时又通过对话、回
忆录等文学手法,将不同的叙事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交错的叙事 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强的真实感和更丰富的表现力。
莫言的小说常常融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现实的 神秘感和超自然的惊奇感。例如在《红树林》中,莫言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奇 幻的故事情节相结合,创造了一个魔幻的世界。这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不仅 丰富了故事的内容
和形式,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五、深刻的社会批判
莫言的小说深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对封建礼教、权力斗争、贫困 落后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例如在《蛙》中,莫言通过一个乡村医生的视 角,揭示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和不合理性。这些社会批判不仅反映了社会的 真实面貌,也提高了读者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莫言笔下的刑罚场景——以长篇小说《檀香刑》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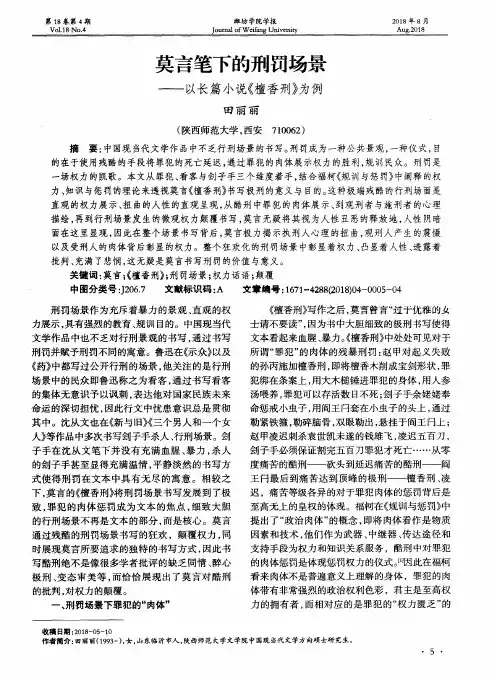
刑罚场景作为充斥着暴力 的景观 、直观的权 力展示 ,具有强烈 的教育 、规训 目的。中国现 当代 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行刑景观 的书写 ,通过书写 刑罚并赋予刑罚不同的寓意。鲁迅在《示众》以及 《药》中都写过公开行刑的场景 ,他关注 的是行刑 场景中的民众即鲁迅称之为看客 ,通过书写看 客 的集体无意识予以讽刺 ,表达他对 国家 民族未来 命运的深切担忧 ,因此行文 中忧患意识总是 贯彻 其 中。沈从文也在《新与 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等作 品中多次书写刽子手杀人 、行刑场景。刽 子手在沈从文 笔下并没有充满 血腥 、暴力 ,杀 人 的刽子手甚至显得充满温情 ,平静淡然 的书写方 式使得刑罚在 文本 中具有无 尽的寓意 。相较 之 下 ,莫言 的《檀香刑》将刑罚场景书写发展到 了极 致 ,罪犯 的肉体惩罚成 为文本 的焦点 ,细致 大胆 的行刑场景不再是文本 的部分 ,而是核心 。莫言 通过残酷的刑罚场景书写的狂欢 ,颠覆权力 ,同 时展现莫言所要追求 的独特的书写方式 ,因此书 写酷刑绝不是像很 多学者批评 的缺乏 同情 、醉心 极刑 、变态 审美 等 ,而恰恰展现 出了莫 言对酷刑 的批 判 ,对 权 力 的颠覆 。
收稿 日期:2018—05-10 作者简 介:田丽丽(1993一),女 ,山东临沂市人 ,陕西师 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 当代文 学方 向硕士研 究生。
· 5 ·
潍坊学院学报
2018年 8月
象征 ,因此公开行刑下 ,对罪犯 肉体的残暴方式所 要 展现 的不 是法 律 的不 可遏 制 而是 皇权 的至 高无 上 。公开处决是一种司法——政治功能 ,它是重 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 的仪式。用最能够展现君 权 壮观 时 的情 景来恢 复 君权 ,是权 力失 而 复得 的 仪 式 ,通 过使 用 占有优 势 的皇 权对 罪犯 的 肉体 进 行残酷的摧毁 ,公开处决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 权力 ,其残忍性 、展示性 、暴力性 、力量悬殊 的演 示 、精细的仪式处处彰显着权力 。 从福柯理解的 角度 ,就可以窥探公开行刑之下为何对罪犯 的肉 体穷追不舍 。《檀香刑》中 ,太监小虫子偷盗皇上 的七星鸟枪 ,咸丰让刑部想 出一种奇特 的刑罚来 整治小虫子 ,从 阎王闩刑罚 的是否使用 ,到其制作 的过程 ,再到其真正的实践过程中都要接受皇上 的命令 ,在执刑过程 中,小虫子 的皇上饶命 、请皇 上 开 恩 的乞求 声彰 显 着 皇权 的至 上 。在执 刑结 束 后 ,皇上 的一句“你们都看 到了吧 ,这就是你们的 榜 样 ”,让 众 臣不 由磕 头谢 罪 。正 因为 罪犯 的 肉体 惩罚体现着皇权 ,因此权力为 了彰显 自身怎能放 过罪犯 的肉体?
最新-莫言檀香刑 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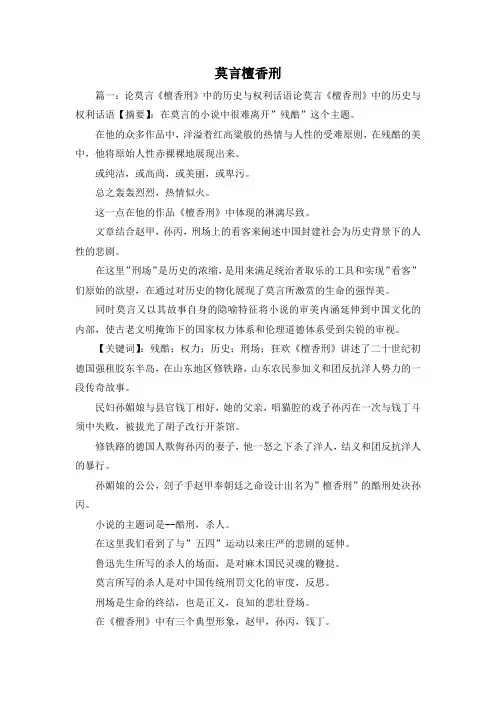
莫言檀香刑
篇一:论莫言《檀香刑》中的历史与权利话语论莫言《檀香刑》中的历史与权利话语【摘要】:在莫言的小说中很难离开”残酷”这个主题。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洋溢着红高粱般的热情与人性的受难原则,在残酷的美中,他将原始人性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或纯洁,或高尚,或美丽,或卑污。
总之轰轰烈烈,热情似火。
这一点在他的作品《檀香刑》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结合赵甲,孙丙,刑场上的看客来阐述中国封建社会为历史背景下的人性的悲剧。
在这里”刑场”是历史的浓缩,是用来满足统治者取乐的工具和实现”看客”们原始的欲望,在通过对历史的物化展现了莫言所激赏的生命的强悍美。
同时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征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文化的内部,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受到尖锐的审视。
【关键词】:残酷;权力;历史;刑场;狂欢《檀香刑》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强租胶东半岛,在山东地区修铁路,山东农民参加义和团反抗洋人势力的一段传奇故事。
民妇孙媚娘与县官钱丁相好,她的父亲,唱猫腔的戏子孙丙在一次与钱丁斗须中失败,被拔光了胡子改行开茶馆。
修铁路的德国人欺侮孙丙的妻子,他一怒之下杀了洋人,结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行。
孙媚娘的公公,刽子手赵甲奉朝廷之命设计出名为”檀香刑”的酷刑处决孙丙。
小说的主题词是--酷刑,杀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五四”运动以来庄严的悲剧的延伸。
鲁迅先生所写的杀人的场面,是对麻木国民灵魂的鞭挞。
莫言所写的杀人是对中国传统刑罚文化的审度,反思。
刑场是生命的终结,也是正义,良知的悲壮登场。
在《檀香刑》中有三个典型形象,赵甲,孙丙,钱丁。
莫言檀香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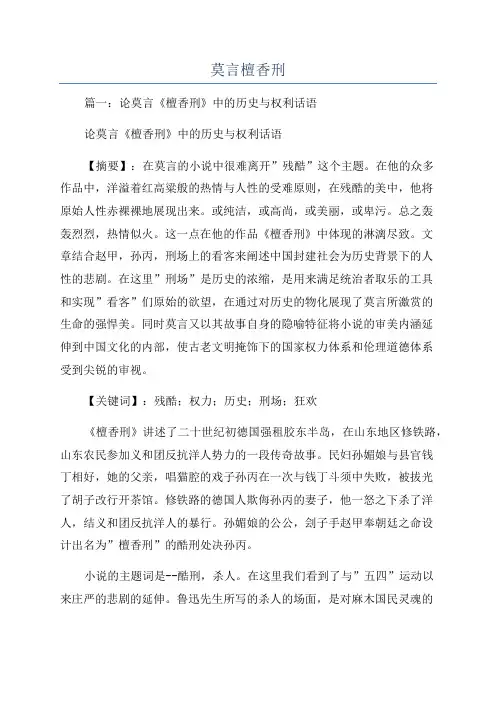
莫言檀香刑篇一:论莫言《檀香刑》中的历史与权利话语论莫言《檀香刑》中的历史与权利话语【摘要】:在莫言的小说中很难离开”残酷”这个主题。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洋溢着红高粱般的热情与人性的受难原则,在残酷的美中,他将原始人性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或纯洁,或高尚,或美丽,或卑污。
总之轰轰烈烈,热情似火。
这一点在他的作品《檀香刑》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结合赵甲,孙丙,刑场上的看客来阐述中国封建社会为历史背景下的人性的悲剧。
在这里”刑场”是历史的浓缩,是用来满足统治者取乐的工具和实现”看客”们原始的欲望,在通过对历史的物化展现了莫言所激赏的生命的强悍美。
同时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隐喻特征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文化的内部,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受到尖锐的审视。
【关键词】:残酷;权力;历史;刑场;狂欢《檀香刑》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强租胶东半岛,在山东地区修铁路,山东农民参加义和团反抗洋人势力的一段传奇故事。
民妇孙媚娘与县官钱丁相好,她的父亲,唱猫腔的戏子孙丙在一次与钱丁斗须中失败,被拔光了胡子改行开茶馆。
修铁路的德国人欺侮孙丙的妻子,他一怒之下杀了洋人,结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行。
孙媚娘的公公,刽子手赵甲奉朝廷之命设计出名为”檀香刑”的酷刑处决孙丙。
小说的主题词是--酷刑,杀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五四”运动以来庄严的悲剧的延伸。
鲁迅先生所写的杀人的场面,是对麻木国民灵魂的鞭挞。
莫言所写的杀人是对中国传统刑罚文化的审度,反思。
刑场是生命的终结,也是正义,良知的悲壮登场。
在《檀香刑》中有三个典型形象,赵甲,孙丙,钱丁。
他们一个是受宫廷礼仪熏陶了数十年的刽子手,一个是民间文化的杰出代表,一个是熟读经史子集的进士。
这三个人物将国仇,家仇,情仇,以及种种戏剧化的方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清朝末年外敌入侵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这部作品中以刽子手赵甲一生的施刑经历展现了刑场与权力,人性的扭曲。
一、权利的异化--赵甲赵甲作为刽子手的代表,封建权力社会的执法者,在小说中他成了历史的第一见证者与参与者。
【莫言小说鉴赏】论莫言小说中肉意象的文化蕴藉
作者简介:申长崴,硕士,讲师,鸡西大学,黑龙江·鸡西。
邮政编码:158100文章编号:1672-6758(2011)04-0100-2论莫言小说中“肉”意象的文化蕴藉申长崴摘要:莫言小说中的“肉”意象鲜明而独到,在“肉”意象的世界里,既有莫言“独特强调”的言说,也有莫言“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立场,还有莫言独具的文本特色和人性情怀。
试从“食”“色”两个方面阐释莫言笔下“肉”意象的文化蕴藉。
关键词:莫言;文化蕴藉;“肉”意象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莫言在众多小说中通过吃的畅快、肉的斑斓描写,刻画了“肉”意象,其文学的丰沛蕴藉与文化的无限丰富相结合,造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蕴藉,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我们探寻莫言小说中“肉”意象的文化蕴藉,也就是要追求文学与历史、文化、传统相互融合后的财富积淀。
一曰“食”:“不肉不欢”的斑斓盛宴1.饕餮之肉。
首先,小说中呈现出人物对“肉”的热爱。
无论对待何种肉,主人公们都投注了巨大热情。
以《四十一炮》为例,嗜肉如命的罗小通从小就对肉充满了深情,他自己说“我是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
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
“我还感觉到了这块肉在我的手中颤抖不止,我知道它决不是因为恐惧而颤抖,它是因为幸福而颤抖。
……所以我也就理解了肉的激动。
在我拿着肉往嘴巴里运动的短暂的过程中,肉的晶莹的眼泪迸发出来,肉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肉的眼睛里洋溢着激情。
我知道,因为我爱肉,所以肉才爱我啊”。
可以说,莫言笔下一个个阳刚壮美、野性粗犷的人物大多对肉情有独钟,于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昆虫猛兽、水族家禽皆可畅快朵颐。
其次,超出一般的食欲与巨大食量。
将饕餮之肉表现到至极的是《野骡子》、《四十一炮》,例如:传说中少年罗小通“曾经一次吃了八米肉肠、两条狗腿,外加十根猪尾巴”,至于一顿吃掉半条狗则是小菜一碟;平日里他对肉朝思暮想,有肉则来者不拒、吃之无数;吃肉大赛上,气定神闲吃完五斤一盆的牛肉,打败了冯铁汉等吃肉高手,一举夺冠;肉食节上更是风光无限。
论莫言小说中的反讽叙事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 So56 Science Edition )第30卷第6期2020 年Vol. 30 No. 62020$-文学研究-论莫言小说中的反讽叙事李昱颖,张学军(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69;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在莫言的小说中,修辞反讽较多地表现为政治话语的借用、语言的矛盾和悖谬、刻意营造夸张与失真 等方面。
将某一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用语移植到另一领域,语境的变化影响了这些特定用语表达本义,话语变得 似是而非,产生了反讽的效果。
情景反讽,则是设计出复杂的情境,主要表现在叙事主体的设置、多重故事结构的 嵌套、对文本的戏仿等等。
其中既包含着对形式的探索,也带有对“真伪”的反讽,通过形式表达出意义指向。
主题 反讽也经常出现在莫言的作品中,对人物遭际命运的揭示,反映出的是莫言对于既有观念的反讽式观照。
意象反 讽是指意象与其背后的象征意旨存在着悖逆乖离,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所以能穿透社会假面,形成悖论和反 讽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莫言小说;修辞反讽;情景反讽;主题反讽;意象反讽[中图分类号]T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3842(2020)06 -0073 -12何为反讽?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
文学理论家将反讽理解为一种结构原则, 对一篇篇作品进行细读,归纳出反讽的特质;哲学家将反讽提升到存在层面,认为从苏格拉底开始, 反讽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理论研究的众声喧哗里,很难寻找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来确定反 讽的研究边界。
从理论家们不无困惑的解析中,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也许反讽在产生 之初就是一片混沌,这个来源于希腊古典戏剧角色“佯装无知者”的概念,只不过是一个权宜的命 名而已。
通常情况下,反讽被理解为一种修辞,表现的是文本意义在语境作用下发生的扭曲,出于作者 的有意安排,语义和语境并不完全匹配,然而在这种不和谐中,却传达出了更深刻更丰富的意义。
浅析《月光斩》叙事策略
6浅析《月光斩》叙事策略焦皎西北大学摘要:莫言的《月光斩》利用独特的叙事策略,通过复杂的对称时间结构与同心圆时空结构展示了时空交错的故事情节,以第一人称视角下在第一人称叙述中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多层次的叙述视角构建了读者与小说中各个时空的交流,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反抗、复仇的惩恶案件,表达了没有解决社会贪腐的本质问题的无奈、抨击、悲哀。
关键词:叙事策略;时空结构;多层次视角莫言的《月光斩》发表于2004年10月1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被收入《莫言文集》第十六卷,是对《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王冢”故事所表达的“复仇”母题进行的现代演绎。
莫言运用独特的叙事策略与叙述对象保持距离,并用现实传闻和历史因缘,将故事笼罩在极具神秘气息与传奇性的魔幻色彩之下,用荒诞的喜剧形式召唤悲剧精神,曲折地反映出平民阶层对于社会的某些不公正现象的一种臆想性的“白日梦”般的反抗,用行动的荒诞和无意义引起人类主体内心深处的悲伤和怜悯。
纵览全文,故事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故事,分别是:一表弟与“我”的邮件往来;二刘副书记死亡谜团;三月光斩的由来。
从时空秩序的叙述视角来看,呈现出的叙事结构拥有着时空交叉的特点,不仅形成“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过去——现在”的复杂时间结构,更形成“圆心——圆环——圆环”的同心圆时空结构。
故事从表弟的来信开始,用附件内容引出了刘副书记离奇死亡的事,用倒叙的手法,以死亡案件引起读者的注意,用案件细节描写渲染故事魔幻的基调,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先讲述了炼制蓝钢,然后讲述了锻刀的过程。
奇刀月光斩的由来是发生在死亡案件之前的,因此这部分不仅讲述了过去时态的故事,还穿插了过去的过去发生的事。
而后讲述了死亡案件只是一个恶作剧,县委为了减小影响而采取各种措施,最后“我”看完附件中的闹剧给表弟回信,这一部分是从过去时态的故事回到了现在时态。
在小说中将所有的故事、传说情节按时间顺序排列,应该依次为:炼钢、锻刀、发现刘副书记死亡、发现死亡案件是恶作剧、表弟给“我”写信、“我”阅读信、“我”回信。
《檀香刑》:狂欢化叙述中的女子
《檀香刑》:狂欢化叙述中的女子
马知遥
【期刊名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20)006
【摘要】莫言在<檀香刑>的叙述中采取的是民间"狂欢节"的叙述方式,说书人的叙述语气,以及让人物刚开始出场时都采取的是戏剧中"独白"的方式介绍自己,语言铿锵,节奏明快.借助狂欢节叙述的方式,读者将欣赏到这样叙述的诸多好处:广场化、杂语化、粗俗性等等,而人物的爱憎就是在呼喊和嬉笑怒骂里得到了体现.另外在人物塑造中,莫言采用了加冕和脱冕的方式,其目的是起到民间的戏剧效果.眉娘就是狂欢化叙述的产物,是小说狂欢理论的典型写照.
【总页数】3页(P91-93)
【作者】马知遥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论莫言《檀香刑》的狂欢化色彩 [J], 周琳琳;
2.历史的突围与超越--论莫言《檀香刑》狂欢化叙事美学 [J], 凤卓;彭正生
3.论莫言《檀香刑》的狂欢化色彩 [J], 周琳琳
4.狂欢化的刑罚与变异的权力--《檀香刑》的主题意蕴 [J], 赵先锋
5.《檀香刑》中的狂欢化色彩赏析 [J], 赵彬彬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 莫言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李钦彤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从最初的《红高粱》的发表到现在面世的《檀香刑》,莫言的作品中一直存在对暴力的描写,他以独特的感官展示暴力带给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莫言展示人性的残忍,并揭示这种暴力残忍形成的原因,即源于生活的苦难对权力的渴求。他从儿时的饥饿、孤独的生存体验出发,以一种悲悯和宽容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暴力,希望以此来拯救人类的灵魂,给人们以希望。 关键词:暴力 苦难 权力 悲悯 自《红高粱》发表后,莫言一炮走红,他以奇绝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觉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莫言滔滔不绝、汪洋恣肆的语言和包容一切、容纳百川的叙述在当代文坛上具有别具一格的风采,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成为其梦魂萦绕的叙事空间,如同苏童的枫杨树故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李锐的吕梁山,已成为一个文化地理空间。依托于高密东北乡,莫言写出了《红高粱家族》、《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神聊》、《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既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抗日的血泪牺牲,也有奇人异事,鬼怪神魔,土匪强盗往来其中,奇人异士络绎不绝。相对于余华的“文学的减法”①,莫言则是文学的加法..,过去和未来,外在和内心,客体对象和主体意识,社会历史和个人记忆,错综复杂,纠缠不清。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的作品都打上了这种商标,在《红高粱》中,莫言讲述了在红透半边天的高粱地中,土匪余占鳌的英雄史和风流史,描写他的狂放不羁,有情有义,让人想起同样发生在山东境地的水浒英雄,聚义梁山,替天行道。《檀香刑》中则塑造了民间艺人孙丙的英雄形象,再现义和团的英雄事迹和民族气节。《红高粱》是其代表作,也是其成名作,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历史观和叙述视角以及对暴力、死亡的审美感觉打动了读者;《檀香刑》同样以残酷的刑罚挑战着读者的心理和生理,从始至终,莫言对暴力有种特殊的迷恋和迷惑,念兹在兹。本文试图分析莫言作品中暴力的描写,暴力背后所揭示的苦难、权力、人性以及作者创作的心理、心态。
一 从功利到审美 《红高粱》让莫言成名,在莫言笔下,抗战历史吸取了红色经典的粉饰铅华,被还以民间的本来面目,他以“灵性激活历史”②令读者为之振奋。同样,也以其对暴力、死亡的直面描写而令读者胆战心惊,觳觫不已。犹如红透半边天的红高粱,暴力鲜血弥漫于空中,在高粱地中氤氲不散。余占鳌为了自己的情欲,剥夺了吃拤饼的人的生命,血洗了单廷秀父子一家,并占了人家的房子。作品中更令人侧目的是活剥罗汉大爷的血腥描写,莫言动用自己独特的感觉,把视觉转化为听觉,以审美的姿态描写血淋淋的场面,挑逗着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作品)这一切的暴力描写都是为了表现高粱地东北乡人民的骁勇血性、狂放不羁而服务,余占鳌的血气方刚、敢做敢为,罗汉大爷的英勇不屈,即使是强奸犯余大牙,在临死时也表现了英雄气节。这是一群不适合用传统的道德伦理来评判的人,道德在这里延迟,更多被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体验。为了表现土匪所体现出来的原始生命力,叙述者以一种独特的激情和叙述腔调认同了这种暴力以及鲜血,而不自觉掩盖了其他生命的意志和价值。于是,单廷秀、单扁郎便成了这种叙述的牺牲品和淹没者,同时,这种情感倾向也淡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这种创作不由得让人想起土匪黑社会的经典代表作品——《水浒传》。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英雄好汉,江湖义士,他们聚义一堂,替天行道,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暴力、战争、死亡、血腥。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作者将过程一笔笔细细写来,巨细无遗,细致而酣畅淋漓,色香味俱全。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飞浦楼,将张都监府上的人全都认认真真地杀了,一个也不放过,丫鬟、佣人也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李逵劫法场,沿着浔阳城临长江的大道突围,挥着板斧一路砍杀,见一个杀一个,连老百姓也不放过,砍上了瘾,沉醉其中,有乐而不思其返的味道。(作品)这一切都源于叙述者施耐庵的认同叙述,他的一种激情,一种欲望宣泄,一种愤懑情绪的排遣。在这里,读者出于对镇关西、张都监的愤怒不平,认 2
同了作者的叙述,鲁智深、武松们的暴行便得到了认可,甚至是赞许。在读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鲁智深的包打不平激情的双重作用下,镇关西的生命从那一刻起便不再属于他,他本人的主体意志和生命权利便被剥夺了,成了暴力的牺牲品。但是,在正义的名义下,暴力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如果是这样,正义便成了暴力的同谋,成为杀戮的共犯,共同掌握着生杀大权。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私淑前人的良苦用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主题对于叙述腔调、情感倾向的制约,《水浒传》中为了塑造一个流传千古的黑社会,而放纵了暴力的横行,为了表现高密东北乡人民的血性、野性、豪情,莫言同样认同了这种暴力的泛滥;另一方面,便是中国作家内心精神结构的一脉相承:即是对暴力的渴望和迷恋。“中国文化有极其冷酷无情,极乏人文气息的一面。无论是就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而言,还是就日常生活形态而言,内心深藏着对于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④但由于法制的规训和刑法的惩罚和恐吓功能,人们的这些欲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于是作家便诉诸笔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生活是规范的,是受到限制的,而写作则是随心所欲的,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他的全部欲望在现实中表达出来,法律和生活的常识不允许这样,因此人的无数欲望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在内心里转瞬即逝。然而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⑤暴力以其是内心的渴望,故而使作家心醉神迷,念兹在兹,成为表现作家内心欲望和笔下主人公的原始生命力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不仅如此,在暴力和生命力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暴力与性也有暧昧关系,我们得小心翼翼从文本中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将其剥离出来。《红高粱》中,余占鳌与戴凤莲的风流史都与暴力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抢亲,野合,都以暴力为依托。战争的残酷也决定了暴力与性的存在意义,当人的生命时时处于死亡与毁灭的阴影下,就特别渴望着它能迸发热力与激情。 中篇小说《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黄胡子与副官长为了争夺“玫瑰”,结下了仇怨。怯于副官长的武力,黄胡子将愤怒、仇恨转移到了红马的身上,他毒打红马,赛马时,他在马鞍中放了针,导致副官长的失败,让司令把玫瑰抢走。然后,他将自己一手导演的败局的失败的仇恨都转向了副官长,在相互厮打中杀死了对方。在作品中,马的意象一次次出现,马的奔跑姿势,昂首嘶鸣的形象,被认为是男性的象征,是性的升华——生命的自我实现的象征。⑥黄胡子一次次毒打红马,象征着他的情欲的难以实现的愤怒,暴力由此而产生。黄胡子这个人物,让人很容易想起苏童《十九间房》中小兔、小鼠式的人物——春麦,怯懦的春麦面对土匪头子睡自己的老婆,敢怒不敢言,无奈中,把仇恨发泄在老婆身上,手中的砍刀没有砍向土匪头,却落在妻子的手臂上。在暴力的对抗中,暴力最终指向了更弱的对象。女性又一次成了男人争权夺势,争夺欲望权的牺牲品。短篇小说《翱翔》中,为了维护乡村伦理制度、婚姻制度,男人世界的权威和对女子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像疯狗一样去捕捉燕燕,对于他们来说,“跑了新媳妇,是整个高密东北乡的耻辱。”为此,他们对一个弱女子使用了弓箭、鸟枪、狗血。叙述者同情燕燕的不幸,为她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燕燕终究没能逃脱男人统治的世界,成为农村换亲的牺牲品和男人暴力的侵犯对象。 莫言以暴力的展示挑逗、挑衅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檀香刑》中则发挥到了极限,淋漓尽致描写展示残酷的刑罚。与《红高粱》中的剥皮表演的偶一为之相比,《檀香刑》中可以说是蔚为大观,惨烈冷酷,其中有七大刑罚处决场景: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库丁;余姥姥和赵甲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余姥姥凌迟妓女美女;赵甲凌迟钱雄飞;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场面越来越壮观,惩罚技巧也花样翻新,技术越来越出神入化,鬼斧神工。莫言发挥其奇崛怪异的想象力,用汪洋恣肆的如椽之笔为我们展示一个个令读者悸动、颤栗的残酷冷漠世界,血肉横飞,鲜血四溅,惨绝人寰,暴殄天物,给读者带来生理的恶心和精神上的震撼。在每一次的刑罚处决中,莫言动用一切感官,视觉、听觉、味觉酣畅淋漓、快意无比地展示着刑场上的腾腾杀气。 在刑法的展示中,莫言为我们揭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在肉体上的运作,在刑罚中,惩罚者和被惩罚者的二元对立体现的是君主本人的过剩权力和罪犯的权力的匮乏,⑦昭示着双方权力力量的悬殊和不可逆转的倾斜,并将这悬殊对比在刑罚中发展到极致。正是为了展示君权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库丁、小虫子、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变成了展现统治者权力的最佳所在。在这种公开处决的仪式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成为了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公开处决的目的是以儆效尤,不仅要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人发泄怒火的场面唤起恐怖感”⑧在刽 3
子手处决小虫子和钱雄飞时,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吓得面如土色。但是角色却是多义的。一方面他们是恐吓对象,但同时他们也是一个主动、好奇的围观者,通过喝彩、鼓掌,他们将这种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在这狂欢的节日,满足他们猎奇、嗜血的心理,为此他们对刑罚趋之若鹜,争先恐后,来看一场罕见的人生景观。(作品)在这些处决场面中,观众看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的展示,可以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砍头、腰斩、凌迟、檀香刑,从零度酷刑到痛苦延长,再到痛苦极点,“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⑨凌迟钱雄飞,给孙丙上檀香刑,让观众欣赏到了这种痛苦的量化艺术,这种艺术恰恰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声哀嚎、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⑩观众的这种嗜血心理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看客,在鲁迅笔下,主要针对看客的愚昧麻木,但看客同样表现了这种狂欢节的侧面,他们鼓掌喝彩,不仅希望能看到犯人的痛苦,刽子手的技巧,也希望听到在即将处死这个保护伞下罪犯的胡言乱语,对自身行为的无悔和对官方、政府、法律的咒骂。 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莫言毫不吝啬也不惮于展示暴力,残酷景观,暴力即景一再在笔下流露,步步升级,不可遏止,有如秋天的雨横风狂让人好奇而又恐惧。这其中,莫言经历了从表现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功利到暴力的审美,“寻根主义者开始重新诠释和扩展他们手中的暴力语汇,把它与原始
生命力的语义分离,而后从暴力自身的形而上语义出发,将其逼入美学的极限。”○11这也正如莫言自己
所说:“我之所以能够如此精细地描写酷刑,其原因就是我把这个当成了戏来写。”○12但无论如何转换,在暴力描写的背后隐含的是叙述者一贯的心理行为模式,一种无法抹去的经验记忆。莫言曾在一篇谈短篇小说的短文中谈到少年时读鲁迅《铸剑》时的感受:“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气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这种印象深深影响了莫言的少年时代,长大之后,再读《铸剑》,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渐渐地我将黑衣人与鲁迅混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