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
鲁迅和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之比较

内容提要鲁迅和高晓声都成功塑造了中国农民的典型,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
他们在题材的选取上都是以农民为写作对象,创作的目的是改良人生和为人生;而在语言表达、结构、主题的深刻上又有各自的风采。
(应该直接把论文标题中的要点连接成一段话写进来。
否则很空洞。
)关键词:鲁迅,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比较目录一、(一)(二)二、(一)(二)(三)(四)鲁迅、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之比较自鲁迅开创了农村题材的小说后,就涌现出了一批批现代文学史上写农民的佼佼者,其中以高晓声最为突出,业绩显著。
高晓声在农民题材以及深入探讨国民性问题上也对鲁迅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此就从他们的创作主题与创作风格进行比较。
一、创作主题独具匠心鲁迅与高晓声都是通过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揭露农民的病态心理,警醒人们改变思想认识,改变国民思想落后的现状。
另外基于农民狭隘、保守、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的思想,鲁迅与高晓声都提出了“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
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创作主题也都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但二人在创作主题上又各有侧重。
(一)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批判批判国民性是时代的重任,“五四”是一个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振兴民族文化的重任,一方面要批判封建文化的糟粕;另一方面要介绍西方先进文化,开启国人心智。
鲁迅曾说过,“他无情的解剖别人,也无情的解剖自己”“无情的解剖自己”是要去掉自己身上的“鬼气”和“毒气”——去掉中国“国民性”中消极影响。
[1]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鲁迅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面对落后文化的根深蒂固,鲁迅由农村题材的小说入手研究中国国民性。
他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农民,从批判的角度理解农民,用揭露的笔调表现农民,把农民身上的“奴性”“劣根”彻底的挖出来。
在《故乡》中,鲁迅塑造了一个麻木自卑的中年闰土,他在挑选的许多家用物品时,毫不犹豫地选取祭器,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祖宗或神灵主宰,“仿佛石像一般”,连在童年的小伙伴面前也是战战兢兢,仅有的一点灵性完全被磨灭了。
中国农民个性与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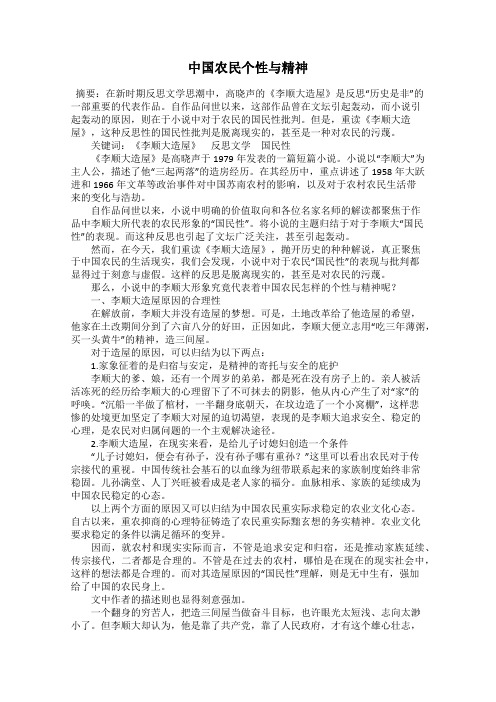
中国农民个性与精神摘要:在新时期反思文学思潮中,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是反思“历史是非”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品。
自作品问世以来,这部作品曾在文坛引起轰动,而小说引起轰动的原因,则在于小说中对于农民的国民性批判。
但是,重读《李顺大造屋》,这种反思性的国民性批判是脱离现实的,甚至是一种对农民的污蔑。
关键词:《李顺大造屋》反思文学国民性《李顺大造屋》是高晓声于1979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
小说以“李顺大”为主人公,描述了他“三起两落”的造房经历。
在其经历中,重点讲述了1958年大跃进和1966年文革等政治事件对中国苏南农村的影响,以及对于农村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与浩劫。
自作品问世以来,小说中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各位名家名师的解读都聚焦于作品中李顺大所代表的农民形象的“国民性”。
将小说的主题归结于对于李顺大“国民性”的表现。
而这种反思也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甚至引起轰动。
然而,在今天,我们重读《李顺大造屋》,抛开历史的种种解说,真正聚焦于中国农民的生活现实,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对于农民“国民性”的表现与批判都显得过于刻意与虚假。
这样的反思是脱离现实的,甚至是对农民的污蔑。
那么,小说中的李顺大形象究竟代表着中国农民怎样的个性与精神呢?一、李顺大造屋原因的合理性在解放前,李顺大并没有造屋的梦想。
可是,土地改革给了他造屋的希望,他家在土改期间分到了六亩八分的好田,正因如此,李顺大便立志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
对于造屋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家象征着的是归宿与安定,是精神的寄托与安全的庇护李顺大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
亲人被活活冻死的经历给李顺大的心理留下了不可抹去的阴影,他从内心产生了对“家”的呼唤。
“沉船一半做了棺材,一半翻身底朝天,在坟边造了一个小窝棚”,这样悲惨的处境更加坚定了李顺大对屋的迫切渴望,表现的是李顺大追求安全、稳定的心理,是农民对归属问题的一个主观解决途径。
浅谈《陈奂生上城》的叙事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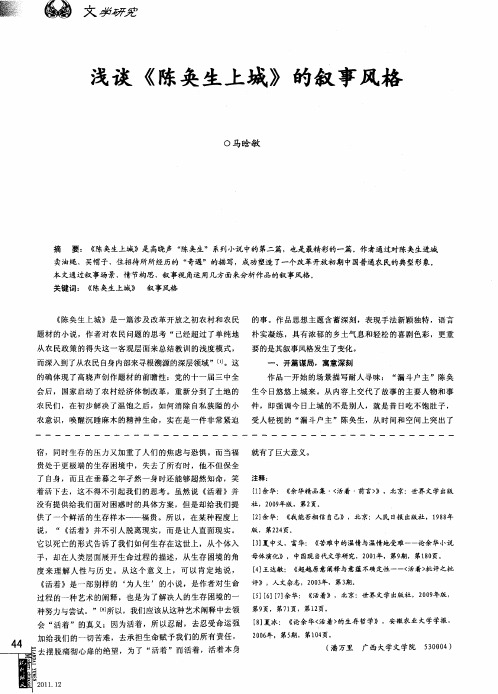
供 了一个鲜活 的生存 样本——福 贵 。所 以,在某 种程度上 说, “《 活着》 并不 引人脱离现实 ,而 是让人直面现 实。
[】 2 余华 : 《 能否相信 自己》 ,北京:人 民日报 出版社 ,1 8 年 我 98
版 ,第 24 2 页。
3夏 苦难 中的温情 与温情地受难 一一论余华小说 它以死亡的形式 告诉 了我们如何生存在 这世上 ,从个 体入 【】 中义,富华: 《 01 期,第1 0 8 页。 手,却在人类层面 展开生命过程 的描述 ,从生存 困境 的角 母体演化 》,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 究,2 0年 ,第9
描 写 天 气 情 况 , 而 且 烘 托 出 陈 奂 生 这 位 “ 斗 户 主 ” 因 政 已晚 不 能 回 家 只 能在 火 车 站 凑 合 一 宿 ,正 好 碰 上 吴 书 记 就 漏
策的变化而过上 了温饱生活之后的幸福感和 自由感 。 接下
“ 理所 当然 ”地看病 ,然后再送他 上招待所 。作者 就这样
“ 可 能 ”化 成 了表 面 上 的 “ 能 ” 。 不 可
人 公当时 的主观 心理 : “ 心想吴书记照顾 得太好 了,这 哪
《 奂 生 上 城 》 的 叙 事 模 式 仍 然 沿 用 民 间 故 事 或 童 儿 是我 该 住 的地方 !… ” “ 样好 的房 间 ,不 知要 多少 陈 这 话 等 叙 事 作 品 中 的 常 见 模 式 : “ 事 开 始 时 主 人 公 在 正 常 钱 ,闹不好 ,一夜 天把 项 帽子 钱住 掉 了 ”,描 写陈 奂生 故 境 况 中 , 随 后 便 遇 到 了 意 外 的 事 件 甚 至 不 幸 ,经 过 若 干 波 既对 吴 书记 感 恩戴 德 ,又担 心 住宿 费太 高损 失太 大 。接
高晓声农村小说的思想特质及文化内涵解析

高晓声农村小说的思想特质及文化内涵解析作者:杨晓玉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9年第1期摘要:在我国现代文学中,自鲁迅在其小说中引入农民并赋予他们主人公身份后,农村题材小说被重视,农民成为现当代文学审美的对象。
高晓声以其严谨的现实主义笔法对我国农民的命运变化、生活境遇进行描述,探索农民心灵世界,风格幽默。
本文主要对高晓声农村小说进行阐述,解析其小说的思想特质、文化内涵,为读者鉴赏高晓声农村小说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晓声农村小说思想文化内涵高晓声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接触古典文学,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
在20 世纪50 年代初,高晓声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1979 年,其发表了《陈奂生上城》等描述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并在当时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高晓声的作品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主,其作品激情褒扬农民优点、善意嘲弄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传达思想、警示人们,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一、高晓声农村小说的思想审视(一)审视灵魂在文坛沉寂二十余年后,以“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为目的,高晓声再度执笔事文,通过文学唤起农民当家做主人翁的思想意识。
高晓声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新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喜怒哀乐进行展现,描述真实的农村生活,摄录人物灵魂的演进及社会迈步的足音。
例如,在《李顺大造屋》作品中,作者描述了李顺大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历经千辛万苦建成三间普通房屋的故事。
且在故事背后,作者意在揭示李大顺身上的奴性意识、“跟派”思想,并反思像李顺大这样的人物是否具有一定的责任,是否应该思想醒悟等问题。
同时,高晓声的动机是解剖人物灵魂,是通过“他审”小说人物进行“自审”。
在高晓声的作品中,不仅解剖小说主人翁,也对自己进行解剖,并巧妙结合“他审”“自审”,将作品思想表达指向民族命运。
例如,在“陈奂生系列”小说中,作者借助知识分子陈正清、农民陈奂生之间的对话来“自审”自我。
在小说中,“公家人” 陈正清向陈奂生借钱、陈正清说“事实是为需要服务的”等场景,均说明了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渺小、尴尬,以此“自审”“我”类知识分子。
余晓声四句话

余晓声四句话
这四句话是梁晓声在绍兴文理学院,三个星期讲了六节课其中的一节课上说的。
作家梁晓声说过“文化”可用四句话表达: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作为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
梁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谋取私利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
相反,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虽然终日为生计所奔波,但却享受着精神生活上的充实。
在这种层面上,反映了梁晓声在"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的抗争与回归,主张回归质朴、知足、正义的人性,摒弃那冷冰冰的理性,那装饰得漂亮的诺言。
《21世纪你应关注的中国人》。
2020年成教、电大《中国现当代文学》期末考试复习题试题库及答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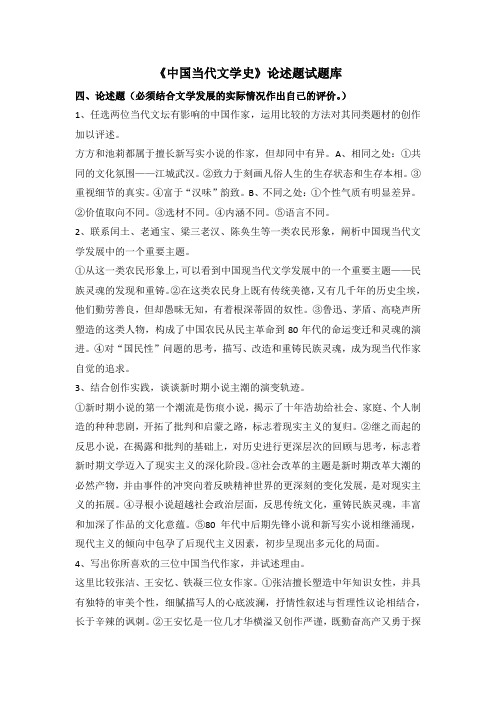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述题试题库四、论述题(必须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
)1、任选两位当代文坛有影响的中国作家,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其同类题材的创作加以评述。
方方和池莉都属于擅长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但却同中有异。
A、相同之处:①共同的文化氛围——江城武汉。
②致力于刻画凡俗人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本相。
③重视细节的真实。
④富于“汉味”韵致。
B、不同之处:①个性气质有明显差异。
②价值取向不同。
③选材不同。
④内涵不同。
⑤语言不同。
2、联系闰土、老通宝、梁三老汉、陈奂生等一类农民形象,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①从这一类农民形象上,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
②在这类农民身上既有传统美德,又有几千年的历史尘埃,他们勤劳善良,但却愚昧无知,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
③鲁迅、茅盾、高哓声所塑造的这类人物,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80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
④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描写、改造和重铸民族灵魂,成为现当代作家自觉的追求。
3、结合创作实践,谈谈新时期小说主潮的演变轨迹。
①新时期小说的第一个潮流是伤痕小说,揭示了十年浩劫给社会、家庭、个人制造的种种悲剧,开拓了批判和启蒙之路,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复归。
②继之而起的反思小说,在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更深层次的回顾与思考,标志着新时期文学迈入了现实主义的深化阶段。
③社会改革的主题是新时期改革大潮的必然产物,并由事件的冲突向着反映精神世界的更深刻的变化发展,是对现实主义的拓展。
④寻根小说超越社会政治层面,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⑤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相继涌现,现代主义的倾向中包孕了后现代主义因素,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
4、写出你所喜欢的三位中国当代作家,并试述理由。
这里比较张洁、王安忆、铁凝三位女作家。
①张洁擅长塑造中年知识女性,并具有独特的审美个性,细腻描写人的心底波澜,抒情性叙述与哲理性议论相结合,长于辛辣的讽刺。
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

——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
刘旭
内容提要 高晓声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作家,其反映农民苦难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渐渐脱离了现实,他的农民形象只停留在了80年代之前,而评论界和文学史对其评价也同样滞后。究其原因,执着于脱离现实的、静止的国民性批判是主要原因。高晓声创作及评论界的刻舟求剑状态则昭示了重读作品的重要性。同时,对现代性大背景下的国民性话语的再思考也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陈奂生上城》的产生,就是由于我自己住了每天租金五至六元的招待所,触发了一个念头;农民绝对住不起,如果一个农民进了这样的招待所又将如何?让一个农民表演一番,一定很有意思。为了使陈奂生住招待所合乎情理,就安排了陈奂生进城做生意、想买顶帽子、车站发病、巧遇县委书记等等情节,以弥补漏洞。⑨一个普通农民住进了想都不敢想的招待所,而且还是县委书记亲自送进去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高晓声却让陈奂生在“上城”成功“表演”后,很精彩地出演了一个“系列”。这是因为高晓声不时地又“触发了一个念头”,将自己成名后的生活和经验派给了陈奂生,仿佛回归作家队伍、成名后的高晓声的日子有多丰富,陈奂生的日子就有多光鲜。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在突然想起式地将陈奂生不由分说拉进自己的生活和小说之后,高晓声对此显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用了“表演”二字。想想“表演”这个词,有点意思:其一,日常语言的这个语境里,它多半是贬义色彩的;其二,但凡“表演”总怕“穿帮”,也就是说,从“陈奂生系列”的第二篇开始,高晓声就已经将他的农民小说建立在了某种“假设”的、“不可能”的基础之上了。在高晓声看来,这种“不可能”的戏剧化情境,更能让农民在惊惶失措之下暴露出某种精神的“本质”,何况那种无痕迹地混淆人物角色和叙述人的叙事方式,又还让那些“不可能”化成了表面上的“可能”呢。
从李顺大造屋到蜗居

从《李顺大造屋》到《蜗居》1979年,一部小说《李顺大造屋》横空出世,在众多知识分子沉浸于“伤痕”中时率先开始反思。
反思产生社会悲剧的原因与教训,对历史是非做出深沉而严肃的评价,进而反思自我对历史应付的责任,寻找在新时代面前自身的使命和位置。
2009年,一部电视剧《蜗居》刺激人心,在众多历史题材剧作中独树一帜,以通篇饮食男女、家长里短,彰显世态本色,生存哲学,道出当今时代下年轻人的各种疯狂与苍凉。
两部作品时隔三十年,却从颇多方面有着相似性。
它们都反思了时代问题,将社会底层、种种众所周知却秘而不宣的阴暗面搬到台面上来剖开给人看,并且挖掘了国人身上存在已久难以根除的性格弱点。
这里我们不谈别的,暂且说说贯穿故事始终的房子的事。
当年,杜甫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表现了人民困苦,无处安身的生存困境,感动无数人。
流传千百年,房子仍然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在解放后,立志要以“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可是却历经坎坷,三起两落,耗去30多年的人生岁月仍然没造起来。
据陆文夫对文章的回忆有这样的话:“《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
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
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
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指高晓声,本文作者注)修改结尾。
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吧,造了几十年还没有造成,看了使人难受。
另外,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也可能会容易些。
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也同意我的意见。
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
”《蜗居》中的海萍与苏淳、海藻与小贝,分别住在租来的10平米的石门库房子和三居室的一间,都努力攒钱,等攒够首付就光荣跃居“房奴”,为了房子,即使跨入“百万负翁的行列”也在所不惜。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高晓声的小说及其“国民性话语”——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刘旭内容提要高晓声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作家,其反映农民苦难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渐渐脱离了现实,他的农民形象只停留在了80年代之前,而评论界和文学史对其评价也同样滞后。
究其原因,执着于脱离现实的、静止的国民性批判是主要原因。
高晓声创作及评论界的刻舟求剑状态则昭示了重读作品的重要性。
同时,对现代性大背景下的国民性话语的再思考也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
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高晓声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推出了数篇极有分量的农村小说,大胆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几十年的苦难。
《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极具现实性和文学性,而之后的《陈奂生上城》更是攀上了一个不易复制的高度。
这也就难怪高晓声吸引了众多批评家的注意力,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从1979到1991年,历经12年,高晓声精心构筑的“陈奂生系列”全部推出,同时,高晓声也稳步踏入了文学史。
作为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代表性作家,“高晓声”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象。
然而相当令人遗憾的是,迄今20多年过去了,“高晓声”依然被定格在当初批评家们所塑造的形象,不仅照旧被鲁迅和“阿Q”的阴影笼罩着,甚至在去世多年之后,许多文学史讨论起高晓声来,仍然只限于他80年代中前期的作品。
所以,本文试图对高晓声的创作进行再解读,以期发现高晓声的更多侧面。
或许,一个立体的“高晓声”显得不再那么高大全,而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值得的,借重读高晓声为契机,重返80年代的文学场域,也真切地面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若干问题。
一1979年,当许多知识分子尚沉浸在自己的“伤痕”之中,《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横空出世,而这时,高晓声自己的右派帽子也还没有摘掉。
因此,即便仅仅是因为高晓声敢于触碰敏感话题的胆魄、为农民兄弟呼吁的情怀,这两篇小说也无愧于其时大量的文学批评以及其后的当代文学史①的基本评价:深刻地反思了“极左”时期农民的苦难。
事实上,这一切高晓声做来又相当自然:我二十多年来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准备就这样过一辈子。
我在农民中间,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共同生活,所以对农民的思想比较了解,但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写他们。
为什么后来又写了呢?粉碎“四人帮”以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中,都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关心群众疾苦的传统,我深受感动,就想为农民叹叹苦经,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
②这篇《创作思想随谈》里,“叹叹苦经”后还有一句话:“农民有些什么苦?我认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
”非常朴素,又真是抓得非常准!李顺大和陈奂生,一个一直没有房子住,一个一直吃不饱,“住”和“吃”两方面的艰难处境,正是中国农民生存的最基本问题所在。
22年的“共同生活”使高晓声的自我经验与农民的经验深切地合一,因此,他要为农民“叹叹苦经”,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22年农村生活叹苦经?高晓声被打成“右派”下放,经历过“大跃进”之后的饥荒年代,他不得不想尽办法疗饥驱饿;还因为肺病,三根肋骨被摘除,重活不能做,便也学会了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从他还懂得育蘑菇和挖沼气池之类来看,高晓声还是个当得挺称职的农民。
所以,初回城市那阵子,高晓声总觉得生活过得太好就对不起农民,他见朋友家有二十吋的彩电,曾不止一次感慨说,这相当于农民盖三间房啊③。
另一方面,下放了的高晓声终究还是一位作家,和农民有同样的生活经验同时,他又有超越普通农民之上的观察和思考能力。
所以,也只有他才能成功地将农民的苦难转化为艺术形式与历史叙述:《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中,高晓声仿佛一个民间说书艺人,将故事缓缓道来,仅截取了几个片断,就把农民的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其中的那样一种沉重,又分明像在说自己的故事。
据陆文夫回忆,这里还有个故事:按《李顺大造屋》本来的小说结局,李顺大弄到最后仍没有盖成自己的房子,“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
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④。
也就是说,即使为了发稿的需要,在“光明的尾巴”里,高晓声还是动足了脑筋;更足以见得高晓声对农民的理解程度,不肯加一点虚幻的花环来点缀。
或许当时被迫修改结尾的高晓声,心中还有着许多的愤懑和不平,他的经验让他相信中国农民的历史只是苦难史,甚至即使一个非常的时期结束了,但是,农民的苦难仍难言终结。
因为,农民的弱者身份始终没有改变。
迅速改变着的是高晓声的身份。
《李顺大造屋》发表当年即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这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大事件。
轰动文坛之后,《陈奂生上城》趁热打铁,紧随着发表。
这部作品虽说是陈奂生系列的第二篇,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关注的依旧是农民,而焦点则由物质生活转向了精神生活,这在当时非常轰动。
很多作家连农民的题材也很少顾及,对农民的精神生活更似有千山万水的隔膜,而高晓声关注农民的精神状态,的确体现了他的前瞻性: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已经启动了,重新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们,在初步解决了温饱之后,如何消除小农的保守和狭隘,实在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而且如何克服“小农”心态,不仅仅关乎农民,它简直就是8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一大核心问题,关涉到了我们民族积极实现精神上的现代“改造”的大问题,是国民性批判工程的重中之重。
相应地,《陈奂生上城》的叙事风格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
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
”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钱花得值透。
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
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5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晤!……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5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
这个非常著名的段落,历来被视为最能体现陈奂生非常具备“阿Q”精神的描述,它是怎样把陈奂生的自欺欺人揭示得入木三分的呢?其叙述方式大有讲究:开始尚有“自问自答,左思右想”作为角色心理活动的标志,但接下来,叙述角色心理活动的标志便经常被取消了。
“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是叙述人的客观陈述吗?之后黑体的部分“试问……”一句的叙述视点就更加暧昧起来,是叙述人在叙述还是陈奂生在自言自语?“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一句却又用了第三人称,像是叙述人的客观陈述。
用罗兰·巴特的人称替换法可以发现⑤,这段全部可以替换为第一人称而不发生意义变化。
这样看来整段话其实都是以陈奂生为视点的心理活动。
再者,那些表示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仍然存在,尤其是最后的拟声词“晤!”更增加了直接引语的感觉。
因此,这段话是叙述人以隐蔽的方式取代了人物角色,把这些与直接引语有同样效果的心理活动从引号中剥离出来,形成了流畅的叙述,主语的省略又成功地抹去了转换的痕迹,叹号的保留又让间接引语保持了直接引语的现场感,这一切共同制造了“客观”的假相,让一般受众把陈奂生心理活动的部分也当成了叙述人的客观陈述,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当时的评论家不是没有注意到高晓声叙事风格的与众不同,但在80年代,绝大多数评论者只把它当作独特的语言风格来赞扬了,很少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包括后来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⑥。
目前所见,例外的是王晓明的《在俯瞰陈家村之前》⑦,其中分析高晓声小说的叙述人与角色经常混淆不分,是一种“混合重唱”。
而换个规范些的叙事学术语来说,高晓声的叙事可算是较典型的“自由转述体”⑧。
这一叙事方式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由翻译小说进入中国文学,传到高晓声手里被派上了大用处,尤其是在《陈奂生上城》中,由于这种手法的大面积、高密度使用,大大增加了主观的成分,而这些主观性又以各种方式被巧妙地转换成相对客观化的叙述,并借助叙述人的全知权威性,增强了叙事的可信度;这样,很大程度上增强叙述者对角色的无形控制。
当然,所有的这些隐秘的主观性和批判性,都全部指向了陈奂生,一个中国农民的被指认的国民劣根性。
不可否认,高晓声做得非常成功,于是,一个保守而猥琐的当代阿Q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我们看来,《陈奂生上城》叙事形态的改变,完全不是外表形式、个人风格的成型那么简单,它是从这篇小说起,高晓声的“创作程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的表征。
高晓声一向在小说中替角色说话、思考,做人物的全权代言人,看起来《陈奂生上城》也没什么太特别。
问题是,这之前的高晓声,用一句俗话来说,是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而如今,高晓声的身份及其感觉变了,即高晓声所处的现实和个人的经验,同现实中的农民、他笔下的农民相比,已经不很一致了。
那么,高晓声还有能力代言吗?那些被代言了的,在高晓声作品中还能保持本色吗?这种疑问并非杞人忧天,再看一段创作谈我们就能发现:《陈奂生上城》的产生,就是由于我自己住了每天租金五至六元的招待所,触发了一个念头;农民绝对住不起,如果一个农民进了这样的招待所又将如何?让一个农民表演一番,一定很有意思。
为了使陈奂生住招待所合乎情理,就安排了陈奂生进城做生意、想买顶帽子、车站发病、巧遇县委书记等等情节,以弥补漏洞。
⑨一个普通农民住进了想都不敢想的招待所,而且还是县委书记亲自送进去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
高晓声却让陈奂生在“上城”成功“表演”后,很精彩地出演了一个“系列”。
这是因为高晓声不时地又“触发了一个念头”,将自己成名后的生活和经验派给了陈奂生,仿佛回归作家队伍、成名后的高晓声的日子有多丰富,陈奂生的日子就有多光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突然想起式地将陈奂生不由分说拉进自己的生活和小说之后,高晓声对此显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用了“表演”二字。
想想“表演”这个词,有点意思:其一,日常语言的这个语境里,它多半是贬义色彩的;其二,但凡“表演”总怕“穿帮”,也就是说,从“陈奂生系列”的第二篇开始,高晓声就已经将他的农民小说建立在了某种“假设”的、“不可能”的基础之上了。
在高晓声看来,这种“不可能”的戏剧化情境,更能让农民在惊惶失措之下暴露出某种精神的“本质”,何况那种无痕迹地混淆人物角色和叙述人的叙事方式,又还让那些“不可能”化成了表面上的“可能”呢。
这一移形换位的代言方式,或许又意味着高晓声的国民性批判的主体由农民转向了他自己。
因为离开农村后,高晓声基本与农民脱离了联系,据叶兆言回忆说,高晓声反复提到农民的时候,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农民,回城没两年他就感觉当众和农民接触让他难堪⑩。
从《陈奂生上城》开始,他所描述的农民生活,是他不熟悉的。
这样,继续原有的写作路数就会有题材来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