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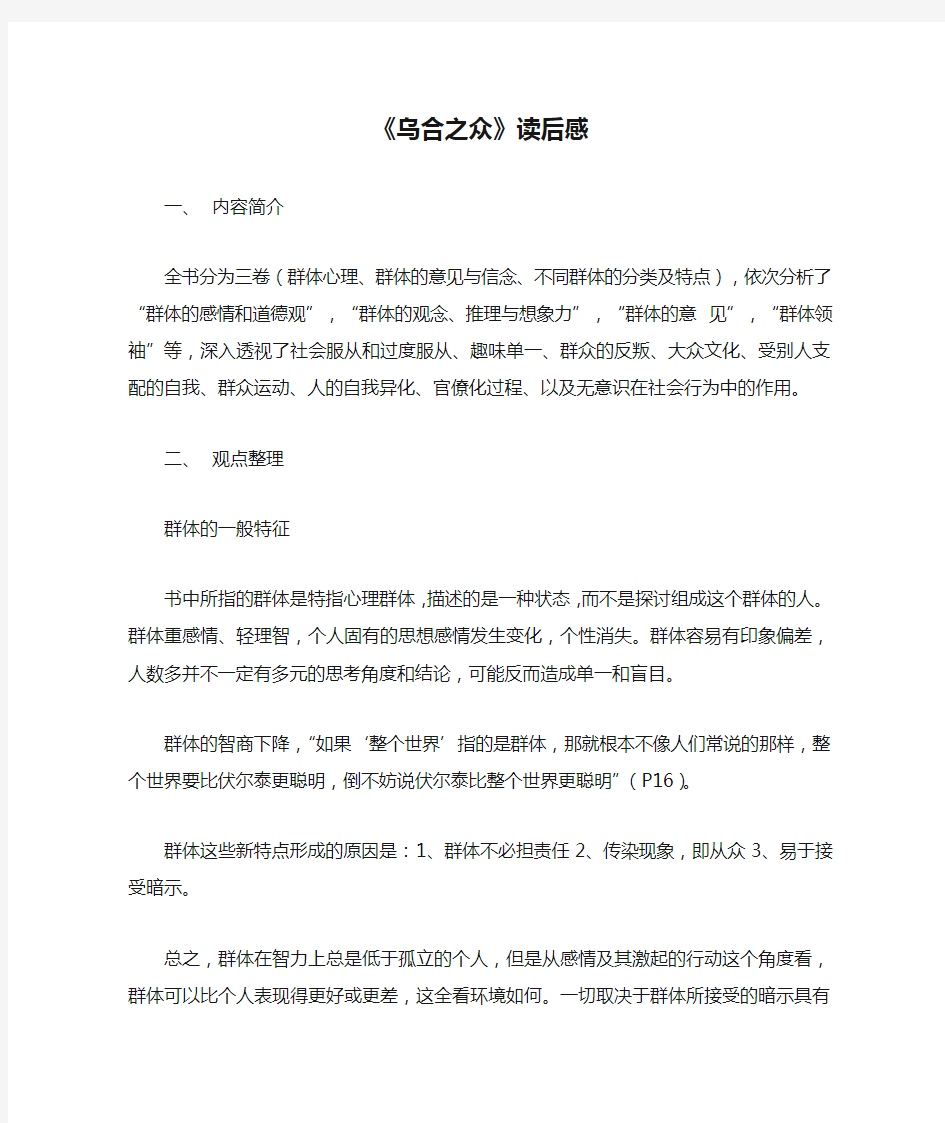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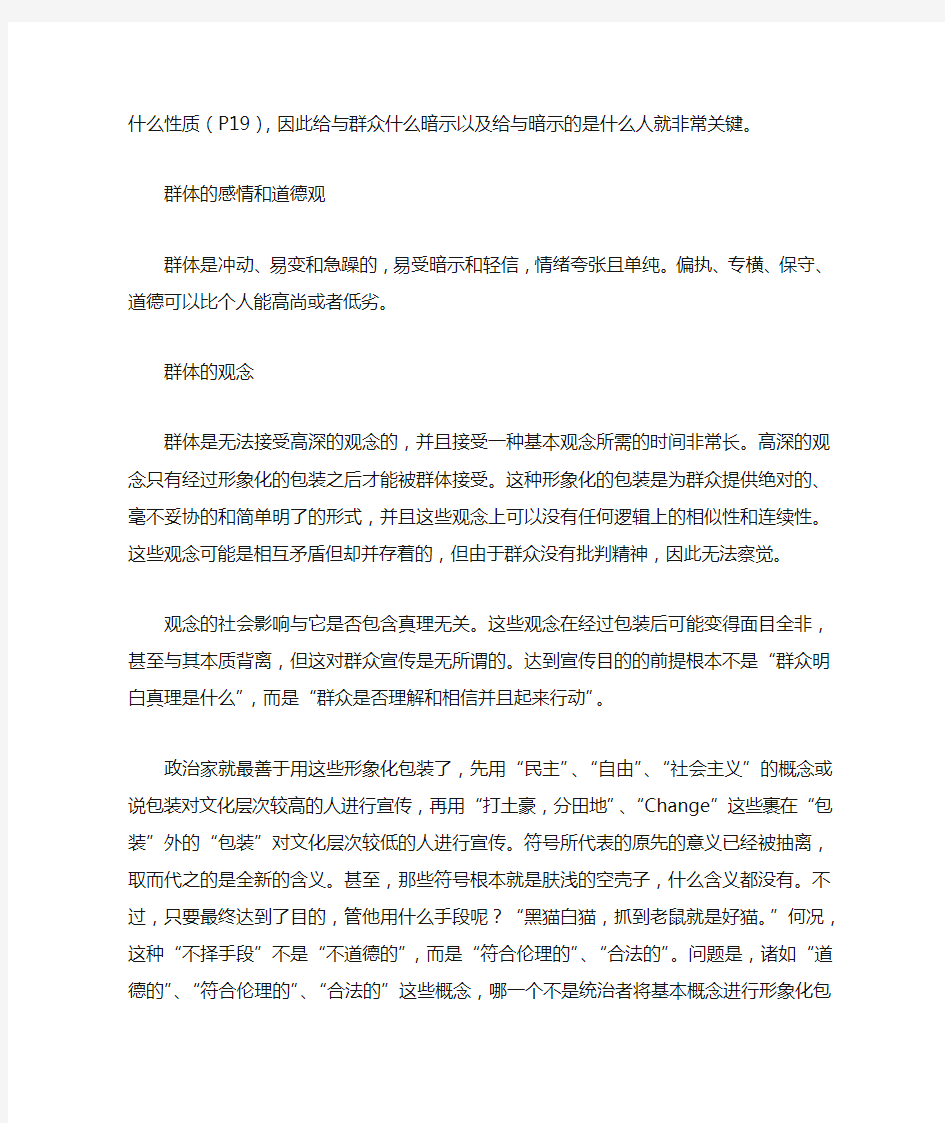
《乌合之众》读后感
一、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三卷(群体心理、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不同群体的分类及特点),依次分析了“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群体的意见”,“群体领袖”等,深入透视了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以及无意识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二、观点整理
群体的一般特征
书中所指的群体是特指心理群体,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探讨组成这个群体的人。群体重感情、轻理智,个人固有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个性消失。群体容易有印象偏差,人数多并不一定有多元的思考角度和结论,可能反而造成单一和盲目。
群体的智商下降,“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P16)。
群体这些新特点形成的原因是:1、群体不必担责任2、传染现象,即从众3、易于接受暗示。
总之,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P19),因此给与群众什么暗示以及给与暗示的是什么人就非常关键。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群体是冲动、易变和急躁的,易受暗示和轻信,情绪夸张且单纯。偏执、专横、保守、道德可以比个人能高尚或者低劣。
群体的观念
群体是无法接受高深的观念的,并且接受一种基本观念所需的时间非常长。高深的观念只有经过形象化的包装之后才能被群体接受。这种形象化的包装是为群众提供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并且这些观念上可以没有任何
逻辑上的相似性和连续性。这些观念可能是相互矛盾但却并存着的,但由于群众没有批判精神,因此无法察觉。
观念的社会影响与它是否包含真理无关。这些观念在经过包装后可能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与其本质背离,但这对群众宣传是无所谓的。达到宣传目的的前提根本不是“群众明白真理是什么”,而是“群众是否理解和相信并且起来行动”。
政治家就最善于用这些形象化包装了,先用“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或说包装对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进行宣传,再用“打土豪,分田地”、“Change”这些裹在“包装”外的“包装”对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进行宣传。符号所代表的原先的意义已经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含义。甚至,那些符号根本就是肤浅的空壳子,什么含义都没有。不过,只要最终达到了目的,管他用什么手段呢?“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何况,这种“不择手段”不是“不道德的”,而是“符合伦理的”、“合法的”。问题是,诸如“道德的”、“符合伦理的”、“合法的”这些概念,哪一个不是统治者将基本概念进行形象化包装后喂食给群众的呢?因此,正是利用了群众缺乏对观念的深入理解、缺乏批判精神,使群众相信观念就成为容易的事。这些观念之间都能互相证明,且不乏循环论证。统治者构建出A和B两种观念,再用a和b的形式对观念进行包装,a能证明b的意义,b亦如此。
群体的理性
群体的理性是很有限的,有些意见轻而易举的就得到认同,其原因就在于群体无法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就听信了他人。群体容易有印象偏差,人数多并不一定有多元的思考角度和结论,可能反而造成单一和盲目。
不过关于这点,有心理学家的研究结论与此正相反。比如James Surowiecki的畅销书《the Wisdom of Crowds》就认为,虽然个体在单独做决策的时候是会有偏差的,但是所有的偏差叠加在一起就是零,也就是说群体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当然前提是大家不会相互讨论以免受影响。我认为对群体理性产生意见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否让群众相互讨论。如果讨论了,那么群体会听信他人,则群体容易产生印象偏差。这就是庞勒所说的。但如果不给相互讨论的机会,虽然各自还是有各自的偏见,但偏见本身是多元的,因此叠加为零。而且庞勒也在后文论述议会,认为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议会是以独立个人的状态呈现,因而保
佑了其理智和智商。可以看出,在群体理性与否的问题上,他所得出的结论跟Surowiecki是一致的。的总之,虽然两位心理学家的结论看似不同,但我认为只是讨论的是一个问题,结论也是不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给不给群众互相讨论的机会。
群体的想象力
群体的想象力很强大,通过形象思维将毫无逻辑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群体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往往关注那些不常发生或者实际影响力一般但是充满戏剧性的的事物。群体的这种丰富而幼稚的想象力是政客们统治他们的基础。
如果不怀好意地来看这本书,或者这类书,会觉得它就是腹黑学。就像书里说的:“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通知他们的艺术。”好在对于群众来说这些书并非禁书,然而又有多少群众承认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盲目性、非理性呢?即使能够意识到,我们能避免吗?然而,意识到群体非理性并非是一种“幸免于难”。非理性、片面性是由好处的。比如选择性记忆就帮助我们迅速过滤信息,被过滤的信息可能对判别是非是很重要的。一旦信息被自动过滤,大脑就用想象力去填补确实的信息,群体非理性就又占了上风。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理性不可呢?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首先,庞勒在这里讨论的主题是群众的宗教感情而非宗教对象。所谓“宗教”是一种泛指,或说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概括群众的信念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因此使用宗教感情来称呼。这种宗教感情可以涉及的对象有上帝、实物、英雄、偶像或是政治观念。它们的名称可以不一样,但本质都是宗教式的。例如,纳粹对希特勒的崇拜,纳粹德国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崇拜,上世纪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现代朝鲜人对朝鲜领导人的崇拜。这种宗教感情是跨国界、跨文化、跨时代的。
虔诚的教徒往往是偏执和妄想的,“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
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P53)。
自是英明的人往往五十步笑百步,一边冷眼旁观和嘲笑他人盲目而狂热的宗教感情,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同样掉入一种或几种宗教感情中去。即使崇拜的对象和信奉的内容不同,形式上是异曲同工的,“比如对想象中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P53)。
崇拜偶像明星的90后们常被人称为“死忠的脑残粉”,带有贬低和嘲笑之意。而信仰某种宗教的人则被称作“虔诚的信徒”。这两者的本质不是一样的吗?或许我们可以将两种称呼互换,便能立马体会到这种宗教感情的异曲同工之妙。
恐怖的政治信仰和邪教组织(例如纳粹主义)为何会受到群众狂热的崇拜呢?其原因与崇拜偶像明星是一样的,归根结底在于崇拜者能从中获得幸福。“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群体意见和信念中的因素
形成群体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有两种因素,一种是间接因素:种族、传统、时间、政治和社会制度和教育。这相当于一种长期洗脑过程,旨在说明这些长期洗脑工具是如何将群众变得、或者维护群众的非理性、低智商的。
譬如,群体是固守传统的,“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并且指出,最狂暴的反叛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P65)”,“支持者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P66)”这种固守陈见的态度使得群众无法接受理论上很好的、通过理性思辨得来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他认为政治和社会制度并非能改进社会的弊端,社会变革的发生是渐进式的,并不是靠一纸文书或暴利革命来实现的。或者说,在实际运用上,没有绝对好和绝对坏的制度,只有适应与不适应、需要与不需要,它的好坏评判是随着时间和民族而变的。
决定群体需要什么制度的是群体的内在性格气质,而非外在制度。“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P65)。”
总之,对的制度总会在必要之时出现,而非来自思辨式的推理。教育会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让本来冷漠的群体变为狂热不满的大军。例如他批评当时法国学校的教育,现在看来是多么贴切目前国内的状况:“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包者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P73)”
另一种是直接因素:形象、词语、套话、幻觉、经验和理性。这些相当于短期的刺激和诱因。比如形象、词语、套话,可以用符号来概括。政治家抽空符号的本意,并视情况赋予其不同的含义,以此激发群体的激情。或者将同样的含义改称不同的符号,以麻痹群体的大脑。而理性与前几者不同,它对群体产生的传播效果很弱。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说法
群体是非常需要一个领袖的,因为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甚至,庞勒毫不留情面地说:“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
将观念植入群众头脑的三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是: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三种方法所塑造的是名望。譬如,没有人敢贬低名望高的艺术品,即使它看起来就
是一对破烂。但名望让这些东西看起来不仅是表面的样子,而是与厚重的历史牵连在一起。名望使我们忽略了事物本身的是否对错之面目,而变得麻木。再比方说,中国上下五千年将一个普通的男人当作天子来崇拜和朝圣,甚至这个男人也将自己当作天之骄子。表面来看不是很荒谬的吗?但臣民们没有对天子的概念进行讨论的权利和意识。他们只需俯首叩拜即可。一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对“断言、重复和传染”最佳的应用案例,给了一个可能乳臭还未干的小伙子至高的名望,好让他来统治自己,好让自己找到奴役的对象。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牢固的信念植根于人们心中。它是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根本,而不是有形的人或某种权力。帝王之所以能够成为暴君能够控制群体,是因为有人相信他具有这样的权力。因此唯一暴力的、支配群体的是这种普遍的、不经思考的信念。普遍的信念虽然荒谬,但不妨碍它得到传播和认可。
“荒谬”是存在主义哲学特别重要的概念。不经思考地尊崇历史、固守信念、遵守规范就体现了荒谬性。按照持这种观点的人来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处处荒谬的世界,因为哪里都有规则,哪里都有固有信念,即使这些人自己也无法摆脱,我们生来就是如此,我们就是被固守观念的人和环境抚养成人的。荒谬性体现在他者身上,更体现于自身。
除了固有信念,群体的意见又多变,易于破碎。
群体的分类
群体按照组成者的特点可分为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异质性群体受种族的影响很大。同质性群体由教育、信念结合起来。但本书探讨的是异质性群体,因此对后者的特点不展开讨论。
罪犯:犯罪群体的特征与一般群体特征很相似,例如易受怂恿、轻信、以便、夸大感情、表现出某种道德等。
我常疑惑,那些残忍的屠杀者,特别是犯罪群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和目的作了如此残忍的事呢?他们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还是明知故犯?按照庞勒的解释,他们是法律上的罪犯,心理上却不是,甚至还自视为为民除害的英雄。因此,他们既凶残又善良。对于朋友或者敌人的敌人,他们表现得像圣上一般,对于敌人他们则是恶魔。
陪审团:陪审团的判断独立于他们的人员成分。只需赢得关键的陪审员的支持,通过他们来影响其它人,那么就能获胜。陪审团作为群体的不理智、情绪化是有好处的,是为了抗衡法官所代表的法律的冷酷、不通融、没有同情心。
选民:正如之前所言,名望是选举获胜的关键。演说靠的是断言、重复和传染。降低群体智商的是群体这种形式,而与组成群体的个体素质并无大关系。因此即使是一帮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做选举,其结果可能与一帮工人一样。
议会:议会的一般特征是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情感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除此之外,还有意见的简单化、极端化,名望加上辩才几乎等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过议会也有其优点,优点既是议会不常成为一个群体,而是大多数情况下以独立个人的状态呈现,因而保佑了其理智和智商。
本书总结
关于文明进化的共同阶段、特点。一个民族的生民循环过程:文明诞生之初,松散的野蛮人聚集起来,群体关系不牢固(乌合之众);松散的小群体形成了有共同特征的、稳固的种族;种族经过情感和思想的统一,形成理想,成为民族。至此,文明达到巅峰,之后又止步不前,开始衰落。民族的理想衰弱,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动摇;个人意识代替种族意识;国家兴起,发挥作用;理想彻底丧失,种族的才华消失,从文明的聚集跌落到原始的乌合之众。
对本书的一些质疑
本书相当于是一篇心理学研究论文的研究结果与讨论部分,研究者的价值
观显露无遗。庞勒单刀直入的批判是我很喜欢的。国内译者将《The Crowd》一致翻译为《乌合之众》我也倒同意,甚至我认为可以翻为“愚众”,即告诉你群众的“愚钝”,与此同时又向有心人说明如何“愚弄”群众。统治者利用群众的乌合和愚钝进行宣传和统治,来愚众。行文之间带有很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庞勒虽然将群体特征揣摩得似乎分毫不差,但似乎是站在统治者的高度俯视群体,实在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
“世上的一切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再说得平庸一点,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是不自觉地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性格有着出自本能但往往十分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对这种性格有正确的了解,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P6)
群体愚钝(包括非理性、无逻辑、感性、歇斯底里等)的作用除了“被统治”之外,并非毫无道理和必要性。试想,如果群众不愚,而是一个个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具有灵魂和头脑的个体,我们的社会就不是现今看到的这样了,也根本不存在“社会”这个概念。
几乎所有学科、流派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认为自己所研究之物是世界发展的推动力。这似乎是所有学科所预设的观念。例如庞勒说:“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P1)。庞勒认为,导致人类思维转型的原因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P2),其次才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庞勒说历史学家只从自然主义的视角研究革命,而非社会心理学,因而他们看不到事件的起源。但正如历史学和其它许多学科一样,在批判另一说法的同时,难免也抬高了自己的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