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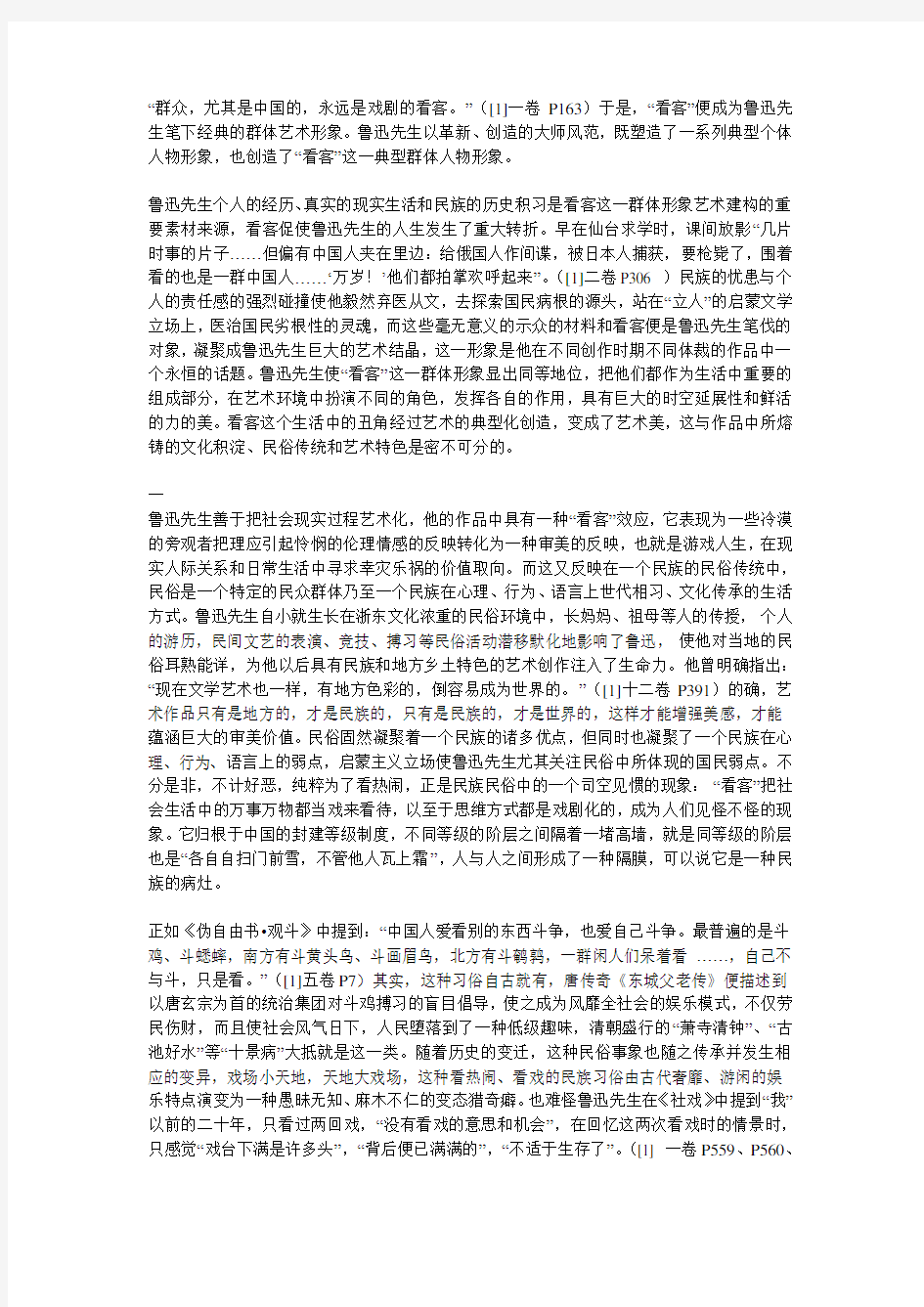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一卷P163)于是,“看客”便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经典的群体艺术形象。鲁迅先生以革新、创造的大师风范,既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个体人物形象,也创造了“看客”这一典型群体人物形象。
鲁迅先生个人的经历、真实的现实生活和民族的历史积习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艺术建构的重要素材来源,看客促使鲁迅先生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早在仙台求学时,课间放影“几片时事的片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间谍,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1]二卷P306 )民族的忧患与个人的责任感的强烈碰撞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的源头,站在“立人”的启蒙文学立场上,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是鲁迅先生笔伐的对象,凝聚成鲁迅先生巨大的艺术结晶,这一形象是他在不同创作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鲁迅先生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显出同等地位,把他们都作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时空延展性和鲜活的力的美。看客这个生活中的丑角经过艺术的典型化创造,变成了艺术美,这与作品中所熔铸的文化积淀、民俗传统和艺术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一
鲁迅先生善于把社会现实过程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看客”效应,它表现为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把理应引起怜悯的伦理情感的反映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反映,也就是游戏人生,在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幸灾乐祸的价值取向。而这又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传统中,民俗是一个特定的民众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世代相习、文化传承的生活方式。鲁迅先生自小就生长在浙东文化浓重的民俗环境中,长妈妈、祖母等人的传授,个人的游历,民间文艺的表演、竞技、搏习等民俗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使他对当地的民俗耳熟能详,为他以后具有民族和地方乡土特色的艺术创作注入了生命力。他曾明确指出:“现在文学艺术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1]十二卷P391)的确,艺术作品只有是地方的,才是民族的,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才能增强美感,才能蕴涵巨大的审美价值。民俗固然凝聚着一个民族的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凝聚了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的弱点,启蒙主义立场使鲁迅先生尤其关注民俗中所体现的国民弱点。不分是非,不计好恶,纯粹为了看热闹,正是民族民俗中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看客”把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当戏来看待,以至于思维方式都是戏剧化的,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它归根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隔着一堵高墙,就是同等级的阶层也是“各自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膜,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的病灶。
正如《伪自由书•观斗》中提到:“中国人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自己斗争。最普遍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呆着看……,自己不与斗,只是看。”([1]五卷P7)其实,这种习俗自古就有,唐传奇《东城父老传》便描述到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斗鸡搏习的盲目倡导,使之成为风靡全社会的娱乐模式,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使社会风气日下,人民堕落到了一种低级趣味,清朝盛行的“萧寺清钟”、“古池好水”等“十景病”大抵就是这一类。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民俗事象也随之传承并发生相应的变异,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种看热闹、看戏的民族习俗由古代奢靡、游闲的娱乐特点演变为一种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变态猎奇癖。也难怪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提到“我”以前的二十年,只看过两回戏,“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在回忆这两次看戏时的情景时,只感觉“戏台下满是许多头”,“背后便已满满的”,“不适于生存了”。([1] 一卷P559、P560、
P561)文章虽以“社戏”为题,却很少着墨于社戏,大多写儿时去看戏和看戏归来途中发生的事情,通过这种对比表达了作者心中美好的童年情结。另外,在《铲共大观》中,他感慨到:“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好几次了。”([1]四卷P106)在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鲁迅先生的眼光往往精锐而独到:“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1]二卷P366)这种在血腥面前游戏人生、玩笑开心的看客群体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在人性上上升到了一个病态的极至,把对象的丑之为丑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正是这些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先生沉默则充实,开口则空虚,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种身患猎奇癖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给予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以特定的代名词:“看客”,使之成为丑的艺术典范,这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社会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美学影响力。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注重个性刻画,同时又注重群体看客形象的描写,他善于在作品中设置一种民俗环境,“除了一般的民俗事象的环境点染……更重要的是作品以人的群体性格作为一个活动背景对某一人物形象的衬托和深化。”([2] P194)这种群体无意识、蒙昧的心理倾向正导致了看客这类畸形群体的出幕,继而把这种集体的情感外化为动作并加以强化,增强了美感的广延度。
例如《祝福》中的鲁镇就是一个极有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小镇,送灶的爆竹、准备的福礼等祝福的仪式为祥林嫂的出场构置了一幅民俗事象图,接着一系列看客的出现为祥林嫂哭诉阿毛的悲惨遭遇增添了些许气氛,然而这种场景让读者感觉到的只是浓重的黑暗。当祥林嫂直着眼睛、不厌其烦地和大家哭诉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时,“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的话,便特意来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走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1]二卷P17、P20)男人的没趣,女人陪出的眼泪,老女人的好奇都归结到一点上:满足,然而这些赚来的眼泪只能是奴性肉体的暂时释放,满足之后又发生了新的趣味:揭别人的“伤疤”。《示众》以淡化情节、截取横断面的手法将看客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中展示下的人物性格显得丰富、饱满。犯人立在马路上示众,刹时间围满了大半圈看客,继而被围了好几层,秃头研究着白背心上的文字,胖孩子看着白背心研究发亮的秃头,飞来的小学生看着红鼻子胖大汉,还有长子、瘦子、老妈子、巡警等人的窥视透现出整个国民灵魂的示众。精神的空虚、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这些人精神上的无意识、麻木,行为上的扭曲。这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手法,突出了人本环境这一表现民俗特色的载体,并且一针见血地体现出这个时代、地区、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病根。
马克思说过:“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3]一卷P47)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个人,一个人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和他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这种互相牵制的人本环境使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成为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的重大课题,民俗的建构正好为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为人生意蕴的追寻开辟了一条路径,具有美的文化底蕴。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描述:“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探头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