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_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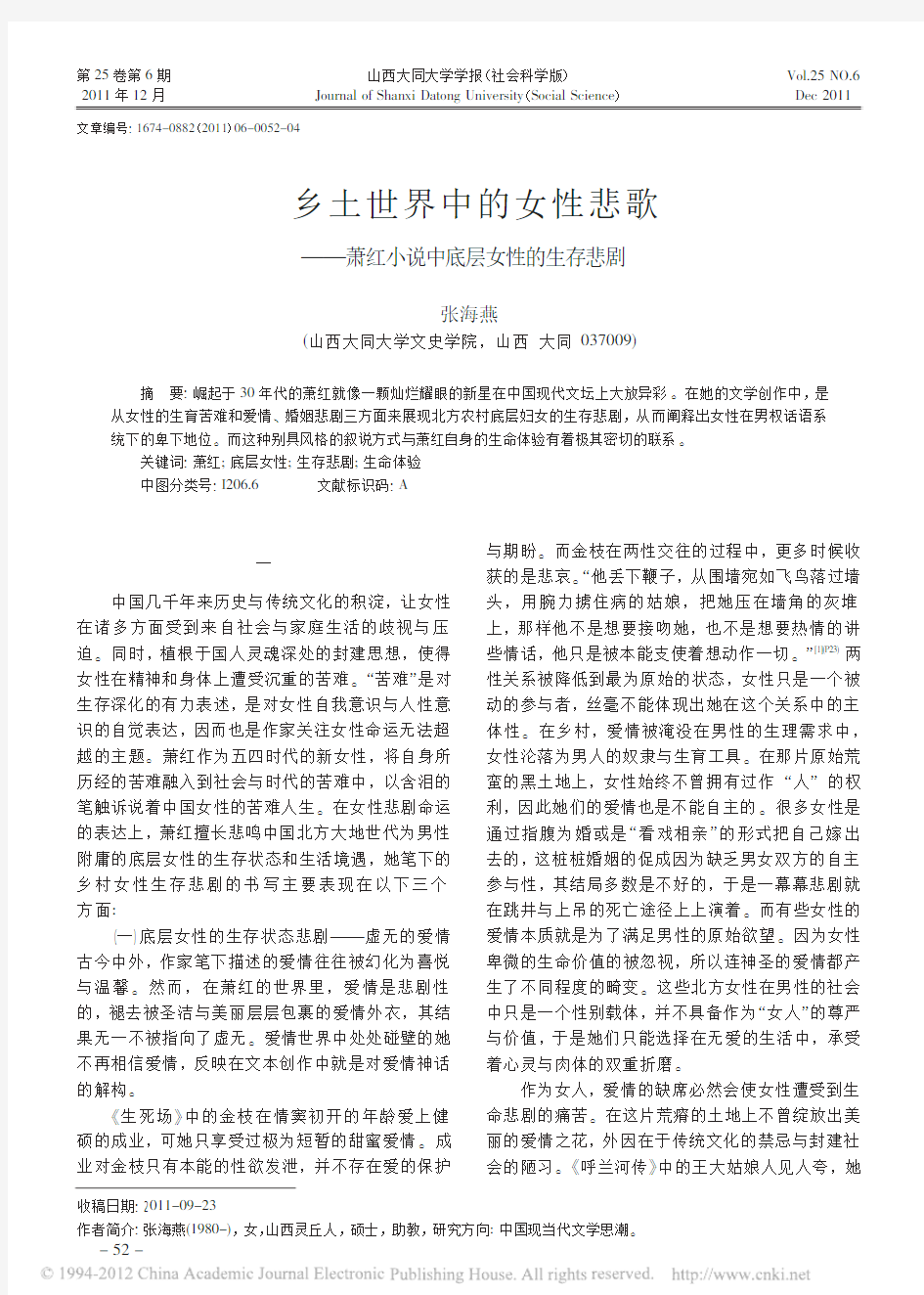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乡土世界中的女性悲歌
———萧红小说中底层女性的生存悲剧
张海燕
(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摘
要:崛起于30年代的萧红就像一颗灿烂耀眼的新星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大放异彩。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是
从女性的生育苦难和爱情、婚姻悲剧三方面来展现北方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悲剧,从而阐释出女性在男权话语系统下的卑下地位。而这种别具风格的叙说方式与萧红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萧红;底层女性;生存悲剧;生命体验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09-23
作者简介:张海燕(1980-),女,山西灵丘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第25卷第6期2011年12月
Vol.25NO.6
Dec 2011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文章编号:1674-0882(2011)06-0052-04
一
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积淀,让女性
在诸多方面受到来自社会与家庭生活的歧视与压迫。同时,植根于国人灵魂深处的封建思想,使得女性在精神和身体上遭受沉重的苦难。“苦难”是对生存深化的有力表述,是对女性自我意识与人性意识的自觉表达,因而也是作家关注女性命运无法超越的主题。萧红作为五四时代的新女性,将自身所历经的苦难融入到社会与时代的苦难中,以含泪的笔触诉说着中国女性的苦难人生。在女性悲剧命运的表达上,萧红擅长悲鸣中国北方大地世代为男性附庸的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她笔下的乡村女性生存悲剧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悲剧———虚无的爱情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描述的爱情往往被幻化为喜悦与温馨。然而,在萧红的世界里,爱情是悲剧性的,褪去被圣洁与美丽层层包裹的爱情外衣,其结果无一不被指向了虚无。爱情世界中处处碰壁的她不再相信爱情,反映在文本创作中就是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生死场》中的金枝在情窦初开的年龄爱上健硕的成业,可她只享受过极为短暂的甜蜜爱情。成业对金枝只有本能的性欲发泄,并不存在爱的保护
与期盼。而金枝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更多时候收
获的是悲哀。“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
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1](P23)
两性关系被降低到最为原始的状态,女性只是一个被
动的参与者,丝毫不能体现出她在这个关系中的主体性。在乡村,爱情被淹没在男性的生理需求中,女性沦落为男人的奴隶与生育工具。在那片原始荒蛮的黑土地上,女性始终不曾拥有过作“人”的权利,因此她们的爱情也是不能自主的。很多女性是通过指腹为婚或是“看戏相亲”的形式把自己嫁出去的,这桩桩婚姻的促成因为缺乏男女双方的自主参与性,其结局多数是不好的,于是一幕幕悲剧就在跳井与上吊的死亡途径上上演着。而有些女性的爱情本质就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原始欲望。因为女性卑微的生命价值的被忽视,所以连神圣的爱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这些北方女性在男性的社会中只是一个性别载体,并不具备作为“女人”的尊严与价值,于是她们只能选择在无爱的生活中,承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作为女人,爱情的缺席必然会使女性遭受到生命悲剧的痛苦。在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不曾绽放出美丽的爱情之花,外因在于传统文化的禁忌与封建社
会的陋习。
《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人见人夸,她52--
在前边走后边都有人指指划划地赞美她,甚至连大户人家都愿意将她娶进家门。但是自从她与磨棺冯歪嘴子因爱结合后,她以前所有的优点瞬间被贬斥得一无是处,她成了众人攻击与唾弃的对象,就因为王大姑娘违背了呼兰河小城人们日常奉行的“规矩”。这对夫妻不仅被全院人孤立,甚至还要承受着世俗舆论的指责。他们的私自结合,被房东是看作是“破了风水”,于是在寒冷的冬天将其一家赶出了冰冷的碾磨房。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与贫困交加中,王大姑娘带着牵挂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以上两个作品表现的都是无爱的女性生命悲剧。萧红正是通过情爱缺失造成的女性悲剧命运对男性权威进行消解。萧红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爱情模式,偏向于抒发浓重的虚无情绪。她笔下的女性,爱情还只是朦胧状态时就被男性无情的扼杀了。在崇尚男权为主的社会里,女性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役用的工具,而最令人痛彻心扉的是她们在骨子里就没有任何独立的自我意识。感慨两性关系无真爱的苍凉,是萧红对爱的虚无的呐喊。
(二)底层女性的生活境遇悲剧——
—灰色的婚姻萧红笔下所创造的爱情是缺席的,弥漫着浓厚的虚无情绪,自然以“爱”为前提的婚姻的结合就只能呈现出灰色的情调,这些底层女性困守在婚姻的围城中难以解脱。在萧红的文本中,女性婚姻毫无美感可言,其实质只是一场原始的肉欲婚姻。如若男女双方在青年时还留有一些恋爱的甜蜜,一旦进入到婚姻状态中女人就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昔日的温存烟消云散。男人不再将女人放在心底,在他们的眼中女人只是一个接受打骂,生理发泄的一个物件。
《生死场》中的成业婶婶,在婚前与丈夫有过短暂的爱情甜蜜,然而婚后她的爱的付出却连丈夫的笑脸都换不回。“女人过去拉著福发的臂,去抚媚他。但是没有动,她感到男人的笑脸不是从前的笑脸,她心中被他无数生气的面孔充塞住,她没有动,她笑一下赶忙又把笑脸收了回去。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男人叫把酒杯拿过去,女人听了这话,听了命令一般把杯子拿给他。于是丈夫也昏沉的睡在炕上。”[1](P19)这就是乡村女性的婚姻现状。丈夫漠视妻子的一腔爱意,在每天朝夕相处的生活中,妻子扮演的角色不是爱人,是保姆,是物件抑或是生育的工具。如果说成业婶婶的精神是因为婚姻而变成灰色的话,那温柔美丽的月英则因为婚姻而凋零。婚后的她因为一场病不能再生育了,而她的生命意义也就基本上终止了。残忍的夫家将气息奄奄的她用冰冷的砖头围起来,任其自生自灭。在男权话语下系统下,女人的生存价值就是传宗接代,一旦失去了这个层面的意义,女性就只有生命的终结了。
在这群悲惨的女性中,有一个孩童的面孔令人难忘,她就是小团圆媳妇。年仅12岁,就过早地走进婚姻,至此开始的是她梦魇般的悲惨生活。刚踏进夫家的大门,婆婆就虐待了她一个月。天真的少女经不起这恶梦般的折磨,已然气息奄奄了。婆家人于是开始了给她治病的“漫漫征程”。“热心”婆婆们烧了一大缸的沸腾状的热水,把被扒光衣服的小团圆媳妇死命般的按在水中,“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不一会儿,浇得满脸通红,她再也不能够挣扎了,她安稳地在大缸边站着,她再也不往外边跳了,大概她觉得跳也跳不出来了”。[1](P164)“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花季少女就这样生生地被折磨死了。小团圆媳妇“热闹”般地离开人世的文本意义在于:男性在婚姻中固然是摧残女性的刽子手,而那些年长女性将自己遭受过的生命苦难施加于年轻女性,这更是女性社会群体存在的莫大悲哀。
对婚姻的描述,萧红选择了灰色的基调,并且她对造成女性婚姻苦涩的男性进行了贬斥和虚化。她是满怀愤慨在叙述着男性形象,这些人把自身所享有的原始性别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一边在欺辱弱小女性,一边却被生活、命运所欺辱,而他们的人生也是沉重的,人性是缺憾的。萧红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她们“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可叹的是,男性以及女性自我人格的缺失是把她们推向如此沉重生存境遇的罪魁祸首。总之,萧红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和婚姻的神话,她笔下的爱情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浪漫,夫妻之间没有举案齐眉的温馨,有的只是爱情的缺席与婚姻的晦暗,在文本的苍凉底蕴中折射出作家灵魂深处的人道主义光芒。
(三)底层女性的生存价值悲剧——
—苦难的生育女性生育本来是一次繁衍人类的伟大创造,而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亦是通过生育体现出来的。然而在萧红的笔下,贫苦的农妇们将生育视作是苦难人生中的巨大痛苦与灾难。面临如同死亡般的生产,她们的生存价值已经贬低为生不如死。麻面婆在生产
5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