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命运
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

毕业论文--------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生得挣扎,死的抗争--------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莫延福【内容提要】现代女作家萧红,关注妇女问题,在其小说中,塑造了王阿嫂、黄子良、翠姨、长青妈、王大姑娘、王婆等一系列女性形象,描写了她们的屈辱与挣扎,觉醒与抗争,本文通过萧红这些形象的分析,归纳了这些形象的两种类型,分析了这些形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作家塑造这些形象的社会形象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生,死,挣扎,抗争生得挣扎,死的抗争--------试论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人,现代著名女作家。
代表作品中篇小说《生死场》,短篇小说《小城三月》。
萧红是30年代出现在我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其作品主要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描写农村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幸与抗争。
萧红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又一度被软禁在农村叔伯们的家里,这使她耳闻目睹了不少地主剥削、欺压农民的血泪斑斑的罪恶。
萧红对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和不幸,有着特别的关注,她自从19岁逃离家后,屡遭坎坷、历经磨难,从而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独到而深刻的体验,因此,对农村下层劳动妇女的痛苦与不幸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并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妇女生活的优秀作品。
(一)萧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认识是深刻的。
1938年,她曾联系自己的身世对聂绀驽说:“……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的,倒是怯懦,是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自甘牺牲的惰性。
”这是女作家萧红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和不幸之后,经过深沉的而又不无忧伤的历史反思,对妇女问题所作的深刻剖白,它不仅反映了天才女作家同旧世界抗争的独特的生活历程,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妇女不甘奴役的反抗精神。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和作为女性作家的历史使命感,萧红才蘸着自己的血泪,以“女性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着力表现东北沦陷后的劳动妇女“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生动、形象,令人颤栗的妇女形象。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她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题,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悲剧遭遇。
本文将以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为探讨主题,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芳草地》三篇作品入手,分析其中女性角色的遭遇和她们的悲剧意识。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遭遇,展现出她的无助和无言。
小说开头,女主人公阿红被绑在牛车上进城卖身,她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选择和反抗的权力,只能默默承受着命运的安排。
阿红的婚姻也是一个悲剧,她没有选择的嫁给了一个无能的男人,并为此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
阿红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她一直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最终死于饥饿。
通过描写这些女性角色的遭遇,萧红展现了她们的悲剧意识,她们在社会中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任凭命运摆布。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萧红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通过比较两位女主人公的遭遇,揭示出女性在家庭中的悲剧地位。
红玫瑰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她在传统家庭中无法被接受,最终选择了自杀。
而白玫瑰则是一个传统女性的代表,她按照社会的期望选择了婚姻,但最终却陷入了婚姻的苦闷之中。
通过对这两位女性角色的描写,萧红展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被束缚和被压迫,她们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对自由、对个人追求的渴望和无力实现的无奈之中。
《芳草地》是萧红的一篇自传体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自述,展现了她在农村生活中的苦闷和悲凉。
女主人公身负家庭的重任,需要照顾残疾的父亲和弟弟,她没有时间和精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一个没有知识和文化的环境中,女主人公无法得到解脱,她的生活被彻底消磨殆尽。
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生活,萧红揭示了女性在农村社会中的悲剧命运,她们无法摆脱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只能在苦闷和无助中度过一生。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和探讨。
通过对女性角色的遭遇和内心情感的描写,萧红反映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和悲剧遭遇。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精神扭曲为特色,其中女性的悲剧意识也是她作品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面对着家庭、社会和历史的压迫,身份低下,地位微弱,被迫经常处于表面平静却内心激烈的状态中。
她们不仅遭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侵犯,还要承受着生命的苦难和悲愤。
其次,萧红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她们的命运中。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女主角白玫瑰本来是个有头之辈,但她因为家庭原因,嫁给了一个不喜欢的男人。
为了不让自己的婚姻破裂,她不得不奉献自己,染上了性病,最终背负着绝症走向死亡。
同时,在这部小说中,萧红还通过描写她的姐姐红玫瑰,表现了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处境的悲剧。
红玫瑰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娘子,以求得自由和幸福,但最终却成为了别人的卖花女,也说明了女性在社会环境中面临的难以改变的命运。
最后,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她们的爱情中。
在《呐喊》中,萧红通过三重叙述的方式,描写了一个名叫刘秀云的女子最终遭受精神疯狂,爱情的崩塌。
而在《凤凰池》中,又写出了男女主角在一起后,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摩擦和矛盾,最终他们的爱情也走向破碎的结局。
这些作品表现了女性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彷徨和悲哀,她们不仅仅要承担家庭的责任,还要面对爱的困难和挫折。
综上所述,萧红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意识一直是她研究的重要课题。
她通过深入挖掘女性的命运,生动地描绘了她们的苦难和痛苦,对于探究中国现代女性的文学历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女性权利的关注和思考,是一种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探讨。
浅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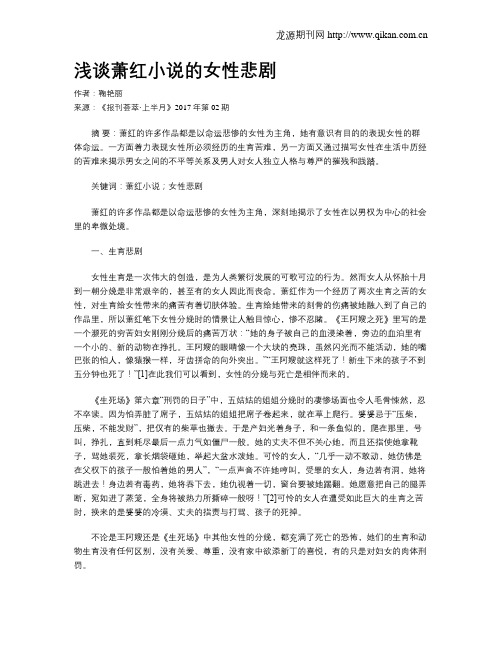
浅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悲剧作者:鞠艳丽来源:《报刊荟萃·上半月》2017年第02期摘要:萧红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命运悲惨的女性为主角,她有意识有目的的表现女性的群体命运。
一方面着力表现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另一方面又通过描写女性在生活中历经的苦难来揭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女人独立人格与尊严的摧残和践踏。
关键词:萧红小说;女性悲剧萧红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命运悲惨的女性为主角,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微处境。
一、生育悲剧女性生育是一次伟大的创造,是为人类繁衍发展的可歌可泣的行为。
然而女人从怀胎十月到一朝分娩是非常艰辛的,甚至有的女人因此而丧命。
萧红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次生育之苦的女性,对生育给女性带来的痛苦有着切肤体验。
生育给她带来的刻骨的伤痛被她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里,所以萧红笔下女性分娩时的情景让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王阿嫂之死》里写的是一个濒死的穷苦妇女刚刚分娩后的痛苦万状:“她的身子被自己的血浸染着,旁边的血泊里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巴张的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的向外突出。
”“王阿嫂就这样死了!新生下来的孩子不到五分钟也死了!”[1]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分娩与死亡是相伴而来的。
《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五姑姑的姐姐分娩时的凄惨场面也令人毛骨悚然,忍不卒读。
因为怕弄脏了席子,五姑姑的姐姐把席子卷起来,就在草上爬行。
婆婆忌于“压柴,压柴,不能发财”,把仅有的柴草也撤去。
于是产妇光着身子,和一条鱼似的,爬在那里,号叫,挣扎,直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如僵尸一般。
她的丈夫不但不关心她,而且还指使她拿靴子,骂她装死,拿长烟袋砸她,举起大盆水泼她。
可怜的女人,“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
沉寂的女性悲歌_论萧红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

文学评论萧红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著名女作家,在她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许多风格独特、意蕴丰富的作品。
尤其是笔下的女性形象最为人所称道,尽管形象各异,但基本上离不开一个凄惨的的结局。
而这些具有震撼力的悲剧形象与萧红那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里是息息相关的。
她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女性为视角的,始终关注着中国广大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触及到当时中国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被视做“异类”的女性叔本华曾说过,“别人看待我们范围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这包括我们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再加上由此而激起的种种思想。
”如果将整个社会比做轮子的话,那些靠近轮子轴心的则是强势的社会群体,对于处在轮子边缘,遭受了不幸命运的人,不是同情、悲悯,而是将承受命运的人残酷的、错误地认定为厄运的本身,将自己对不幸的恐惧与厌恶发泄到不幸的人身上,从玩赏别人的痛苦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快感。
《手》中的王亚明不辞辛苦地来到城里求学,这是一个努力地改变自身命运的励志型女性,尽管勤奋苦读,但因基础有限,家境贫寒,再加上那双因帮手工染坊的父亲干活而染成的“又蓝又黑又紫”的手,受到了师生的排斥。
因对这双手的害怕和恐惧,竟没人愿意和她同铺睡,以致寒冬腊月还不得不睡在过道的长椅上,“怪物”,原来还只是根深蒂固在他人的意识中,现在也开始斑斑驳驳地投影在她那日渐脆弱的心上了。
如果说《手》中的王亚明是因为那双显而易见的肮脏的黑手成为相对社会群体的“异类”的话 ,那么《呼兰河传》的小团圆媳妇则是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
便将小团圆媳妇判作“异类”,一步步被异化的过程。
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们永远也不会消失。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戏;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戏”。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从女性视角解读萧红_生死场_中的女性悲剧

22-167CN14-1034/IMZXS4/2008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涌入中国,为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它通常采用带有解构意味的分析方法,强调叙事者的主体性,从性别角度评价文学作品,涉及到叙事者主体位置与笔下人物关系,以及叙事者在叙述时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角度、方式等。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其小说《生死场》,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
如果立意从性别角度切入对萧红作品《生死场》展开思考,分析萧红作品女性的独特认识,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女性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这样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悲剧。
一、从女性话语的视角,解读女性的生命苦难“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会因女作家和男作家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①。
由于男性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男性用男性话语解读女性、书写女性,女性也模仿男权话语自我解读、自我书写,从男权文化大门走出去的,是被扭曲了的“男人眼中的女人”和“男人化的女人”。
要打破这一文化格局,女性必须“逆流而上”站在女性视角用独特的女性话语进行真正的“自主选择”、“自我照型”,自己撩开隐蔽世界的重重帷幕,展现自己。
而这一过程中,女性最先可以依靠和建构的便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身体上的真实感受。
法国女权主义者海伦娜·西索提倡“白色墨汁”来写作,“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②。
由于处于男权文化压制下的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
写作使妇女超脱自我结构,回到未经男权制文化扭曲的起初的自我。
在男权制的文化下,只有这些可以逃脱男性文化,摆脱女性被审美、被想象的“他者”处境,这才是真正的从女性视角来透视女性形象。
《生死场》中的王婆自杀未遂时可怖的身体毁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地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之后遭丈夫的折磨而死,此外,从未出现的女性体验作为书写视角在历史中浮现。
论萧红作品中的悲剧意识.d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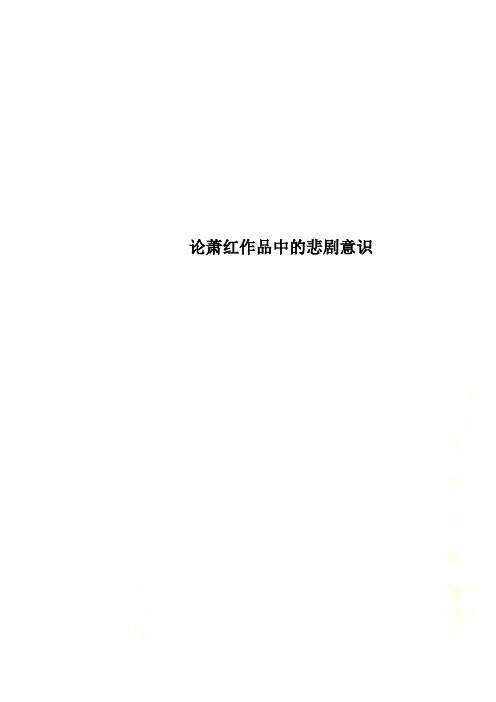
论萧红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论萧红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摘要: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极富才华和个性的现代女作家。
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说蕴涵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
特别是她的那些触及女性生育和死亡的作品,更是被女性主义艺术奉为女性表达女性性别的经典。
萧红始终把关注和表现的目光放在处于苦难下层劳动妇女的悲剧命运上。
另一方面,揭示女性的隐秘世界尤其是女性生育苦难,萧红也把关注的视野投向女性这一群体,使小说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悲剧意识。
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文本中的悲剧意识及对女性隐秘世界的揭示,来寻求萧红作品中悲剧意识产生的原由,并进而站在女性的立场感悟更为隐秘、更为女性的身体世界、生命世界、情感世界。
最终目的是为了唤起社会对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
关键词:萧红悲剧意识小说创作女性隐秘世界Abstract: Xiao Hong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very talented writer and modern personality. Her works, especially novels contain a sense of deep tragedy. Especially those touched her birth and death of women's work, but also by women as the feminist art of the classic expression of female sex. Xiao Hong's always shown concern and attention on the plight of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of working women in the tragic fate of the. On the other hand, by women reveals the hidden world of women in particular, to reveal the suffering of birth, the Xiao Hong is also the concern of this group of women into the fieldof vision so that a novel filled with strong awareness of the tragedy .Aimed a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agic sense of the text and the world reveals the secret to women, to seek the tragedy of Xiao Hong's works have a sense of reason, and thus the position of women standing on sentiment more secretive, more women's physical world, the lives of the world, emotional world. The ultimate aim is to arou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dignity of women attention.key words: Tragic Sense Fiction Hidden word of women最深切的是她鲜明独特的女性悲剧意识。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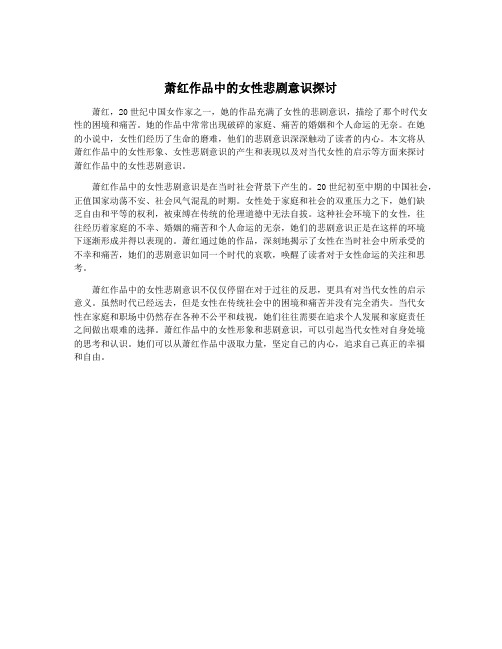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探讨
萧红,20世纪中国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充满了女性的悲剧意识,描绘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困境和痛苦。
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破碎的家庭、痛苦的婚姻和个人命运的无奈。
在她
的小说中,女性们经历了生命的磨难,他们的悲剧意识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内心。
本文将从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女性悲剧意识的产生和表现以及对当代女性的启示等方面来探讨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20世纪初至中期的中国社会,正值国家动荡不安、社会风气混乱的时期。
女性处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下,她们缺
乏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被束缚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无法自拔。
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女性,往
往经历着家庭的不幸、婚姻的痛苦和个人命运的无奈,她们的悲剧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下逐渐形成并得以表现的。
萧红通过她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承受的
不幸和痛苦,她们的悲剧意识如同一个时代的哀歌,唤醒了读者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不仅仅停留在对于过往的反思,更具有对当代女性的启示
意义。
虽然时代已经远去,但是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困境和痛苦并没有完全消失。
当代女
性在家庭和职场中仍然存在各种不公平和歧视,她们往往需要在追求个人发展和家庭责任
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悲剧意识,可以引起当代女性对自身处境
的思考和认识。
她们可以从萧红作品中汲取力量,坚定自己的内心,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
和自由。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女性生命的悲歌——论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命运引言萧红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受伤害、被遗弃的过程,尽管她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可是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为她提供一个相应的精神家园。
她是在可疑的、阴冷的家庭中长大起来的,被侮辱与损害的恶境中孤零地挣扎过来的。
童年的萧红是寂寞而又孤独的,父母仅仅因为她是女儿便对她轻视和无视,,女儿作为一种自然性别注定了萧红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也注定了她一生被封建父权专制放逐的悲剧命运。
“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1](P257)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才华的女作家——萧红在她的作品中发出的慨叹。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和痛苦。
其曲折痛苦的独特生活经历,决定并影响着她的视野和审美态度。
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观照社会世态,抒写了一部女性的悲歌,上演了一幕生命的悲剧。
这种体现生命悲凉的意蕴贯穿其作品的全部,形成其独特的艺术世界,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占一隅。
“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而萧红又是女人中的格外不幸者。
短短的三十一年的生涯倍受女性的种种劫难。
作为女儿,事与愿违的出生背叛了家庭对男嗣的期待,成了一个性别原罪,从小缺少父母的抚爱,因抗拒包办婚姻被视为“异己”、“不肖”、“忤逆”,被父亲开除了祖籍,放逐家门外;作为妻子,她即使做了再多的自我牺牲,再怎么隐忍退让,也得不到认可,落个“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妻子”(萧军语)的评断;作为母亲,她经历了两次十月怀胎,但两次刑罚般的分娩都没能给她带来些许初为人母的激动与欣悦。
被汪恩甲欺骗所生的女婴源于无爱迫于生活送人,与萧军所生的男婴产后即不幸早夭。
萧红,一个被视为“不肖女儿”“不合格妻子”又做不得母亲的不幸女人,仅为想做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女人的信仰被世俗的父权专制和男性偏见打得个“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
”,年仅31岁客死香江,临终前无力地道出“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这样沉痛的肺腑之言。
对萧红来说,由于作家本人的那些痛苦的、悲剧性的人生经历,融进了并决定着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对女性悲凉人生的沉思。
“萧红是带着沉重的人生枷锁走上文坛的,她短暂的一生‘尽遭白眼冷遇’”。
[2](P103)作为女人,萧红是不幸的,作为女作家,萧红又是幸运的。
不幸的个人身世成了她关注农村妇女现实生活和当下命运的悲剧起点,凄凉落寞的个体经验成了她创作的生命底色,敏感细腻的“越轨笔致”使她不滞留于悄吟个人哀怨,而是基于对人性的关怀和性别自我沉思,为我们描绘了旧中国有着酸苦命运的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
一、女性苦难命运的图景在萧红短短的31年生命历程中,和她性别相对的“男人”,是她生活的重心,也是她人生灾难和悲剧的制造者。
可以说“她亲身感受和体验了一个女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生存痛苦与不幸,她对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人的所有冷漠、轻视、摧残、迫害与不公有着深刻的身心体验。
”[3]幼年的她,因为是女孩子的缘故,受尽家人的冷眼和虐待。
祖母曾用针刺过她,母亲也不喜欢她,父亲对她则是贪婪而没有人性的。
孤独寂寞的她从小就体验到女性的不幸和男权的可怕。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小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
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4](P242)上中学时父亲武断地给她定下一门婚事,迫使她离家出走,更让她生出对父权制社会的不满。
萧红如娜拉般勇敢地走出父亲的家园,等待着她的却是男性的伤害、爱情的失落和抗争的失败。
不断积淀的性别苦难促成了萧红女性意识的产生,驱使她始终以女性视角和女性体验为切入点来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女性艰难的生存真相,为这些挣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女人们发出愤怒的呐喊和反抗。
坎坷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萧红选择广大底层女性为书写对象,她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寡妇、农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
她们不仅面临着和男人一致的社会危难和贫困饥饿等多重攻击,更要承受男权的压迫与折磨。
萧红用她那明丽细致的女性笔触描摹了一幅又一幅悲惨血腥的女性生命景观图。
有过两次生育经历却未曾感受过母性之乐的萧红基于切身体验对男性一向歌咏的生育话题加以质疑,以往笼罩着美丽光环的生育在萧红这里呈现血腥和残忍的一面。
萧红常常将生育和死亡连在一起,生是非人的生,死是非人的死,孩子的生日在年轻产妇的身上很快会变成自己的忌日。
萧红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述说的便是底层妇女王阿嫂在遭受张地主的一脚狠踢后难产而死的故事。
《生死场》中萧红更是触目惊心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毫无价值的生育和死亡:金枝在丈夫欲望的动作中难产了;麻面婆大喊着要剖开自己的肚子;李二婶濒临死亡的绝境;五姑姑的姐姐被难产折磨得痛苦不堪,醉酒的丈夫却喝令她拿这拿那,将长烟袋投向她,把一大盆冷水泼在她身上。
女性的生育在这里变成了“刑罚的日子”,“她们和动物们一起忙着生产”,“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而“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5] (P32)生命的诞生失却了以往的伟大和幸福,呈现出非人性和动物性。
而作为人类的女性在生育时除了饱尝动物般的生育之苦外,还要承受男人的指责和打骂,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女人们仍逃脱不了男性的欺压和凌辱。
在传统社会和文化体制中,女性只是男性价值的证明,是性的符号和工具,女性的自我价值是完全缺席的。
萧红以冷静犀利的笔触给我们展现了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非人生活,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冷漠和残忍,为浸泡在血泪之中的女人们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一)情感爱情,是男女双方共同拥有的美好情感。
但因为男性在生活中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中国千百年来父权专制对爱情的偏见,使得爱情的主动权往往落在男人手中。
女人即使有爱,也常常不敢开口。
唯有这样,才不被视为出格,越轨,对得住男权偏见下所规范的那份矜持与操守。
爱醒了,却无路可走。
萧红通过笔下的农村女性对这一永恒的文学主题提出质疑,写出她们在爱情的泥泞上艰苦的跋涉。
《生死场》中金枝与成业这对乡村青年男女开始是相爱的,然而两人的爱的指向有着截然的不同,在对他们情爱的表现中更多的是性的欲求。
在《生死场》中第二节描写了金枝与成业的相爱。
在摘柿子的金枝听到成业唤她的口哨声,便找了借口循声而去。
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着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吸引的铁跟住了磁石。
静静地河湾有水湿的气味,男人等在那里。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跨压在那里。
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
尽量地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
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这一切都在叙述人看似客观、实际上处于女性立场的审视中。
姑娘被形容为“小鸡”,而男人被直接指称为“野兽”。
作者笔下,两人都有“非人”性,都是被性欲所左右的动物,和自然界的其它生物没有区别。
男人在女人面前象野兽一样释放他的生命力,雄壮、粗野、充满破坏性,使性变得丑陋可怕,使爱在丑陋可怕的性面前隐逸。
男人眼中的女人形象只是满足他性欲的客体,是“物”。
成业一点也不关心金枝的身体以及因为怀孕将要面临的羞辱。
当他再次遇到姑娘时,他仍然“受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金枝给他看已隆起的肚子。
“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性的欲求实际上在此意味着对爱的否定。
同时也说明被仅视为一具“肉体”或“白的死尸”的女人是无法言说的,是被动和沉默的。
他们之间只有“无爱的性”。
两人的命运发展也是如此。
成业娶回金枝后,象所有男人一样压迫和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妻子。
而金枝对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命运也充满了仇恨和厌倦。
“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
”到后来,在生活艰难的压力和烦恼中,一怒之下的成业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小金枝摔死。
作者将叙写小金枝死的一节称为“罪恶的五月节”,这罪恶产生的根源从表面看是贫穷饥饿造成的。
但忙忙碌碌的生、惨酷无名的死中,悲哀的根源仍是生死场中的人们思想的蒙昧。
金枝的命运实际上就是生死场中农村妇女们整体的悲剧命运写照。
在《生死场》中,萧红借情爱叙事表明农村的底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爱关系实质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所以金枝在绝望中说过那句话“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实际上金枝恨的是这种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伦理文化造成的男权意识,是它造就了中国男人的专制和暴虐,造就了金枝似的中国女人的苦难和牺牲。
同时我们从萧红在《生死场》中的情爱叙事中也感到作者十分明显的对性欲所持的否定立场和畏惧心理,也许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作者以另一种与之全然相反的极端方式来描述和表现“真爱”,前者是野蛮、粗暴的,后者却温婉、忧伤的。
萧红笔下的情爱表达还有一特点:爱是单方面的,爱总是无望的,爱是一种无法被理解和珍惜的珍贵情感。
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小城三月》)。
“我”的堂哥虽然喜欢翠姨,但并不理解翠姨这种爱的意义,爱的深度。
他和“大家”一样与翠姨的心灵隔膜着。
只有翠姨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爱总是以悲剧告终,以沉默告终,以孤独告终。
作者既表现了对爱的憧憬和期待,又表现了对爱可实现的否定。
在爱中的翠姨受到来自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双重压抑,我们从叙述人的平静、似懂非懂的少女叙述当中,可感觉到翠姨对爱情的强烈压抑,以至于郁郁寡欢最后得病而死,以病来拒绝世俗强加的婚姻,以死来殉自己的爱。
爱本身是生命力、生命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翠姨这种对生命力的压抑有一种惊人的悲剧效果,同时翠姨以死来表明对封建伦理文化强加的命运的拒绝,这种拒绝姿态又是女性不屈的弱者式反抗。
《小城三月》是典型的女性叙事,作者所站的女性立场虽然不象以往那样为女性的牺牲而激越控诉,而是温婉平静,但所产生的人性震撼却更有力,更无处不在,文本所具有的审美内涵更丰富。
翠姨可以看作是作者自我内心的投射,是作者对情爱理念进行诠释的符号。
《朦胧的期待》中的李妈一厢情愿地单恋主人家的卫兵金立之,纯朴憨直的她刻骨铭心地忧郁着梦中情人的未归,过大年似的喜迎梦中情人的归来,但就在一转眼为梦中情人买烟的工夫却换得金立之的不辞而别,只能在自己虚拟的幻影中作朦胧的期待。
爱醒了,不敢开口的翠姨悒郁而终;来不及开口的李妈只能痴痴地傻等。
从叙事层面来看它是以仆人李妈对主人家的卫兵金立之具有的朦胧的爱情期待为叙事线索,但在深层意蕴上这种期待不仅仅指向爱和爱的对象金立之,而是指向人生及人生中种种不确定而又渴望去把握的实在。
作者以自身女性的经验来表达李妈的心灵世界,质询一个女性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作为个体而言人生愿望落空的那种荒凉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