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文史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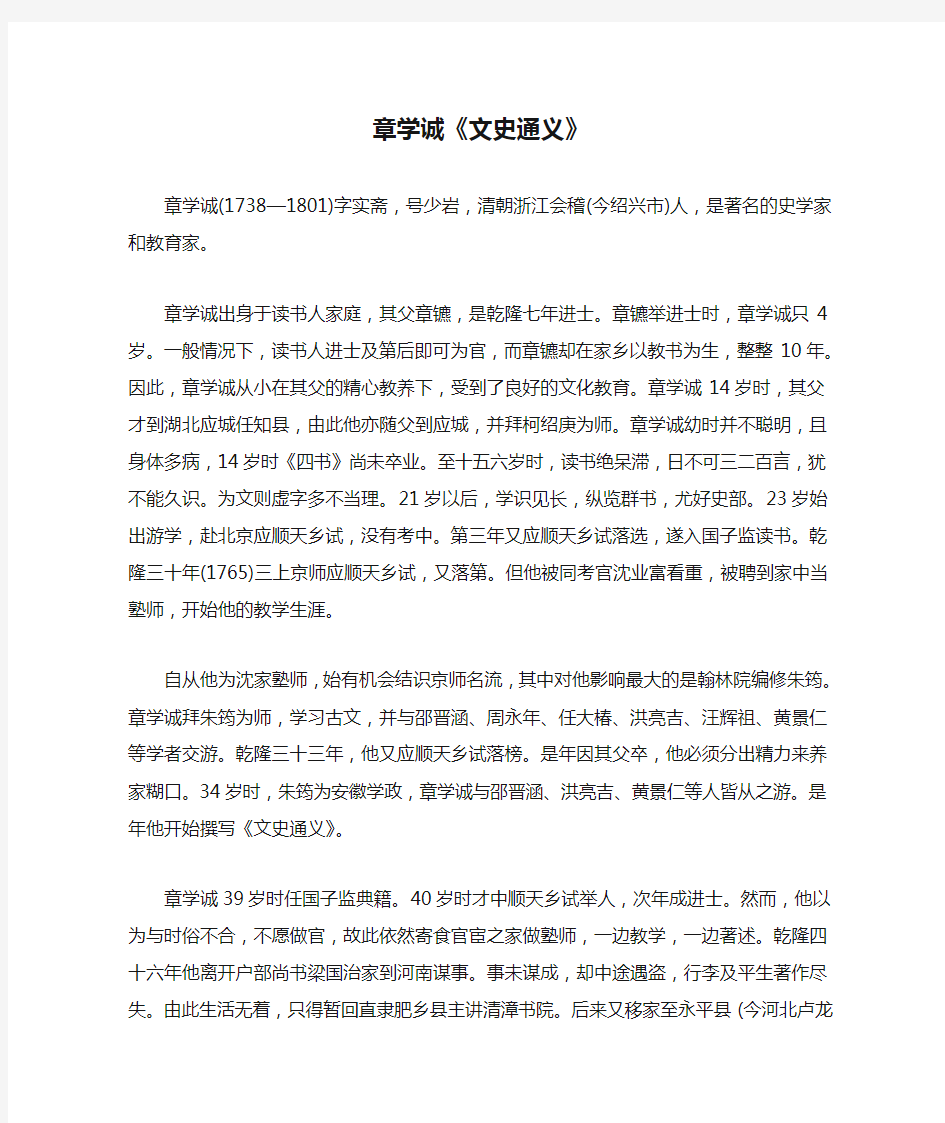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经毕沅同意,仿朱彝尊《经籍考》体例,开始编纂《史籍考》。但不久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中断。乾隆五十五年,章学诚去武昌依毕沅从事编纂工作,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主修《湖北通志》,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
作。
章学诚晚年将家眷从亳州接回会稽,而他则离湖北而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继续从事他的讲学与著述,直至嘉庆六年十一月卒。章学诚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文集》、《乙卯札记》、《丙辰札记》、《史籍考》等,其《和州志》、《永清县志》等也很受世人推重。其著作后人编为《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探讨古今学术、文史、教育等文章和论学书的汇编,原无固定体例,章学诚生前也没有编成定本。今所见的最早刻本,为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的刻本,亦称大梁本,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另有《校雠通义》3卷,收录的文章不完备。章学诚之子章华绂在序文中说:“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1920年吴兴刘承于所刻《章氏遣书》中的《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标点排印本的《文史通义》11卷,其中内篇6卷、外篇3卷、补遗与续补遗各一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本亦11卷,其中《内篇》5卷。《外
篇》3卷,附《校雠通义》3卷。该版本与大梁本的内容大致相同。《文史通义》是章学诚自35岁时始著之书,经20
余年的精心探讨,竭思尽力,积文而成。故它凝结了章学诚的毕生精力和思想精华,可以说是章学诚的代表作。
《文史通义》一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学术著作?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史学界以为它是研究文史的名著,文化史专家则以为它是文化史专著,思想史学家则视其思想史专著。这说明它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但从教育学的学术价值观论之,它应当是一部基于文史渊流的探究和学术评品之上的,刻意矫正学风以倡导经世致用教育的学术著作,其讨论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归宿点是教育。因此,我们把它列入教育名著来评介是相当必要的。
(一)关于经与史的关系
《文史通义》指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一观点章学诚以前已有隋儒王通、宋儒陈傅良、明儒王守仁等人提过。他们提出这种观点都是对当时的治学学风有所
指责的,并且着意整顿经学教育,要求通过经学的教育革新,使文字章句的经学及经学教育转变为对客观历史规律及治
道的切实关注上来。章学诚也不例外,其“六经皆史”说,从本质上讲是旨在救当时经学以训诂考据的“求道”的流弊,要求经学及经学教育要转移到经世实用的“实学”上来。
“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之一。章学诚认为,古代之人官师治教合一,职官之事即国家礼乐治教之事,未尝以文为著作,礼乐治教之道均以实事来表现,“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盖自宫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文覃也”。经既然是作为古代礼法制度的记实,不是圣人有意要立言垂教的,因此学习六经,如果只把它看作空言道理的东西,或只看作离开事实与事理的文章,则“是以文为擊帨绣之玩,而学为计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注重文字与训诂,使史实与事理被遗弃,道隐法无,故其学问文章不足为国家之用。因此,“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
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
《文史通义》的《易教上》曰:“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经解上》亦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这里的“史”,不是一般史学意义上的记录事实,搜罗材料,排比现象,而是指“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是“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是客观人伦日用和治世之道的必然之理。因此,章学诚指出,学习六经的意义,不应在文字章句的表面去求知识,不应舍却自家现实事物、人伦日用上去寻训诂考订,而应当“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于经术精微”,去探索社会治乱规律和根本法则,通经以致用。事实上,章学诚的“通经致用”就是他的经学和经学教育目的。
《文史通义》卷五《史释篇》指出,经即史,学习六经但又不是教人去效法古人,而是通过经书的学习与理解,从根本精神上认识社会的发展需要其相应的文化变革和制度
变革,质言之,经只提供人们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上的治世
经验,它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要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必须从现实客观着手,探讨人伦日用、典章制度、官司职掌的治道。章学诚在该文指出:“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于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为可御饥寒,不须衣食也”。
(二)关于经与史的学习目的与态度
《文史通义》一书,反复强调六经是言事的,其理蕴于事中,“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事有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把理与事的关系比作水与器的关系,批评当时学者离事而言理,犹舍器而言水之“挹注盈虚”,以为这种学风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是“不知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圣人之言,以为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之外耳”。
清代崇考据学的风气很浓。考据学主要是对经书文字章
句的考订,辨别其正误讹谬,探本求真。自顾炎武到戴震,这种学风日渐影响了学术界和教育实践。章学诚对顾氏和戴氏的考据训诂之学的目的是充分肯定的。他说:“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但是,章学诚认为时人虽受其学风影响,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就以为考据训诂即是经学;天下的教育亦受其风气影响,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以崇尚训诂考据为真学问,广征博引,遗经义而求文字之表,从而离却了事物,不知学问为何用。这种经学及其教育是失去了经世致用的目的,不过是陋儒末习而已。
清代重考据,称考据学派为浙西学派,这是世人推崇顾炎武为开国儒宗的缘故。章学诚对考据学学风的流变十分不满,故要求以浙东学派的重史学风来补救之。《文史通义
·浙东学术篇》指出,世人只知顾炎武开创的浙西之学而不知黄宗羲同时开创的浙东之学。浙东之学“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悖
于朱者也”。他提倡学者打破门户之见,以经史之学来补救考据之学的流弊,摒弃单纯的离经义而偏考据的治学态度,使经学教育切实不务空疏,而落实到现实人事政治上来。
在《浙东学术》中章学诚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以经史之学补救考据训诂之学,这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致力于学风改造和经学教育目的转变的重要主张。
但是,这一主张并非要求以史学代替经学,或史学即经学,而是要求根据以史学的观点来探讨六经中的有关人伦日用、典章制度的“自然之道”,使人通过这种学术研究和经史教育,知其治道之所以然,然后有为世用。《文史通义》认为,道不外人伦日用,“道有自然”。既然“道”是客观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故求道必然要在人伦日用之中去探讨。探讨自然之道,是为了在必然王国之中求得自然亦即自由。道是不断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必不尽同”,故六经不足以尽道的。由此,章学诚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对待六经,
即既要研究六经以考察古代事物之道,知古今道之变化的必然,同时又必须看到六经皆史,道在历史现实之中,所以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对现世人伦日用事物的研究上。如果不是这样,“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足与言夫道矣。”章学诚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非他能立言垂训,而是他从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中知其道之自然,并遵自然之道而经纬人间事物。“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在《原学篇》中,章学诚指出:“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六经文字是对历史事实之道的记述和揭露,学习六经不应当去一味地追求成贤成圣,以致舍己从人,而是“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即为效法也。”古训是必要的,但必须要知道,训诂是为了多闻识见,是为了博学,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和更真切把握六经所揭示的“道”,它是“求效之资”的必要手段,但如果以为这就是经学,就可“效法”,那就背离了经学的目的。《原学下》指出:“博学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
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矜其艳于云霞,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拘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穷于考索、竭思为文、空谈义理,都不是以“效法”为目的为学之道,都是不良学术风气的表现。然而,要改变这种学风,则必然要以真学问来开风气。章学诚以程颐“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的名言为论据,以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倡导以独立思考、由博返约、实事求是来开辟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
章学诚《师说》阅读练习及答案
师说 章学诚 韩退之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又日:“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 人失其道,剥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艾例,皆为道体所该。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其斫取法,无异梓人之恭o琢雕,红女之传烯绣o,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于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④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于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于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有删改) (注)①慕(ji):教,指点。②烯(chi)绣:绣有彩纹的细葛布,此处泛指刺绣。③昭:通“劭”,勤勉。④冁(chan):笑的样子。 7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B.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月酷毛心市耐妊彰是亦不可易之师/ C.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冀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March ,2012 第25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Vol.25No.22012年3月 Journal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收稿日期:2011-09-14 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 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1914年11月26日,鲁迅得到二弟所寄书籍两束,其中有《文史通义》一部六册,同月的29日,鲁迅 “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这是鲁迅日记中对于《文史通义》的记载,从中看不到鲁迅对《文史通义》阅读情况,遑论影响了。但1933年鲁迅所写《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到文坛的斗争、谩骂和诬陷,就谈及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撝叔,如水火之不可调和。[1](P247)由此可知,鲁迅非常熟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为《文史通义》里就有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文章。章学诚对于鲁迅的影响,陈方竞先生已经做了论述[2],笔者试加以补充。 一、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的影响 鲁迅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浙东历史学存在着密切关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方志,“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3](P256)浙东史学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特征是“提倡方志学,推广方志这种社会史体”[4](P256)。浙江自古就有撰修方志的传统,《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方志史上最早的地方志雏形。这个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延续,形成了浙江修志最为繁盛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被章实斋从理论上给予阐发,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到章学诚,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章 学诚在自己与前人撰修方志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起源作了明确的探讨。 章学诚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5](P124)章学诚也明确了方志的作用。“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3](P263)“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6](P138)在阐释方志的社会功能上,章学诚很明显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依然以传统的诗教来解释方志的作用。但只要把章学诚的理论还原到乾嘉学派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考据学派编修方志的理论观点是“志以考地理”,将作为地方史的方志纳入考据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证之学。继承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他毅然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同国史一样,具有维护纲常、裨益世教的功用。鲁迅辑录丛书,其目的与之遥相呼应。《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告白辑录目的曰:“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逸,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吴谢承始传 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赵献涛,李晓彩 (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鲁迅;章学诚;史学;影响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2)02-0088-03 88··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09-01-21 13:16:00 ] 作者:裴元凤编辑:studa0714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 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 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 ①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①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②”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③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④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⑤ ①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②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③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④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4页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讲解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略论章学诚对郑樵的推崇 郑樵,生活于南北宋交界时期,后世对他的《通志》评价不高,多认为“其言绝可怪笑,以谓不足深辨,置弗论也①”。而六个多世纪后的章学诚却在其毕生心血之作《文史通义》里单列《申郑》、《释通》、《答客问》等诸篇为郑樵辩护,并大加赞赏,《申郑》篇云: 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翦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②目前学术界对郑樵、章学诚二者的单独研究众多,而二者的比较研究却鲜见。本文不自量力,欲就此问题稍尽绵薄之力。 一、实学之发展 郑樵生平勤于著述,自述“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③”,但流传下来的书很少④,关于他作《通志》的原因,如今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几部书中略窥一二。他在《寄方礼部书》中说: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寻纲法纪。呜呼!三馆四库之中,不可谓无书也,然欲有法制,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实未见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⑤ 按郑樵作《通志》,很大一部分原因自然是贯彻其“会通之意大矣哉⑥”的思想(详后),但郑樵对空言的不满和对实学的推崇也是推动他作《通志》的原因。“实学”思想在郑樵的著作里多有体现: 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⑦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飨,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⑧ 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荣,至于实学,则置之不问。⑨ 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⑩按郑樵认为有些学问必须要亲身实践方能明白,而且学问亦要付诸实用。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篇则曰: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 钱穆先生对章氏的“六经皆史”说有过解释,大意指六经皆三代之史,各守专官之掌故,并非圣人有意要作文章,后人尊崇三代,于是便尊崇所谓“六经”。钱先生引章文: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于空言。 古人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于是宾四先生说道“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捨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 ①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卷五,47页 ②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8年第一版,卷五,46页 ③郑樵:《上宰相书》,《夹漈遗稿》卷3,此书我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列于集部四,别集类三 ④参见顾颉刚:《郑樵著述考》,《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2091页 ⑤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⑥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一版,1页 ⑦郑樵:《上方礼部书》,《夹漈遗稿》卷2 ⑧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4页 ⑨郑樵:《昆虫草木略》序,《通志二十略》,1979页 ⑩郑樵:《图谱略?索象》,《通志二十略》,1826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经毕沅同意,仿朱彝尊《经籍考》体例,开始编纂《史籍考》。但不久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中断。乾隆五十五年,章学诚去武昌依毕沅从事编纂工作,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主修《湖北通志》,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 [1](p603)白寿彝的思想,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不仅继承、发展和总结了1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理论的成就,而且揭示出历代学术变迁、社会演变和史籍历史发展的法则,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过去研究乾嘉史学,探讨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文章相当丰富,然而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一、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几个主要阶段,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章学诚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道家和佛教,自然不重视释老之学。他以六朝隋唐的辞章文学代替玄学和佛学,全面考察历代学术的发展及其利弊得失,形成了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历代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学术思潮的质文递变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法则,“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2](《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说明,不同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学术思潮的循环。所谓“循环盛衰,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风气对思潮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风气不断改变,导致学术思想的利弊两方面失去制衡,物极必反,互为循环。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宋代以后,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的作用。尽管宋儒具有良好愿望,至元明两代,理学渐渐演变为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汉唐学术注重征实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逐渐扭转空谈“义理”之弊,开创出质朴求实的学风。但是,朴学纠正宋学空疏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宋儒之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家书五》)在章学诚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乾嘉学者徇于世风,训诂章句,考订异同,补苴罅漏,有功实学。然而朴学流弊是把“求是”作为治学终极目的,不重“义理”,完全忽视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
文学的独特魅力:传统中国独特的文学观
传统中国所谓的文学,与今人所谓的文学是两回事。 《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天性强过文化的修饰,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文化的修饰掩住了天性,就导致浮华夸饰。文质相互平衡,这才是君子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有着特别的注重。当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马上反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倘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区别,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区别。君子之道,固不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文化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君子,对文的意义有了深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天下,让天下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想,可以统谓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体实施的路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此,在孔子那里,在早期儒家那里,文学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人格。 儒家认为,学者毕生所学,不过是求得人格的完全,亦即是“仁”。仁,古文字亦作上身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谓。今人入孔庙,凡孔庙中必有两副匾额,一副为“中和位育”,一副为“与天地参”,并出于《中庸》。与天地参(sān),意即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这是孔子为中国人所开示的民族信仰。完善的人格即法天则地、与天地参。效法天地运行之消息,让自己的人格臻于天地伟美之境,此即儒家的根本意旨所在。 完善的人格在气质上表现出的就是温文尔雅。尔雅的尔,通“迩”,是“近”的意思,尔雅就是亲近于雅。“温”是温柔敦厚,“文”者谓君子言行举止,皆合于规矩,合宜、合度、美好。然则温文尔雅的美德自何处而来?只能从文学中来。 先秦时凡饰身润德的学问,都谓之文学。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文学便有了更加明晰的定义,只有“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才被认为是文学。即是说,文学须出于深沉细腻的审美感受,抒情达意,须借优美的文辞声韵传递开来。此后直至二十世纪前,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盖皆不逾于此。 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所谓的“文学”,则是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义有二,一为文学须有独特的语言艺术,二为文学须表现作家独特的心灵世界。朱光潜先生无疑是受此文学观影响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侦探小说不是文学,因为侦探小说满足的是读者的理智,而不是读者的情感。但倘若持此文学观观照中国传统文学,直是圆凿方枘,扞挌难通。如载道的文,用于酬应的表启,乃至祭文哀诔,这一类的作品,在新文学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学,然而它们恰是中国文学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所谓的文学,有着比今日之文学更崇高的地位。文学,是国学的三鼎足之一。中国传统学问,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文学就是辞章之学。辞章不仅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经部中诗经、易传、尚书、礼记、左氏传何尝不是辞章?诸子百家之文,皆是后世习文的涂轨;史部中《史记》、《汉书》是古文正宗,唐人刘知己《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两部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又都是漂亮的骈体文;中国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龙》,清人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录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一部文学理论的著作,竟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这在已为西方文学观所俘虏的今之学者那儿,是无法想象的。
章学诚史学的特点
章学诚史学的特点 章学诚,字实齐,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一年)。他生在专门汉学、不谈义理的时代,他的学问不合时好,以致他的言行,在死后一直被埋没多年。但也正是他,在那样的时代,发出了一种对汉学的抗议,部分地继承了十七世纪大儒的传统。所谓“部分地”,是说他的成就是在文化史学方面,他还不能全面地深刻地光大清初大儒的近代意识。他自己说: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缘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姑孰夏课甲编小引”) 学诚所说的文史不外于道,其语气虽然谨慎,但他的这种文化哲学或文化史学的理论,便足以成为当时对汉学最出色的抗议,诚如他所说的“所撰著,归正朱先生(筠)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同上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他在专门汉学的空气中,是遭受着异端之嫌疑的。但他自信不疑,卓然有见。所以他又说: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群反约,原非截然分界……。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儿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他在“与汪龙庄书”中说: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同上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 他自三十五岁起开始写“文史通义”,至“稍刊一二”之年,中经二十四年的光景。因恐“惊世骇俗”,他只是“择其近情而可听者”刻印出求,当不能尽所欲言。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校雠通义”不只不能全刻出来,而且原稿也被盗了。被盗的原因大可寻味。因为他这时正得罪了一个权贵,出走河南,很可能是为了他好为议论,招人诟厉,以致有人故意来同他这样捣乱的。 学诚言论风度的不投时好,见于李威“从游记”。他记朱筠事说: 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 使“见者愕然”的他的言论风度,是不合于乾嘉时代的世俗好恶的。学诚自己给钱大昕的信也说: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祟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 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同上卷二十九外集二“上钱辛楣宫詹书”)他在这封信里,把那种畏戒时趋的情境毕现出来。他所谓“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可以说就是对于当代“专门汉学”的抗议。这时汉学的主持者正是康熙以来的文化政策执行者,奔赴者则是他所谓的利禄文士,这何尝还有清初学者活生生的气象容乎其间?这种风气,他在“文史通义”中更慨乎言之。我们仔细研究,几乎“文史通义”每篇都有反对当时“专门汉学”的议论。“原学”下篇曾举其要旨说: 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 [1](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 一 章学诚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按照传统儒家的看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定时代和具体事物而永恒存在的“道”。其实,孔子未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章学诚指出:“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乾坤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3](《易教上》)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导致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章学诚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3](《原道中》)倘若轻视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与人伦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义理,以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舍本逐末之举。宋明理学求“道”的局限,恰恰是以为上古圣人之“道”超然于人类社会之外而独立存在,最终陷入理障。章学诚认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故宋人讥韩昌黎氏,以谓因文见道,不知韩子未至于孔、孟者,义方敬直之功,存心养性之学,不能无间然耳。若以因文见道为韩子之弊,是离学问文章以言道,恐韩子所不屑也。”[4](《与邵二云论学》)在章学诚看来,唐代韩愈所提倡的“因文见道”、“文以载道”之说在学理上有没有错误是一个问题,而韩愈能不能够达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3](《言公中》)由此可见,韩愈以文为载体而明“道”在学理上本不错,但是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0一年)。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作《文史通义》八卷、《校雌通义》三卷和《史籍考》著名。《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第一句,亦即全书开端第一句,开宗明义提出的重要论断 ,并成为章学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众说纷纭。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一些理解。一、“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有不少关于评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文章 ,几乎都肯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章学诚首创的。柴德庚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8 日第四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 ,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仓修良先生则不同意上述提法 ,他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仓修良先生是研究章学诚比较透彻的人物之一,著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书。我的观点和仓先生的比较相近。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类似说法的有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 ,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 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 一) 。王世贞在《四部稿》卷一四四亦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三王之世 ,若泯若灭 ,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 ,噫 ,史其可以已耶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而大思想家李贽 ,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说得就更加明显了 ,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史之所从来 ,为道屡迁 ,变易匪常 ,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也。”据上所引 ,我们可以看出“六经皆史”的命题, ,既不是章学诚的创见,也不是到了章学诚才大胆提出的 ,前人在行文中都涉及到了 ,只不过章学诚将其作为重要命题提出来。二、“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六经”原指“六艺”,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是孔子删订的 ,后来被捧为“经”。当时因为缺乏科学的分类 ,孔子把三代以来积累的所有知识都囊括在“六艺”里面 ,因此“六经皆史”事实上包含有“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 ,皆是史学”这层意义。“六经皆史”实际上是“经”的“还原” 。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剥掉了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是有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一、功力、学问与性情“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 “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章学诚主张做学问首先要从“性情”人手。“性情”指的是个人的天资和兴趣,也包含读书中的个人感悟和体会。他在《说林》说:“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道”具有“公”的性质,有“天下之公器”之意。而学术则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必然会打上个人兴趣才力的烙印,具有个人特色。“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博约中》)章学诚论学深受王阳明良知良能说的影响。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之说,进一步阐释“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认为人内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学习的能力和成为圣人的能力。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体与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验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才能被主体自觉认识,良知只有在功夫展开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章学诚对此进一步发挥,将其运用到治学之上,就是要寻找学术中与主观天资相契合之处。“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他主张为学之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资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