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符号意蕴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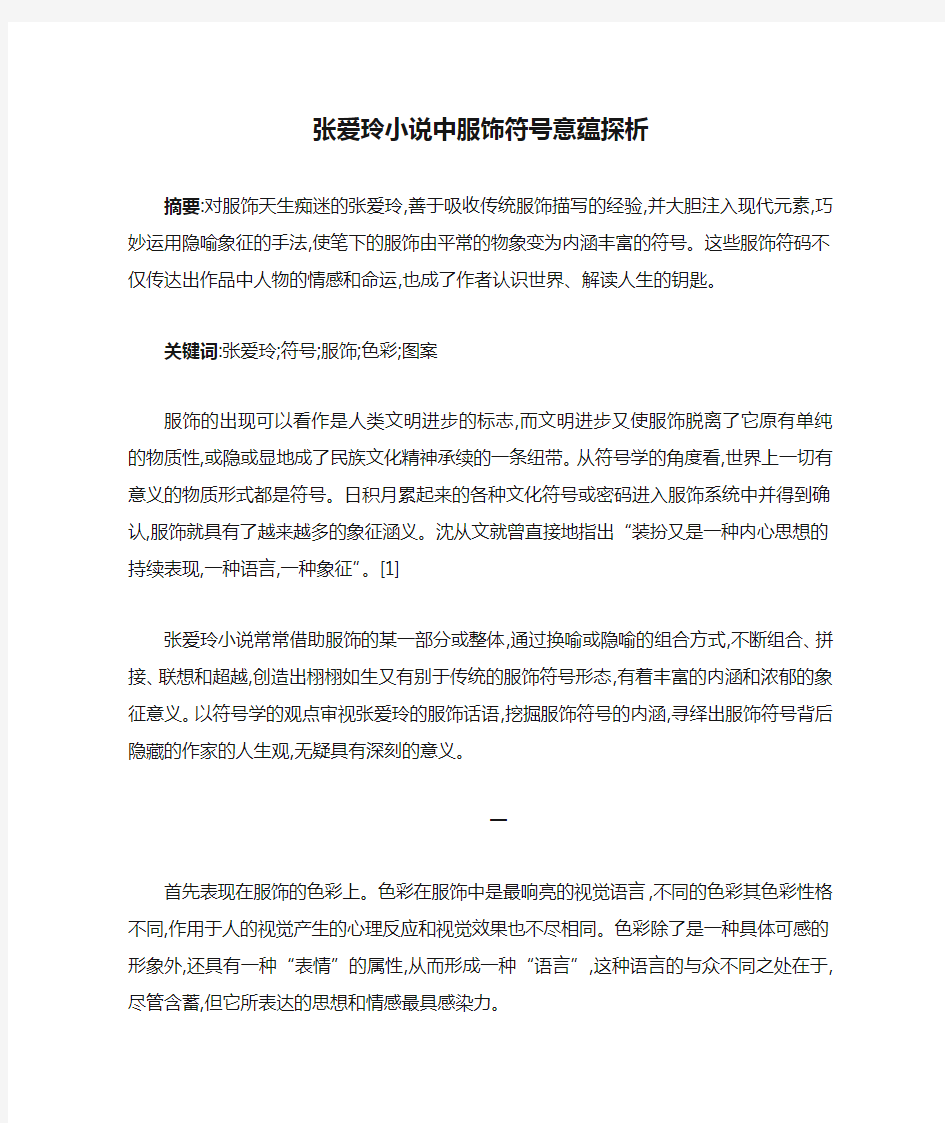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符号意蕴探析
摘要:对服饰天生痴迷的张爱玲,善于吸收传统服饰描写的经验,并大胆注入现代元素,巧妙运用隐喻象征的手法,使笔下的服饰由平常的物象变为内涵丰富的符号。这些服饰符码不仅传达出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也成了作者认识世界、解读人生的钥匙。
关键词:张爱玲;符号;服饰;色彩;图案
服饰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文明进步又使服饰脱离了它原有单纯的物质性,或隐或显地成了民族文化精神承续的一条纽带。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世界上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形式都是符号。日积月累起来的各种文化符号或密码进入服饰系统中并得到确认,服饰就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涵义。沈从文就曾直接地指出“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1]
张爱玲小说常常借助服饰的某一部分或整体,通过换喻或隐喻的组合方式,不断组合、拼接、联想和超越,创造出栩栩如生又有别于传统的服饰符号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浓郁的象征意义。以符号学的观点审视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挖掘服饰符号的内涵,寻绎出服饰符号背后隐藏的作家的人生观,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
首先表现在服饰的色彩上。色彩在服饰中是最响亮的视觉语言,不同的色彩其色彩性格不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色彩除了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外,还具有一种“表情”的属性,从而形成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含蓄,但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最具感染力。
张爱玲对色彩的敏感异于常人。“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个世界显得更真实。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在那里了,就使人安心。”[2]色彩作为等级的重要标志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虽然已不明显了,但人们在接触人物的服饰色彩时,还是会常常不自觉地通过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把握藏在色彩表象背后的意蕴。在张爱玲的服饰话语里,利用色彩来暗示人物的身份、心境、命运的例子俯拾即是。
《金锁记》里有13处写到七巧的服饰,其中有一处是这样描写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他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这“一小截粉红丝线”正暗示和象征着七巧的情感欲望。对“钻石”的欲望和对爱情的欲望于七巧来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她得到了“钻石”就得放弃情欲,而情欲在她的心里偏偏来得嚣张,那发髻心子里的“粉红丝线”是她想压却压不住的情欲的象征。最让读者难忘的莫过于《金锁记》里长安的服饰色调搭配了。七巧正在随随便便地向童世舫编谎言:“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此时的“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七巧的话长安势必听到了,此时作者没有对长安的面部表情进行刻画,也没有对长安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进行直接的交代,有的只是鞋与袜的色调特写。在这日色昏黄的楼梯上,人们的视线正随着两只鞋被引向“没有光的所在”。这玄色的绣鞋与白丝袜放在一起产生了“必死无疑”的象征,因为玄色,不管从它的物理性质上,还是从它造成的精神状态上看,都包含着一种死亡的因素。而白色,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把它与纯洁、忠贞相联系外,更多的是把它和无生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常有的意向也是死亡。用这样的服饰符号暗示出长安孤苦无助和对生活最后一点幻想死灭的绝望心境。
其次表现在人物服饰图案的选择上。服饰图案作为一种符号,这让人感受到古老图腾文化在渐渐地向生命个体渗透、转化和投影。图腾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基层文化,它也是中华服饰的基层文化。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儿童帽饰中的虎头鞋帽、兔子帽、蝴蝶结等款式中,感受到远古图腾及冠礼的遗风。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一个看似简单的服饰图纹,都可能是图腾形象的原生态或历史演变之物,它们负载着厚重的人生内容,散发出庄严神圣的氛围感。
《茉莉香片》里冯碧落的服饰是通过照片来写的:“她穿着古式的摹本缎袄,有着小小的蝙蝠的暗花。现在,窗子前面的人像渐渐明晰,他可以看见她的秋香色摹本缎袄上的蝙蝠。”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把蝙蝠看作是长寿与幸福的象征。然而,冯碧落因父母的门第观念与幸福擦肩而过,不幸的婚姻让她早早地凋谢了。追求与现实的南辕北辙,这服饰的图案更让人感到辛酸和沉重。“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了象征性。”[3]张爱玲小说中的每一个服饰意象都是寻常的,符合规定情境,符合日常的经验,没有变形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然而它们本身却具有非常复杂的意蕴,具有足够的象征力量。
《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本来是瞒着父母向姑妈求援,以求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在姑妈一步步的引诱下,由一个纯洁的中学生变成了有名的交际花,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痛惜之情作者借助下面的服饰细节很好地表达了出来:阴历三十夜葛薇龙和乔琪到湾仔看热闹,花炮乱飞,她的旗袍着火了。结果是薇龙屈膝蹲在地上,乔琪用他那带灰的鞋底“两三脚把她旗袍下摆的火踏灭了。那件品蓝小银寿字织锦缎的棉袍上已经烧了一个洞”。这里很明显运用了象征,象征着薇龙的感情、命运就像这件“烧了一个洞”的旗袍被人践踏得千疮百孔。
二
每个作家都在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岁月的星霜,遭遇的波折,现实的境况,心情的状态,都给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打上不可掩盖的印记。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族、动荡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她的服饰话语也处处烙上了她悲观的人生哲学。
张爱玲在作品里常常不厌其烦、极其详尽地盘写一个个人物上袄下裙穿什么料子花式,头面鞋脚什么色调。她明白通过服饰等生活细节来诠释人物、勾勒迅速走向现代的中国人的精神轮廓,绝对比透过嘴中的“思想”精确得多,因为日常生活下面埋藏着人生的痛苦和绝望。她善于借日常服饰之“实”去揭示人生深处大悲哀之“虚”。在她的小说里,主题永远是悲观。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鸿鸾禧》这篇小说几乎是服饰的狂欢。二乔、四美和邱玉清姑嫂三人一开篇就在为婚嫁忙着买衣试衣评衣,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是由件件不同款式、色彩、线条各异的服饰来铺垫和推动的。作者详细叙述了邱玉清如何办嫁衣,说她买了软缎绣花睡衣,相配的绣花浴衣,织锦的丝棉浴衣,金织锦拖鞋,白色婚礼服等。一切是那么的琐碎,一切又是那么的完满。出人意料的是在婚礼结束时“白礼服似乎破旧了些,脸色也旧了”,婚礼照片上的新娘是“立在那里,白礼服平扁浆硬,身子向前倾而不跌倒,象背后撑着纸板的纸洋娃娃”,这件有着不谐之音的白色婚礼服成了邱玉清婚后悲剧生活的预兆,再加上大陆父母这对怨偶做背景,其透彻的悲凉更让人发颤发麻。通过她们为婚嫁的服饰忙碌写人生的无奈和婚姻的悲苦,实乃作者的高明之处。
张爱玲认为“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所以没有一出戏能用快乐为题材”。[4]日常生活在她看来,始终是阴暗和沉重的,生活本身充满了不幸和悲伤。她善于借人物的日常服饰,把人从生活表面推向人的内心,并对人的各种生存状态提出追问,用闪着刀子一样寒光的眼睛,毫不犹豫地给我们挑落笼罩在人生边上这出戏上的温情面纱,把人生和人性的真相摆在读者的眼前。她揭示的真实让我们恐怖,因为恐怖而生悲哀,因悲哀而站在人生的边上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