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阿来创作论——精选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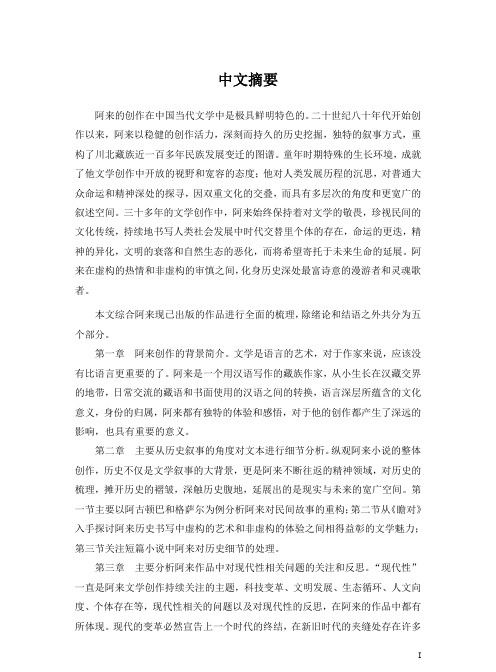
中文摘要阿来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极具鲜明特色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阿来以稳健的创作活力,深刻而持久的历史挖掘,独特的叙事方式,重构了川北藏族近一百多年民族发展变迁的图谱。
童年时期特殊的生长环境,成就了他文学创作中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他对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对普通大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寻,因双重文化的交叠,而具有多层次的角度和更宽广的叙述空间。
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阿来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敬畏,珍视民间的文化传统,持续地书写人类社会发展中时代交替里个体的存在,命运的更迭,精神的异化,文明的衰落和自然生态的恶化,而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生命的延展。
阿来在虚构的热情和非虚构的审慎之间,化身历史深处最富诗意的漫游者和灵魂歌者。
本文综合阿来现已出版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阿来创作的背景简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没有比语言更重要的了。
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从小生长在汉藏交界的地带,日常交流的藏语和书面使用的汉语之间的转换,语言深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身份的归属,阿来都有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对于他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主要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细节分析。
纵观阿来小说的整体创作,历史不仅是文学叙事的大背景,更是阿来不断往返的精神领域,对历史的梳理,摊开历史的褶皱,深触历史腹地,延展出的是现实与未来的宽广空间。
第一节主要以阿古顿巴和格萨尔为例分析阿来对民间故事的重构;第二节从《瞻对》入手探讨阿来历史书写中虚构的艺术和非虚构的体验之间相得益彰的文学魅力;第三节关注短篇小说中阿来对历史细节的处理。
第三章主要分析阿来作品中对现代性相关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现代性”一直是阿来文学创作持续关注的主题,科技变革、文明发展、生态循环、人文向度、个体存在等,现代性相关的问题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在阿来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现代的变革必然宣告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新旧时代的夹缝处存在许多I的“最后”,“最后的猎人”、“最后的马队”、“最后的土司”、“最后的巫师”……它们曾是时代的辉煌,却因时代变迁而悄然衰落,最终以悲壮或惨淡谢幕,被遗忘在时间的废墟中,阿来用文学的方式拂去它们的尘埃,重燃它们的生命最后之光。
春意挂上了树梢读后感

春意挂上了树梢读后感《春意挂上了树梢》是当代作家阿来创作的一部小说,通过讲述瑶族少女晓梦和基诺族少年明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展现了瑶族文化与基诺族文化的交融,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理解。
读完这本书,我深受感动,引发了我对于文化传承与融合的思考。
《春意挂上了树梢》以云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描述了身为瑶族少女的晓梦和身为基诺族少年的明子之间发生的故事。
晓梦和明子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理想,他们都喜欢音乐,希望通过音乐来连接与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
他们结成了一支音乐队,参加了全国大赛,最终取得了成功。
但是,在成功的背后,他们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迷茫。
通过这个故事,阿来深刻揭示了瑶族与基诺族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
晓梦和明子代表着两个民族,他们通过音乐来传递自己的文化,使得民族之间的理解更加深入。
他们的音乐穿越了种族和语言的障碍,让人们更加熟悉和了解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
在小说中,晓梦是瑶族的代表,她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非常自豪,她努力学习瑶族音乐,让自己的音乐才能得以传承。
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她面临着异化和同化的压力,她开始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稀薄。
她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但她始终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瑶族文化的自豪。
她希望通过音乐来唤醒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对根本问题的思考。
与此同时,明子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作为基诺族,他精通基诺族音乐,并希望通过音乐来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
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他民族的认可,成为瑶族和基诺族之间的桥梁。
他意识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自己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传承基诺族的文化,以使其与时俱进,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基诺族文化。
阿来通过晓梦和明子的故事,深刻地描绘了民族文化传承所面临的问题,并给我留下了许多的思考。
作为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我们是如何看待并传承自己的根源文化的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如何保留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潮流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人和民族成长的问题。
尘埃仍未落定——潜隐在阿来文本中的矛盾和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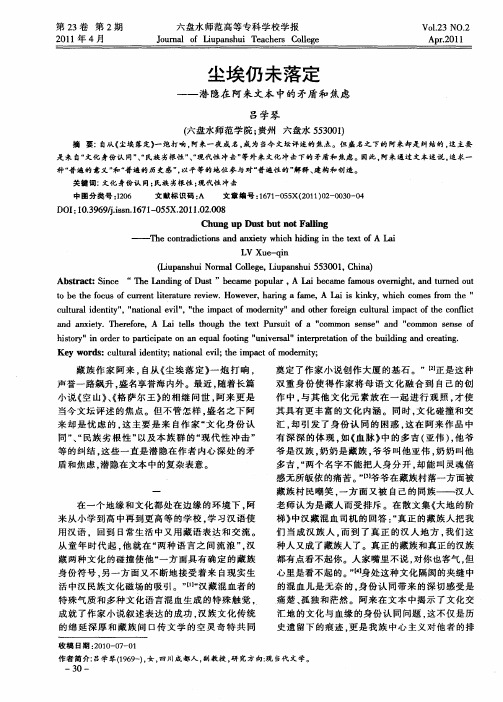
(ip nh i om l ol e Lu a su 5 0 1 C ia Lu a su r a l g , ipnh i 3 0 , hn) N C e 5
Ab ta t ic “T eL n i go u t”b c mep p lr, L i e a o so eng t a dt re u sr c :Sn e h a dn fD s e a o ua A a c mef b m a u v r ih, n un d o t
形式 对 复 杂 的 汉 藏 文化 交 界 地 人 们 几 十 年 的 生
活做 文化 与历史 的宏 观把 握 。” 】 君在 《 【邵燕 5 以阿
平等 的地 位参 与对 “ 普遍 性 的 ” 释 、 解 建构 和创 造
【 】 们
,
为消除文 化 隔阂摒 弃偏见 而努力 。
来 ( 山) 例》 空 为 中说 无论 是从 宗教 信 仰还 是 从 生 活方 式上 ,阿来 都与 中心 地 区 的藏人 相 对疏 离 ,
宝教 授 尖 锐地 说 , 阿来 基 本 上 是 从 小 就失 去本 “
嘉 绒 当作 第二 故 乡 。关 于身 份认 同 的困惑 , 阿来 虽 然 也 是 伤 痛 和 敏感 的 ,但 他 并 不 像 文 本 中 的
“ 吉”“ 血 司机 ” 样不 知所 措也 无处 述说 , 多 ,混 那 把 这一 切 归为 宿 命 。 而是 奋 笔 疾 书 . 以文 学 表 意 的 方式 , 以一个 嘉 绒知 识分 子 的 身份 继续 书 写着 本 民族 的历 史 , 过文本 追 求一 种 “ 遍 的 意义 ” 通 普 和 “ 遍 的历 史感 ” 消 除别 人 眼 中 的 “ 类 感 ” 以 普 , 异 。
民间文化资源在当代作家创作中的表述——阿来长篇小说论的开题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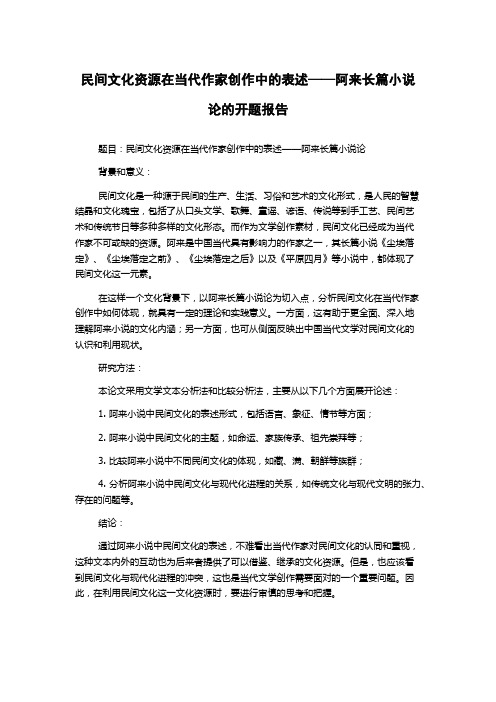
民间文化资源在当代作家创作中的表述——阿来长篇小说论的开题报告题目:民间文化资源在当代作家创作中的表述——阿来长篇小说论背景和意义:民间文化是一种源于民间的生产、生活、习俗和艺术的文化形式,是人民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瑰宝,包括了从口头文学、歌舞、童谣、谚语、传说等到手工艺、民间艺术和传统节日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
而作为文学创作素材,民间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作家不可或缺的资源。
阿来是中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尘埃落定之前》、《尘埃落定之后》以及《平原四月》等小说中,都体现了民间文化这一元素。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以阿来长篇小说论为切入点,分析民间文化在当代作家创作中如何体现,就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方面,这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阿来小说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可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对民间文化的认识和利用现状。
研究方法:本论文采用文学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1. 阿来小说中民间文化的表述形式,包括语言、象征、情节等方面;2. 阿来小说中民间文化的主题,如命运、家族传承、祖先崇拜等;3. 比较阿来小说中不同民间文化的体现,如藏、满、朝鲜等族群;4. 分析阿来小说中民间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张力、存在的问题等。
结论:通过阿来小说中民间文化的表述,不难看出当代作家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和重视,这种文本内外的互动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继承的文化资源。
但是,也应该看到民间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这也是当代文学创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在利用民间文化这一文化资源时,要进行审慎的思考和把握。
阿来小说二十年研究综述

阿来小说二十年研究综述作者:张姻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21年第10期摘要:阿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但学界对阿来小说的研究可以说是直到2000年《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才真正起步。
此后学界对这个来自汉藏文化交汇地的作家愈发关注。
将阿来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分析,可以發现,学界对阿来小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藏区主题、认同主题、现代性主题、历史主题、生态主题及其叙事艺术上。
这些论者对阿来小说中叙事主题的分析呈现出愈发细致深入的特点,通过综述,以期推动阿来小说的研究。
关键词:阿来小说;研究综述;叙述主题;叙事艺术1959年,阿来出生于一个叫马塘的小村庄。
马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马尔康市,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区,多民族文化共同孕育了阿来。
“1982年,时年24岁的阿来发表了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文学旅程。
”[1]从1982年到1984年,阿来一直从事诗歌创作。
1984年,阿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红苹果,金苹果……》。
1998年,经过数年沉淀与数次出版风波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0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文学界开始真正关注这个来自汉藏文化交融地区的藏族作家。
粗略统计,研究阿来小说的相关论文有900余篇,硕博论文60余篇,少量学术专著。
持续关注阿来文学创作的学者有梁海、陈思广、贺绍俊、曾利君、白浩、丹珍草、张学昕、余宏、徐新建、徐其超、徐美恒、伍宝娟、吴义勤、吴道毅、王妍、彭超、刘大先、栗军、李康云等人。
从《尘埃落定》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阿来的创作活力不减。
先后创作了“机村六部曲”、《格萨尔王》、《瞻对》、“山珍三部曲”、《云中记》等作品。
学界对阿来的关注也一直热度不减,2014年,陈思广等学者主编《阿来研究》,预示着学界对阿来的研究更为系统化,曹顺庆在卷首语称阿来把弱势文化推向全球公共领域,完成了藏族文学表意功能的转化。
认同与交汇——论文化身份“困境”中的阿来

不 确 定 给 当事人 带 来 程 度 不 同 的苦 恼 和 焦 虑 。 由此 引发 “ 我 是谁” 的表 述危 机 。 阿来在 《 地 的 阶梯 》 大 中描 述 了嘉 绒藏 族
特 有 的心 态 :真 正 的 当地 人把 我们 当成汉 人 , 到 了真正 的 “ 而 汉 人地 方 , 我们 这种 人 又 成 了藏 族 了 。真正 的 藏族 和 真正 的
认 同 与 汇 父 交 L
论文化 身份 “ 困境 ” 中的阿来
口 刘 云 生
毋庸讳 言 , 阿来 作 为极 具 代 表 性 的少 数 民族 作 家 . 的 他 《 尘埃 落地 》 作 品在 主流 文 学评 价 中获得 热 烈 赞誉 的 同时 , 等
却 不 得不 接受 一种 近乎 偏 执 的质疑 。有 研究 者认 为 阿来 的创 散 文 、 谈 和演 讲 中 。 访 阿来 都 特 别 强 调 自己 创作 中身 份 构 成
身份感 充 满着 不确 定 。这 种“ 身份 边界 的模 糊或 破碎 ” 生 的 产
即使 面对 这样 的指 责 ,阿来 做 出 的 回应 也 极 为低 调 和谨 慎 。
阿 来强 调 , 当你 所处 的 民族还 没 有 达到 同你 一样 的理性 层 面 时 , 想对 它有 所 批评会 有 些不 忍 。因为一 旦 批判 它 , 你 就会 被 认 为站 在 强势 文 化 这一 面 。其 实 , 阿来 的这 种创 作 压 力与 其 说是 来 自个 体 的文 化 身份 困境 . 不如 说 是代 表 着 少 数 民族 作 家 在现 代性 进 程 中力 求构 建 面 向 未来 的 、 型 的文 化 与 自我 新 身 份的不 易 。
赏时 , 有足 够 的智 力去 拨云 见雾 、 能 曲径 通 幽。
论阿来_尘埃落定_中的身份认同

第28卷第3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8No.3 2008年5月 Journal of South-C 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 ciences) M ay2008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唐红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以藏族作家阿来的代表作《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为研究对象,细致辨析了其中主人公“傻子”形象及其意识特征,指出了这一形象负载的再现嘉绒藏族历史、塑造藏族文化身份的积极作用,进而探讨了这一形象体现出的作家阿来的身份认同策略,积极评价了阿来对藏族文化身份的新理解。
关键词:阿来;《尘埃落定》;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8)03-0167-04 2000年,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创作的更多关注。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围绕其小说创作体现的文化身份认同,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其文学创作实现了对狭隘的民族自我的超越,另一种则因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跟普通的不懂汉语的藏族人的距离,而对其创作及其体现的文化身份采取了一种含蓄的批评态度。
前者以徐新建等的观点为代表,后者主要由藏族学者德吉草提出[1]。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阿来代表作《尘埃落地》中的“傻子”形象,探讨阿来创作中身份认同策略的具体体现途径和特征,来回应以上两种批评观点,并提出关于阿来小说创作身份认同的不同看法。
一、《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及其意识特征在谈到创作《尘埃落定》的最初动机时,阿来曾说:“我只是想,作品究竟会写多长,取决于小说中的人物有意思的时间有多长,而我惟一想做的是在社会文明进步、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寻找到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精神,在藏族民间,在怀旧的情绪中,我找到了这种精神。
身份问题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以阿来为个案

J 0URNA F JXI U VE I Y L O I NI RS T
Vo.1 J 0
o2 .
21 0 0年 4月
A r2 0 p . 01
文 章 编 号 :6 2— 78 2 1 )2— 13— 17 6 5 (0 0 0 0 0 2
立 观 察 和思 考 的立 场 。
是藏族人 , 亲是汉族 人 , 出身来看 , 就是一 个汉藏 母 从 他 混血儿 , 身上流 淌着 两个 民族 的血 液。在这样 的背景下 ,
阿 来 对 于 汉 人 和 汉 文 化 的 认 同 是 自然 的 。“ 从童 年 起 , 一
从先锋小 说发起叙 事革命 开始 , 小说 写作 就不仅 是 再现经验 , 讲述 故事 , 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和语 言的创 造。先锋派 、 写实 主义等文体试验对文学传 统的反驳 、 文
学的商品化 、 私语 化等 , 以及女 性 主义批评 、 殖 民主义 后
个藏族 人就 注定 要 在两种 语 言之 间流浪 , 小学 , 中 从 到 学 , 到更 高等 的学校 , 再 我们学习汉语 , 用汉语 , 使 回到 日
常生活中 , 又依然用 藏语 交流 , 表达 我们看 到 的一切 , 和
对 于 文学 商 品化 、 业 化 的 反 驳 和 对 精 英 文 学 立 场 的 坚 商
传说 、 寓言故事等。在《 尘埃落 定》 , 有 丰厚的藏族 文 中 “
化意蕴 , 清淡的一层魔幻 色彩 增强 了艺术 表现 开合 的力 度 , 言轻巧而富有魅力 ……充满灵动的诗意” 语 。不仅 如
此 , 来 小说 还 吸收 了汉 文化 的精髓 , 现 出汉化 的特 阿 呈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阿来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
毫无疑问,这是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关键词】阿来小说文化身份认同超越
阿来,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
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
主要作品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长篇地理散文《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
《尘埃落定》,198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对阿来文学创作更多的关注。
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创作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阿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论,往往绕不开对“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解读和阐释。
那么什么事民族文学那?“从广义上来说,作为生命个体的创作,所有的文学,都是民族文学,都是由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生命个体创作的。
每一个作家,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身份进行创作的,也必然地要进行他所选择的文化表达,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在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就自然的获得了某种文化意义,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换句话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民族文学的创作,任何作品,都是民族文学的作品。
”[1]但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主体、各民族共存的多民族背景下,民族文学又有了特别的意义,一般指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即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作家是少数民族,二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或者反映了民族生活。
阿来的小说创作具有以上鲜明的特点。
他从本民族的深厚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通过文学话语,来建构自我作为藏民族个体的文化观。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陷入“民粹主义”偏执的狭隘视角。
在对汉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比较中,使作者对自我的民族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阿来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鲜明特色。
毫无疑问,这是民
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阿来的小说创作既坚持不懈地把艺术触角深入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茫茫的历史迷雾中寻找民族文化的踪迹;又在不断地寻找中为民族文化的当代转换和重构探寻着超越之路。
阿来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是不断嬗变的。
阿来在《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一文中指出,“我是一个藏族人”,作为一个“跨族别”、“跨文化”体验者,虽然“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但始终依靠着母族文化,在回归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原乡。
藏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汉语嫁接后的语言形式,形成了一个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在这种新的“第三语言的空间”,在叙述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发散式的语言系统,为阿来的文学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阿来的早期作品所表现的文化身份呈现为单向度,即确认“自我”(藏文化),拒斥“他者”(非藏文化)。
它通常将小说背景至于清净明朗而相对封闭的藏区高原,故事情节简单。
因此,“阿来早期作品更多的是对古老的藏族文明的认同。
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阿来逐渐意识到他日益陷入族际边缘人的尴尬处境:在藏地他被认为是汉人,在汉地又被认为是藏人,始终无法找到灵魂的归属,与此他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
这种复杂的感情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民族文化深层次的迷恋、对族群文化心理的细致剖析以及作为文化弃儿的焦虑”。
[3]此后阿来逐渐开始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将困惑的目光投向“他者”,其作品塑造的人物不再是单纯的藏族血统,而是更多地赋予双重文化身份。
《空山》着力表现一个村庄的秘史,不再是单一民族的故事,也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传奇,而是对于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的深刻思考。
在阿来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藏民族文化之“根”的深切关注,其实也就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关注,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自觉地、深刻地体认。
阿来对自己民族那份深沉的爱和作为被边缘的藏区——嘉绒人的那份对文化身份的焦虑始终萦绕在他的小说中。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阿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主要落实在对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现代书写和重塑上。
阿来深刻的意识到,文化的“根”对少数民族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融过程中追溯本民族的伤痛史,从而在伤痛中进行反思,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族群文化的神话起源的关注是阿来创作中非常明显的特点,通过对神话传说的借用和改写,阿来在精神上与嘉绒祖先取得了联盟,沟通了当代社会与民族历史。
嘉绒藏区作为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可以代表藏区今天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剧烈冲击,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关系遭到破坏。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作家,阿来内心的那份焦虑更为集中、猛烈。
因此,通过他的小说,他写出了美好的农耕文明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被工业文明
带来的现代观念一步步吞噬、变异。
阿来所采用的方法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而是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因此他毫不犹豫的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渊源之地——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民间文化。
在民间文化的海洋里,阿来试图寻找一种能够为民族的当代发展提供积极意义的精神启迪,从而在强化本民族社群与个体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激活传统文化中潜藏的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因素。
阿来既是一个不断回望历史的艺术追求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自觉地超越意识的作家。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艺术视角固定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肌体上沉迷不移,而是始终以一种阔大视野在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寻求民族文化的嬗变与提升。
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指引下,阿来的创作表现出了颇具力度的批判意识和清醒的超越意识。
在阿来的文学视野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延续的“根”,没有了它,一个民族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因此,追溯民族文化的根源是一个民族确立自身存在的根据。
但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一种被过滤的单一存在,鉴于此,在追溯传统文化根源时,必须持有足够的批判意识,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在发展中获得新的力量,从而继续向前拓进。
在《格萨尔王传》种,作者对这种批判意识展开了充分的实践。
“格萨尔王”是在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他已经内化为藏族文化心理的一种文化“本能”,被“历史化”为一种本真的存在,从而取代了历史的真实。
于是藏族文化中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不断地给“格萨尔王”增添想象的成分,不断地神化与“格萨尔王”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比如说关于它的说唱,使其越来越神秘化,从民间滑向了天界。
作为一种艺术产品,这样的艺术处理毫不为过,但在历史研究中把它也神化,则是缺乏理性精神和现代超越意识的表现。
阿来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弊病,对于神话题材的在创作,他采取了一种世俗化的路径。
“格萨尔王”就是一个传说而已,说唱者也不过是凡夫俗子。
显而易见,阿来对这个原本严肃的话题进行了降格处理,他追求的是一种贴近生活现实的文学叙事,尽管他选取的题材充满了神圣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文化态度,那其中包含的文化批判意识确实是很有力度的。
与批判意识相伴随的是阿来的超越意识。
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时阿来表示:“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种比较笼统的说法,我是一直不以为然的。
从老派一些的文学方式出发,这种提法容易倡导一种外在的风俗化的写法。
外表上具有一些现代感的,又很容易找到一些甚至一堆文化符号……所以,我并不认为《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或那片特别的地理状况的外在景观。
当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读者有权猎获一些奇异的东西,特别的东西,都市生活里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体味的东西”。
[2]看得出,追求一种具有人类存在普遍意义的艺术境界,是阿来创作所渴求的目标。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藏族是具有浓厚宗教信仰的民族,“格萨尔王”故事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宗教因素的巨大影响。
作者在《格萨尔王传》的写作中,
很注重对宗教情感的艺术处理,强调“淡化宗教色彩,甚至还有些反宗教的意味。
在对格萨尔这一中心人物的刻画中,突出了其人性的一面,并借鉴其他民族对史诗英雄的塑造手法。
这样,在内容和形式上,阿来实现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批判性反思与超越。
参考资料
[1]余达忠.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建构[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2]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N].新华网.2008
[3]胡志明、秦世琼.族群记忆与文化多样性书写——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J].
江淮论坛.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