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国看中国人
论1 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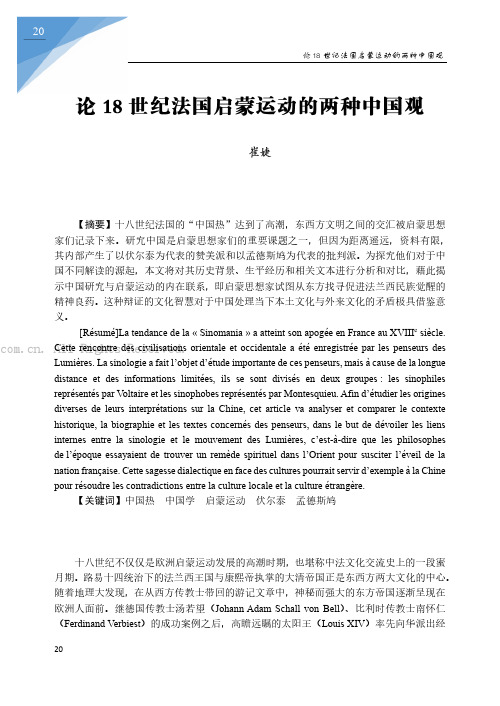
【摘要】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达到了高潮,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被启蒙思想家们记录下来。
研究中国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因为距离遥远,资料有限,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
为探究他们对于中国不同解读的源起,本文将对其历史背景、生平经历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和对比,藉此揭示中国研究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即启蒙思想家试图从东方找寻促进法兰西民族觉醒的精神良药。
这种辩证的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处理当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极具借鉴意义。
[Résumé]La tendance de la « Sinomania » a atteint son apogée en France au XVIII e siècle. . All Rights Reserved.Cette rencontre des civilisations orientale et occidentale a été enregistrée par les penseurs desLumières. La sinologie a fait l’objet d’étude importante de ces penseurs, mais à cause de la longuedistance et des informations limitées, ils se sont divisés en deux groupes: les sinophilesreprésentés par Voltaire et les sinophobes représentés par Montesquieu. Afin d’étudier les originesdiverses de leurs interprétations sur la Chine, cet article va analyser et comparer le contextehistorique, la biographie et les textes concernés des penseurs, dans le but de dévoiler les liensinternes entre la sinologie et le mouvement des Lumières, c’est-à-dire que les philosophesde l’époque essayaient de trouver un remède spirituel dans l’Orient pour susciter l’éveil de lanation française. Cette sagesse dialectique en face des cultures pourrait servir d’exemple à la Chinepour résoudre les contradictions entre la culture locale et la culture étrangère.【关键词】中国热中国学启蒙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十八世纪不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堪称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蜜月期。
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18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上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
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17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17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775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
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
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
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省略。
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已经详细讨论,《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一一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吴莉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此也有深入分析,因此本书不再为此多施笔墨,而要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
本书要谈论的是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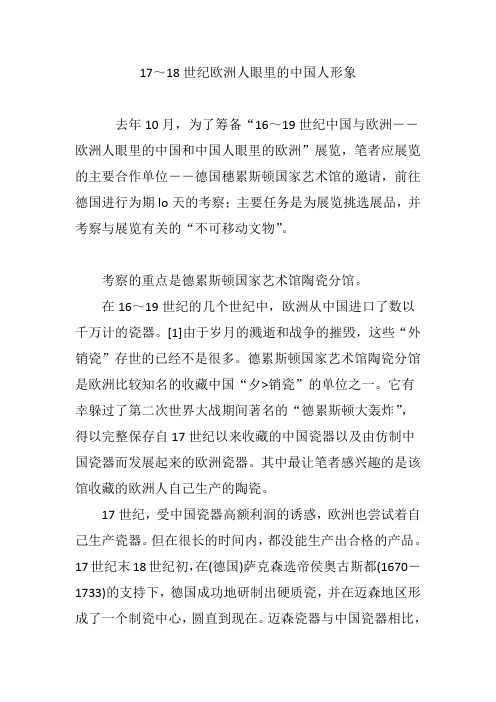
17~18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去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穗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lo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
[1]由于岁月的溅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夕>销瓷”的单位之一。
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17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
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17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
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德国成功地研制出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圆直到现在。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到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
图一、图二是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的―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我们中国人见此,恐怕没有人会不忍俊不禁的。
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不过,是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在l7~18世纪,由于东西方的隔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
他们或是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文字描写,或是根据去过中国南部沿海经商的欧洲商人、水手的描述,或是根据中国漆器、瓷器、手工艺品和绘画作品上的图案,甚至仅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甚至把近东、中东的许多因素误加在中国人身上。
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

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拐点
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法王路易十五与他的大臣贝尔坦商讨革除国家流弊的对策。贝尔坦提出要对民众的普遍精神进行改造,法王问:“你有何打算?”贝尔坦答:“陛下,为法国人灌输中国精神。”这件事发生在18世纪上半叶,时值欧洲启蒙运动高潮和中国的乾隆盛世,它反映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在这场借助对中国文化的解读而实现自我批判和更新、为现代欧洲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文化变革之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变化,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连续几个世纪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与美化渐行渐远了。
启蒙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和创新运动。它为欧洲未来的发展树立起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从此,历史有了民主与专制、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世界有了进步与停滞、文明与愚昧之隔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是大革命前夜的一次思想洗礼和文化动员,它要号召人们进行战斗,就需要理性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现代和传统的截然分明的对立。这样,法国的启蒙思想就停留在历史矛盾的绝对对立之上,缺少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种思想方法上的弱点,使得它在树立现代价值标准的同时,不仅隔断了它与欧洲中世纪的联系,也隔断了它与中国、东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联系,并把其他文化推到了西方的对立面。无形之中,启蒙运动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提供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文化价值标准,世界被一分为二了。
近代史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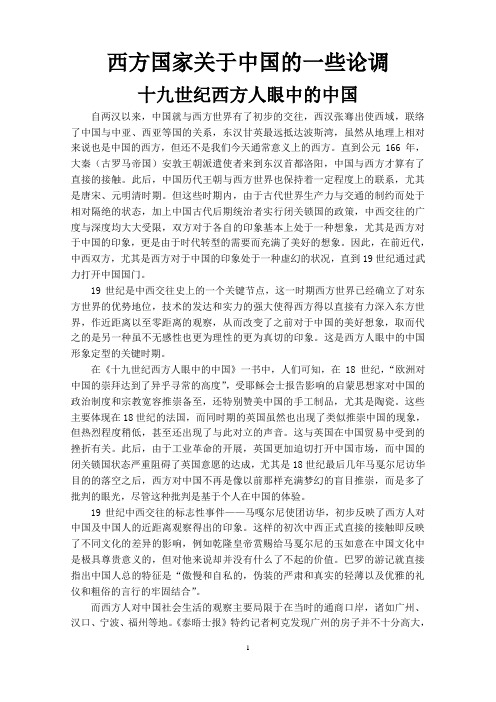
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
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
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
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
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
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
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
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十八世纪欧洲画家对中国风俗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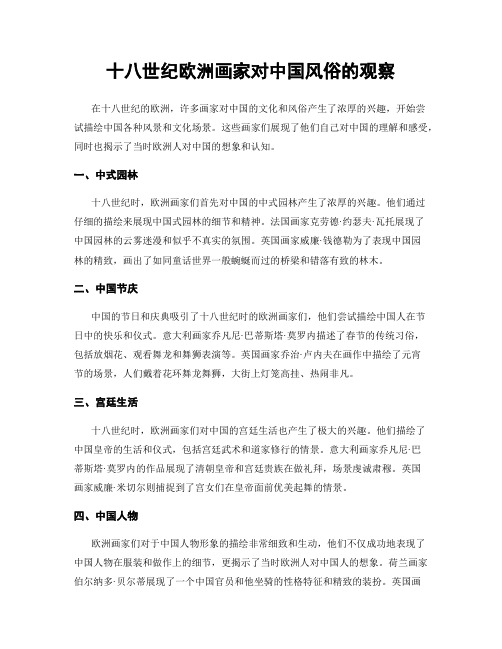
十八世纪欧洲画家对中国风俗的观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许多画家对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尝试描绘中国各种风景和文化场景。
这些画家们展现了他们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揭示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
一、中式园林十八世纪时,欧洲画家们首先对中国的中式园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通过仔细的描绘来展现中国式园林的细节和精神。
法国画家克劳德·约瑟夫·瓦托展现了中国园林的云雾迷漫和似乎不真实的氛围。
英国画家威廉·钱德勒为了表现中国园林的精致,画出了如同童话世界一般蜿蜒而过的桥梁和错落有致的林木。
二、中国节庆中国的节日和庆典吸引了十八世纪时的欧洲画家们,他们尝试描绘中国人在节日中的快乐和仪式。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莫罗内描述了春节的传统习俗,包括放烟花、观看舞龙和舞狮表演等。
英国画家乔治·卢内夫在画作中描绘了元宵节的场景,人们戴着花环舞龙舞狮,大街上灯笼高挂、热闹非凡。
三、宫廷生活十八世纪时,欧洲画家们对中国的宫廷生活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描绘了中国皇帝的生活和仪式,包括宫廷武术和道家修行的情景。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莫罗内的作品展现了清朝皇帝和宫廷贵族在做礼拜,场景虔诚肃穆。
英国画家威廉·米切尔则捕捉到了宫女们在皇帝面前优美起舞的情景。
四、中国人物欧洲画家们对于中国人物形象的描绘非常细致和生动,他们不仅成功地表现了中国人物在服装和做作上的细节,更揭示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象。
荷兰画家伯尔纳多·贝尔蒂展现了一个中国官员和他坐骑的性格特征和精致的装扮。
英国画家威廉·丹肯则描绘了一个在园林中行走的中国学者,武术功底深厚,从他的样子和举止中可以察觉到他的阅历和博学。
总之,十八世纪的欧洲画家们对中国的风俗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描绘,这些画作不仅保存了当时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也成为了中国风俗史和艺术史上的重要记录。
别笑,严肃点!看看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啥样

别笑,严肃点!看看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啥样18世纪法国美术最显眼的就是洛可可艺术风格。
洛可可艺术影响有多大?如今洛可可一词成为西式皇家、贵族样式的代名词,充斥在从服装服饰、婚纱影楼到家居装修各个角落里。
其实,18世纪的洛可可艺术跟中国艺术有着不解之缘。
洛可可艺术的表现就是在家具和建筑装饰上多采用C形、S形或者漩涡形的曲线,这种灵感来自于中国瓷器的装饰。
洛可可时期家具洛可可时期家具中国,青花瓷。
中国瓷器上的装饰多为曲线形,这种装饰被认为影响到了法国洛可可艺术。
中国的英文为“china”意思就为瓷器。
虽然瓷器在中国历史悠久,但在直到19世纪,瓷器才被西方人烧制成功。
在此之前,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的瓷器是由鸡蛋壳和某种贝壳混合而成的液体浇铸而成,此处真的是脑洞大开啊!不过,这并不影响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狂热,收藏瓷器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当时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瓷器有些是直接出口的,有些来自于西方人的定制,而西方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中国的瓷器。
问题是我们的瓷器从来不描绘当时陶工所处时代的东西!反而经常描绘戏剧人物,比如这个清康熙年间的“五彩人物纹瓶”主题就来自于《隋唐演义》:秦叔宝策马迎战尉迟恭,唐王李世民和徐茂公临城观战,空间衬以矮山花树。
这种图案俗称“刀马人”。
清朝的人根本不穿这样的衣服!所以,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有时候真的可以用“稀奇古怪”来形容了,比如洛可可艺术的代表画家布歇就很喜欢中国的东西,他先后画了《有中国人物的风景》、《中国皇帝上朝》、《中国捕鱼风光》、《中国花园》和《中国集市》等中“中国风”作品。
布歇,曾任法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他的绘画风格深受贵族喜欢,他二十岁就获得了美术学院展览会的一等奖,然后就去了意大利留学。
不过学成归来的布歇,其风格却是地地道道法国皇家气派。
布歇肖像布歇《浴后的狄安娜》,狄安娜是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孪生姊妹,她司职月亮女神、狩猎神。
此外,狄安娜也是妇女和儿童的守护神。
【转】18世纪末,欧洲开始轻视中国-金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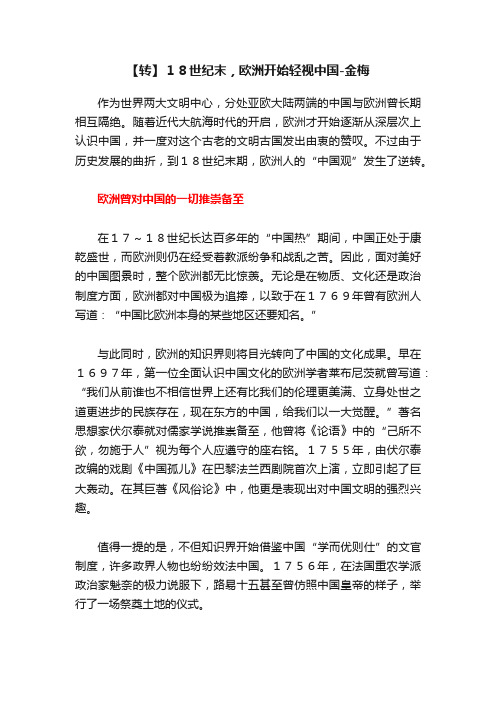
【转】18世纪末,欧洲开始轻视中国-金梅作为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分处亚欧大陆两端的中国与欧洲曾长期相互隔绝。
随着近代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欧洲才开始逐渐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并一度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发出由衷的赞叹。
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逆转。
欧洲曾对中国的一切推崇备至在17~18世纪长达百多年的“中国热”期间,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而欧洲则仍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
因此,面对美好的中国图景时,整个欧洲都无比惊羡。
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致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与此同时,欧洲的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
早在1697年,第一位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欧洲学者莱布尼茨就曾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
”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
1755年,由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上演,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其巨著《风俗论》中,他更是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不但知识界开始借鉴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
1756年,在法国重农学派政治家魁奈的极力说服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祭奠土地的仪式。
欧洲知识界嘲笑中国文化然而到18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一改“中国热”流行时的论调,转而鄙视中国文化。
比如孟德斯鸠在写《论法的精神》的时候,就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暴政。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沃尔内也把中国政治概括为棍棒专制主义。
同一时期的法国作家德·萨德甚至描写道:“中国皇帝与官吏不时地采取措施,逼迫人民造反,然后从中获得血腥屠杀民众的权力。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书摘->2006年第1期十八世纪法国画家笔下的中国“猴形人物”刘海翔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曾掀起过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哲学、艺术、中国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开明君主制”等等,都是法国宫廷和主流社会里时髦的谈论话题和积极的摹仿对象。
本文作者十多年前赴美留学,十分关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他曾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短期研究工作,深入该馆库房探访亚洲部藏品,也曾四访欧洲,探寻欧洲艺术“中国风”的遗迹,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品味艺术品上记载的世纪风云。
《欧洲大地的“中国风”》一书,就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该书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将大量“中国风”的图例贯穿起来,再现十八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一个特殊风貌。
下面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章。
一、“猴形人物”(法语:Singerie)现象在十七世纪快要落下帷幕的时候,让·贝然(Jean Bérain)在把中国艺术的素材引入他的装饰设计中去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支流——“Singerie”,即猴形人物。
在猴形人物作品中,猴子穿着人的服装,做着人的事情。
他用猴子代替了传统艺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的形象,创作了一些这一类的作品。
后来比较正式地画“猴形人物”的,是华铎的老师克劳德·奥德安,他在1709年装饰玛利城堡时,作了一幅猴子坐在桌边的画。
后来,华铎也画过一幅“猴子画家”(法语:Les Singes-Peintres)的图画。
其实贝然、奥德安和华铎笔下的猴子,就像一群衣着光鲜的巴黎人,只不过他们猴性十足,在造型中显示出一种轻松的幽默和略微的讽刺。
也有学者考证说,早在十六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人们就已习惯地把雕塑家和艺术家戏比作猴子。
到了1735年,当克里斯托夫·休耶在香地里城堡画了一“大幅猴形人物”(法语:Grande Singerie)画作的时候,其装饰图案已经非常华丽复杂,要仔细察看才能分辨出图案中部两侧的猴形人物。
也就是从这幅图画开始,“猴形人物画”的特性趋于鲜明。
(附图59)也是在那一年,休耶为波旁公爵作了十幅涉及中国和东方人物的画。
在休耶的“大幅猴形人物”画中,那些猴形人物开始穿上中国衣袍。
比如其中有一幅表现身穿中式衣服的东方人物悬空似地坐在棕榈树叶上,看着一群猴子在拉紧的绳索上表演走绳索。
那组画的一个明显特征,便是画家只是随意地借用东方题材,来达到一种表现异国情调的装饰目的。
二、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状况的了解在进一步探讨“猴形人物”之前,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服饰等习俗的了解。
早在1667年的一幅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印制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铜版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穿戴的中国宫廷服饰被很写实地描绘了出来。
汤若望于1591年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他本人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最早期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
在德国完成学业后,他跟随金尼阁神父于1622年抵达中国,先学习汉语,他曾在西安居住过若干年,后来常住在北京。
在中国期间由他推算的月食发生时间,三次都应验了,从此他在天文方面的声誉大振。
由于汤若望的天文知识,1650年他被满清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任命为天象署的一个官员,负责观察天象,制定日历。
但在顺治驾崩后,汤若望获罪被关押,于1666年死于中国监狱。
(附图60)这幅铜版画就是画了穿着中国宫廷服装的汤若望。
这幅肖像表明,当时欧洲的画家其实是看到过中国服饰的真实模样的。
曾有人向路易十四进贡过一组描绘中国不同等级官员的画像,后来吉法尔用铜版制作了印刷版,并有布维神父的说明文字,于1697年以“中国现状”(法语:L' 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为题出版。
这些铜版画相当尊重原作,如果把它们和贝然或华铎的画作做一个对比的话,人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贝然和华铎的作品和中国原型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甚至可以说相差甚远。
而休耶的“猴形人物”,就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当时在清朝担任宫廷画家的郎世宁也画过猴子。
与“猴形人物”把人物画成上蹿下跳的猴子形状相反,郎世宁笔下的这只猴子姿态神情优雅高贵,好像有几分人气和灵性。
而差不多同时期在德国梅森出产的陶瓷猿猴(附图61),是由约翰·基希纳在大约1735年前后制作的,它怎么看也就是一只猿猴,没什么特别动人之处。
而郎世宁的画则有所不同,从郎世宁的画中,观者好像可以感觉到此猴非猴,颇有人性。
郎世宁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艺术传神写照,落笔有情的特点。
另一个可以说明当时的欧洲画家,实际上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服饰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这幅插图中看出来。
(附图62 ,“中国驯鸟人”,Chinese Man with Bird))在这件欧洲瓷器的彩饰画上,一位东方人物头戴插有孔雀羽毛的毡帽,左手提着个鸟笼,右手托着一只长尾斑鸠,一幅悠闲自在的样子。
尤其是驯鸟人留着两撇长胡子,形象生动有趣,姿态诙谐自然,可以看出“中国风”画家的绘画功底。
再来看看这幅“中国驯猴图”(附图64),这是一幅十八世纪时的中国绘画作品。
画中人物百态,神色各异,生动自然,皆勃勃有生气焉,其中一群人围观正在做着把戏的猴子,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闹市街景图”。
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对人物和猴子的形象描绘很有把握,画得栩栩如生,但并没有表现出对透视原理的在意,象是兴之所至,一组一组场景单独地画出来的。
在1751至1752年间,意大利著名画家提耶波罗(1696至1770年)应德国王子之邀,为其在乌尔兹堡的行宫创作壁画。
从乌尔兹堡行宫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台阶上抬头仰望,行宫内精雕细刻,在工整的对称中有生动的细节装饰(附图65)。
提耶波罗在楼梯顶的天花板上,画了一幅“四大洲寓言”,表现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各色人种在各大洲的生活。
虽然和其它三大洲的画面比起来,“亚洲”部分的画面显得较为简单,塑造的人物也比较少,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说出这些人的种族,其中包括一位撑着布伞、戴着尖帽的男子,和一位留着长须的老汉。
(附图66、67)能够证明欧洲至少有部分人知道中国人的长相衣着之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陪同马戛尔尼公爵使华的威廉·亚历山大在1805年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服饰:中国人衣着及举止图例》,用整本书专门介绍中国的服装,中国人的相貌及其举止神态等等,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身穿朝廷命服的官员,拿着烟枪在吸着他的水烟。
衬托该人物的背景相当简单,只有一些树木和依稀可见的寺庙。
然而该图详实逼真地描绘了人物的面部形象和表情,也如实地画出了他所穿的官服:他头顶帽子上镶着的孔雀羽毛顶戴,是皇上赏赐的象征,他脖子上还挂着珍珠玛瑙项链。
三、为什么会出现“猴形人物”?前面所谈到的这些现象,让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既然欧洲人知道并了解当时中国人的真实模样,为什么在这么多“中国风格”的作品中,像布歇的“中国钓鱼聚会”这样比较忠实地再现东方人和他们的生活场景的作品却比较少,为什么在“中国风格”作品中,许多人物都被画得古里古怪,甚至还有“猴形人物”?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可以来看看出自乾隆年间的一件中国镀铀玻璃瓶。
在这个玻璃瓶上,由花形装饰在瓶肚上形成一个画框,画框里画的是休闲的欧洲人物,画面上的人物形象生动,衣饰鲜艳,并采用了明暗对比法创造出立体效果,用透视法形成远近大小的视觉效果。
这件工艺品显示,如果想要做的话,中国艺术家也能忠实地画出欧洲人的真实面目。
当时的中西方艺术家对彼此的真实外貌,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对“猴形人物”的一个解释,就是欧洲艺术家在创作“中国风格”作品时,有意夸张变形甚至歪曲了人物的形象,并且把这些人物形象放在一种虚渺的境地里,以制造出一个奇异和有趣的氛围。
人们能想象欧洲贵族们在自己家中的私人空间里,愿意整天与形象逼真的外国人物朝夕相处吗?不仅如此,欧洲画家笔下的猴子,也经常穿着欧式服装。
这幅“举枪的猴形人物”(Singerie with Gun) (附图63),就是猴形人物画的典型作品之一。
这只毛猴穿着的是法国军服,手举毛瑟枪,正在向着猎物瞄准射击。
看着它那聚精会神、煞有介事的样子,后面却拖着一只长尾巴,看了真是让人忍俊不住。
有艺术评论家认为,把外国人物画成猴子,或者把外国服装穿在猴子身上,这种通过图像来表达的丑化,代表了一种文化偏见,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曾经也有欧洲学者认为,“猴形人物”的出现,是因为欧洲人的狂妄自大,因为他们把中国人看作是生活在树上的半开化人群。
但是问题似乎不应该这么简单地归类划一。
实际上,早在“中国风格”流行之前,欧洲艺术中就有“猴形人物”,而且在西方文化中猴形人物也带有某些寓言的味道。
艺术史家詹森在他写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猿猴与猿猴传说》一书中就有很详细的阐述。
猴子三分像人的长相和它们善于摹仿的本能,使它们成了盲目摹仿的象征。
在华铎的“猴子画家”里,猴子在画一个用假人做的模特,也有恶作剧的作品,比如一个匿名画家便把蓬巴杜夫人的一幅为人们所熟知的肖像改头换面,画上了一个猴子的头部。
同样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喜的孙悟空,就是一个猴子的形象,而孙悟空是正义、智慧、诙谐的代表。
相信自《西游记》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孙悟空的猴子形象,而认为这是作家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或者污蔑。
中国和欧洲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标准,可能也造成了这种图像上的变形曲解。
在中国传统国画中,景物是主要的内容,人物常常是用简单的笔法带过,只是景物的点缀,表现出一种神似。
而久经欧洲传统(希腊式)学派熏陶的欧洲艺术家则强调形似。
他们不能容忍中国艺术中简约的人形,评论家路易·勒康特在1699年这样写道:“真希望中国人在瓷器上的画能够更漂亮一些……”,他认为“人物的画像都被糟蹋了,他们使只能通过这种载体来了解他们的外国人心生困惑,让外国人以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像瓷器上画的人物那样滑稽可笑。
”英国作家约翰·夏比尔(1709至1788年)在1755年写了《英国书简》一书,该书假托是翻译自一位在伦敦居住多年的意大利传教士所写的原文。
对“中国风格”作品,特别可能是针对“猴形人物”作品,他这样挖苦道:“放眼望去,几乎皆是中国之物……家居中的每把椅子、桌子、镜子的围框等等,都必须是中国的:墙上贴满的是中国壁纸,上面画满了根本就不像是上帝所造之人的人物,在一个谨慎的国度里,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应当让孕妇看到。
”他还指出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中国建筑的狂热是如此之盛,以至当今的贵族狩猎者在打猎的过程中,骑马越栏不慎摔坏了腿的时候,如果那门不是东方式的向四处伸展的柴扉,他都会觉得不过瘾。
”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热在当时确实是很热,也是很时髦的事物,并不能简单绝对地归为“文化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