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教育改革如何面对“钱学森之问”,谈谈你的看法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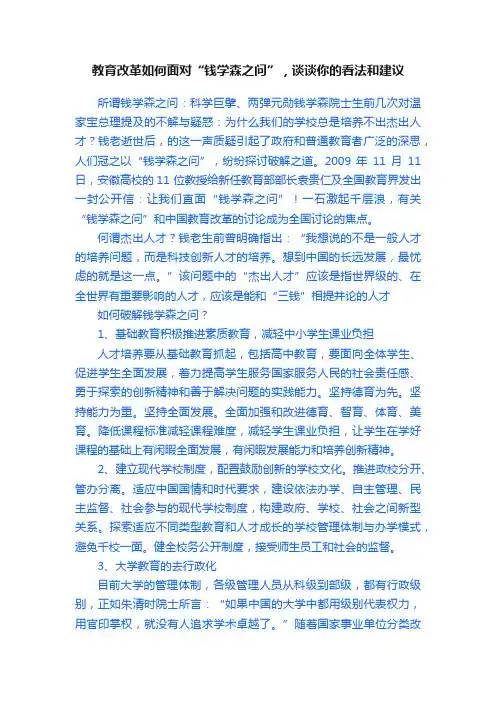
教育改革如何面对“钱学森之问”,谈谈你的看法和建议所谓钱学森之问:科学巨擘、两弹元勋钱学森院士生前几次对温家宝总理提及的不解与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逝世后,的这一声质疑引起了政府和普通教育者广泛的深思,人们冠之以“钱学森之问”,纷纷探讨破解之道。
2009 年11 月11 日,安徽高校的11 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钱学森之问”和中国教育改革的讨论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
何谓杰出人才?钱老生前曾明确指出:“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想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该问题中的“杰出人才”应该是指世界级的、在全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人才,应该是能和“三钱”相提并论的人才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1、基础教育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人才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包括高中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坚持德育为先。
坚持能力为重。
坚持全面发展。
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降低课程标准减轻课程难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在学好课程的基础上有闲暇全面发展,有闲暇发展能力和培养创新精神。
2、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配置鼓励创新的学校文化。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
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
3、大学教育的去行政化目前大学的管理体制,各级管理人员从科级到部级,都有行政级别,正如朱清时院士所言:“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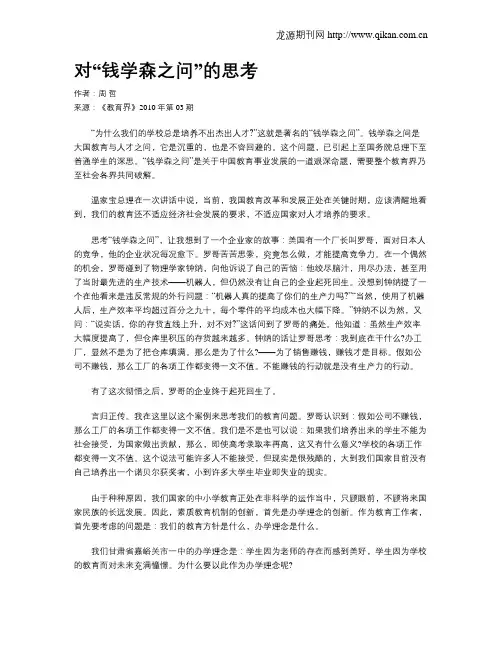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作者:周哲来源:《教育界》2010年第03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间是大国教育与人才之问,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个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思考“钱学森之问”,让我想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故事:美国有一个厂长叫罗哥,面对日本人的竞争,他的企业状况每况愈下。
罗哥苦苦思索,究竟怎么做,才能提高竞争力。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哥碰到了物理学家钟纳,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他绞尽脑汁,用尽办法,甚至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机器人,但仍然没有让自己的企业起死回生。
没想到钟纳提了一个在他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外行问题:“机器人真的提高了你们的生产力吗?”“当然,使用了机器人后,生产效率平均超过百分之九十,每个零件的平均成本也大幅下降。
”钟纳不以为然,又问:“说实话,你的存货直线上升,对不对?”这话问到了罗哥的痛处。
他知道:虽然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了,但仓库里积压的存货越来越多。
钟纳的话让罗哥思考:我到底在干什么?办工厂,显然不是为了把仓库填满。
那么是为了什么?——为了销售赚钱,赚钱才是目标。
假如公司不赚钱,那么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不能赚钱的行动就是没有生产力的行动。
有了这次彻悟之后,罗哥的企业终于起死回生了。
言归正传。
我在这里以这个案例来思考我们的教育问题。
罗哥认识到:假如公司不赚钱,那么工厂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为社会接受,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即使高考录取率再高,这又有什么意义?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变得一文不值。
这个说法可能许多人不能接受,但现实是很残酷的,大到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自己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获奖者,小到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关于_钱学森之问_的遐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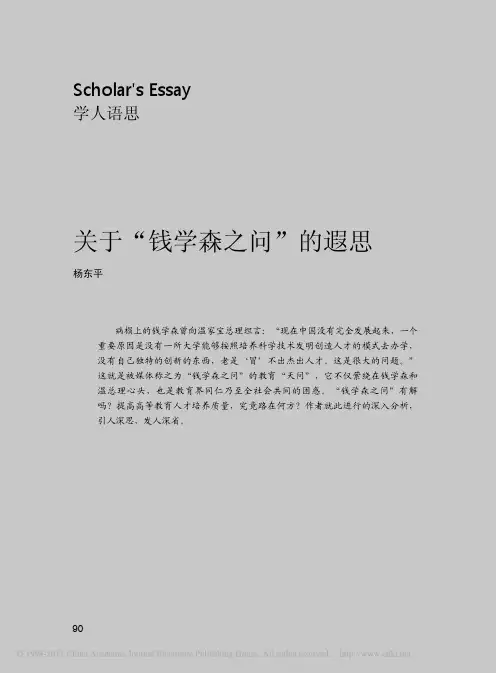
学人语思Scholar's Essay关于“钱学森之问”的遐思杨东平90病榻上的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坦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被媒体称之为“钱学森之问”的教育“天问”,它不仅萦绕在钱学森和温总理心头,也是教育界同仁乃至全社会共同的困惑。
“钱学森之问”有解吗?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究竟路在何方?作者就此进行的深入分析,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90不久前,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公开信,信中写道:“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
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人的最后遗言,大多是无所顾忌、一吐为快的。
因而,赵丹讲真话,说管得太多了,文艺没希望。
巴金讲真话,希望反思“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
病榻上的钱学森则向温家宝总理坦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被媒体称之为“钱学森之问”的教育“天问”,它不仅萦绕在钱学森和温总理心头,也是教育界同仁乃至全社会共同的困惑。
随着老一辈大师的相继离去,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一个比较直接的统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至2008年共有14位获奖者(其中2004年度空缺)。
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80岁,大多数毕业于1949年之前。
近些年来,尽管我们在国防科技、工程技术、基本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真正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科学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初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就几乎没有达到世界前沿的高水平成果。
对钱学森之问的理解和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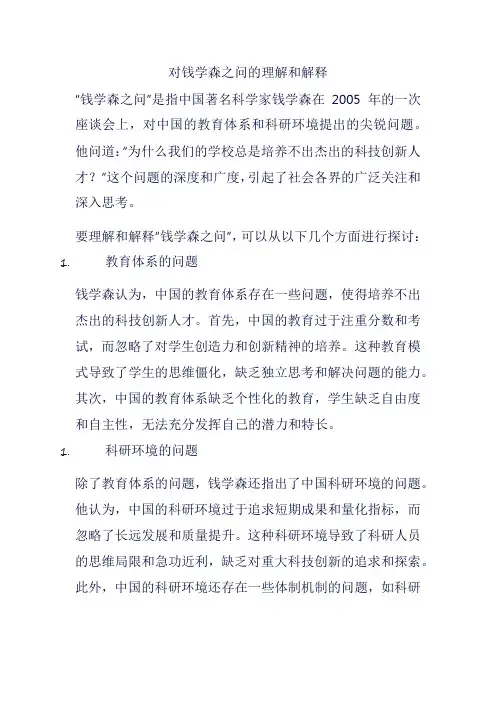
对钱学森之问的理解和解释“钱学森之问”是指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2005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环境提出的尖锐问题。
他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这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
要理解和解释“钱学森之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教育体系的问题钱学森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首先,中国的教育过于注重分数和考试,而忽略了对学生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这种教育模式导致了学生的思维僵化,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中国的教育体系缺乏个性化的教育,学生缺乏自由度和自主性,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
1.科研环境的问题除了教育体系的问题,钱学森还指出了中国科研环境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科研环境过于追求短期成果和量化指标,而忽略了长远发展和质量提升。
这种科研环境导致了科研人员的思维局限和急功近利,缺乏对重大科技创新的追求和探索。
此外,中国的科研环境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如科研资金分配不公、科研人员评价机制不合理等,这些也制约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1.社会文化的问题“钱学森之问”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些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服从、遵守规矩,而创新和独立思考则被视为离经叛道。
这种社会文化氛围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使得培养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更加困难。
此外,中国的社会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浮躁和功利的心态,这也影响了人们对科技创新的追求和投入。
为了解答“钱学森之问”,我们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反思和改革。
以下是一些建议:1.改革教育体系首先,我们需要改革教育体系,注重对学生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这包括改变过分注重分数和考试的教育模式,加强对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考核。
其次,我们需要推行个性化的教育,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特长。
这需要教育机构减少对教育的限制和干预,增加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
“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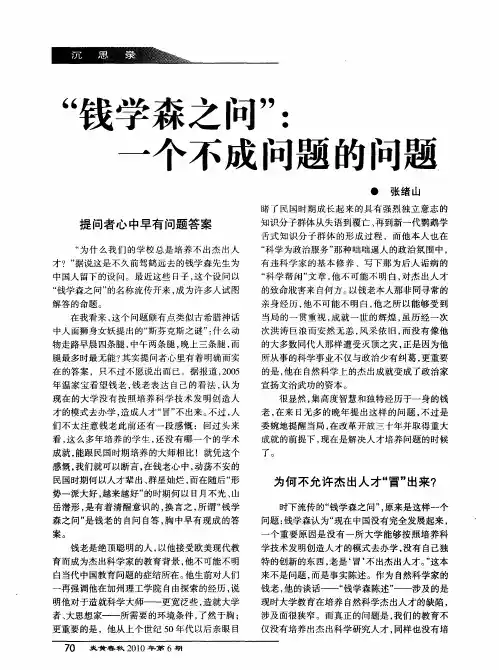
学森之问” 已经 扩 大 了 “ 学 森 陈述 ” 钱
的 内涵 。
19 9 9年 1 2月 8 E 。 泽 民 到 中 国 “ 空 计 划 之 父 ” 学 森 家 l江 太 钱 不过 , 即使扩大了内涵 , 这个提问 中去看 望他。右为 副总理李 岚清( 新华社 ) 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
“ 学森 之 问 ” 钱 的名称 流 传 开来 , 为 许多 人 试 图 成 解答 的命 题 。 在我 看 来 , 这个 问题颇 有 点类 似 古希 腊 神话 中人 面狮身 女妖 提 出 的“ 芬克 斯 之 谜 ”什 么 动 斯 : 物 走路早 晨 四条 腿 , 中午两 条腿 , 晚上 三条 腿 , 而 腿 最多 时最 无 能? 其实 提 问者 心里 有着 明确 而 实 在 的答 案 ,只 不 过不 愿说 出而 已 。据报 道 ,05 20 年 温 家 宝看 望 钱 老 , 老 表 达 自己的看 法 , 为 钱 认 现 在 的 大学 没 有 按 照 培 养 科 学 技 术 发 明创 造 人 才 的模 式去 办学 , 成 人才 “ 不 出来 。 造 冒” 不过 , 人 们 不 太 注意 钱 老 此 前 还 有 一 段 感慨 :回过 头来 看 , 么多 年 培 养 的学 生 , 没 有 哪一 个 的学 术 这 还 成就 , 能跟 民 国时期 培 养 的大 师相 比 !就 凭 这个
中国人 留下 的设 问。最 近 这些 E子 , t 这个 设 问 以
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 、 再到新一代鹦鹉学
舌 式 知 识分 子 群 体 的形 成 过 程 ,而 他本 人 也 在 “ 学 为政 治服 务 ” 科 那种 咄 咄逼 人 的政 治 氛 围中 , 有 违科 学 家 的基 本 修 养 、写 下 那 为后 人 诟 病 的 “ 学 帮 闲 ” 章 , 不 可 能 不 明 白 , 杰 出人 才 科 文 他 对
试答“钱学森之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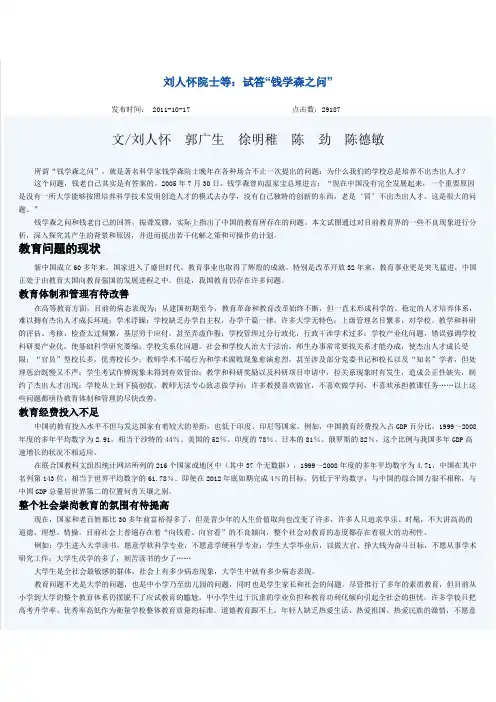
刘人怀院士等:试答“钱学森之问”发布时间: 2011-10-17 点击数:29187文/刘人怀郭广生徐明稚陈劲陈德敏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晚年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钱老自己其实是有答案的。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和钱老自己的回答,振聋发聩,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教育界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进而提出若干化解之策和可操作的计划。
教育问题的现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进入了盛世时代,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中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发展进程之中。
但是,我国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教育体制和管理有待改善在高等教育方面,目前的病态表现为:从建国初期至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始终不断,但一直未形成科学的、稳定的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拥有杰出人才成长环境;学术浮躁;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办学千篇一律,许多大学无特色;上级管理名目繁多,对学校、教学和科研的评估、考核、检查太过频繁,基层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学校管理过分行政化,行政干涉学术过多;学校产业化问题,错误强调学校科研要产业化,使基础科学研究萎缩;学校关系化问题,社会和学校人治大于法治,师生办事常常要找关系才能办成,使杰出人才成长受限;“官员”型校长多,优秀校长少;教师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涉及部分党委书记和校长以及“知名”学者,但处理惩治既慢又不严;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未得到有效管治;教学和科研奖励以及科研项目申请中,拉关系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公正性缺失,制约了杰出人才出现;学校从上到下搞创收,教师无法专心致志做学问;许多教授喜欢做官,不喜欢做学问,不喜欢承担教课任务……以上这些问题都亟待教育体制和管理的尽快改善。
钱学森之问是什么
钱学森之问是什么钱学森,中国的航空航天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誉为中国的航天之父。
他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科技领袖之一。
在他的一生中,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钱学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中国自己的航天事业?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和贫困的时期,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国内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科研体系。
但钱学森坚信,只有通过发展航天技术,中国才能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投资建设航天科研机构、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发展航天工业等。
这些方案的实施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钱学森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这个问题主要是指如何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钱学森看来,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提升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他提出了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投入、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等方案,推动了中国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钱学森还认为,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将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他认为,科技的发展要与社会的需求相结合,要追求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的双向互动。
他提出了加强科技普及教育、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福祉等方案,不仅促进了科技进步,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钱学森之问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
这些问题提醒着我们,科技发展不仅需要关注技术层面的突破,更需要关注社会、经济和教育等领域的发展。
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为中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向。
只有深入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走上科技强国的道路。
总结起来,钱学森之问是一系列关于航天科技发展、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社会发展等重要问题的提出。
“钱学森之问”的解答
“钱学森之问”的解答姓名:程正中班级:072094班2009年10月,我国科学巨匠辉煌而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然而,在钱学森生前,温家宝总理去看望他时,钱老提出了一个“刺痛”整个教育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对于这个艰深的问题,很多教育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钱学森前辈已经给出了他自己的解答,他曾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可见,“钱学森”之问直指了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以及人才培养问题,那么,怎样从实质上和实际上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要回答钱老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何谓“杰出的人才”。
在如今这个时代,引领全球和社会发展的无疑是“科学”,再很多方面和层次上,科学已经成为众多领域衡量的标准;而至于人才,他所具备的实力当然得代表时代前进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一个“杰出的人才”主要就是指“科技创新人才”。
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呢?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曾经给温总理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我觉得关于人才的培养的关键不应该只是教师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各大高校,我们很容易发现,学校依然是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放在首位,虽然近几年来教育部门一直提倡“素质教育”,但现实很明显,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大的改变。
另外高校相对而言的比较强调实践的,但实践的一直都是那些技术上的小细节,没有多少创新的成分,实践也就成了徒劳之举。
纵观我国,建国几十年以来,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反映的不只是科技一个方面,而是科技创新、医学、金融、文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显而易见,这诸多的问题的原因不只是教师的问题,更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问题,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其实,“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
这个人就是李约瑟。
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
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它的背景源自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么多年过去了,“钱学森之问”就像是悬在教育界头上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时不时就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好像教育工作者都被拷问一样。
首先,从钱学森老先生本人的经历来看,钱老是1955年回国的,这个时候,他本人是44岁。
之前虽然有国内求学的经历,但是,他的深造以及科研积淀时期,基本都是在国外所完成的。
基本也可以说明,钱老所受的教育并不是国内所能提供的,科研条件和教育条件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好。
当然了,在他那个年代,能在国外求学、发展,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够做到的。
这里可以看到,钱老说民国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其实,不是国内在“民国”那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其他科学家,基本都有和钱老类似的教育背景。
现在,经常有人津津乐道的一些“民国风范”,其实是说的一些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的表现,那个,确实有古代传统知识分子遗风留存。
不过,那个,无法直接比较,现代和民国,到底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更好。
要是说学问,谁能说胡适就一定要比现代的那些文史研究者要水平高。
更别提那些”大师“们在道德上的黑料了,要是放到今天这种自媒体舆论氛围中,能被喷死。
民国,整个社会有90%是文盲(有的研究者认为超过了90%,有的认为略低于90%),这样的教育土壤上,能诞生什么“大师”?而且,整个民国时代,基本上,没有几天消停时候,战火纷飞的日子,连基本安全保障都无法实现,更别提教育了。
再说到现代,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出教育事业的。
高考,虽然刚建国的时候,还有,但是,文革期间就停了,后来,已经是文革之后才逐渐恢复,走上正轨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形成现在的教育体系,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公立的教育,也就是国家所推动的教育,其实,主要是为了托举”底线“,就是让社会上普遍的适龄人都能够接受教育,很多时候,是无法照顾到”上线“的。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提问者心中早有问题答案“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
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
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来。
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
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
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为何不允许杰出人才“冒”出来?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
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
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
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在表达方式的变化中,“钱学森之问”已经扩大了“钱学森陈述”的内涵。
不过,即使扩大了内涵,这个提问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追问人才为何不能“冒”出来,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何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一样文不对题,一样怪异荒谬。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亚里士多德已回答此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
而历史的怪异逻辑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
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文化实用主义(所谓学以致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决定了对形上思维的欠缺,而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
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志满意得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天下英雄”实际上已经在体制上和思想上沦落为“食君俸禄,为君分忧”、“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的奴才。
儒家所谓“修齐治平”的“治人术”成为士大夫阶级“学问追求”的核心内容,注定了学者的心灵与“非人事”学问的隔膜,“仰望星空”、追求为学问而学问成为不可能之事。
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
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蜚声世界学坛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为题,被称为“李约瑟命题”。
“李约瑟命题”在本质上与“钱学森之问”乃是异曲同工,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陈独秀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实际上从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回答了“李约瑟命题”。
“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官场诱惑力对非功利的纯学问的兴趣的销蚀,从一开始就阻断了杰出人才走向学术研究与文化思想事业的途径。
试看今日官场如何“潇洒”地挥霍国民财富,再看如今国人如何聚谈官场现状则为之痛心疾首、切齿为恨,独处观望则心向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国人的兴趣何在了。
在一个读书人看到官场荣华则黯然神伤、自惭形秽,或情不自禁发出刘邦式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的社会,读书人对学问的兴趣很容易被更强大的竞争者压倒。
对于杰出人才的成长,思想自由简直就如同空气与水分对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绝非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能提供。
在我族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上,“思想自由”是与“无父无君”一样被视为怪异可怕的名词,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
这是两个政治上非常态的时期,但又是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的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在于,数十年时势演变孕育的杰出人才,如灿烂星河的群星一时间布满天空,但旋即随着思想自由的消失而归于消失。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国家不幸诗家幸”,即大一统政权与思想自由的不两存。
解决这个难题的理想途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权利。
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群体在随后时期不得善终,相反遭受灭顶之灾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思想自由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意义。
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不惟新的学术大师不能出现,就是已经卓然而立的学术大师也不能正常存在。
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
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天才,从青年时代就坚持“读书不为他人忙”的学术宗旨,深知思想自由乃学术研究之根本要素。
1953年底,他的学生汪篯南下广州,劝请他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氏提出的条件是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随后更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重申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主张:“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然而,在领袖思想笼括一切真理的新天地中,陈氏只能徒叹奈何,晚景凄凉。
汤一介教授面对人们给予他的“哲学家”称号敬谢不敏,认为其父汤用彤一代许多人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但他这一代人不能称为“哲学家”,因为这代人的任务是解释领袖的思想,不是独立思想的创造者。
换言之,在领袖思想面前,任何独出心裁的创见都是旁门左道的“异端”,是不能作为人类正当的思维成果而存在的,其道理正如基督教徒所谓《圣经》之外无真理,必须加以消灭一样。
对学术研究有真兴趣的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思想自由条件下研究活动的进行。
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钱钟书与季羡林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然而,钱钟书有下放“干校”劳动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经历,季羡林有过进牛棚、挨批斗的遭遇,此二人都为“不得闲”而荒废了一生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闲暇而在学术研究上绽放出应有的光彩。
当我们明白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后,我们还会纠缠于所谓“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样的问题吗?对“钱学森之问”的解决不要抱太大希望杰出人才每个时代都有,但天才人物成长的环境并非任何时代都具备。
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强调的是杰出人才顺时而生,是时代的产儿。
鲁迅以其深沉的历史感指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
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
换言之,杰出人物的成长,只有得遇社会环境提供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充足的闲暇——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任何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存在都基于相应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传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是统治者渴求的理想状态。
这套治国思路曾丝毫不爽地再现于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最高当局的基本认识,所以在发动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之后,还于1968年坚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