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散文选读
有关鲍尔吉原野写的散文

有关鲍尔吉原野写的散文鲍尔吉原野民族题材的散文是一种文化乡愁的抒发和表达,弥漫着浓郁的游牧民族气息,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
小编精心收集了鲍尔吉原野的散文,供大家欣赏学习!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河流日夜向两岸诀别河流看到岸上的人,如同火车里的旅客所见的窗外的树,嗖就过去了。
让河水记住一个人是徒劳的事情。
河流像它的名字说的那样,一直在流。
没听说哪个人的名字叫流,张流李流,他们做不到。
河流甚至流进黑夜里,即使没有星星导航,它们也在默默地流,用手扶着两岸摸索前进。
无月的黑夜,哗哗的水声传来,听不出它们朝哪个方向流。
仿佛河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流入一个井。
河留不住繁花胜景。
岸上的桃花单薄羞怯,在光秃秃的天地里点染粉红。
枝上的红与白星星点点,分不清是花骨朵还是花,但河已流走,留下的只是一个印象。
印象如梦,说没发生过亦无不可。
倘遇桃花林,那是长长的绯红,如轻纱,又如窝在山脚下浅粉色的雾气,同样逝去。
马群过来喝水,河只看到它们俯首,不知到底喝没喝到水,河已走远。
河水流,它们忘记流了多少年。
年的概念适合于人、如秋适合于草、春适合于花、朔望适合于潮汐。
没有哪一种时间概念适合于河,年和春秋都不适合描述它的生命轨迹。
河的轮回是石缝的水滴到山里的小溪再到大海的距离,跟花开花落无关。
当年石缝里渗出的水跳下山崖只为好奇,它不知道有无数滴水出于好奇跳到崖下,汇成了小溪。
它们以为小溪只是一个游戏,巡山而已,与小鱼蝌蚪捉迷藏。
没承想,小溪下山,汇入了小河,小河与四面八方的河水汇合,流入浩浩荡荡的大河,它们知道这回玩大了,加入悲壮的旅程,走入不归路,归是人类的足迹,恐田园将芜。
河水没有家园,它只灌溉别人的家园。
河的家在哪里?恐怕要说是大海,尽管它尚没见过海。
如果把河比喻为人,它时时刻刻都在诀别,一一别过此生此世再也不会见到的景物。
人看到门前的河水流过,它早已不是昨日的河水。
今日河水与你也只有匆匆一瞥,走了。
没有人为河送行,按说真应该为河送行。
诗意流离的草原牧歌——读鲍尔吉·原野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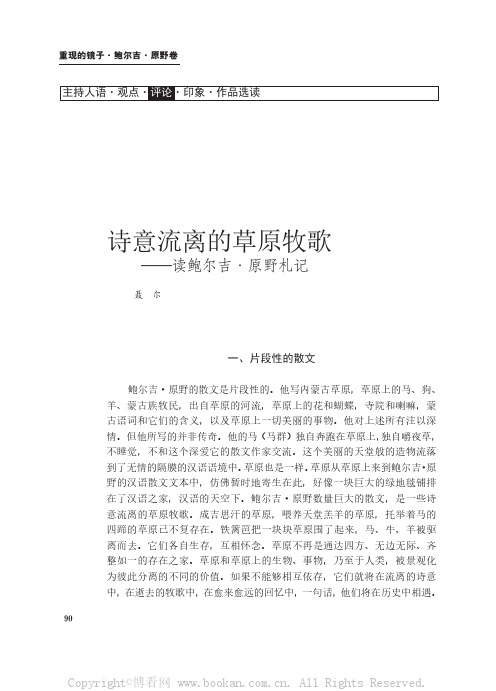
诗意流离的草原牧歌 ——读鲍尔吉·原野札记 聂 尔一、片段性的散文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是片段性的。
他写内蒙古草原,草原上的马、狗、羊、蒙古族牧民,出自草原的河流,草原上的花和蝴蝶,寺院和喇嘛,蒙古语词和它们的含义,以及草原上一切美丽的事物。
他对上述所有注以深情。
但他所写的并非传奇。
他的马(马群)独自奔跑在草原上,独自嚼夜草,不睡觉,不和这个深爱它的散文作家交流。
这个美丽的天堂般的造物流落到了无情的隔膜的汉语语境中。
草原也是一样。
草原从草原上来到鲍尔吉·原野的汉语散文文本中,仿佛暂时地寄生在此,好像一块巨大的绿地毯铺排在了汉语之家,汉语的天空下。
鲍尔吉·原野数量巨大的散文,是一些诗意流离的草原牧歌。
成吉思汗的草原,喂养天堂羔羊的草原,托举着马的四蹄的草原已不复存在。
铁篱笆把一块块草原围了起来,马、牛、羊被驱离而去。
它们各自生存,互相怀念。
草原不再是通达四方、无边无际、齐整如一的存在之家。
草原和草原上的生物、事物,乃至于人类,被景观化为彼此分离的不同的价值。
如果不能够相互依存,它们就将在流离的诗意中,在逝去的牧歌中,在愈来愈远的回忆中,一句话,他们将在历史中相遇。
90现在,它们在鲍尔吉·原野的汉语散文中相遇。
二、私性的母语鲍尔吉·原野是一个蒙古族的用汉语写作的散文作家,或者说他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蒙古族散文作家。
这种词序的简单换位并非文字游戏。
在他的童年时代,他曾“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蒙古人”“这是语言造成的”。
是的,我们都曾经有过童年的宇宙,那是语言造成的,后来不同的语言又将其夺去或改变。
像我们这些只说母语的人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认为语言是没有边界的,世界便也是没有边界的。
但是,说两种语言的鲍尔吉·原野“被汉语领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从此蒙语成了家乡,汉语成为世界。
母语被汉语覆盖,成为在底下的永不消失的深藏之物。
汉语成为上面的,公共的,可学习可辨析的,客观的,无法改变的,因为它是一个实体的世界。
鲍尔吉原野散文集

鲍尔吉原野散文集在下雨之前,树枝把汁水提到了身边,就像人们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它们扬着脖颈等待与雨水遭逢。
我想,它们遭逢时必有神秘的交易,不然叶苞何以密密鼓胀。
下面是有,欢迎参阅。
乌梁素海的蒙古语含义为“红柳湖”,水域面积29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370平方公里,好大。
这座湖通过蒸腾作用每年向大气补水3亿立方米。
如果没有乌梁素海,乌拉山与狼山之间会因为缺少水源涵养而形成新的沙尘暴发源地。
我们开船进湖,船工把湖叫大海小海。
小海长着无边的蒲苇,把水面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水城,其中有行船的巷道。
大海子则一望无际,说这是太湖也有人信。
船在苇子的城墙下边走,苇子里似乎藏着无数座隐秘村庄。
枯干的苇子漂在大海子上,远看似一片黄色的陆地,上面白点密布,近看全是鸟。
白鹭的飞行最为优雅,它不紧不慢,白翎如扇,收紧笔直的、像设备一样的细腿,好像这里不是巴彦淖尔,而是巴黎。
几百只白鹭在蓝天盘旋时,天上如有祥瑞气象。
比白鹭小的白鸟是鸬鹚,在水面上拖泥带水的黑鸟是䴙鸬,当地人管它们叫红眼。
船工说,鸟妈妈正带着小鸟训练呢。
小鸟出徒后,随妈妈飞到鄱阳湖过冬。
天空蓝得正好,配上苍鹭和白鹭的身影也正好。
让远处呆呆的云朵羡慕。
乌梁素海的鸟儿真多,好像比苇子还多。
我在湖上转了两个小时,尽抬头看鸟了,记不起湖的模样。
鸟多的时候,在我们头顶编成一个网,从空中抛起来,然后被一只无形的手收到了东边或西边,所有的小鸟变成了小点,最后没了。
拜拜!咱们鄱阳湖见。
乌梁素海,你为什么不叫鸟海呢?我特想告诉各地的小鸟,夏天你们飞到乌拉特前旗吧不是后旗,海子特大,鱼多得是,还有苇子,快去吧!我们上岸,开车走了四五里地,见到一只细长的白鸬鹚像暖瓶似的蹲在草地上,司机说:“这家伙吃鱼吃恶心了,上这儿吃草籽养养生。
”在我的心目中,阿拉善盟有金黄的、曲线柔美的沙丘,有泉水和绿洲,有高大隐忍的骆驼,还有来自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族人。
我进入阿拉善,第一眼看到的是贺兰山,它有说不出的雄峻,如奔马腾空而来,远方则是它卷起的烟尘。
鲍尔吉·原野精品散文文章

鲍尔吉·原野精品散文文章鲍尔吉· 原野倾情描写人间的美善,使人回味不已。
在他繁星般的散文篇章中,纯真和善良始终像乳汁流淌在字里行间。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鲍尔吉·原野精品散文文章,供大家欣赏。
鲍尔吉·原野精品散文文章:曙色曙色是未放叶的杨树皮的颜色,白里含着青。
冻土化了,水份慢慢爬上树枝,但春天还没有到来,还要等两个节气。
日落时,西天兴高采烈,特朗斯特罗姆说像“狐狸点燃了天边的荒草”。
日之将出,天际却如此空寂,比出牧的羊圈还冷清。
天空微明之际,仿佛跟日出无关,只是夜色淡了。
大地、树林和山峦都没醒来,微弱的曦光在天空蹑手蹑脚地打一点底色,不妨碍星星明亮,也不碍山峦包裹在浓黑的毯子里。
这时候,曙色只是比蚌壳还暗淡的一些白的底色,天还称不起亮。
杨树和白桦树最早接收了这些光,它们的树干比夜里白净,也像是第一批醒来的植物。
在似有若无的微明里,约略看得到河流的水纹。
河流在夜里也在流动,而且不会流错方向。
河水在不知不觉中白了起来,虽然岸边的草丛仍然黑黝黝的。
这时,河水还映照不出云彩,天空看不到有云彩游荡,就像看不清洒在白布上的牛奶的流淌。
星星遗憾地黯淡下来,仿佛退离,又像躺在山峦的背后。
露珠开始眨眼,风的扫帚经过草叶时,露珠眨一眨眼睛,落入黑暗的土壤里。
鸟儿在树林里飞窜,摇动的树枝露出轮廓,但大树还笼罩在未化的夜色中。
鸟儿在天空飞不出影子,它们洒下透明的啁啾。
受到鸟的吵闹,曙色亮了一大块,似乎猛地抬起了身子。
我没听到过关于天亮的计量术语,它不能叫度,不叫勒克司(lx)与流明(lumen)。
大地仍然幽暗之际,天空已出现明确的白,是刚刚洗过脸那种干净的白,是一天还没有初度的白。
它在万物背后竖起了确切的白背景,山峰与天空分割开来。
天的刀子在山峰上割出了锯齿形状。
天光让树丛变成直立的树,圆圆的树冠缀满叶子,如散乱的首饰。
河水开始运送云朵,这像是河上的帆。
最后退场的星星如礼花陨灭于空中,它陨灭的地方出现了整齐的地平线。
鲍尔吉原野散文《让高贵与高贵相遇》再阅读

鲍尔吉原野散文《让高贵与高贵相遇》再阅读让高贵与高贵相遇鲍尔吉原野有泪水在,我感到自己仍然饱满。
对不期而至的泪水,我很难为情。
对自己,我不敢使用伟岸、英武这样高妙的词形容,但还算粗豪的蒙古男人。
这使我对在眼圈里转悠的泪水的造访很有些踟蹰。
我的泪水是一批高贵的客人,它们常在我听音乐或读书的时候悄然来临。
譬如在收音机里听到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黑人音乐的旋律,令人无不思乡。
想到德沃夏克这个捷克农村长大的音乐家,去纽约当音乐学院当院长,但时刻怀念自己的故土。
一有机会,他便去斯皮尔威尔——捷克人的聚居地,和同胞一起唱歌。
“35 5 -│32 1-│23 5 3│2---│”。
我的泪水也顺着这些并不曲折的旋律线爬上来。
譬如读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伊瓦沃罗的诗集《清凉的水罐》,诗人在做针线活时,窗外缓缓走过满载闪光的麦秸的大车,她说:“我渴望穿过玻璃去抚摸那金色的痕迹”。
她看到屋里的木制家具,想:“砍伐多少树才能有这一切呢?露水、鸟和风儿的忧伤。
……在光闪闪的砍刀下倒下的森林的凄哀心情”。
读诗的时候,心情原本平静,但泪水会在此优美的叙述中肃穆地挤上眼帘。
读安谧的诗集新作《手拉手》,说“透过玫瑰色暮霭的轻纱/我看到河边有个光脚的女孩/ 捧一尾小鱼/小心翼翼向村口走去”。
这时,你想冲出门去,到村口把小女孩手里的鱼接过来。
那么,在地上洒满白露的秋夜,在把身子喝软、内心却异常清醒的酒桌上,在照片上看到趴在土坯桌上写字的农村孩子时,蓦然想起小心翼翼的小女孩,捧着小鱼向村口走去时,难免心酸。
那么,我想: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为何会常常流泪?一个在北国的风雪中长大的孩子,一个当抄家的人踹门而入时贴紧墙壁站着的少年,一个肩扛檩子登木头垛被压得口喷鲜血的知青;我,不应该流泪,在苦难中也没有流过的泪水。
生活越来越好了,我怎么会变得“儿女沾巾”呢?至今,我的性格仍强悍。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
泪水,是另外一种东西。
这些高贵的客人手执素洁的鲜花,早早就等候在这里,等着与音乐、诗和世道人心中美好之物见面。
鲍尔吉原野散文:珊 瑚

鲍尔吉原野散文:珊瑚鲍尔吉原野散文:珊瑚珊瑚的红不通向桃花的渡口,不偏心于牡丹。
对我来说,走进珊瑚的红里,会走进蒙古高原,就像红茶的红通往科尔沁。
珊瑚那种说不出来的红让人喜欢,人喜欢它说不出来的色阶。
说它浅红吧?它比谁浅?不是比胭脂浅,跟胭脂没关系。
当然也不能说比红浅,它就是红。
它是珊瑚的浅红。
鲜红的珊瑚属于深红。
深不深不是跟红比,比不出来的,这是深水的深,从这一边看不到那一边的深。
珊瑚之深红如一滴血的深与红,纯净的血深不见底,血的红在红里面最为中正。
珊瑚坐在白银的摇篮里变成一枚戒指。
人的手指开发了一朵有银子的花。
植物的花朵美固美,可惜花朵上没镶白银的边款。
我觉得生活里面的白银太少了,我觉得白银不是金属,它是硬朗的花,应该开遍我们的手足衣衫。
银扣子多美,它缀在衣服上。
银泡钉多美,钉在马鞍上。
银戒指戴在人手上,手被赋予沉静的美。
半夜醒来,我曾经想银子现在干啥呢?戒指、手镯、包银边的木碗,它们干啥呢?不必点灯,我已猜出银子在黑夜里微笑,在手指、手腕或者喝茶的木碗上露出乡村儿童的微笑,银子根本不睡觉,它们精力充沛,日夜睁眼呆着,白而亮。
银子跟谁最好?不用问,银子跟珊瑚最好。
不知是谁最早把银子和珊瑚交集一体,这个人了不起,懂得造物的秘密。
我老家的汉人管珊瑚叫“山虎子,”挺亲昵。
我觉得珊瑚可能真是山虎子。
矿物质里面也分飞禽走兽。
绿松石像小翠鸟,琥珀像猞猁,孔雀石就是孔雀,而珊瑚竟然是虎,是这样吗?有可能。
它是一只红虎,像一团火苗在石头里窜跑,它的前额有王字,尾巴也很厉害,啪!啪!树干被扫断。
只是,所有矿物的走兽飞禽在岩石被开采粉碎提炼之时中了定身法,动不了了。
这没什么奇怪,人经过此生进入彼岸后也动不了了。
变成了什么,我说不清楚。
珊瑚见到了银子情投意合,如果它们不合,人把戒指戴在手上怎么能吉祥呢?我看到白银镶嵌的珊瑚戒指,觉得它们俩正用人耳听不到的波长唱蒙古歌呢。
珊瑚(女)唱道:“赶上流水似的马群呀,脸上照着初升的阳光,日轮花随风飘来芳香。
鲍尔吉.原野关于善良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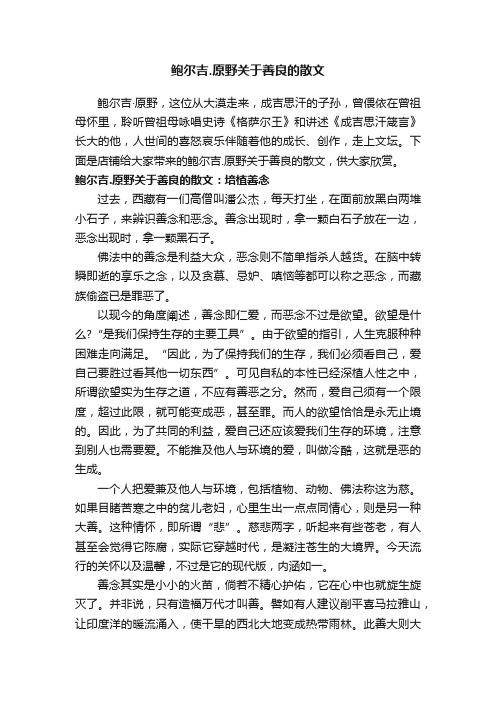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关于善良的散文鲍尔吉·原野,这位从大漠走来,成吉思汗的子孙,曾偎依在曾祖母怀里,聆听曾祖母咏唱史诗《格萨尔王》和讲述《成吉思汗箴言》长大的他,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伴随着他的成长、创作,走上文坛。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鲍尔吉.原野关于善良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鲍尔吉.原野关于善良的散文:培植善念过去,西藏有一们高僧叫潘公杰,每天打坐,在面前放黑白两堆小石子,来辨识善念和恶念。
善念出现时,拿一颗白石子放在一边,恶念出现时,拿一颗黑石子。
佛法中的善念是利益大众,恶念则不简单指杀人越货。
在脑中转瞬即逝的享乐之念,以及贪慕、忌妒、嗔恼等都可以称之恶念,而藏族偷盗已是罪恶了。
以现今的角度阐述,善念即仁爱,而恶念不过是欲望。
欲望是什么?“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
由于欲望的指引,人生克服种种困难走向满足。
“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看自己,爱自己要胜过看其他一切东西”。
可见自私的本性已经深植人性之中,所谓欲望实为生存之道,不应有善恶之分。
然而,爱自己须有一个限度,超过此限,就可能变成恶,甚至罪。
而人的欲望恰恰是永无止境的。
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爱自己还应该爱我们生存的环境,注意到别人也需要爱。
不能推及他人与环境的爱,叫做冷酷,这就是恶的生成。
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这为慈。
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
这种情怀,即所谓“悲”。
慈悲两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
今天流行的关怀以及温馨,不过是它的现代版,内涵如一。
善念其实是小小的火苗,倘若不精心护佑,它在心中也就旋生旋灭了。
并非说,只有造福万代才叫善。
譬如有人建议削平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的暖流涌入,使干旱的西北大地变成热带雨林。
此善大则大矣,却要我们等得太久。
古人有诗:“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虽然琐细,读后感觉心中暖暖的,大过印度洋的暖流。
鲍尔吉·原野《没有人在春雨里哭泣》高考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文,完成第9——12题。
(15分)没有人在春雨里哭泣鲍尔吉·原野①雨点瞄着每株青草落下来,因为风吹的原因,它落在别的草上。
别的雨点又落在别的草上。
春雨落在什么东西都没生长的、傻傻的土地上,土地开始复苏,想起了去年的事情。
雨水排着燕子的队形,以燕子的轻盈钻入大地。
这时候,还听不到沙沙的声响,树叶太小,演奏不出沙沙的音乐。
春雨是今年第一次下雨,边下边回忆。
有些地方下过了,有些地方还干着。
春雨扯动风的透明的帆,把雨水洒到它应该去的一切地方。
②走进春天里的人是一些旧人。
他们带着冬天的表情,穿着老式的衣服在街上走。
春天本不想把珍贵的,最新的雨洒在这些旧人身上,他们不开花、不长青草也不会在云顶歌唱,但雨水躲不开他们——雨水洒在他们的肩头、鞋和伞上。
人们抱怨雨,其实,这实在是便宜了他们这些不开花不长青草和不结苹果的人。
③春雨殷勤,清洗桃花和杏花,花朵们觉得春雨太多情了。
花刚从娘肚子钻出来,比任何东西都新鲜,无须清洗。
不!这是春雨说的话,它认为在雨水的清洗下,桃花才有这样的娇美。
世上的事就是这样,谁想干什么事你只能让它干,拦是拦不住的。
④春天的雨水下一阵儿,会愣上一会儿神。
它们虽然在下雨,但并不知这里是哪里。
树木们有的浅绿、有的深绿。
树叶有圆芽、也有尖芽。
即使地上的青草绿的也不一样。
有的绿得已经像韭菜、有的刚刚返青。
灌木绿得像一条条毯子,有些高高的树才冒嫩芽。
性急的桃花繁密而落,杏花疏落却持久,仿佛要一直开下去。
春雨对此景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
它去过的地方太多,记不住哪个地方叫什么省什么县什么乡,根本记不住。
⑤春雨继续下起来,无须雷声滚滚,也照样下,春雨不搞这些排场。
它下雨便下雨,不来浓云密布那一套,那都是夏天搞的事情。
春雨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打雷谁不会?打雷干嘛?春雨静静地、细密地、清凉地、疏落地、晶亮地、飘洒地下着,下着。
不大也不小,它们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看屋里需不需要雨水,看到人或坐或卧,过着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日子。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善良是一棵矮树(by 鲍尔吉.原野)如果善良与邪恶分别是两棵树的话,好看的是邪恶之树。
邪恶之树茂盛,绿叶如盖,果实鲜艳。
善良之树生长缓慢,不引人注目,有时没有果实。
这就是人们拒绝善良的道理所在。
如果仅仅从生长与结果来判断树的价值,那也只是它的价值之一,而不是价值的全部。
当人们把眼光投入果实时,善良之树在做什么呢?它在地下默默地固沙,在没有人烟之处亮出一片风景,在清新每人吸入的氧气。
然而善良也有果实,那就是人性的纯粹和人性的辉煌。
邪恶之树尽管疯长,但颓衰也过于迅速了。
罂粟花不也是极美丽吗?然而消失得也迅速。
贝多芬说,“没有一颗善良的灵魂,就没有美德可言。
”这是说善良与美德是密不可分的,但对于不需要美德的人来说,似乎可以不需要善良了。
还有一句格言很精彩,但不是名人说的,而是我的一位朋友田睿口述,“如果善良也是一种武器的话,我在生活中惟一的武器是善良。
”这话令人玩味再三。
生活并不仅仅是“吃亏是福”的问题,敢于善良也不是敢于吃亏。
善良常常是无损失可言。
作为一种天性,善良的人往往能化险为夷。
因而善良之树也是常青之树。
跟穷人一起上路鲍尔吉·原野那一次,我从油麻地去香港岛看维多利亚湾的夜景,途中步行经过一个隧道。
隧道的名字已忘记了,印象是宽亮如昼。
走着,目光被左壁招贴画吸引。
———一个风尘仆仆的汉子迎面而来,他刚毅精悍,左腿是机械假肢,肩膀有些前斜,吃力地、渴盼地向前疾行。
画面下方的文字说此人为病中的穷孩子募捐,正在旅途中。
画中心有大字———跟穷人一起上路。
这位汉子一定走过了千山万水,不然不会有如此深邃的目光。
他刚毅的表情背后掩饰着隐痛,用这条假肢走,每一步恐怕都要痛。
那么———如图所示———他正徒步穿越新疆的独山子、玛纳斯、一碗泉,甘肃的马莲井、黄羊镇、娘娘坎,然后经陕鄂湘粤到香港。
他是香港人。
一个忍痛的行者用假肢穿越过大西北的旷野,信念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让没钱的孩子治病。
照片用镀铝金属镶框,内置灯光照明,一幅连一幅延伸到前面。
画面上的汉子像排队一样,一个接一个向你迎面走来,昂着头,有些吃力地移脚。
然后是一行比一行小的字———跟穷人一起上路。
香港街头,很少见到通常印象中的穷人,大家似乎衣食丰足。
在这幅视觉冲击力强烈的招贴画中,“穷人”两字竟很尊贵,关注他们如同每个人的责任。
就是说,此刻我感动了,血液从各处奔涌而出,冲撞全身。
心里默念:跟穷人一起上路!跟穷人一起上路……这时,耳边歌声趋近,不远的地方有一支乐队。
四个淡蓝色牛仔装的年轻人弹唱,三男一女。
隧道高瓦数的橙光把他们的脸庞勾勒得十分柔和。
他们沉静吟唱美国乡村歌曲,弹电贝司的女孩子很卖力,头发在肩膀上跳。
他们脚下一只干草色的牛仔礼帽里有散钞,纸卡写着“为脊髓灰质炎病童筹款”。
乡村歌曲在海底隧道回荡,宁静而朴素。
曲调如R ICHQEDMAFX的风格,把渴盼压在了心里,舒展、大度而倔犟。
譬如f ool ’S gam e 。
又如my confession 。
吉他、蓝色牛仔装和他们头发上金黄的轮廓光,与音乐一起构成了奇妙的效果,身后招贴画上的独行者目光炯炯,简直就要破壁而出了。
我想站下多听一会儿,但听众只有我一个人。
别人扔下钱匆匆而行,我把仅有的一些港元扔进干草色的礼帽里,感到轻松。
这几天我被这钱弄得枯燥,买东西剩下的这点钱,大件买不成,小件又不想买,还得动脑筋找打折的商店,比如“S OGO ”,又要算计地铁费用等等,哪如此刻省心。
乡村歌曲对爱情、忧伤和前途均有独特的诠释方式,就像枝头上的花与瓶里的花不一样,像赤脚在五月的玉米地里走过,脚丫缝感到土壤的湿润,像衣衫带着松香味,指甲缝里有洗不尽的新鲜泥土。
但我把所有的钱放进礼帽之后,伫立倾听就有一些惭愧。
我想有钱真是不错,隔一会儿,往那里扔点钱,再接着听。
但是把钱分几次给一个募集善款的乐队,似乎也不像话。
他们并没有用目光驱人,眼神里多少还有一些谢意,感谢我目不转睛地倾听。
跟港人比,我有许多时间,但仍然不能长久流连。
乡村歌曲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我用目光接过一幅又一幅的“跟穷人一起上路”,向出口走去。
这时口袋空空,我把它翻出来,像两只兔子耳朵在腿侧垂着。
我童年曾玩过这样的游戏,那时没有钱,口袋里是一些纸团。
现在演习一遍,竟很新鲜,好像洗手套一样把自己翻过来洗干净了。
培植善念鲍尔吉原野过去,西藏有一位高僧叫潘公杰,每天打坐,在面前放黑白两堆小石子,来辨识善念恶念。
善念出现时,拿一颗白石子放在一边;恶念出现时,取黑石子。
佛法中的善念是利益大众,恶念则不简单指杀人越货。
在脑中转瞬即逝的享乐之念以及贪婪、嫉妒、嗔恼等都可称之恶念。
而欺诈偷盗已是罪不容赦了。
以现今的角度阐述,善念即仁爱,而恶念不过是欲望。
欲望是什么?“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
”(卢梭)由于欲望的指引,人生克服种种困难走向满足。
“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爱自己,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东西。
”(卢梭)可见自私的本性已经深植人性之中,所谓欲望实为生存之道,不应有善恶之分。
然而,爱自己需有一个限度,超过此限,就可以变成恶,甚至罪。
而人的欲望恰恰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爱自己还应该爱我们生存的环境,常常注意到别人也需要爱。
不能推及他人与环境的爱,叫做冷酷,这就是恶的生成。
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
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
慈悲两字,听起来有些苍老。
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
今天流行的“关怀”以及“温馨”,不过是它的现代版,内涵如一。
善念其实是小小的火苗,倘若不精心护佑,它在心中也就旋生旋灭了。
不是说,只有造福万代才叫善。
譬如有人建议削平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的暖流涌入,使干旱的西北大地变成热带雨林。
此善大则大矣,却要等待很久。
古人有诗:“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虽然琐细,读后感觉心中暖暖的,大过印度洋的暖流。
潘公杰大师在黑白石子中辨识善恶二念,到晚上检点。
开始时黑石子多。
他掴自己的耳光,甚至痛哭、自责,你在苦海里轮回,还不知悔过么?三十多年之后,他面前全变成白石子了,大师后来修成菩提道。
我们达不到高僧那种至纯之境。
爱自己原本也没有错,我们是凡人。
然而无论“利己心”走得多远,有善念相伴,你都会是一人。
鲍尔吉·原野:杏花露出了后背鲍尔吉·原野:杏花露出了后背“笃、笃、笃……”沉睡的众树木间响起了梆子。
梆子的音色有点空,缺光泽。
是什么木的?胡琴桐木,月琴杉木,梆子约为枣木吧。
梆子一响,就该开始了。
“开始”了什么,我也说不清。
本想说一切都开始了,有些虚妄。
姑且说春天开始了。
梆子是啄木鸟搞的,在西甲楼边的枯杨树上,它和枯树干平行。
“笃……”声传得很远,急骤,推想它脖颈肌肉多么发达。
人说,啄木鸟啄木,力量有15公斤;蜡嘴雀敲开榛子,力量20公斤。
好在啄木鸟没对人脑袋发力。
有了梆子,就有唱。
鸟儿放喉,不靠谱的民族唱法是麻雀,何止唱,如互相胳肢,它们乐得打滚儿;绣眼每三分钟唱一乐句,长笛音色,像教麻雀什么叫美声;喜鹊边飞边唱,拍着大翅掠过树梢,像散布消息。
什么消息?———桦树林里出现一条青草,周围的还黄着。
这条青草一米宽,蜿蜒(蜿蜒?对,蜿蜒)绿过去,像河水,流向柏油路边上。
这是怎么回事儿?地下有什么?它们和旁边的青草不是一家吗?———湖冰化水变绿,青苔那种脏绿。
风贴水面,波纹细密,如女人眼角初起的微纹。
在冰下过冬的红鲤鱼挤到岸边接喋,密集到纠缠的程度。
———柳枝一天比一天软,无事摇摆。
在柳枝里面,冬天的干褐与春天的姜黄对决,黄有南风撑腰,褐色渐然逃离。
柳枝条把袖子甩来甩去,直至甩出叶苞。
在英不落的树林里走,树叶厚到踩上去趔趄,发出翻书页的声音。
蹲下,手拨枯叶能见到青草。
像婴儿一样的青草躺在湿暗的枯叶里做梦,还没开始长呢?英不落没有鹰,高大的白杨树纠结鸟巢,即老鸹窝。
远看,黑黑的鸟巢密布同一棵树上,多的几十个,这些老鸹估计是兄弟姐妹。
一周后,我看到鸟巢开始泛绿,而后一天比一天绿,今天绿得有光亮。
这岂不是……笑话吗?杨树还没放叶,老鸹窝先绿了。
请教有识之士。
答我:那是冬青。
冬青,长在杨树权上,圆而蓬张?再问有识之士。
说,鸟拉屎把冬青籽放置杨树之上。
噢。
在大自然面前,人无知的事情很多,而人也没能力把吃过的带籽的东西转移到树梢上发芽与接受光照。
人还是谦虚点吧,“易”之谦卦,六爻皆吉。
其它的卦,每每吉凶相参,只有谦卦形势大好,鬼神不侵。
啄氏的枯木梆子从早上七时敲响,我称之开始。
对春天,谁说“开始”谁不懂事儿。
春天像太极拳的拳法一样,没有停顿、章节,它是一个圆,流转无尽,首尾相连。
林里,枯枝比冬天更多。
拾柴人盯着地面东奔西走。
杏树枝头的叶苞挣裂了,露出一隙棉花般的白,这是杏花白嫩的后背,现在只露出一点点。
鲍尔吉·原野:每一寸光阴都有用从质地上说,花瓣是什么?它比绸子还柔软,像水一样娇嫩。
雨后的山坡上,如果看到一朵花,像见到一个刚睡醒的婴儿,像门口站着一个被雨淋湿的小姑娘。
花瓣的质地,用语言形容不出来。
而它的鲜艳,我们只好说它像花朵一样鲜艳,无论是小黄花、小白花都纯洁鲜艳。
花能从一株卑微的草里生长出来,人却不能。
从性格说,马比人勇敢,而性情比人温和。
马赴战场厮杀,爆炸轰鸣不会让它停下来,见了血也不躲闪,冰雪、高山和河流都不会阻挡马的脚步。
它的眼睛晶莹,看着远方。
把勇敢与温良结为一体,在人当中,可谓君子:在动物中,是马。
从胸怀看,鸟比人更有理想。
当迁徙的候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雪崩不会让它惊慌。
鸟在夜晚飞越大海,如果没有岛屿让它歇脚,它不让自己疲倦,一直飞,它不过是小小的生灵,却有无上的勇气。
人的勇敢、包容、纯洁和善良,本来是与生俱有的。
在漫长的生活中,有一些丢失了,有一些被关在心底。
把它们找回来,让它们长大,人生其实没什么艰难,每一寸光阴都有用。
鲍尔吉·原野:不要跟春天说话春天忙。
如果不算秋天,春天比另两个季节忙多了。
以旅行譬喻,秋天是归来收拾东西的忙,春天是出发前的忙,不一样。
所以,不要跟春天说话。
蚂蚁醒过来,看秋叶被打扫干净,枯草的地盘被新生的幼芽占领,才知道自己这一觉睡得太长了。
蚂蚁奔跑,检阅家园。
去年秋天所做的记号全没了,蚯蚓松过的地面,使蚂蚁认为发生了地震。
打理这么一片田园,还要花费一年的光景,所以,不要跟蚂蚁说话。
燕子斜飞。
它不想直飞,免得有人说它像麻雀。
燕子口衔春泥,在裂口的檩木的檐下筑巢,划破冬日的蛛网。
燕子忙,哪儿有农人插秧,哪儿就有燕子的身影。
它喜欢看秧苗排队,像田字格本。
衔泥的燕子,从不弄脏洁白的胸衣。
在新巢筑好之前,不要跟燕子说话。
如果没有风,春天算不上什么春天。
风把柳条摇醒,一直摇出鹅黄。
风把冰的装甲吹酥,看一看冰下面的鱼是否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