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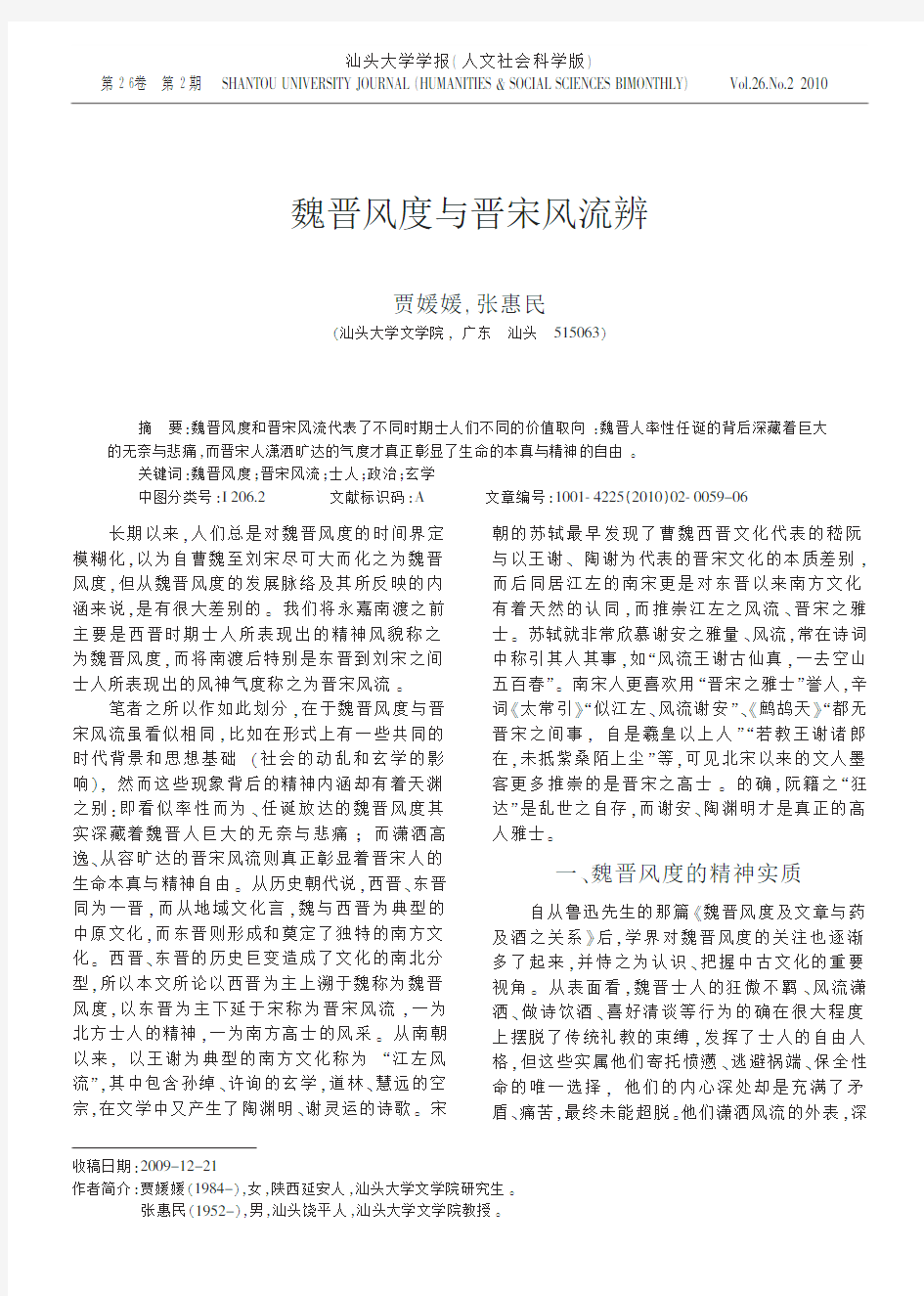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魏晋风度的时间界定模糊化,以为自曹魏至刘宋尽可大而化之为魏晋风度,但从魏晋风度的发展脉络及其所反映的内涵来说,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将永嘉南渡之前主要是西晋时期士人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称之为魏晋风度,而将南渡后特别是东晋到刘宋之间士人所表现出的风神气度称之为晋宋风流。
笔者之所以作如此划分,在于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虽看似相同,比如在形式上有一些共同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社会的动乱和玄学的影响),然而这些现象背后的精神内涵却有着天渊之别:即看似率性而为、任诞放达的魏晋风度其实深藏着魏晋人巨大的无奈与悲痛;而潇洒高逸、从容旷达的晋宋风流则真正彰显着晋宋人的生命本真与精神自由。从历史朝代说,西晋、东晋同为一晋,而从地域文化言,魏与西晋为典型的中原文化,而东晋则形成和奠定了独特的南方文化。西晋、东晋的历史巨变造成了文化的南北分型,所以本文所论以西晋为主上溯于魏称为魏晋风度,以东晋为主下延于宋称为晋宋风流,一为北方士人的精神,一为南方高士的风采。从南朝以来,以王谢为典型的南方文化称为“江左风流”,其中包含孙绰、许询的玄学,道林、慧远的空宗,在文学中又产生了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宋
朝的苏轼最早发现了曹魏西晋文化代表的嵇阮与以王谢、陶谢为代表的晋宋文化的本质差别,而后同居江左的南宋更是对东晋以来南方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而推崇江左之风流、晋宋之雅士。苏轼就非常欣慕谢安之雅量、风流,常在诗词中称引其人其事,如“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南宋人更喜欢用“晋宋之雅士”誉人,辛词《太常引》“似江左、风流谢安”、《鹧鸪天》“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紫桑陌上尘”等,可见北宋以来的文人墨客更多推崇的是晋宋之高士。的确,阮籍之“狂达”是乱世之自存,而谢安、陶渊明才是真正的高人雅士。
一、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
自从鲁迅先生的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学界对魏晋风度的关注也逐渐多了起来,并恃之为认识、把握中古文化的重要视角。从表面看,魏晋士人的狂傲不羁、风流潇洒、做诗饮酒、喜好清谈等行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发挥了士人的自由人格,但这些实属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唯一选择,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充满了矛盾、痛苦,最终未能超脱。他们潇洒风流的外表,深
收稿日期:2009-12-21
作者简介:贾媛媛(1984-),女,陕西延安人,汕头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张惠民(1952-),男,汕头饶平人,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
贾媛媛,张惠民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魏晋风度和晋宋风流代表了不同时期士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魏晋人率性任诞的背后深藏着巨大
的无奈与悲痛,而晋宋人潇洒旷达的气度才真正彰显了生命的本真与精神的自由。
关键词:魏晋风度;晋宋风流;士人;政治;玄学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0)02-0059-06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26卷第2期
SHANTOU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BIMONTHLY )
Vol.26.No.22010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2010年)
藏着太多的悲苦。
(一)政治与士人的关系
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到公元420年永嘉南渡,200年间,中国始终处于分裂动荡之中,除了战场上的血雨腥风,更有政权内部各派系的明争暗斗。曹丕代汉、司马氏代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等,特别是西晋一朝,整个政局始终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朝廷的建立借助于不义的、残忍的手段。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了曹魏政权。按封建礼教规定,这种做法显然属于不忠,违背了礼教,但司马氏上台后,却仍然高树礼教大旗,宣扬以名教治国,对于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扣上反叛礼教的罪名而杀害。因此,在血腥杀戮和政治高压下,许多文人朝不保夕,动辄罹祸。政府、社会的黑暗使得文人对统治阶级大失所望。为远祸避灾,就得远离官场,远离权贵,然而,为保护自己,为掌握自己的生死命运,更可靠的办法,还是得依附某位权贵或者干脆跻身于权贵之列。魏晋以来,多少文人士大夫,在这样的“阴影”下挣扎,在这样的“诱惑”中陷溺……政治的迫害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极大的矛盾和痛苦。
“(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不得言而止。钟会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1360-1361可见阮籍本来是想建功立业的,他从小就深受礼教的影响,在《咏怀诗》中说自己十四五岁就十分热爱儒家诗书,立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从他正始时期所写的《乐论》看,他对儒家礼乐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认为礼乐是治理人民的两件相辅相成的法宝:“礼制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2]正是同一个阮籍,在高平陵政变后变得如此旷达不羁,成了庄子的信徒。他居丧其间喝酒食肉,箕踞啸歌,散布反礼教言论,把礼法之士说成是“裤裆中的虱子”。他因为看不惯司马氏的虚伪,才有大醉拒婚的举动,可最终还是因“胆小”写了“劝进书”并登上西晋朝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给阮籍的内心带来莫大的痛苦和无法排遣的愁绪,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2]1361。这种“痛哭而返”正是其内心矛盾、煎熬的一种表现。
嵇康应该是名士中不拘礼教、不慕仕途的代表了。他的思想似乎比阮籍更激进,行为也更旷放不羁。他猛烈抨击名教,誓不做官,隐居达十多年,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面看是脱俗了,但其自身又充满了极其矛盾的言行。他不做官并非不想做官,而是因为他本身就“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1]1369,他拒绝出仕司马氏,采取了一种“逆世”的态度,同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荐举他做司马氏的官时,他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1]1372在这篇文章里,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被司马昭以毁坏礼教的罪名所杀。嵇康是真的毁坏礼教吗?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3]513这段论述指出了嵇、阮诸人内心与行为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其实就是现实政治混乱的结果。嵇康最终丧命于司马氏集团之下,但就是这位面对屠刀从容就义的勇士,在留给儿子的《家训》一文中,却表现得异常平和,一改反儒学的态度,对儿子进行了一番深刻的礼法教育。嵇康为儿子所指的是一条循规守礼之路,这与他平日的行径也是极不相称的,由此可见他的矛盾和痛苦之深。
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统治者对反对派和疑为反对派的士人大加杀戮,魏晋士人不得善终者大有人在。在整个魏晋时期,政治对士人的迫害太大太深了,而士人们又不能完全的超脱。相反,他们只能是一个极度痛苦、郁闷、受压抑的群体,如此痛苦的一群士人,他们的洒脱、他们的风度又有几分真实几分无奈?可见,魏晋人越俗超凡不乐仕宦,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行为,依然处于仕途的阴影之中。
(二)“魏晋风度”背后的真实
魏晋人虽外在表现为旷达超远、风流潇洒、崇尚自然,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魏晋士人是从内心眷恋红尘,不能摆脱俗世的,他们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只是超级痛苦的一种变相反映,潇洒风流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无奈和悲苦。
魏晋士人确有许多狂荡放纵、任性妄为、率真直性的言行,但绝不是真的无所顾忌,而是极有限度的,“狂”的背后更有一个“慎”字存在,我们称之为狂者亦慎。阮籍曾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4]他不顾礼法,和嫂子聊天,又常常喝醉了酒就顺势倒在卖酒少妇脚边酣睡,甚至在给
60
贾媛媛,张惠民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第2期
母亲守丧期间公然当着司马昭的面喝酒吃肉,可谓狂了。但这样一个人却从不评论当时人物国事的好坏。《世说新语·德行》刘注引李秉《家诫》记司马昭言:“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阮籍如此放诞,作为一种处事为人的策略,无疑是为了避祸免灾。魏晋之际是多事之秋,司马氏与曹氏的激烈争战,将多少士大夫送上枉死台!对恐怖政治的憎恶与恐惧,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嵇康之“狂”更甚于阮籍,而嵇康的“狂”中仍然有“慎”。嵇康非毁礼教的狂言肆行比比皆是,但他却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判礼悖教。嵇康在狱中作《家戒》,教导儿子恭守礼法,慎言慎行:“夫言语,君子之机,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嵇康不厌其细地告诫儿子何言可讲何言不可讲,何人可交何人不可交,何事可与何事当避……为人处事更要以儒家教义为圭臬:“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弟,此忠臣烈士之节。”可见嵇康虽自己任诞狂傲,但教子却如此恭谨。狂狷者之狂,是个体对乱世杀夺的防御性反抗。而狂狷者之慎,则是乱世的一种无奈的防身术,是抵御暗箭明枪的盾牌。
酒对魏晋名士实在是太重要了。何为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痛饮酒方算得上名士,名士不可一日无酒。酒,甚至成了“名士徽章”。还有一位王姓名士对酒更为看重:“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篇中还载有许多饮酒者的轶事:“阮宣子(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山季伦(简)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再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其举止狂放不羁,风流自赏。
魏晋士人如此沉醉于饮酒,与这一时代文人的命运与遭际是分不开的。他们表面上狂饮酣醉,行为十分放达而超脱,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无法排遣的悲哀与忧怨。现实世界充满残杀和伪善,名士们借助酒精,尽情地宣泄了心中的郁闷、愤懑;同时又以酒人的“糊涂”,成功地避免了以狂伤人、以狂刺主,最终避开了权势的淫威,达到了“以狂自晦”的目的。酒,无疑是魏晋名士避祸的防身术,同时也是他们享受生命、于乱世苦痛中讨取些微欢乐的重要手段。
(三)玄学与魏晋风度
“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社会政治之动乱造成思想之巨变。昔日士大夫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权威思想全面崩溃了。社会环境的严酷,加之魏晋之交,门阀制度渐成,九品官人制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而流为世家大族手中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这对广大热心于建功立业的读书人而言不啻当头一瓢冷水。于是,士人们的内心失去了平衡,普遍出现了心理苦闷、焦虑的文化症候,这就必然要为精神寻找一个避难的场所,而老庄学说所体现的精神价值指向,正好符合当时士人的心理需要,人们便纷纷从老庄的“玄虚”思想中寻找精神慰藉,以获取心理层面上的解脱超越。魏晋士人从清谈、谈玄、注玄中,不知不觉地对老、庄思想做出了新的解释。魏晋玄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土壤和精神气候下应运而生的,它是士人寻找来的一种思想归宿,一种用以填补儒学失落之后的新的理性的依归。
正始年间,谈玄之风盛行,反映了其时士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巨大的理论热情。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为代表的正始玄学家主要是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其谈玄的谈资,所谈的主要是本末、有无、言意诸命题。他们对玄学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上,谈玄并未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正始名士王弼注释《老子》,提出了“贵无”论学说,认为圣人体“无”。他只是为当时的士人言行寻找一种理论依据,而真正的玄学要义并未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之后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但并未很好的解决。玄学家郭象在嵇阮之后,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政治上主张名教即自然、儒家即是道家的合一思想,调和玄学与现实的矛盾,但他没能成功,他的玄学理论本身就充满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说,他的人格构成亦充满了矛盾。据《晋书》本传:郭象“好老庄,能清言”,“州郡辟招,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对现实抱一种超越的态度,但他同时又热衷于追逐权势,“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
61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2010年)
外”[1]1397,对现实抱一种迎合的态度。
由此,早期玄学名士不但违背道家祖师的教诲,甚至也没有按他们自己的理论行事。这些以新道家自居的玄学名士们,尽管拼命鼓吹老庄哲学,都异口同声地号召人们学习“道”,以“自然无为”作为自己生活的座右铭,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实践了“自然无为”的理论:何晏积极追随曹爽集团而被处死,违背了道家与世无争的学说;王弼因争强好胜,喜欢讥笑别人的缺点,而触犯众怒,不符合道家谦逊虚心的主旨;夏侯玄因才能声望太高而引来杀身之祸,没有理解庄子“废物支离疏,无才而获福”的寓意;还有郭象,积极争权夺利,毫无老子“后其身”和“外其身”的退让品德等等。他们都没有从世间的功名利禄中超脱出来,没有那份优游容与的超然。
二、南方文化的晋宋风流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魏晋风度、晋宋风流无论从哲学思潮还是从社会风气上讲,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社会背景所造就的士人心态的不同,而使他们在人格追求上亦有许多不同之处。东晋刘宋人已经不再像魏晋名士那样在佯狂醉酒中充满了沉痛、在竞豪斗富中显现出鄙俗,晋宋人在这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在不涉世务的宁静悠闲中吟诗清谈、游山玩水、琴棋书画。他们即使感情浓烈但表现出来的却温文尔雅,含蓄而不粗俗,追求一种优雅从容、风流潇洒的气质和风度。魏晋名士刻意而求名,晋宋高人自然而清高。
(一)政治与士人的关系
东晋初期,南渡执掌政权的北方士族,面临着南方的门阀士族集团的强烈反抗。田余庆先生认为偏安于江左的东晋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所谓门阀政治,他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解释为:“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5]这种政治的基本特征即在于士族和皇权共治,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从东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权力经历庾亮、谢安、桓玄等,士族大家不断地为增强家族势力而努力,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特别是东晋一朝,实际主政的基本上是门阀士族,他们执政治军事之牛耳,权倾人主,晋帝反成附庸,十一帝中有三名(海西公、安帝、恭帝)被大臣所弑,其余亦碌碌无为。这一点从东晋立国起便可看出,元帝司马睿号称“中兴之主”,然史书的记载却显示出他对门阀士族的深深依赖。《晋书·元帝纪》载:“永嘉初,(元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1]144然而吴人却并不服从,《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云:“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1]1745
司马睿是如此依赖王导,难怪他要尊称王导为“仲父”并引其“相登御床”。(《世说新语·宠礼》)更有甚者,当面对强臣失御时,皇帝往往显示出百般的无奈,如元帝便曾对起兵造反的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琊,以避贤路。”[1]155正是因为这些事实,沈约在《宋书·武帝纪》中便说:“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遂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6]60由上可见,东晋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是门阀士族。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
东晋的这种门阀政治对士人的压迫较之以前缓和了许多,这就使得士族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多的闲情逸致来享受偏安一隅带给人的享受,士族们才可以在南方秀美的山光水色中优游山林,坐赏美景,才可以使他们少一份对家国责任的顾及而多一份个人享受的情趣。
(二)晋宋风流的精神内涵
偏安江左的名士们完全不同于邺下文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不同于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想人格追求,更不同于金谷文人为了家族、为了个人利益而汲汲于功名利禄,他们有着自身的生活情趣,他们在江南的名山丽水中,极力追求一份宁静的心态,追求一种淡泊的逍遥。在重物质享受的同时,更重精神的满足。
62
贾媛媛,张惠民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第2期
时至晋宋,高士们更加追求心灵上的自由与乐趣,于是率性而行,回归自然。他们大多都拥有一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通脱释然的心态。
谢安在东山时,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忽然风起浪涌,众人皆喧动不坐,顿失平时优雅雍容的风度,主张调船返航。唯谢安从容镇定,吟啸自若,“众咸服其雅量”[1]2072。又,谢安与人围棋,在获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时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客问,亦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王子猷居山阴,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迭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徽之竟不顾主人,尽赏而去”。
特别是东晋末、刘宋初的“靖节先生”陶渊明更是以其旷达超远、宁静淡泊的气度向我们诠释了晋宋风流的真谛。早年时的陶渊明亦曾步入仕途并想建功立业,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他所处的时代政权迭变、战乱未绝、世风奢靡,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匡时济世是根本行不通的。面对黑暗、混乱的时局,不能建功立业,特别是当他发现这种仕途生涯有违素志,觉得虚伪奸诈的官场依然存在,这对于他渴求的精神自由、人格尊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束缚。于是他怅然慷慨,“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6]2287,毅然拂衣归田。陶渊明结束了他“心为形役”“委屈而累己”的生活,开始了躬耕南山的田园生活,极其洒脱地挣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并最终形成了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实现了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统一。
陶渊明的言行不拘泥于形式,严守节制和适度,不烦人不扰人,重在内心感悟。他弹无弦琴最能说明这一点。陶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1]2463朱光潜认为:“这故事所指示的,并不是一般人的‘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它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诗里,而且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7]的确,陶渊明追求“琴中趣”的弹琴,最具晋宋风流的韵味,正所谓心中有乐处处皆琴,又何必在乎有弦无弦,但其实这种境界已远远地超越了拘泥于形式的一代名流。王子猷爱竹一定要种竹的做法固然是晋宋风流人物本真的体现,殊不知心中有竹,处处皆竹的境界,更是大境界、大风流。
对生死的态度也反映了陶渊明旷达超远的气度风流。死生无常、人生易老。生死这对无法调和的永恒矛盾困扰着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陶渊明也不能免俗,同样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短促,并抱有人生虚幻的基本观念:“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陷入消极感叹人生的泥淖,而是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超脱中化解了生死之结,保持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运达观态度。他的心灵总能够从平凡艰苦的田园生活中品味出超然脱俗的意趣,在乱世中保持着一份清醒而理性的生活,虽然他也有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却没有陷入彷徨,更没有走向狂放不羁。在他曲折的人生经历之中,他不仅化解了魏晋知识分子的苦闷,而且让自己的人生体验形成了精神与现实的和谐统一并实践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的这种潇洒脱俗、旷达超远的风度,正是晋宋风流的鲜明特征,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晋宋风流的迷人魅力。
对南方山水的审美养成晋宋士人全新的生命意识。西晋时士人就开始把诗、酒、伎乐与山水游观相结合,但山水游乐只是作为他们的生活点缀,他们所能理解的人生的欢乐,主要是金碧辉煌,是锦绣歌钟,是豪华的物质享受,真正把点缀变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的,是东晋士人。南方优美的山水,使人目不暇接的风光,不能不使名士们顿生超脱出世之意。过去那不安的心灵,愤激的情感,完全可以消溶在这秀丽的自然景观之中。《世说新语·文学》篇曰:“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就是时人对东晋江南优美自然景观的真切感受。此时的士人已经有了强烈的山水审美意识,他们移情山水,把强烈的生命意识移植于山山水水之中。这一特点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兰亭集会。
由王羲之执笔写的《兰亭集序》记叙的就是士人们悠游山水的一次大集会,他们于江南的名山秀水中得到宁静的心境,暂时忘掉世俗的纷争,他们从山水的审美通向了对生命的体认,宇宙万物是那样的生生不息,无穷无尽,而人生是那样的短暂易逝。为此,感慨生命无常,探究生存
63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2010年)
方式便是其主要内涵。在序中他认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从而进一步深入地探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产生了一种珍惜时间、眷恋生活、热爱文明的思考。人的生死之变、生命终将消逝,人生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生命本身。生命本身的存在,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源。人性本能,是渴望生命永存,但生命的存在又无法超越自然造化的局限,终有一死,而面对宇宙无穷,生命又极其短暂。感悟到人生这种无奈的悲剧性的终极处境,眷恋生命的人怎能不情动于衷?王羲之就这样在《兰亭集序》完成了他对人生的深重悲慨,写出了古往今来的共同人性,既表达了他对生命悲剧性的终极体验,更表达了他对生命执著的眷恋。
由此可见,兰亭集会的士人们是一群从忧世走向优生的群体,因为政治环境的相对安定、自然环境的秀丽优美使得他们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忧愤,所以他们有的只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一种面对宇宙无穷、生命短暂的忧患。
(三)玄释合流与士人心态
玄学任自然、重情性之风发展到东晋已经不是西晋人那种为所欲为的放诞,而是任自然而有节。在庄子思想中加进了儒佛思想后,感情的满足和感情的节制便统一起来了。特别是此时的般若佛学开始大力借助于本土的玄学思想中国化,而时代的动乱、思想的大解放,玄学也需要般若空学的积极参与。于是,佛学和玄学的关系逐渐亲密化,并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许多名僧与名士交往日益亲密,佛理进入谈座,与玄学结合:如谢灵运常与当时高僧慧远交往。《高僧传慧远传》载:“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相见(慧远),肃然心服。”还有东晋时期的著名僧人支遁也与当时的许多名士如会稽王司马昱、谢安、王羲之、殷浩、孙绰、许询等多有交往。
名士与高僧交流,谈玄和悟空合一,玄佛互释在清谈中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玄释合流的趋势贯穿整个晋宋。而最能代表此时的玄学理论成就的,就是孝武帝时期张湛的《列子注》。张湛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的“至虚”说。他认为:“至无者,故能为万变之宗主也。”可见张湛是“无”本论者。张湛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郭象,郭象是归之于“有”,言“有”自生、自尔、自化,而张湛最终则还是“无”。他的《汤问篇》注:“谓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指言也”,“既谓之无,何处有外?既谓之尽,何得有中?所谓无无极无无尽,乃真极真尽矣。”他的意思是说,万物万形,虽忽尔自生,忽尔自化,但是其实都归之于虚无,“有”只是一种假象,而生化之本是无。
张湛的这一思想无疑受着佛学思想之影响。佛学思想从它说空的根本点上看,与玄学之言“无”有相通之处,因之它与玄学迅速合流。玄释合流其实正是晋宋之际士人心态的最好的理论表述。东晋士人从西晋士人的纵欲转向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则般若说空实在是最好的理论引导。虚静而逍遥,他们的宁静是潇洒风流的宁静,他们的逍遥是任性适情的逍遥。这就是玄释合流带给此时士人们最好的理论导向,也是他们追求的真谛。
综上所述,魏晋风度和晋宋风流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士人不同的文化取向。我们觉得魏晋风度就像是一个孩童一样,或慷慨赴义,或悲愤满怀,或傲诞不羁,他们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宣示了人格的独立,冲击着礼教的重重藩篱,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更多的悲愤和荒凉,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孤独,无奈与痛苦。而晋宋风流则像风流倜傥的少年一样,他们从精神到容止,从内心到行为都成熟了许多也风雅了许多,他们可以在仕途与隐逸之间优游容与,也可以在大自然秀丽山水中尽享一种审美的愉悦,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他们的气质与风神、洒脱与风流。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阮籍.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3.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沈约.宋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71.
(责任编辑:李金龙)
64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No.295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exploration for how China constructed legal society,the scholars found that law thought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legal society.Civilians with this thought would think about issues intuitively from the legal point of view when dealing with social problems.The basic feature of law thought is to think according to law and to have made a habit of thinking according to law.The training of law thought needs to,on the basis of the economy,to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and internal conscience and belief.
Key words:law thought;concept;feature;training
Cultural Root Exploration of Zhaoyun Fiesta
YANG Zi-yi
(Department of Chinese,Huizhou College,Huizhou,Guangdong516007)
Abstract:Su Shi’s concubine,Wang Zhaoyun,died of illness in Huizhou in the third year of Song Shaosheng,and was buried at Xichan Temple by the Huizhou Western Lake.Her tomb was renovated by many dynasties and worshipped for hundreds of years.Poems and essays in praise of her were so many that the secondary almost superseded the primary,producing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Zhaoyun Fiesta.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was deeply rooted,which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ashion of taking concubines in Lingnan Area.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local history record show that the culture of Lingnan taking concubines and the twisted notions and attitudes of keeping female virginity existing among the scholar bureaucrats were the soil on which the Zhaoyun fiesta was bred and grew.
Key words:Zhaoyun fiesta;taking concubines in Lingnan;notion of keeping female virginity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Areca Chewing Custom in Marriage Ceremonies in Lingnan Area:
Centered in Hakka Area in Eastern Guangdong
SONG De-jian
(Hakk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Guangdong514015)
Abstract:Through the lo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oral information from the anthropology investigations,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revailing times,the prevailing areas and the specific forms of the areca chewing custom in marriage ceremonies in the Hakka area of eastern Guangdong,and offer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sons of the popularity of this custom.
Key words:Lingnan;marriage;areca chewing custom;Hakka
Amateur Writing of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nd Wenyibao in17Year Period
(1949-1966)
LIU Xiao-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Xihua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Sichuan637002)
Abstract:Wenyibao(Literature and Art Newspaper),as an official governmental journal,played considerable role in the amateur writing of the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This article surveys how Wenyibao propelled and influenced the amateur writing from1949to 1966,and how it guided and normalized this sort of writing.The investigation of this literary phenomenon reveals how the state journals superseded the“tongren kanwu”(journals for one’s peers)in May Fourth Movement,and how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ame about and evolved.
Key words:Wenyibao;governmental journals;amateur writing of 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before Yan’an Zhengfeng and Ding Ling’s Revolutionary Artistic
Activities
HUANG Dan-luan
(Shantou Radio and TV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515041)
Abstract:In the earlier period of Yan’an,Ding Ling’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have two themes:anti-Japanese salv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She was able to be engaged in the revolutionary artistic activities based on her own revolutionary and artistic ideas,which wa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relatively free before Yan’an Zhengfeng,(Yan’an Rectification).Meanwhile, what cannot be neglected,the awareness of struggle and the revolutionary complex are the knot of Ding Ling research.Only with a command of the formulation tracks of Ding Ling’s spiritual complex can we understand her artistic sense of“for the sake of life”and her complicated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Key words:Ding Ling;artistic policies in the earlier Yan’an period;Ding Ling’s artistic activities
Differences Between Wei-Jin Grace and Jin-Song Style
JIA Yuan-yuan,ZHANG Hui-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515063)
Abstract:Wei-Jin Grace and Jin-Song Style represented different senses of values in different periods.Wei-Jin people concealed enormous desperateness and sadness behind their unrestraint while Jin-Song people’s style of openness and naturalness shows the truth of life and freedom of spirituality.
Key words:Wei-Jin grace;Jin-Song style;scholars;politics;metaphysics
On Attainment and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Civil Personality:Private Rights Function Perspective
KANG Tian-xio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Chongqing400031)
Abstract: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ket formulation of China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Chinese civil subject system is incessantly changing and developing.The traditional civil subjec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on the abstract personality theory and assumed the form of duality,neglecting the state’s marketing function,thus being eliminated from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ivil subject system.With the decline of nationalism,individualism prospered,which made the state acquire the status of the civil subject while restricting it to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
陶渊明诗与隐逸文化
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东晋至南朝结束应当看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文化发展的第四阶段,其代表人物非陶渊明莫属。他生活在一个“乱”与“篡”的时代,抱负和理想尽皆付诸东流。陶渊明不断出仕,即又旋即辞官,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不适应。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会郡遣都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陶渊明屡次去职的根本原因,而他的《归去来兮辞》更从生活情调的深处说出了这一点: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心为形役”是他最大的精神痛苦,他决心要摆脱自身躯体及物质的役使,获得心灵的自由高蹈。他在历经了官场的龌龊和束缚之后,终于迷途知返,把“良辰孤往”、“植杖耘耜”、“东皋舒啸”、“清流赋诗”看成自己的“天命”,因而从心灵的深处释放了政治上的失落感,“乘化归尽”,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这位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大诗人本人就是一大隐士,对于隐逸,他有着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其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一)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 既不是冷漠的避世,也不是愤不释怀的怨怒,而是摆脱樊笼后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并将这种独立和自由积极地指向对无道现实的批判和矫正。陶渊明的这种独立、自由、深情而又刚劲的生命情调是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由两汉经西晋终于在陶渊明这里找到了较为确切的定位:怀道而隐,以隐彰道。 魏晋名士和隐士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肯定了“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然而,鲁迅先生也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至于他们(孔融、嵇康等)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过执得多了。”言外之意是批评孔融、嵇康坚持礼教,而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处的具有永恒合理性的文化理想,如果连这一点都否定了,那我们就更失去了维系精神的力量,鲁迅所说的魏晋时期的“乱”与“篡”必将愈演愈烈,整个民族也许会就此毁灭。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与“使气”便是直抒胸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应当说,林泉之隐大都是些胸怀大志甚至是“志深轩冕”的人。他们生逢无道之世,文化的发展把他们推向了怀疑君主专制、实现文化理想的阶段,所以他们处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的尴尬境地,他们的心灵忍受着撕裂磨啮的巨大痛苦,即使平和如陶渊明,也还是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足见其人格的分裂。所以说,魏晋士人欲做直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他们在这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中,如病蚌生珠一样,创造出了丰富的文化价值,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能量。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世号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
魏晋风流的内涵及其意义
魏晋风流: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来源: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
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身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美学命题: 王弼:得意忘象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1)言、意、象。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魏晋风流的内涵及其意义
魏晋风流的内涵及其意义 所谓“魏晋风度”,基本上是杜人所倡导和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唱的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精神自由的提升,对吃药、喝酒、聊天的怪异的精神深度。魏晋风度因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自古以来,对魏晋风度的评价数不胜数。其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魏晋风度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其意义一直存在争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魏晋风度的价值。作者结合自己的理解和体会,阐述了自己对“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的看法。在我国历史上,魏晋风度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魏晋风度产生于魏晋末年,一直延续到晋朝。“魏晋风度”实际上是对魏晋名人生活的高度概括。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主要指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所具有的清俊通脱、率真任诞的行为风格。在魏晋时期,名士们普通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纵情山水、服药饮酒。由于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社会环境复杂,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其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其人格行为思想等又非常的不拘礼节、不滞于物、风流潇洒自信。士人们颇喜雅集,大多数独立特行。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丝毫不拘礼节,经常积聚于竹林中喝酒纵歌,洒脱倜傥,清静无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来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主要指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所具有的清俊通脱、率真任诞的行
为风格。在魏晋时期,名士们普通崇尚的生活方式就是纵情山水、服药饮酒。由于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社会环境复杂,新兴门阀士大夫阶层有着极其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其人格行为思想等又非常的不拘礼节、不滞于物、风流潇洒自信。士人们颇喜雅集,大多数独立特行。其中的代表人物为“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丝毫不拘礼节,经常积聚于竹林中喝酒纵歌,洒脱倜傥,清静无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来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的精神所在和时代特征就是遵乎达生、轻蔑名利,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为风流气度和萧散怀抱。这两者的有效结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性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不仅在当时的魏晋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士文化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在于它将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发展趋势。魏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社会环境险恶,政治斗争惨烈,这些让魏晋名士感到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如履薄冰。这样的背景下,名士面对生死选择经常有忧生之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魏晋名士之间惺惺相惜,无论是在人生态度还是处事方式上面,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趋同性。而且,魏晋名士的人格精神在这个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一致。就像刘师培先生指出的一样:“西晋之士,非法其文,唯法其行。用是清谈而外,别为放达”等。从某种程度上说,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具体走向以及相应的发展趋势,均
1.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李泽厚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终学的崩溃.烦琐、汗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文,完成1—3题 陶渊明——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和艺术化人生的具体表现。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的“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而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晋风度的文化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末年,延续至晋。“晋风度”是对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涵。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晋玄学和晋风度。晋风度是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晋风度是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晋风度与晋玄学 谈及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