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主义
在摸爬滚打中成长——新写实主义所描绘之现实

在摸爬滚打中成长——新写实小说之现实在现实主义宏大叙事所蕴含理想价值消弭之后,新的生存困境使社会目光投注到鸡毛蒜皮的日常之中,新写实小说所记录下的一段段现实人生可以说是时代进程之中的微观脉动。
从现在来看新写实,却可以将这些微观的血肉拼接成一整幅中国社会在摸爬滚打的时代中的宏大叙事图景。
新写实小说的三位代表作家——刘震云、池莉、方方,他们的创作所拼凑成的整体图景恰恰可以覆盖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层次:刘震云《官场》《单位》《一地鸡毛》写微观下的政治人生活,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写微观下的工业、知识人生活,方方《风景》《桃花灿烂》《出门寻死》等写微观下的底层人生活。
《单位》《一地鸡毛》是一对姊妹篇,《官场》可以说是它们的上位篇。
《官场》里是地委若干人及所属各县县委的暗流涌动,这是在人情权力金钱交织影响之下的官场故事,《单位》里是北京某部某局某处各色人等勾心斗角谋职谋权谋生活的单位情景,《一地鸡毛》是《单位》里那位“小林”与妻子两位公务员小家庭的生活困窘。
这些故事写的是大小“官员”的琐碎。
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地鸡毛》,小林和妻子的一地鸡毛般的琐屑生活。
小林在《单位》中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单位工作时还是一个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年轻人,后来有了家庭,逐渐感受到了生活的责任压力才转变态度以求上进,这个过程也是极其不易的。
在《一地鸡毛》里“小林”受到的更是四面夹击,工作晋升无望、妻子调换单位抱怨不断、老家来人尽受白眼、女儿入园的困难重重……甚至购买冬储大白菜也是一道左右不得的难题。
这些生活琐屑是极度庸俗而又逃避不得的,在这样的生活之中损耗的是对生活的信心与追求,小林夫妇一对大学生也曾经有过纯真与诗意的日子,但是无奈他们的时代是一个饿死诗人不偿命的时代,他们也无力追求“诗和远方”。
小林不再和“狗屁无病呻吟的诗”有一丝瓜葛,小林妻子也“从诗意的少女变成偷水的妇女”。
这庸俗生活明明白白展现了“诗意的丧失”。
新写实主义小说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

新写实主义小说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区别—以《烦恼人生》和《平凡的人生》为例历史文化学院章驰 2010213331摘要: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病的暴露,人们浪漫热情和“理想王国”的幻想破灭,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这种尖锐负责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
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表现出作家们对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
而新写实主义文学是20事迹90年代后国内文学界出现的新现象。
它强调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绝少作家的情感投入和主观想象,反对人为地粉饰和拔高现实。
本片论文旨在以池莉的《烦恼人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为例做比较,从比较中分析两种文学思潮对于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区别。
关键词:新写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比较人物形象正文:一.新写实主义小说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概述新写实主义是开端于80年代后期的一种小说思潮,它对应于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大写的“人”解体,文学中终极理想的消失,政治热情降温,个体生存艰难复杂的现实,以及1987年之后先锋小说遭遇冷落的艺术现状,是对于现实和小说的双重反映。
新写实主义文学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市民形象,反应百姓的日常生活,侧重庸常。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病的暴露,由于人们浪漫热情和“理想王国”的幻想破灭,于是形成了一种冷静务实的社会心理。
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这种尖锐负责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
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虽然也是小人物,但是往往以小见大,从小人物个人的命运轨迹可以看出作家对于人物所处的阶层的关怀,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反思和思考,侧重于崇高。
新写实“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1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是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新写实”的产生背景及创作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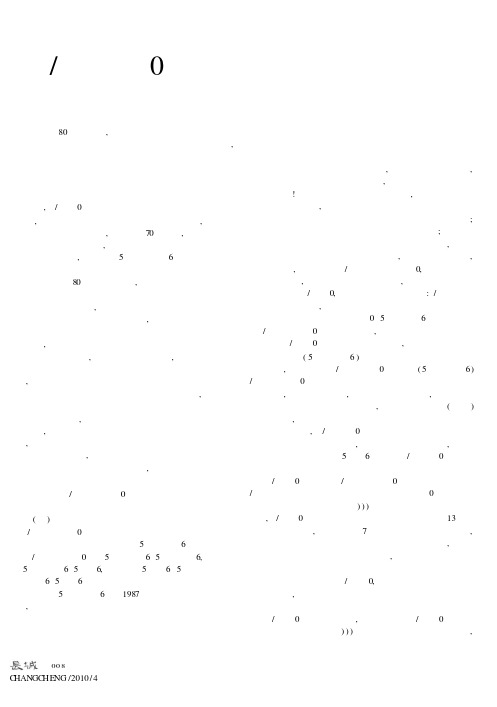
长城论坛N G NG /新写实0的产生背景及创作分期贺永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写实写作手法开始勃兴于文坛。
新写实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社会人生,运用琐碎的手笔记录芸芸众生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
一、新写实主义顺应各方面的要求而产生首先,/文革0十年及前十七年是浪漫主义在中国风行的时期,但那时浪漫主义作品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没有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于是,上世纪70年代末,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登陆了,当时文坛上也发表了很多呼唤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产生了5天云山传奇6等一系列作品。
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在困难的境遇中主人公如何的英勇崇高。
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情调开始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在作家思想中扎根。
当现实主义被作家真正地嚼烂、消化、吸收后,新的突破便产生了。
作家和读者的视线被引入了平庸而琐碎的现实生活,凡夫俗子浑浑噩噩的生活开始成为作品的主题。
于是新写实主义传播开来。
其次,新写实主义的出现顺应了人民大众世俗化的要求。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广大读者的目光不再像刚解放时过多地看重崇高的人品、高尚的道德修养,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与他们切身相关的世俗生活。
他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经济物质生活和世俗精神生活,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
因此也需要一种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文学产生,新写实便应时而生了。
最后,先锋小说等一批超前实验小说放弃了广大的通俗读者,仅仅成为专家们研究文学理论的范例文本。
于是普通的读者也放弃了他们,而去追求一种贴近平民百姓世俗生活的文学。
新写实有了广阔的读者市场,发展更加迅速了。
二、/新写实小说0创作的两个时期(一)前期创作/新写实小说0的前期多数作品着重表现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
代表作如池莉的5烦恼人生6及与之一起构成/人生三部曲0的5不谈爱情65太阳出世6,刘震云的5一地鸡毛65官场6,方方的5风景65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65黑洞6等。
池莉的5烦恼人生6在1987年发表时曾引起极大的反响,小说描述了一名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琐碎生活。
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是当代一个重要文艺理论,从总体上讲,它还是属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大范畴,但相比传统的现实主义无疑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特别是在题材的选择和对“现实生活”的处理方式上,其创作特点则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它以写实为主要特征,并特别注意现实生活还原形态,真诚直面现实和人生,放逐理想,解构崇高。
在题材上注重对凡俗生活的表现,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与操劳庸碌的小人物成为作品的中心。
电影新写实主义又叫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电影运动,其特点在关怀人类对抗非人社会力的奋斗,以非职业演员在外景拍摄,从头至尾都以尖锐的写实主义来表达。
主要代表人物有罗贝多.罗赛里尼、狄西嘉、鲁奇诺.维斯康堤等。
这类的电影大主题大都围绕在大战前后,意大利的本土问题,主张以冷静的写实手法呈现中下阶层的生活。
在形式上,大部份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运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与讲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相较于战前的封闭与伪装,新写实主义电影反而比较像纪录片,带有不加粉饰的真实感。
不过新写实主义电影在国外获得较多的注意,在意大利本土反而没有什么特别反应,1950年代后,国内的诸多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复苏已获抒解,加上主管当局的有意消弭,新写实主义的热潮于是慢慢消退。
特点“非典”新闻是故事的源泉高群书曾说:“我的影片基本都是一个新闻事件来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的。
”其实,以新闻事件来作为故事背景的影片数不胜数,然而高群书的新闻事件却都是非典型的新闻事件。
如其以前拍摄的《金豌豆》、《中国大案录》所选的事件都是一些对国家历史影响不大的事件,包括《东京审判》。
这些新闻事件虽不是当时的代表性历史事件,但是这些事件、这些非典型性新闻却蕴含着很深的内容在其中。
因此,与《三峡好人》的大故事背景相比,高群书从一个并不起眼但很有意思的故事开始下刀,这样的角度,最能够贴近生活。
有个性的角色高群书所选的事件不仅很有特点,而其中的人物也很具个性,这是“新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的一大不同。
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南帆罗兰·巴特曾经感叹地说:“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
”[1]可是,提出“叙事话语”这样的概念却是不久的事情。
此前,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叙事话语的存在--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的话语类型,叙事意味着话语对于实在的一种简化,一种排列,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解释。
他们更习惯于省略“叙事”环节,无视叙事话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欣然地将叙事的内容作为实在本身予以接受。
这是叙事话语所产生的幻觉。
叙事学的出现破坏了这种幻觉。
通过叙事学,人们从叙事话语背后看到了幻觉赖以产生的一系列精密框架,看到种种叙事成规如何通过种种文本互相传递。
这些叙事框架与叙事成规不仅意味着叙事话语的运作支撑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它们体现的叙事知识同时还出示了--用利奥塔的话说--社会的“法定标准”。
利奥塔指出,许多流行故事不外讲述了主人公事业的成败荣辱。
然而,“这些成败的教训,不但使社会制度合法化[也就是所谓的‘具有神话功能’],同时也表现主人公[或成或败]是如何在既定制度之中适应自己,并形成正反两种生活模式。
从一方面看,各种叙事性的说法,是源自社会,但换一角度来看,这些说法又让社会自身去界定社会的法定标准,然后再依这些标准去评价,哪些巳然在社会中实践了的说法,哪些是可在社会中实践的说法。
”[2]这些发现意味着,叙事学同样将汇入科学主义肢解乃至破除神话的行列。
当然,这些发现仍然遭受到许多有意无意的抵制。
人们必须估计到,叙事话语所产生的幻觉具有顽强的惯性;许多时候,幻觉是一种迷人的安慰,哪怕这种安慰已经丧失了令人信赖的基础。
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之中,人们可能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冲突:一方面是对于叙事话语的幻觉深为迷恋,另一方面是对于叙事话语的幻觉进行种种揭示与解构--这样的冲突产生在新写实主义小说之中。
一“新写实主义”之称的大规模流通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无论是嘉许还是否弃,人们都意识到这个概念的规格与份量。
基础写作关于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写作,是一种平民化的写作,也称平民美学。
代表作如《手机》《中国式离婚》、《蜗居》等,新写实主义的立足点是当今社会,源于作家对社会生活落差的敏感度。
新写实主义小说开端于2 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中期仍有影响,它崛起于小说界相对疲软的转型时期,承担着过渡性角色。
刘震云《一地鸡毛》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
这部作品描写的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描写小林的一家生活中的琐碎的生活,把小林的一家的生活面貌,运用细致入微的描写方式表现出来,在刘震云的笔下,生活也非由平庸、琐碎的事构成的。
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组成了生活的全部,什么奋斗的精神,理想的愿望,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已慢慢磨化,甚至消失,从整个作品画面来看,有点乏味、世俗之感。
这便突出了其写作特点:一是写平凡人生活的艰辛;二是强调对客观描写的真实,在叙事原则上,描写所谓的生活的“原生态”时。
“新写实'把它的创作视线与叙事目标不仅移在普通人的身上,而且更热衷于去描写这些普通人的生存处和状态,写精神、物质的贫乏,也写世俗的沉落,也写人际间的挤压,写人在这些环境困扰下的焦躁与无奈、变异与扭曲。
作者对此所做的描写大多保持一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态度,显示出局外人的超脱,不热衷于去做判断,做情感上的宣泄。
作者们对于不合理现象的激愤和对于人的正常发展的期望往往潜藏于故事的深处或反讽的手法,让读者去领悟和体味。
意义新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次回归。
但是和历史上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它淡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中那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力求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关注“原生态”的生活,这样对其他的新现实主义创作及个人化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这种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迎合大众文化及其趣味的冻结,但在深层次上,也包含了对当代文学创作“反映现实”方式的反思。
它打开了一个关注当代现实生存状况的新的写作空间。
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新写实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并较为直接地开启课后来的新生代写作。
新写实
新写实小说的缘起、变化及意义分析(一)新写实小说的缘起“新写实主义”是开端于80年代后期的一种小说思潮,它对应于8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社会大会的“人”的解体,文学中的终极理想消失、政治热情降温、个体生存艰难等复杂的现实,以及1987年之后先锋小说遭遇冷落的艺术现状,是对于现实和小说的双重反应。
正如《钟山》1989年第2期“新写实小说大联盟、卷首语”中所说:新写实“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它们“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人生。
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在这个大旗的号召下,80年代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叶兆言等作家推出了一大批新写实小说,并形成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和热点。
80年代中后期发端“新写实小说”,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其创作方法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它减褪了过去传统的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以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强烈的历史的意识,深刻的哲学意识,追求一种更为丰富的博大的文学境界,作者情感冷静而自信,零度情感介入,阅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创作,作家——文本——读者共同展示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作用。
“新写实”三个字从此成为众多理论者经常提及的一个名词。
对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有人曾经概括为五个方面:1、粗糙朴素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
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
3、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
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
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
5、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景。
中国新写实主义诗歌作品展示
中国新写实主义诗歌作品展示
以下是一些中国新写实主义诗歌作品:
1. 余光中的《乡愁》: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语言朴实自然,情感真挚动人。
2. 舒婷的《致橡树》:这首诗以树为喻,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语言简练明快,意境深远。
3.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语言清新自然,意境开阔。
4. 顾城的《一代人》:这首诗以一代人的视角,描绘了历史的变迁和人生的短暂,语言凝练有力,意境深刻。
5. 北岛的《回答》: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和追求,语言简练明快,富有感染力。
这些作品都展现了中国新写实主义诗歌的特点,即注重现实生活的描绘和表达,追求真实、自然、朴素的诗歌语言和意境,以及关注社会问题和人类命运等主题。
波普艺术
沃霍尔的绘画中常出现 涂污的报纸网纹、油墨不朽 的版面、套印不准的粗糙影 像,让人像看电视一闪尔过 ,而不是欣赏绘画般仔细观 看。
利希滕斯坦
利希滕斯坦是以画卡通式的图像而著名的。与安 迪· 沃霍尔一样,他不仅对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以及现代 商品化社会的粗俗形象偏爱有加,而且,还喜欢以一种不 带个性的、中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形象。对于它们,他 既不攻击批评,也不吹捧美化,只是简简单单地陈述—— 这就是我们身临其境的城市,这就是那些组成了我们生活 的图像和象征符号。 1961年他开始将那最为平淡无奇的连环漫画中的形象 ,放到他的大幅的画面上去,甚至把那廉价彩印工艺中的 网点,都不厌其烦地复制出来。就画面的讲究和制作严谨 而言,其画风显得十分古典。
波普艺术的表现方式瓦解了现代主义的紧张感和严 肃感,为享乐主义敞开了后门。因此,各种各样奇怪的产品 造型、各种各样特殊的表面装饰、非常特别的图案设计都让 进入丰裕社会时代的人们大吃一惊、眼前一亮。
波普风格在不同 的国家有不同的形 式,如美国电话公 司就采用了美国最 流行的米老鼠形象 来设计电话机,意 大利的波普设计则 体现出软雕塑的特 点,如把沙发设计 成嘴唇状,或做成 一只大手套的样式。
《可口可乐瓶子》
沃霍尔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 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 谈来填满它。” 实际上,安迪· 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 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 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沃霍尔的作品,突出 一种嘲讽与冷静。他描 绘了简单清楚而反复出 现的东西,这些都是现 代社会中最令我们记得 的形象符号。
波普艺术是当今较底层艺术市场的前身。波普艺术家大量复制印刷的 艺术品造成了相当多评论。早期某些波普艺术家力争博物馆典藏或赞助的 机会。并使用很多廉价颜料创作,作品不久之后就无法保存。这也引起一 些争议。1960年代,波普艺术的影响力量开始在英国和美国流传,造就了 许多当代的艺术家。后期的波普艺术几乎都在探讨美国的大众文化。 波普艺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对于流行时尚有相当特别而且长久的影响 力。不少服装设计,平面设计师都直接或间接的从波普艺术中取得或剽窃 灵感。 波普艺术其创作特征是直接借用产生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进而从 中升华出艺术的主题。它的出现不但破坏了艺术一向遵循的高雅与低俗之 分,还使艺术创作的走向发生了质变化
论新写实主义与现代传统主义小说的区别
论新写实主义与现代传统主义小说的区别The manuscript was revised on the evening of 2021试论新写实主义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以池莉的小说为例摘要:在1989年的《文艺报》上出现了一条《新写实小说在文坛兴起》的消息, 消息中说: “这些小说以它直视现实、人生的写实特征, 以及探索人类生存状态的总体精神, 表现出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新写实小说吸收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精华, 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框架, 保留了传统小说的基本描写方法, 但更贴近生活, 更注重显现生活的原色。
”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人物,池莉的小说总是能给读者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
这种感受是触手可及的,是实实在在的,总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去体会生活的平常、淡静、烦恼,却又浓郁的温情。
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相比,新写实主义小说吸收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长处,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框架,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描写方法,但更贴近生活,更具生活的原始色彩。
在本文中我将从小说的内容、叙事、情节安排等三个方面来谈论新写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
关键词:新写实现实主义小说池莉引言新写实主义小说其实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的流派, 但又不完全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而是在传统( 经典)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的对峙中, 采取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和再现生活的方法, 同时又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
故此,新写实主义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管是在小说内容、叙事手法以及小说的构架等方面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区别和联系。
一小说内容方面的差别有人认为,新写实主义小说是由传统现实主义注重对生活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还原到对现实生活的纯客观描写,即就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忠实再现。
其实不尽然,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作者往往也会通过对这些生活小细节一丝不落的描写刻画来表达他们自身对于现实生活的某些情感和态度,或者是由此来透视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存观和生活状态等等。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南帆罗兰·巴特曾经感叹地说:“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
”[1]可是,提出“叙事话语”这样的概念却是不久的事情。
此前,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叙事话语的存在--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的话语类型,叙事意味着话语对于实在的一种简化,一种排列,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解释。
他们更习惯于省略“叙事”环节,无视叙事话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欣然地将叙事的内容作为实在本身予以接受。
这是叙事话语所产生的幻觉。
叙事学的出现破坏了这种幻觉。
通过叙事学,人们从叙事话语背后看到了幻觉赖以产生的一系列精密框架,看到种种叙事成规如何通过种种文本互相传递。
这些叙事框架与叙事成规不仅意味着叙事话语的运作支撑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它们体现的叙事知识同时还出示了--用利奥塔的话说--社会的“法定标准”。
利奥塔指出,许多流行故事不外讲述了主人公事业的成败荣辱。
然而,“这些成败的教训,不但使社会制度合法化[也就是所谓的…具有神话功能‟],同时也表现主人公[或成或败]是如何在既定制度之中适应自己,并形成正反两种生活模式。
从一方面看,各种叙事性的说法,是源自社会,但换一角度来看,这些说法又让社会自身去界定社会的法定标准,然后再依这些标准去评价,哪些巳然在社会中实践了的说法,哪些是可在社会中实践的说法。
”[2]这些发现意味着,叙事学同样将汇入科学主义肢解乃至破除神话的行列。
当然,这些发现仍然遭受到许多有意无意的抵制。
人们必须估计到,叙事话语所产生的幻觉具有顽强的惯性;许多时候,幻觉是一种迷人的安慰,哪怕这种安慰已经丧失了令人信赖的基础。
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之中,人们可能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冲突:一方面是对于叙事话语的幻觉深为迷恋,另一方面是对于叙事话语的幻觉进行种种揭示与解构--这样的冲突产生在新写实主义小说之中。
一“新写实主义”之称的大规模流通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无论是嘉许还是否弃,人们都意识到这个概念的规格与份量。
不少批评家认为,“新写实主义”是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面旗帜;它足以与后两者相提并论,从而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内部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无论如何,新写实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事实。
大批引人瞩目的小说簇拥于这个概念周围,显示出声势赫赫的阵容;许多富有实力的作家正在一个新的美学口号之下重新集结,踊跃欲试;批评家围绕着这批小说作出了兴致勃勃的阐释,从而使这个文学事实拥有了相应的理论深度。
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文学刊物。
不止一个刊物为新写实主义小说辟出专栏,或者刊载专题论文。
在这个意义上,新写实主义的提出包含了多方面的成功:它是一次别具一格的小说聚会,一个精明的办刊策略,一个审时度势之后文学话题的设计,一种机智的广告术,一种美学偶象的塑造,一次文学批评的力比多渲泄,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成功已经足以在当代文学史上记载了醒目的一笔。
不言而喻,诸方面成功之中,小说本身的成功最为重要。
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距离,目前还很难断言能否从这批小说之中涌现经典之作;预言这批小说具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远大前途,这更象批评家的善良祝愿。
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至少可以毫不胆怯地宣称,新写实主义的名义之下已经出现一批重要作品--重要意味着公众舆论的持续注意;相当一段时间内,一些新写实主义的小说可能作为中国九十年代文学的某种代表而得到反复的谈论。
虽然如此,我仍然愿意坦率地承认,“新写实主义”这个概念的风行使我深感意外。
在我看来,“新写实主义”显露出过多逻辑上的破绽。
尽管这个概念暗示出一个新的文学事实,但是,理论上的软弱使之无力解释这个文学事实。
换言之,相对于上述诸方面的成功,这个概念的理论阐释却留下许多难堪的纰漏。
显然,人们最易于察觉到新写实主义的大而无当--“无边的现实主义”所造成的混淆开始重演。
为了招兵买马,壮大声势,批评家兴高采烈地将各路作家圈定于新写实主义的称谓之下,他们未曾意识到滥用概念所包含的理论危险。
目前为止,新写实主义已经成为一张过份廉价的入场券,许多个性迥异的作家都轻而易举地得到这张入场券。
一些批评家将刘震云与余华、格非或者王朔共同合并于新写实主义之下,如此粗糙的概括很难赢得人们的信任。
事实上,即使象朱苏进这样的作家--《绝望中诞生》曾在《钟山》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中获奖--也很难冠以“新写实主义”。
从《绝望中诞生》、《欲飞》至《金色叶片》、《祭奠星座》,朱苏进小说内含的激烈搏动恰恰是许多新写实主义作家所匮乏的。
概念的含混首先体现为内涵与外延的含混。
这使新写实主义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明晰的鉴别能力。
它无法作为一个严格的理论尺度衡定作品;相反,它只能悬空于作品上方,游移不定;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新写实主义时常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概念的规定性,通过迁就作品的个性而维持自身的空洞存在。
因此,叶兆言与苏童--不少人心目中的新写实主义骁将--曾经毫不讳言地宣称,“新写实主义”不过是批评家活跃文学气氛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玩艺,作家必须保持警觉,不为所动。
[3]换言之,这并非一个十足的理论概念,它的作用更象一杯开胃的佐餐饮料。
新写实主义所遇到的另一个麻烦来自它的理论立足点。
新写实主义的概念由一个偏正词组构成:“新”与“写实主义”。
众所周知,“写实主义”亦即“现实主义”--它们是“realism”的两种译法。
可以看出,这个偏正词组力图呈现出两方面的涵义:新写实主义一方面与现实主义保持了密切的血缘联系,另一方面又对现实主义加以修正。
然而,如同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至今依然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
[4]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新写实主义”的定义扑了个空。
在现实主义的涵义统一之前,新写实主义的屋下架屋不过是徒增纷乱而已。
当然,为了阐释新写实主义增添了什么,不少批评家都曾事先设定他们心目中的传统现实主义图景。
但是,一些时候,这种努力难免类似堂?吉诃德对于风车的攻击。
批评家所贬抑的“现实主义”带有不同程度的虚构,他们概括的某些内容无法得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的验证。
另一方面,出于同样的原因,批评家所形容的新写实主义很可能就是人们所习惯的传统现实主义。
事实上,新写实主义的诸多特征已经或显或隐地包容于传统现实主义之内。
鉴于这种状况,有些批评家们仍然谨慎地将新写实主义归诸现实主义范畴之下[5];而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方方则干脆地说,将“新写实主义说成是批判现实主义也行”。
[6]批评家开始正面阐释新写实主义的时候,人们可能发现更多的问题。
不少批评家喜欢重复这一点:新写实主义展现了现实的“原生态”,将“原色原汁原味”和盘端出,并且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
他们竭力论证说,无论是现实主义抑或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叙事均有意遮蔽了现实的本真面貌;新写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功绩恰恰是破除叙事的修饰与隔阂,从而让生活无比真实地裸露在人们面前。
然而,不论批评家阐述得多么生动,这些观点的破绽仍旧一目了然:批评家忘了给予叙事话语一个恰当的位置。
时至如今,叙事学已经作为一个醒目的理论背景而存在,因此,无视叙事的意义显然是一个刺眼的疏忽。
叙事学包含了大量精致的文本分析。
从叙述时间、聚焦、叙述层到语态、行动元、复调,诸如此类的考察剔精抉微,甚至不无琐碎。
这种状况往往掩盖了叙事学所具有的揭露性功能。
事实上,如同罗兰?巴特反复阐明的那样,叙事学同时还揭开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作家所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中性的,公正无私的;种种权势与意识形态隐蔽地寄生于叙事话语内部,作为语言体系的规则而形成一种专横,一种独断,一种语言的暴力。
巴特发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已经在写作的字词空间内部消失;字词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
巴特曾经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过现实主义。
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力图造成一个错觉:人们可以避免话语的干预体察现实。
现实主义试图隐蔽叙事话语的相对性与社会性,它把叙事话语装扮成天然的、与对象合二而一的符号;现实主义不象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那样歪曲世界,它的唯一任务仅仅是展现事实的“真面目”。
巴特特地指明,这象是一个语言设置的圈套。
其实,语言本身是有“重量”的。
语言结构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地平线,它并非世界本身。
如果人们将叙事话语视为天然的透明符号,那么,人们必然将小说所呈现的世界当成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天然存在--这无疑是一种巧妙的伪饰。
新写实主义显然重蹈旧辙。
一些作家与批评家联合通告,新写实主义已经剔净意识形态的所有指令。
新写实主义在字面涵义的解释上即巳强调了这一点。
然而,只要叙事话语存在,语言的权势就不可祛除。
新写实主义完全有权利强调某种特殊的叙事方式,但批评家却转身向舆论许诺某种不可能的绝对真实--这暗示了新写实主义理论所可能面临的歧途。
二阐释新写实主义的时候,“还原”是一个相当时髦的词语。
在这里,人们无须纠缠“还原”在现象学中的多重涵义。
许多批评家不过是从字面涵义上挪用这个词语,表明新写实主义解除叙事话语的蒙蔽而接触现实的本真。
于可训解释道:“所谓…还原‟,见之于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不去精心地构造完整的情节和生活故事,以避免将生活过份戏剧化,而是遵从生活的原生态,通过大量琐屑的、平凡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生活事件表达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7]如果将“还原”视为新写实主义的新意所在,那么,这显然是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而言。
新写实主义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制作颇有微词。
简言之,典型的制作可以理解为一种聚焦。
一旦作家将焦点凝缩到某个人物身上,使之高度清晰、放大,那么,周围的人物背景相对虚化、模糊乃至弃而不取。
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情节叙述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作品往往因为过于明显的剪裁痕迹而令人生疑。
韦勒克曾经指出,传统现实主义同样是一种艺术惯例,它同样存在“不自然”的一面。
[8]毫无疑问,新写实主义可以挑选另一种它所满意的艺术惯例予以取代。
然而,恰恰在这时,新写实主义冒失地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理想:“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
”换言之,新写实主义决心撤消所有碍手碍脚的叙事惯例,从而让现实毫无修饰地天然浮现。
王干毫不犹豫地说:“作家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一片透明,不带丝毫偏见,不渗入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只原原本本把生活具象原始地还原出来,以达到一种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现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实。
”[9]与此相仿,另一些批评家则是简约地将这种“对象自己呈现”称之为“叙述现象化”。
[10]他们也许未曾意识到,这种超级叙事并不可能出现。
尽管作家发誓将他们的叙事提炼得如同空气一样透明,但是,叙事话语的本身性质却无时不刻地毁坏这样的理想。
巴特说过,“语言按照其结构本身包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异化关系”;[11]按照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的考察,语言是人们经验事物的最初线索,同时又是人们感觉、认识、想象赖以定型的形式;换言之,语言已经全面操纵了人们与世界相互接近的方式。
